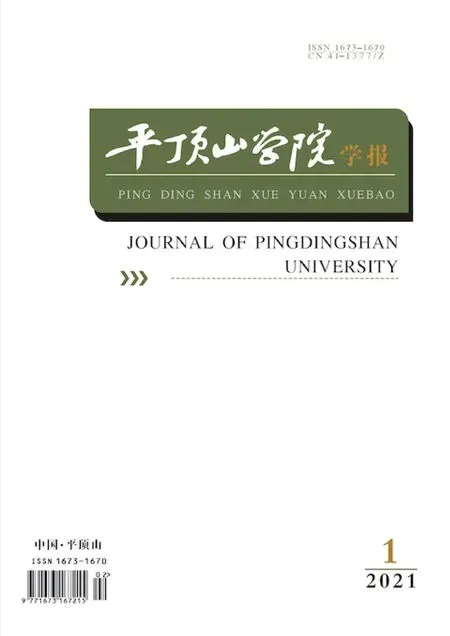居住权与抵押权之顺位冲突
马明明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难题所提出的奋斗目标,随后党的十九大对保障住房又提出了新要求。在民法典草案经过审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民法典物权编两次草案审议稿都对居住权制度进行了规定[1]。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在物权编增加规定“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明确在未有约定的情况下,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其设立方式为合同约定或者根据遗嘱,登记是居住权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经登记后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并非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居住权制度的确立对于老人养老、保障离婚时处于弱势的妇女权利以及对保姆等特殊人群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以上困难人群的住房问题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是我国追求法制健全道路上的一个重大亮点。虽然居住权制度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罗马法的人役权制度,我国的居住权制度也先后经历了十几年的讨论才最终确立,但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此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讨论的焦点是居住权制度确立的必要性、居住权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居住权制度的域外立法模式借鉴等方面,对于居住权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尤其是当作为物权的居住权与同为物权的抵押权产生冲突时实现顺位的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法律实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新制度的产生,而是要以该制度有效地回应现实生活的需求。所以,居住权制度的产生并非仅满足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上更加周延和立法手段看起来更加高端的表面功夫的需要,其本质目的在于对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回应。对新诞生的居住权在未来还需要根据实践和人民的需求进行更多的配套规定,才能在保障人民“居有其屋”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物的其他效能。
一、居住权与抵押权的顺位冲突问题之缘起
(一)问题的提出
“物尽其用”与“保障交易安全”是物权法的最基本的立法理念。所有权是一种最为完全的物权,任何人都可对自己所有的特定物进行全面支配和排除一切人对于其行使权利的干涉。世界各国所有权立法的初衷都是在保证所有权人的权利不被侵害的前提下,更大限度的发挥该物的其他效能。因此,在立法层面,多采财产与权利分离的立法技术,允许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的物进行抵押、质押、出租等,从而实现对特定物的最大化利用,杜绝物因闲置无法流转而造成的效能浪费。《民法典》对于物权编编撰的初衷就是在所有权保护的基础上,规范各种财产与权利相分离的行为,鼓励交易,打造所有权保护与充分发挥财产效用的双赢局面。
居住权与抵押权就是在不移转物的所有权的前提下,对特定物的其他功能进行的利用。就性质上而言,居住权与抵押权均属于物权。就发挥的功能而言,居住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同时也是种利他权利,是所有权人提供自己的房屋供他人无偿地占有、使用,主要发挥的是满足特殊群体生存保障的功能。而抵押权则是一种担保物权,在效力上从属于主债权,不得单独转让。《民法典》第411条规定了抵押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序,但是随着居住权制度的确立,当同一不动产上居住权和抵押权并存时,哪种权利应优先实现引发了法学界的讨论。但遗憾的是,此次《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分编仅以6条法律条文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综观整个民法典,也未对居住权与抵押权发生冲突时的解决机制进行确定,笔者不揣谫陋,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对实践中存在的居住权与抵押权之冲突问题进行了归纳。
(二)争议问题的归纳
1.抵押权人与抵押房产受让人设立的居住权的冲突
《民法典》第406条规定了抵押财产转让的规则,改变了原《物权法》第191条对于抵押物在抵押期间要想转让,必须经过抵押人同意的严格规定。实际上,在财产上设立抵押权,只要抵押权跟随抵押财产的转移而一并转移,抵押权人的权利就能够得到保障。认识到这一点,《民法典》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从宽的规则,即在抵押期限,在当事人未作约定的情况下,抵押人在其转让抵押财产之时,对抵押权人只负有通知的义务。与此同时,抵押权随着抵押财产的转让而转让,第三人在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取得了抵押物的所有权之时,也同时取得了抵押物上所负担的抵押权,要受到抵押权的约束。当抵押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抵押权人仍可主张对该物实现抵押权。此种宽松的抵押财产转让规则,有利于促进物在市场中的流通,通常设置抵押权负担的物,尤其是不动产,其转让价格会低于市场价,资金不宽裕的受让人为了满足其居住需要,即使知道设有负担但出于价格优势也会更倾向于选择此类房屋。基于此,实务中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是,抵押财产受让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以该房屋为他人无偿设立了居住权,当抵押人清偿债务时,抵押权人为了实现其合法债权而主张行使对该物的抵押权,抵押权与因房屋受让而设立的居住权发生冲突,此时应优先保护谁的利益?
2.设立在前的居住权与设立在后的抵押权之间的冲突
此种居住权和抵押权实现顺位的问题成为实践中困扰大众的第二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张三以自己的房屋为其父设立了永久居住权,供其养老居住,并办理了居住权登记。在此之后,为了生意上资金的流转,又将该已经设立了居住权的房屋抵押给银行,经过登记后获得了贷款,以期解燃眉之急。因为经营环境的恶化,张三无力按期偿还其所贷款项,银行想要通过主张抵押权的方式受偿,但因我国《民法典》并未对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解决机制作出规定,在此情况下,银行的抵押权该如何实现?不动产抵押权能否对抗居住权而优先实现?
3.设立在前的抵押权与设立在后的居住权之间的冲突
我国《民法典》允许对已经设立过抵押负担的财产进行转让,仅需通知抵押权人即可。因此,即使在民法典未做规定的前提下,当然也可类推得知不动产所有人在以该财产设立抵押之后,可以继续以该不动产为他人设立居住权。此时,产生了与第二个问题相反的问题,即同一层财产上抵押权成立在先,居住权成立在后,抵押权人欲实现抵押权时,居住权人的居住期仍未届满,此时二者在权利实现的顺序上发生冲突,则应当先实现谁的权利呢?
二、居住权与抵押权顺位冲突之司法案例观察
居住权制度虽作为《民法典》的新增内容,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加以确定,但实务中有关居住权适用问题的讨论却屡见不鲜。即使在法律未对居住权进行规定的情况下,实践中也早已有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其他民事主体根据双方达成的合意,以自己的房屋为他人设定居住权,供他人在一定时间内甚至终身无偿占用、使用的先例。在居住权确定之前,实践中的争议主要围绕在法律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意定设立的居住权是否生效的问题,诉争的当事人也多为房屋的继承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的冲突,但通过检索案例得知,对于居住权生效后与抵押权的效力冲突问题也并非无所涉及。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实务中存在的有关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冲突顺位问题进行了回应。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与张雯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价值衡量的角度考虑,房屋购买者的居住权与抵押权相比,居住权在效力上具有优先性。因此,在《民法典》颁布之后,有学者提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此案中关于居住权与抵押权实现顺位的裁定,得出当一个房屋上既有居住权又有抵押权的情形时,居住权与抵押权相比,效力具有优先性的结论。笔者认为,该案例发布于《民法典》颁布之前,由其案情可知,此案中的居住权指的是房屋购买人本人对已经购买的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根据该案所依据的《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29条第2款规定可得出,第三人对于已经设立抵押负担的房屋合法受让后,因其名下没有其他房屋可以居住,且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此种情形下,为了保护房屋所有权人对于涉案房屋的居住权利,不至于使其流离失所,才从价值衡量的角度,优先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因此,该案法院所提及的居住权与《民法典》确定的以自己房屋无偿供他人占有、使用的居住权不属同一概念,虽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保障困难人民有房屋可以居住,其裁判结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仍应对两种“居住权”所体现含义进行区分处理。若在居住权入典之后,仍不区分情形,一味地肯定居住权人应优先于抵押权人得到保护,则会有损抵押权人的权益,不利于资金的有效流通。
因此,在争议的房屋上有居住权和抵押权并存时,在法律未做规定的前提下,司法应在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平衡居住权人与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权利冲突之时的利益取舍,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双方利益。进而,为了保障司法发挥其定纷止争的中立者功能,就有必要对居住权与抵押权的权利冲突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使法院裁决案件时有法可依。
三、以权利登记时间先后解决居住权与抵押权冲突的合理性
(一)租赁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解决机制
《民法典》第405条规定了抵押权与租赁关系之间的效力等级,若某一财产已经被出租,且已经被他人合法占有之后,再以该财产为他人设立抵押权来担保债的履行,即使在抵押人无法偿债的情形下,抵押权人也不得在租赁期间内主张实现对抵押物的抵押权。租赁关系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基于租赁合同而形成的,有偿允许特定人对特定房屋进行占有使用。而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具有物权的一般特性,原则上优先于债权实现。此种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为承租人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更好地体现诚实信用原则。
租赁权与居住权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无力购买住房的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二者相比,租赁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基于有偿合同设定的权利,而居住权除非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下,通常为基于双方达成订立居住权合同的合意无偿获得的权利。但究其根本,二者的本质都属于对他人所有的物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只不过租赁权以租赁合同为准,合同生效即可享有权利,而居住权则以居住权合同经登记机关登记为生效要件,二者在功能上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当居住权与抵押权发生冲突时,在法律未有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参照租赁权与抵押权冲突解决规则适用,即在抵押权设立之前,房屋已经设立了居住权并且移转占有的,已经设立的居住权不受抵押权的影响。换言之,居住权成立在先,则后成立的抵押权在居住权存续之间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
(二)质权与抵押权的冲突解决机制
《民法典》第415条规定了在同一个财产抵押权和质权并存时该财产的清偿顺序[2],属于民法典最新增加的一个法律条文,是关于同属于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与质权的关系的规定。因为我国允许以动产为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抵押权。因而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财产上既被设立了抵押权,也被设立了质权的权利并存局面。此种情形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该财产经拍卖或者变卖方式所获得的价款,以登记或者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3]。原出台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采登记的公示效力大于交付的公示效力原则[4]。随后发布的《物权法》未对此问题作出安排,仍沿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5]。2019年11月5日发布的《九民会议纪要》第65条与尔后公布的《民法典》第415均认为登记与交付的公示效力相同,明确了在同一财产上既设立了抵押权又设立了质权时,应当按照公示的时间先后确定二者的清偿顺序。由此可知,《民法典》在同一财产上并存两种以上不同权利之时,采取的是更为简捷高效的解决措施,不再对公示手段的效力进行区分,依据权利设定的时间先后确定权利实现的顺序。动产抵押的设立相对于不动产抵押的设立而言更加宽松,采登记对抗主义,因此在适用过程中,相较于不动产抵押而言情形会更加复杂。
“举重以明轻”是法律经常运用的一种解释方法,笔者认为,就权利生效的条件而言,单就不动产方面进行讨论,无论是居住权还是抵押权都要以居住权合同或抵押合同登记为生效要件。由于居住权或者抵押权设立之后将对不动产的租赁、转让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设立居住权与不动产抵押权之时,除了不动产所有人与居住权人或抵押权人要达成书面的合同之外,还要向登记机关申请居住权或者抵押权登记。因二者均采法定的登记公示手段,其公示效力当然相同,在公示效力不同的情形下还可根据权利设立时间的先后确定权利实现的顺序,更不论公示效力相同的情形。此外,无论是抵押权成立在先还是居住权成立在先,在进行权利登记之时,交易相对人都可在登记机关查询到房屋上是否存在权利负担,且法定登记具有公信效力,会产生令社会相信的法律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在同一不动产上并存居住权与抵押权之时,在法律未做规定的情形下,应当以两种权利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权利实现的顺序。
结语
居住权制度入典,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解决特殊困难群体住房难的社会问题,做到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的利用价值,真正实现让每个人都住有所居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进行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对交易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有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注意该房屋上是否存在抵押、出租等权利负担,还需要注意该房屋是否设立了居住权。居住权登记可以起到权利公示的作用,不仅能够保障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不动产交易活动中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未对居住权抵押权冲突进行规定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权利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权利实现的顺序,若居住权经登记设立在先,后登记设立的抵押权在居住权期间内则不得对抗居住权人;若抵押权登记设立在先,则后登记设立的居住权则无法对抗抵押权人。此种冲突解决机制只是法律未做明确规定下协商适用的结果,居住权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还需要日后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作出更多的配套规定,才能在保障居住权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物的其他效能,避免为保障特定困难群体居住的立法追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房产所有人或其继承人的终身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