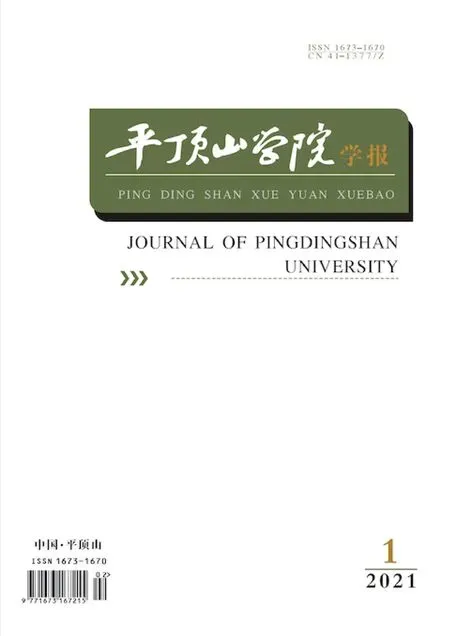作为隐微修辞的“晚明”历史记忆
——以《古今》杂志的“晚明”书写为中心
鲍良兵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 面对日寇的侵略,大片中国领土沦陷。身处亡国之际,作为浸染传统中国文化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曾屡次发生的易代记忆往往成为其借助的思想资源。正如学者袁一丹所指出的:“抗战时期的诗文史论中反复出现朝代间的类比,用以与当下处境相提并论的是东晋、南宋与晚明。为什么拿这三个朝代作类比?这种修辞策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渡’这一相似的历史情境。类比的修辞法往往出现在朝代交替、重叠的时刻。”[1]正是基于家国兴亡这一特殊历史时空下政治伦理的要求,身处亡国阴影下的文人常常通过对历史资源的调动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史学家陈垣认为:“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2],不出这四种选择。尤其是对于身处“沦陷区”的文人,在敌伪高压统治的阴影下,心态上无形的“自我压抑”,也在对历史——能与当下的处境构成互文关系的,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再发明中,发展出一种“微言”式的修辞与喻意策略。隐微修辞,无疑提供一种较为隐晦的修辞策略,同时亦起到保障性的功用(1)关于“隐微修辞”,本文借用袁一丹的说法。袁一丹在研究北平沦陷区文人的诗文史著时认为,将沦陷时期文人的诗文史著当作文本来细读,这些文本分属于不同的文类传统,甚至被划入不同的学科框架,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修辞特征,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这种“加密文本”不妨统称为“隐微修辞”。具体参见袁一丹:《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第9页。。除此之外,这一修辞策略亦可为“贰臣”或“灰色文人”所使用,成为他们发皇心曲的中介。以明季钱谦益为例,有研究者指出:“钱谦益的史诗说紧扣遗民处境建立,且述说之际,俨然以遗民自居。这也许是一种建构‘意欲形象’的努力。世人咸知,钱氏身世明清二朝,为‘贰臣’。钱氏通过诗史论述而以遗民形象出现,或欲洗刷其‘贰臣’的历史污点?或欲赋其未遂之志?道德性压迫之下,成为微言心曲的修辞策略。”[3]基于历史情境的深刻相似性,“晚明”这“易代”之际的历史经验和士人的出处选择,成为抗战时期文人学者进行身份构建,表达认同,或隐曲地寄托个人情志,或为自己的出处辩护的重要资源。
本文主要以《古今》杂志为中心,通过考察“灰色文人”对晚明的言说,借用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的理论,对其言说做一种症候式的阅读。阿尔都塞认为,至少存在两种阅读方法:一是就外在单纯字面的理解;另一则必须透过所谓“症候式阅读”,才能了解真相。因此,笔者将这些文章视作“潜文本”,即隐微心曲的一种修辞。
一、“晚明”记忆与“灰色”文人的遗民拟态
1942年,依附汪伪政权的文人创办了《古今》杂志(1942年3月至1944 年10月),在沦陷区文坛形成了一个散文书写的风潮。这个杂志刊登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散文随笔,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隐居在沦陷区的文人投稿,形成了一个“亲汪文人”的文学空间。而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这个杂志所营造的文学空间无疑是“灰色”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古今》可视为一群怀抱感伤怀旧情绪的附逆文人的温床,他们既有羞耻和自怜的心情,又有辩护与忏悔的复杂心境,形成了战争时期特殊的“遗民”文学[4]66。事实上,《古今》杂志的出现,可视为“灰色”文人的自我建构身份的努力。对于直接与日、汪伪政府牵涉者而言,无论他原来是否从事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写作提供了“政治身份”之外的另一种转换身份的可能以及另一个说法的管道,而散文可谓是表露心迹、寄托遥旨的最便利、最切身的文体。
除此之外,审视《古今》杂志上的文章,与时人借用“晚明”史事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相类似,沦陷区的“灰色文人”同样借助“晚明”史事的言说来曲折表达自己心声。学者傅葆石在研究上海沦陷区文人的出处选择和精神世界时,曾努力避免道德上的简化,强调在极端恐怖环境下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和暧昧性,采用了消极抵抗、积极反抗与附逆合作的三分法来提高对道德模糊“灰色地带的认识”。他指出,和许多为民族而战的反抗者不同,一部分作家选择隐遁的生活协调个人生存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冲突,消极隐退成为他们一种象征性的抵抗态度,而另一方面,许多附逆文人则想办法减轻他们的道德负罪感,常将自己描绘成遗民,以与现实完全矛盾的生活方式,在怀古中表达他们感情的疏离(2)关于“灰色文人”的研究,参见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页。。而袁一丹也指出1940年代沦陷区中遗民意识泛化的现象,称为“遗民拟态”,而明清易代的历史成为遗民拟态的最佳资源。
事实上,在国家伦理道德面前,沦陷区的“灰色文人”陷入言说的困境。正如文载道在《借“古”话“今”》一文中所说,人类的感情思想,无论是哀和乐,它的最崇高的表现也无过于沉默与无言。然而,“人究竟还是无往而不矛盾,也便是无往而不可怜的东西,我们终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始终”[5]。因此,那些难言之隐被编织进了文章。于是,讨论“明清易代的遗民,甚至道德有亏的‘贰臣’,经营理想和美化的怀旧小品和随笔,辩证忠孝议题,以期在通敌与抵抗、妥协与爱国的价值对立中找到解释自身处境的平衡等,很容易成为《古今》杂志文人消解和逃避‘通敌者’的道德困境,同时又以修复中华文化和日常中国身份的认同,强调自己在儒家忠孝道德外特立独行的依据”[4]66-67。
首先,从形式和涉及的人物题材看,明清之际的遗民故事已经成为古迹,谈论他们成为一种怀旧的表征,从而营造出“去政治化”的氛围。而《古今》杂志从第9期开始改用新的封面:刊名的《古今》,用阴文当作书眉,字体占封面三分之一,在视觉上突出“古旧”这一特征。下面则印以石涛的画,题云“两人山际论古今”,山上席地而坐“隐士”之类的人物两人,下泊一小舟,船尾有童仆各一。这一改造策略与那些怀旧小品和随笔,在沦陷区这个高度政治化的空间中,恰恰成了一种表征,营造刊物一种“隐逸”的氛围,进而塑造创作者一种“遗民”的身份感。在题材上,《古今》杂志的文章也常常选取“古事”来谈,其中不乏晚明遗民的轶事逸闻。例如郑秉珊的《八大山人与石涛》一文谈八大山人与石涛的轶事。文中叙述八大山人弱冠遭变,弃家遁奉新山中,薙发为僧,以及闹市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的异事;山涛在国变后只用手语和笔谈,因为山人那时候已自讳为哑巴。文中展现的是国变后作为异人奇士的遗民轶事,通过“谈遗民轶事”这一题材,表征自家的“逸”,从而塑造一种“不谈风云”的自身形象,而这一点尤其可以从周黎庵这一时期的文章题材的转变上看出。抗战初期的周黎庵非常积极,是“孤岛”上海的爱国史家。他以随笔的形式号召民众抗战,曾在1938年与文载道等人一起出版《边鼓集》,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9年,他有一系列的读史笔记发表在《宇宙风(乙刊)》上,如《明末浙东的对外抗争》《清初镇压士气的三大狱》等,借古讽今,通过“明清鼎革”之际的史实揭发“异族”的残酷统治。1940年,其个人文集《吴钩集》中收录的历史小说《迎降》,就是通过汉奸钱谦益的“附逆”行为来影射“现代人的嘴脸”。但是,随着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孤岛”上海的彻底沦陷,周黎庵的文章题材发生了转变,所谈多集中于清代的太监、明代的妓女等这样适宜清谈且有猎奇意味的话题,他的文章中已很难看到反抗的气性和斗志了。周黎庵的转变显然并非个别现象,其前后之所以不一,主要是整个政治、军事和舆论环境发生了转变。日军在占领上海租界以后,加强了对上海舆论的管制,对文化人则采取引诱和威胁的方法,稍有名气的作家都不能幸免。正是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下,既不愿公开附逆,又不敢公然反抗,身居“异态时空”的文人陷入言说的困境,只能选择适合清谈的话题。而《吴梅村的私情诗》《吴梅村与晦山和尚》《朱竹垞的恋爱事迹》《朱竹垞咏古诗》等,文人在这些题材上的自我选择,聚焦于名人轶事,通过书写有趣的小品,营造“不谈风云,只谈风月”的姿态,背后是其作为“遗民”表征的努力。
二、晚明“孤臣孽子”的心声追认与身份建构
在此乱离之世,在沦陷区的“灰色”文人体认或追认“明季遗民”的心声,也成为其幽微言说自身道德困境的重要策略之一。如在文载道撰写的《关于风土人情》一文中,文氏以自己卧病而读记风土之作营造出一种因身体羸弱而“忧伤”的感觉。生病之人,其心思比常人显得更为敏感,所以“不禁深深引起了风土人情之恋。然一面亦有感于胜会之不再,与时序的代谢,诚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民之感。人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之中,往往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觉得俯仰啼笑,仿佛一无是处”[6]23。在欲语还休中,文载道特别肯定遗民笔下的风土之作,认为他们的笔下最有声色,其记叙、抒情、写景,因为“有情”,所以作品“含着至性至情”。从一地之风土出发,肯定写作者对脚下风土之痴爱。而细读该文,此种“有情”文字,文氏如此表彰风土人情之重要性,不无“偷梁换柱”地用“地方性”来“取代”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用心。在文章中,文载道还引明遗民张宗子的《陶庵梦忆》,认为《陶庵梦忆》中所记述的虽然是旧日时光中的一地,一肢一节,即便“琐琐写来”,但也是“文情并茂,而转折多姿”。内容“虽不及午梦堂的声泪俱下,但如果先看一看其‘自序’,则似乎也不在午梦堂之下;所谓‘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螘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矣’”[6]23。换一种说法,人们在“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之后所留下来的,却是千锤百炼之后的一种生之执着——由此出发的对于过去彻骨的眷念,如陆士衡所谓“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者!通过理解张宗子的生之恋,文载道是否也在忏悔自身的偷生?作者似乎不无此意。
而文中他猜想宗子的心思则显得更富有意味:
这些过眼烟云,在“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时的陶庵想来,真也成为一番“孽”,所谓“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而非“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可了。我们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梦忆”中所记载的一切陈迹,似乎皆足以令人感到沉痛悱恻,感到低徊反覆而不能自己,如他自己所说,如“刦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再说得迂旧一点,则世上最可悲矜的,也惟有“孤臣孽子”之心![6]26
通过追认张宗子的“孤臣孽子”之心,文氏在字里行间却透着自身“孤臣孽子”的心声:自己迫于现实,屈身乱世,此间种种难言之隐,又有谁能体味?这又何尝不是文氏本人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再如文载道的《关于〈日知录〉》一文,他自述阅读顾炎武《日知录》的感受:觉得这的确是一部好书。无论于朝章国故、学问道德、人情节操、风俗舆地,都有很精彩、很广博的启发。文中表达对明亡以后的几位遗老如王船山、黄梨洲、归玄恭、叶天寥等的品格与学问的追慕,认为他们这些人“其性格或有狂放狷介,豪爽凝静之分;其治学处世和出身,也各有截然不侔之处”[7]17。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对于陵谷之变迁,身世之慨叹,却无处不表现其苍凉抑郁之感”[7]17。而且还竭智尽忠、苦心孤诣地,以这与生俱来的“执着”做种种的奋斗。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不过头颅一颗,昂藏七尺,再加上三寸的秃笔与唇舌而已。信如诗国风《黍离》章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7]17。强调他们身上有一种原始而淳朴的无言之痛。尤其是他感叹顾炎武的孤臣孽子之心,“呜呜乎,‘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患虑也深’,故其中虽言旧制处而依然切合当时现实。惜因‘古今’篇幅所限,未能多所引证,而鄙人浅陋,尤未能达先生用心于什一,清夜书此,只望能作‘知惭愧’之裨助而已”[7]20。同样是表达了文氏自己那种“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患虑也深”的忧世心声。
三、晚明“道德异端”和道义事功化的自我辩解
作为一种隐微修辞,明季富有争议性的人物自然也成为“灰色文人”的言说对象。而纵观这一类文章,写作者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常常在文中辩证道德和事功的议题,强化事功的道德性,字里行间中为自己的出处进退辩护。是以,需要在他们的文字书写中体察其细微用心。
审视明末,最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非自居“异端”的李贽莫属。他在思想上对女性态度的通达以及割喉自杀的传奇都足具话题性,而他发覆前人对秦始皇、冯道等人的历史评价,以为孔子的言论不足据和对正统道德主义的强烈抨击,给予后世文人充分发挥的空间。1943年,发表在《古今》第26期上的《从李氏焚书谈到李卓吾》一文中,作者何淑就特别对其生平言论进行了述评。在文章中,何淑以简介李贽的生平开篇,重点强调其对假道学的批驳:“他那种才华横溢,放诞不经的狂态,颇引起道学先生的反对与攻讦,可是李卓吾也最看不起这班伪道学者,所以他说:‘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女子之手’,这句话连东林派学者的顾宪成都佩服得五体投地。”[8]27文中简述其死时的情状:“李卓吾入狱的时候,年事很高,已有七十六岁,可是他被害下狱的罪名,却是污辱儒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我们只要看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的劾疏,攻击得到多么没有理由。”[8]27何淑认为张问达的劾疏中说李贽所谓以思想惑乱人心、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明劫人财、强搂人妇等,所论皆非;认为世人的批评,不过将他视为一狂士,这是认错了李卓吾的个性,而且埋没了他非常高的抱负与不世的才华。作者在归纳李卓吾思想的基础上,将其视为哲学的社会主义,认为他揭破世人对圣贤的偶像崇拜,肯定李贽在《答耿司寇》书中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8]28的观点。文章尤其指出李贽切重实际,不务空言。何淑如此为李贽“正名”,可谓是心有所托。因为儒家思想注重道德节气,而李卓吾的“异端”挑战道德,强调实际,不尚空谈等,在某种程度上与自我标榜敢于在民族国家道义面前与敌协作、强调“实行”的亲汪文人有着类似之处,因而“异端”李贽被重点肯定而成为“灰色”文人遥寄心声的对象之一。
与何淑一文思路相类似,南冠则将李贽和深受李贽影响的周作人“相提并论”。在《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一文中,作者将周作人类比李卓吾,肯定周作人和李卓吾的说实话的真诚,他写道:“说诚实话一点,两人盖是相同的。关于这一点,知堂曾说:‘凡是以思想问题受迫害的人大抵都如此,他岂真有惑世诬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独秘,思以利他,终乃至于损己而无怨。’这即是郭沫若先生所极称赞的一点,即余永宁的《李卓吾先生告文》所言:‘先生古之为己者也。为己之极,急于为人。为人之极,至于无己。则先生者今之为人之极者也。’”[9]9正是因为世人不能了解李卓吾的用心,所以反被表象所蒙蔽。也正因如此,“甚至闹出认明遗民张岱是没有心肝的笑话来”[9]9。与此类似的误解,作者认为也体现在世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中。文章指出,胡风将矛头指向周作人,认定其消沉且已为时代抛弃的言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攻击,就是不了解的偏见,“只要看知堂在《苦茶随笔》中有那些剑拔弩张的文章即可知道他实在并不消极”[9]9。认为与世人误解李贽一样,多半是误会周作人。文中表彰周作人和李卓吾的行为在一般人眼中的“偏见”,其实是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大道”。而他之所以肯定李卓吾和周作人的“实话”,用意则恐怕暗指时人“抗战必胜”等宣传的“大话”,企图将民众目光引向现实处境,标榜这种不可为、无能为、只能在最大可能中活下去的“现实主义”生存态度,从而无形中来消解抗战中民众的超克现实生活的雄心,同时也不乏为自己的出处行为辩护的用心。
南冠认为,李卓吾被世人误解,最终他被视为“倡乱道,惑世诬民”: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刺谬不经,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艺术,所谓观音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有明劫人才,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9]11
结果圣旨下来,“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街五城严拿治罪”[9]12。他的书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9]12。文章中同样是替李卓吾的“异端”进行辩护,指出世人的偏见,表白“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心曲。
除李贽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的钱谦益显然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复杂人物。《清史稿·文苑传》中的《钱谦益传》主要叙述他的政治、历史行迹。概而言之,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钱谦益名隶东林党,屡历明季数朝党争。二、崇祯帝殉国后,他先拟拥立潞王,等到福王登极之局面形成后,投靠福王,结交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三、清军南下,钱谦益以礼部尚书迎降,复仕清。四、辞官里居后,因黄毓祺谋复故明案,下狱南京。钱谦益的这几件事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关乎明季政治内幕及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人格操守,再加上他“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学成就,足以引起后世许多论者的兴趣。自然,钱谦益及其诗文也成为《古今》杂志的“灰色文人”一再论述的对象。
留玉在《读〈吾炙集〉小记》一文中,通过阅读钱谦益辑的《吾炙集》,体味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的逋逃生活及各种各样之政治心理,以此推知当时社会情状。对于《吾炙集》,留玉的评价是“味有胜于读小说者”。作者特别强调诗集中记述了当时之“混乱与恐怖”,对钱牧斋记录国变后士人的活动更是心有戚戚。留玉指出,阅读《吾炙集》给他深刻印象的是当时人心之私,“世当变革,人事纷歧,恋旧趋新,各便所向,斗龙角虎,惟力是衡”[10]24。尤其是钱牧斋记录明宗室遗臣等谋求复兴者的秘密活动之诗句最为有声有色,如写化装:“最喜龙蛇随处杂,可知牛马任他呼。半在人家半在寺,行藏尽教世间疑。”写工作活动:“去来未必真游戏,成败何须细讨论,不为长饥投米店,岂因多病叩医门?”而各地的活动,就是招收“复明同志”。留玉指出此种吸收工作“虽当日民意激昂,就此集所见,知其亦非易事”,因为在“顾国运变迁之际,人心莫不自私”[10]25。文中引罗元益在《安龙逸史》序中所曰“宏光有可为之时,而首坏于马士英阮大铖,隆武有可为之姿,而再坏于郑芝龙,分符之勳镇,尽属叛臣,列土之公侯,俱为逆党,事缓则竞宠以邀荣,事急则卖降而鼠窜,虽曰奉主,大半营私,明之天下,洵无一片干净土也”之语,虽然觉得此说比较激切,但是也基本上符合事实,“熹宗之季,凶阉内擅,流贼外讧,逮乎崇祯,文恬武嬉,将骄卒惰,而且水旱相仍,饥馑频告,天灾人异,明奚不亡?当李闯进逼京畿,一时即多依附,论者以为獐头鼠目之流,谓反颜事讎,复罹其毒云云,虽曰风教,亦一是非”[10]25。指出自己从诗集中看到的都是人心的自私,他写道:“而今《吾炙集》诸作家,丹心贯日,所遇如何?‘住山几个甘长饿?断酒多年怕独醒。’同志变节矣,‘士女竞传灯火节,衣冠齐倒酪浆杯。’新人腾欢矣。”[10]25而对于面对国变之后士人的种种选择,留玉不像一般写作者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进行批判,反而认为颇可同情,“彼诸君子之失败,或隐遁或转变,有可无愧于天地间者,其种种活动,非野心自私智出发也”[10]25。尤其是“特当时为一姓一家之争,虽曰忠君爱国,惟国家体制之败毁,以势孤力弱诸书生,当然无可挽回大局”[10]25。而与一家一姓的王朝失得相比,留玉认为更重要的是挽救民生,“而民生凋疲,有待于将息者又甚亟也”[10]25。
细察文章,文中作者理解“诸臣”之私心,其如此通情达理的态度背后,恐怕不无自己的用意。其如此小心翼翼肯定改朝换代后的士人的“私心”,即是以人性之私来消解对国家的道德“忠义”,从而缓解自身的道德压力。文章中强调相比一家一姓王朝的得失,更重要的则是“民生”,此种“民生为大”的话语背后,事实上和打着“民生”旗号的汪伪政权所宣传的“和平建国”运动异曲同工,强调民生以缓解自身道德紧张,从中可见一斑。
郑秉珊则在《关于钱牧斋》一文中,一开始就对当下人用贰臣之名来讽刺、揶揄钱谦益的现状表示不满:“失节两个字,注定了钱氏的人格,使他永不翻身,即如现在的报纸上,还时常有钞撮前人揶揄钱氏的文字,不啻替乾隆帝摇旗呐喊,做励节正心的工作,真不可解。”[11]13在该文中,他主要评述钱氏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成就,引用《清史稿》曰:“谦益为文博瞻,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振之。”高度赞扬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感叹其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故事。与以上相对的是,他特别指出钱谦益政治上“却有诸多失败”,并且着重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多文为累。他的诗文高妙,果然得到许多人的赞美拥护,但也为敌人所特别注意。在二十九岁通籍后,休闲十年,方才出山,出山后典试浙江,就有卖关节事,被人诬陷,旋即削籍回家。崇祯初年,起自废籍,召为礼部侍郎,又因枚卜的竞争,给温体仁周延儒的联合攻击,终周温两人当国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入京供职的机会。由周延儒“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这句话看来,可知周氏们的如何忌视他了;第二是夸大之病。他秉有好大喜功铺张扬厉的情性,自以为是顾宪成的弟子,王图的门生,是东林的嫡子,自顾高等死后,第二期东林的中坚是文震孟黄道周倪元璐等,功名都落后十余年,所以他便以东林领袖自居。他著有何君实墓志,里面说他和何氏在少年事读书破山寺,寺里的四金刚,托梦于何氏,说你们时时进出山门,累我们起立迎送。又仆妇生病,祷于城隍神,神凭妇人说道,乞得钱相公一个名刺,便可宥赦,所以他便自以为将来必定位居宰执,自命不凡。由他的文章看来,他派别的观念极深,往往流于意气。又是一个雄辩家,言语颇不谨慎,因此政敌恨他刺骨,崇祯九年张汉儒诬陷之狱,便是由温氏策动,险些送掉性命的。第三是志大才疏。这是东林诸人的总缺点,钱氏也未能例外,他们自以为未君子群而不党,惟以文章气节相呼应,以犯上敢谏为能,而没有敌党组织的严密,因此政治活动,东林始终下风。即如崇祯初年,逆案已定,东林再起,但阉党的冯铨杨维垣等,身虽下野,而潜势力极大,交通内外,东林也奈何他们不得。及至崇祯殉国,钱氏与史可法谋立潞王,那知又受马士英的欺骗,福王即位南京,东林中人,仍旧没有握到实权,党祸纷起,南都很快的覆灭了。[11]14
总结钱氏失败的缘由,不是为其政治上失意表达一种遗憾,而是以此为钱氏发皇心曲,表达对钱谦益此后种种行为的同情和理解。正因钱氏屡经忧患:
渐知政治的须用手腕,所以在张汉儒事件中,不惜和太监曹化淳,逆党冯铨交往。在复社发达时,不惜倾身下交后辈的张溥。为要打倒温体仁系的薛国观,又不惜和政敌周延儒联络一起。弘光即位因主立潞王之故,恐惧得罪,又不惜拥护马士英,举荐杨维垣,次拍阮大铖,可是东林中人,纷纷怀疑他的人格,清誉也日减了,由今日的我们看来,这是无足怪的。因为他那时年纪已经六十三了,以前通籍三十年,居官不过三四载,这次再不出山,那么以后别无机会了。又他眼见以前东林的失败,敌人的战胜,种种因果,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基础,不得不随俗浮沉,从权行事。本来据十五世纪马凯维里的政治学说而论,政治学应该和伦理宗教分离,才切合现实,我们读《史记》,觉得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变化无穷,东林墨守儒家迂腐之见,欲求得胜利,何异缘木求鱼呢?[11]15
文中表面上是为钱牧斋翻案,背后则是强调事功大于道义。文末述及牧斋归降后即退隐,“杜门却扫,自谓:‘不读世间书,不作世间文,不见世间人,不谈世间事。’情态恶劣,可以想见,但不忘明室,而暗中仍与黄毓祺来往。顺治十年,黄氏被捕,他于三月晦日也锒铛入狱,在南京狱中一年多,才得释归”[11]15云云,恐怕也是别有怀抱,以身在曹营心在汉为自拟(3)郑秉珊的《关于钱牧斋》一文发表后,引起陈旭轮的知己同感。1943年第24期的《古今》杂志上刊发了一篇陈氏与周黎庵的通讯。文中陈旭轮为钱谦益发声,认为当日与牧斋往返者“无非孤臣孽子,畸行异能之士,若果如乾隆帝所诋为顽钝无耻之长乐老者,则如黄梨洲魏叔子之辈,文章气节,至今为士林乐道者,肯与之往还通声气乎?若非当日别具苦心,志在复明,何能见信节烈风概之朋侪如黄毓祺乎”。以钱牧斋相交之友人来反证钱是苦心复明。继而在文章中简述复明志士黄毓祺的生平,以感叹历经百年,历史记载已经面目全非,难得真相,强调“历来惊天地泣鬼神之大忠大义,应于民众口碑中探之”(见陈旭轮:《钱牧斋与黄毓祺》,载《古今》1943年第24期)。事实上,1941年《宇宙风·乙刊》上就曾有过钱谦益的争议。唐伟之的《关于钱谦益》一文为钱谦益翻案,而玄棠的《我也谈谈钱谦益》一文对唐文进行了批驳(分见唐伟之:《关于钱谦益》,载《宇宙风·乙刊》1941年第41期和玄棠:《我也谈谈钱谦益》,载《宇宙风·乙刊》1941年第50期)。从中也可窥钱谦益历史评价背后的不同立场。。
此外,明末亡国的历史殷鉴中,以“道义自任”的东林党人的“士风”备受后世批评。而以古鉴今,这也为“灰色文人”批评“空谈亡国”、表彰道义“事功化”提供了言说例证。刘平在《明末的人物》一文中,批评晚明的士风只有空谈,不务实际。“明末三案,那班朝士们很因此慷慨激烈地争论了一番,反复得简直令人生厌,结果好像是雷声大,雨声小,收束得颇为模糊;倒引得他们沾沾自喜,以为总算替国家出了力,办了事,而其实也只是东林及非东林诸君之扰扰嚷嚷而已。”[12]19相反倒是太监魏忠贤始终不动声色,“颇足见出沉默之与嚷嚷者的形势。此后是一段凄惨的历史,朝士们默默地挨受着刑罚和虐杀了”[12]19。与“忠君爱国”的扰扰嚷嚷相比,太监反而看惯了这些“世故人情”,一朝权在手,往往袭取主子之故技以遂其征服欲。作者在文中感叹:“朝士仅只是朝士,只在于嚷嚷之间,倘有压力加诸其身,抵抗是没有的,但他们嚷嚷却未必因而趋于消灭。前之东林,后之复社,无非为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12]20结果是“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拉倒”[12]20。文章引《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中云:“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可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大祸。”[12]20认为恰是书生空谈误国,“宜乎赵翼有‘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之叹了”[12]20。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唯一的能力只有嚷嚷:“这些人也自有其本领,嚷嚷为其一;其二,也还是嚷嚷;其三,倘不是嚷嚷,便只是一死。”[12]20文中引李刚主云:“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穀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12]20指出:“明末朝士虽不终日忙着做‘策论’‘经义’或‘赋得’什么的,但那些时文似乎永远隐隐地刺在他们的脸上,后来读史的人也往往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嚷嚷之间看得出,颜习斋谓‘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于虚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12]20一帮“朝士”空嚷鼓噪,自身获得了名利,但结果则是朝政荒废,受苦的则是老百姓。
尤其是到了王朝危亡之际,这帮“朝士”个个都束手无策,“城破时,朝廷里没有一个官,连那些阁臣们也作鸟兽散了,也不知他们究竟‘巷战’了没有?及至崇祯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才觉得他一个人是完全孤独的。至于殉难的朝士之中,竟无一人杀贼而死,大都非自缢,即投井,可见‘巷战’之说,也还是骗骗皇帝的”[12]22。文中嘲讽这帮“朝士”空谈气节,不是逃跑,就是以自杀来换取名节。作者显然对此种行为持批判态度,认为殉难的诸多朝士死得并不冤屈或应该有所怨艾。刘平说:
彼辈以为事急时为皇帝一死即是忠臣,一了百了,就此塞责,而平日的扰嚷以及殃民误国等等,到此便可一笔勾销,而大摇大摆地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其实气节是必须讲的,但却是不得已的最后一着棋;若不谋于先,也只是一着空着,那危险是不仅仅关系于个人生命之殒灭的。所以推诿才真真是罪恶。但这原是明末诸朝士的第三着绝技了,即所谓“三上吊”是也。看罢,党祸时一死了之,破国时一死了之,绝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一哭二闹”是错误和荒唐。至于后来,连“三上吊”似乎也不多见了,剩下的,只是扰扰嚷嚷之更厉害些而已。颜氏学记性理书评中有云: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之语,有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悽者久之。这一段的意思颇可见出习斋低徊激越的心情。但我似乎记得他也有过那么两句诗:“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则又不过是甲申殉难诸朝士的一流人物罢了。[12]22
刘氏该文还是围绕“道义的事功化”展开,批判“明季朝士”空讲气节,空谈误国,当外敌入侵时以死尽忠于事无补,其行为的背后则是为自己赢取忠义的美名,结果是国事陵夷,百姓受苦。强调在内忧外患之际,要敢于任事,讲求事功,有着重新塑造道德伦理的企图,讲求实际,能够解民于倒悬之际,这才是道德的真正“大道”。
由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古今》杂志的“灰色”文人通过晚明史实的言说,塑造自身“遗民”形象,或阐扬心曲,其背后无非是“不得已”“忍辱”“被误解”“要实行”“道义事功化”等“自我诡辩”,对比颠沛流离中其他文人的坚守,不由令人感慨。危急时刻的言说,固然是“知识”、是“学问”,但更重要的是“气节”和“情怀”。
面对战争带来的裂变,沦陷区的“灰色文人”不免陷入道德的焦虑之中。他们讨论“晚明”人物种种史事,塑造自身“只谈风月”的“逸士”形象,或辩证道德与事功,消解或重塑道德伦理的标准,以期在通敌与抵抗、妥协与爱国的价值对立中找到解释自身处境的平衡,可谓是“良苦用心”。本文关注“灰色文人”对“晚明”史事和人物的言说,“揭示”其幽微复杂的心声,并无意为其展开的道德申辩张目,事实上,通过明末“符号”来隐微表征自家心声,此一种隐微修辞成效如何,有待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内部的检视和确认。而且,相对于“言说”,面对日寇的侵略,现实中的行为才是判断文人伦理道德的真正标准。是以,本文的重心与其说是揭示沦陷区文人在道德伦理与现实困境之间自我言说的复杂一面,毋宁说是考察“灰色文人”晚明历史记忆与自我辩解之间的表微机制及其言说的挣扎和欲说还休的辩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