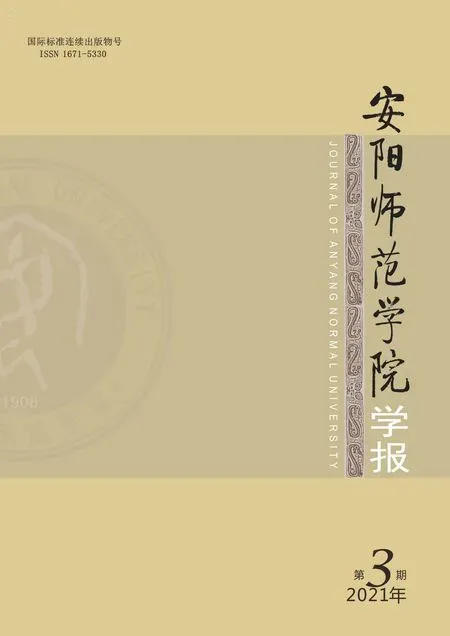朱谦之对《周易》的创造性阐释
唐诗杰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朱谦之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治学涉及哲学、宗教、史学、音乐等诸多领域,在五四时期,他以倡导唯情论闻名。他的唯情论严格而言可划分为本体为“无”与本体为“有”两个阶段,二者都依托《周易》进行阐发。相较而言,朱谦之在本体为“无”的唯情论时期,所依托的《周易》思想资源是有限的,只是在《先秦诸子学综述》中偶有提及,而在本体为“有”的唯情论时期,则以《周易》为依托,写作《周易哲学》,阐发其唯情论思想体系。在后一阶段,朱谦之思想的生成与《周易》的渊源联系颇深,且在近代易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值得深入探析。
一、借《周易》阐发的唯情论
在《周易哲学》一书中,朱谦之首先拈出“情”字概念,作为其唯情哲学的核心概念。《周易》中的“情”字,共出现了14次[1],皆出现在《易传》中,如《系辞上》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 设卦以尽情伪”[2](P82)。《系辞下》中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P58),又有“变动以利言, 吉凶以情迁”[2](P91)“圣人之情见乎辞”[2](P86)。此外大壮卦的彖辞中有“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2](P48)对于这些“情”字的解释,历代争讼甚多,但大多认为,《易传》中“情”的含义并非完全同一的,有的“情”是“情状”之义,更偏向于指代现象、具象,带有形而下色彩;有的“情”是“情实”之义,偏向于指代本体、本质,带有形而上色彩。还有的学者在解释“圣人之情”的“情”时,认为此“情”是指个人的感情。而朱氏毅然弃历代争讼于不顾,提出《周易》中的“情”从始至终都是指作为宇宙本体的“情”。他以独得秘法心传的口吻说道:“大概《周易》千言万语,都只是这‘情’字,更无其他。”[3](P103)“我敢说这‘情’字便是孔学的大头脑处,所谓千古圣学不传的秘密,就是这个。”[3](P102)“可见我的学就是《周易》的学,——孔圣传来的学。”[3](P101)朱氏认为,《周易》一书实际上是在向人揭示宇宙的本体,这才是他所说的“情”,而历代注家失此真义,如今他把这《周易》中的核心秘密,即言说宇宙本质的真理揭示出来了。
朱谦之认为,“宇宙本体就是存于天地万物的一点‘真情’”[3](P102),但这一“情”的提出,并非是在具体的万事万物背后设置一个独立的、与现象二元对立的本体。相反,作为宇宙本体的“情”是与具体万事万物体用合一的,“情”既是本质也是现象。朱谦之在借《周易》阐释出的宇宙论中,本质与现象是不分的,现象即本质,本质即现象。“所见天风、木叶、鸟语、花声,无非‘真情之流’的大道理,所谓命,所谓道,所谓太极,总是这一个东西。”[3](P116)为了论述本质与现象的合一,朱谦之本于系辞中“生生之谓易”一句,提出作为本体的“情”并非静止的,而是永恒变化、不可分割的,时时刻刻处于流动变易之中。为了强调“情”的变易性,他将“情”称为“真情之流”。由于“情”是时刻流动变化的,作为本体的“情”的流动就生成了具体万事万物,具体万事万物就是“情”的流动本身。他以咸卦的彖辞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P46)解释此义,将此处的“情”理解为实体,即宇宙的实在本体,而所谓“感”就是“情”的自然流动,本体的自然流动就是把自己表现、展现出来,由此生成万物。
由于万物即“真情之流”,而“真情之流”即万物,二者体用无二,不可分割,因而人与人的思维活动本身也是这一股生生不息的“真情之流”。在这一宇宙论前提下,人探求真理的行为,即认识宇宙本质的行为便不再需要借助于理性,而只需通过直觉。因为理性认识论是建立在物我二分基础上,悬置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世界,通过理性使主体与客体相符合。而在朱谦之的宇宙论体系中,物与我相统一,没有主客体之分,作为主体的“我”只要回归本来就与客体统一的本性,就能把握宇宙的本质。这种认识模式是非理性的,朱谦之将此称为“默识”。他将《系辞》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2](P83)一句,与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4]结合起来,将非理性的“默识”视为认识世界本质与宇宙本体的方法。他解释系辞中的该句道:“成里边有个秘诀,就是‘不言而信’,只信着就得了。难道能用言语文字去推证其所以然吗?因为‘神’是不靠观念和符号直接默识的,那种明了透彻的程度,用言语是说不出来,所以孔子才要‘予欲无言’。”[3](P107)因而他在该文开头即说“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求一种神秘的直觉(Mystic Jutuition),以神的智慧作自己的智慧,大开真情之眼,以与绝对无比不可言状的‘神’融合为一,这就是孔门所谓‘默识’了!”[3](P107)可见,他所说的“默识”即是直觉。
此处他所说的“神”即是“情”,由于朱谦之这套直觉-默识认识论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非理性的、不可分割、绵延不绝的“真情之流”,只有承认了这一个前提,其认识论才是有效的。而要考察这一前提的有效性,就其理论自身的逻辑来说,又不能依赖理智,而只能依赖直觉,由此造成循环论证的困难。这一矛盾使得承认前提的行为不能依靠理智,而只能是“选择相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信仰的范畴,因而朱谦之格外强调“信”作为直觉的前提,并把“情”称为“神”,以强调“相信”在这一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信”的前提下,也即在承认了世界的本质是一股非理性、不可分割的“真情之流”的前提下,理性所依赖的词语、概念、逻辑这些界限分明的认识工具就不再有效,相反,它们对于认识世界本质更是南辕北辙。因而理性不再被视为可靠的认识工具,作为非理性的直觉,即朱谦之所说的“默识”成为其唯情论体系中唯一有效的认识方式。
由此,朱谦之借助《周易》建构起了一个非理性的宇宙论与认识论,这二者相互依托,实为一体。宇宙的本质是一股生生不息、永恒绵延的“真情之流”,它不可分割,因而无法借助边界明晰的语言符号来把握,无法依赖于语言符号的理性进行把握。万物即从此“真情之流”中流出且是这“真情之流”的一部分。本体与万物、本质与现象不可分割,同为此“真情之流”。在这一宇宙论模式下,人作为“真情之流”的一部分,其本质亦为“真情之流”,故而他不用通过外求,不用通过立足于主客分离基础上的理性,而只需“复性”回归本性,通过非理性的“默识”,即可认识世界的本质,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
二、朱谦之对《周易》的言说方式
由上可见,朱谦之依托《周易》,阐发了一个以“情”为本体,以“默识”为认识方式的非理性唯情论体系,他的这一阐发方式是依托于一套极具特色的言说模式。
首先,朱谦之所依托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文本,而是整个《周易》的接受与阐释体系,他所依托的是《周易》的整个注疏系统,一个历时性的文本。其一,作为朱谦之唯情论核心概念的“情”,既未出现在《周易》的卦名中,也未出现在《周易》的卦爻词中,而是出现在远晚于《周易》卦爻辞的注释性文本《易传》中。从这一点来看,朱谦之阐说唯情论的著作不应叫《周易哲学》,而应叫《易传哲学》。其二,朱谦之唯情论体系的几个关键衔接处,都依托于后世对《周易》的阐释体系,而非《周易》本经。例如,在解释“真情”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时,朱谦之征引的材料是《文言传》中的“利贞者,性情也”[2](P17)一句,但此句情与性是并列,故为了解释“情”就是“性”,他征引了惠栋《周易述·易微言》中“《彖传》屡言天地之情,情犹性也”[5]一句,由此才把“情”就是人的本性这一逻辑打通。朱谦之在《周易哲学》中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包括将作为宇宙本体的“情”解释为生生不息、永恒绵延的状态,也依赖后世的注疏。自然,朱谦之对这种立足阐释传统上的生发有一套自洽的逻辑,即他认为所悟出的“情”正是《周易》的本义,是数千年来秘而不宣的真理与孔门秘法,在这带有道统色彩的逻辑下,那些与其思路接近的先贤注疏,就不再只是后人带有私人色彩的解说,而是向终极真理的靠近了。
朱谦之所立足的阐释传统,并不局限于《周易》的注疏传统,而是将解释所借助的传统,从《周易》扩展到整个儒家经典体系。如他的“默识”认识论所依赖的资源更多的是《论语》的阐释体系,而《周易》一书中并无“默识”一词,有的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2](P83)。朱谦之借明儒对《论语》中“默而识之”一句的解释,将此句解释为阐说体悟世界本体的认识方式应是非理性的直觉。“默识”说源自孔子,宋代以前儒生们对此谈论不多,至宋明理学与心学兴起,借“默识”阐发摆脱语言的体悟方式的做法才多了起来。朱熹注《论语》此句时说:“默识,谓不言而存诸心也。”[6]明儒邹颍泉进一步发挥此义:“子曰默而识之,识是识何物,谓之默则不靠闻见,不倚知识,不借讲理,不涉想象,方是孔门宗旨。”[7](P346)王塘南亦云:“默而识之,即自性自识,觌体无二,不可以悬想言。”[7](P477)又耿楚倥有“默识,识天地之化育也”[7](P260)之言。既然“默识”是指摆脱语言的非理性直觉,此处又言“默识”能识天地化育,所谓“天地化育”不正是指宇宙间那个生生不息、永恒绵延的情本体吗?如此,朱谦之便把孔子的“默识”与非理性的真理认知方式勾连起来。此处我们可以看到,朱谦之将《周易》原文的意思到他所主张的直觉认知方式,中间经过了多个中介,这些中介不仅不是《周易》本身的经与传所有,甚至连对《周易》的注疏都不是,朱谦之所依赖的是整个历时性的儒家经典阐释体系。
其次,朱谦之对《周易》所做的是一种宏观的把握,一种提纲挈领的言说。他不是像汉、清两代的儒生一样垂心于字句训诂,而是注重把握《周易》的核心观点与精神气质。或者说,朱谦之阐发周易的方式,与传统的经学方法相疏离,而更贴近于五四时期的哲学方法。他的整部《周易哲学》甚少着意于易学传统上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即便其中有不少对历代注家的引用,但也是作为论据为其核心观点服务,而非解决历代争讼。就其篇章安排来看,导言《发端》总括性地提出主要观点;第一章《形而上学的方法》讨论默识、直觉的认识论模式;第二章《宇宙生命——真情之流》讨论宇宙本体是“情”,是“真情之流”;第三章《流行的进化》讨论“情”的永恒绵延性;第四章《泛神的宗教》讨论“信”在其唯情论体系中的重要性;第五章《美及世界》讨论情与美的关系;只有最后一章《名象论》介入了易学史上对言、意、象三者关系与名实关系的讨论,即便如此,此章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想强调他所提出的“情”是一种非理性存在,因而难以用语言言说,只能用体悟的方式,通过“意象”来把握。由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该书每一章的主题都非常集中且明确,而且这些被论述的核心观点,都是对《周易》的宏观把握,是提纲挈领地对《周易》所体现出的哲学倾向与思想特征的概括。
同时,朱氏的这种把握,又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如上所述,《周易哲学》一书章节分明且每一章的主题都集中明确,而这六章所揭示的观点又构成了其唯情论的核心与基本框架。可以说,朱氏虽然声称他的唯情论本于《周易》,是得《周易》秘法得来,但从文本而言,他是先有唯情论的框架,再对《周易》进行唯情论阐释的。与其说他解说《周易》,不如说他是在用《周易》搭建其唯情论的框架,借《周易》的文本言说其唯情论思想。他在《周易哲学》的导言中说:“我这套唯情哲学,虽由于心的经验,但也不为无本,大概都具于《周易》中。”[3](P101)从接受美学而言,任何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都难免带上个人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使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中显现,但朱谦之对《周易》的阅读与解析,展示出的个人性与主体性极强,以至于他自己都承认,是先有显性的先在理解,才去进行阅读与阐释。
这种立足极具个人色彩的宏观式解读方式,在当时受到了质疑,其中比较直击要害的是对以“情”作为整个《周易》核心观念的质疑。有人认为“情”字在《周易》文本中出现得并不多,只是集中于《咸》《恒》《大壮》《萃》几卦的彖辞中,而非六十四卦每卦皆有,何以能作为《周易》一书的核心概念?朱谦之对此回应道:“六十四卦都是要发明天地万物之‘情’,然每卦而言,就不胜其言,所以圣人只就《咸》《恒》《大壮》《萃》诸卦,偶发其数,并不是这些卦和他卦特别。如说‘观是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本有言不能尽之意。《系辞》更明明白白地说∶‘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如此,怎见得不是六十四卦都如此呢?若能因天地万物之‘情’,而悟六十四卦生生之理,就知道一部《周易》都只是这‘情’字,都只是道着天地万物之‘情’”[3](P107)。
朱谦之的这一辩驳,关键之处在于他将“万物之情”“天地之情”的“情”字实体化。在通常的理解中,这两处的“情”字是一种属性指称,而非实体指称,或翻译成“情状”,或翻译成“情实”,是对某一实体的属性的描述。但朱谦之此处却将这种属性描述实体化,忽略通常的解释中“情”的背后还指向一个具体的实体,而直接将“情”作为实体。这种理解方式,只有在首先相信世界的本体是“情”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逻辑在这一阐释体系中的自洽。换言之,朱谦之是带着强烈的前理解来阅读《周易》的。
朱氏的这些把握,虽然是宏观又个人化的,但又非凿空式的另立新说,而是有本可证的。如朱谦之所强调的变化不息、永恒绵延的观点,与易学史上公认的《周易》强调“生生”的观点是相近的。郑玄早在其《易赞》与《易论》中就提出了“变易”一义,其后崔觐、刘贞简等发挥此义,提出“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2](P7)。《易》中言“生生”之理,大体为历代注疏家接受与继承,及至与朱氏同时代的章太炎,也接受并提倡此义。他在《易论》中说:“上《经》始乾坤,‘既成万物’,而下《经》讫于未济‘物不可终穷’,言‘既济’者,斯局促矣。”[8]借解释卦名,阐发生生未尽、永恒变化之义。可见朱氏的这些个人化的把握,虽然乍看起来有些怪诞,但又由于其宏观性与选用材料的普遍性,在精神气质与主要观点上又不游脱于易学史上的通说观点。
三、《周易哲学》的前理解构成
朱谦之对《周易哲学》的言说与阐发是极具个人化的,这种个人化色彩,出于其丰富的前理解,主要是人生观转变构成的前理解,朱谦之的《周易哲学》肇源于其人生观危机。朱谦之写作《周易哲学》时,正处于人生观转变时期,这构成了他阅读与阐释《周易》的前理解。朱氏早期曾信奉虚无主义,认为宇宙的本体是虚无,由此推出人生无意义的人生观,这一宇宙观与人生观曾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甚至一度走向自杀。在其因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被捕入狱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由此发生转变,开始承认世界的真实无妄,因而他在《周易哲学》中反复强调“真情之流”的实有性。同时,他在反思自己此前的虚无主义时,将其归咎于出于理智的怀疑思想,他在宣示其世界观转变的《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对此反思道:“大概我的根本错误,在不根据生命的事实而来,所以推演辩证的结果,不能不认‘无’为‘情’。”[9](P473)在写给李石岑的信中也说:“由怀疑去求真理,真理倒被人的理知赶跑了,怀疑的背后,有个极大的黑幕,就是‘吃人的理知’”[3](P99)。由此,他在这一人生观危机引起的反思中,确立起两种信念:一是相信世界的本体是真实无妄的“情”,二是认识世界本质与真理的方式是非理性的“直觉”而非理性。这两个预设的结论,贯穿于他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之中。
但人生观的危机能带来的只是转变,并不能决定转变后思想演进的方向,影响朱谦之思想指向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国内最早介绍柏格森的学者是钱智修[10],1913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所介绍的哲学家第一位就是柏格森。1920年,杜威在华作《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演讲,为各大报纸刊载,借着杜氏在华的声望,柏格森在中国变得火热起来,冯友兰、李石岑、钱穆等纷纷发表关于柏格森的文章,梁启超和张君劢等甚至在法国拜访了柏格森。1921年,《民铎》杂志刊出“柏格森专号”,掀起一股“柏格森热”。朱谦之的人生观发生转变时,学界正处于这股热潮之中,读书甚勤且追逐国内思想新潮的他,不可能不受这股热潮的影响。在其《偶合唯情论者的人生观及宇宙观》中,他反复提到柏格森,并且将其学说作为阐发观点的理论论据。
然而,正如高瑞泉所言:“不同的中国哲学家或中国哲学派别实际上所赞成和发挥的并不是同一个柏格森 。”[11]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偏向于接受柏格森的进化主义不同,朱谦之更多地表现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偏好。柏格森对朱谦之的影响,大致通过梁漱溟实现,朱谦之在回忆录中曾说,自己在人生观转变时期受梁漱溟影响很深。而梁氏此时正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与研究部同学的朝话中承认:“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12](P126)“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12](P126)。此书中几个核心观点,如强调宇宙是生机、生活,“尽宇宙是一生活”[13](P376)。提倡直觉并认为此是孔门真义,“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13](P453),以及梁氏强调《周易》中的“生生”观念等等,显然都带有柏格森的印记,与柏格森所提倡的世界的本质是绵延、是生命这类观点在宏观上不谋而合。而梁漱溟的这些核心论点,不仅是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四梁八柱,甚至连句式都与朱氏的表述高度相似。由此来看,朱谦之通过梁漱溟,使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构成了他阅读《周易》与写作《周易哲学》的前理解。
与此同时,构成朱谦之解读《周易》时前理解的还有其自幼年形成的个人英雄主义性格。他4岁丧母,其后丧父,不久又痛失作为知己的姐姐。至亲的相继离去,使得他自觉只有自我个人可靠,由此生成个人英雄主义的信念与性格。他在《回忆》一文中说:“到十一岁时,父亲又弃世,这时零丁孤苦,所可自信的只有‘我’,上是天,下是地,我只坚持我所固有的去抵抗外力的引诱和侵掠,所以在我少年时候,便立志要大做一个人了。”[14]也正是这种以“我”为中心,以作为主体的“我”裁夺一切的思想使其怀疑一切,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而由此带来的反思结果,强调“信”“直觉”和“物我合一”则贯穿在对《周易哲学》的行文之中。同时,即便是反思了自身的怀疑与唯我主义,他在《周易哲学》中也未能摆脱这种性格的影响。该书中动辄独得孔家真义、掌握宇宙真理的语气,处处流露着其唯我主义的独断色彩。如前所述,朱谦之对《周易》的唯情论解读,建立在承认世界的本质是永恒绵延的“真情之流”这一前提下。这一前提在朱谦之的理论中却是无法论证的,只能诉诸选择相信,因而他不得不祭出泛神论,强调“信”的重要性。然而,从发生学上来说,这一前提的有效性来源于朱谦之个人体验与柏格森学说的结合,这就使得他的整套解说带上一种独断论的色彩:迫使人相信由他个人体悟而来的前提就是真理。由此可见,正是朱谦之身上极度自信的英雄主义特质,让其自信地认为其所悟就是宇宙真理,就是数千年来孔门与《周易》的真谛,这使得他对《周易》的言说带上了极强的个人化色彩。
四、《周易哲学》言说方式的现代性阐释
上文对朱谦之在《周易哲学》中对《周易》的言说与阐释方式及其所依赖的前理解进行了分析,而此时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朱谦之的这种阐释方式意义何在?朱谦之的《周易哲学》发表不久,就遭到了不少质疑。即便是现代的研究者,对朱氏五四时期宣扬唯情论的几部著作也有所保留。国内较早研究朱谦之的学者张国义就如此评价朱氏的虚无主义:“朱谦之的虚无主义来源芜杂,佛老是根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是其思想方法。但客观来讲,他对佛老都没有精深研究,只是书读的多,人聪明,将几种思想比附,拿来便能为我所用,并不很严谨,如将黑格尔与老子附会,佛老与无政府主义糅合,如柏格森生命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结合而成的‘流行进化说’”[15]。此处虽是评价其虚无主义,但“流行进化说”被朱谦之继承并用来对《周易》进行解读,故用词语评价朱氏的《周易哲学》也大体无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朱谦之在其《周易哲学》中对《周易》的阐释与言说?
或许借助罗兰·巴特的“文本”概念,我们更能体会到朱谦之言说方式的价值与意义。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提出区别于“作品”的“文本”概念:“文本应不再被视为一种确定的客体……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可能就是‘某种文本’,而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则可能根本不是文本。它们的区别如下:作品是感性的,拥有部分书的空间(如存在于图书馆中);另一方面,文本则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16]巴特将文本视作接近于能指的不确定客体,与作品不同,它的意义不是固定的,由此取消了作者对于文本的权威,文本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其含意与作者间有着稳固不可动摇关系的存在物。巴特认为,文本是复数的,是其自身与其他文本的交织物。这种复数不是多种意义的共存,而是一种过程,一种扩大,一种撒播,它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复合体。文本像语言一样,虽有结构但抛弃了中心,是一种没有终结的动态过程。从巴特的文本理论来看,我们可以说朱谦之的做法是将《周易哲学》视为一种“文本”,由此那些以不合原义为理据的批评就丧失了立场上的有效性。既然文本的意义是其自身与其他文本的交织物,那么朱谦之汇合历代注疏解释周易,在一个庞大的儒家经典系统中,搬用其他文本为其解读《周易》服务,就不再是“强制阐释”和“空谈义理”,而在文本的性质上具有一种意在笔先的合法性了。
巴特否认作品是一个有中心和固定意涵的结构,取消作者权威,高呼“作者已死”,这就为读者进入文本留下了空间。朱谦之的《周易哲学》是对《周易》一书的解读,因而我们可以把他写作《周易哲学》的过程视为阅读《周易》的过程。如前所述,朱谦之的《周易哲学》肇源于其人生观危机,是为其解决人生观危机服务的。他对其人生观危机的反思,如强调信、强调世界的真实无妄、否认理性而突出直觉,都被他带进对《周易》的解读中,这一做法可在巴特的文本理论中找到合法性。从朱谦之对《周易》的阅读与言说过程而言,他正是不自觉地将《周易》视为文本,因而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其前理解与人生观危机带来的体悟融入《周易》之中,而不过于顾忌所谓的“原义”。承认朱谦之的主观目的仍然带有一层复归原义的色彩,否则也不会声称是证得孔家真义,但从其客观的解读与言说方式来看,他在阅读与言说中恰恰是抛弃了真义的包袱,而将文本架空,使其主观体验与历代注疏畅通无阻地进入其中。
同时,所谓的“前理解”与作者前在的意识形态,很难与文本进行一个严格的区分。就朱谦之而言,他如上体悟的发生,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对《周易》的阅读也非突发奇想与临时的,而是长期的翻阅与积累。即便是在促使他人生观转变的被囚禁期间,他亦是带着《周易》到狱中阅读,并写作《周易哲学》。因而我们很难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诘难去追问:是先有对人生观的反思才带着反思去阅读《周易》,还是在阅读《周易》时获得反思而发生了人生观的转变?此处或许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更能解释这一阅读与写作发生的过程,即朱谦之的反思是在主体与文本的交互性关系中产生的,反思与阅读是交互的,相互促进的。《周易哲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朱谦之长期对《周易》一书的阅读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长时段中,朱谦之的生活体验与阅读反思很难严格地区别开来,而常常是在日常体验中获得阅读的前理解,而在阅读中又不断引证、修正对生活的体验与反思。
五、朱谦之《周易哲学》的历史意义
朱谦之对《周易》的这一言说方式,使他在对待《周易》一书的立场上有别于近代其他《周易》研究者。近代易学的发展,大致有三条脉络,其一是杭新斋、尚秉和、章太炎等沿用传统易学的路径又有所创新,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易学史上的经典问题,如名与象、易与数、道与气、易经的版本、经与传的成书年代及关系等等,但运用了一些新晋的方法与视角。如章太炎用唯物史观解释卦名,依“六经皆史”的观点将卦名串联成原始社会的演进史。其二是顾颉刚的古史辩派,他们打破《周易》的神圣地位,质疑《周易》及其他儒家经典所塑造的贤王圣业的历史叙述,将《周易》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研究。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周易》视作反映上古社会的史料,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其中反映的早期社会形态。其三是对《周易》进行哲学化研究,或是将其作为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早期材料,或是将其作为材料纳入自己的新儒学体系中。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借《周易》的生生思想阐发其以“意欲”为核心进化的宇宙观,熊十力借《周易》建构其新唯识论,“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17]
朱谦之的《周易哲学》表面上看是从属于对《周易》进行哲学化研究的脉络,但仔细比对又不然。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借《周易》阐发其新理论,背后的关怀是以此解决“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正如梁漱溟所说:“我早期的思想,是受中国问题的刺激。”[18](P130)他们是在意识到西方理性主义带来的危机后,借西方对自身理性主义的质疑,为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争得可能的空间。他们的逻辑是:既然西方的理性出了问题,那么,作为拥有大量非理性资源的中国文化,显然能补蔽西方的缺陷,由此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从而争得中国文化的生存权与话语权,他们学术关怀的背后是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但朱谦之阐发《周易》,并未表露出过于明显的这一意识。对他而言,无论是中国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思想,都只是其思考解决人生观问题的资源。对此,他在《东西文化一元论》中讲得很直白:“本来全宇宙是一整个,所以东方西方,同是这个心,同是走一条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9](P465)他并不想比较中西的优劣,也不想用谁来补救谁。对他而言,他只想追逐最终的真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思想,都只是他追逐真理所依托的工具罢了。他相信他所求得的真理是普世的,因而所有提示这一真理的材料都被视为一种迫近真理或揭示真相的文本被使用,不需要区分中西。对他而言,阐发《周易》,写作《周易》哲学,只是因为该书揭示了他所认为的真理,而并无拯救中国文化的包袱。相较而言,在对《周易》进行哲学化阐释的脉络中,新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是一种带有中国文化本位的阐释,而朱谦之则是为了解决人生观危机,并由于他推己及人的自信,转化为建构一种普遍的真理。
朱谦之《周易哲学》的意义,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待。从主观上而言,他是想解决人生观危机,同时,他又是在建构一种普遍性的理论;从他的主观目的来说,他是将《周易》视为作品而非文本。但从客观而言,朱谦之的言说与阐释方式,实际上又是将《周易》视为文本,并无意中建构了一个中西得以对话的空间。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指出,文明的对话需要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具体形态的语言,而是“某种事物成了冲突双方共有的东西”[19]这种共同的东西,是构成共同话题的普遍的“体验形式”与“生命形式”。而朱谦之的《周易哲学》,则是在无意中利用这种共同语言——对理性的质疑——实现了一次近代易学史上中西的交融。理性造成的危机,虽然在学理与具体表现形态上中西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宏观的体验形式,它构成了中西对话的空间。朱谦之在《周易哲学》中把中西间各自质疑理性的资源汇合起来,构筑起一个非理性的唯情论,使得柏格森的思想借助质疑理性这一共同话题进入中国的传统文本《周易》之中,从而产生出一个以《周易哲学》为基的唯情论。
将非理性作为中西对话的资源,并非朱谦之一人的做法,而是五四时期被划为玄学派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诸人的共同做法。但新儒家诸人,是把西方自身内部的质疑视为西方现代对其传统主流的否定,并借西方现代的否定为中国文化寻得未来的合法性,其核心并非巩固这种共同的话题,而是将共同的话题视为中国主流传统与西方主流传统间的差异。朱谦之则不然,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历史上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派别,因而他并不想将非理性视为中国或现代西方与传统西方之间的区别,而是将其视作真理与非真理的区别。他说:“因为生命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凡走上生命的路的学说,通是对的,那不走上生命的坦坦大道的,至少都有些偏见。就东方西方的文化当中,自都不免有人走偏见的路的学者,或者有他偏见地方,也自有他独到的地方。”[9](P466)由此避免了狭隘的中西高下之争,而把视域与目标转回真理上来,这正是朱谦之在近代易学史上所做的独到贡献。
《周易哲学》里中西对话的实现,首先依赖于朱谦之在对《周易》的阅读与言说过程中,将其处理为一个空心化的文本,而非固定且实心的作品,这就给历代注疏与西方资源的进入留下了空间。其次,朱氏解决人生观危机的初衷,以及这一初衷与其个人英雄主义气质的混合,使其无意中成为了一种建构普遍理论的行为或不自觉的关怀。正是这一不自觉的关怀与行为,使其不局限于狭隘的中西之争,不屑于去讨论中西孰是孰非、谁优谁劣的问题,而将目光集中于获得宇宙唯一的真理。正是这一气魄使其自觉且在主观上无碍地自由使用中西方资源,使得各种思想得以在《周易哲学》中汇合、碰撞。最后,正是朱谦之对理性的反思,使得他所调动的中西方非理性资源得以在《周易哲学》一书中相遇相合,为后世讨论中西间的相似性与区别留下了丰富的思路与样本资源,并取得了一个汇合中西资源建构普遍理论的朱谦之方案:依托于《周易哲学》的唯情论。
综上所述,朱谦之出于个人的人生观危机,对《周易》进行了一种以解决个人危机为目的的创新性阐释,这一阐释立足于一个历时性的阐释系统,并引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由于朱谦之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他将解决个人危机而提出的方案推己及人为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在这一逻辑之下,其对《周易》的解读,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在这种普遍性理论的建构中,中西文化得以在一个共同话题中相互融会,这种融会又因建构普遍理论的关怀,区别于近现代新儒家。文本、对话、普遍理论三者,成为朱谦之《周易哲学》在近代易学史上的区别性特征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