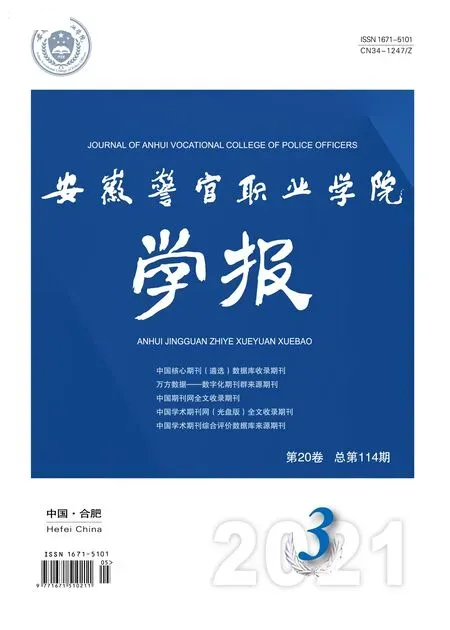疫情防控下监狱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与破解
陈世定
(四川省雷马屏监狱,四川 峨眉山 614200)
新冠肺炎疫情安全风险属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前所未有地严峻考验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而坚持依法防控显得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1]实际上,监狱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缺失和供给不足的问题,确实值得思考研究。
一、监狱面临的有关法律问题
(一)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上国家赔偿问题
由于监管安全风险和疫情安全风险双重叠加,监狱组织及民警面临的法律风险与责任更大。监狱组织及民警如果防控不力或存在失职渎职,对罪犯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不力,除承担政治责任风险外,势必面临法律责任风险。
这场重大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验着国家和监狱对罪犯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等基本权利的保障能力。监狱是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的特殊场所,具有高度封闭、人员密集的特点,一旦发生重大疫情,产生的风险很大,传染很快,且难以及时予以控制,这势必严重危及罪犯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这次重大疫情具有前所未有的严重危害性,使得罪犯存在思想认知的严重不足和产生出很大的心理恐慌及不良的情绪反映等问题。
面对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风险的危害和影响,一旦罪犯或其亲属提出控告监狱及民警存在因救治不力、失职怠职的情况,监狱组织及民警会因失职或没有履职给予及时救治而受到国家赔偿法律责任追究,包括对直接责任民警追偿在内的法律责任风险。
(二)在收监、释放环节上面临的法律问题
1.收监环节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交付机关(看守所)存在超期羁押罪犯问题,存在对罪犯实行隔离观察或治疗延期,而不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正常时间和程序将罪犯送押到监狱改造;同时,长时间累积后的罪犯人数变多送押到监狱,会形成很大收押压力和产生更多的风险。如果看守所送押到监狱来的罪犯存在发烧情况,监狱方面考虑到疫情安全风险的影响,则会不予收押;同时,监狱在收押中,可能会存在看守所对罪犯检测不准确或不到位的情况,而给监狱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危机和关押改造压力。然而,针对重大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如何办?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包括其中的责任风险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2.释放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当刑满释放人员还处于患病感染状态中,如何对其进行有效隔离和治疗,同时应由哪个机关负责强制隔离,是由监狱或监狱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决定、公安机关执行,还是由刑满释放人员居住地或原籍地的政府机关决定、公安机关执行,这在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如果是由监狱机关负责执行强制隔离,则存在近似于继续执行刑罚的嫌疑,而在法律上无任何依据,因此不可行。而监狱是否有权对刑满释放罪犯实行强制性隔离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如果由罪犯服刑的监狱所在地的司法局安置帮教办牵头,负责落实隔离与治疗方面工作,而安置帮教办属于行政部门,行使的是行政权,如对刑满释放人员实行强制隔离,这在法律上也没有依据,而且一旦人员不配合,则没有其他办法,甚至如果发生逃离或死亡问题,这涉及到责任由谁负的问题;同时,这还涉及到隔离与治疗的费用由谁支付的问题,如由刑满释放人员支付,会存在支付困难,也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对没有染新冠肺炎病的刑满释放人员,如果由监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负责实行隔离观察,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无染病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不够任何治安处分或刑事处罚。
监狱对刑满释放人员实行隔离14天后放行,起初司法部下文是这样要求的,但在执行中受到了检察机关认为不合法的质疑,由于刑满释放人员已是自由公民,法律上没有授权监狱对其实行强制性医学隔离;于是,改为由监狱报告监狱所在地的卫健委负责这项工作,但卫健委认为司法部的文件是单方决定,没有与国家卫健委一起发文,存在执行效力不够。
目前的主要做法是,由监狱负责组织刑满释放人员进行体温和核酸检测,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一是对没有疫病的人员,针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方式放行,其中,对评估为改造上的重点人员或有较大社会风险的人员,通过协调对接工作,由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送到其户籍地或居住地县级安置帮教办;对一般人员,联系其家属前来接回。二是对患新冠肺炎的人员,由监狱报告监狱所在地的卫健委,由卫健委负责采取医学隔离和治疗与观察。这里的问题在于:刑满释放人员是自由公民了,而法律没有赋权监狱可以继续控制其行为自由或加以管制,否则,监狱作为就是违法行为;而且一旦刑满释放人员不配合甚至抗拒接受检测和医学隔离观察,还会产生一些连带问题和不良后果。
(三)在与地方政府机关协调联动上存在的法律问题
关于监狱与地方政府机关之间的协调联动问题,这虽然有的单位之间已经建立,但是没有保持常态化联动。根据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应急管理体制是“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监狱机关与地方机关部门在重大疫情风险防控安全的协调联动上,监狱疫情防控自然应归入所在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统一管理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存在对接协调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顶层制度设计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制度文件或法律法规的强制的执行性规定;二是管理体制基本上,监狱属于省管体制,而与地方机关部门存在协调对接的难处,在公共卫生、生产安全等方面都特别的突出。
因此,虽然我们经历了如2003年“非典”这类重大社会范围的疫情事件,仍然没有高度重视而形成制度化的联防联控机制。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属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事件,首先就武汉女子监狱、山东任城监狱等而言,他们实在有些措手无策,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机制体系上存在不足和很多问题,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比如,在“14+14+14”执勤模式上,监狱请求地方政府机关提供民警安全隔离场所(点),经过多方沟通协调,费了不少的周折;在疫情信息数据报送体系上,当初,由于从管理体制上看监狱属于省管单位,也没有直接纳入当地社会报送体系。这些表明,监狱在管理体制上的不同造成了与地方社会的对接和融入不够。
二、破解思路
(一)加强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在重大疫情突发的紧急情况下,对监狱面临的法律问题,应做好顶层设计,才能做到依法防控防治。具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中央政法委作出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卫健委等可根据情况联合发文。针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国家应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监狱法》等有关法律制度上,明确将监狱面临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非传统安全纳入社会安全治理体系,明确地方政府机关与监狱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联防联控中的责任和义务,以舒解工作的艰难。
基于监狱是非常特殊的场所,面对发生地震、火灾等重大灾害事故和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政法委及时下文,指导和规范政府机关及部门、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对疫情的联防联控联动,同时,明确将监狱疫情纳入所在地方的医疗防控应急体系,包括医疗防护物资的常态化储备保障体系。因此,必须尽快建立监狱纳入所在地方的对接联动一体化体系,实现协调推进、合作会商、应急处置救援、物资保障、信息资源共享的工作机制。
(二)正确认识把握法律责任
1.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只要监狱组织或民警完全合理合法地积极尽到了履行义务,及时救治罪犯,没有故意或恶意隐瞒疫情或染病事实,或没有拖延或放弃救治的失职渎职行为等,则不应追究监狱组织及民警的刑事责任。当然,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党纪政纪处分。因为监狱民警不具专业医生水平,况且新冠疫情前所未有、甚至超出了专业医生的认知水平,在疫情发生后也不能深刻预见这种疫病的严重危害性和传染方式,因此,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鲁兰律师认为:不应以法律上过失犯罪的“疏忽大意”、“过于自信未能预见”的认定要件予以判罪定刑。①引自2020年3月9日在“为你辩护网”上的撰文《监狱民警疫情期间执法刑事风险详解》。对于民警虽然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某些新冠肺炎感染症状,但是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相关诊断结论、检验报告的,根据2020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能认定为其中规定的“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也就是说,事后经过诊断、检验,为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的,不适用《意见》关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构成有关犯罪的规定。[3]当然,如果是民警因主观故意而恶意传播病毒的情形,则其应承担法律责任。
2.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看,如果监狱组织及民警明知已存在具有极大危害性的事件,而故意隐瞒或放任不管或心存侥幸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如果是需要隔离治疗、观察,而强行抗拒或存在逃离情况而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么,就属于主观积极作为发生的侵权行为,则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受到应有的制裁。
3.深刻理解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监狱机关发生的国家赔偿属于刑事赔偿类型,该法将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所发生的赔偿责任,刑事赔偿是指侦查、检察、审判权的机关和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所发生的赔偿责任。2010年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款情形明确:“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刑讯逼供或者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赔偿义务机关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足以证明合法合理尽职履责,则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第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无过错、赔偿义务机关行为与被羁押人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赔偿义务机关过错致使赔偿请求人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由赔偿义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从上述《国家赔偿法》的内容看,该法第17条第4款情形的规定,一方面,从直接表述看,刑讯逼供或者殴打、虐待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行为,属于暴力执法行为,并且此种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法律后果;其中,“放纵”行为是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中增加的内容,201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有关问题的调研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中对“放纵”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做了具体化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具有制止殴打、虐待等行为条件的情况下,明知殴打、虐待等行为已经发生,但不予理睬、听之任之,严重不负责任,放任甚至追求损害后果发生或者加重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放纵情形,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关于其中的“等”字,而法律上的“等”字包括“等内等”和“等外等”两种情况,“等内等”表示列举事项完毕的煞尾,明确了法律规定的边界,“等外等”表示列举未尽,还包括其他的。然而,《国家赔偿法》中的“等”字,属于“等内等”还是属于“等外等”,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其实,按照《监狱法》第7条规定,为保障罪犯合法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法律对监狱组织及民警执法管理中所禁止的行为,肯定不限于前述的暴力行为,应包括未列举完的造成罪犯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失职、渎职行为,即“等外等”,其包括:对艾滋病、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管控的失职、渎职行为,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的行为。因此,对明知已存在具有极大危害性的重大疫病,而故意隐瞒或放任不管或心存侥幸所造成严重后果的;对需要隔离治疗、观察,而强行抗拒或存在逃离情况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因消极不作为、过失等怠于履职情形或没有履行好隔离观察和救治义务而造成罪犯感染上传染性疾病严重后果的,监狱组织或民警应承担法律上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10月16日对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中([2012]赔他字第3号),明确了怠于履职情形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其对“等行为”是做的“等外等”解释,即:当认定监狱对生病罪犯未尽到及时救治义务,并与罪犯死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则属于怠于履职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综合考虑怠于履职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比例和数额;前述《会议纪要》第3条第3款明确:“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罪犯之间殴打、虐待等行为发生时,存在人员脱岗、工具失管等怠于履行职责情形,或者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存在其他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形,且以上情形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具有一定关联的,应当综合考虑该情形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适当考虑国家赔偿的比例和数额”。
同时,监狱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能有力证明自己无责任,则应承担刑事赔偿责任;当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第6条规定,只要监狱机关举证足以证明做到了合法合理的尽职履责,则不必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三)明确监狱及民警在收监和释放环节上的法律责任
在收监环节。对看守所超期羁押与监狱之间的沟通协调对接问题,在疫情期间,看守所存在关押容量受限,加之先行医学隔离,必然累积的罪犯数量较大,形成巨大监管压力和疫情压力;监狱由于担心疫情期间收押罪犯可能存在潜在疫病风险,或监狱发生了严重疫病而无法及时收押,那么,要按照法律制度安排,顺利搞好协调对接工作。
在释放环节。依照法律规定,罪犯刑满应当按期释放,而对患病的刑满释放人员,由谁实行隔离治疗和控制,需要法律上予以明确。从《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和第78条的规定看,对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是取得执业认证的医疗机构。由此看,获得执业认证的监狱医疗机构属于合法实施主体,具有采取隔离治疗和控制的责任;对于当刑满释放人员仍处患疫病时,如由监狱医院负责隔离治疗和控制,则需在法律上或司法解释上加以明确。
为确保监狱和社会安全,监狱组织对没有疫病的民警实行有效医学隔离,这种管理属于单位内部的行政管理性质。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看,为防止狱内可能将潜在的疫病带入社会造成风险,对刑满释放人员包括查处患有新冠肺炎的或没有查出患病的实行安全有效医学隔离,法律制度上应规定由监狱向监狱所在地的卫生行政主管机关报告,由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决定隔离治疗和观察,如果刑满释放人员不配合,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由监狱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协助,予以行政强制隔离治疗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