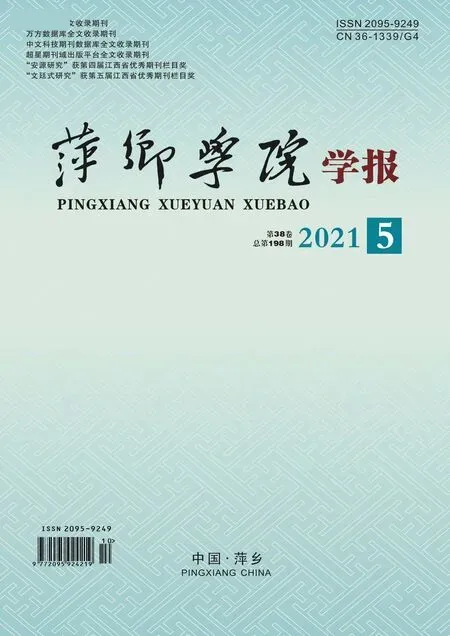康德定言命令公式的建构主义修正性阐释
唐思浩
康德定言命令公式的建构主义修正性阐释
唐思浩
(西北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罗尔斯基于社会正义理论对康德的定言命令诸公式作出了建构主义阐释,但这一阐释将面临与康德一样的诘难。近来,国内学者李科政从“严格的方法”“无知之幕的限定”两个方面修正了罗尔斯这一建构程序。但这些修正并不完全是一种康德式的,其中会产生诸多新的质疑。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建构主义阐释,该阐释一方面主张普遍法则公式包含在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之中,它在建构程序中是用于保证符合法则的准则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强调自律公式是作为自我立法的普遍法则公式,它限制了普遍法则公式道德价值的来源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外在对象。
定言命令程序;道德法则;建构主义
罗尔斯(J. Rawls)“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正义理论与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已经做过非常多的讨论,以至于本文在这方面的任何添砖加瓦都显得是陈词滥调。但罗尔斯为了构建自己的正义原则,而对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进行的建构主义阐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其中有很多的问题关系到对康德哲学主旨的理解,非常值得讨论。本文首先对罗尔斯建构程序的论证进行重构,并特别探讨该程序面临的可能的诘难;然后考察一种新的修正的视角,说明其并不完全是一种康德式的建构,其中会产生许多新的质疑;最后根据两者所遇到的问题,本文给出了一种较为合理的康德式建构主义的构建思路。
一、罗尔斯对“康德定言命令程序”的建构:CI程序
罗尔斯本人承认,关于道德建构主义的阐释,并非他本人的创见,而是他对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作出的新阐释。但他同时认为,康德建构主义的道德观念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正义原则。本文将依据罗尔斯相关的主要论文和讲演录对他的建构主义诠释进行重构,无意于讨论这个建构程序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关系与渊源。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清晰地展现罗尔斯的建构程序,讨论他遇到的与康德相似的诘难。
在讨论罗尔斯的建构程序之前,罗尔斯提醒我们,一个独特的人的观念(Conception of the person)就是建构程序中理想的道德行动者(Ideal moral agents)。道德行动者具有“理性的(Reasonable)”和“合情理的(Rational)”这两种道德能力。他们也分别对应康德哲学的两种实践理性的形式——纯粹的实践理性和一般(经验)的实践理性。由于有理性的道德能力,人们可以期待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理性地选择普遍的、一致同意的条款[1],因为它具有互惠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对应着定言命令;而对于合情理的道德能力,罗尔斯一般从工具论意义上来理解,它对应着假言命令,是按照适当的规则谋取自身利益的能力。罗尔斯认为,康德的理性概念一旦表现在人的身上,这两种道德能力是都具有的。接下来的建构程序就是这个理想的道德行动者根据自己理性能力对自己的准则作出取舍的过程。
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罗尔斯对其定言命令公式的建构主义诠释作了详细的介绍。罗尔斯首先对道德法则、定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程序三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命令式只是表达一般意欲的客观法则与这个或那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例如与一个属人的意志的主观不完善性之关系的公式。”[2]32由于属神的意志是完全善良的意志,他符合道德法则是不表现为被强制的,因此不适用于命令式。但是,由于有限的有理性存在者除了受理性的规定之外,还受感性欲望的牵制,这样将道德法则作为对感性经验的限制就表现为命令。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德法则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而定言命令则仅适用于有限的有理性存在者。
在区分了两者之后,罗尔斯就进入到了关于定言命令程序的讨论,罗尔斯把它称为四个步骤的CI程序(The Four-Step CI-Procedure)。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的这个程序是依据定言命令的第一个公式进行建构的①。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要将主观的准则上升为客观的普遍法则,或者说用以检测主观准则的道德价值。该程序的第一步是“合理而理性的”的人,作为诚实的道德行动者,按照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提出一条行动准则。他的标准形式是:“(1)在C条件下,为了产生Y,除非Z,我想要做X。”[3]227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要将这条准则普遍化,如果这个准则能够普遍化,即普遍化之后不会自我取消,那么就能上升为一条客观的实践法则。于是,准则便被表述为:“(2)在C条件下,为了产生Y,除非Z,每个人都想要做X。”[3]228罗尔斯在第三个步骤中将这条实践法则进行自然法则的类比,将普遍的法则转换为一条自然法则:“(3)在C条件下,为了产生Y,除非Z,好像遵守自然法则一样(好像这个规律是通过自然本能根植于我们身上的),每个人都想要做X。”[3]228通过这种类比和转换,在第四步中,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自然秩序,“(4)我们将把步骤(3)中的‘好像’自然法则与现行自然法则结合起来(因为这些法则已经为我们所理解),一旦这种新结合到一起的自然法则有了充分时间发挥作用,我们便尽最大努力来揭示自然秩序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3]229罗尔斯将这一新的自然秩序称为“调整过的社会”(Adjusted social world),当人们作为被调整的社会成员并在其中行动,那么就能按照自己的那个准则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合理而理性的人”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某个准则,同时通过定言命令的程序对这个准则进行限制,将那些主观的目的、欲望进行排除,对那些基于主观目的的准则进行否定,采纳那些能够通过普遍化检测的准则。这样一来,经过建构程序而得出的道德法则就具有了普遍性。通过这一建构程序,行动的道德性就在其中体现出来了,或者说通过定言命令的程序被建构出来了。
但是这样一个建构程序最后所得出的“调整过的社会”,始终是围绕自然法则公式进行的。那么,通过第一个公式所建构的定言命令程序就将面临与康德一样的质疑。这种质疑最初在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被提到:“于是,就在这里,再明确不过地宣布了,道德责任是纯粹而且完全地建立在预先假定的互换利益上的;因此它是完全自私的,只能以利己主义解释。”[4]这也就是说,这一程序所建构出来的道德法则中隐蔽着一种利己主义的自爱原则,实际上也是假言的。李科政敏锐地指出:“这种诠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既然它把‘自然法则’概念用作采纳法则的标准,那么,定言命令的普遍有效性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普遍有效性。”[5]
正是出于想要避免这样可能的诘难,罗尔斯给出了这个建构程序所包含的两个限制条件。这两个限制条件是基于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提出来的。“第一个限制是,我们将忽视人们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比较特殊的特点,将忽视他们的和我们的最终目的和欲望的特殊内容”[3]237;“第二个限制是,当我们问自己,我们究竟能否想要与我们的行为准则相联系的调整过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将以似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那个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来推脱。”[3]238这两个限制条件使得理想的道德行动者处于“无知之幕”背后,不知道自己的特殊目的和欲望的特殊内容,也不知道在通过定言命令程序进行调整过后的社会中,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来,这个道德行动者就受到了限制,他不会基于纯粹主观的特殊情感和欲望来选择某种合乎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准则,同时也由于对自己未来社会地位的无知,会全面地、理性地考虑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这两个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质疑。
二、一种被修正的建构程序:定言命令公式的联合运用
罗尔斯对康德定言命令的建构主义诠释,经过一些研究者,如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奥尼尔(Onora O’Neill)等反复运用与不断发展,在学界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解读。科斯嘉德认为,“我们人类创造了价值,我们发现某条准则适合于成为法则,并且同时愿意它成为法则,那么它才能成为一条法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创造了结果的价值”[6],因而,价值是由为我们自身立法的程序建构出来的②。有研究者甚至将科斯嘉德的建构主义看作是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7]。奥尼尔则认为“康德的策略是对理性的权威作一个建构主义的解释,理性的最高原则只不过是一种准则或策略,即避免那些基于不可能被所有潜在的行动者所采纳、而不管它们可变特征是如何的原则而行动和思考”[8]。但是不论这种建构主义呈现出什么形态,罗尔斯在这一诠释中,显然没有按照康德式的进路进行讨论,而是选择对“无知之幕”的两个限制条件作经验性描述。罗尔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我国学者李科政给出了两点原因:其一是由于罗尔斯对定言命令公式有着严重的误解,即将定言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和自然法则公式看作是同一公式,这就必然导致上述诘难,因而罗尔斯要选择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其二是由于康德的定言命令公式对于其社会正义理论来说太过严苛,关于社会正义原则的推理不同于个人的道德法则,它必须考虑某些经验性的条件[5]。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李科政认为必须要对罗尔斯的建构程序作出修正,使其成为一种康德式的诠释。
他首先指出罗尔斯对定言命令的误解,从而修正了罗尔斯建构程序中的“严格的方法”。李科政认为罗尔斯将自然法则公式作为“严格的方法”而成为建构程序的依据是基于对定言命令公式关系的一个严重误解。李科政认为,定言命令公式一共有四条,必须将普遍法则公式与自然法则公式严格区分开来,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普遍法则公式“没有援引任何经验性的概念来充当采纳法则的标准”[5]135,而自然法则公式通过自然法则这个经验性的概念让定言命令更为直观和接近情感。李科政看到,除了普遍法则公式,其他的定言命令公式都可能会被误解。自然法则公式由于采取了一种自然法则的方式理解道德法则,因而会导致一种自然普遍性的误解;目的公式如果不加限定,就有可能为特殊的外在对象所规定;自律公式中的立法者也有可能被误解为一个立法的“独裁者”。因此,在这个修正的建构程序中,普遍法则公式毋庸置疑地作为“严格的方法”而成为整个建构程序得以可能的中心公式,这个建构程序是依据普遍法则公式来建构的。现在,由于普遍法则公式没有援引任何经验性的概念,因而在这个建构程序中,法则的普遍性绝不可能被视为自然的普遍有效性,因为这里根本不要求有自然法则公式的参与。
李科政进而指出,普遍法则公式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性的概念,其普遍化的根据仅仅依据“愿意”就能成为可能,因此,他根本无须任何限制就能保证自身的普遍性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普遍性,而不是基于自然法则的普遍性。他将普遍法则公式作为“严格的方法”构建定言命令程序,而其他三条具有经验性概念的附属公式均不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关系,即“目的公式限制了我们对自然法则公式的理解”[5],“意志立法公式限制了我们对前两条公式的理解”[5]。目的公式告诉我们始终要将自己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视为目的,这样一来,自然法则公式就不会产生一种“利己主义”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具有互惠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要求人是目的。自律公式提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2]52这一理念,这就使得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的立法者不是任何外在于自己的对象,而是自我的立法。概言之,自律公式确保了一切法则都是出于自律。
李科政的建构主义诠释有两个要点:1)必须将定言命令的总公式和附属公式严格区分开来;2)附属公式不能独立地进行理解,必须是一种联合应用。这两个要点构成这种修正版的建构主义的全部核心要素。诚然,这种建构主义阐释能有效避免一种康德式的诘难,但是这种建构程序并不完全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康德式诠释,其中存在与康德伦理学基本要旨相违背的缺陷,会产生许多新的质疑。
首先,在这种建构程序中,始终将定言命令诸公式视为分析的,即有一个总公式——普遍法则公式,其他三个附属公式是从这个总公式中分析得出的。这样的做法就理所应当地导致普遍法则公式成为最重要、最严格的命令式,就这一点来说,是与康德的思想相违背的。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后文称《奠基》)的文本叙述来看,绝不能否认自律公式是比普遍法则公式更为严格的定言命令。在《奠基》中,我们看到康德将自律原则作为“唯一的道德原则”,“定言命令式所要求的不多不少,恰恰是自律”[2]63。实际上,在康德哲学中,自律的意志是唯一能独立于自然因果性的一种原因性,只有从这种原因性中,我们才能看出人作为有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而自由作为康德“纯粹理性,甚至思辨理性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9],是康德哲学的最终诉求。因而自律公式必然要成为定言命令公式中最重要、最严格的公式。李科政却忽视了康德这一重要的论述,反而将自律原则看作一种经验性概念,仅仅是联合应用中的一个要素。我们且不说,在康德哲学中,自律的意志和自由的意志是一回事,绝不允许自律成为一个经验性概念。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果将普遍法则公式作为定言命令最严格的公式,那么自由完全不能通过这一公式而被认识到的。因此康德“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9]就成了一句空话。李科政始终简单地将意志自律作为一个经验性概念,而使其作为一个主观性理解的限制,这实际上是与康德思想相违背的。
其次,我们看到李科政将普遍法则公式与其他附属公式分开,单独将普遍法则公式作为严格的方法而进行定言命令程序的构建,这样一来,附属公式在康德定言命令公式中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定言命令程序的构建实质上无关乎附属公式,这个建构程序只要通过普遍法则公式就是可能的。这样,其实定言命令的联合应用也是不必要的。这个建构程序单通过普遍法则公式就能检测出在某种条件下的准则是否可以被普遍化,因而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所以,联合运用在这个建构程序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看到,李科政主张定言命令公式有一种分析关系,即普遍法则公式是定言命令的总公式,其他公式是附属公式。但是通过他“定言命令公式的联合应用”,我们并没有发现附属公式是如何从普遍法则公式中分析出来的。实际上,这种解读一方面主张有一种分析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将普遍法则公式和其他附属公式的关系割裂了。因此,李科政的这种修正的建构程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一种康德式的诘难,但是并不是一种康德式的诠释,甚至与康德的思想相冲突。
三、一种新的思路:保证与限制的协同构建
虽然这些建构主义的诠释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是这并不是说一种建构主义的诠释不可能,只要对这种建构程序的诸要素进行必要的修正,一种康德式的定言命令建构主义诠释是可以成立的。
首先要指明我们这种建构程序的两个目标:其一,与罗尔斯建构程序的最初目标一样,是要保证这个建构程序的道德价值,或者说通过对该建构程序的描述和论证,展现定言命令道德价值的来源;其二,这种建构程序还希望通过这一程序中定言命令的不同形态,说明这个建构程序还构建了定言命令公式在有限的有理性存在者那里的形态。本文采取一种“保证与限制”协同构建的思路。在这个建构程序中,也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普遍法则公式具有道德价值的保证作用;其二是自律公式的限制作用。第一点是本文对“严格的方法”的修正;第二点表现为对“限制”的修正。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两个要点进行详细地阐述。
本文认同李科政的观点,将普遍法则公式视为建构程序中的“严格的方法”,但其作用却不是为了检测准则的道德价值③,而是用于保证符合该条公式的准则的道德价值。那么,普遍法则公式是如何保证其他定言命令公式的道德价值的呢?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具体考察一下普遍法则公式的内涵。康德首先确认“定言命令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只要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2]40在这条命令中,有三个关键细节:第一,“能够”和“愿意”是这条法则的重要内容。但鉴于它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不对其进行详细考察。第二,这里说“定言命令式只有一个”,并不是说后文中所提到的命令就不是定言的,而是明确地指出定言命令的本质规定。“只有一个”仅仅表达的是,具有普遍法则公式特征的命令式都是定言的命令式。第三,“准则成为法则”指出了定言命令的本质规定到底是什么。这种本质规定就在于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形式性。正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在其《康德实践哲学》中所指出的:“在康德看来,道德虽然归根结底是普遍性的东西,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在道德的内容实质中,而是存在于‘应是普遍的’这一法则的形式之中。”[10]因此,这个命令公式虽然指出了什么样的命令式才能是定言的命令式,但是它却仅仅只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形式,是极为抽象的。所以阿利森才会认为:“普遍法则公式仅仅只是在轮廓和形式上的命令概念。在这个概念被应用之前,它必须被充实。”[11]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普遍法则公式是定言命令公式的严格的规定,普遍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但是,普遍法则公式并不像李科政所认为的那样,自身就足以担保其普遍性是纯粹道德的普遍性,而是依然可能被认作他律④。
在此,本文必须回应一种可能的质疑,这种质疑来源于对普遍法则公式作出仅仅普遍化检测理解的研究者。很多研究者认为普遍法则公式只能排除那些不能被普遍化的准则,而有些假言命令也能通过普遍化检测⑤,因此普遍法则公式是有缺陷的,还需要目的公式在行为动机上对普遍法则公式进行限制。因此,这些研究者将质疑本文得出的结论,普遍法则公式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准则都是定言命令式。但是这种看法建立在一种对普遍法则公式的误解之上。本文认为普遍法则公式仅凭借自身就能保证其道德价值,因为通过上文考察普遍法则公式的内涵就会发现:普遍法则公式当中的“法则”本身就是无条件的。并且康德在得出普遍法则公式之前对法则做出的限定就是“法则不包含任何限制自己的条件”[2]40,因此,这条公式凭借自身就是无条件的。它不会允许任何具有普遍性的假言命令的提出。
普遍法则公式是定言命令的最基本的内容,它分析地包含在每一个定言命令公式中,任何定言命令公式都必须以普遍法则公式为基础。它作为“严格的方法”在定言命令程序中并不是用于检测准则的道德性,而是用于保证符合该条命令的准则的道德价值。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必须要以普遍法则公式的预先提出为基础。任何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定言命令的新公式的推导都必须将普遍法则公式包含在自身之中。在《奠基》中,这种新公式的推导思路分为三个步骤,即首先指出一个经验性的概念,然后将这个经验性的概念添加于普遍法则公式之上,最后得出定言命令公式。通过三个步骤的推导,普遍法则公式在其中保证了任何一条命令式都是定言的,因而都具有道德价值。在这里,虽然普遍法则公式本身就具有道德价值,但这却不是像道德法则实在论者说的那样,“唯一根本的和无条件的价值是作为自在目的的理性本性的价值”[12]92,由于人性或者理性本性其存在自身就应具有绝对价值,因此道德价值是客观存在的[12]85–86。在笔者看来,这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在于道德法则实在论者颠倒了康德将理性本性看作具有绝对价值之存在的原因,即不是由于人性或理性本性具有绝对价值,它才成为道德自我立法的根据;而是由于人性和理性本性能够在道德上自我立法,因而才具有绝对无条件的价值。因此,道德价值虽然存在于普遍法则公式当中,但却依然有其来源,这种来源就在于理性本性的道德自我立法的能力。
对于一个无限的神圣存在者,由于他能保证一切道德价值的自我赋予,那么有普遍法则公式就足够了,蒂默曼就指出“道德法则对完善的存在者来说只是描述性的,而并非规定性的”[13]。但是这一道德价值要具有自我赋予的含义,还需要普遍法则公式受到自律公式的限制⑥。因而行动者才理所应当地能被自身规定,正是在这方面,伍德才颇有洞见地指出:“自律公式要求你积极地按照能够将其作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动……这些准则的立法形式使其成为真正的普遍法则。”[14]因而,自律公式也限制了普遍法则公式,将其普遍性视为由自我立法而来的普遍性,而不是自然法则的普遍性,或者一种神意的普遍性。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变化,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是普遍法则公式添加一个经验性概念而提出来的,但是自律公式的推导却与上述两个公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自律公式的推导是通过前面公式的要求而必然地推导出来的,它是定言命令的最终形式和最高限制条件。自律公式是将前两个公式包含在自身之内而推出的最丰富的公式,这个公式其实就是普遍法则公式的自我完善,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的提出是为了使得纯粹形式的普遍法则公式自身获得具体的规定性,普遍法则公式通过这两个公式逐渐丰富自身,意识到自律公式就是自我立法的普遍法则公式[15]。这样一来,普遍法则公式为什么具有道德价值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它通过自律公式说明其本身就是自我立法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所以才能具有道德价值。
我们看到在这个建构程序中,普遍法则公式作为“严格的方法”保证了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的道德价值,自律公式限制了普遍法则公式,规定了其道德价值的来源是出于理性存在者自身。自律公式是由之前的实践原则必然推导出来的,其中不仅包含了普遍法则公式的全部本质特征,而且还包含了自我立法的理念,因而“极为适合成为定言命令”。普遍法则公式只是抽象的形式,仅仅指出定言命令的本质要求,而自律公式通过自然法则公式、目的公式将这种本质要求落实到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身上,因此他对于人类存在者来说,是定言命令的最终形态,是唯一的道德原则。
四、结语
让我们再回到罗尔斯的建构程序,该程序面临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普遍性难题⑦,而罗尔斯对这一建构程序的限制又是经验性的,因而并非是一种康德式的诠释。而李科政的修正倒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康德式的,但是却面对着新的难题,即取消了自律公式至高地位,割裂了总公式和附属公式之间的关系。因此,一种新的对康德定言命令公式进行的建构主义修正性阐释,必须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其一是建构的定言命令的普遍有效性不能像罗尔斯那样,被误解为是自然的普遍有效性;其二是这一建构程序也应该将自律公式的至上地位凸显出来。本文主张普遍法则公式分析地包含在具有经验性概念的自然法则公式和目的公式之中,它在建构程序中不是用于检测道德价值,而是用于保证符合法则的准则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自律公式是自我立法的普遍法则公式,它限制了普遍法则公式道德价值的来源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外在对象。如今,上述问题的解决在这一“保证与限制的协同构建”的新思路中就做到了,这一建构思路避免了罗尔斯那里出现的普遍性难题,因为它根本不以自然法则公式为中心,而是以纯粹形式的普遍法则公式为中心,因而不会遭到此类诘难。再者,正如上文中指出的,这一建构程序将普遍法则公式的本质要求落实到有限的人类存在者身上而形成了自律原则,因而凸显了自律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那里的至上地位,宣示了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本性,由此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样一来,本文就通过对罗尔斯建构程序的两方面修正,即对严格的方法和限制的作用的修正,获得了一个比罗尔斯和李科政的建构程序更为周全的新建构程序。但本文的工作远没有就此结束,这一解读是否能与康德其他文本融贯,是否能解决康德文本中的其他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与研究。
① 罗尔斯对定言命令的理解显然深受帕通(H. J. Paton)的影响,采用一种综合式的解读,即定言命令有三条,其中第一条是普遍法则公式,自然法则公式是这条公式的变形。
② 这种解释的理由在于:“因为我们作为理性行动者拥有这种赋予价值的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成为有价值的理性行动者。”正如范志均指出,“它不仅把一般的道德价值看作是通过程序被建构的,就连人性的无条件价值也看作是被建构的。”具体可参看范志均《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③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康德在普遍法则公式中有一个普遍化检测的过程。而本文认为这种普遍化检测确实存在,但却不是通过普遍法则公式,而是通过自然法则公式进行普遍化检测的,亦即将一个主观准则与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进行类比,从而确定主观准则是否能成为客观的道德法则。而普遍法则公式由于其纯粹性和抽象性,不宜作为普遍性检测的公式。并且要澄清的是:以自然法则公式作为普遍化检测,依然不会存在“自然的普遍有效性”的危险,因为这里所使用的是排除自然法则的直观和一切依赖于直观的内容的合法则性形式。可参看《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模型论”。
④ 在此,请不要将本文的观点误解为普遍法则公式在逻辑上不包含自律公式。本文在这方面认同伍德的系统论的观点,即诸公式构成一个系统,要理解某一个公式,必须从这个系统的角度来理解。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自律公式才能知道普遍法则公式的完整含义。普遍法则公式中所包含的自律属性也只有在其发展为自律公式时,才能显示出来。因此,我们毋宁说自律公式其本身就是普遍法则公式,只是它经过了自然法则、人是目的和自律的充实,是更丰富的普遍法则公式。这也是康德为什么要将自律公式看作是“完备规定”的原因。关于系统论的观点可参看伍德近些年出版的著作Formulas of the Moral Law第74–75页。关于笔者这一对定言命令关系的看法请参看拙文《康德定言命令关系的辩证模式解读》。
⑤ 比如这样的假言命令:为了促进自己的幸福,就必须也让他人幸福。这个命令式显然是假言的。但是它却能通过普遍法则公式的普遍化检测,即每个人也都想意欲这样的准则作为客观的法则。
⑥ 本文不同意李科政“愿意”就能保证普遍法则公式不是任何形式的他律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愿意”的法则也可能是其他外在的特殊存在物的立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我们更愿意自然法则成为我们的行动法则。
⑦ 由于罗尔斯建构程序的问题在于以自然法则公式作为中心公式而建构的定言命令的普遍性极有可能被误解为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这是康德决不允许的。因而本文将这一难题称为“普遍性难题”。
[1] J.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0(9): 528–529.
[2]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M]. 李秋零, 译注.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罗尔斯. 道德哲学史讲义[M]. 张国清,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 叔本华.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 仁立, 孟庆时,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79.
[5] 李科政. 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J]. 道德与文明, 2018(1): 131–137.
[6] 科斯嘉德. 规范性的来源[M]. 杨顺利,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29.
[7] E. Watkins, W. Fitzpatrick. O’Neill and Korsgaar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ormativity[J].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002(36): 359.
[8] O. O’Neil. Constructions of reason: explorations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4.
[9]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2.
[10] 安倍能成. 康德实践哲学[M]. 于凤梧, 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32.
[11] H. Allison. 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M].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4.
[12] A. Wood. Kantian eth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 J. Timmermann.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ommenta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2.
[14] A. Wood. Formulas of the moral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69.
[15] 胡好, 唐思浩. 康德定言命令关系的辩证模式解读[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9(4): 10–17.
A Constructivist Revision of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Formulas
TANG Si-hao
(School of philosoph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730070, China)
Rawls has made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formul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but this sort of interpretation will encounter the same criticism as Kant did. Recently, Chinese scholar Li Kezheng has revised Rawls’ constructivist procedure from two aspects: “the strict method”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veil of ignorance”. But his revisions are not entirely Kantian, which give rise to many new doubts. Therefor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nstructivism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this interpretation advocates that the FUL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 which is used to ensure the moral val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he norms, should be analytically included in the FLN (Formula of the Law of Natural) and the FE (Formula of E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that the FA (Formula of Autonomy) is the FLN to give itself the moral law, which limits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moral value of the FUL is derived from any other form of external object.
CI-Procedure; moral law; constructivism
2021-1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ZX090);甘肃省教育科技创新项目(2021CXZX-307)
唐思浩(1996—),男,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古典哲学。
B516.31
A
2095-9249(2021)05-0018-06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