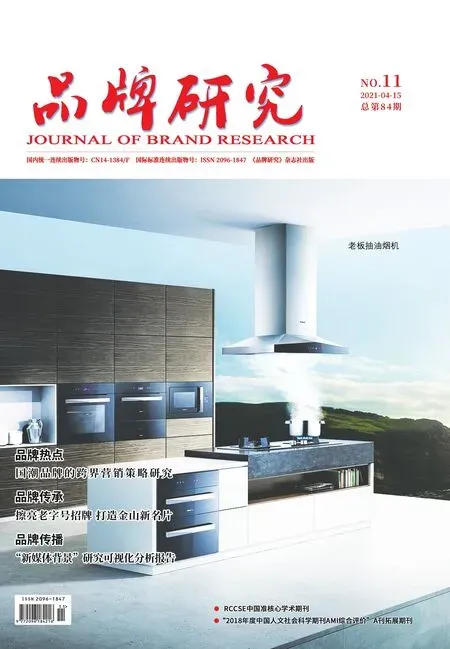社会风险视角下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影响分析
——以云南省G村为例
文/刘琳(兰州大学)
一、提出问题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蔓延至其他省份,举国上下为抗击疫情,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与聚集,采取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封闭式管理、停产停工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不仅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更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短期负面冲击。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但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3%,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15.6%,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25.6%。这期间,疫情防控加大了物资运输成本,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大大增加人们的生活成本,加剧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负担。虽然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不同程度地波及农村,但相比之下,农村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3.31亿亩,春耕备耕全面展开,受这次社会风险的影响较小。本文研究发现,城乡在面对此次社会风险时展现出的较大差异,主要因素在于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土地生产的相对稳定性使农民在面临社会风险时,仍然可以依靠农作物度过短期风险。
自农耕社会至前工业时代,农地经营始终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方式,农民可以在自有土地或租借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由此获得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当前对于农地保障功能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功能替代论”“安全论”及“弱化论”。
“功能替代论”方面的研究认为,土地的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有一定影响。首先,劳动承载力功能替代程度及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与农民转出土地的意愿成正比(万亚胜等,2017)。农地就业保障功能在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以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聂建亮等,2015;唐焱等,2015)。其次,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难以实现(何宏莲等,2011)。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替换农村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闫文,2013)。
“安全论”方面的研究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时难以建立的条件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实际上是由土地来承担的,即所谓土地保障(李郁芳,2001)。土地保障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命安全保障,是农村家庭保障的核心(梁鸿,2000),土地作为就业岗位的功能已经十分微弱;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则十分突出(徐琴,2003;钟涨宝,2008;吕军书等,2011;徐琴,2003;姚俊,2009),在土地各个功能中,其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平均值最大(王克强,2005)。耕地在农户心目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不是经济功能,而是社会保障功能(陈美球等,2008)。社会保障功能是耕地资源社会功能的主体,其中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又是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的主体(孔祥斌等,2008)。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强化了土地的保障功能(王银梅,2009),欠发达地区农民偏好于土地的生产功能、保障功能,以家庭保障为主,保障水平较低,而发达地区则相反(徐美银,201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但是目前我国农村还不具备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农民社会保障还不能完全脱离土地保障,土地保障仍然是中国转型期发展和稳定的需要(李南洁,2008)。
当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弱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论”的学者认为,土地对农户所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已经大大下降,土地不再像历史上任何时期那样是农民的“命根子”(罗必良,2013)。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户从粮食市场获得粮食的比例较大,参加非农就业的机会较多,农户对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较低、被替代程度较大(张雪靓等,2013)。土地保障虽然仍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但农地经营权的让渡、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及土地比较收益逐渐下降等原因,导致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不断弱化(邹宝玲等,2019;黎翠梅,2007;樊小钢,2003)。同时,以土地作为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载体,也阻滞了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樊小钢,2003)。
上述三方面的研究虽然侧重各异,但都基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土地保障功能的研究已经很多,其中只有闫文指出土地在我国将长期承担着由于政策性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的保障责任(闫文,2013)。总体来说,对于土地保障功能的研究尚未从防范社会风险这一角度对农地保障功能进行研究。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云南省G村为例,探讨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社会风险时,土地的保障功能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如何影响农村的抗风险能力。
二、当代乡村社会下的土地功能
1978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民实际上占有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收益权,土地不仅承载着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功能,还承载着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指农户以土地收获物供给其基本生活资料或者以土地收入作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抵御社会风险的主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农村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土地的生产功能及集体互惠功能作为支持农村家庭防范社会风险的后盾,发挥了主要作用。
(一)土地的生产功能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基础,不仅给农民带来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资,也承担着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基本职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更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而形成当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造成不同阶层的农村家庭对农地生产功能的依赖性也不同(贺雪峰,2018)。
现有农村家庭的普遍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亦工亦农,主要有“代际分工”和“男女分工”两种(赵晓峰,2012),分别为青壮年进城打工,中老年人从事农地生产经营;或者女主人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照顾父母及抚养孩子,男主人进城打工。这种农民家庭的收入有务工收入和农作收入,其中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对农地生产功能的诉求以维持家庭粮食供给、维系基本开支为主。由于非农产业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多种因素致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对于这类农村家庭来说,土地仍然是家庭必需的生产资料,通过土地经营一定数量的较为稳定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底线。第二种是普通的农业经营者,这种农民家庭基本没有非农收入来源,可供其生产经营的土地有限。农户主要从事生产经营种植,但土地主要局限于自家承包地,部分农户也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耕种着其他农户的少量土地,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力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这种家庭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土地经营收入,对土地的生产功能依赖性较强。
(二)集体互惠功能
农村社区的熟人关系网络资本能够将农地的其他功能转换为互助性的社区保障。基于血缘与地缘双重构建的自然村落及宗族,因天然信任与地缘认同形成的集体行动与合作互惠,成为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天灾人祸时候的重要补充。农村的熟人社会性质促使农民在同一村落中形成认同感、归属感,并不断强化这一功能。即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不断解构,农地的集体互惠功能呈现减弱趋势,但当较大的社会风险来临时,这一功能也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土地对于亦工亦农及普通农民的家庭来说都是生产功能,但其发挥的效用不一样。熟人社会的网络使得农村家庭土地经营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在村庄中作为礼物相互流动,在新冠肺炎期间成为农村家庭防范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土地的生产功能与互惠功能二者是同时发挥效用的,其中互惠功能建立在土地的生产功能基础上,只有农户进行土地生产,才有农产品作为礼物相互流动。总而言之,只有土地生产满足了亦工亦农的家庭的基本供给,及普通农户家庭的预期收入,土地的互惠功能才能进行。
因此,形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此外,贺雪峰指出,从全国普遍情况看,“亦工亦农”模式的家庭占比为70%,普通农户占比为10%,全家进城的农户占比约为20%,这类农户已经完全脱离土地,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大规模种植农户在本文的田野点只有一户,且根据贺雪峰的研究,这类农户在全国占比较小,因此本文也不做讨论。
三、疫情下的土地功能对家庭的影响
本文田野点G村位于云南滇中地区,坝区、临山,属于自然村,共95户。G村的耕地以坝区平底为主,其耕地面积240,000平方米。G村临山,山里有私人企业开的采石场、水泥厂,这两个企业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此外,距离镇政府及县城各5公里。因此,在G村88%的农户都为“亦工亦农”家庭,这些家庭的男主人在采石场或其他地方打工,而女主人则照顾自家的地。对于这种“亦工亦农”家庭来说,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男主人,而女主人耕种的作物则支持家庭基本生活,如大米、菜籽油等,都用于自家。此外,“亦工亦农”家庭还有夫妻都在打工,老人种植耕地的模式。在面对疫情期间停产停工及由于防控疫情造成的物价上涨,G村村民家庭能够依靠自耕地的生产经营度过暂时的短期经济危机。
(一)家庭基本供给:战时防范状态下的重要支撑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计算性、不可控性、不可逆性及全球性。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个体化极大地加重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性。在新的时空环境下,时间的易逝性和空间的可变性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由于流动性使疫情暴发风险的规模和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原来局部的、地方性的风险越来越扩散成为一种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文军,2020),从而导致乡村内外道路封闭,基层实行闭环式管理严禁人员外出。面对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加大道路管控,从而增加物流运输成本,并带来生活物价上涨的情况时,土地生产经营的农作物成为村庄社会风险战时防范下的重要支撑,土地生长的蔬菜能够支持农村家庭度过这种短期的经济社会风险,免遭物价上涨之灾。
与传统村庄一样,G村一直处于原子化、碎片化的分散农业生产经营状态,每个农户家庭都拥有自耕地,对于“亦工亦农”家庭来说,女主人或者老人在照看家的同时自己经营少许耕地,种植农作物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但农作物基本用于维持家庭生活,不对外出售;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自家便是种植蔬菜,更不会缺乏蔬菜食用。“新冠”来临时,大米等谷物在G村农户家里均有屯粮。首先,G村的“亦工亦农”家庭表现为女主人在家进行土地经营生产,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以及年轻夫妻在外打工,父母在家种植土地。由于家庭平时有人照看,G村的“亦工亦农”家庭均有养殖少许禽畜供家庭内部实用,此外,土地中日常蔬菜均成熟可正常食用。
风险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它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让我们意识到风险无处不在,而且,风险的形式多到使我们无法预计(张康之,2020)。在短期的冲击较大的短期社会风险面前,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使他们心里“有底”的,是自家土地里有暂时充足的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食物供给,并且即使不够,也能通过播种的形式补充家庭供给。由此可见,在面对短期的社会风险时,土地的生产经营功能可以转变为保障功能,维持农村家庭的生活。
(二)家庭收入:社会风险下基本正常的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民可以用自己多余的粮食换取其他的生产生活资料,这是封建社会以来土地生产实现农民生存以外的更多经济功能的突破,也充分体现了土地对于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新冠”肺炎疫情给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业带来了较大冲击,并影响着这些行业的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与此相比,土地生产的稳定性则大大减轻了农村普通农户所遭受的经济风险。贝克认为,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种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这种来自健康、经济的不安全感深刻影响着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种不安全感则要少很多。
G村的普通农户正常从事农业经营活动,而由于疫情影响带来物价上涨,蔬菜的收购一直在正常进行,并没有受到较大影响。李家、刘家等在G村是全家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农户,主要种植西葫芦、茄子、白菜、西红柿等。其中,李家自己搭建了大棚,棚内种植西葫芦和西红柿,正值成熟时期;刘家规模稍大,种植应季蔬菜,如茄子、白菜等,在蔬菜成熟时也请村里人帮忙收摘。其中李家的蔬菜一直送到私营老板那,于是每天采摘回来便送过去,未受疫情影响,而刘家的蔬菜则售卖到县城,由于距离县城较近,同样未受影响。
与城市相比,乡村人口密度底,人员流动性小,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风险时,受到的冲击更小,这一因素使农村家庭在面对社会风险时仍然可以从事劳动。贝尔指出,与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然而对于这种短期压缩式的社会风险来说,农村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能够延缓这种社会风险的冲击性,促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因而土地的经济功能与保障功能都是发挥作用的。
(三)互惠功能:熟人社会下的集体防范风险
中国社会结构中尤以农村地区最为显著,实行的是特殊的家族制度,并以家为社会“核心”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而社会价值系统都是由传递给个人,即使如今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人社会关系的关系,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在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并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社会环境下的关系取向,进一步促使熟人社会中信任、互惠的“差序格局”(赵泉民等,2007)。在这样的村落结构下,村民之间的互惠随着村庄的封闭性而强化,并具有排他性、组织性与规范性特征,熟人之间的互惠合作成为在面对社会风险时的重要力量补充(邹宝玲等,2019)。相对于危险,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强,尽管科学手段能够对风险进行评估,但人类认识能力的本质缺陷以及风险的客观特性,使得风险仍然是不确定的(黄新华,2016)。风险呈现出一种蚕食关系。它们使实质上和时空上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和危险的关联。因此,风险社会里,人们比以往都更加团结为一体,而具有深远互惠合作文化的乡村则在应对某些社会风险时更具优势。G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互惠在面对此次经济社会风险时便表现得尤为重要。
阎云翔指出,关系紧密的乡村中,在许多情况下,私人网络比物质或金钱更珍贵,食物作为村民之间的礼物不仅是关系网络的体现,也是社会援助体系。这一体系使个人在遭遇诸如食物和避难处等基本需求的非常情况时,道德义务连同先前的社会交换所造成的人情债务,创造了一种高度可靠的紧急援助机制(阎云翔,2000年)。由于G村的村民平时均种植家庭食用的蔬菜,加上李家和刘家为蔬菜种植户,其他农户可低价从这两家农户中购买蔬菜,也有相互赠送者。而对于熟人社会的乡村来说,互惠合作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种更多来自物质上的支持在乡村面临社会风险时能够成为抵抗社会风险的重要力量。
四、总结
贝克与吉登斯都认为风险是无处不在的,风险的不被感知性、难以预计性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风险。此外,风险的威胁是全球性(人类、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的现代性起因,是现代化的风险,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人类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人类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过去曾经是自然的许多东西,现在都不再完全是自然的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止涉及自然——过去所涉及的多是自然,如婚姻家庭的变革为人们带来各种机会与风险。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展时,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如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的灾难。
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突如其来的社会风险时,在经济方面,由于农村拥有土地,当农民缺乏充足的财富积累及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时,依靠土地生产经营能够获取粮食供给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亦工亦农”家庭来说,土地在留家“照顾”的家庭成员经营下,生产出的大米、蔬菜能够支持家庭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风险;对于普通农户来说,全部家庭成员都从事土地种植,由于农村土地面积广阔,在面对这样的社会风险下,他们的生产、生活计划受到的影响较小。此外,农村熟人社会的性质所构成的以“已”为中心互惠的结构圈层也在强有力地支持着农村家庭对抗社会的风险。如上文所言,由于种植的蔬菜较少,隔壁的婶婶便将自家蔬菜送到门口。实际上,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在农村较为常见,但是当面对重大社会风险时,土地的互惠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面对社会风险时,农村的土地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并且在特殊时期,土地的生产功能可以转变为保障功能及集体互惠功能,维持农村家庭的生活。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index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