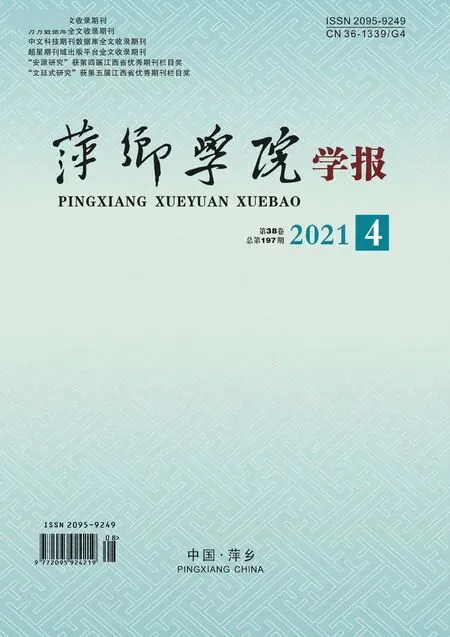明代“强盗”案中亲属身份关系对司法裁断结果的影响——以《盟水斋存牍》中“杨维翰”案为例进行分析
石 泉
明代“强盗”案中亲属身份关系对司法裁断结果的影响——以《盟水斋存牍》中“杨维翰”案为例进行分析
石 泉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明代州县官员对辖下案件的审理结果始终力求有充分的证据支撑作为实现情理和法理双重标准下“信谳无疑”社会效果的关键因素。具体到“强盗”类案件,则要求对案中人行为责任的界定和惩处必须要兼顾物证搜集、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主观认罪口供等诸多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参酌律文内容完成案件结论中刑罚施行方式选择和轻重程度的合理限定;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承审官员在实际分析案情过程中的主观视角以及进而所遵循的思维路径上出现了很大差异,集中表现为上述定罪量刑结果的不同和个人司法能力的高低。其中明代“杨维翰”一案 “强盗”行为和亲属身份间矛盾竞合关系的突出特点,直接影响了官员间对于如何在兼顾二者的同时,使审理结果符合 “情理两协,勿枉勿纵”标准要求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观点和争论。
“杨维翰”案;矛盾竞合关系;思维路径;结果差异;司法效果
《盟水斋存牍》是颜俊彦①在担任广州府推官期间将其本人所经手的部分案件谳词和公文略作分类汇集而成的公牍专集。其中内含刑、民、行政、诉讼诸法,包括商业纠纷、土地制度、宗族事务等诸多方面。同时也正因书中所涉案例内容广泛多样,使得当今学界在法史学、社会学、宗族问题等诸多研究领域选择将该作品作为了解当时社会现实情况的珍贵史料。其中叶显恩在《晚明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情态的忠实记录——〈盟水斋存牍〉简介》中基于社会史的角度对该书所反映的当时社会情况进行了提炼总结,探讨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吕丽、倪晨辉则在其《〈盟水斋存牍〉中的慎行理念分析》中依托案例着重分析明代基层法官的慎行理念;而童肖安图的《从〈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东女性财产权》一文中以明末广东女性这一特殊身份群体为研究视角,探析其在面对家庭财产继承问题时的真实境遇。但综观以《盟水斋存牍》为对象的研究中,出现“杨维翰案”此类案中人行为责任法律承担和亲属身份关系按律减等两大因素同时并存于案情,且直接左右案件最终结果的特殊情况尤为鲜见。故本文对颜氏以及相关人员在承审该案过程中的具体表述进行分析,以明确如何通过案件的实际特点出发去引律断罪,使定案结论在维护传统观念下“情法两谐”目的的同时,又能够满足理据充分的程序规定和“慎重人命”的司法标准要求。
一
据《盟水斋存牍▪一刻▪谳略(一卷)》中所载,当日杨维翰、沈广居、沈确赞、沈江存四人冲入邻地冯姓家中,意图掳人行盗,及进至屋内方发现屋主冯梦祥不在,于是便将搜出的另一人杨洪现强行带至荒远禾场,威逼其交赎免祸。事后冯梦祥立即率众人追赶,抓住沈确赞,从其口中得知杨洪现被掳之地并将其安全解救,同时在现场发现了强迫其书写保证交付赎金的纸笔和部分用于“强盗”作案的刀棍工具。不久当地官府又陆续将其他三人下狱监候,拟待各方依律审结后再做处理[1]22–23。
实际上,案中情节本身并不复杂。明代法律规定:“凡强盗已行,不得才(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才(财)者,不分首从,皆斩。”[2]140也即杨维翰等四人掳走杨洪现的行为不论是否实际获取财物,都会被首先归入“强盗“犯罪名目下,然后再进行后续刑罚标准的具体考量;另外,该条律文同时也暗含了对“强盗”罪中责任人“行为犯”特点的性质认定。具体到本案,即便不考虑前述杨维翰等四人最后是否劫得财物这一问题,仅是因为“掳掠”行为本身的出现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行为中止”情况适用于对案中人宽免刑罚的可能②。而与之相反,杨洪现、冯梦龙以及当场发现的刀具纸笔等作为人证物证在审理过程中无不将起到对案中四人有罪认定的证明作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入户掳人勒赎之盗“律同杀人,引例枭示”。所以,综合已有案件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杨维翰等人面临斩、绞一类的死刑判决结果本应是不存在任何疑义的③。
不过随着对案中人相互间身份关系信息情况的有效掌握,承审官员内部对原本拟定的“死罪”结果是否真正符合“处断平允”的司法标准出现了很大争议。起因于案中“强盗”行为施行人杨维翰、沈确赞与被掳者杨洪现“一系功服,一系缌麻,有服例减等之律文在。”也就是说,“亲属相犯,按律减等”这一情况因为案件调查的逐步深入,已然被承审官员所知悉,并进而在事实上“介入”且不断否定部分官员主观层面对犯罪责任人先前拟定量刑结果的“合理性”认识。而亲属身份关系情况由于兼有深厚的社会情理基础和明确的律例文字支持④,这也就直接导致审理者内部原有主张“死刑”观点的人很难依靠纯粹的理论逻辑实现对坚持“按律减等”意见官员的否定和说服目的,因此,也自然影响了最终文字性判决结果的生成和付诸执行。
二
关于本案,颜俊彦在《盟水斋存牍》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若辈之拥众突入,非杨洪现家乃冯梦祥家也,当夜洪现在,掳之以去耳,使適不在,而多人执械夜分突入人家,缚而致之,以为强盗乎?非强盗乎?……以掳洪现来,不以劫梦祥来也,将重其罪乎?将轻其罪乎?”[1]22
应首先明确,所有已制定生成的法律文字条例是相对固定的,并可随时适用于特定案件情境的裁断处理。但律文内容所涉及的可规制范围却有其“边界性”,并非可以无限的“延展”和“扩张”。由此,承审官员在具体分析案情的过程中即需要凭借主观认知将不同的案件依特点尽可能“归入”最相符合的律例条目下,并进而比照该处的量刑界定标准去完成最后责任的轻重划分。但在司法实践中,案件的过程本身经常会出现“交叠”于不同法律条文所“囊括”范围之间的情况,即既符合某一条例适用情况的同时,又不与另一条文所涉及的内容相矛盾⑤。故承审人主观一旦形成内心决断就势必会不自觉地沿着该罪名情况所“预设”的框架进行逻辑思考,并在最后“触发”与之相匹配(对应)的裁断结果(也即落实到文字层面并需付诸执行的审理结论)。
本案该对话中所反映的争论问题首先是案中杨维翰等四人究竟应以纯粹的“强盗罪”认定,还是应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亲属相犯”情况予以减等处理。前述文中实际已经说明,如果完全按照纯粹的“强盗”罪进行裁断,那么“劫盗勒赎”行为肯定面临死罪的刑罚结果。但如果将此案视作杨维翰、沈确赞与杨洪现“亲属”间的犯罪行为,那么依循这一“路径”进行思考所得出的处理结论就会和前者有很大不同。尽管“服制减等”有违法律本身保障平等、公正的社会功用,但在古代维护统治“差序格局”目的需要的影响下,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某种程度上和自然界的“不齐”“不同”一样,是完全正常、合理的现象。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3]。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同罪相异”背后根据血缘身份亲疏远近来定罪量刑的“服制”关系,会成为长期立法、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性原则。
具体到本案,杨维翰、沈确赞二人能否“死里逃生”的关键某种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本身已施行的犯罪行为,反而承审官员如何对整个案件进行性质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最后究竟是哪一项律例条文将会成为本案的刑罚裁定依据⑥。明代法律规定:“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四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若行强盗者,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2]142换言之,同样是在“强盗”律文之下,如果该条律文适用本案就会直接使原本“枭示”的拟处理意见“减等”为流、杖等能够保全性命的刑罚结果,而二者至少对杨维翰和沈确赞而言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只不过杨、沈二人在案中的行为(“强盗”行为)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所以,如何让这一具有“免死”作用的条文“应用于”案中,使承审官员沿着该文字背后所预设的“路径”去进行思考,问题的关键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整个案件从何种角度进行“审视”。即不同的思维视角决定了不同的思考“路径”,并在此“路径”下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审理结果⑦。
三
本案在进入审转程序后,复审官员给予的批复同样代表着差异“视角”下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
分守道批:“杨维翰、沈广居等拥众突入冯梦祥之家,掳去杨洪现置之荒远禾场,此时若非梦祥率众追获沈确赞,搜出洪现,寡妇孤儿当不知作何鱼肉矣。劫盗律同杀人,殊不得以服为解。事干多命,仰府覆(复)审拟夺,仍候巡道详行缴。”
兵巡道批:“杨维翰等劫掳杨洪现,执械强捉,缚致禾场,盗情逼真,各犯以无生理,但援亲属相盗,幸有一线活路。其如冤对,坚执誓不与俱生,何孽?实自作于人,何尤之生。至死四命攸关,仰广州府覆(复)审确招详夺。”[1]23
不可否认,案件审理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求取真相。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社会不存在所谓“法律事实真相”和“客观事实真相”的区分概念,只认为所谓客观公正的判决结果具有唯一性,承审官员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找并证明其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相本身,否则便是尸位素餐,有负皇权和民众的期望[4]。而现实情况却往往因为官员的个人能力有限,使得本应作为整个审理过程主体力量的他们不能够探明绝对的客观事实真相,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解释了为何师爷、幕友等身份群体有机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下其手,取代前者在事实上主导整个司法过程中具体案件的审理方向[5]。另外,就是在求取真相的过程中,各方对相关证据的搜集和掌握永远只能是相对充分状态,尤其是当证据不足影响后续审理过程的推进时,承审官员本身必然会成为该局面下的首选追责对象(而非师爷、幕友),因此,官员本身很大程度上在得到证据后,并不愿去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评已得证据的证明力乃至真伪性问题,而习惯于沿着该证据内容所“指定”的方向去进行思考和形成最终的文字裁断⑧。
而本案中亲属身份关系这一信息就起到了对整个案件审理进程的“导向”作用。因为该信息内容本身有与之相符的法律规定(亲属相犯),同时不采用该信息也有另一种裁断依据(纯粹的“强盗”罪),即不存在所谓的是、非问题。从证据角度而言,身份关系属于事实问题,采纳与否服从于承审官员主观对整个案件的性质认定,即减等情况往往只作用于量刑阶段;至于情理角度,正如颜俊彦本人所言,“……减(杨)维翰、(沈)确赞,而独坐(沈)广居、(沈)江存,非平也,论情则服例载有明文,论法则掳赎应用重典,况掳人勒赎,独此地见惯浑闲,宪台之不欲姑息此辈,良有深虑尔。”虽然,司法官在审判具体案件时,经常把儒家思想中的情理内涵作为判案的依据,如“引经决狱”、“亲亲得相首匿”等等,体现了古代“司法”对于情理的“屈从”[6]。但首先应将其视作维护社会统治和强化“人治”需要的手段,如同本案,两种判决结果都能做到理据充分,但也都存在着让支持另一方观点的人指出自身不足的可能。这种相互间矛盾的根源,实际就代表了情理与法理始终围绕着最终真相结果的客观、公正、唯一性(而非合理、合情)问题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并通过承审团体内部的差异性认识(观点争论)予以显现⑨。
①颜俊彦,字开眉,浙江嘉兴桐乡人。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进士,授广州府推官,庚午年(1630),因故被论罢职。为官期间清廉自持,断案理狱“不厌详慎,矜恤为怀”,时人称之曰“广之皋陶,才操神理,迥然独异,……谳词如金科玉律,确不可易。”《存牍》中所收录的内容即为此三年间作者本人所裁断部分案件的汇编集合。盟水,意喻执法如水之平,澄澈无讳,方能清合天一,察奸究邪。关于颜俊彦的生平经历及《盟水斋存牍》的体例内容参阅:姚莹:《〈盟水斋存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
②所谓“行为犯”,意指以危害行为本身的故意实施作为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重要标准,而不要求必须出现一定物质的、有形的危害结果。就本案而言,其特点在于犯罪行为(即掳人勒赎行为)一旦发生,其行为从初始到完成(既遂)的整个过程具有明显的“瞬时性”,而这也就直接否定了所谓传统意义上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等有助于减轻行为人在定罪量刑阶段责任承担情况出现的可能。参阅:王志祥、黄云波:《行为犯之基本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③此处必须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在律例文字层面对案件承审官员所做出的裁断结果以及具体的审理过程有着明确的标准要求。通常表现为在“众证齐备”的基础上“断罪必输服于供词”,同时对案情本身要做到“反复研鞫”,并本着“疑罪惟轻”的原则实现刑罚适中,以避免“出入人罪”。否则将很可能会在后续的审转程序中遭到复审官员对原审结果的“合理怀疑”。具体到证据方面,“强盗”类犯罪通常会将受害者本人的呈控(如果受害者因强盗行为死亡,一般会由其亲属或地方里甲乡长代为告诉),损失财物的文字性记录,旁人对事实情况的指证说明,施行“强盗”行为的工具物品,身体伤损或尸体检验的报告说明以及犯罪人的认罪口供等诸多方面纳入到最后判决结果的证据考虑因素当中。不过这也导致了地方官员虽然一方面形成并确立了“慎重人命”的司法态度,但同时迫于对审理时限、“官司出入人罪”、“断罪不当”等律文规制内容的现实压力,往往会基于个人仕途和政绩考评的目的考虑,选择将回避或伪造证据作为应对承审困局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对证据要素中犯罪人认罪供词这一关键证据的获取,几乎无法避免刑讯手段在州、县实际审理过程中的普遍使用。参阅:石泉:《明代审转程序下“审慎”观念的现实功用——以“陈得”案为例进行分析》,《荆楚学刊》2020年第1期。
④之所以如此表述的原因在于,“五服”关系本身应视作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特点的一种外在表现;随着“礼法”合一的不断深入,“准五服以治罪”就成为后期“礼”这种特权思想对“法”之平等、公正基本精神“异化”后的产物。当然,必须承认,“五服”制度有其在中国历史社会长期存续发展的合理性,其上升为法典并成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任何特定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不过必须明确的是,“礼法合一”虽然自唐以后实现了高度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律文条例间甚至某一具体律条内容本身不存在相互矛盾冲突的情况,只能理解为 “礼法合一”这一趋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后世法典所兼具的礼、法表征愈加完善、体系化;而不会简单地对依照其进行裁断后所得出的结果从礼或法一种角度就能够轻易地在外部完成否定性评价,从而使这些礼法“结合体”受到纯粹法律所固有的公正性、合理性质疑。关于“准五服以治罪”的历史源流及存续合理性问题,参阅:于巧辉:《论“准五服以治罪”历史传统及当代借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1年。
⑤这里与我们当今在刑法和民法学领域研究中经常会涉及的竞合问题颇为相似。所谓“竞合”,可视作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概念的发生,并使这些概念之间发生重叠或冲突,甚至使法律运行难以顺利进行的现象。应当认为,一方面法律竞合是法自身内部矛盾问题的必然显现,同时也是人们力求全面把握法律现象和追求法制统一的尝试性手段和方式。只不过法律所谓的完整性目标只是一种朝着理想状态不断趋近的努力,真正的法律协调、法制统一、立法完善,还需要不断去更新法律观念,优化法律认知。关于法律竞合的相关问题,参阅:毛翯:《法律竞合初论》,《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⑥此处笔者并不否定案中人本身的行为会影响最终裁断结果的轻重程度这一观点。诸如自首,供述同案犯有效信息,积极退还赃物并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等行为都有被纳入最后审理结果从轻处理考虑情况之中的可能。只不过上述情况在明清时期和文中所讨论的身份关系问题相同,因为该类客观事实行为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承审官员主观“视角”下是否将确已掌握的情况认可为“可考虑因素”,只有如此才可能“触发”相应条文的适用,并对案中人起到减轻或加重刑罚处理的效果。
⑦也就是说,杨维翰、沈确赞二人入户“劫盗”杨洪现并由勒赎情况是已有事实,此处并无争议。但围绕该并无争议的问题却因身份关系情况的出现,形成了对该案件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杨、沈二人进入冯梦祥家中行盗,只是后续“意外的”发现了具有亲属关系的杨洪现,所以其本身只是纯粹的“强盗”行为,依照“行为”犯的情况并无宽免的可能,理应按例“枭示”;但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杨、沈二人的确是进入冯梦祥家中行盗,但“劫盗”罪的施行对象却是有亲属关系的杨洪现,所以应根据该事实结果对杨、沈二人适用“亲属相盗”减等处理。实际上,二者所针对的是同一案件事实,并无差异,其中的亲属关系情况两方也并不否认。只不过前者集中于案中人施行犯罪时的主观态度,后者则更多关注事发后出现的最终结果,而这种“视角”的不同,所影响的就是对整个案件完全不同的性质情况认识(“强盗”犯罪,“亲属相盗”犯罪),进而由这种认识左右着不同条文律例使用下量刑结果的差异。特别是当案中涉及生死问题时,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争议,就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⑧明代法律规定对一般案件的审理期限为两个月,另捕限超过一月以上者,就将受到罚俸和笞刑处分。某种程度上这些规定都是承审官员潜在且无法回避的“压力”,特别是在由科举取士而担当承审职责的官员司法能力有所欠缺的情况下,官员承审后可能会力求快速、准确地生成一个文字性的判决结果。所以拟定结果所必须有的证据“支持”问题就凸显了出来,由此“伪造证据”或有意无视部分证据,往往成为承审官员在困局之下可能会选择的解决方式。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可以在无证据或证据缺失甚至已有证据内容间出现相互矛盾时减少审理时间的“花费”并提高“司法效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续的审转程序不会纠察其中的问题。这只可视为承审官员在趋利避害心态下被动的选择手段,特别是当承审官员本人因政绩考评与所拟定的结果建立了“利益联结”后,会选择极力维护该结果的“正确性”来对抗上级审转程序对事实真相的探寻,使得案件审转过程表现为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司法博弈。关于该问题参阅拙文:《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宁波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⑨文末需要补充的是,从纯粹的法理角度而言,真相结果只能是唯一的。这就意味着文中所述的“法律事实真相”和“客观事实真相”中必有一个和真相本身有所“偏差”。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多地苛求古人,古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并逐步固化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并影响着对案件真相的把握。正如徐忠明在《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信谳无疑”的司法理想永远都是主观想法和客观真实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在于前者本身的“合情理”性以及与后者间的相“契合”程度,这往往决定了到最后能否获得相对层面“信谳无疑”的结果。
[1] 颜俊彦. 盟水斋存牍[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 怀效锋点校. 大明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3] 杭宁. 论丧服制度对中国礼法文化的影响[J]. 青海大学学报,2005(4): 93‒97.
[4] 徐忠明, 杜金. 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8.
[5] 殷啸虎. 公堂内外——明清讼师与州县衙门[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26.
[6] 宋俊飞. 司法中情理与法律的冲突与协调[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8: 15.
The Influence of Kinfolk on the Judicial Verdict in the “Robbery” Case in M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YANG Wei-Han” Case in
SHI Q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ing 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0,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ce was taken as the key element to support the verdict of cases by prefecture and county officials in realizing the social effect of “verdict without doubts” under the emotional and legal principles. When it comes to robbery cases,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enalty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llection of physical evidence, witness testimony, on-site inspection record, and subjective confession while referring to the legal provisions to decide the form of penalty and the scale of sentence 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case. But discrepancy, especially in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and judicial ability, may arise in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thinking path followed by the trial officer in the actual analysis of the case. In the case of YANG Wei-han, the trial officers, influenced by the contradictory co-opetition between the “robbery” and the kinfolk, showed disagreement in balancing the two and conforming the verdict to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emotion and law and free from wrongful and conniving judgment”.
the YANG Wei-han case; contradictory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thinking path; discrepancy in verdict; judicial effect
2021-04-13
石泉(1989—),男,黑龙江双鸭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D909.2
A
2095-9249(2021)04-0065-04
〔责任编校:吴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