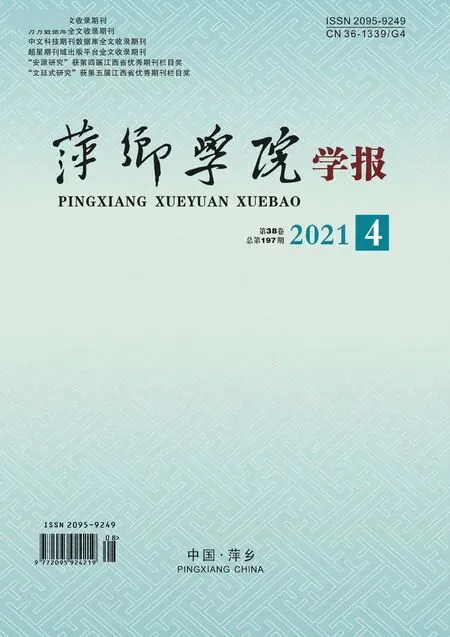积极刑法观提倡之得失:基于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考察
余越洋
积极刑法观提倡之得失:基于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考察
余越洋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上海 200063)
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为及时预防社会风险带来的法益侵害并回应公众安全诉求,积极刑法观得以提出。该刑法观念在严格预防社会风险的同时,对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形式性限制与构成要件解释论的贯彻均有负面作用。应基于谦抑性保障、多渠道规制、注重文义解释三个向度提倡折中的积极刑法观,以期在及时保护国民利益的同时,兼顾犯罪构成系统与外界的良性互动,实现犯罪构成理论的系统性、时代性与合目的性。
积极刑法观;风险社会;犯罪构成;系统论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刑法呈现出了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态势,即在刑事立法、修法与司法的过程中均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严格防控社会中的风险行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最大程度保护公民利益。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我国刑事法领域划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愈发多的现代社会风险行为被规定为犯罪①。整体而言,我国刑事法领域现今已秉持积极刑法观进行活动,刑法从传统的最终手段性开始转变为富有弹性的手段优先性特征[1]。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正是积极刑法观的立法实践,其新增的18个罪名以及修改扩容后的14个罪名加1个总则条款,共计33个条文,都在进行着犯罪化的立法[2]。积极刑法观的贯彻涉及对行为性质的价值判断,在积极入罪观念的驱动下,司法机关对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会倾向于认定构成犯罪。但是,认定犯罪所依据的犯罪构成有其自身的理论定位,其旨在通过判断构成要件的完备与否以及犯罪性阻却事由的有无来认定犯罪,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认定犯罪的有序性、公正性与整体性,同时落实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精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3]。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体系中具有内在结构性的系统理论,具备其自身的理论旨趣。积极刑法观显有偏颇的价值取向会破坏刑法谦抑性,无法贯彻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精神,冲击犯罪构成自身的理论系统。因此,应深入检视刑事法领域兴起的积极刑法观,以缓解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与犯罪构成理论系统保障人权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积极刑法观的提出:风险社会的形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借助技术进行的新型犯罪在社会生活中越发猖獗,如互联网犯罪、金融犯罪。同时,在技术发展的浪潮下,传统犯罪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食药品犯罪等,其手段呈现技术性变化趋势,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性也愈发严重,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安全风险。简言之,我国社会已全面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新型风险在生活世界的泛化,大大刺激了公众的安全神经[4]。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所内生的刑事侵害风险主要根源在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社会已转变为高效能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刑事犯罪的手段相对单一,犯罪行为指向复数对象的情况较少。在传统刑法典中,更多的是对自然犯罪进行规制,侧重将造成了实害结果的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对象,如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刑法条文将该类犯罪的既遂形态固定在实害结果出现之后。反观风险社会,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之下,诸多由新兴技术引发的新型犯罪涌现到社会生活层面,譬如:互联网犯罪、金融犯罪等。前述新兴领域本是为促进社会高效能发展,推动社会公众利益的整体性实现。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行为人通过技术平台实现行为的高频性与行为侵害对象的复数性,在增加犯罪实在收益的同时扩大了法益侵害的广度与深度。此外,传统犯罪在高新技术的赋能下,也呈现出手段革新的外在特征,如:电信诈骗犯罪、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该类型化犯罪借助高新技术大幅提升犯罪效率与收益。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的刑事侵害风险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新型犯罪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层出不穷,传统犯罪也在技术的诱导下进行手段革新,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公民的日常生活暗含了更大的刑事侵害风险。
其次,我国社会样态由熟人社会转变为生人社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人口流动性加大,地域间经济互动频繁,社会样态已发生了较大转变。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生活、商品交易在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而展开的,呈现“点对点”的接触模式。公民在工作生活范围之内能够较为容易地建立熟人网络,公民生活一般在可预知的范围内进行。而在现代社会下,由于地域间交流的增加,异地生活择业愈发普遍。熟人生活圈在建立伊始,很可能就因为生活范围的变动而消散。此外,互联网技术为现代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社交、购物与娱乐平台,公民能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满足自身需求,社会交往呈匿名化。例如:在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模式下,顾客通过网络进行交易,无法准确获知或核实商家的真实情况。商家在匿名状态下,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全国性、全球性的商品交易。简言之,我国社会样态已转型为匿名化的生人社会,公民的社会交往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公民在面对个人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得不在传统的生活模式之外,探寻应对焦虑和不安的方式[5]。
最后,现代社会的法益侵害风险无法根除。如前文所述,现今社会下的风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社会风险,而是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指技术风险[6]。由此可能引发的互联网犯罪、金融犯罪、生物安全犯罪等无时无刻威胁着公民的安定生活。应当看到,新兴犯罪所依托的技术手段均与社会发展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换言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运转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与信息互通必须依托技术优势保持前进的态势。但只要社会持续运用技术,可能利用技术进行刑事侵害的风险就必然长期存在。因此,现今的法益侵害风险不可能得到根源性解决,只能通过加强立法应对此类现象,严格规制可预期的风险行为,防止刑事风险转化为现实侵害。由于公民的日常生活处于泛化的风险之下,部分风险转化为实际侵害的现实案例也逐渐产生,公民风险意识也越发强烈。
面对周遭世界的不确定风险,不仅个人需要不断地进行风险管理,现代国家的政策也必须更多地以管理不安全性为目标[7]。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强调只有在结果出现之后刑法才予以干预的传统刑法观,明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具有较强风险性的行为必须提前防范,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8]。
一言以蔽之,刑事法领域应对社会风险进行积极干预,从消极的“守夜人”转变为积极的“干预者”,以回应社会的安全需求[9]。反映在刑事立法中则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刑事立法者积极扩大犯罪圈。将部分法益侵害性较大的行为积极地规定为犯罪进行打击,以预防风险行为可能带来的法益侵害。另一方面,立法者通过刑法修正案对现行刑法已有条文进行修正,将实害犯修改为具体危险犯,将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或是将抽象危险犯规定为行为犯,以此实现刑法打击触手的前伸②。可以看出,刑法领域早已在民众安全价值诉求下采取了积极的刑法观。
在积极刑法观下,社会风险能够在严密的刑事法网中得到最大程度防控,公民的价值诉求得到了充分安抚与回应,刑法显然是积极保护社会安全的工具。然而,由于积极刑法观存在明显的价值偏向性,贯彻这一刑法观念对立法、司法实践具有较大影响。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重要的理论根基,具有自身的体系逻辑与功能定位,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系统,积极刑法观在指导刑事司法实务运作的过程中,势必对犯罪构成理论系统造成冲击。
三、积极刑法观的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考察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分化使得社会交往建立在特定的沟通系统中,各种系统建立了自身的结构、确立了系统进行沟通所围绕的主题,例如:刑法便是围绕犯罪问题展开的。因此,可以将规范性的刑法看成是一种社会沟通(social communication)。刑法规范在明确了沟通主题,完成了文本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与借鉴,逐渐形成了一种运作上的自治[10]。换言之,刑法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系统,并借助立法司法活动与外界进行社会沟通。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自身严密的理论系统。随着德日刑法的引入与本土理论的发展,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不断进行变革,但无论是德日三阶层理论还是本土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均承担着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作用。在实务中,司法人员基于刑法文本,凭借犯罪构成要件或是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在逻辑,分层次、分阶段地对行为进行出罪或入罪的判断,即构成要件之间互相制约、相互配合,以此完成判断犯罪的形式与实质逻辑。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是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特定性能的有机整体,具备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特征[11]。
(一)系统论视角下犯罪构成理论的功能指涉
基于前述分析,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要完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必须借助犯罪构成理论系统内部诸要素的有序运作,在“发现疑罪—进行判断—出罪或入罪”的形式逻辑下完成实质判断。目前学界颇有争议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德日三阶层理论与传统四要件理论,二者均是完成犯罪行为评价逻辑的重要理论,犯罪构成理论系统功能的实现也以此为基础。
众所周知,德日三阶层理论本质上为层次判断,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阶层,逐一对犯罪行为的成立进行排除式判断,其结构性与层次性不待自言。而传统四要件理论长期以来受到的批判便是系统内构成要件排列上存在无序的弊端。部分学者认为,传统四要件理论是一种耦合式理论[12],构成要件之间不存在逻辑判断层次,整体呈现扁平化结构。因此,司法人员对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的判断存在较大的恣意性,在实务中更像是为了积极将行为入罪而进行的拼图式判断,区别于德日三阶层理论排除式出罪的判定思路。
应当看到,虽然在形式上传统四要件理论未明示各要件的判断逻辑,但层次性的有序判断依然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务中,要合理适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必须依照一定逻辑顺序串联各构成要件,依照案件事实对构成要件是否齐备进行顺序判断,才可能实现对案件的高效处理。如果只是对构成要件恣意挑选进行判断,则不具备合理有效处理案件的可能,刑事司法实务则无操作性可言。在理论中,主流观点也同样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具有内在逻辑,现今的四要件理论已能进行分层次的理解。详言之,犯罪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侵害,犯罪客体所反映的就是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在判断时首先就应当考虑犯罪客体要件。同时,只有在社会关系被犯罪行为侵害后才会转变为犯罪客体,而行为必然与因果关系、犯罪结果相关,在判断上则自然地引出犯罪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的客观要件的内容。又由于客观事实是主体在主观的引导下实施的,进而进入对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判断[13]。因此,传统四要件理论依旧具备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逐步判断逻辑,与德日三阶层一样,能够通过阶段性的功能运作,完成对行为出罪与入罪的有序判断,实现犯罪构成理论的系统目的。
一言以蔽之,犯罪构成理论均具有实质的层次逻辑,各要素在该逻辑框架下互相作用与联系,并使理论系统得以运作,实现其自身的功能效用。基于对犯罪构成内部要件、层次顺序的分析,可以看到犯罪构成理论系统必然有其功能指涉。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系统随着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明确、反映系统论思想的三大功能指向。
首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系统中各构成要件承载于刑法条文中,即明示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被立法者固定在成文刑法中。犯罪构成的判断过程必须依托成文刑法典,系统的运行必然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构成的判断必须基于法律明文规定进行,排斥习惯法与有罪类推。落实有利于被告人精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防止罪刑擅断的发生。
其次,保证个案的精准判断。正如前述,犯罪构成理论系统依靠内在要素的有序判断完成运作。根据判断顺序,司法人员必须逐次对行为是否符合要件或是阶层要求进行判断,对不符合阶层要求的行为,就必须在该阶段对其做非罪处理。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系统具备筛选行为的基本功能。一方面,分层次对行为进行判断,增加了行为接收系统检视的次数,实现层层把关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分层次的顺序判断基础上,每一顺位中的判断要素均是对犯罪认定所需的不同方面的指涉,确保了行为接受构成要件要素考察的广度,有利于全方位、立体化考察犯罪行为。
最后,维护刑法的谦抑性。基于早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而非法律后续授予。而作为国家法律序列中最为严厉的刑法,一经发动则会对犯罪人的权利产生严厉剥夺。犯罪构成系统的文本基础就是规定了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行为的刑法条文。换言之,只有经过犯罪构成考察并被确定为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才能被作为犯罪处理。不符合这一条件的行为,将会在犯罪构成理论中予以排除。因此,对刑法谦抑性的维护,也是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当然功能。
(二)积极刑法观对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冲击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事法体系中的理论系统,是实现刑事司法功能的重要系统保障,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良性运行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系统论的观点,犯罪构成系统在进行运作自治的同时,也基于系统自身的开放性和外界频繁互动[10]。刑法观念作为直接影响刑事司法实务的价值风向标,势必在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外部互动过程中对其造成功能性影响。换言之,积极刑法观虽能强势预防新时代下公民的安全风险,但也应看到,这一理念价值在通过立法、司法传导的过程中,对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基本功能造成了负面影响,破坏了犯罪构成理论的功能性、整体性与合目的性。
一方面,积极刑法观弱化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限制。积极刑法观是对社会风险的灵活回应,会导致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立法走向象征性与情绪性[7]。法律条文的稳定才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体现,积极刑法观下的过度回应,反映了立法者被大众情绪裹挟,跟随大众情绪进行立法。《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犯罪就是情绪性立法的例证,即便醉驾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但入罪后的司法成本则不容忽视,如行为人的公职存续以及下一代择业均会受到较大影响,对其通过刑罚进行打击的必要性有待商榷。进言之,罪刑法定原则通过规定构成要件要素将法益侵害性严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给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运作提供文本基础,具有形式限定功能。而积极刑法观下的情绪性立法则将无需刑罚处罚,甚至将不具备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无疑是对这一限定功能的破坏与弱化。
另一方面,积极刑法观也冲击了构成要件的解释方法论。构成要件理论系统功能效用的实现依靠解释论完成。由于受目的刑论的影响,目的理性的刑法体系思想逐渐拉近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距离,刑事司法实务需要服务于刑事政策目的,这就要求发展受刑事政策目标指引的功能化的刑法解释论[14]。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刑法解释论极容易走向实用主义。详言之,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泛化的法益,将刑法的目的解释置于解释方法的首要位置,就会使得规范文义的解释被恣意性支配。因为,刑法的目的难以捉摸且歧见纷呈,规范目的往往成为解读主体贯彻其意图的借口,经常通过目的限缩或目的扩张改变规范文义。导致文义解释中的形式逻辑日渐衰落,难以对文本进行严格解释,使得目的解释越发趋近于类推解释[15]。进言之,积极刑法观下的功能主义解释立场容易导致刑法的过度解释,这一刑法观念过分关注刑法的实质性与目的性,预防现行社会风险成为宣誓性的刑法解释论价值导向,刑法文本含义逐渐被束之高阁。但是,法条文本才是立法本意最初的载体,倚重实质的过度解释偏离了法条文本,解释结论无法真正符合立法目的。或者说,解释结论所符合的目的,根本不是立法者的最初立场。
简言之,积极刑法观的片面坚持与贯彻对构成要件理论系统的运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存在极强的侵略性,不利于系统功能性利益的实现。因此,应施以更为缓和的刑法理念,与立法、司法活动进行有序互动,达成外部理念指涉与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良性沟通,以期实现系统运作、发展的最优化选择。
四、系统论下积极刑法观的缓和进路
基于前述分析,积极刑法观在指导并影响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促使刑法功能快速扩张并泛化,反而影响了系统功能的实现。诚然,积极刑法观的功能倾向有其可取之处,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及时防范社会风险。进言之,刑法理论系统的工具主义是必然的,关键看如何均衡工具主义的偏向,要避免对其工具性的过度使用[1]。因此,笔者认为,在积极刑法观以“惩治风险行为,维护公民利益”为旗号渗透进刑法体系,并逐渐产生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保持审慎态度,力求刑法观念的折中与合理。一方面,要杜绝一味坚持纯粹积极刑法观对社会风险的无节制回应,防止刑法工具性无限放大,冲击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为了革除积极刑法观弊端而固守传统刑法观念的封闭思想,全盘放弃积极刑法观内蕴的时代优势。换言之,要避免以风险时代的积极功能主义刑法学之名大闹一场之后,最终还是沉寂于四平八稳的传统刑法学的极端走向[18]。
一言以蔽之,应在刑事司法领域秉持折中的积极刑法观,在实现预防性刑事防治的同时,兼顾刑法文本的规范性限制作用,以维持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合理运作,达成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在立法、司法积极化的刑事理念思潮下,树立前述相对缓和的刑法观念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在积极刑法观下的刑事司法实务中应着重进行谦抑性考察。刑法谦抑性原则是保障罪刑法定原则不受侵扰与破坏的重要理念,积极刑法观的实际体现更多的是扩大现有犯罪构成系统所规制的犯罪圈,这明显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内生的谦抑特质相左。在积极刑法观引导下的刑事司法实务中,新修法律必然在规范上彰显着对风险行为的犯罪化倾向,而刑法条文是犯罪构成理论系统运行的基础。对积极刑法观下的刑法条文进行规范解释,本就意味着预防性、前瞻性的刑法条文得到运用。在此基础上,如果不对解释空间、解释方法加以限制,任由积极刑法观扩大犯罪圈思路的大肆指引,则难以防止解释结论的走向偏颇。
因此,在积极响应社会需求的同时,必须重点保障刑法谦抑性的落实,而非一味地回应公众需求,对公众的情绪化诉求保持足够的理性与警惕[16]。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考察增设新罪的必要性,警惕极端个案带来的舆论诉求,杜绝因极端个案动用刑事立法权进行积极回应。刑法具有保障法的天然体系定位,必须是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才能由刑法进行规制。进言之,在增设新罪时要坚持以系统性、体系性的眼光考察,对能够通过现有刑法规定进行解释处理的行为则无须积极地增设新罪进行处理,避免因实质上的重复立法带来刑法体系的冗杂,以确保刑法体系的整备性与经济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严而不厉”的刑法系统特点,在积极刑法观下,增设新罪后的刑罚配置必须以必要性为标尺,不应为回应公众诉求对新罪设置过重的法定刑。应当以既有条文法为定刑依据,根据法益侵害性大小配置相应的法定刑,例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的基准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妨害药品管理罪”,基准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规制的行为是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一般行为,法益侵害性明显比生产、销售、提供劣药行为更弱,因此,立法者对其规定了低于第一百四十二条的法定刑,保证了法定刑配置的协调。在严密刑事法网的同时,对处罚必要性也进行考虑,此举有利于犯罪构成系统在判定行为后能够获得较好的特殊预防效果,间接实现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规范目的。
其次,对风险行为进行多渠道规制。积极刑法观所坚持的是通过及时、灵活的刑事立法规制具有较强法益侵害风险的行为。诚然,刑法是为保护法益而存在,但并非保护法益的唯一手段[1]。换言之,部分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可以考虑通过刑法之外的方式进行预防,构建分层级、多样化的风险行为法律预防体系。如前所述,社会的变革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安全风险,的确应当及时打击风险行为,预防风险实害结果的进一步发生。但这一规范目的并非只能通过刑事法才能实现,如前述,刑法具有最终手段性,且刑事司法运行也需符合经济性,只有最为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才需要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其他风险行为完全可由法律体系中的其他部门法进行防范进行。详言之,对风险行为进行预防,要充分发挥行政法的前置规范作用,风险社会下被规定为犯罪的法益侵害行为大多是具有双重违法性的行政犯。笔者认为,如果危害较轻的法益侵害行为有相应的、较为完备的行政法规体系能够进行惩治,且通过前置法就能够取得足够的威慑效果,则无须动用刑罚进行打击,以实现刑罚的经济性,实现行为与责任的合理对应。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设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根据法条罪状描述,最容易触犯该罪的是运动员、教练员群体。但通过设立足够严厉的处罚后果,如施以生涯性禁赛处罚,则足以对这一群体产生威慑效果,能够实现一般预防效果,因此无须通过刑罚对其进行规制。另一方面,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相比刑事立法而言要高效得多。基于维护刑法体系的稳定性考虑,刑事法规范不宜频繁变动,而为了便于行政机关进行管理,在行政立法上往往注重立法效率,因此,行政法领域对风险行为的打击与预防能够更为高效地开展。
概言之,在风险泛化的当今社会,行政手段应当作为新时代预防风险的重要渠道。否则,社会风险形式层出不穷,过于积极的灵活回应必将导致频繁的刑事修法,使得刑法条文不堪重负。因此,对于一般的社会风险行为,应当优先考虑对其进行行政法规制。对于法益侵害较为重大,有必要通过刑法进行处罚的行为,则可在确立了行政法惩处的基础上纳入犯罪处理。同时,为了避免刑法文本自身过于频繁的修改,对于有必要进行刑事回应的法益侵害行为,也可以考虑采取单行刑法的方式进行规制,以维护刑法系统的稳定性,并以此形成多渠道的风险预防法律体系。
最后,在司法实务中立足刑法文义解释。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具体运作需要司法人员在实务中对刑法文本展开解释。积极刑法观的弊端之一就是极易在司法实务中以保护法益为名,对刑法条文进行所谓实质性、合目的的解释。但是,如果过于追求实质解释,很容易脱离刑法规范文本的限制。立法原意、立法目的这些形而上的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不同解释者的心里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答案,如果一味强调实质解释,解释者所追求的目的也很可能与立法原意渐行渐远,最终所依据的“立法原意”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解释者一厢情愿的本意。
进言之,立法者的意图是根据其所规定的法条记录下来的,人们只有通过具体文字才能把握刑法的含义,如果脱离法条文字去追求“正义”,公民在生活中的具体情况下就没有预测可能性,刑法本身也丧失安定性,无法保障国民自由[17]。并且,刑法正义性的缺失也与积极刑法观保障国民利益的初衷也是相悖的。因此笔者认为,司法实务应当立足于刑法法条文本,注重文义解释,以此限制积极刑法观偏向性。换言之,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自我运行应当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即便文字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产生内涵变化,但解释者的想象力也不能偏离文字可能的文义涵涉范围。否则,很可能在积极刑法观的引导下,解释者以保护实质法益的名义,模糊了扩大解释和有罪类推的界限,过分发挥刑法的工具性,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
一言以蔽之,应秉持折中的积极刑法观,在积极预防社会风险、回应公众安全需求的同时,注重刑法观念的辩证与合理,以维持犯罪构成理论系统,乃至刑事法律系统的合目的运行。
五、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系统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个案精准判断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司法实务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新时代下,可能侵害公民权利的安全风险层出不穷,必须同时兼顾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有效性与时代性,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效能,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一般的积极刑法观通过理论系统的内外互动指导司法实践,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限制与构成要件解释论运用方面均有负面作用。折中的积极刑法观有利于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刑事法系统与外界的良性互动,在立法、司法层面均强调司法人员审慎对待法益侵害行为,在不断变革的时代环境下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的情势变化,以实现犯罪构成理论系统的时代性、整体性与合目的性。
① 犯罪圈扩大的具体形式有增设新罪、将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等。
②我国刑法中实害犯、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行为犯的成立均是作为既遂形态规定的,但其行为发展阶段的完整程度依次减少。如果行为发展越不完整但仍被规定为犯罪的,一般认为其行为完整发展后的法益侵害性越大,立法者希望通过刑法在行为发展的前期阶段就介入进行打击。
[1] 付立庆. 论积极主义刑法观[J]. 政法论坛, 2019, 37(1): 99–111.
[2] 刘艳红. 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中国实践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的分析[J]. 比较法研究, 2021(1): 62–75.
[3] 刘宪权.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及其基本精神[J]. 法学, 2006(12): 69–77.
[4] 劳东燕. 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J]. 法学评论, 2017, 35(6): 12–27.
[5] 劳东燕. 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 中外法学, 2014, 26(1): 70–102.
[6] 陈兴良. 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J]. 中外法学, 2014, 26(1): 103–127.
[7] 劳东燕. 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3): 126–139+206.
[8] 黎宏. 预防刑法观的问题及其克服[J]. 南大法学, 2020(4): 1–21.
[9] 姜涛. 为风险刑法辩护[J]. 当代法学, 2021, 35(2): 92–104.
[10] 刘涛.实质法益观的批判:系统论的视角[J]. 刑事法评论, 2017, 40(1): 1–22.
[11] 何秉松. 犯罪构成系统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58–59.
[12] 龙长海. 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 社会科学家, 2012(10): 91–94+99.
[13] 刘宪权著. 刑法学名师讲演录: 第2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11.
[14] 劳东燕.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方法与立场[J]. 政法论坛, 2018, 36(2): 10–27.
[15] 赵运锋.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评析与反思——与劳东燕教授商榷[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38(2): 183–191.
[16] 周光权. 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 法学研究, 2016, 38(4): 23–40.
[27] 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第2版(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Positive View of Criminal Law: A Review Based on the Systemic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YU Yue-yang
(School of Criminal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63, China)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isk society, when the positive view of criminal law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prevent the infringement of legal interes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risks and to respond to the public’s demand for safety. In strictly preventing social risks, this view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implementation the limitation of for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under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positive view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ree directions: guarantee of principle of modestly restraining, multi-channel regulation and emphasis on literal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ime constitution system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to realize the systemic, contemporary, and purposeful nature of theory of crime constitution
positive view of criminal law; risk society; constitution of crime; systemic theory
2021-05-12
余越洋(1997—),男,江西南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
A
2095-9249(2021)04-0059-06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