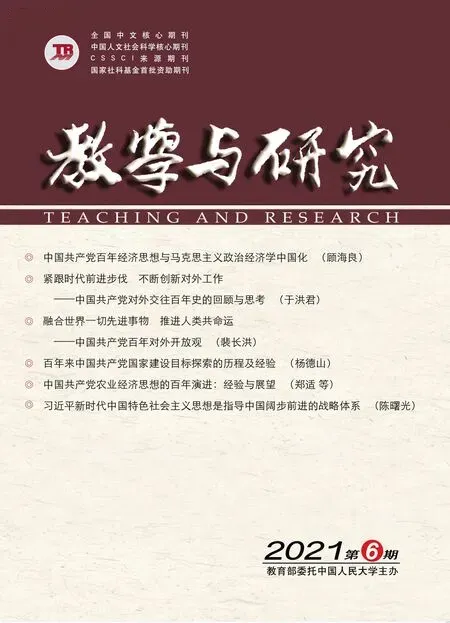不彻底的“辩证的数字现代性”
——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与重构之审视*
杨慧民,宋路飞
当今时代,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大数据所打造的生产技术基础和所反映的经济现实,不仅逐渐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地带,还突出地改变着多种社会文化现象,并塑造着与之相应的“大数据意识形态”。尽管与大数据相表里的时代景观总是依循社会发展的不同性质、水平和阶段,以及文化传统的不同传承定向而获得其相应实现,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已全然通过各种理论形态如雨后春笋般地呈现出来。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与重构就是对这一理性逻辑的哲学省察,其意义在于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切近地理解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的整体分析架构,还开启了从哲学上批判性地检视大数据资本主义重构理路的先河。对这一批判与重构的辨明,有助于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发展的重要特征,对审视我们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确定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亦有积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福克斯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浪潮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的算法和数字机器正在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大数据,并做出使人类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决策。这种发展导致了一种特殊性质的数字资本主义出现:大数据资本主义。”(1)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3,p.46,p.59,p.57.大数据资本主义拥有影响、改变人们决策和行为的神奇魔力,资本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苦苦追求的理性力量在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达到新的高度。和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一样,在大数据资本主义框架内,“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因为过于张扬工具理性而出现的数据分析和算法霸权,使得人的主体性和感性体验丧失了存在必要和生存空间。大数据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加剧,而潜在的更大系统性风险正在来的路上。用福克斯的话说:“工具理性的二元分裂是资本主义统治一次又一次不断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基础,它破坏资本主义精神的美妙承诺,触发社会危机和冲突”。(3)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3,p.46,p.59,p.57.
(一)大数据资本主义在现实幻象掩盖下重构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结构体系
大数据资本主义转型的背后,是资本剥削范围和方式的变化、政治利益的攫取、文化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拓展。这些层面的影响彼此互相加强,使得大数据成为催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的重要力量,并再生产出以数字霸权为中心的当代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和总体秩序。
在经济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几乎所有事物(包括数据和社交)都实现了商品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基于大数据的各种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购物网站、共享云等数字平台表面上“免费共享”的数字体验背后,实则掩盖的是资本主义新型剥削关系,是对非雇佣互联网用户“数字劳动”的剥夺和“消费中的剥夺”,其本质在于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把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进一步延伸到生产场所之外。福克斯说:“如今可以通过点击牟取利润”。(4)Christian Fuchs,“From Digital Positivism and Administrative Big Data Analytics towards Critical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32(1):38.资本不仅剥削雇佣劳动,而且通过把“生产线”内置到移动设备或 PC 端剥削互联网用户的无酬劳动,资本“隐性”延长使用雇佣劳动的时代已然来临。在福克斯看来,“大数据”这个词一点都不血腥,但它所代表的却很难说不血腥。“数据商品化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并加剧了互联网的剥削倾向。”(5)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3,p.46,p.59,p.57.资本正在被“全社会”所生产,平台规模经济正在大幅递增,但巨额回报却被拥有数据掌控能力的少数科技大公司私有化了。“大数据资本主义是由数据公司驱动的”,(6)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592.有获取、处理大数据能力的大科技公司正在利用大数据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
在政治方面,监视可以监视的一切,一种以猜疑、竞争、广泛性和个体化为基本特征的控制文化已然出现。“已经形成一个监控工业复合体。”(7)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3,p.46,p.59,p.57.借助预防犯罪、防止恐怖主义、沟通选民以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托词而进行的数据收集、存储和量化分析,其实都是在政治利益驱动下进行的。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证实,基于“算法公民身份”的监控是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维持自身运转的重要方式。福克斯揭露说:“大数据产生于资本控制(基于大数据的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国家对公民的监控源于这样一种错误思想观念,即解决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监控和警察国家)。”(8)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219.“大数据资本和技术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监控机制,它侵犯隐私和公民权利。”(9)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592.这种规模化、系统化监控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它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对人们思维、语言和行为的全方位操控。在福克斯看来,过度监督行为与其说是为了震慑破坏行动,倒不如说为了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施加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在全球化推动下,这种商业监控和政治监控复合体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伴已跨越国界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监控。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大数据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殖民扩张的、新的隐形工具。大数据蓬勃发展推动了传统“理论意识形态”向“大数据意识形态”的转型。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形式开始突破以往仅靠词语语句来传播和表达的理论形式,走向互动叙事、视觉、视听等更加丰富多样的感性形式,这加速了感性意识形态操控的崛起。“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经过算法设计的操控形式,即情绪和注意力的操控。”(10)Christian Fuchs,“Social Media,Big Data,and Critical Marketing”,in Tadajewski,M.(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Marketing,Routledge,2018,p.472.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出现高度分化并呈现出弥散性的特征。在福克斯看来,网络民粹主义、网络原教旨主义、政治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激荡交锋,都是意识形态话语多元和复杂化的表征。在这一形势下,福克斯敏锐地洞察到坚守文化唯物主义立场的重要性,他特别提醒说:“在不同的工作形式(信息工作、服务工作、体力工作等)中,都应看到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的嵌入性。”(11)Christian Fuchs,“Culture,Communication & Ideology=Forms of Work”,in Sava Çoban.(Ed.),Media and Left,Brill,2014,p.41.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个性化满足为外表的数据文化渗透,使得国家间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变得更加隐蔽和激烈。
(二)大数据资本主义重数据轻理论、重相关关系轻因果关系的科学思维模式并没有使科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失去价值和意义
大数据充分肯定经验数据在科学实践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但单纯的经验数据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科学实践中的解释、预测和技术应用,也代替不了人类理性对科学模型或理论的构造。福克斯认定:“用简单的算法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的。”(12)Christian Fuchs,“The Antagonistic Self-Organisation of Modern Society,”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2004,73(3):194.在福克斯看来,科学实践活动很难完全超越因果性探究而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相关关系上,以归纳推理为核心的实证研究也很难完全取代逻辑演绎的科学方法论。
第一,数据分析并不能代替经验与理论。大数据研究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人文计算、数字人文等新学科的出现,它们特别强调经验数据本身的自足性。“这种观念背后的新哲学理念是,足够强有力的计算程序可以探究海量数据集,并且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规则”。(13)Cristian S.Calude and Giuseppe Longo,“The Deluge of Spurious Correlations in Big Data”,Foundations of Science,2017,22(3):596.“大数据研究通过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经验主义彰显了归纳推理的重要性,自动的数据采集会直接催生新的科学发现。”(14)Fulvio Mazzocchi,“Could Big Data Be the End of Theory in Science? A Few Remark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Data-driven Science,”EMBO Reports,2015,16(10):1250.早在2008年,安德森就抛出“大数据意味着‘理论终结—经验主义重生’”的论断,并宣称“只要有足够的数据,数字就可以为自己说话”“面对海量数据,自然科学的主要进路——假说、模型和检验等一系列科学方法正在变得过时。”(15)Chris Anderson,“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Wired,2008,23(6).福克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重数据收集背后隐匿的危险倾向的洞察。“计算机科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开拓殖民地。危险在于,计算社会科学导致了理论的死亡,并根除了批判性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16)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9,p.48.在福克斯的理论视野中,大数据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数字分析并不能代替经验和理论,在没有理论或模型作切入点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数据的本质”。
第二,相关关系离不开因果关系。大数据开启了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思维革命: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取代“因果性”成为大数据探究的新目标,它强调归纳、推理等方法在经验数据中的应用。依安德森所言:“相关关系超越了因果关系,科学的发展根本无须自洽的模型、统一的理论或任何真正的机械论的解释。”“只要掌握了这些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17)Chris Anderson,“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Wired,2008,23(6).福克斯批判性地揭开了“相关关系”完美神话的一角。在福克斯看来,相关系数并非因果关系,计算机能看懂的只是“类数据”,因而并不能识别出数据背后因果关系并做出合理解释。由于热衷关注“相关性”,数据和现象背后的批判性、辩证性、因果实在性等问题信息确如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往往被视为形而上学问题而被回避掉或悬置起来。福克斯断言:“问题在于,多样化的数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种或同一类型肤浅信息,它使人们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或能给世界带来改变的信息和传播上。”(18)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594,588.
第三,大数据认知模式在科学认知过程的突显,催生了“大数据拜物教”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拜物教是塑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母体,幻化逻辑是商品拜物教的生成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讲,数据的商品化过程、幻化逻辑的展开和大数据拜物教的生成是同步进行的。在由商品拜物教向大数据拜物教转变过程中,经验数据被视为唯一的科学认知对象以及用数据间的关联关系取代传统科学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思维模式无疑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助推作用。在福克斯看来,紧随大数据而至的是大数据解决主义,“海量数据集可以控制、解决和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19)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9,p.48.它的口号是:一切事物都可以数据化,经验数据分析无懈可击,向计算机臣服吧!但福克斯随后又指出,通过大数据研究将使人类更富有、更民主、更安全的思维逻辑忽视了现实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大数据拜物教无视计算机技术使用的社会背景、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它主张用算法逻辑代替人类的决策和行动。”(20)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594,588.事实上,资本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在性质上都是拜物教的,因为它试图使特定形式的统治和剥削合法化、自然化、正当化。福克斯由此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役性现象正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三)大数据资本主义因充分张扬工具理性、剔除真实感性体验而陷入了纯粹理性主义的“云端仙境”
脱离人的感性体验的大数据算法类似于康德所指认的“纯粹理性”,极易造成感性体验缺失,催生“理性主义妄想”和“先验幻相”。“通过大脑的反射能力获得理性知识和通过感觉器官获得感性知识之间的康德区分被打破了。”(21)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6,p.74,p.48.
首先,大数据算法使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能力空前提升,但单纯依赖大数据的自动化决策并不一定能生成完善的科学决策。数字机器通过数据流产生的大数据对事件识别、分析乃至决策,仿佛跨越人机鸿沟具备了认知能力。殊不知,收集到的数据以及数据分析、预测方式都是主观上“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在福克斯看来,依托大数据的自动化决策只是“单纯模仿”大数据操控者赋予数字机器的理性形式,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逻辑的幻相”——经验数据和数据分析本身具有足够的自足性。事实上,“逻辑的幻相(误推的幻相)在于对理性形式的单纯模仿,它只是产生于对逻辑规则的缺乏重视。”(2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在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这一逻辑规则就是福克斯所极力批评的:“大数据资本主义将所有一切都置于市场的等价交换原则或算法霸权之中。”(23)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6,p.74,p.48.单纯依靠大数据科学地决策并不能直接导出完善的决策,究其根本,还在于科学决策往往都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效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工具理性逻辑的大数据算法虽然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原则,但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未必一定相等同。
其次,极致的数字化对工具理性的追求抽掉了道德、情感、伦理、价值等知识,贬斥人的感性价值,带来“博学的无知”和“虚假的社会价值”。数字机器通过传感器生成大数据,模拟和自动化人类体验,解决现实问题,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关怀、爱、和谐等人类独特的品质。福克斯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数据极具诱惑力,人们可能会越来越依赖它们,也会因此忽略很多更重要的因素。“大数据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往往无法将统计和计算研究结果与更广泛的人类价值、理解、经验、态度、道德价值、伦理困境、用途、矛盾和社交媒体的宏观社会学影响等分析联系起来。”(24)Christian Fuchs,“From Digital Positivism and Administrative Big Data Analytics towards Critical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32(1):40.福克斯进一步指出,凡是涉及决策,背后其实都有感性体验和价值标准,“大数据的数字实证主义逻辑只强调数据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却忽略了它潜在的负面效应。”(25)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588.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纯粹理性”的大数据算法知识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使得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福克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算法政治与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26)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6,p.74,p.48.如果不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谋求加以匡正,泛滥了的大数据更有可能成为大数据权力掌控者散布愤怒、煽动仇恨、推行维权政治的媒介。福克斯于2018年就写了《数字煽动家:特朗普和推特时代的威权资本主义》一书,详尽地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如何使用推特(Twitter)、借助数字和娱乐文化表达他的威权主义主张。(27)Christian Fuchs,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Pluto,2018,p.253.在福克斯看来,当“民主社会主义”的号角开始向大数据使用者的“感性真空”吹响时,“一种威权资本主义”“国家高压统治”和“狂暴右翼民粹主义”的出现就在所难免。
面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上述发展境况,福克斯认定:“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需要批判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28)
二、福克斯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重构
在福克斯看来,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大数据资本主义则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一方面,“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因果论、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可计算性和决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性,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种辩证否定,已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给现代社会带来灾难。”(29)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带向辩证的现代性,反而彰显了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二元论逻辑。那么,怎样才能突破和超越大数据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实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呢?
福克斯给出的答案是,看到大数据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数字技术,回到前现代技术。尝试创造全新的后现代技术,完全打破现有技术,这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拥有的每一项数字技术都具有二重性。它们在强化大数据解决主义和数据操控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合作和解放的潜力。问题的关键是,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结构、统治和剥削从来没有让社会和技术成为完全辩证的。现代性一再使理性走向它的对立面,摧毁了自身的发展潜力,并引发了灾难和危机。”(30)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9,p.45,p.49,p.45.福克斯强调,不应当抵制现代性,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重构现代性。据此,福克斯在把脉大数据资本主义后开出一张药方:辩证的数字现代性。它主要有“三味药材”配伍而成,即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有机融合。
(一)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与缺失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抽象工具理性的批判有助于破除传统主体/客体、感性/理性、人/机器、人/技术等二元结构,它是导致大数据资本主义感性缺失的逻辑根源。原本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启蒙理性,在资本逻辑强力推动下,在现代性的过程中被限制在了狭隘的工具理性范畴。大数据资本主义不仅延续了这一发展趋势,还进一步强化了工具理性传统和理性主义的功能化或绝对化,创造出新的统治和剥削方式。“每一种革命性的创新都承诺会将技术从垄断者的魔爪中解放出来……然而在所有的创新中,人性都一仍其旧。新网络并没有大刀阔斧地重新分配权力,而是被新的垄断者牢牢控制。”(31)[美]富兰克林·福尔:《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舍其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9页。为彻底挣脱启蒙理性带来的束缚,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主体性、中心性和同一性,以解构主义方法对现代性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也给福克斯大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带来了思路和灵感:“批判的、辩证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工具现代性的一种替代选择。”(32)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59,p.45,p.49,p.45.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将自身和现代性视作完全对立的两极,在解构中失去了对主体性的追求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洞察。其一,为解构传统二元结构对立,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消解中心性、主体性,以观念上的消除在场达到解放主体的目的,其最终结果是人被彻底忽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视角呈现出一片虚无主义图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具有严酷的批判力量。但它大部分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几乎不能帮助我们看到后现代的分界线,或者分界线以外的东西。”(33)[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孟庆时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页。福克斯直接指证,后现代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抵制并没有超越现代性,反而构建了另一种现代性。”(34)其二,后现代主义在猛烈的批判言辞中沦为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帮凶。“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机遇而非设计、解构而非综合、不在场而非在场、无政府状态而非等级制,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内在性而非超越性,等等。”(35)这种消极的解构,把工具理性、经济危机等消解为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实则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冲突产生的现实根源。福克斯一再申明:“需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辩证的分析。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自由主义。如果只看到它们的同一性,就忽略了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它包含着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潜力。”(36)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5,p.44,p.45,p.49,p.45.在福克斯看来,现代性应当是开放的、辩证发展的,可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改造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悖论。
(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有着反对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遗产的狂热,常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视为二元传统的一部分而将其解构。但福克斯认为,它们对构建辩证的数字现代性具有重要价值。
一方面,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矫正后现代主义无中心化和对“他者”漠视的偏差,弥补后现代主义的主体缺失问题。在后现代主义批判视域中,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批判的对象,这导致了一种“人学空场”。福柯就曾断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可能正在接近其终结。……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画着的一张脸。”(3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506页。由于“人”被遮蔽,后现代主义对失业、贫困等问题置若罔闻,只是把社会问题归因于僵化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则从主体角度对现代性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它致力于“重建人的总体性”。无论是萨特的“人学空场”理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还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在批判资本主义启蒙理性的前提下,都贯穿着一条力求现实地解放“主体性”的主线。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突显“主体性”而显然更具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威力。这同样给福克斯大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带来了思路和灵感。“关键是要以不同的、辩证的方式塑造技术和社会,使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不再处在分离状态,而是基于辩证现代性的逻辑,呈现出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38)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5,p.44,p.45,p.49,p.45.
另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有助于打破后现代主义无结构化的静态模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为了反对现代主义的规范性、同一性、目的性,后现代主义倾向于以碎片化的形式重塑现代性结构,以期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外观。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后现代状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拼装我们文化的碎片,并将之推至极限”。(39)[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这种对现代性亦步亦趋的无休止解构,使后现代主义陷入一种静态认知模式,催生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知识”世界。受老搭档钱德勒的启发,福克斯指出,“我们应当超越二元逻辑,把世界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整体来分析。”(40)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5,p.44,p.45,p.49,p.45.要做到这一点,“概括说来,我们需要再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且这种再现应同时体现在媒体、传播、文化、数字和互联网的批判辩证理论中。”(41)Christian Fuchs,“The Dialectic: Not just the Absolute Recoil,but the World’s Living Fire that Extinguishes and Kindles Itself,”TripleC,2014,12(2):874.福克斯给出的理由是,“它认为世界是以矛盾的形式发展的:任何现象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只能通过与另一种现象的关联而存在。”(42)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Routledge,2014,p.351,p.322.在福克斯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差别,但更多的是关联性,只有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视作辩证性两极,才能把后现代主义的静态认知模式转换为辩证的动态分析过程,使现代性得以在批判性、动态性和开放性观念中涌现出来。
(三)辩证的数字现代性的前景
福克斯对“辩证的数字现代性”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这样的未来不是前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一种辩证地实现了自身发现潜力的另一种(数字)现代性。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反抗,更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扬弃。”(43)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9,p.220.在福克斯看来,这种现代性将重塑现代数字技术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未来。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种现代性充分肯定了数字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同时融合了感性和理性,使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不相分离。“计算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但当工具理性塑造计算机技术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时,问题就出现了。当计算机技术不能替代而是助力人的活动时,人性化的结果就产生了。”(44)Christian Fuchs,“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TripleC,2017,15(2):608.另一方面,它还坚持了将大数据与大数据的资本主义使用相剥离的理论立场,这需要通过“占领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数字机器的占领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为取代数字资本主义而战,以及数字和互联网的去商品化、去资本化和去商业化。……当数字公民组织被发动起来去颠覆数字资本逻辑、推动数字共享超越和废除数字资本主义时,数字占领有望成为数字斗争的一种有效形式。”(45)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9,p.220.福克斯非常乐观地认为,占领运动标志着社会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是社会运动的一种黑格尔式扬弃。(46)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Routledge,2014,p.351,p.322.
三、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与重构的限度
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是切中肯綮的,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构蕴含着他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新的可能性的积极探索,但福克斯试图借助于“辩证的数字现代性”来打破大数据资本主义对人的抽象统治则显示出其批判理论的限度和无出路状态。
第一,福克斯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重构是主观的、不彻底的。一方面,福克斯基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抽象存在”展开批判,从重构主体性认知视角寻求解决之道。在福克斯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高度工具化的社会,大数据资本主义则是这一工具化社会的最新表现,它引发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但是,工具化社会是概念化的虚假意识而非现实存在本身,福克斯显然混淆了现实与抽象的关系。“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福克斯以抽象的“辩证的数字现代性”去批判抽象的存在,偏离了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方向。马克思指出:“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216、547页。必须回溯到马克思感性活动的演进脉络,即大数据是人的现实感性活动的产物,必须在人的现实感性活动中使之革命化,而不能使之凌驾于感性活动之上。“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另一方面,资本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是人的感性活动被放逐的罪魁祸首,福克斯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重构并未超出资本确定的旧世界、旧结构、旧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时,便已跳出理论演绎的怪圈,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216、547页。要使大数据在人的现实感性活动中革命化,必须穿透大数据构筑的外在堡垒,深入到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之中。大数据作为社会经济和现代性发展的新的驱动力,固然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诸多领域的权力结构,然而,大数据资本主义即便是穿着大数据外衣出场,也仍处于资本编织的“权力场”中,必须服从于资本生产的总体性逻辑。“大数据资本主义预示着关注焦点的转移,它是一种新型资本和新的资本积累方式的概念化变迁。”(51)Jathan Sadowski,“When Data is Capital:Datafication,Accumulation,and Extraction”,Big Data & Society, 2019,6(1):9.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大数据资本主义是数据信息资本化的结果,是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现代性生活状态。因此,批判和扬弃大数据资本主义,打破数字资本的垄断,应置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大数据与资本持续互动的“总体性权力”布局上,断然不能脱离资本逻辑来抽象地批判大数据资本主义。福克斯显然忽视了产生数据垄断的因果关系:数据垄断产生于数字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脱离资本增殖这一最高目的的批判与反抗只能是无的放矢。这样一来,福克斯原本想借助辩证法实现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重构,却因不懂得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深刻要义而只能“寿终正寝”。更何况,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操作起来相当复杂,原本就面临许多新的现实挑战,且这些挑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组织性、法律性、社会性,甚至是文化性的。
第二,由于未将感性导向对象化活动,福克斯“辩证的数字现代性”沦为一种抽象的主体性认知,导致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脱节。一方面,福克斯沿袭了康德对感性理性的划分,也无可避免地继承了康德哲学先验论的缺陷,福克斯的感性与理性认知存在着一个无法弥合的逻辑鸿沟。具体而言,福克斯预设大数据资本主义“感性—理性”“主体—客体”的对立框架,并将消除这种形式上的对立视作问题根本,在逻辑思辨中陷入形而上学。福克斯认为,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二元逻辑造成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感性缺失问题。“我当然同意,主体/客体、文化/自然、人/技术、意识/身体、社会/经济、交往/劳动、再生产/生产等二元逻辑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关键方面,它适得其反,造成了全球性的社会治理难题。”(53)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4.为了弥合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感性理性裂痕,福克斯为后现代主义补充了一个感性“数字主体”,但这是一个强加的框架。这是因为:“自康德以来,自我占据了双重位置:既是世界上的一个经验主体,表现为众多客体中的一个;又是一个面对世界的先验主体,并把世界作为一切经验对象的总和加以建构。”(54)[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感性活动这一能动的、实践的基础,福克斯不得不求助于黑格尔辩证法,试图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来实现现代性的连续性、动态性建构。福克斯是这样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可以描述为主客体的辩证法:一个主体为了生存而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55)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Routledge,2014,p.360.在福克斯看来,主客体的辩证性运动能够打破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二元逻辑的机械对立。但问题的关键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上的动态认知,而非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世界的辩证运动——人的感性活动。结果,打着辩证法旗号的福克斯只能止步于针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抽象批判和外在性超越。“不管是丹·席勒还是福克斯都没有充分利用批判辩证法,使他发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作用”。(56)参见 [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加]文森特·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下), 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第782页。
第三,由于没有找到现实的革命主体去打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樊笼,福克斯的革命理想最终只能以乌托邦主义的方式谢幕。福克斯陷入了一种抽象主体的实践规划中,仅凭一个抽象“数字主体”根本不可能打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也无法将对大数据的批判“照进”资本主义现实世界。这种理论上的抽象性质,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假的阶级意识,无疑是福克斯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的真正薄弱之处。这一情形十分类似于齐泽克在《捍卫失落的事业》中所强调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种看似可疑又太过简单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承诺一些理想却不可能实现的修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抗,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57)Slavoj Ziz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Verso,2008,p.6.由于受“数字主体”幻相制约,且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限制在大数据框架内,福克斯只能谋求在“数字公域”中发动“占领运动”。需要注意的是,福克斯视野中“占领运动”只是一种工人阶级对剥削关系的集体洞察力和反应,一种为共同占有经济和社会交往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形式,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在高度复杂、信息技术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根本性问题迅速推向前沿,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任何革命或变革都难成气候。“没有一个明确的替代体制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的抗议运动从来没有胜利过: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想胜利。抗议运动甚至还有一个术语:‘拒绝胜利’。”(58)[英]保罗·梅森:《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熊海虹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页。试图在不触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占领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方向迷失,它固然可以给人们带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体系的希望,但并不具有力挽狂澜、剑走偏锋的实践效用,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切实摆脱大数据资本主义困境的现实道路,而是更多地停留在了修辞层面,由此也很难促成一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实际运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结 语
大数据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为摆脱资本积累严重过剩、缓和由此带来的更迭难休的经济社会危机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危机延缓、矛盾修复和资本增殖机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条件和方式所做的新的调整,它以大数据神话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基于资本逻辑(尤其是数字资本逻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抽象统治。福克斯虽然指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意识到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和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站在自己的独特立场上对大数据资本主义进行颇为深刻的批判性分析,洞察到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性质,但却停留在分析资本主义“普遍异化”现实的直接性上,且从主体性方面寻找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因而未能将这一理性批判与建构贯彻到底。这就意味着,福克斯已降的大数据资本主义批判徒有批判和建构的外观,而无批判和建构的实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克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忽视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单列一节讨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指明两条通达现实的思想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科学的起点是从感性的具体出发,从中分离出抽象的规定(从具体到抽象),但要呈现对象的整体必须从抽象回到具体,把对象理解为事物,呈现为规定性的统一体,呈现为概念中的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福克斯堪称“完美”地走完第一条线性分析的道路,却未能走好第二条道路。以批判和审视的眼光从有效的普遍概念中推演出有真实关系的论断,解释真实的现状,并巧妙地运用历史辩证法的“圆圈”打通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核心内涵和生命力之所在。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本身,只有确立满足人的现实价值需求的大数据发展导向,只有在推进数据和数据分析去商品化、去市场化(“非商品”式供给),尤其是扬弃私有制的现实运动实际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摆脱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理性算计和数字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