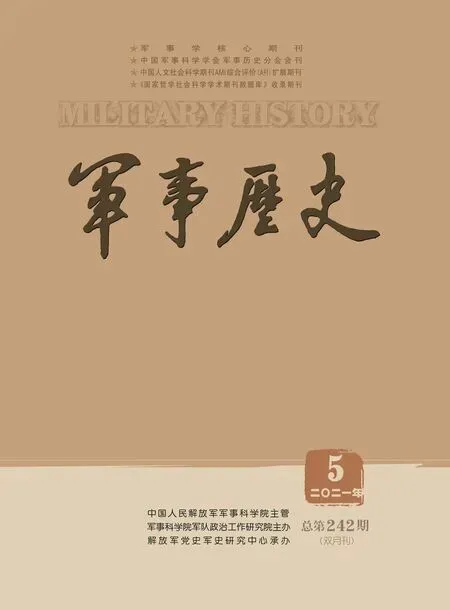《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军事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荚 丽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孙膑兵法》的出土,不仅使得《孙膑兵法》是否存在的疑团涣然冰释,而且为研究战国时期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对《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军事伦理思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兵学体系、战略追求和治军作战的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等方面,《孙子兵法》是《孙膑兵法》始终所无可比拟和无法企及的,但《孙膑兵法》的军事伦理思想较《孙子兵法》有了长足进步。
一、战争伦理观——从“安国保民”到“战胜而强立”
无论是《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是《孙膑兵法·见威王》的“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都鲜明地显示出两位“孙子”对战争的慎重态度。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安邦定国的,唯有以战止战才能实现王道。由此,两人的战争伦理观也是一脉相承的,从“安国保民”到“战胜而强立”,明确了保家卫国是决定和统率军人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伦理原则。
在举兵用战与安邦定国的关系上,孙膑的看法与孙武如出一辙,在突出“兵”之重要的同时,强调“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①《孙膑兵法·见威王》。,把战胜作为强国的首要条件。孙膑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以禁争捝。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②《孙膑兵法·见威王》。他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分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就会爆发战争,此时唯有以战止战,而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改变。战国中期,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上的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孙膑主张“战胜而强立”,明确指出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国家统一,即使是圣君也需要用战争“禁争捝”,为了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仅仅依靠仁义、礼乐、礼让是不可能的。“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①《孙膑兵法·见威王》。,充分说明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强大必须要靠战胜来实现。那么,如何实现“战胜”的战略目标呢?孙膑否定了当时诸学派以“政教”“散粮”“静”等为强兵之道的观点,提出适应政治形势和思潮的“富国”论,认为“富国”才是“强兵之急”②《孙膑兵法·强兵》。,即发展经济才是强化军事实力的硬道理。由于简文残略,孙膑“富国”主张的具体措施不是很清楚,但仍存有“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③《孙膑兵法·篡卒》。之语,深刻揭示了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和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孙膑把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孙武“安国保民”的战争伦理观里,比较亮眼的是其“兵以利动”的思想。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孙子兵法》存世十三篇,全文共有6111 字,其中正文字数6075 字,题目字数36 字,可谓字字珠玑。其中,用“仁”字3 次,“义”字1 次,“利”字则有51 次,其重利轻仁的态度,跃然纸上、一目了然。比如《九地篇》中“令于利而动,不令于利而止”,《火攻篇》中“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军事篇》中“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令为变”等,可以说,“求利”“趋利”是孙武确立的最高战争伦理原则,也是其选择、运用战术的一条重要出发点和归宿。在孙武看来,“求利”是战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不求利益的战争,没有一定利害关系绝不轻易参战。《谋攻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里又一次明确了其战争伦理原则——军事功利主义。养兵用战,目的就在于“争利”,而不是穷兵黩武,揭示了一切军事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本国、本军和本国人民利益的本质。孙武一扫传统军事伦理仁义、礼让的说教,提出了“兵以利动”“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伦理思想,在当时能毫无顾忌地打出“利”字大旗,改变之前传统军事伦理迂腐古板的一面,把强烈的功利意识贯穿于通篇,可谓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大特色。当然,孙武虽然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同时也注意到“利动”可能带来的误导,因此特意在《见吴王》(银雀山汉简)中强调了战争的起因和目的都是为了争利,战争是争利的手段,不能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思想。在孙武看来,有利、有得、国危是发动战争的三个主要原则,他只是“利兵”而绝非“好兵”。
与孙武重“利”有所不同,孙膑更加看重“义”,而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伦理观由重“利”向重“义”演进的时代写照。两人的着重点虽有所不同,但终究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战胜,只不过由于着眼点和思考路径不同,导致战争伦理观也有所不同。孙膑在孙武“兵以利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胜非所利”的主张,这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治了孙武“令于利而动,不令于利而止”可能产生的偏颇和流弊。然而,不论孙武还是孙膑,他们都没有阐明保家卫国到底是在何种背景下实现的目标。“非危不战”的“危”,究竟是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时面临的危局,还是因为国内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引起的混乱,抑或是诸侯争霸制造的假象,孙武并没有详加阐述;而孙膑提出“战胜而强立”必须以义战为前提,但对于什么是“义”或“不义”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读,所以尽管观念上主张正义战争,但是事实上“正义”的内涵需要服从国家政治与安全需要,甚至是君主主观意向,这就为非正义战争埋下了祸根,也为肆意发动战争提供了理由。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保家卫国的战争伦理观,在实践中往往很容易走向与“正义战争”相悖的窘境。
二、治军伦理原则——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到“人为贵”
战国时代的兵家在治军之道上,多趋同于孙武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④《孙子兵法·行军篇》。,大家都很重视“和军”,但是,在如何“和”的问题上看法又不尽一致。
孙武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治军“德法同济”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行军篇》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在孙武看来,只有把“文”“武”二道的建设结合起来,导之以德,严之以法,才能把军队建设好。从将帅修养角度来说,对士卒只威不爱,不仅难以立威,而且容易养怨兵、生叛心,只有爱威并举才能真正获得士卒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唯有如此,才能在将帅和士卒之间建立起互相依赖的良好关系,平时养成令行禁止的好习惯,战时“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①《孙子兵法·九地篇》。。而从士卒的角度而言,如果只是贪图自由宽松,而无视军纪之严酷,就很容易“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②《孙子兵法·地形篇》。,自然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因此,只有“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善养“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的“可用”之兵,才是真正的治军良策。
孙膑也认为治军作战离不开“人和”,《孙膑兵法·兵情》充分诠释了“人和”的“兵之道”,指出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密不可分,只有精诚团结、密切配合才能克敌制胜。在“人和”思想的基础上,孙膑尤为强调“人为贵”的价值思想,并将这一价值理念运用于治军中。《月战》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充分肯定了军人在军事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与决定性作用。从篇名看,该篇其实是在讨论战争与天时的关系。古人崇拜日月星辰,以日为阳精、月为阴精,认为“兵尚杀害,阴之道也,行兵贵月盛之时”③《左传·成公十六年》孔颖达疏。。孙膑所谓“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即是这种观念的一个例证。但是“十战八胜”之月能,终究不如“十战十胜”之人功。而之所以能十战而十胜,就是因为将帅善于治军的作用超过了天时的作用。从《月战》首句的“莫贵于人”到结尾一句的“将善而生过”,足以说明孙膑充分肯定人的因素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可贵的,孙膑认为“德行者,兵之厚积也”④《孙膑兵法·篡卒》。,只有那些有德行的贤良之才、善于团结人的人才是可贵的。无“德”之将,无“气”之士,不“和”之军,即便是装备优良、将多士众,也不足以称其贵。
对比两部“孙子兵法”,可以发现孙武和孙膑都主张“和军”,在对待士卒方面都提倡“爱卒”“教卒”。但不同的是,孙武一方面主张将帅要爱护士卒,视之如婴儿,另一方面却又把士卒当作工具来使用,主张实行愚兵政策:“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人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⑤《孙子兵法·九地篇》。而孙膑一方面继承了孙武爱卒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辩证阐述了“爱卒”与“用卒”的关系,提出对待士卒要“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⑥《孙膑兵法·将德》。,即平时对待士卒要像对待孩子一样,但真正到了战场上要舍得用兵、敢于用兵,用士卒的牺牲来换取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孙膑主张对待士卒要既爱且敬,这是孙武所没有的,而这也正是孙膑“莫贵于人”人本思想的体现,反映了孙膑对生命的珍视与敬畏。孙膑认为战争胜利取决于每个士兵的主观努力,要充分调动起每个士卒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爱惜他们。由此可见,孙武和孙膑都重视“和军”,重视人的作用,但孙武更重视人的工具性价值,孙膑更重视人的目的性价值,这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治军伦理由人的工具性向人的目的性的演进过程。
三、将帅武德修养——从“五德”到“知道”
历代兵家都极为重视将帅武德修养,孙武将“智、信、仁、勇、严”这“五德”作为将帅修养及选将任贤之道,赋予其特定的军事伦理内涵。后世在用将之道及将帅素质修养等的设计上,虽然标准不尽一致,但差异中有大同之处,即美德与功利相结合。将帅的选任和修养的提升,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打胜仗的功利目的。
《孙子兵法》首篇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孙子兵法·计篇》。这既是其选将用将之道,也是对将帅素养的基本要求。就此,孙膑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②《孙膑兵法·八阵》。认为将帅只有懂得用兵之道,才能保卫国家和人民,才能树立国君的威信。所谓“知道,胜”“不知道,不胜”③《孙膑兵法·篡卒》。。在孙膑看来,“知道”是通往一名优秀将领的必经之路,将帅是否“知道”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孙膑的“知道”包括了智、义、勇、数战、得民心、知敌情等素质,他认为这些是成为“王者之将”不可或缺的。可以看到,孙膑的“知道”与孙武的“五德”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各自的观点。
孙武更加看重“智”,他把军事人才视为国家栋梁,“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④《孙子兵法·谋攻篇》。,因此将帅的“智德”尤为重要。所谓“智德”,指的是“个人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在追求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秀道德品质”⑤肖群忠:《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 页。。在军事领域,智德就是特指在治军和用兵过程中,通过道德培育和个人养成,从事军事活动的军人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对军事及其相关领域科学知识、智慧才能以及道德价值的崇尚、热爱和积极追求,以及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按照一定军事原则和规范正确运用智能减少战争伤亡、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秀品质,包括崇知尚智、变革创新、慎战智战、以智求善、追求正义战争等。智德,超出了一般作为战术才干层次上的释义,在更高的道德层面赋予一种敢于坚持功利原则的军事伦理内涵。“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⑥《孙子兵法·九变篇》。,在孙武看来,是否符合军事功利原则,符合“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是衡量有无智德的根本标准。
相对孙武看重“智”,辅以“信、仁、勇、严”,孙膑更加看重“义”,辅以“仁、德、信、智、忠、敢”。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主要是因为孙武重在以战争看战争,看重战胜之道;而孙膑重在以政治伦理看战争,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和伦理上的得失。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是比较纯粹的战争哲学,《孙膑兵法》则赋予战争更多的政治伦理要求。春秋和战国时期在战争实践上都惯用变诈之兵,但是从战争伦理看,春秋尚诈,战国尚义。这说明,战争伦理的发展通常并不和战争实际相同步,往往表现为现实中缺什么、理论上就提倡什么。春秋前期,战争持续时间不长,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天,当时诡诈还没有成为人人奉行的战争规则,因此,孙武第一个大胆提出“兵者诡道”的主张。而当“诡道”成为人人都奉行和遵守的准则时,人们才明白用道义对战争行为进行制约是多么重要,因此倡导仁、义、礼、让的战争伦理,主张战争需要有道德制约。然而,诡诈之风既然已经形成,再欲代之以仁义、举之以道德,就显得乏力了。因此,战国诸兵家虽然理论上都倡导效仿商周古军礼,但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基于以上分析,不难明了为何孙武主张进入敌境之后实行“侵掠如火”⑦《孙子兵法·军争篇》。“‘重地’则掠”⑧《孙子兵法·九地篇》。,而孙膑则主张恭暴相错、不亢不卑。显然,孙膑的主张更具道德高度,追求既不要过于谦恭,也不要过于残暴,因为过于谦恭会招来敌国轻视,而过于残暴则必使敌国顽抗而致兵力大耗。由此来看,孙膑比孙武又往前走了一步。若将此作为逻辑起点,孙武的战争伦理重点向人的工具性展开,而孙膑的战争伦理重点向人的道德性展开,因此形成孙武尚智、孙膑贵义的将帅武德修养差别。
四、军人道德选择——从“君命有所不受”到“御将,不胜”
无论是孙武的“君命有所不受”①《孙子兵法·九变篇》。,还是孙膑的“御将,不胜”②《孙膑兵法·篡卒》。,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思想,那就是将帅不能过于受制于君主。当然,封建政治体制下权力来自最高统治者,整个封建政治体制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平稳运行。所以,关于“君命有所不受”“御将,不胜”等,凡此种种,都是极有限度的。历代兵家谈到军纪的时候,首要强调的必然还是“军令如山倒”和“顺命为上”,然而“君命有所不受”“御将,不胜”,这些也的确是战场上所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出现了这样的道德冲突,到底是服从命令还是机断处置呢?这其实也是军人经常遇见的一种道德冲突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道德冲突?主要是依据两个原则:一是“求实”原则,也就是视具体客观条件、实际情况而决定;二是“价值”原则,就是将帅作决策时要以是否符合保家卫国的最高价值目标为标准。
据目前可见史料,首次提出“君命有所不受”观点的是司马穰苴而非孙武。司马穰苴与孙武皆系田完后裔,处同一时代,而比孙武稍长。穰苴约卒于公元前518年,而孙武则是在公元前512年始为吴将。相传穰苴被齐景公初任将职时,曾斩违令的监军庄贾“以徇三军”,景公遣使持节赦贾,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③《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穰苴此举,不免让人联想到孙武吴宫教战斩二姬之事。姑且不论谁先谁后,孙武强调“君命有所不受”原则,为解决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置的道德冲突确立了一条科学的选择方针,这一方针蕴含着“求实”与“价值”原则的相统一。“求实”原则以真理性的要求,赋予了将帅临机应变、果断处置的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价值”原则则以至善的要求,强调将帅负有保家卫国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责任和义务。道德选择的自由“权利”与必然的“责任”“义务”的统一,正是“君命有所不受”的伦理真谛。
关于胜败,《孙膑兵法·篡卒》列出了五个关键因素:“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孙膑认为可能导致军队打仗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御将,不胜”。当然,诚如孙武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主身处国家权力中枢,对于军事行动不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当然,英明的君主也应该学会努力克制自己,适当放弃自己的判断,毕竟战场上瞬息万变,而身处其中的将帅才是最了解战场实际情况的人。古代作战不像今天这样交通便捷、信息透明,一句“家书抵万金”足以说明当时人们传递消息的困难程度。如何将千里之外的军队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又能把仗打胜,这是千百年历代帝王绞尽脑汁思考的难题。唐代安史之乱中,哥舒翰认为潼关非常重要,一定不能轻易出战。但是唐玄宗置之不理,反而批评哥舒翰,严令他出关迎敌。最后哥舒翰“恸哭出关”,不出意外地中了叛军诱敌之计,二十万大军仅几千人生还,唐玄宗只得丢弃长安逃往四川,唐朝从此由盛转衰。所以,正如孙膑一直主张的,“不得主弗将也”④《孙膑兵法·篡卒》。,将帅与君主之间需要的是互相信任与支持,需要的是互相配合。当然,这个尺度在实践中确实很难把握,既需要君主的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心胸开阔,也离不开将帅的精忠报国、有勇有谋、肝胆相照。
五、军事道德环境——从“众陷于害”到“战日有期,务在断气”
孙武从实战中深刻地感受到道德环境效应的军事实践意义,他在《九地篇》中反复强调将帅必须善于适时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而《孙膑兵法·延气》提出“战日有期,务在断气”,即交战日期一旦确定下来,就应该实行“断气”,其具体方法是:“将军令:军人,为三日粮;国人,家为……断气也”。交战日期确定后,要求全军将士每人只准备三天的口粮,为了国家、个人和家庭而决战,这就是断气。可以看出,在军事道德环境的创造上,孙膑与孙武的理念是大同小异的,其精髓是一致的。
“众陷于害”环境创造的道德意义在于:首先,军人会更加勇敢。孙武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①《孙子兵法·九地篇》。军队被“投之无所往”,也就是无路可走了,如此,主客观上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不得已则斗”,怀着“吾将示之以不活”的决心去死战的军队,往往却可以绝处逢生。其次,军人会更加服从命令听指挥。孙武说:“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②《孙子兵法·九地篇》。如何可以“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呢?这其实正是“众陷于害”的环境给将士们带来的积极的道德心理体验效应。再次,军人之间会更加团结。孙武说:“无所往则固”;“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③《孙子兵法·九地篇》。当军队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唯有决一死战时,大家一定会空前的团结互助、同仇敌忾。
很显然,孙膑的“战日有期,务在断气”继承了孙武“众陷于害”道德思想的内核,他们都认为优秀的将帅应该善于体察士卒道德心理的发展与变化,适时地营造“众陷于害”的环境,激发其积极道德情感的生成与道德潜能的充分释放。当然,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众陷于害”也好,“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也罢,绝对不是置士卒的生死于不顾,这里的“害”“断气”,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体验,它们是让士卒充分地体验到“危境”状态,同时又不惧怕和气馁,相反地,这种体验可以激发出士卒更大的勇气和斗志去奋战杀敌。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典兵学奠基之作,蕴含着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孙膑兵法》中有关军事伦理思想,是春秋时期军事伦理思想向战国中后期军事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从《孙子兵法》到《孙膑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对军事伦理的重视与发展,其中的伦理底蕴和理性光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汲取精华,为新时代强军兴军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