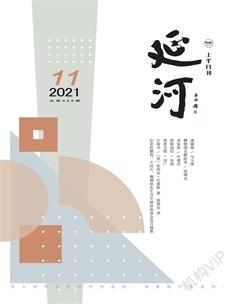白马还乡
蒋兴刚
喂,别把我丢掉
搬家的时候,院子里唯一搬不走的树成了心事。走的时候,养的鸡鸭可以装进石棉袋,到了新地方把它们一放了事,如果新地方不允许养鸡,也可以宰了犒劳自己。猫狗也是,到了新家比人熟悉还快,几天下来都找不到它们。
到了搬家的最后一天,能移动的都搬走了,再回头看自己认为最熟悉的地方,会发觉很陌生,它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连门窗也被卸下抬上了车,我与它还有什么瓜葛?家一旦被掏空,就是一坨水泥、一堆砖瓦,冷冰冰地放在那里。
终于把家搬空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什么没有搬干净,在床上思来想去,辗转反侧。会有一个声音不停在耳边喊:“喂,别把我丢掉。”
借着晨曦回到老房子,那棵歪脖子树似乎歪得更厉害了,披头散发搁在围墙上。记得种下它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父亲觉得门前侧角荒着,种一棵大树可以招财,也可以用来拴狗绳,于是趁下夜班不知从哪里顺来一棵。树开始一直朝树的模样长,生叶拔枝,在一个陌生地方,树远比人容易适应。长个三五年就基本长成了树的模样。树冠被一对喜鹊看上,开始有了鸟窝。我把头伸出窗户,刚好看到鸟窝里的一举一动。奶奶说过,喜鹊上门是好兆头。
大树的脖子歪得有些突然。树正对院子大门,大门正对大路,大路对着柴岭山。有一年,一阵来自柴岭山的歪风推开了院门,缠住了大树的头发不放,好像树的原主人,寻找多年终于在这个角落发现了它,拼了命要把它拔回去,而树早已在这里扎实了根。于是整整一晚,歪风撕扯,扯得满地都是风声。
大树留了下来但侧向了一边。那时我想父亲没有把它及时矫正过来,或许心上也有愧疚。我是站在树这一边的,毕竟树的命运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树已经适应了这里,这往往需要付出五年十年或更久时间。树越老越歪越靠近围墙,成了家的一部分。
大门被卸掉之后就像一件中山装的领子被卸掉了,堂前再无法关闭。这座房子里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现在明显发生了变化。儿子练毛笔字的纸,小狗小花磨牙用的仿真骨头,母亲从社坛庙求来的神符……这些它特有的味道再也闻不到了。整个村庄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有补偿款传来的油腻气味,有扔掉的老棉袄旧衣衫的陈酸气味,有满满一车家什压在车胎上、橡皮轮胎猛烈摩擦地皮的气味,它们掺和在灶台炒菜的肉香味、晒太阳的床单味和女主人的脂粉体香味里……
它们是各种不知名的微小尘粒。
整幢楼从没有像这一刻这样安静过,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尖叫。来到自己的床榻位置,我能想象从前的我是如何在上面折腾,面对嘈杂的人世,这里是唯一私密的,我的床铺位置积满了灰尘。这些灰尘就像一粒虫、一棵草,在它浩荡的群落里孤单地面对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其他的尘埃不可能知道……
我再把头伸到窗外,歪脖子树上的喜鹊窝不知去了哪里,它们是不是也搬家了?它们是不是也会飞回来看看这里的过往……
记忆追上我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金家河在缓缓流淌。再仔细看,这条河流幻化成无数细小水珠进入岸上的庄稼、稻田、房屋、耸入云端的大树……它们闪闪发光,最后又汇聚在一起,进入我的身体。仿佛一条线,紧紧把我和金家埭串联起来,我知道我这辈子就如自由的风在上面生发,风里散发着我的童年和青春的气息。
最早的记忆是一种感觉。和每一个村里人一样,被父母带到人世,住到一所住过几代人的房子里。每天,听到鸡鸭叫就醒来,撒上一泡尿,然后去院子里走上几步。看着家里人一个个出门忙各自的事情,开始我也会紧张,想他们会不会丢下自己不回来了。日子久了,就会感到这没有什么不正常,他们偶尔会急匆匆地回来上个茅坑拉泡屎,或者,回来做顿饭又出门。到了黄昏,出去的人都会回来,挤在房梁下,一天就过去了。
金家埭人这种养娃、过日子的方式延续了几百年,估计和金家埭人种地、种庄稼得到的经验有关系。春耕撒下的种子,时间一到就顶到地面上,每天正常的日照、雨淋,它们就可以自然地长高长壮实,时机成熟了就能被收割,它们就是一堆时间的附属物,仅此而已。
刚满六岁,父亲就告诉我这很重要,说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一个人在院里院外跑,大人们在忙碌,在晒太阳,不理会我会不会摔跟头,会不会尿在裤裆里。我已经学会扑蝴蝶、蜻蜓,能和隔壁的孩子玩躲猫猫。如果肚子餓了,也会爬上餐桌够点剩菜剩饭充饥。
我是先学会扑蜻蜓还是先学会扑蝴蝶已经记不起来了,就像小时候吃过的蒸糕、发糕、清明团子,早忘了当时的香糯。金家埭到了春夏之交,荒地里、田埂边、池塘对面,该绿的草木都绿了,该开的花都开了。棒头草、山高粱、酢浆草、蛇莓、猪殃殃……五彩斑斓。这时候的金家埭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簇拥在花草的海洋里。那时候,见到红彤彤的蛇莓,总想摘一些尝尝。比自己大几岁的狗蛋阻止了我,说吃了会变成哑巴。
金家埭的蝴蝶是一夜之间摸进来的。推开窗,突然发现围墙上、石臼上一大堆蝴蝶在扇动翅膀。有些蝴蝶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停在围墙上就像一叶叶绿草;有些翅膀的正面却是金黄色,上面还有一些花纹,飞舞时就像是朵朵金花;还有一些带黑色斑点的白蝴蝶,扇动着翅膀上下翻飞,像朵朵可爱的小白花。它们一会儿翩翩飘在空中,一会儿又悠悠落在物件上,好像是蝴蝶变成了花朵点缀着院子,又像是花朵长出了翅膀飞舞在空中。它们开始一定是冲着墙外的花草香来的,飞入我家院子,纯属串错了门,但它们发现院子里面清幽,散发着生活的况味,就再不愿散去。那些日子抓蝴蝶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背着奶奶用零布头做的大网兜,从院里追到野地……我把“空中花朵”养了起来,搁在窗台上欣赏。
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正在长大。我家有一条小狗,我给它取了当时我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名字——小花。小花是流浪到我们家门口的。那时,金家埭家家户户都热衷养狗,壮年时可以看家护院,等到老了可以宰了做红烧狗肉。小花应该是被狗爸狗妈遗弃的。某一个早晨,奶奶出门看到冷风中的它一副可怜的模样,动了恻隐之心,便把它留了下来。
我带着它一起跑,一起转进围墙外的荒地去疯去野。这条狗也渐渐成为一个孤独者,没有见到我就趴在鸡窝边上发呆。我的三个姐姐给它骨头,它也只是礼节性地嗷上两声,从不主动缠上去。小花是一条认人的狗,来家没多久它就能分辨出人的脚步声,如果是我回来,它会第一时间窜出墙门。
小花整整陪伴了我五年,直到某天起床,忽然发现它不见了。一条突然消失的狗,让我把整个村庄翻遍了,我去我们耍过的草甸上、沟渠边、河埠头……还是踪影全无。它像被淹没在金家河,而水面已经被风抹平。那时候我常常梦到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条肚子饿扁的狗,在为一根干骨头走村串巷、挨家乞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从它的影子里走出来。
小花的消失成为我童年最无法释怀的事。哪怕之后我家有了第二条第三条狗,哪怕它们更加忠心地对待主人,也无法激起我对狗那份最原始的喜欢。我会像调教一头小牲口那样调教它们,偶尔还会脱口骂上几句粗话。
在我们那个大家庭中,奶奶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个老式的裁缝师傅,就是那种用手摇缝纫机做衣服的手艺人。她年轻时在很远的地方谋生,老了回到她的故乡,养养鸡鸭,种点小菜,也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奶奶重男轻女,孙儿四个中处处护着我。她把糖果、糕点分成两份,我占一半,三个姐姐占一半。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很少生气,遇上与周边邻居、远房亲戚有人情往来,她也会从夹袄袋里摸出两张纸币。每年夏天,奶奶都会用她的私房钱给我们姐弟买冰棍、汽水和绿豆汤。
奶奶对吃不是特别讲究,最开始还吃点荤菜,到后来就以素食为主。她的穿着比较讲究(相比其他居住在金家埭的人),这应该与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她在村里的人缘不错,在我的记忆里,上门做衣服时要是有人背地里谈论别人的坏话,奶奶会替那个人辩解……
记忆就是一艘漂浮在金家埭旧时光里的船,一闭眼,舵就掌握在一根草、一把稻穗、一排树手里。后来,奶奶归了佛,成了一个虔诚的人!
西河路和西河路的玉兰树
玉兰树又长高了一截。蔡天新说,你要是去到一个陌生地方,想快速摸清这里的情况,就仔细看看当地的植物,或许就能瞄出端倪。这话出自一个去过近百个国家的旅行家口中,我相信了。
西河路上种的是玉兰树,一种落叶乔木,每隔十米一棵,排布得整整齐齐。如果非要说西河路的玉兰树与别处的玉兰树有所区别,真的有些刁难人的意思。就像在西河路上生活的人,他们分开是一个人,聚在一起是一群人。西河路的玉兰树也是这样,它们聚在一起,具有了无比强大的排他性,或许就是最大的特色。
每年早春,我把头伸出鸽子楼,就能看见风从眼前跑过去。
风跑到西河路就成了跨栏运动员。它们从萧然山和北干山的豁口进入跑道,一棵玉兰树一棵玉兰树的跨越,它们既要保证风速,又要面对高栏的阻隔,只得放下姿态与脾性。一段路跑下来,它们裹挟着的冰雪的寒气,就被消磨得寥寥无几。
风跑累了经常会停下来休息,这时候,它们会抱住楼下的几棵玉兰树不停地摇。很多次,我都感到烦躁且气愤,好好的玉兰树又没招谁惹谁,干嘛这样死缠着不放。但当我早晨醒来,楼下的玉兰树往往是整排玉兰树中最早开花的那几棵。
很多玉兰树就这样争先恐后地在不经意间开花了!
有时我在想,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上天安排好的,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它们总在我们不经意间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玉兰树不光在花季受人关注。早些年,菜价、肉价还没高到离谱,周围的住户家家要灌香肠、晒鱼干、腌白菜、酱板鸭鸡腿。因为西河路住的大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陆续都安家到了外面,西河路上的几百户每户身后都隐藏着几户小家庭),酱货、腌货都是一批又一批地做。在相同的时间段,这么多酱货、腌货,必须及时晾晒,才能拔出里面的鲜味,这就需要兰树发挥它的作用了。不难想象,近年底时西北风爬上树,玉兰树的叶子也掉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家家户户叉上树杈的美食。
日子久了,西河路上每棵玉兰树的使用权,大家都心知肚明。大伙按就近原则分配。通常,路左边的绝不晾晒到路右边,门对出的原则上不会有人来抢,对着公厕、路口的几户,都会找同侧的玉兰树,哪怕走得再远些。当家家户户把一年准备的年货挂上了树,谁家根枝散得开就一目了然了。
西河路是老城区与人民路相交的次干道。人民路上种的是法国梧桐树,高高大大,遮天蔽日。每次遇到台风、暴雨这种极端天气,人民路上的梧桐叶也会跑到西河路,西河路上的玉兰叶也会跑到人民路。两种树叶难得相遇,被风裹挟着纠缠在一起,似乎在传递两条路上不同的消息:车流量、人流量、路两旁的商户、路上的斑马线、路灯的种类与规格,甚至巡逻的交警……
几棵银杏树
抬头,看到了薄雾中的银杏树。
西风进村时,首先爬到树杈上,像猴子喜欢蹭在树上摇一样。西风进入我家时,首先爬上院墙外的银杏树,再从二楼窗户跳入我的房间。翻翻昨天写的诗稿,摸摸我买来准备御寒用的衣服,熟络得很。它们把银杏树枝作为进门的跳板,偶尔也会用力过猛,第二天一出门,地上全是银杏叶。
我们家在金家埭的最边上,再往前走就出了村庄。也就是说,西风一旦从我家出去就走完了整个村庄。当然,我家边上的银杏树也是一样,树叶被稍稍带出一点就出了村庄。
金家埭是柴岭山下几个村庄中的一个,一般来说南方的村庄不大,村东头和村西头通过一条狭长的路连在一起。风不知道这个村庄有多大,它们从我家出去,突然发现四周是无垠荒野。它们常常想留一留,于是便死死抱住银杏树狠狠地再摇上几摇。
整个下半年银杏树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每一阵风过后,银杏树都会朝着自己计划的方向努力生长。每一个外地人来到金家埭,如果从路这一头进村,远远地望过来,一定是先望见几棵银杏树再望见整个村庄。刚开始的時候,银杏树颜色是生生涩涩的,那时候的风柔和得多,爬在树上也是慢条斯理的样子,随着季节的不断深入,风才逐渐变得狂躁起来,转眼之间就把树摇得一片金黄。
那时候金家埭是一年中最安静的。人是一个一个走掉的,天麻麻亮人就出村劳动了。那是一年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晚稻收割以后播撒下麦子,错过了就错过了一年。村庄是静止的,除了银杏树偶尔会动一动,头上的几片云偶尔会动一动。
在金家埭活久了,就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一条拴在银杏树上的狗,从呆萌可爱的来到这里,到长成保家护院的生猛模样,我没看见家里人给它喂过几顿狗食,直到有一天发现它躲在树荫底下站不起来了,我知道它活得差不多了。想想,一条狗来到金家埭到离开金家埭一辈子像梦一样飘忽而过。
树上那窝鸟,反正我是说不上名字,第一次发现它们,我还兴奋得要命。有时我花一晌午工夫看它们飞进飞出,等我刚刚有些看腻了,它们就被蒋四五的弹皮枪给收拾了。为此,我还约蒋四五到交货塘空地决斗,怂包蛋没敢来。
有时想想,在金家埭做一棵树也是不错的。我年轻时的那些年,也像银杏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金家埭的泥土里。我是个没有太多抱负的人,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人,吃哪里饭,干哪里活。天一亮,金家埭人吃饭我就吃饭,金家埭人出门我就出门。太阳下山,金家埭人回来我也回来,金家埭人睡觉我也睡觉……
银杏树也一样,它和其他树保持距离,不喜欢泥土把它带到它不喜欢的地方。每次到了秋天,槐树、杨树、泡桐树还在努力守着自己的脸面,不愿意交出那点少得可怜的绿,金家埭的银杏树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西风过后,继续保持笔直的姿态。至于叶黄叶落,这只是为了告诉路人,金家埭昨夜留住了风霜与时间。
记忆看见我
我在金家埭一住就是几十年,却还是觉得这几十年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太短了些。
那年我出世,一家人喜极而泣。终于添上男丁了,这已是这户人家等来的第四个孩子,前面三个都是女娃。男娃可以站着撒尿,可以到社坛庙抡大锤搡年糕,可以赤膊下金家河摸鱼虾摸螺蛳,有太多女娃不能比的好处。
为了庆祝我降生,父母卖掉了年猪,掏出压箱底的全部积蓄,为我风风光光地办了十几桌剃头酒。父亲不停给祖上磕头,感谢香火的来之不易。奶奶忙上忙下招待客人,分糖,分花生,分蜜枣……母亲是那天的另一位主角,七姑八婆围着她,把好听的话说尽了。
我的幼年没有跨出过金家埭。一开始被做裁缝的奶奶带在身边,她在家收一些村里人送来的布料做衣服,一把剪刀,一竿尺子,一台老式缝纫机,一个熨斗,这是她全部的设备。全不像种地,要祈祷风调雨顺,撒化肥打农药,如果遇上不好的年景会旱死涝死,颗粒无收。通常我会在院子里自己玩,看家里的猫捉老鼠,看家里的狗警惕地看进出家门的陌生人。我也会凑上去和它们玩耍,过家家时当玩具将它们摆放在一个地方。通常它们也一动不动,眼珠子跟着我转来转去。有几次我不小心弄疼了它们,它们就会叫喊,奶奶便从堂屋冲出来,不分青红皂白狠狠训斥它们一顿。
在金家埭哪家有事都少不了来请奶奶帮忙,有人会来把缝纫机抬过去,奶奶除了把工具带上,还要带上我。奶奶干活我就在这户人家东转转西瞅瞅,碰上没见过的东西就凑上去闻闻摸摸,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对金家埭做近距离的观察与调研。奶奶在村里的人缘很好,经常能收到一些饼干、糖果等礼物。奶奶总是先悄悄让我挑,我的三个姐姐收到的往往是挑剩下的。
后来渐渐长大也依旧没有踏出过金家埭。幼儿园在社坛庙的角落里,六岁那年我被送了过去,教我们的是位姓邓的老师。她是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妇女。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每个孩子会分到一块糕点和两颗牛奶糖,偶尔也會轮换一下,上午发糖,下午再发糕点。
很多年以后,我再次见到她,她已经退休,在家带小孙子。我想凑上去问问邓老师,你还在用老办法管孩子吗?她存放在记忆中的糖果与糕点是不是已长出了绿毛?
那时候,白天成年人都需要去地里劳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在村庄。那时候的村庄是那么大,晚上那么多人住在里面一点不觉得拥挤,一到早上,人一个一个走掉,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人,那么多门、窗虚掩着,总让人感到深不可测。
我悄悄地走在村里的土路上,用那双幼小的脚丈量过,从村庄东走到村庄西要走多少步。直到我背上书包,真正开始读书,我每天还是在反复丈量金家埭到底有多大,我至少需要走完多少步,才可以跨进位于村庄另一头的校门。
我和同学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的家就在这个村上,可以走读,所以一天至少有四次在土路上走的机会。有时候因为被某件事耽搁迟了便走得快些,有时候由于时间充裕,慢悠悠地踱过去。我觉得我对金家埭的认识,与这条路是分不开的。它就像村庄的主神经,背负着曾经与它一同生活过的众多生命的珍贵印迹。
我曾经私下想过,这么小的我能够看懂这个看似毫无头绪的村庄,是不是与我那么认真地观察一条路有关?路的两边一定是树和矮墙,它们相互掩映,但泾渭分明。金家埭路边种的基本上都是水杉——一种被认为活化石的笔直树种。它们本来是没有主人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全部金家埭人的。可是,总有一些人,空下来就去树下转转,把水牛拴到上面,把狗拴到上面,再用篱笆围起来。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再没有谁去想那棵树真正的主人是谁,时间再一长,树也长得差不多可以派上用场了,这棵树便会成为他家的梁上之木。我看到好多棵这样的树悄无声息地爬到梁上,也没见到谁提出有何不妥。
土路要经过一个水塘,大概几亩的水面,和金家河相通。水塘有河埠头,周边的人和牲口都喜欢池塘里的水。蒋四五家就在池塘边上,当年他端了我家鸟窝我就想灭了他。他们父子先去野地里刨来一小片土,贴在路边上,种上南瓜和葫芦,朝着池塘搭了一个巨大的瓜棚。第二年又去野地里刨来一些土,往池塘进一步拓展。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三五年下来,这块地就成他家的了,再拉来两车砖,围墙砌好就成了他家的猪圈。后来我总结,在金家埭要干成一件事,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等到大家习以为常了也就成了。
在金家埭住久了,我会知道凡从路上拉来运去的东西,没一样不遗落一些在路上。它们可能是没倒干净的土渣,扬起灰尘成了金家埭的霾,可能是吃剩下的粮食,明年长成了金家埭新的谷子和苞米,可能是打底肥的粪球、尿,从路上弥漫开去,翻上围墙与围墙里的气味发生关系,成金家埭的独特气味。
西山马场
为一匹骏马安个家。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来自西山豁口的风喜欢在下午和人捉迷藏,它们跑进草丛里一股一股地吹。蜻蜓一动不动停在栅栏或拴马用的皮质缰绳上。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蜻蜓,光线打在它们透明的薄翼和花色各异的细长尾巴上,倒颇有几分意趣。马偶尔走动几步,又回到原地,它们和蜻蜓一样,打算在天黑前走过围栏,走到马厩。
对于马和它的伙伴来说,我是闯入者。但是马并不在乎,它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它比人更诗意地栖居于美妙的自然,享受着这份安逸。我掏出相机,它也坦然,它似乎明白,它就是我的风景。
每隔一段时间,草丛中就会窜出几只鹌鹑。它们发现马的蹄印旁,一坨刚落地的马粪好像刚出炉的新鲜披萨,充满着诱惑。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它们迅速地靠近,啄了啄又迅速地离开。我知道鹌鹑是聪明的动物,贪嘴容易暴露自己,所以它们冒险一阵后就会自动安静下来,如同一切从未发生过。
一只屎壳郎探头探脑,从马蹄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它们生活在另一个马场,它们是来打探什么的?小的时候,我最喜欢抓屎壳郎玩。给它们也套上缰绳,安上车轱辘(拖一个火柴盒),在大树下跑拉力。我们握住它们从黑暗中伸过来的手,接住它们从地底下喘上来的气息,从单调的童年生活中找到一点乐趣。
“一匹马跑起来了”,像鹞鹰脱离榆树,一愣神的工夫,就把马场放大了几倍甚至几十倍。没有见过马奔跑的人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看过马在眼前奔跑的人根本感受不到马的这种扩张能力。从西山开始,从地面到云层,整个大地浮现出一骑绝尘的辽阔无垠。蒿草再不是一根简单的草,风也再不是简单的风,它们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速度。
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我跟马没有长久的接触经历,要去的地方好似没有远到要骑马才可以到达。马从来不属于谁。我牵来一匹白色的马,翻身骑了上去,马也不认生,撒开腿便跑到了马的队伍里。或许马早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又一个马鞍,高高地安置在背上,替它看路、拉缰绳。在西山马场,万物都是通马性的。这里的人不是主角,马场主人的宝马车也不是,而且我认为这里的马最大的马性是即便它等了一下午,也无所谓。
在西山马场,我丢失了所有时间,而我的时间被马捡走了。
责任编辑:谢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