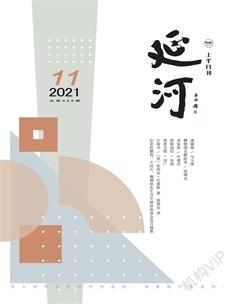透明女人
邹世奇
小叢又看到了那女人。
她有着清秀的脸庞,这么多年了,她却一点没有变老,看上去还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一个髻,两绺鬓发从脸颊两侧垂下来。她是那么清瘦,白色衬衫、白色长裙穿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宽大。最重要的是,她几乎是透明的,仿佛是周遭空气的一部分。她看着小丛,神色悲悯而哀伤。她不说话,可是她的姿态、眼神却分明在说:“孩子,跟我来吧,我领你到没有痛苦的地方去。”
她叫小丛“孩子”,可是小丛已经快三十岁了。
小丛已经在江边站了很久了。她来的时候,夕阳还在远处的群山后斜斜地照着,江面上客船、货船来来往往,从这个距离看过去,在江天一色的巨大背景下,它们全都移动得很慢。在离小丛八九步远的江里,有块大石头露出水面,一只水鸟停在上面。水鸟歪着头看了小丛一会儿,飞走了。江边很多散步的人,扶老携幼,更多的是情侣,牵着手,搂着腰,好像永远不会分开一样。
男友嘉伟刚刚离小丛而去,带走了他俩所有的积蓄。
关键不是嘉伟离开,而是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一个交代也没有,甚至一场吵架也没有。关键不是他不打招呼地离开,而是他还带走了小丛所有的钱。嘉伟是个编剧,没有署名权的那种。小丛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能接到点散活的,后来就逐渐接不到了。有活干、有钱拿的时候,他拼命买游戏装备,等到没活干的时候,他就在他和小丛的出租屋里没日没夜地打游戏。五年多时间,房租、水电、生活费都是小丛在付。那时两人感情还算好,嘉伟有时过意不去,小丛就说:“你只管好好写。我只等你编出一部《琅琊榜》来,一朝成名天下知,我好夫贵妻荣呢。”渐渐的,小丛知道,他是不可能成名了,而且他对自己也就那样,甚至算不上体贴。但,小丛想,就像和小猫小狗相处久了,处出感情来了,虽然它偶尔对你龇牙,甚至挠上一爪子,也不能把它扔出去,让它变成流浪猫狗。哪怕就是一块石头,在手心里攥久了,也总还是有点温度吧。可是,一个相处了两千个日日夜夜的活人,他居然就这么自顾自消失了,还带走了小丛辛苦攒的二十万!
工作六年,小丛就只攒了这二十万,这个钱没了,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刚工作的时候。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像嘉伟这样的男人都不要自己了。本来,在工作上失意的时候,好歹觉得还有可以相互取暖的人,原来,那个人早就在盘算着抛弃自己了。这时候小丛再回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上班六年,从入职那天起就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工作内容,不喜欢公司氛围,多少次想换工作,嘉伟都劝自己再忍忍,再等等。因为嘉伟收入极其不稳定,为了两人的生计,小丛也只好劝自己再忍忍。可忍的结果是:太多的心力花在抵抗这份不适应、不舒服上,自我消耗就非常厉害。自己觉得非常累,很辛苦,可工作并没有做好。一起入职,学历、业务能力都不如自己的人,现在发展得最慢的也都是部门副职了,只有自己还在最基层的岗位上。现在跳槽的话,人家还是要看她在前公司的职位,然后只能再给她基层的岗位。
嘉伟悄无声息地离开本身是一种伤害,这伤害带来更大的次生伤害。因为他的离开,小丛突然发现,自己快三十岁的人了,没房没车没积蓄没前途没对象。往后看,过去六年唯一增长的似乎只有年龄。往前看,未来也依然看不到好转的希望。升职、攒够房子首付遥遥无期,而行业的三十五岁大限已然在眼前。与不喜欢的工作缠斗六年,这已经耗去了她的大半心力,和嘉伟的相处又耗去了她其余的心力。无论工作还是感情,这一刻,她觉得自己都已无力开启新篇章了。不知不觉间,她的人生竟已残破至此。
夜晚的江面升起一层白色的寒烟。白天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此刻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灯。灯火在江面缓缓移动,那么遥远。看久了,就有点恍惚。这时,她出现了。
就在白天有水鸟停靠的那块石头上,她坐在上面,看着小丛,悲悯地,哀伤地。她宽大的裙幅飘在水面,随水打着旋儿。
小丛想,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了。上一次还是几年前,在城郊的水库。
那是个周末,小丛和嘉伟、嘉伟的两个哥们、哥们的女朋友们一起去水库游泳。这是小丛第一次游野泳。她那在游泳池学的泳技,本来绝对没有这个底气和胆量来挑战野泳,但经不住被一再怂恿,嘉伟保证会一直在旁边保护她,她才去了。
等看见水库那辽阔的一泓清碧,与游泳池的人头攒动正相反,这一刻居然只属于他们六个人,小丛就有些兴奋,当然,胆寒也是真的。三个女孩在他们开来的车里脱去了外面的衣服,只留下穿在里面的泳衣,嘻嘻哈哈地鱼贯下了水,其中一个女孩还套着游泳圈。水有点凉,但是真的清,入口有微微的清甜。不像在游泳池,小丛总觉得水里有各种人类体液,不小心入口,恨不能呕出来。三个男生都是游泳健将,一下水就像鱼一样自在。小丛和女孩小雅只敢在边上水浅处游,小雅比小丛游得好,渐渐地也跟着男孩子们往水库中间游,浅水处就只剩下了小丛和套着游泳圈扑腾的圆圆。
水库的能见度居然不输泳池。小丛透过泳镜看见一个原生态的水下世界:水草在水里柔软地竖着,飘飘荡荡,像穿着绿罗衣的古代舞女,身姿修长、衣袂飘举,姿态妩媚极了。小鱼小虾们成群游过,有的在水草间流连嬉戏。再往下是黄色的砂石,作为这水晶宫的城垣。
远离了工作的烦琐、同事的可憎面目,小丛心情大好,顺着一段岸边游来游去,时不时潜水到原地折腾的圆圆身边,摸一摸她,弄得圆圆尖叫不已,然后小丛浮出水面,两人一齐大笑。
突然,小丛感觉右脚被一只冰凉柔软的小手拽住了,拽得极有韧性,使劲蹬腿竟也无法前进,她心知必是水草,连忙伸手去解。动作失去平衡,身子就往下沉,然后心一慌,一大口水呛进肺里。难受慌张中,什么动作要领都忘了,完全凭本能瞎扑腾起来,于是更加下沉,更多水草缠上来。小丛眼睁睁看着那些绿衣的古代舞女,这一刻全都姿态摇曳地扑上来,向自己舒展着绿色的衣袖,索命一般。她呼气,晶莹的气泡像无数珍珠,扶摇直上,穿过摇曳的绿色丛林,在水面消失不见。
小丛胸口憋闷得要炸掉,她想喊,一张口,整个水库的水朝她灌,把她的呼救生生堵回去。胸口即将爆炸的感觉迫使她本能吸气,从鼻腔吸入肺的却只有水,窒息加上呛水,痛苦加倍。她凝聚起全身的力量抵御这痛苦,四肢停止了无谓的挥舞、挣扎。她看见圆圆的游泳圈就在不远处的水面漂浮着,像一朵七彩的莲花。圆圆雪白丰满的腰、臀、腿悠闲地浸在水里,时不时晃呀晃、划呀划的,像莲花下面洁净的莲藕。
她多想碰碰那莲藕,让圆圆知道自己溺水了,让圆圆帮她呼救,可是她已经没有了力气挣脱绑缚在自己身上的水草,更别说游到她身边了,三四米的距离,此刻远得像天涯海角,她怕是永远抵达不了了。隔着厚厚但透明的水墙,她甚至能看见头顶湛蓝的天,天上飘着大团大团的白云,棉花糖一般。一只孤雁飞过,雁儿伸长脖子,应该是发出了一声嘶鸣,然而小丛却听不见。原来水下的世界如此寂静。
这时,她出现了。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在水中飘舞,头发松松地绾在脑后,两绺鬓发在两颊飘动。她的身形几乎是透明的,似乎是以水凝聚成形、又天然地与水融为一体。她的神色悲悯而温柔,她朝她伸出一只手,清瘦的、苍白的手,她的嘴唇似乎动了动,在这无声的水下世界,小丛却清楚地感觉到她在说:“来吧,孩子,我带你到没有痛苦的地方去。”缠住小丛的水草忽然松开,柔软的森林忽然朝两边倒下,绿衣美人们集体倾颓,小丛的身体自由了。并且,她惊喜地发现,胸腔憋闷得即将爆炸的可怕痛苦已然消失,全身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跟在那个女人身后,轻盈地、欣悦地朝水的深处走去。
胸口在被人用力按压,一下,又一下,压得十分沉实,按得肋骨几乎要断掉。小丛呻吟一声,慢慢睁开了眼睛,阳光刺眼,周围一片欢呼:“醒了!醒了!”嘉伟身子一歪,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还是圆圆发现了小丛溺水。她戴着游泳圈原地转圈,水太清,她先是看见小丛身上连体泳衣的橘色,在很深的水里,在一大蓬绿色水草中间,宛如水草开出的艳丽花朵。然后看清小丛仰面躺在水底,四肢摊开,一动不动,像洋娃娃。直觉带来的恐惧,让她确定小丛不是在潜水,于是歇斯底里地喊起来。嘉伟和他的朋友们迅速从远处游回来,三个男生一齐潜下水,合力把小丛从水草丛中拽了出来。
这一刻,小丛站在江边,与十步之外的半透明女人怃然对视。女人哀凉的目光,如一件轻柔的羽衣披在小丛身上。小丛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郊外水库溺水的那一次,跟着她走向水的深处,居然一点窒息的痛苦也没有,全身上下十分松快。她还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她的奶奶,濒死的小女孩走进奶奶的怀抱,那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安全的所在。
女人向小丛伸出一只手,那水草般纤瘦的手,夜色中显得更加苍白。此刻那手如同塞壬的歌声,具有了无限诱惑的意味:跟随她去吧,你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不告而别的男友、没有糟心的工作、没有令人生畏的明天……这样想着,周遭的世界开始旋转,江里船上的灯,马路上的路灯、霓虹灯,成了一根根细细的闪亮的线、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彩虹、一团团色彩绚丽的光晕,在她的周围旋转飞舞。
眩晕中,小丛朝女人的方向跨出一步,江和岸的高低落差让她有种一步踏空的感觉,等她本能地站住时,她整个人都在江里了,水深及大腿,冰凉的一激灵,世界停止了旋转。
岸上有人飞快地朝小丛跑来。近了,是一个穿制服的人。他一探身,一双大手攥住了小丛的胳膊:“女士!水深危险,请不要给我们的工作造成麻烦。”是江边夜巡的辅警。小丛大脑空白,像只木偶一样被他抓在手里提上了岸。
水顺着小丛的腿和脚往下流,很快在她站立的地方积成一滩。她这时才听到上下牙打战的声音,感到自己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不远处有辆警车停着,警灯闪烁,一个警察和两个辅警正朝自己的方向快速走来。稍远处,城市建筑华丽高耸,射灯朝无垠夜空打出变幻的光柱。建筑一侧整面的电子屏幕上,无数玉兰花瓣正缓缓飘落,从大楼顶部飘落至底部,无穷无尽的花瓣,无休无止地飘落。城市的夜晚,美得如同幻境。而小丛还有很多好东西没享受过,她才二十九岁。随着最后这个念头跳入脑际,小丛被自己刚才的行为惊出一身冷汗。她回首看向江里,辅警以为她要再次往下跳,紧张地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其实小丛只是想再看一眼那个女人,她在心里喊了一声:“妈妈。”然而那个女人——她的妈妈,已经不见了。
在小丛十岁到十二岁这三年,她多次看见妈妈。那是和后妈、爸爸一起生活的三年。在那之前,她由奶奶带,像个普通孩子一样在爱里长大。在那之后,她就住校了。唯有那三年,是她这半生中最黑暗的三年。后来,每当她看到后妈虐待、杀害继女的报道,都会在心里默默庆幸:幸亏自己的后妈不是一个变态,而只是一个普通“坏人”,一个有体制内工作的“体面人”,才没有让那些诸如刀割、烟头烫、喂粪便、针线缝嘴、塑料袋蒙头等酷刑使用在自己身上,才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成报纸上的一则法制新闻。大多数时候,小丛身上的伤都是皮外伤,巴掌扇的、皮鞋踹的、皮带抽的、头被按在墙上撞的,是可以不经医治而自愈的那种。除了暴力,更多的是冷暴力,很多时候,小丛觉得家里冷得呀,阳台上应该挂满手臂粗的冰棱柱才是。
小丛妈妈自杀的时候,小丛还不满半岁。据说是因为小丛爸爸有了外遇,她接受不了。
在与丈夫的漫长冷战之后,在一个春雨蒙蒙的早晨,小丛妈妈,这个刚结婚两年不到的二十六岁的女人抱着小丛出了门。她一直走,走到了江边。她没有打伞,牛毛般的细雨打湿了她的衣服、孩子的襁褓,在她和婴儿的头发、眉毛上聚起一层细细的雨珠。她抱著孩子站在水边,远远近近有一些新鲜的黄绿,那是早春的树色、草色,然而她已经接收不到这颜色中的生命信息了。在她的世界里,天和地是一种浑然一体的青灰色。连续下过几场雨,江水涨得厉害,满满一江浑黄的水,飞快地向东流去,稍近距离看两眼就令人目眩。
年轻女人最后一次回望了来时的方向,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她闭上眼睛,抱紧了怀里的婴儿,往前迈了一步。就在这时,婴儿发出了“嘤嘤”的哭声,不知是不是被江水吓到了。年轻女人站住,想了想,往河堤顶部走去,把婴儿连同襁褓放在了如茵的黄绿色浅草上。然后,她独自走下河堤,走近水边,一跃而下。
当然,这一幕是小丛根据奶奶的讲述想象的。每次经过江边,无论坐车、骑车还是步行,小丛都要出神一番。发展到后来,她看到河、湖、塘都要想入非非,几乎成了一种病。
在小丛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次次抚着胸口说:“真后怕啊。她把你放在江堤上,你要是打两个滚,就滚下江堤,掉到江里去了呀。”长大后的小丛觉得奶奶的想法有些奇怪,她是想不到还是不愿去想:也许妈妈的本意就是要带小丛一起走,只是后来一念之差,才把她留下来的。更值得后怕的,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吗?
小丛很少怨后妈,因为觉得怨不着,她只是个不相干的外人。要怨只能怨亲妈。特别委屈、特别孤单的时候,小丛就会不由得想:亲妈给了自己生命,却把自己扔在世界上受苦。她若有知,应该回来把自己接走才是。
这么想着想着,小丛就真的看见妈妈了。小丛已经记不得那天是为了什么事又被爸爸打了,只记得又是后妈当面挑唆,爸爸打给后妈看的。那是一个明月夜,小丛躺在床上,下意识摸着被爸爸用皮鞋踹过的小腿,被爸爸按在墙上撞过的额头。恍惚中,小丛觉得窗外的月光变得远超平常的明亮,不知什么时候起,房间的外墙消失了,一条银子铺成般亮堂的路,从自己床前一直延伸向远方。一个女人站在那条路上,离自己只有十步远的距离。她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一个髻,两绺鬓发从脸颊两侧垂下来。她是那么清瘦,白色衬衫、白色长裙穿在她身上都显得过于宽大,飘飘荡荡。她整个人几乎是透明的,身上散发着微小的、银子般的光芒。她看着小丛,神色悲悯而忧伤。她没有说话,可是她的眼神、表情却在说:“孩子,跟我来吧,我领你到没有痛苦的地方去。”小丛坐起来,大喊一声:“妈妈!”
小丛飞快地穿好出门的衣服,没有一秒的犹豫,立刻跳下床穿上鞋子,撒腿就跑。她要顺着那条银子铺成的路,跟随妈妈而去。突然重重地撞到什么东西上,此前被爸爸按着在墙上撞过的额头这下钻心的疼。小丛醒了,是撞在房间的门上,原来墙并没有真的消失,没有什么银子铺成的路,没有透明的、散发着银子光芒的妈妈,什么都没有。小丛顺着门滑坐在地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从那以后,小丛便时不时看见妈妈,一年总有两三次吧,被冤枉得特别厉害、被打得特别狠的时候。妈妈总是神色凄婉,总是从不说话,但眼神和表情都在说:“孩子,跟我来吧,我领你到没有痛苦的地方去。”到了后来,小丛只是远远地看着她,因为她知道,眼前的美景不过是海市蜃楼,一旦自己朝妈妈奔过去,一切便会消失不见。小丛情愿就这样,安静地和妈妈待一会儿。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果然,只消过一会儿,也许就五分钟?三分钟?妈妈就会和她周围的幻境一起,变得越来越透明,直至消失不见。
小丛的眼泪,要到这时候才掉下来。
奶奶来看小丛了。晚上就寝时间,小房间里只剩下祖孙两人的时候,奶奶便哭起来:“我算看出来了,你在这家里做什么人家都看不上。好吃的好穿的没有你的,还让你伺候小的,连洗脚水都要小的洗剩下才能洗。”小丛不说话,心想这还是有你在这里,他们已经非常克制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冬天天冷,她飞快地脱下毛衣,只穿小背心钻进被窝里,但还是被奶奶看见了大臂上的瘀紫。奶奶盯着问是怎么回事,小丛说:“走路不小心撞墙上了。”她只想蒙混过去,赶紧睡觉。奶奶却不依不饶地拉着小丛的胳膊:“不可能。撞的话只会撞胳膊前边、外边,你这是胳膊里边,胳肢窝下面,怎么可能撞到。”小丛见糊弄不过去,只好说实话:“我洗碗倒多了洗洁净,我妈掐的,教育我不能浪费。我以后把家务做好了,她就不打我了。”奶奶的眼泪“唰”一下落下来:“没用的,丛儿啊。人家这是嫌弃你,挑剔你,折磨你,你做得再好、再多人家都不会满意的。”
暗夜里,耳边始终有老人的啜泣,窸窸窣窣,哭得空气都跟着潮湿起来。小丛就迷迷糊糊地说:“奶奶,别哭了。他们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妈妈就会来看我。”啜泣声戛然停止:“你说啥?谁来看你?”“我妈妈。她穿一身白色的衣服,就远远地站在门外面。有好几回差点带我走。”黑夜里再也没有了声音。
过了半年,奶奶再来的时候,趁后妈带着妹妹出去买东西,奶奶神神秘秘地叫过小丛爸爸,当着小丛的面,压低着声音说:“我跟你说啊,上次我来的时候,小丛夜里跟我说起,她亲娘时常来纠缠她,吓得我呀。我回去就花钱请了神汉,神汉来做了场法事,在坟上钉了桃木樁、柳木桩,用上了朱砂,还拿符镇上了。我那媳妇是好媳妇,可是为了我孙女,我只好对不起她了。现在她应该不能再来纠缠丛儿了……”爸爸听了,不置可否地干笑了几声,就走开了。从小丛记事起,妈妈在爸爸这里就是禁忌话题,因为想象不出会有什么后果,小丛从来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妈妈。偶有一两回被奶奶提起,爸爸都是这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从不接话,好像奶奶说的是另一个次元的人和事。
寒意从心底升起,小丛全身发凉。她也沉默,让奶奶的话在屋子里自个儿风干。
好在过了不久,在爸爸当着后妈的面,拿竹竿狠抽了小丛一顿之后,她面朝下趴在床上,又一次看到了妈妈。深秋的夜晚,十点多钟的样子,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不知哪里的灯光映过来,半明半暗的。这次打得很厉害,即使趴着也无法睡着。小丛无意中看向窗口,发现墙又消失了,外面出现了一条蜿蜒的河,雨滴是无数条发光的线段,纷纷落进河水里消失不见。而妈妈站在河心,穿着她那宽大的白色衣服和裙子,衣裙在风雨中飘摇,她整个人是半透明的。小丛觉得特别欣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母女俩凄然地对视着。
小丛在心里对妈妈说:“我好害怕,怕你被朱砂封印在里面,再也出不来。”
透明的妈妈没有说话,但是小丛清晰地感觉到她“说”了:“怎么会呢。我并不在那里,我在你的心里。”
小丛问出了她一直想问的一句话:“看见我被后妈、亲爹虐待,你有没有后悔过当初丢下我?”
妈妈原本哀伤的眼睛突然涌出了泪水,像两只泉眼一样汩汩地往外涌,两条泪河沿着面颊滚滚而下。这一次,小丛没能感觉到她“说”了什么。在泪水冲刷中,她变得越来越透明,很快和那条河一起,消失了。
张爱玲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小丛觉得,自己的生活生来就是一件千疮百孔的旧袍子,从没华美过,上面虱子、跳蚤格外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和嘉伟在一起的那些年,她无法想象自己能在早上八点之前起床;而现在,她每天五点半起床,做早饭,吃早饭,给明祥和保姆留好早饭。然后她匆匆捯饬下自己,七点整踩着高跟鞋出门,转公交和轮渡去上班。如果运气好,有座位,路上能眯一分钟都是种幸福。终于换了工作,但仍然不是自己喜欢的,她已经把这辈子做不到喜欢的工作当作宿命接受下来。说到底是自己大学时专业就选错了,专业不喜欢,只要是拿毕业证找的、对口的工作,就一直不会喜欢。
对明祥也是。小丛从来没有觉得很喜欢他,就像当初也没有很喜欢嘉伟。小丛上大学的时候,倒有一个很喜欢的学长,然而她觉得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上自己呢?自己这么一般,容貌、学业都这么不起眼,于是就放弃了那一点“非分之想”。婚后有次去学长的城市出差,学长看到她发的朋友圈,主动打电话来请小丛吃饭。在约定的地点,学长和他太太一起出现了。小丛发现,与自己相比,学长太太长得更一般,但她举手投足都那么从容、舒展,一看就是被爱富养大的女孩,自信让那平凡的面孔焕发着光彩。回到酒店后,小丛才明白自己受到了多大的震撼。她觉得,如果自己不是那么自卑,总觉得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自己的份,当初也不至于不敢选自己喜欢的专业、不敢去吸引自己喜欢的男人。到如今工作、感情都不忍细看,归根到底,當时觉得自己配不上的人和事,到后来就真的配不上了。
工作日的每一天都是宫斗剧般的一天,小丛还从来不是那个赢的小主。然而下班回到家才发现,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保姆只负责带孩子,一天下来孩子换下来的脏衣服、弄乱的家都需要小丛来处理。当然小丛要先做晚饭、洗碗。保姆带了一天孩子,小丛还要小心照顾她的情绪。保姆的工资是明祥父母付的,他们还承担了房子首付。不然就凭小丛和明祥,不要说请保姆,一家三口能不能在这城市活下来都是个问题。至于明祥,自从有了孩子,他每天能回来多晚就回来多晚,回来了也不过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在客厅角落里打游戏到深夜,从头到尾不会朝忙着拖地、整理、洗衣,在房子里移动个不停的小丛看一眼。小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找的男人都喜欢打游戏到深夜?
小丛唯一的支撑是孩子。哦,孩子。从小丛经历惨烈的分娩过程后看到她的那一刻起,从小丛第一次把那个柔软的小肉团子抱在怀里的那一刻起,从她第一次用她无牙的小嘴含住小丛乳头那一刻起,从她第一次发出无力的哭声朝小丛伸出要抱抱的小胖胳膊那一刻起,小丛就知道,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都丧失了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力。不仅如此,很多过去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无力承担的,在孩子出生后她发现都能面对,能承担了。孩子那么柔弱,除了自己,还有谁能全心全力保护她?明祥吗?自己若不在了,她会活下来,然后被变成另一个小丛吗?不不不,那样小丛即使肉体腐烂了,灵魂也会长久地颤抖在炼狱的火焰里。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越长,她的这种想法越坚定,哪怕满身血污与呕吐物,在粪便里爬着也要活下去,因为她是一个母亲,她有一个母亲的责任。
小丛有时还是会想起自己的妈妈。那个永远二十六岁的女人。她头发在脑后松松地绾一个髻,两绺鬓发从脸颊两侧垂下来。她是那么清瘦。她看着小丛,神色有些凄迷——这是奶奶帮小丛保留的唯一一张妈妈的照片,摄于妈妈新婚不久。这张照片在和后妈、爸爸生活的那三年里,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小丛希望有机会对妈妈说:“我原谅你了。”每个人的敏感点不一样,也许那时候,爱人在你心目中的分量远远重过我。也许那一刻,你实在痛得顾不了任何,包括我了。也许,当你在水中还有意识的最后几秒,你曾牵挂过我。从此以后小丛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透明的女人。
责任编辑: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