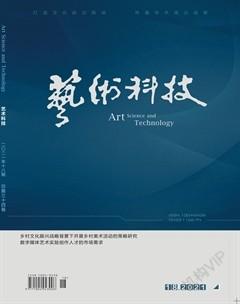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摘要: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正在全球崛起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引发我国学者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文章梳理现有文献,通过对时间、期刊、作者、关键词分布的分析,指出我国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研究方兴未艾,建设性新闻的起源、发展、价值逐步得到呈现。研究主题类型主要分为学术史梳理、理论研究、对比研究及应用研究四大类型。文章认为今后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应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探明建设性新闻的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积极心理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8-00-03
0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大众被赋予传播信息的权利,既有传播格局发生改变,原先的大众传播时代逐步转变为公众传播时代。这导致两个问题出现:一是传播技术门槛降低,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垄断,扩大了公众的话语权;二是公众参与的传播使得信息过剩,虚假新闻与谣言盛行,事件真相被迫置于次要位置[1]。西方传统媒体多以冲突视角展开负面报道,使受众产生“同情疲劳”,有学者认为报道中连续不断的坏消息,同时缺少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导致“同情疲劳”的关键因素[2]。在此背景下,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重视解决方案、未来导向、赋权于民的建设性新闻为新闻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设性新闻以其独特的价值在欧美受到学者关注。“建设性新闻”作为新闻术语最先由丹麦的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在2008年提出,他认为建设性新闻在补充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的同时,能够平衡负面新闻带來的消极影响。“建设性新闻”作为学术概念由美国学者凯伦·麦金泰尔2015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他认为其是一种在保留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应用积极心理学技巧进行报道,从而更具创造力和吸引力的新闻形式。英文学术期刊《新闻实践》《新闻》分别在2018年及2019年对建设性新闻进行专题讨论。目前欧美学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以凯伦·麦金泰尔为核心,以吉尔登斯特德·凯瑟琳、赫尔曼斯·莱斯贝思、索贝尔·梅根等人为重要补充,其致力于将建设性新闻进一步概念化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实验探明建设性新闻的作用及影响。
我国对建设性新闻的关注略晚于欧美国家。2017年,中国学者晏青采访凯伦·麦金泰尔后,建设性新闻在中国得到正式介绍。201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以“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为主题展开学术探讨,与同年12月《新闻与传播研究》建设性新闻增刊一起,将学界对此新闻报道形式的关注推向高潮。学者在探讨其内涵及外延的同时,分析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实践,试图总结建设性新闻传播的“中国范式”。
为了进一步明晰国内建设性新闻研究进展,文章梳理现有期刊论文,了解目前研究动态及热点,总结研究主题类型,最后提出评价与展望,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些许建议。
1 方兴未艾: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逐步展开
笔者以“建设性新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期刊论文119篇、学位论文3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89篇。笔者对这89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分析,以了解建设性新闻研究现状。
第一,从时间分布来看,建设性新闻研究集中于2019年和2020年。2019年有23篇,2020年有64篇,这两年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呈增长态势。其中,2019年12月论文发表的高峰与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的召开密不可分;2020年3月和2020年4月是两个高峰,分别有18篇、12篇,这与2019年末我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其中多数论文分析媒体报道方式,探讨建设性新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从发稿期刊分布来看,国内有几本期刊对建设性新闻发展的关注尤为密切,如《青年记者》《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编辑之友》等,形成遍地开花之势。据统计,刊载3篇及以上与建设性新闻相关的学术论文期刊共有8本,其中《青年记者》《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编辑之友》分别刊载18篇、17篇、16篇和10篇论文。有期刊以“建设性新闻”为专题刊登论文,这说明建设性新闻已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学者逐渐开始集中讨论在公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在传递基础信息之外,如何在社会治理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帮助解决问题,并且如何在这过程中调动起公众积极正面的情绪。《当代传播》刊载的多篇论文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理运用建设性新闻能够缓解公众恐慌情绪,化解社会危机。由此可见,建设性新闻已引起各个期刊的集中讨论,学界全面深入的研究亦有利于看清建设性新闻在我国的发展动向。
第三,从作者分布来看,国内已经有几位学者在建设性新闻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如殷乐、蔡雯、邵鹏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殷乐共发表6篇论文,从历史溯源到概念界定,总结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探索,考察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路径,认为中国建设性新闻探索始于正面报道,与欧美国家新闻实践并行发展,并与之产生共鸣[3]。蔡雯从行动主体、目标、策略和方法等方面对建设性新闻与其他类型新闻进行比较,发现西方国家部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已发生转变,其中建设性新闻是重新构建新闻价值的积极因素。邵鹏不仅梳理了建设性新闻与另外五个类型新闻的发展历程,而且以澎湃新闻垃圾分类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内现行新闻报道理念与建设性新闻理念之间的异同,认为建设性新闻能够丰富我国新闻理论的建构。在众多学者中,芮必峰视角新颖,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设性新闻不仅契合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且突出强调新闻媒体“主动记者”的角色定位。在不同学者的探讨声中,建设性新闻的理论起源、发展趋势、内核价值逐步得到呈现。
第四,从关键词分布来看,“积极心理学”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公共新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疫情报道”“正面报道”“社会责任”等词语紧随其后。“积极心理学”出现频率达到8次,因为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的基础是积极心理学,它试图打破传统新闻报道对世界负面扭曲的描述[4],所以国内学者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关注较多。有学者认同麦金泰尔的观点,认为积极心理学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大众的正面情绪;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声音,认为建设性新闻对积极心理学的响应和“挪用”存在观念局限和理论风险。“公共新闻”因与建设性新闻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受到关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面报道”可以看出学者乐于探寻建设性新闻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推崇正面报道的新闻报道框架下的可行性。建设性新闻虽近些年才被引入,但从上述关键词可以看出学者正尝试从多角度了解建设性新闻,以期从不同方面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对建设性新闻概念进行介译、吸收后,我国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学者对其的关注度日渐提高,论文发表量逐步增加;多本刊物对建设性新闻保持持续关注,认为建设性新闻是解决媒体在公众传播时代所面临困境的最佳报道方式;殷乐、蔡雯、邵鹏等学者逐步形成对建设性新闻的见解,抽丝剥茧地梳理建设性新闻历史、发展及实践。
2 循序渐进:四大研究主题
从时间线来看,我国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呈现层层深入、循序渐进的态势:从挖掘学术脉络到理论研究,再到对比与其相似类型新闻的发展,最后解读建设性新闻在新闻生产实践领域发挥作用的应用研究。我国学者寻踪觅源,从不同角度探析建设性新闻的历史、内涵与价值。
2.1 学术史梳理:从历史视角总结其发展脉络
徐敬宏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建设性新闻六大特征。史安斌、王沛楠二人溯源建设性新闻的历史脉络,抽丝剥茧地梳理其理念演进以及在各国的实践,深度分析建设性新闻是如何重新塑造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殷乐、高慧敏考察欧美建设性新闻的发展,从媒体公共服务、媒体公众参与、个人认知平衡三个维度探求其本质,认为该理念在我国新闻业发展中一直有所体现,并为我国建设性新闻发展提出三个层面的意见。学术史的梳理从历史维度,展现出建设性新闻的发展路径。
2.2 理论研究:在理论层面为其找寻理论依据
陈薇一方面站在美德伦理学视角,洞察其“新闻之善”,探讨后现代社会中主导建设性新闻创新的核心要素与价值;另一方面,以积极心理学为出发点,探讨其情感动因、核心价值与实践策略等。吴飞、李佳敏从布洛赫希望哲学的角度分析建设性新闻的哲学基础和现实意义,认为该理念不仅只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解构,更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有益报道方式。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性新闻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凸显了其深度与广度。
2.3 对比研究:比较相近类型新闻异同,总结其价值
蔡雯梳理公共新闻、公民新闻的发展进程,认为公共新闻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由新闻界主导的改革,要求将报道与媒介活动结合。记者不仅要报道新闻事实,更要介入其中,带领读者进行思考与讨论,帮助公众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公民新闻出现的原因是21世纪初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公众受益于技术赋权,成为新闻活动的第一主体,脱离了专业媒体的框架和限制。她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设性新闻是公共新闻的延续和发展,是对西方传统新闻报道方式的反叛,但坚持了保护公共利益、推进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在不同类型新闻的对比研究中,建设性新闻能够引导积极情绪、帮助问题解决、面向未来、赋权于民的特点得到了全方位展示。
2.4 应用研究:结合我国新闻业发展,探讨其实践意义
陆玉方站在学界和业界结合的角度,分析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总结了在我国进行该类型新闻报道的三点经验。漆亚林在剖析我国多个媒体对建设性新闻元素的使用后,认为我国已有较成熟的案例,已经形成以中国协同主义范式为主要表征的中国报道。对建设性新闻实践进行分析后,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谋而合,党媒想要在融媒体时代继续创新发展,应用建设性新闻是必由之路。2019年末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学者集中观察新闻媒体在此期间对建设性新闻的使用,发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建设性新闻可以调和冲突,减少负面信息的消极影响从而激发大众积极情绪,消除“信息疫情”带来的恐慌,提升舆论引导力,维护社会稳定。立足我国新闻事业观察建设性新闻,可以更好地看清其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融入、发展与变化,明确其实践意义。
总体来说,我国研究是由表及里的,学术史研究厘清建设性新闻的历史脉络,理论研究为建设性新闻提供理论依据,对比研究阐明不同类型新闻侧重点,涉猎最多的应用研究探明我国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路径,为后续发展提出建议。
3 结语
近几年,我国学界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这些研究为建设性新闻在我国的概念梳理、理论发展做了铺垫,但是当前建设性新闻在我国仍处于理解、接受、吸纳的阶段。
第一,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目前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同质化问题比较明显,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以历史溯源、概念界定、特点辨析、价值判断居多,缺少对建设性新闻概念化的研究;二是对疫情报道关注较多,缺少对其他版块新闻的关注。针对这两个问题,一方面我国研究可以将建设性新闻进一步概念化,荷兰学者提出需要通过对新闻产品、新闻行业和受众的进一步调查研究,更好地将其概念化,我国学者亦可从这个角度入手。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传统媒体自视为“瞭望者”“看门狗”,一贯采用负面、冲突式的报道模式,我国新闻业坚持马克思新闻观,以正面报道为主,所以建设性元素在诸多新闻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学者可以广泛关注不同媒体对不同社会事件的报道,分析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及价值。此外,学者可以关注近些年中西方媒体对同一国际时事热点报道的情况,探析其中建设性新闻的使用,在比较分析中实现研究的多元化。
第二,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目前我国研究多局限于建设性新闻本身,或从建设性新闻视角分析媒体报道。凯伦·麦金泰尔曾在和晏青的学术访谈中提到,西方已有学者使用框架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自我调节理论、记者角色理论等解释建设性新闻如何“选择”与“凸显”,如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调节受众心理,如何重塑记者定位。我国学者可以此为鉴,结合不同理论,从多个视角探究建设性新闻对我国新闻业的意义和启示。此外,学者还可以加强跨学科交叉合作。建设性新闻与积极心理学密不可分,可以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探索它对人产生的影响,从而推进研究的深入。
第三,研究方法有待优化。目前,我国对建设性新聞的研究大多是经验总结和文献分析的结果,部分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在荷兰,赫尔曼斯·莱斯贝思和吉尔登斯特德·凯瑟琳为了了解人们如何评价在新闻中融入建设性元素,对3 263名20~65岁的成年人进行受众研究。在西方不仅对有对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研究,还有针对儿童的实验研究。玛丽斯卡·克莱曼斯、路易斯·F·施林德温、罗斯·多曼三人对336名9~13岁的青春期前儿童进行接触到建设性新闻或非建设性新闻的实验,发现建设性新闻报道可以作为朋辈讨论的桥梁,减少负面新闻对青春期前儿童的危害。这些研究为我国进行受众分析、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借鉴。但我国与西方的新闻业差异较大,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设计研究要立足于中国,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建设性新闻在我国实际运用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唐绪军.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新闻的建设性[J].当代传播,2020(2):1.
[2] 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信息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D].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大学,2015.
[3] 殷乐.并行与共振:建设性新闻的全球实践与中国探索[J].新闻与传播究,2019,26(S1):33-41.
[4] 凯伦·麦金泰尔,吉尔登斯特德·凯瑟琳.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J].新闻实践,2018,12(6):662-678.
作者简介:高淑慧(1996—),女,江苏苏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建设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