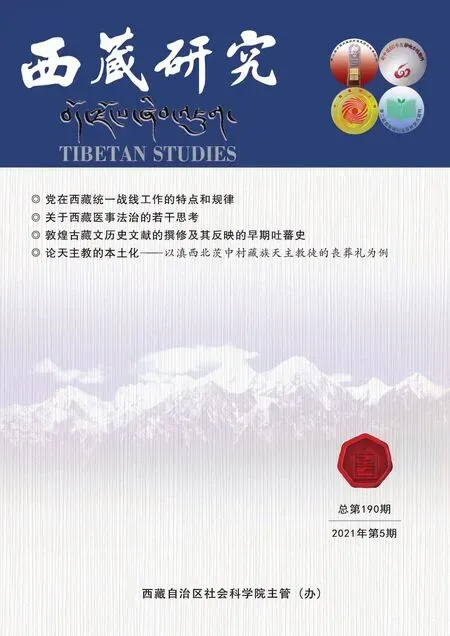论天主教的本土化
——以滇西北茨中村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礼为例
叶远飘
(广东医科大学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湛江 524000)
自16世纪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关于其本土化的议题就广受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成果大多聚焦于宗教经典的翻译、义理阐释、文献汇编和传教士活动等,而从普通信徒的宗教实践出发展开的讨论仍显缺乏。本文以人类学为视角,基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风俗,尝试对“天主教本土化”作一新的探究。
一、相关研究回顾
尽管天主教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但有关藏族天主教徒丧葬的研究却不常见,德吉卓玛的论文指出了西藏芒康县上盐井村的藏族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在丧葬仪式上的区别——天主教信徒只实行土葬,且必须在坟墓前立碑、刻字、印生卒年月[1]。刘琪等人基于茨中村一场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仪式讨论了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在(丧葬)期间的差异化宗教实践[2]。这些研究对于学术界理解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文化有所裨益,但并没有深入到丧葬“礼”的层面,“礼”之重要正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的体现,是维护人与人交往的秩序,也是维持社会运行的一种制度。17世纪天主教会人员针对中国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丧葬礼指南——《临丧出殡仪式》,其文本结构模仿南宋大儒朱熹所撰写的《家礼·丧礼》的结构,表明17世纪以后,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已经改变了纯粹的欧洲天主教的丧葬仪式,开始与儒家的丧葬礼呈现出一种“交织”的状态[3]。康志杰在对湖北磨盘山的天主教丧葬礼研究时曾与这份指南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份17世纪编写的指南一直沿用至今[4]。不过,肖清和的研究指出,历史上这种“交织”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以儒家仪式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纲常、长幼尊卑以及社会秩序做出改变为代价的[5]。由于藏族丧葬礼仪与汉族儒家丧葬礼仪有所不同,因此,对藏族天主教徒丧葬礼的研究,是了解天主教在藏族地区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当地的社会与文化,进而实现“中国化”“本土化”的应有之义。
二、茨中村概况
茨中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东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西靠德钦县霞若乡粗卡桶村,南部和北部分别与燕门乡巴东村和春多乐村相邻,整个村庄坐西向东,面向缓缓南流的澜沧江,村民多为纳西族和藏族,其中纳西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藏族主要信仰天主教。
7世纪之前,茨中村所在地属羌人游牧之地;唐贞观八年(634),吐蕃将势力推及至此,屯兵万余人,其后与南诏、唐王朝在此展开了大规模的拉锯战;宋元以来,此地又成为“茶马互市”的必经之路;明代,位于丽江的木府土司对吐蕃政权分裂后占据此地的地方势力发起军事战争,大批纳西族随之迁徙至此;清代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用兵和对边疆的开发,大批中原地区人士迁入此地[6]。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巴黎外方传教会将驻西藏欧洲传道团的教士分为三组,其中南下的一支传教士以茨菇、盐井为依托,进至德钦,联结一线;再推至白济讯(小维西)、吉岔、花园菁、保和镇(维西县城)及巴东等地,以澜沧江中段为活动重点[7]。在此计划之下,法国传教士余伯南于1866来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菇村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统辖德钦、维西和贡山三县的教务[8]。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茨姑教堂在当地人民的驱洋教事件中被焚毁,之后经清政府的斡旋,教堂于1909年在茨中村重建,自此以后,天主教成为当地藏族的主要宗教信仰。藏族接受天主教以后,传统的丧葬礼与天主教信仰融合后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以下笔者按照天主教丧葬礼中的丧礼、告别礼、送别礼和葬礼分别叙述。
三、茨中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礼
(一)丧礼
在茨中村,当天主教徒去逝以后,家属要为逝者设置灵堂。灵堂通常设在堂屋大厅中央,首先搭一张长1.5米左右,高约0.7米的长方形祭台,面向门外,台面铺以白色的苇布,两端点燃长形蜡烛,烛台下面枕着长条形的红布,中间安置带有苦像的十字架、圣杯、放圣体的小盒以及香炉,此设置完全是模仿教堂的圣坛而做。因为在欧洲,天主教徒死亡后,其丧事完全在教堂举办——家属把装着死者遗体的黑色灵柩抬到教堂,神父穿上挂着圣带的白色礼服与侍从和圣职人员在教堂门口迎接,为灵柩洒圣水、做吟诵。从这一刻起,死者的灵魂开始交到神父的手中,他作为天主和信徒的“中保”,开始带领教友们在教堂念诵亡者日课和丧礼弥撒,直到亡者去逝后的第三天出葬。但在茨中村,人们还是依照传统习惯,在自己家里设置灵堂。灵堂,特别是祭台的布置与教堂的圣坛布置一样——这是因为在天主教看来,教堂的圣坛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逝者的灵魂往往是从这里得到拯救的。教堂的神父向笔者表示,在这个意义上,丧事如果像欧洲那样到教堂举办应该是最理想的,但村民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也不方便干涉太多。茨中村村民们所做的是把教堂的神父请到家里去炼净死者的灵魂。搭祭台的同时,家属还需要把死亡的讯息告诉另外两个重要的人物,即天主教教会的会长和茨中村的村长,前者的任务是通知村中的教友前往死者家里帮忙,包括敛尸、装饰棺材、做亡者日课和弥撒等;后者的任务是把亡者去逝的信息通知给其他非天主教徒,目的是让大家当天晚上到死者家里“守夜”。
“守夜”是茨中村传统丧葬活动中最核心的环节。所谓“守夜”,指的是村里无论是藏传佛教信徒还是天主教信徒家属去世,每家每户至少要出一个人到死者家里“过夜”,这是当地数百年来的传统,下面的个案颇能说明村民对此事的重视:
2018年9月的一天,茨中村一刘姓家庭有老人去世,茨中村村民永追正在前往县城德钦的路上,由于从茨中到德钦需要6小时左右的车程,她本来打算第二天才回去的,但当天在路上接到电话得知村里有人去世以后,她就在半路下车赶了回来,晚上9点才到家,目的就是为了去“守夜”。永追说,因为丈夫在外地干活,现在家里只有她,如果她再不去,家里就没有人去帮忙“守夜”,这样的话会被别人说闲话。
“守夜”通常在村长通知的当天晚上7点开始,参与“守夜”的人们会带一些酒、玉米或者面粉作为慰问品,近几年也有直接给现金的,金额从10元到100元不等。参与“守夜”的既有天主教信徒,也有其他非天主教信徒,两拨人的表现是不同的。天主教徒的任务是到祭台前念经,为死者的灵魂赎罪;非天主教徒则在死者家庭的院子里打牌、喝酒、聊天。念经的人坐在祭台前,以圣像十字架为中轴,男信徒和女信徒以男左女右的方式分开对坐,一直延伸到院子里,颇有规律。这种无意识的动作从文化的逻辑分析,其实是藏族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天主教组织的延伸——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还有男女在丧礼中守夜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在晚上7点到10点这段时间,参与“守夜”的几乎都是男人,因为这个时间段女人刚从农田干活回来需要做各种家务劳动,如为家人做饭,吃完饭后做家务、照顾孩子做作业等。若家庭需要女人去守夜,她们一般都在晚上10点甚至更晚的时间才能到达,所以“守夜”在上半场和下半场表现出来的场景很不一样:在念经方面,女人的嗓子天生就有优势,但由于上半夜去的男人多,他们念经的声音反而被非天主教徒在院子里的打闹声、喧哗声、谈笑声给掩盖了,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主人家在办丧事,反而有点喜庆的味道;到了下半夜,去的多是女人,而且男人们打牌、喝酒的时间长了,也累了,大多有困意,这时院子里传出的是女人们悠长的念经声。除了男女左右对坐以外,从祭台延伸到大院的念经队伍里还呈现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格局,即越靠近祭台的人年纪越大,越往外的人年龄越小。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与老年人大都脱离生产领域,生活比较清闲有关,退出生产领域的老年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过宗教生活,在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在第一时间到达办丧事的人家中;而中年人却不行,因为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要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由于老年人到的时间比较早,自然坐到了祭台的前面,在念经的过程中,随着中青年的慢慢加入,年龄阶序就自然而然在丧礼中呈现出来。
(二)告别礼
天主教的教徒去逝后的第三天通常是出殡的日子,这是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丧葬礼仪在茨中村的继承。丧家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需要为来送葬的人提供早餐,村里许多热心的人也会早早赶来帮忙洗菜、洗碗、搭炉子做饭,送葬的人们也陆陆续续到来,非天主教徒不需要念经,他(她)们吃过早饭以后就在院子里随意聊天,天主教信徒吃过早饭后陆续进入灵堂念经、做弥撒。做完弥撒以后,天主教会会长起身带领大家围绕棺材洒圣水,这时候死者的晚辈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茨中村,有些天主教教徒和藏传佛教信徒在同一个家庭同时存在,但任何时候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丧礼的持续,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明白“死者为大”的道理,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向死者表达尊敬:例如天主教信徒会在棺材前下跪,左右手象征性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非天主教徒则跪下磕三个响头。哭丧仪式往往也在这个时候自然启动,几个平时与死者关系比较好的或者感情比较深的妇女左手扶棺,右手做捶胸状态,声音由小到大哭起来,显得悲切凄凉,但在别人的安慰下,哭泣声很快就停止。哭泣为什么不能太久?按照藏传佛教徒的说法,哭得太久,就说明家属很伤心,不舍得让亡灵离开,那灵魂也舍不得走,这样就会影响灵魂的转世。天主教虽然不相信转世,但也认为死亡本身只是天主对人类肉身的惩罚而不是对灵魂的惩罚。肉身消失以后,灵魂仍然可以得到天主的怜悯和宽恕。一位信徒向笔者表示:“死亡是天主呼唤信徒们回归父家的方式,因为人来于天主,那么回到天主身边就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荣耀,是那些在可怜的尘世生活的人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由此看来,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对死亡的解释虽不同,但在丧葬仪式实践中却殊途同归,即都认为“死者为大”的道理,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向逝者表达尊敬。
虽然茨中村天主教徒的告别礼在时间上继承了欧洲传统,但在程序上却有别于欧洲。在欧洲,告别礼的主持者是神父——他为死者做最后告解,洒圣水以后即可抬棺出殡。但在茨中村,出殡前大家必须先听村长讲话——人们把棺材从堂屋抬到院子里,放在两张长凳上面,村长开始登场讲话,整个过程大概10分钟左右,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简单回顾死者的一生,给死者一个比较好的评价;二是安慰死者家属的话;三是劝勉村中所有人勇敢面对生活,好好工作等。村长讲话结束以后,人们才开始起灵送葬。
(三)送别礼
天主教的送葬队伍大体由三部分构成:最前面的一部分是高高举起的带有苦像的十字架、香炉、宫灯、天主圣像亭、总领天神亭等天主教信仰的标志,手拿着这些天主教信仰标志的一般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一系列天主教信仰标志之后,神父穿着紫色的祭服,戴紫色领带,手持《圣经》领队,他的后面跟着手捧白色蜡烛、身穿礼服、两两并行的圣职人员,其后是漆成黑色的灵柩,教友们跟在灵柩后面进行祷告和吟唱圣咏。茨中村送葬队伍的排序既有天主教特点,又呈现藏族传统特色。主要表现在队伍的前两部份是相同的,但跟着神父之后的送葬人员不同,送葬人员一路需要唱歌,在欧州,送葬人员的歌声多来自女性(因女性的嗓音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但在茨中村,送葬人员几乎全为男性,唱歌也由男性完成,因为在茨中村藏族传统里,女人是不能送葬的。然而,女性不送葬不等于说女教友完全消失了——在丧葬礼中,她们会比送葬队伍提前到墓地,早早在墓地等待着为死去的教友举行葬礼。送葬队伍中的教友团体之队列看似很随意,但大体上还是呈现出老中青的阶序感,即走在最前面的是老人,然后是中年人,再后面才是青年人。茨中村天主教下葬所使用的灵柩与欧洲天主教相同,颜色漆成黑色,呈长方形,由六块二到三寸的厚板组成,长约2米,宽约0.5米,棺盖处刻有大型金色花形图案,头部还刻有小型的十字架符号。不同于欧洲天主教送葬仪式的另一点是,茨中村的送葬过程中有孝子扶柩,村里其他不信仰天主教的中青年人在吆喝声中轮流抬棺,在茨中村,人们乐于做这些事,因为这是帮助他人,同时也是一种善事,传统上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积累阴德,获得更多的福报。
(四)葬礼
灵柩被送到目的地以后被缓缓放在墓穴旁边,这时,非天主教徒退至外围,天主教信徒再次聚集在棺材周边,神父带领大家念经,然后环绕棺材两圈,洒圣水、下葬、封土,整个丧葬过程就算结束了,人们手拿树叶象征性地把自己在墓前留下的脚印抹去,然后各自离去。这个过程基本是欧洲天主教葬礼仪式的复制。
四、藏族传统丧葬礼与上帝信仰
天主教丧葬礼是天主教群体向社会展示信仰的重要方式,也是教会等级制度的反映,欧洲纯粹的天主教丧葬礼主要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丧礼举行的地点是在教堂——信徒如果在家中死亡了,并不意味着丧葬仪式可以开始了,只有当人们把棺柩抬到教堂,棺柩从亲属的手中转移到神父的手中,真正的丧葬仪式才开始;二是神父在丧葬仪式中的角色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自丧葬仪式启动的那一刻起到结束,他主持所有的环节;三是死者的亲属与前来送别的其他人没有明显的主次地位,他们都只是普通的天主教信徒的一员。但这些在茨中村明显已经发生了改变。
(一)丧礼地点发生变化
从上文不难看出,茨中村天主教徒举办丧礼的地点由西方的“教堂——墓地”变成了“家——墓地”。根据茨中村天主教教堂马神父提供的信息,近年来,茨中村有7名天主教徒去世,只有1个家庭(编号为L5)把丧事操办的地点设在了教堂,而其他家庭都是在自家里操办。那么,促使人们对地点做出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神父认为主要取决于各家到教堂的距离,他说:“在茨中村,人们居住的比较分散,像在河对面或者半山坡住的那些信徒,要把棺材抬到教堂需要过河或者下山,然后再抬往山上的墓地,就比较麻烦。L5不一样,他家离教堂比较近。”(1)访谈时间:2018年10月14日,地点:茨中村天主教教堂,访问对象:茨中村天主教教堂神父,马永平。
不过笔者随后对神父所说的7个家庭进行距离上的测量,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7个家庭距离教堂最远的是3公里,最近的是1公里,L5家庭距离教堂1.5公里左右。换句话说,L5的家庭并不是离教堂最近的。再则,无论距离长短,几乎每个信徒平常都能坚持到教堂做礼拜,为何到举办丧事的时候会嫌距离远呢?由此看来,距离并不是人们选择不去教堂举办丧事的因素,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一样,天主教徒平日去教堂做礼拜只是个体至多是天主教群体内部的事,但死亡却远远超越了天主教会,它本身就是村落生活的公共事件,必须要考虑其他非天主教徒的态度。特别是藏族有“守夜”的传统,如果把丧礼的地点设在教堂,就等于将自我与其他非天主教徒(藏传佛教信徒)进行区隔,因为后者不可能进教堂参与“守夜”。事实上,茨中村教堂前面也设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平时天主教教会举办活动的时候藏传佛教信徒也会到院子去跳锅庄舞、耍坝子。虽然“守夜”对于藏传佛教信徒来说也是到丧家那里打牌、喝酒、玩乐,但是体现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正如一位村民指出的一样:“我们去‘守夜’虽然只是喝酒、聊天,但这是大家关心死者家属的一种表现,只能去死者的家里才能体现出来嘛,把地点改到教堂的院子就真的是只有吃喝的意思了。”至于L5的行为,村民大多不认同,许多村民指出他性格孤僻,在村里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很少参加村里其他活动,去世前他主动要求在教堂办丧事。
(二)仪式主持者发生变化
在茨中村丧葬仪式中,神父的地位下降了,他不再像欧洲天主教那样,承担仪式主持的角色,而作为“地域共同体核心”的村长则处于中心位置,在整个丧葬礼过程中他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主角负责把丧事通知给非天主教信徒的家庭,第二次则是送殡仪式中,在亡者即将送葬前讲话。这与茨中村的传统息息相关,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历史上滇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发生,滇西北地区的村落组建原则并不是最原始的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地缘建立起来的,历史文献将这种组织形式称为“属卡”。一般来说,一个属卡由一个以上的自然村组成,推本溯源,它可能决定于最初土司所划的土地之界线。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就曾经发现:“大中甸当时还存在10多个属卡,小中甸有5个属卡,尼西有30个属卡,江边境有8个属卡,归化寺所属的300户‘摧扔’和70户‘罗扔’分属若干个小属卡[9]28。每个属卡有自己固定的领地、牧场和田地,仅供属卡内部的成员使用。属卡与属卡之间的分界线往往以河流、道路、山坡或者森林等等为标志。“老民在属卡和自然村中为长老,平时婚丧或宴请聚会都坐首席,处于权威的地位。”[9]120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属卡”组织逐渐消亡了,但其文化惯性仍然存在——村长处于丧葬礼的核心位置,神父仅作为一名普通的信徒参与与信仰相关的活动,虽然他也主持“弥撒”,但此时的“弥撒”在家里举行而非教堂举行,事实上已经降低了天主教的地位。
(三)教友身份发生变化
在茨中村藏族天主教徒的丧葬礼当中,教友不再平等,至少显示出了两个等级。一是年龄等级。在丧礼的亡者日课、弥撒、告别礼、送别礼以及葬礼的集中祷告中,越靠近天主信仰标志的人年龄越大,人群的组合中“老—中—青”的阶序感非常明显,这是对茨中村传统社会组织原则的继承。二是性别等级。在整个丧葬礼中,男左女右分开对座,也是茨中村天主教教徒平日在教堂做礼拜时的就座方式:茨中村教堂以圣像为中轴左右摆放着供信徒做礼拜的长椅,左右两边的长椅被中间1米宽的道路隔开,做礼拜的时候,男信徒通常是无意识选择坐在中间过道左边的两排椅子上,而女信徒则相反,大多坐中间过道右边的椅子。此外,在藏族的传统丧葬的送殡队伍中,女性自始至终是不允许出现的,许多藏族同胞解释道,因为送葬的路途会遇到恶鬼,女性只有半条命,所以不宜前往[10]。这种观念在藏族天主教的丧葬礼中有延伸也有改变,说它是延伸,那就是在大多时候,女教友不随送葬队伍出发,而是提早比送葬队伍到达墓地。不过,女教友提前到墓地为亡者念经祈祷又使藏族传统的丧葬观念发生了变化,但它并没有打破传统送别礼的结构。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茨中村,天主教信仰与当地藏族传统习俗互有嵌入,有效地防止了信徒与社会其他群众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这实际上也是藏族文化在多宗教背景下绵续的方法。而社会结构,是我们透视天主教与藏族传统文化交融的有效路径——相比于汉族地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结构,滇西北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以共同地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属卡”社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依附的人际关系是地缘不是血缘,是从家庭拓展出来的地域关系。在“属卡”社会,每个“属卡”都制定有条例或者公约以规范内部成员的言行,虽然各个属卡制定的条例各不相同,但中心内容无非都是对内强调民主、平等、容忍等的观点,对外强调维护本“属卡”的利益[11]。在这种结构之下,天主教信徒与其他非天主教徒一样把“公”与“私”都分得很清楚,例如天主教徒也一样热衷于村落的各种公共事物。在藏族地区,地缘共同体的社会是以神山为边界的,例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某人说:“我是属于某个神山属地的人”即为明证,藏族传统的神山崇拜是这种现实关系在信仰上的集中反映,如茨中村就三面环山,东面的神山名叫“代立出家”,西面的神山名为“次里别处”,北面的神山是“阿杜白丁”,村民都视它们为村里的保护神。事实上,从神山崇拜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它是集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一体的信仰,藏族的许多民间传说中都有天神下凡到某座神山然后统领人间的说法,民间也认为神山上存在着通往天界的“天梯”[12]。在藏语中,“祖”[(g)tsug]的意思是“头顶(前顶、颈背等),”[13]与“高”“天”同义。以茨中村的情况来看,村落的坟场就建立在西南一座神山上,名字为“扎拉凶姆”,也称为“帕拉尼姑”,意为人死后的归属地,很显然,从这个名字的音译来看,反映了茨中人也存在将神山崇拜和祖先崇拜融合的迹象。茨中村的藏族在接受天主教以后,这些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针对天主教教义中认为人死以后灵魂应回到天堂的说法,不少信徒就表示,“天堂”之所在地就是天界,而神山就有通往“天堂”的“天梯”,因此,茨中村的藏族天主教徒对神山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虽然不像其他非天主教徒把神山看成神一样,但同样是圣物,轻易动不得,每当藏传佛教徒在“转山”“祭山”的时候,天主教徒乐于祷告,他们认为祷告其实就是藏传佛教徒的“拜神山,形式不同,实则意义一样,都是对神山的尊敬”。这也说明天主教教义与地缘社会共同体结构本身存在着某种深层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