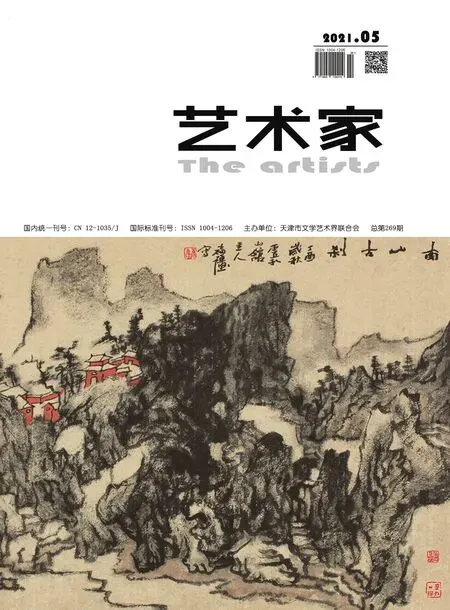探究多生态语境中莲箫舞的生存境遇与角色价值转换
□刘怡玲 福建师范大学
一、莲箫舞的历史渊源
莲箫舞又名“莲厢舞”“连响舞”“金钱棍”“霸王鞭”“舞花棍”“柳边柳”等,其历史源远流长。目前,考古研究认为莲箫舞主要从我国汉代时期的民间舞流传而来,其诞生源地说法较多,但也证明了莲箫舞在古时流传的范围便十分广阔,如今在我国的陕西、四川、云南、安徽、苏州等地均有类似莲箫舞形式的舞蹈,只是叫法不一、服饰多样、讲究不同。众多莲箫舞中以陕西榆社地区的“霸王鞭”最为著名,但究其根源,诸多地域的莲箫舞依然来自同一本体语汇特征和“钱棍”形式的道具形制。莲箫舞的道具多采用三尺三的长木棍,中间稍细,两端各钻上几孔,每个孔用线穿上铜钱,再用红布或彩条绑在棍的两头,在做动作时,铜钱会伴随舞者对身体各部位的击打动作发出“擦擦”的声响,也正因如此,得名“连响舞”。同时,因其舞蹈风格粗犷豪迈,热烈矫健如霸王出鞭,故又名“霸王鞭”。而“莲箫”之名,主要来自四川地区的称呼,由于其主体“棍”主要采用细直竹棍制成,加之两头钻孔形同“竹箫”,两头彩条翻飞如莲,因此称其为“莲箫”。
莲箫舞传承人常说:“莲箫是穷人的艺术,也是谋生的手段。”在早期中国的传统莲箫舞表演中,表演场合主要是市井街头,表演者也多是乞讨的穷人[1]。在康熙年间的《百戏竹枝词》中有记载:“徐沛伎妇,以竹鞭缀金钱,击之以歌。”这其实描写的就是莲箫舞,边歌边舞是其传统形态。后来,莲箫舞逐渐从民间走向宫廷,在同一时空的不同境遇下同步发展。譬如,榆社县志中曾记载了在西晋末年,赵王石勒在战争胜利后为了庆祝,以手持彩鞭起舞的方式表达喜悦心情。在诸多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莲箫舞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发展脉络,这为我们把握莲箫舞的当下与未来发展可以提供了更多的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
二、莲箫舞动作风格特征
莲箫舞的动作有多种规律线路,舞起来时主要用道具击打身体或碰击肩、肘、背、跨、膝等部位,或者以棍击打地面发出节律。其道具握法主要是以手握棍的中部,虎口上为“棍头”,虎口下为“棍尾”,手心为正,背手为反。莲箫既可一人舞,也可两人对舞或群舞,其步伐多样,有立、跪、跳、行进、蹲等,在不同步伐中莲箫击打次数不一,主要跟随舞者步伐和动作进行改变。莲箫舞的基本动作主要以“推擦”及“拉擦”为主,一般为双腿呈八字步站位,右手握棍横于胸前,“拉擦”动作时右脚前吸腿,左脚屈膝,同时左手屈肘掌心向下,在胸前拍击棍头,同时左转四分之一圈,目视被击点[2]。“推擦”表现为左脚前吸腿、右脚屈膝,同时左手屈肘掌心向上,右手持棍中,棍头与左手掌心推擦,棍头向左,左手心向右。在舞蹈中虽基本韵律元素不变,但其动作轨迹发展和转换连接各式多样,如“棍头横击左右大手臂”“击左脚”“棍头尾转圈击地”“棍尾拍击右大腿及右脚背”等。
莲箫舞在表演时与音乐的结合十分紧密,且不仅仅限于在节奏中击打四肢,在传统的民间莲箫舞中,表演者要伴随着歌律、唱词进行表演。其歌词内容根据各地不同的民间故事和风土人情进行创作,有《采花》《十对十》《放风筝》等[3]。四川地区的莲箫舞中有一首代表作——《数十二月》,其歌词为:“柳啊柳柳连柳,四月芒种把秧插,柳啊柳,五月龙船下河坝,柳啊柳,六月间扇子就在手中拿,七月亡人回家下,柳啊柳啊柳,八月中秋望月华……荷花柳灯儿连,海棠花……”在进行演唱时,伴随着旁边简单的击鼓节奏,舞者手执道具或边击打脖子,或往前走十字步颤,时而将莲箫抛向空中,时而从胯下穿过,动作形式极其丰富,表情喜悦生动,气氛热烈欢快。在这样边唱边舞、边逗边乐的喜悦环境中,莲箫舞为民间百姓带去了贴近生活、落于本土的艺术,而莲箫舞也在百姓的认可中得以流传千年。
三、不同地区莲箫舞传承发展的生存困境
由于早期跳莲箫舞的多是“乞巧者”,所以随着人口的流动,莲箫舞逐渐流散、传播于全国各地,但由于时代发展和审美变化,以及学习莲箫舞的人数不一,莲箫舞在不同地区面临着不同的生存状态。四川地区的莲箫舞如今也面临着与传统民间舞一样的窘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审美的变化,使莲箫舞落于创新
四川莲箫舞传承人文莉经历了莲箫舞从辉煌到落寞的跨越,她曾在采访时遗憾地说:“从2008 年左右,莲箫舞的演出就少了,现在那几根曾丁零作响的莲箫棍只能在角落孤零零地放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流行文化、快餐式时尚令人目不暇接,莲箫舞作为传统文化中本就小众的艺术,其发展和传承变得更加艰难。除四川地区以外,湖北恩施莲箫、江苏苏州莲箫等也都面临着传承和发展困难的问题。这对我们的传承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立足本舞蹈的精神与动律进行创新,在守正与创新基础上创作更符合新时代审美形式和思想的作品。
(二)上辈传承人老龄,新代传承人培养不足
根据调查,我国现有的上一辈莲箫舞传承人最小的已有60 多岁,如四川地区的莲箫舞传承人文莉已68 岁;湖北恩施莲箫舞传承人李思义已75 岁;眉山莲箫舞传承人马金花已81岁……上一代传承人逐渐老去,培养新一代莲箫舞传承人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老艺人的“传帮扶带”,更需要年轻人转变思想,接受与认可本地区的文化,愿意主动学习和传承。
(三)莲箫舞的传承机制不健全,政府辅助不足
莲箫舞在全国分布虽然较多,但其表演规模和体系在逐渐缩小,一方面是由于形式落于现代审美,舞蹈本体较为固化;另一方面是引文保护与传承莲箫舞的传承机制不健全,甚至有的地方的莲箫舞的传承只靠一两位老艺人苦苦支撑。在这样的极危境遇下,为了不让莲箫舞失传,政府应该加大对莲箫舞的扶持与保护力度。
四、当下莲箫舞的角色价值与审美功能转换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莲箫舞想要扎根与繁荣,需要结合生存土壤和相应的文化语境。为了发展莲箫舞,许多地区也在进行着不同的尝试,概括起来主要是从审美形式、角色的功能转变及内容的表现上进行掘进和开创。四川地区就有民间莲箫舞艺人从“唱跳”形式中的“唱词”入手,在歌词上进行创新,演唱符合新时代内容的歌词。譬如,民间艺人创作出赞美十大民生的莲箫舞歌词:“莲箫是根竹棒棒,这头打来那头昂,党的惠民政策好,听我来给大家唱。一唱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群心爽……”在审美功能上,除了改编歌词来贴近时代外,安徽霍山地区的人们还将传统的莲箫舞编排成欢度春节的表演节目,增加了更多花哨与高难度的动作,铜钱撞击身体发出的“哗哗擦擦”声更烘托了过年的热闹气氛,使得莲箫舞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日常中。这种表演场合与形式彻底去除了莲箫舞早期乞巧的“穷人气”,变成了喜笑多彩的舞蹈节目。除了舞蹈本体的审美动作上的变化,莲箫舞的传承者还不断开发着莲箫舞的科学健身和体育功能,如安徽巢湖的人们就将打莲箫转变为民俗体育活动,在各个公园与广场中打健身莲箫。这样的做法直接转变了莲箫舞在百姓生活中本来呈现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虽然脱离了舞蹈以美为基、以情为本的要求,但为莲箫舞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各地传承莲箫的许多方式都非常新颖与科学,既结合本土与百姓的需要,也为莲箫舞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前进的路径。但此种各地随意开发和转变莲箫舞的举措不一致,水平参差不齐,对资源的整合不够充分,过度商业化或过度消退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要使莲箫舞能长久活态传承,还需要在尊重各地莲箫舞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成体系的保护。
五、推动莲箫舞发展的建设性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久居深闺”的古董摆设,也并非易碎、遥不可碰的。现代中国强调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莲箫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当担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成为展示中国多样文化形象的名片之一[4]。在当前时代,文化的斟酌与发展更应当慢下来,让其在生活实践中慢慢散发韵味。我们不仅要让莲箫舞“活下去”,更要使其“活起来”,将有历史感的莲箫舞与高新化社会相连,与百姓需求相连。因此,为了完成“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任务,笔者对莲箫舞的发展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一)取精去糟的形式和与时俱进的表达
莲箫舞最早期的形式虽是从乞巧表演而来,有的舞蹈动作和寓意也较为低俗,虽然动作是舞蹈发展的本体生命密码,但诞生于人民并创新于人民才是使连箫舞能传承下去的“药方”。要想以活态的形式传承莲箫舞,就需要把握其文化基因、审美特质、内涵价值,要体现当地民间文化的特征和内在生命力。活态传承也体现了莲箫舞是灵活的、可变的,这更要求莲箫舞的传承人与创作者要自我“内省”,要取精去糟地优化舞蹈的形式,深化和丰富莲箫舞可表达的意兴和趣味。
(二)本土特色莲箫舞形象的文化树立与维护
莲箫舞在各地有不同的讲究与习俗,对莲箫舞的未来发展与传播,各地应该结合本土的莲箫舞进行“不失其魂”的适当包装与推动。当下,许多非遗舞蹈除了本身具有文化保护价值,地方与人民都在努力挖掘其经济和商业价值,还将本地文化与推动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同时打造地方文化名片,形成良好的循环效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消费的天然属性,莲箫舞的保护不应该变成死板的圈养物,应该既让人们了解莲箫舞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又能塑造地区莲箫舞的特色形象。例如,将莲箫舞表演融入当地的旅游体验;将莲箫舞的相关形象做成文化纪念产品等;将“文化”与“市场”进行统一,实现多功能的结合,让小众变为大众,让古老变得新颖,让衰退变成繁荣。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莲箫舞保护机制多层构架
保护莲箫舞不能单靠传承人势单力薄的呼吁,只有建立完整的、系统的机制,才能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使莲箫舞能在共同的文化生态圈中进行细致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对社会中能够影响莲箫舞文化、能够促进其发展的社会团体组织提出要求和准则。按社会学的考察,影响莲箫舞的因素主要有政府、文化馆、民间艺人、学校、演出团体等,这五个因素对传承和保护莲箫舞有积极作用。第一,政府应该正确施行《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莲箫舞传承人进行有效认定,并要发放传承基金补贴,举办相关的非遗展演活动。第二,文化馆应当肩负起重任,开展当地连箫舞的资源搜集及舞蹈创作活动,将非遗保护、传承和公共文化相结合,还要为代表传承人提供相关服务。第三,民间莲箫舞艺人应该发挥自己传承人的作用,自我创新,弥补不足,自觉与时代审美和百姓需要相结合。第四,学校应该承担培育新一代传承人,以及普及当地文化的责任,加强莲箫舞在校园中的普及,如将莲箫舞融入课间操,就符合当地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第五,专业的舞团或表演团体要把握莲箫舞的文化基因和可能结合的新时代内容,将艺术美与内容美相融合,在表演中使当地观众能够接受莲箫舞,使外地观众能够喜爱莲箫舞。
(四)借多媒体媒介扩大莲箫舞影像与资料传播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分量不可低估,莲箫舞要真正走向地区以外,被更多人看到和接受,还需要借助媒体力量,这样莲箫舞才能传播得更远。当前,艺术的跨时空传播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非遗传承人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上传非遗视频,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甚至从中找到了接班人。但是,对莲箫舞的视频传播依然较少。在大数据时代,莲箫舞也应该抓住机遇,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和节奏。无论做商业性质的推广,还是莲箫文化的分享;无论组织性的,还是个人性质的,莲箫舞的多媒体时代、多元文化时代都不应该被淹没。莲箫舞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扩大其影响力,吸引新的观众群体。从口传身授到文字记载,再到屏幕传播,这是时代的进步,但这三方面不是顺向的继承,而应该同步推进,这样才能多方面、全方位地对莲箫舞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发展。
结 语
总之,对莲箫舞的保护与发展,我们不应该影响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存在方式,但可以从客观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莲箫舞能够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摒弃消极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虽然莲箫舞在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在初期建设和探索阶段,莲箫舞已可以借鉴许多非遗舞蹈的成功经验弥补自身不足,而且,莲箫舞应该在结合本体特色与地区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