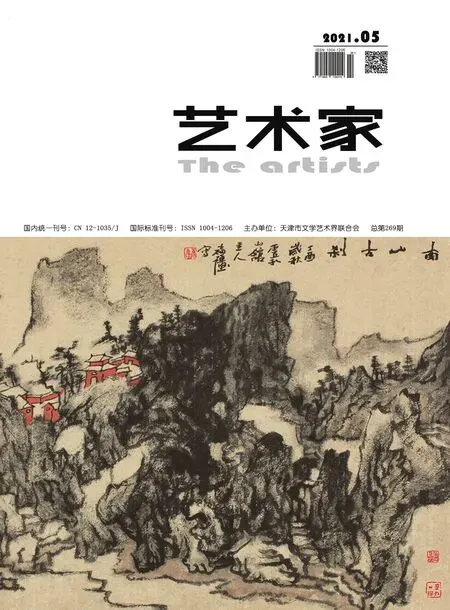论国产奇观电影中“自我东方化”的形成与现状
□慕 韩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随着视觉消费时代的到来,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推进下,越来越多强调视觉奇观的电影被搬上荧幕,并逐渐形成了名为奇观电影的新电影类型。奇观电影往往将奇异的身体、异域的场景、超常的速度和动作等奇幻视觉元素作为卖点来吸引受众。在奇观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东方奇观”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受到国内外诸多导演的追捧。
一、西方之臆想:公式化的“东方”
“自我东方化”的认知来源是在西方权利话语加持下形成的“东方主义”。同理,国产电影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也是在西方的“东方奇观”电影不断的意识形态输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在讨论国产电影“自我东方化”问题前,先了解西方世界对“东方奇观”的影像建构。
西方用公式化的模板创造着文艺作品中的东方形象,这些形象往往透露着隐秘的权利关系,经由西方意识形态重构的“东方”与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联系不大,它只是文化偏见和文化沙文主义共同孕育的怪胎。西方怀着一种“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反复言说着自己捏造的“东方”,并将其变成凝固不变的“东方奇观”。
(一)女性化的“东方”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受环境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女性逐渐变成了男性的附庸,变成了必须听命于男性的“他者”。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性别差异进而演进为社会文化力量上的不平等,即“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1]。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可以说是其典型代表。影片用不乏性暗示的镜头讲述了末代皇帝的生活经历,全片散发着清廷被女性化后产生的“东方”视觉魅力。贝托鲁奇用活动影像将中国构建成与当代消费主义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奇观语境。置身于古老而娴雅、温顺而恭谨的女性化“中国”的视觉奇景中,观众的视觉贪婪被充分满足。美籍华裔电影评论家周蕾进一步阐释道:“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乌托邦和情欲主义出于各种批评目的进行游戏。”
(二)邪恶化的“东方”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伊斯兰形象在西方再造“东方”的过程中一直被描绘为邪恶的化身。实际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逃离被奇观电影邪恶化的命运。
谈及西方电影对中国的邪恶化表述,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要数以傅满洲为主人公的系列犯罪悬疑片。随着18 世纪末“黄祸”论在西方世界的蔓延,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最有传播效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选择顺应西方人“黄祸”的文化心理,开始在银幕上塑造诸如傅满洲这样的邪恶华人形象。身着清代服饰的傅满洲是一个拥有极高智商的犯罪狂魔,他聪明绝顶却阴险狡诈的形象满足了美国人对“排华主义”的政治要求。在该银幕形象诞生后的几十年里,有15 部以傅满洲为主人公的电影陆续上映且票房不俗。然而,其原作者萨克斯·儒默却在之后表示自己并未到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人,只是“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
(三)未开化的“东方”
种族自负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向外扩张的内驱力,而他们的扩张行为又必将进一步增强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导致西方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对异域文化进行贬低和归化的现实。法国学者基亚认为,艺术家所想象和表述的“群体越大,想给这个群体确定形象的人就越要冒着抽象化的风险,事实上,这个形象将会显得是漫画化式的、图解式的和使人惊奇的”。
西方电影在塑造“东方奇观”时,往往怀着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负,将华人塑造为一种未开化的银幕形象。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角色,他们往往操着一口蹩脚的“粤式英语”,缺少文明社会该有的绅士风度,即使会些拳脚功夫也难以使用智慧降服对手。在《燕尾服》中,成龙扮演的唐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角色,作为联邦探员的他在宴会上频频出丑,甚至被趴下了裤子。功夫明星的光环荡然无存,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不知礼教的华人小丑。
二、东方之附和:本土影像中的“自我东方化”
不同国家在拍摄奇观电影时都会理所当然地按照本民族的审美特征创造出不一样的亚种,中国导演在拍摄奇观电影时自然也有自己的独特选择。然而,本土导演在用镜头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却很难跳出“自我东方化”的藩篱,他们往往会用古典元素堆砌、展示阴性弱者的方式来满足国人或不自知的“自我东方主义”心理,并以他者化的姿态向西方意识形态低头。
(一)东方元素堆砌
按照萨义德的说法,西方世界对东方电影的接受往往与“东方主义”关系密切,也就是说,东方电影只有满足西方人对“东方奇观”的臆想,才能够在西方的电影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
最擅长按照西方臆想调配东方“异国情调”的莫过于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在他们执导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菊花簇拥的金銮宝殿、胡杨林中施展轻功打斗的侠女、低眉信手拨弄琵琶的秦淮妓女、“本是男儿郎”的较弱男旦、深宅大院里被鸦片蚕食的美丽少妇。而这一切被置于“东方奇观”中的视觉形象大多数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叙事功用,不过是导演为了满足异文化观者的视觉消费而采取的迎合策略。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西方世界既然已经在过往的历史中建构了公式化的“东方景观”,我国的电影人继续在西方无端臆想的基础上加以符合无异于承认了“东方主义”的合理性。
(二)展示阴性弱者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奇观电影中的阴性弱者并不仅限于女性,同样包括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而陈凯歌就是一位偏好于展示女性化的男性弱者的导演。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或许可以被视作和西方电影中弱者展示完全不同的景观模式,男性角色程蝶衣作为无力反抗欺凌的弱者,体现出中国所特有的“弱者美学景观”,这种投射使“弱者成为一个景观,观看者可以以同情的形式投注大量感情”[2]。而这种同情一定程度上可以塑造观看者的自恋,使西方更加合理地认为东方的阴性弱者是待西方拯救的群体。与陈凯歌不同,张艺谋则偏好于展示女性弱者的悲惨境遇,并用情欲化的身体展示来实现对女性的物化的附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用精致的红唇、红布包裹的小脚、血淋淋的耳朵等女性身体影像将东方女性物化为待拯救的美丽玩偶。“妻妾成群”奇观下美丽而悲惨的女性形象成为“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无耻言论的隐秘辩护。
三、东西之联动:合拍片中的“东方主义”掠影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曾提到“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表述”,因此,西方视域中的东方总是充满“绝望、失败和灾难感”。相反,欧洲人对自己的民族书写则是充满进步和胜利的。这种观点自然不能够被东方人所接受,却经常出现在东方的艺术作品中。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电影市场也被全面裹挟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合拍作为一种新的电影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在中外合拍片中必然会涉及中外之间的意识形态碰撞,其中的显性问题便是影片如何处理和定义奇观电影中的“东方”概念。在近年来的中外合拍片中,我们也经常能找寻到“自我东方化”倾向。
李安导演的经典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可以算说是中外合拍片中的翘楚,影片用唯美的镜头语言讲述了四位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也将温婉的江南和狂野的西域作为充满视觉吸引力的异质化景观展现给观众。影片的情感把握和哲学发问不可谓不老辣,然而,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卧虎藏龙》所讲述的虽然是东方人的故事,但实际上讨论的是西方人的哲学命题。李安借由四位主人公张弛不同的人生态度,讨论的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表述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的命题,四位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则是李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叙事舞台的中国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样一个命题的展开似乎能够在任何文化背景下完成。特别是当李慕白问出“存在与虚无”的问题时,西方人的思考维度更是暴露无遗。
结 语
“东方奇观”作为一种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失真拟像,完全是西方人经由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捏造的。然而,电影中的“东方主义”却不仅仅是西方电影中的常驻意识形态,也是长期以来隐藏在国产奇观电影中的隐痛。近年来的国产奇观电影呈现出的往往是站在异文化立场上审视被“他者化”的东方文化的奇观景象。换句话说,这些电影表现出的是用他者视角讲述的“自我东方化”的东方奇幻故事。这种语焉不详的文化表达和混乱不明的身份定位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