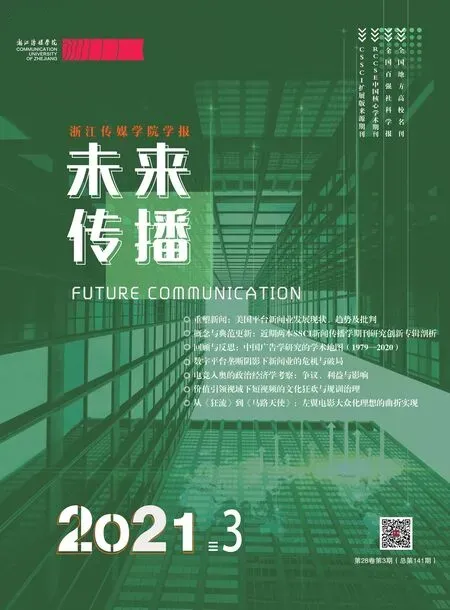论茅盾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
——以《蚀》《子夜》为例
张连义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政治性与文学性向来是茅盾研究的重要议题,茅盾的政治身份及其作品与时代的亦步亦趋似乎坐实了其作为政治家的作家身份,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政治性是茅盾作品的主要特征,其作品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作品的政治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甚至替代了文学价值。“蓝棣之基本否定了《子夜》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只肯定它的社会文献价值,认为《子夜》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缺乏深厚的哲理内涵以及对于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只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在王一川看来,《子夜》欠缺小说味,概念痕迹过重,主题先行,缺少审美价值。此外,王晓明、徐循华等人的文章也对《子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这些文章共同认为茅盾及其《子夜》具有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缺少复杂的思想意蕴,缺少审美价值。”[1]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茅盾的作品忠实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呈现。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就认为:“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茅盾的左翼思想立场对他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在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政治活动经验的文学汲取。这样的忽略,影响到对茅盾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偏向于政治立场的阐释,而淡化了对小说家茅盾的文学经验的考量。”[2]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也以《子夜》的伏笔论证茅盾作品的现实主义:“从许多伏笔之中产生了一种共识,如果把这样的过程视为代表现代中国的一位作家的创作过程,就可以重新认识不能只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议论,来解释茅盾文学中所蕴含的透彻的现实主义。”[3]不难看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茅盾研究的焦点之一。在此,笔者无意延续这种讨论,而是追问:政治性和文学性都是茅盾思想的呈现,在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有没有统一的因素?如果有,又是怎样统一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接下来,就以影响最大的《蚀》三部曲和《子夜》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一、《蚀》三部曲:“在路上”的理想叙事
《蚀》三部曲被称为“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典型作品。作品中,革命与恋爱构成亦步亦趋的关系,一代青年男女在时代变化面前的思想嬗变,即从幻灭到动摇再到追求的变化,都与革命纠缠在一起,或者说,在他们人生彷徨的时候,正是革命给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和人生的意义。也因此,《蚀》三部曲也成为当时社会环境下人生选择的寓言。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青年男女的人生选择和革命的关系又有着内在的龃龉与悖论,从而使作品有了多维度解读的可能。
《幻灭》中,静女士想安心读书,可现实的庸俗使其读书的想法破灭,参加革命之后,革命队伍里的乱象更使其不适应。革命也好,爱情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摆脱人生无意义的工具,尤其是,革命及其倡导的自由与青年的冲破烦闷的发泄杂糅在一起,形成革命的“乱象”,更使静女士陷入彷徨。直到遇到强连长,静女士才找到她心目中革命应该有的样子。《追求》中,不少人关注史循与章秋柳在意志消沉之后的新生,实际上,同学会中众多同学的人生和理想追求才是作品要表现的主要内容。仲昭、曼青等各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只不过每个人的处境不同追求不同而已。相对于史循和章秋柳,仲昭的“半步走”哲学和曼青的人生追求与遭遇更富有典型性。实际上,尽管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但因为处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几乎都是沉闷的。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可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又被现实损耗殆尽,从而只能以麻木的心态随波逐流。对他们来说,政治不过是一种理想,他们更在意人生的追求,尤其是理想的追寻。方罗兰是《动摇》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动摇”的象征。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在方罗兰游移不定的外表下,是对局势的担忧,是对店员和店主的同情。当别人都在把“革命”当作工具的时候,方罗兰坚守着革命的原则,也因为坚持原则,与投机分子、劣绅胡国光结下仇怨。胡国光正是抓住革命对自己有利的规则不断谋取利益,最终将方罗兰逼到逃亡的境地。方罗兰是一个理想型的人物,对革命、对政治始终抱有幻想,对于劣绅胡国光也有着警惕,可是他又尊重规则,结果导致胡国光的影响一天天壮大,他也深受其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摇》的主旨与其说是表现方罗兰的摇摆不定,倒不如说呈现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乱象。“革命”一方面想要解放国民,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尤其是使店员和店主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又不能阻止这一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结果导致不少人投机倒把,甚至到后来革命不再是解放人民的工具,而成为害人的借口。“如所分析,方罗兰之所以摇摆不定,是因为他经历了大革命的复杂性,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来思考大革命中的一些政治现象:把土豪劣绅四个字造成了无数的新的敌人,赶走了旧式土豪,却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要自由结果仍得了专制。他怀疑暴力革命的方式。在感情上,方罗兰则动摇于爱情与婚姻之间,他的怀疑所指向的,是他自己,他怀疑有能力理解孙舞阳的感情。”[4]在革命和解放的过程中,妇女因为处于风口浪尖,注定要接受更多的考验。“妇女解放”给了她们自由,但是,何为解放、解放何为又是没有明确的,这样,一方面她们因为追求自由陷入解放的误区而沦为男性的玩物,如钱素贞;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过程中女性又不能支配个人的命运,甚至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在解放的过程中,很多女性被强行分配给别人。无论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都以革命或解放的名义将她们视为玩物、工具,甚至连无辜的妇女也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方罗兰的动摇,倒不如说这种复杂的社会形势使作家对革命产生怀疑和动摇。
《蚀》三部曲写出了青年男女在时代变化面前的思想挣扎以及他们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革命与理想的复杂关系。他们怀抱理想踏入社会,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未给他们提供实现理想的条件,昏沉、压抑的现实使他们的生活百无聊赖,他们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成为他们理想的寄托,革命描绘的远景更是满足了他们的人生诉求,革命就这样与理想合而为一,革命就是理想,理想就是革命。显然,他们是将革命理想化了。革命是残酷的,理想是浪漫的,当借助于革命去实现人生理想的时候,必然存在着龃龉。尽管革命并不是想象的样子,但革命又是他们摆脱庸俗现实的工具,他们只能以“在路上”的心理追求革命,并以此遮蔽现实的庸俗。方罗兰在革命道路上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是知识分子追求理想时候遭遇的命题。作家并未将革命理想化,而是写出了革命的残酷性、复杂性,以及革命过程中夹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庸俗甚至混乱的男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革命维度解读《蚀》三部曲尽管合理,但也存在遮蔽多维度解读的可能。
二、《子夜》:源于现实的政治文本
《子夜》被视为典型的“社会剖析小说”,阶级性是人物的基本属性,也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和最终的命运。不过,在坚持阶级性的前提下,作品并没有忽视人物的复杂性,而是将其放置于具体的环境,写出他们生存生活的现实,即尊重现实,努力忠于现实,从而使其成为文学经典。作品中,工人、资本家、地主等各个阶级的典型人物均登场表演,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为了金钱展开的明争暗斗更是被不少论者视为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的斗争,甚至作品也被解释为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同表现。实际上,吴赵之间的斗法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而不是个人理想。吴荪甫想通过债券市场化解个人的资本危机,赵伯韬则是为了获取金钱,金钱成为二者矛盾的焦点。所谓的资本家冯云卿、周仲伟等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冯云卿在乡下用尽手段赚了钱到上海当“寓公”,为了不坐吃山空,投资债券市场。可债券市场受金融大鳄控制,冯云卿沦为牺牲品。为了获取内部消息,冯云卿唆使女儿接近赵伯韬。为了金钱出卖女儿当然是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父亲将亲生女儿推到色魔怀中的内疚、无奈、悔恨,也有着十足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显示出冯云卿为了生存的痛苦和无奈。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在上海滩生存下去,冯云卿对自己的女人在外面鬼混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几近失去尊严。周仲伟为了保住工厂而将工厂抵押出去自己做了管理,他不是没有理想,但当生存和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生存更为重要。其他如朱吟秋、陈君宜、四小姐蕙芳、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珊乃至于一般的工人更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夜》无疑展示出各个阶级、阶层的真实生态。
实事求是地讲,《子夜》确实较为真实地呈现出各个阶级在时代变化中的命运和结局,可将其政治化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也遮蔽了作品的丰富性。无论是吴荪甫、赵伯韬还是朱吟秋、冯云卿等,都在为了生存和利益而追求,而挣扎,而不是阶级本性限定的单一性格。同时,作品也未将革命者理想化,而是呈现出其人性自私的一面,比如革命者内部的分歧以及蔡真、玛金等之间的微妙关系等。作品一方面写出了各个阶级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这样一部作品之所以被从政治维度进行解读,甚至与作家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实际上,《子夜》的政治性解读除了与当时左翼的宣传有关,和茅盾基于政治立场的阐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茅盾后来对《子夜》的说明与阐释,赋予或强化了《子夜》鲜明的政治色彩,引导着读者与研究者去对《子夜》进行政治解读。”[1]抛开政治视角,更能发现作品蕴含的丰富思想意蕴。“易言之,后来的研究者受到作者的言说的影响,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来分析作品的思想主题,强调作品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控诉以赵伯韬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意蕴。”[1]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茅盾思想中的政治因素日益明显,当茅盾本人也被政治裹挟,其作品的政治性也就在绝大多数读者意识中形成定论。作为其代表性作品,《子夜》无疑是政治性与文学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
《蚀》三部曲是理想、现实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面对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无奈只能寄希望于革命,革命成为理想的寄托和逃避现实的归宿,现实则是基础。《子夜》艺术化地呈现出政治、现实与理想的复杂纠葛,阶级性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但也没有忽视他们的理想与所处的环境,即现实是他们的出发点。不难看出,《蚀》和《子夜》的基础都是现实,现实成为二者的基础。《子夜》之后,茅盾的作品更是紧跟政治形势,努力写出反映时代政治斗争的作品,以显示其政治身份。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茅盾并未回避社会现实,而是尊重现实,努力呈现社会现实。当现实与政治发生矛盾而政治又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茅盾更是陷入痛苦与彷徨,这既是时代发展中文学的命运,也是作家命运的隐喻。
三、政治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无论文学还是政治,其基础都是现实,也就是说现实是二者共同的出发点。政治只能基于现实而不能凭空想象。近代以来的革命正是基于劳苦大众的受苦受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或者说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是革命的基础。文学的来源也是现实的生活,对于主张自然主义的茅盾更是如此。茅盾认为:“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5]因此,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就要尊重现实,如实地呈现人情百态,而不是对其进行扭曲。就此来说,革命与文学是一致的,二者互为支持,相得益彰。《蚀》写了大革命时期青年男女的幻灭、动摇与追求,政治无疑是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其内容也与茅盾在大革命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有密切关系。作为革命者,政治性是茅盾创作的主动追求,“我的目的,一则想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做一番探讨;二则也有理清一番自己过去的文学艺术观点的意思,以便用‘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6]。可见,茅盾是将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来认识的,既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就要有自己的特征,无产阶级文艺突出斗争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无产阶级文艺毕竟是文艺,既然是文艺,就要尊重现实,从现实出发,呈现文艺本身的特征。这样,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解就有了分歧:政治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斗争性、阶级性,而茅盾更偏重于文艺性。既然偏重于文艺性,就要尊重文学规律,如实呈现社会生活。这也是与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观相一致的。于是,在《蚀》中,我们看到青年男女一方面坚持理想,苦苦奋斗,另一方面又在沉闷、残酷的现实面前无奈、幻灭、动摇和妥协,他们以人生理想的追求和遭遇现实的无奈形象地阐释着茅盾的无产阶级文艺观念与“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显示出与政治的分歧。
虽然政治和文学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但政治比现实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很多时候政治追求的是一种目的而略去中间诸多有争议的环节,即政治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文学则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浪漫化想象,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政治与文学的龃龉是对待现实的两种姿态:政治是以现实为出发点,也是为现实服务的,但略去了中间的诸多环节,要的是最终的结果,这种不要过程只要结果的追求,呈现出将现实理想化甚至概念化的特征;文学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生,在路上的苦难和人的生存状态始终是文学关心的命题,即对个体命运的关切使其显示出现实性。文学与政治一是现实,一是理想,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其选择就成为两难。可贵的是,茅盾“没有选择用作家一厢情愿的想象去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裂隙,而是用他那写实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面貌”[7]。可见,尽管茅盾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本质上还是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家,显示出对现实的尊重,当现实与理想乃至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尊重现实。
其实,对于茅盾来说,政治也好,文学也罢,都不过是人生的工具,是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而要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就要尊重现实。个体的成长和人生追求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选择和性格有关。静女士对理想的追求决定了必须和强连长相识才有人生的意义;章秋柳的逃避是因为沉闷的社会现实使其失去了追求的勇气;孙舞阳的革命追求和情爱选择源于其对自由的追求,但也离不开革命提供的条件。如此等等,都显示出现实对个体的决定作用。即使被公认为政治性代表作的《子夜》,也展示出现实的决定作用。作品中的每个人,从吴荪甫、雷参谋、周仲伟、冯云卿到下层工人,都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政治不过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他们的压力要么是金钱,要么是人生追求,面对现实的无奈是他们的普遍心态。对人物的如实刻画显示出作家对现实的尊重,在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中,文学显示出独立性。可见,尽管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但茅盾并没有将文学政治化,而是以对现实的尊重显示出与政治的某种疏离,从而使创作具有了现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作品的政治性。
四、传统知识分子情结
茅盾是典型的左翼作家。左翼作家实际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政治身份,即革命者,这个身份要求他们将政治作为主要目的,文学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是革命齿轮上的螺丝钉;另一个是作家身份,这个身份要求他们尊重现实,尊重文学规律,并在此前提下为政治服务。这倒不是说政治不能和文学很好地融合——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结合很好的作家大有人在,只不过,面对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当政治压倒一切的时候,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茅盾作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政治性是鲜明的,他本人也毫不避讳创作的功利性:“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信徒;但我真诚地自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那时并没想起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8]茅盾从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到在汉口编辑《国民日报》再到后来一系列的革命选择,都彰显着政治身份。但写作又是他的特长,或者说,他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因此,在创作中,自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其政治身份的内在要求。政治身份要求文学成为革命齿轮上的螺丝钉,作家身份又要求尊重现实,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中的创作,彰显出茅盾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文学不过是人生的补充形式,对他们来说,文学就是为现实服务的。也就是说,文学是功利的,是服务于社会现实的。茅盾的思想正是这种文学功利性的典型体现。早年组织参加文学研究会,参与提出“为人生”的主张,就是文学功用性的典型体现。但在提倡文学功用性的同时,茅盾也认识到文学的复杂性,特别是参照西方文学的发展更使其认识到现实的重要性,他也在此思想影响下提倡自然主义,体现出对现实的尊重。文学虽然有教育功能,但毕竟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其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况且,文学只能为人生服务而不能拯救人生,更不能救民于水火,所以,才有茅盾参加革命的举动。在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上,茅盾显然将革命作为根本目的,文学仍然充当了工具,其小说也就成为政治的附庸。实际上,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服务到左翼身份的为政治服务,即从人生到政治的嬗变,延续着茅盾的文学社会功能论,也就是文学是服务社会的工具——开始是新民和救亡图存的工具,后来成为政治的工具。之所以有这种转变,根本原因是茅盾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改变现实,只能通过政治。也因为这样,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对茅盾来说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选择,且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潜藏着沦为政治工具的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茅盾从古代文人那里吸取了经验。古代文人在追求个人政治抱负的同时也遵守着内在的约束,即既要“弘道”又要“内圣”,“弘道”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内圣”则是保持内心的操守,二者相辅相成,使知识分子在“入世”的同时坚守着节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持的‘道’的人间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9]“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在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9](14)在坚持“道”的人间性格即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秉持的是“内圣”,即对某种观念的坚守,而这种坚守的表现之一就是对现实的尊重和家国情怀,“弘道”和“内圣”即心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传统,是茅盾复杂心理形成的基础。“其主导是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人生观、历史观与社会功利观,重义轻利的道德伦理观;顽强奋进、韧性拼搏的进取精神与着重‘中和’,也着重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10]知识分子的身份内在地要求他积极入世、为民请命,同时又要求他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在很多时候,茅盾的知识分子身份即为民请命和政治身份即革命性是合一的,都要求他救民于水火,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其政治性生成的根本原因。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到为政治服务的政治诉求均源于此。但也有龃龉处,那就是知识分子身份要求他尊重现实,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而政治身份则更多地要求他为了革命事业删减多余的枝蔓而将政治目标作为最终的诉求,知识分子身份与政治身份也由此产生裂隙。实际上,也正是知识分子与政治身份的龃龉使茅盾的作品显示出矛盾性,也使其面临着诸多的争议。
需要说明的是,在小说的叙事思维等方面,茅盾也显示出传统的特征,[7]因为本文主要从内容方面进行论述,故不再论述。
五、结 语
总之,茅盾作品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显示出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两难选择,对二者的处理显示出茅盾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使其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以文学的功用性为社会服务;同时,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又使其尊重现实,以知识分子的情怀维护着作品的文学性,从而形成作品的内在矛盾,从而使其具有了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