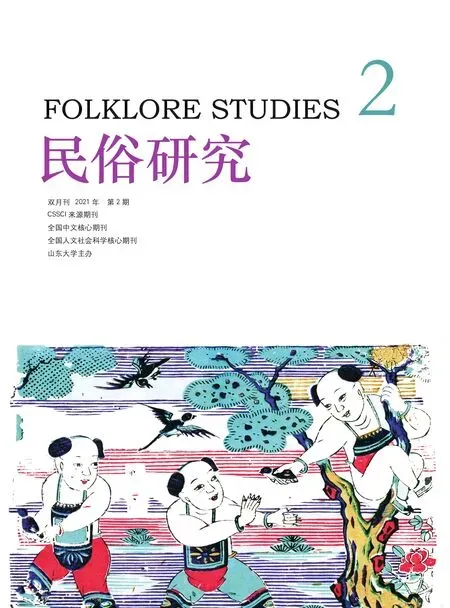驱瘟与添丁:海南移民商坊的共同体意识
——以海口府城行符信俗为例
王琛发 宋 丹
一、行符的含义及来源
“行符”,是海南老府城居住区或商业区年年例行的“迎神”活动。街坊大众以“本境”的名义共同奉祀“境主”神明,每年正月最重要的仪式是把境主请下神案,由壮丁抬着载着神像的轿子巡境,或请神像坐在由众人推拉的车子上巡游。神像在仪仗队的簇拥下,经过想象中境主管辖的各个地方,信徒认为这样的游神仪式可以清除各种妖邪鬼怪,保障本境范围内居民的安全。同时,境主作为本境集体的精神化身,在巡游时上门为境内各家各户祈福、驱邪,由此显示这些人家生活在同一个境主的辖区内。这类活动在海南地区称为“行符”,神符分布基本反映本境认同,社区边界多能以“符”为据。行符之前,家家户户准备好符箓,“行符”开始前由道士将各家各户的符箓带到境主庙里,在主持科仪前后分发给大众。神灵“行符”期间,人们把从庙里取回的神符摆放在家门口迎接境主的案桌上,让香炉压着符纸上端,令其正面图文垂在案子最前端,表示迎接神灵入门。如此,神符便代表着“境主”与诸天神灵对一家人的祝福。仪式过后,神符留在家中,贴在厅堂上,在新的一年中护佑一家大小。
现在有些相互传抄的网络文字表示:海南有行符风俗可从一部叫《千镇百镇桃花镇》的民间符书里面找到根据,又说此书卷三是所谓“太上感应秘法灵符”,文中记载说“行符”应始于汉孝文帝期间,那时共有神符七十二道,勒令奉行此符并传行天下,在香火前供养镇宅,回凶作吉,万祸书消,诸事吉庆。但是,《千镇百镇桃花镇》刊出的符章,多有近代文辞,其符式也不太可能出现在汉朝。实际上,上海广益书店自1921至1931间为应付市场需要,一再翻印清末民初民间书商编制印刷的《阴阳护救千镇压法真符经》《三元备用百镇符》《古贤桃花镇书周公秘法》,后来又以三书合刊,形成了《千镇百镇桃花镇》。对照宋朝《云笈七籖》和明朝《道藏》,该书记载的内容均没有收入,因此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
况且,从学术角度来看,现在府城各处坊里行符的榜文、行符科仪的道士多是由来自海南本岛的正一道传承,并且主持仪式多有延续宋代神霄法雷部诸法,无关《古贤桃花镇书周公秘法》所谓周公与桃花女斗法留下符咒的传闻。其行符的原则,也正如海南府城现存宋徽宗《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首句所说的“道者,体之可以即至神,用之可以挈天地”,牵涉道教传承中华文化思维的天人相通观念,不能被解释为随意或约定俗成的交感巫术行为,以为有几十种符纸就可供应大众不同的要求。更何况,汉文帝的时候,道教尚未有完整教团,造纸术也还未发明普及,总之,网络上以《千镇百镇桃花镇》一书论行符,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
追溯宋元之际成书的道教典籍,两朝各种道书本涉及符箓,多有以“行道”联系着“佩符”或“用符”的关系,其中直接以“行符”两个字结为一个道法专门用词的,包括署名天真皇人编撰的《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该书卷三六有一段说辞:“夫大法旨要有三局,一则行咒,二则行符,三则行法。咒者上天之密语也,群真万灵随咒呼召,随气下降。符者,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随符摄召下降。法者,主其司局仙曹,自有群真百灵,各效其职,必假符咒,呼之而来,遣之而去,是曰三局。”(1)天真皇人:《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第807页。由海口府城现在传承的行符方式,可以做个古今参照,海口府城行符都由道士主持,须由道士以传承的道职上表奏告天庭,以步罡踏斗象征相遇天上诸位神仙,摄诏诸位神仙以精气作用符纸之上;这确实是根据“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随符摄召下降”的说法,设想以仪式完成目标,使符纸有效。而境主参访,又是拜会各家“子孙”,并为各家准备要张贴在家中的符箓加持。
“行符”在海口府城具有悠久历史,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从何而起。不过,根据府县志的记载,到了明代,海口府城的行符活动显然不止是由坊里邀请道士为大众祈祷,而是大众因此也形成各种由家庭而集体的活动,形成地方集体民俗活动传统。而且大众祈求消灾解难,又有着具体的指向。据明朝《正德琼台志》节序记载:“……六日后,各坊或用道士设醮,嬛嫚调神。村落则加抬神像,沿门贴符以禳,名曰遣瘟。间有酬愿立天灯,缚竹木高二三丈,然灯于笼,悬挂彻夜,月尽方倒。”(2)唐胄纂:《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乾隆琼州府志》记载:“六日后坊间村落行傩礼,设醮抬神,悬符逐疫,立天灯,作秋千,每夜张,或为鳌山诸灯……。”(3)萧应植修,陈景埙纂:《乾隆琼州府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由此可见,若按照道经,“行符”在宋元间,作为道教信俗的专门名词,可以是指称道士由制作符箓到发放符箓的过程,也就是保证符箓有效的整个道术操作过程。但来到民间,《正德琼台志》所谓“村落则加抬神像,沿门贴符以禳,名曰遣瘟”,“行符”牵涉家家户户,须神像巡游到家,各家的回应是“沿门贴符以禳”;各地区礼请道士“行符”,满足家家户户的需求,已化为整个社会新春遣瘟的必要步骤。符纸要在迎神的同时出现,最终贴在门前,才算完成“行符”程序,“行符”两字也由原来巡游活动的重要组成兼最终目标,转变为泛指整个巡游情景。
自北宋开宝五年(972)设琼州府治,建城墙,琼山地区长期成为海南衔接中原与交流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移居府城的先民虽然源自不同地方,却是居住在同片土地上,依靠着府城的城墙内外环境生活,逐渐交融成为声气相通、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自古以来,府城一旦爆发传染性疾病,大众便受困于四面环海的岛上,难有外援,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府城人也有很多遭遇瘟疫围城的历史记忆。《海南省志(卫生志)》总结1840年以后的海口疫病情况:光绪七年(1881)霍乱病人进入海口引起霍乱流行;光绪八年(1882)海口,郡城霍乱瘟疫盛行,染病数以千计。(4)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编:《海南省志(卫生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实际上,每年农历正月期间正值冬春交替,气温变化较大,容易影响身体,也容易因天气湿热滋生细菌。此外,海南作为商业社会,频繁的人口流动加剧了新的细菌和疾病进入当地的可能性。因此行符强调驱瘟祈福,处处斋醮、处处烧香祈神,目的在于预防和驱除瘟疫。《素问·移精变气论》引黄帝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5)王维主编:《黄帝内经》,线装书局,2005年,第40页。虽然后来学界对“祝由”的意义有许多分歧,可是即使如唐代王冰解释成“祝说病由”,也是说明古人想象着人间与鬼神沟通,可以由说出病情来源使造病源头退却,如此便有利于以身心调养去防止和减缓病情恶化。为此,人们诉诸鬼神而动员一切预防措施,兼及以鬼神之名做精神建设。这在医药与公共卫生尚未进步时代,也算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位于府城大园社区甘蔗园张天君庙中的乾隆“避瘟”石碑佐证了这点:“闻之时逢端月,进屠苏以避瘟,节届元宵上浆酒以延寿,故古乡傩之典必建于春初,传之至今,皆为乡国闾里所不可或无者也。奈余本境比里寥落,资用维艰,敬邀同心捐资生息,聊为斋醮之需,俾云路享清宁之庆,爰是碑铭录垂不朽。是为序。今将各位姓名捐资银两开列于后……乾隆己未年蒲月十五日。”(6)《避瘟碑》,乾隆四年(1739)立,碑存府城大园社区甘蔗园张天君庙内。
由此可见,行符的主要目的在于“驱瘟祈福”,保佑一家男女老幼安宁、生儿育女无灾无难,让各家各户一代接一代安安心心成家立业,通过传宗接代、慎终追远,延续前人来过活过的存在意义。
府城各街区行符时间是坊间各庙宇按照规定日子举行的,各境行符的时间交错开来,一般是从正月初七至三十。有一种说法认为府城各境行符,基本是按照由东向西顺序进行,传说府城的西边(今金盘坡)、北边(今老机场)是孤魂野鬼的安身地,他们时不时地会入城骚扰百姓。府城隍爷是负责看守城池的保护神,他指令辖区内的境主神正月里要把孤魂野鬼统统赶出城外。于是,境主神各司其职,从城东开始,分段驱赶,直到西部的大路街林公庙的林大天君(正月二十四),北部的北门官市华光庙的华光大帝(正月二十七)将其赶出城外,全城“行符”结束,从此全城一年内百姓出入平安,乐业安居。(7)黄培平:《府城春秋》,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但是,若根据道教与民间信仰神谱,府城隍和县城隍虽然管制当地冥阳两界众生,可是职位低于许多境主在朝廷祀典中的位置,命令不了境主神。而且,按照《正德琼台志》,祭祀孤魂野鬼是国家祀典,国家对一切成为无主孤魂的先民的收纳与祭祀做了合乎礼制的安排:“郡厉坛在城东北一里。洪武三年,知府宋希颜创建,坛墠、廊垣俱备。祭迎城隍为主,其祭物羊三、豕三,祭期每岁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俱按洪武礼制。州县同。”(8)唐胄纂:《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32页。根据这段记载,朝廷已经赋予城隍管理厉坛的职责,令府县安顿亡魂,使冤死者得以申冤、该轮回者得以轮回,不是将其驱赶到他处。同一本地方志中,会有各处发生的行符活动的记载,显然是官方关注也允许民间这样做,其目的在“遣瘟”或“逐疫”,而不是为了驱赶孤魂野鬼。假设不是这样,而是民间有自己一套观念,把行符的目的定位于驱赶孤魂野鬼,要死魂一路由东向西轮流进入各坊区,又要被各坊区境主轮流驱赶,流落至城外另外的方向,这显然违反了朝廷的本意。而且放任孤魂野鬼脱离体制和管辖的地方,游荡四邻,反而会引发各境争端。所以,行符显然是为了“遣瘟逐疫”,而不是为了驱逐孤魂野鬼。
据笔者走访,位于府城东城门旧址附近的东门里关帝庙行符日期为正月十二,再往西北面,位于红城湖路上的玉皇三清宫行符日期为正月初九,其旁陈公庙行符日期为正月二十;位于达士巷的马皇康皇庙及附近马鞍街上的康皇庙行符日期为正月十七,而再往西南,位于甘蔗园的张天君庙的行符时间为正月十四,依据时间与地理位置的冲突,可见府城由东向西“行符”驱逐各地鬼魂的说法略有偏颇。
可是,从“驱瘟”的角度来说,府城驱瘟“行符”活动是由东向西的说法也不一定全无来由,可能源于明代城池扩张与城市扩大的记忆。也就是说,府城“行符”原本真有一段由东向西发展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碎片式的记忆就可能混合在一起。明代,洪武十年(1377),海南卫指挥桑昭在城西门外增设土城380丈,作为子城,在子城开西、南、北三门,并在各门之上建筑敌楼。至嘉靖乙丑年(1565),参议曹天佑、琼山知县曾仕隆重建子城,子城周长有所增加。(9)梁统兴:《琼史百问》,南方出版社,2016年,第264页。驱瘟,原本就是要把瘟鬼驱逐出城外,不让其入城作祟。当城市的内城范围向西扩张,城内新开发区域的坊里日益增多、居民日益增加时,就连城西门外也可能因此人烟渐渐增多。这时府城的驱瘟行符,当然是往西边发展,只是城内与邻近各地坊村驱瘟的日期却不一定是相约好的,不一定越往西越迟。
况且,行符有“走公”的说法,意即本处坊里或村社公认庙中神明为本境的“境主”,同时也将其视为“公祖”,所以当天抬着神像在本境范围内巡行一周,驱逐作怪瘟鬼,保佑子孙平安。而“走公”的禁忌就是不打招呼走入邻坊或邻村的“境内”,这意味着宣示自己不承认他人境界主权,或者是故意把瘟病“遣”入他人境内。在旧社会,“走公”活动常会因此发生械斗。(10)冯仁鸿:《海口人的春节习俗》,王贵章:《海南乡风民俗》,南海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由此可见,大众依靠境主遣瘟,是直接把瘟鬼送到另一世界,不可能各自把瘟鬼一路向西推送,更不可能最后都由最西边的坊村负责解决。
二、行符的具体流程
行符一般分为两天,“行符”的前一天,各家敞开大门,摆上香案,等待庙里使者来放灯和贴符纸。庙里的义工会向坊间各家各户发送“灯鸟”,“灯鸟”必须在傍晚时分放在大门口、堂屋、五方土神、各房门口的两旁,然后由庙里的义工举着火把到各家各户点燃,或由各户人家到庙里接火点燃。“灯鸟”与“丁鸟”谐音,有添丁添福,多子多福,人丁旺盛的寓意。在行符的前夜,各家会在门前亮灯,或放灯笼;而去年添丁的家庭,则要制作或购买土灯到庙中燃点,让“境主”知悉,行符时会额外保护新生子孙。(11)冯仁鸿:《海口人的春节习俗》,王贵章:《海南乡风民俗》,南海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据说,旧时行符,也有在晚上迎接公祖,第二天早上等行符过后,才会点起“灯鸟”;那时候制造“灯鸟”,传统方法是用旧瓦片磨成铜钱大的小块,用胭脂纸包着,并扭成一条小绳子,在绳子上醮了桐油以供点燃;人们将“灯鸟”带回家中,在每个房门口两边安放两个,以求当年家中“添丁”。(12)杨武:《海南省民俗概览》,南方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据调查(13)“琼台复兴计划”课题组成员王琛发、宋丹、李金操于2018年6月至7月在海口府城的调查。,海口府城各个街区“行符”的神符,都得由坊间父老礼请道长画就,并盖上该道长的“官印”,方才符合传统。分发的“符”有大小之分,使用方法也有所不同,大符一般于行符当天放置在案桌上。而现在所谓的“小符”,没有在上面运用任何神明的名字和敕令任何事项,因此其实不算是符,而是根据各家各户参与行符应该分摊的份额,是分发给各家各户的票据;票据内容分为“醮首”和“斋戒”两种,两者均代表男丁,前者表示成年男丁,后者则表示未成年男丁。
古时候,人们通过各家门口所贴的“醮首”和“斋戒”的张数,可以得知该家人是否有能力参与本境的活动,也可以由此计算各家各户男丁的数量,有利于日常或是战争期间对某一区域男丁人数的统计和把握。然而,现在的居民因为“蘸首”和“斋戒”上有吉祥语,就将其当做保护符,贴在门外墙上,作为驱邪赶晦、保佑家庭平安的工具。有些人不明白其原有的含义,在庙里多讨多要,在门外贴得满满当当。因此,现在在府城境内经常会看到一户人家家门口的墙上贴了十几张的“蘸首”和“斋戒”,这并不代表其家中有很多男丁一起居住在里面。另外,不同境内张贴的“小符”样式也有所区别,这与不同道坛供应的票据样式有关。
行符的当天上午,道长在庙里设坛做斋,然后“卜杯”,问神像(俗称“公祖”或“婆祖”)出巡时辰,确定好时辰后就抬神像出游。按照过去的规则,行符出巡队伍其实也要讲排场。行符时刻,出游由四个人排头开路,由两人扛着一口大锣走在前面,边走边敲,另外两人各扛着“肃静”和“回避”的大牌跟在后面,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鸣锣开道”。其次,后面跟着一批“勇”。“勇”的概念,源自旧时坊间的乡勇制度,发生事态时由他们配合正式的兵将,保护百姓安全。过去,这些日常习武者配合“行符”,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十八般武器上街游行,被称为“以壮行色”。再次是幡旗方阵,古时的兵营是以旗为单位的,幡旗越多,越显兵强势大、纪律森严,此阵称“朱雀玄武、威行令肃”。旗阵的后面是海南八音,“仪仗乐队、两部鼓吹”。接着是“公祖”或“婆祖”出巡銮轿,这是整个出巡队伍的亮点,只见“华盖遮天”,坊间父老前呼后拥,甚是热闹。后阵是表演队,扮演诸如“八仙过海”“送子观音”“红叶题诗”“搜书院”等戏剧中的人物。仪仗队伍最后,压阵的是舞狮队。(14)草文ABC:《海口的“行符”》,《南国都市报》2014年5月4日。
现在,坊里行符的队伍规模都大大简化了,往往是锣鼓带头,或只有一面铜锣,有的外加一只或一双舞狮子,唯有神像出入家门的规则不变。
当神像来到户主家时,先由户主代表全家三跪九叩并虔心祝祷,之后则由家中其他人根据家中男女辈分祭拜“公祖”或“婆祖”,待该户全体成员祭拜并祝祷完毕后,户主会带领着全家根据辈分排队,依次在后生抬着的“公祖”或“婆祖”轿銮底下钻,绕行三圈,由此证明自己是子孙辈,而且得到了“公祖”或“婆祖”的赐福。为了表示人的尽心与神的尽兴,行符每到一家,一般家庭都准备红包,让开道的舞狮子来段采青,再烧鞭炮,过后队伍去往邻家,继续相同的活动。行符的当晚,各家各户必备丰盛晚餐,招待应邀前来的亲戚朋友,甚至是路过的客人,坊间称为“吃行符”。宴后,各家各户及前来的亲戚朋友互相招呼结伴前往庙前临时搭建的戏台看“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符与公期是两个不同的活动,虽然坊间也有“吃公期”之说,并且在正月的公期当天可能也会举行行符活动,比如府城鼓楼的三圣宫,其境主三圣娘娘的公期和行符均为正月十二。但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第一,时间点不同。公期是以神明或先祖的诞期为时间点,可能分布在一年之中不同的月份;而行符只在正月举行。第二,中心点不同。公期是以庙宇为中心展开活动,不常有出巡,不绕境访户;而行符则是以社区为中心,境主要出巡绕境。
此外,府城部分社区的行符伴随着公庙里首事的换届,比如位于西面的金花村林公庙,据笔者访谈得知,该庙有十二位首事,在行符头一晚(正月二十一),庙中的首事们会请道士来做法会,首事们还会准备十二根挂着马灯的小竹子,分别放置于村头、村尾、村中的主要路口处,或者是水井和土地庙旁。待完成后,首事们回到庙中点烛燃香,并燃放一串鞭炮,等道士做完法事,第二天就可以行符了。行符结束后,当晚首事们会将十二支竹灯收回并送到新一届首事家中,新首事会将竹竿放置于院中,并把马灯置于祖屋的供桌上,点燃三天,同时每位首事会收到庙里给的两碗糯米饭,也同马灯一起放在祖屋的供桌之上。
在当地能够成为公庙的首事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说明某人在社群之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认可度。首事采用轮流制和自愿报名的方式,一旦被任命为首事,要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负责公庙的大小事宜,为整个社区日常的信俗活动服务,而首事的家人通常也会参与其中。可见,行符是一项服务于各家各户的家庭型活动,每家每户均有义务通过轮值来服务大众。在此过程中,大众对首事们起到监督作用并以此判断其品行,从家庭走向集体,又从集体回归家庭。
三、行符作为驱瘟信俗
正如上述《正德琼台志》提到的“村落则加抬神像,沿门贴符以禳,名曰遣瘟”,历史上,海口府城各个街区的“行符”在大处都相当一致,就是抬着村庙或者街庙中的神明,在所属的地界巡行,由家家户户迎神,然后各家各户都在门前贴符。而“行符”后,抬神轿的人,要抬着神像奔跑,大众在后头追赶急跑和放鞭炮,俗称“走公”,又名曰“遣瘟”。根据《正德琼台志》的记载,当然可将其历史追溯至明代,至少在明正德以前就盛行了。
根据一些记载,解放前各地方行符“遣瘟”的隆重程度,取决于其活动内容。这些内容看似综合了许多迷信成分,但若深究其仪式行为背后的动机,则都是为了能在地方上确保公共卫生,以对付瘟疫。《海南省民俗概览》记载民国时期海口行符信俗,提及一些过去的做法:行符第二天的中午时分,由“首家”雇佣两人抬着一双用纸竹扎制成的纸船,敲锣打鼓收集各家打扫好的垃圾,抬到郊外掩埋,以示清净村场环境;再到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村里组织少年村民抬着村坊大小“公祖”或“婆祖”神像,从村头抬至村尾,挨家挨户供村民祭拜,让小孩从“公祖”或“婆祖”轿下穿过,以求平安;等到抬至树尾供全村人拜祭完毕,要“送神”归天,抬神的人要把神的背部转为前进方向,跑步将神抬回公庙,而居民也会跟在后头边追赶边放鞭炮,一路追到庙内便燃放全部准备好的鞭炮。(15)杨武:《海南省民俗概览》,南方出版社,2017年,第15页。按照这段记载,行符当天有两个关键性的集体活动,即收拾垃圾和放鞭炮,现在的人都明白这些是对付细菌与病毒感染的有效方法。
府城先民将驱瘟与添丁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也是可以理解的。古代不管手工业、商业、农业都主要是人力劳动,都是依靠着人多好办事。所以当地在举行行符活动时,家家户户要在行符前夜挂起灯笼,凡是去年生过男丁的家庭都会制作或购买土灯到境主庙去点燃,祈求神明知悉那家人多添了男丁,行符时要加以保护。(16)冯仁鸿:《海口人的春节习俗》,王贵章:《海南乡风民俗》,南海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如今,府城各坊里和邻近各镇依旧盛行这样的传统,并且各有特色。比如,在府城各坊里之间,某些坊里街区如宗伯里,行符的日期与正月十五上元道场一致。在宗伯里,其2018年上元道场,道士写榜文贴在庙前墙上,称当天为“以今上元行符之际”,因此以祭祀本境境主与诸神为名,将上元科仪结合邻近街众“领符奉镇”的需要,邀请天上、地下、水中的天神地祇显圣坛前,目的在于“崇烈哲诸神,俾门门犬无夜吠之警,牛羊有朝鸣之乐,老少男女悉荣华美满”。道场内坛除陈设天界诸神、道派祖师、府县城隍、本村土地等神明的牌位外,祈请诸神临坛保佑,另外还得具书各路掌瘟治瘟神灵,全套科仪迎送“诸神诸圣至显,春夏秋冬四季瘟神,十二年王十二月将,天府治世五皇大帝,无上洞渊三昧真君,和瘟教主匡阜真人,五瘟圣者六洞魔王,当年行令越王之精,瘟司会中无边圣众”。
四、行符与“街坊共同体”
海南曾经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在历史上发生过持续不断的移民潮,为海南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及生产力,也带来了不同原籍的生活习惯、方言、宗教信仰等。但这些不同原乡的居民毕竟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同源不同流,通过街坊日常生活发生着最基层的互动;因此,街坊之间长期互助,意识到生活上需要相互依靠,久之把凝聚地方历史记忆的公庙神视为“祖先”或“境主”,从而建构出“本境”意识,发展出集体的地方信俗,年年通过行符等活动表达共同的地方文化。
各地移民中以闽、粤、桂籍为主,通过府城当地不同神明及灵物崇拜,亦可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点。位于府城老城区西面的四座“林公庙”有着明显的雷神信仰的特征,四间庙各自都会以林公为本坊“境主”,各自年年举办本境行符活动,而日常生活中又以跨境的“兄弟庙”相认,以拉近坊村间的情谊。如此便形成以各自“行符”认知本境之存在与邻里之结盟的观念。据《民国琼山县志》“建置志”记载,“林公庙,一在西门外大路街,一在下田金花村,一在下田朱橘里,一在子城西南云路坊,而在大路街者则元时所建,神即本坊人,林姓,为雷化,故其庙号雷庙,祈祷多应。给事中许子伟议毁之,以神入梦,乃止”(17)朱为潮、徐淦主修,李熙、王国宪总簒:《民国琼山县志》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由此而言,不同籍贯的人群落籍府城,膜拜有功于民的本坊先人,在其死后奉为“境主”,并视为共同的“祖先”,就是彼此建立“本境”意识的过程。
此外,在府城老城区中部与西部各处街头巷口,随处可见憨态可掬、造型各异的石狗。石狗信仰多谓源于粤西雷州半岛,一般多安置于祠庙、村路、巷头、门口、河岸和墓地等处,具有镇邪驱鬼、庇护平安的意义。而府城的内部,历史上城内经济繁华的坊里地区,处处可见石狗,主要都是伴随着“本境”坊里街区的土地祠而存在的。这些土地祠与石狗,在人们为境主庙举办行符时,也是信众准备茶果糕点兼行祭祀的本境神道。
汉族把街头巷尾的土地公视为观念中最基层也最接近生活的神祇,以自身文化去认识与祭祀土地,包括配祀在土地庙周围的石狗。这说明个人会意识到自身的文化生命与本地资源交融于生活。就府城当地而言,石狗信俗跨越琼州海峡,以符合汉族信仰文化的内涵流播于以汉族为主体的本郡政治与经济中枢地区,足以反映出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又如绣衣坊的晏公庙,古时原由府城的儒学名宦邱濬主导,将本庙建于下田村,香火鼎盛;后于民国初年移建于子城小北门(今绣衣坊)内,现在还成了忠介社区的“老人之家”,用作退休老人的娱乐场所。晏公本是江西的地方性水神,具有平定风浪、保驾护航的基本职能。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晏公庙,在城北大路一里西厢。其神主掌江海,元以其阴翊海运,封平浪侯。今江湖海多奉之,洪武甲戌间,寓士劝化成造,后指挥石坚添修两庑。永乐乙酉,指挥牛铭请命永嘉杨岱宗募缘重建。又今永宁桥西巷,亦有晏公庙。”(18)唐胄纂:《正德琼台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38—539页。清代末年开始编撰的《民国琼山县志》则记载:“晏公庙,在小北门内,元封神为平浪侯,乡人至今所祷。(《旧志》)。谨按:神姓晏名成儒,江西清江镇人,浓眉蛇髯,面若黑漆,生平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知否?”又说:“元初以人材应选为文锦局堂长,谢病归,登舟即逝,时灵显于江河湖海,舟行遇风,叩之即浪平风息。明洪武初,有司以其事闻,诏封为显应平浪侯。江淮间香火甚盛,丘文庄屡祷有应,建庙于下田村祀之。国初建于子城小北门内。”(19)朱为潮、徐淦主修,李熙、王国宪总簒:《民国琼山县志》第一册,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府城的境主均具有本地神的特点,虽然移民们来自中原的不同地方,神明或先贤本身不是海南人,但其后代在此繁衍生息,其生活方式及文化信仰等与当地特色进行了有机融合,于是江西水神也就在下田村转变为当地境主,成了当地的保护神,以后又随着与其原庙有因缘的信仰群体的崇拜,成为新地区的境主。
笔者在晏公庙调研时,对该庙具有一定了解的吴清秀老先生验证了这一点,他说:“晏公庙的行符时间是正月十八,其巡境范围包括绣衣坊及绣衣坊后街,晏公原先是从江西传过来的,这批移民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江西的,过来的人都是讲江西话的,来海南时间久了才变成懂海南话的。”(20)访谈对象:吴清秀;访谈人:王琛发、宋丹、李金操等人;访谈时间:2018年7月18日下午;访谈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绣衣坊晏公庙内。若对照上述《正德琼台志》的记载,其中有所谓“寓士”“指挥”等人称,可见此庙自明朝初年建成,最初称为“寓士”的那批建庙信众,可能是从江西一带移民到府城的军士。
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行符不同,海南府城作为商业移民社会,其行符不是发生于同姓宗族当中,也不是多姓宗族的联合,而是源于不同姓氏家庭组成的地方工商业社群,彼此相互合作而进行共同的活动。不论是行符还是公期,其内在的机理是采用一种“模拟血缘”的形式来巩固其内在的社会关系,每一位民众都认为自己是境主的子孙,大众将境主敬奉为集体祖先神,以此不断强调自身与境主之间“子孙与祖先”的地位和关系,具体表现在府城各庙宇中的石碑或做道场放榜红纸上有“本坊境主”“本坊子孙”“保佑子孙”等字样。这样的传统至本世纪,依然可见。例如,草牙巷(古称永兴坊)三圣宫内《万古流芳碑》中提到“本庙初建于光绪十三年,于一九九三年再发……使三圣娘娘立庙祀之,然后佑吾坊子孙丁兴财旺……永兴坊群众乐捐。”又如府城云路坊林公庙外墙上的添丁酒的红纸上写有“本坊:内巷子孙XX喜添男丁……林大天君、张大天君、火雷娘娘、冼太夫人……神欢人乐”字样。
通过行符,境内的民众一方面确认境主所辖范围,即是本境,亦为吾等作为本境“子孙”之领土。这有利于消减初来乍到时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另一方面,境主作为本坊的集体保护神,当地的土地神和石狗等小神明都听命于他,共同保护本坊的安宁与稳定,由此交织出增进大众安全感、熟悉感的地区神道信俗系统。人们通过这种“模拟血缘”的方式来增强境内民众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对这个“内社会”形成认同和共同体意识,从而增强其内在的竞争力及其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建设和维护“街坊共同体”。
另外,行符与街坊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的,随着民众所在地理位置的变化,境主所辖“境”的范围也随之改变。以现在红城湖路旁的陈公庙为例,该庙为北街村的公庙,陈公为该庙的境主,每年的正月二十举行行符活动。据首事吕先生说,北街村原所辖范围在第三人民医院至忠介派出所一带,位于红城湖路北面,由于后来城市规划等原因,北街村于1959年之后迁至红城湖路南面,现所辖范围原为北胜街与北官村的地界,他们把陈公庙也一起移了过来,仍称自己为陈公的子孙。由此可以看出该村内部民众之间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从地理意义上看,虽然整个村都搬迁了,但民众们依旧保持原有的文化记忆,在来到新地点后,他们重建起整个北街村的概念,并且境主是与民众同在的,仍为该村的地方保护神。
而各境主的庙宇与归属的群众,在“本境”以外的外部社会联系,则通过“联盟”的方式进行联结。以府城鼓楼、草牙巷和宗伯里的三圣宫为例,坊间传闻其境主均为“三圣娘娘”,彼此互为姐妹关系,鼓楼三圣宫境主为大姐火雷娘娘,草牙巷为二姐子孙娘娘,宗伯里为三姐泰和娘娘。(21)黄培平:《府城春秋》,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三者每年行符的时间相互交错,各有不同,大姐的行符与公期均为正月十二,二姐行符日期为正月十五,而三姐是正月十六。每当二姐或三姐行符之日,她们的随行队伍都要去大姐和另一个姐妹家“相互拜年”,然后再回到本境巡境,为子孙们驱瘟祈福,保佑一方平安。另一个例子是林公庙的四兄弟,上文提到府城有四个林公庙,现分别位于金花村、大路街、云路里(后巷)和朱橘里。(22)朱橘里林公庙现位于红城湖路旁家乐福超市附近,原位于下田村朱橘里,与金花村邻近。虽有易位,但当地人仍使用旧称。据访谈得知,相传以前人们用一块木头刻了四个林公像并认为其为四兄弟,金花村的林公是大哥,朱橘里林公排名第二,大路街林公是老三,云路里(后巷)为老四,四位林公的公期均为农历六月初四,但其行符的日期有所不同。其中,老四云路里(后巷)行符的时间最早,为农历正月十六;朱橘里林公行符为正月二十一,金花村是正月二十二,大路街林公庙行符时间最晚,为正月二十四。每逢大路街林公行符当天早上,行符的队伍会先到金花村林公庙里拜神,意为给大哥“拜年”,而后则在金花村村口火雷庙进行舞狮等活动,完毕之后再去其他兄弟庙中拜年,待结束后就出发去游街巡境。在这种本境与他境的联盟中,各自的境主可能是同一神明,但各庙的历史不同,而大众也就根据坊里或公庙的历史年代或其他因素,为它们结成拟血缘的公庙关系,互相称兄道弟。
此外,府城当地还有“神明之间相互结拜”的说法,高登街火雷庙首事王先生曾提到,坊间有人认为火雷娘娘和三圣宫娘娘是结拜姐妹,虽然这种说法来源已经失考日久,各处有时也会出现自认为是结拜中的老大的现象,甚至还会存在一些叙事上的偏颇,但从侧面也可反映出境主间的“联盟”以及各街坊间的凝聚与团结。各境往往有现实中的相互关系,大众宣称神明之间的结拜,有助于当地民众形成更为庞大的街坊共同体,作为境主的子孙,各庙间的境主已成为结拜关系,各街坊间也应保持友好关系,相互协作。可以看出,“联盟”的实质,是将传统宗族村落祖先联宗的关系在城市商业社会中复制并表现出来。
这种境主“联盟”的模式,其实足以反映出各境或各街坊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相较本境内“集体祖先与子孙关系”构成的内社会,当地用“兄弟庙”“姐妹庙”“神明结拜”等传说和概念构建出以神圣为主题的相互历史,再以此构建出人的历史,并加强彼此间的人际交往与团结,从而实现对“外社会”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共生共存,相互协作与保护,共同抵制外界的风险与瘟疫。
五、行符的现实意义
行符作为海口府城的一项重要民间信俗活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现实意义。
首先从行符的活动形式上看,其整个活动流程及祭祀仪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对闽粤各地本有的本境游神文化的延续与变通,反映出府城当地的特色。并且,它是结合着海南其他宝贵的文化遗产,相依相存,包括斋戏、海南八音、舞狮和飘色等,行符为这些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保护。
其次,行符的社会性体现出海口府城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商业社会,各坊里居民是如何在地构建出“街坊共同体”的,通过集体祖先神崇拜及拟血缘的形式实现本坊或本境中“内社会”的联结与凝聚,再将各街坊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投射到神明身上,通过创建共同神话认可相互关系具有神圣性质,将各街坊内境主结为联盟,提出“兄弟姐妹庙”“神明结拜”等概念,以此加强人际间的交往与团结,构建彼此间的历史与文化共识,相互协作,互生互存,增强其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能力以及其内在的竞争力。
随着医疗技术和水平的不断提升,当前的行符活动已不再用于驱瘟,但行符具有的文化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反映了府城极具特色的民间信俗,“吃行符”、舞狮和斋戏等一系列活动,也带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产品的消费,促进了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行符有利于增强民众的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各街坊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与巩固。通过行符,我们可以窥见古代海南社会真实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运作的机理,在历经多年之后,它仍然焕发生机,依旧是府城居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基于对海口府城祠堂、庙宇的考察
——府城鼓楼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