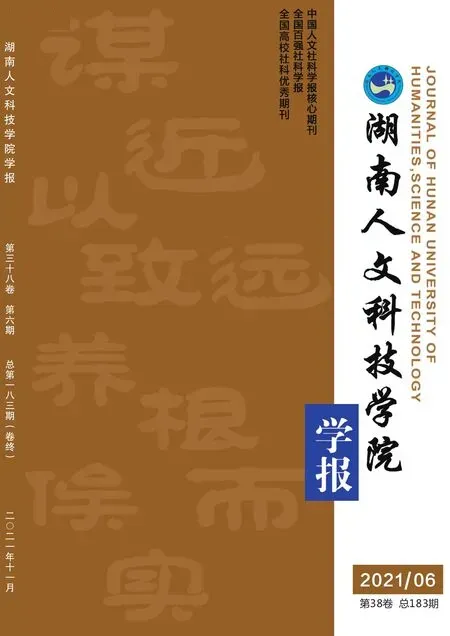意识中的故事
——论《队列之末》的内心对话
万正发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娄底417000;2.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四部曲小说《队列之末》包括《有的人不》(1924)、《再无队列》(1925)、《挺身而立》(1926)和《最后一岗》(1928)。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前后,表现了爱德华时代文化的崩溃和新时代价值观的痛苦呈现。小说主人公克里斯托弗·提金斯本是一位天真、睿智、保守的贵族子弟,历经不幸的婚姻、父母的离世、谣言的攻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最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冲破世俗的束缚,和女主人公瓦伦汀隐居田园。
福特被认为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似乎他的小说是被用来研究的,而不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该小说于2012年被BBC拍成5集电视剧,但是在国内仍然没有受到观众的青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情节上看,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三角恋故事:一个英国绅士在火车上被一个富家女勾引,被迫与之成婚,婚后遭遇妻子的背叛、社会的排斥与不公等种种的不如意。经过战争的洗礼,他认识到生命可贵、爱情价高,于是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也情投意合的女孩在一起。这样的情节自然不够吸引人,但这不妨碍这部小说成为伟大的著作。小说长达八百多页,却并没有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因为小说重点要表达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的意识和思想。在这种以主人公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小说里,情节不再要求是具有悬念的,而是基于人物主观性的内在发展及其对意义的追求[1]。小说叙事的重点是人物意识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叙述的外部事件的主观反应。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并不是一个意识在独白,而是众多意识在进行对话。巴赫金认为,如果过去的小说是一种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即复调小说[2]2。对复调小说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2]82。复调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述中,它有更普遍的意义。在《队列之末》中,也可以看到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发现。福特将主人公的现实,以及外界和周围的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从作者的视角转移到了主人公的视角。
一、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对于复调小说的作者来说,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另一个货真价实的“我”,主人公是作者与之对话的对象[2]103。小说中的主人公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自己的意向性,并使用自己的个人语言。这样,主人公在小说中获得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成为了“他者”,一种根据其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语言生活在叙事中的自主意识。主人公可以体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并代表他们对世界的个人观点。复调小说非常重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虽然对于作者来说,主人公的意识是他人意识,但具有特殊的独立性,这就是复调小说的意识存在方式与独白型小说的意识存在方式最大的不同。在独白型小说中,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尽管表面上形式多样,实际上都是作者意识的不同表现而已,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3]105。复调小说并不重视描写客观的世界,而是注重世界在主人公的意识中呈现的方式。具体地说,一切作者和叙述者对主人公的评价,主人公的自我评价,以及主人公周围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被纳入到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之中。概述之,整个世界都通过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来[2]85。
福特在《队列之末》的叙述中退后一步,为小说的人物赋予独立的声音和空间,通过人物的意识,过滤叙述中的每个事件。无论是从小说人物的视角叙述,还是跟随人物的意识流,他都以第三人称写作。即使福特仍然希望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他都会使用第三人称总结人物的思想,而不是直接将它们呈现给我们。作者运用自由间接言语和内聚焦叙事来描绘人类意识的深度,并通过其主观视角和现实感来表现一切。通过这些方式,他能够向我们展示人物感知到的事件,也就是意识中的故事。
在复调小说中,意识或思想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而是未完成的,变化的,或者说它是一个伴随着生命活动的过程。每个观点都在和与之对立的观点进行无止境的对话[3]112。《队列之末》充分发挥了对主人公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些解释和评价完全是主观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中没有最终的真实,因为从其他人物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气和思想都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意图和重要性。可见,小说中主人公的意识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例如,小说中提金斯孩子的父亲身份、提金斯父亲的自杀以及母亲的死因从未得到作者的确认,而仅由其他主人公的多重意识进行了广泛讨论。读者无法获悉这些问题的绝对或确定的答案,答案只存在于每个人物与自己进行的无止境的持续内心对话中。无论是提金斯还是他的哥哥马克,都试图在他们各自的自我意识中对其他人物的行为进行多次的推理和讨论,以期实现最终的真实。但是,他们唯一能实现的是主观的和个人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只是他们所认为的真实,是他们意识中的真实故事,代表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复调性意识。
二、主人公意识的复调性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与他人的共在,“我”的生存离不开“他人”,“我”需要通过倾听“他人”的声音,并与“他人”对话交锋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我”也必需借助“他人”的眼光、倾听“他人”的评判,积极地与“他人”对话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4]。这里说的“我”和“他人”都是存在于主人公意识中的声音,也就是说,在主人公的意识中通常存在相互矛盾并形成争论与对话的不同品格。小说《队列之末》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机会通过内聚焦叙事以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来阐释自我,将主人公意识中的不同品格表达出来,使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两重性,即存在“另一个自我”的“他人”与“我”进行对话。这样,读者在主人公的意识里,往往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例如,在第一部《有的人不》的叙事中,继高尔夫事件之后,提金斯在杜舍门牧师家的早餐宴上又与瓦伦汀偶遇,宴后和瓦伦汀同行前往温诺普夫人住处的途中,提金斯的内心产生了对瓦伦汀非常复杂、矛盾的情感:
他朝着温诺普小姐的后背说:“该死,你的眼睛!让他们责问你的贞洁吧!你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对陌生男人说话呢!……和好出身的英国男人说话,那会夺去你的贞洁的!……嗯!那就让它被夺走好了……你被牵连的越深,我就越是一个可耻的坏蛋……”[5]108
这段用直接引语表达的内心对话反映了提金斯对瓦伦汀爱恨交加、激情与理性并存的纠结、矛盾与挣扎心理。对他来说,和自己喜欢的女孩一起散步自然是愉快的,但他又为瓦伦汀的声誉考虑,责备她不该在公共场合主动和他这个陌生男人说话,而他的内心又是向往她和他说话的。可见,他的内心活动是多么的复杂多变、矛盾对立。再如,提金斯伤愈后重赴战场的前夜,在是否确认与瓦伦汀的情人关系上,内心也是犹豫不决:
“我支持一夫一妻制和贞洁,所以不要提这件事。当然,如果他是个男人,想要个情人没什么问题。再说一次,不要提这件事……”[5]281
此时提金斯的内心非常缠绕。对于是否和瓦伦汀建立情人关系,他的头脑同时在说“要”和“不要”,两条线搅在一起,像一首赋格的两个主题。小说中存在多处像这样具有矛盾性的两个声音甚至多个声音的相互争论。小说描写主人公多重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各种声音之间的对立,揭示它们的正面与反面,洞察心态中的自尊与自卑,同一情绪中的惶恐与自慰,这就是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这种对话既包括自我的内心对话,也包括自己和他人异质思想之间的对话。
三、主人公意识的多声部内心对话
在复调型小说里,主人公意识具有独立性和开放性,它与作者意识构成了一种新型关系,也就是对话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通过对人的心灵奥秘的揭示,最终是把“人身上的人”逼出来,也就是把人的尊严和价值、精神与心灵的全部丰富性,在这种没有穷尽的对话中展示出来[2]343。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福特也感受到了自己时代的对话性,并发现了不同声音之间的特殊对话关系和对话互动。他不仅呈现主要人物的观点,而且描绘次要人物的观点,并在这些观点之间形成对立和对话。福特叙述的焦点是人物的内在和心理洞察力,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意识通过内心对话得以呈现。因此,构成叙事的大多数对话都发生在人物的脑海中,而且很多对话都是针对人物自己的内心对话。在《队列之末》中,人物以对话形式表达自己,他们都拥有一个对话的自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一样,《队列之末》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在对话的过程中,人物自由地相互展示自己,读者只有通过对话渗透人物的个性才能获得人物的真实生活。
在第二部《再无队列》中,西尔维娅前往战争前线的法国鲁昂看望提金斯时,小说的叙述由三个不同的视角重叠展开,从而突出了四部曲本身的对话性。西尔维娅交给提金斯她截留的一系列信件,其中包括她已经读过的来自马克的一封信。在提金斯阅读这封信时,西尔维娅同时从记忆中复述了这封信的内容,使读者可以从马克、提金斯和西尔维娅的多重视角阅读它。当西尔维娅回忆马克的信时,读者可以看到不同视角之间的对话,同时西尔维娅也能够从马克的视角来认识自己,因为信中提到了她。读者可以一并看到马克在信中对西尔维娅和瓦伦汀的叙述与西尔维娅对马克叙述的反应。此外,读者可以想象提金斯读信时的视角,了解提金斯对信中所涉及事件的感受。在这个场景中,小说以立体的方式使三种不同的意识重叠,将不同风格和声音的思想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不同视角和声音对同一事件进行评论,从而在西尔维娅的意识中形成一种内心对话。在四部曲中,某些事件会反复发生多次,每次都为复调的叙事中已经存在的意义层次增添不同的视角和意义。例如,第四部《最后一岗》又恰好代表了对先前小说事件的另一种解释,这次的视角来自在前三部中没有足够空间展开叙述的次要人物,包括提金斯的哥哥马克和他的爱人莱奥尼、瓦伦汀、西尔维娅、提金斯的儿子小马克、老农民雇工冈宁等。
四部曲本身的核心思想是以对话为基础的,其所表达的英国传统道德价值崩溃、战争的徒劳与创伤、生活的重建等主题都是在主人公意识的多声部内心对话中呈现的。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提金斯和瓦伦汀之间的爱情具有思想上的对话性。提金斯对瓦伦汀的爱不是性的渴望,而是对话的向往。他想追求她,以便与她进行终生对话。因此,爱本身被描述为两个“他者”之间的对话:
你追求一位年轻姑娘为的是能够完成你和她的谈话。要不和她住在一起,这是做不到的。而你要是不追求她,也就不能和她住在一起……这说的是那种意味着你们灵魂最终交融的亲密对话。你们必须要一起等待一周、一年或者是一生,才能开始那场最终的亲密对话……
事实上,那就是爱吧。[5]629
在这里,对话式交流被认为是“灵魂最终交融”,是真爱的本质。真爱不是西尔维娅式的占有和毁灭,而是瓦伦汀式的对话和责任。因此,爱情的最终宣言是与之沟通交流的欲望,与另一种意识进行终生对话,以使自己更加深入了解对方和自己,找到情感的寄托和责任的担当,发现生活的意义。
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能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另一个自我,同一人物的两个自我之间展开内心对话。例如,第三部《挺身而立》中瓦伦汀意识到自己内心挣扎的意识和自我意识:
……她到底想要什么,居然连自己都不知道?她听见自己几乎是带着哭腔说着,所以,很明显,她情绪在波动:“听我说,我反对这一切,反对我父亲把我变成的这样子!……我根本就不应该在这所学校里,我也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看到瓦诺斯多切特小姐迷惑的表情,她自语道:“我说这一大堆到底是为了做什么?你还以为我在试图和这所学校脱离关系!我是这么想的吗?”[5]534
此处瓦伦汀不仅对自己说话,还直接与另一个自我进行交谈,并提出质疑。在这段文字中,瓦伦汀的无意识自我的隐藏欲望与她的理性之间发生冲突,通过这一冲突她试图理解自己情感的本质。提金斯、瓦伦汀、西尔维娅等主要人物以及麦克马斯特、坎皮恩将军等次要人物都经历了内在的心理冲突。例如,当坎皮恩将军写信给陆军部长汇报关于提金斯的情况时,他发现在问及自己该做什么,就好像他在和一个陌生人或其他意识说话一样:
写到每句话的结尾他都在想——他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满足感写着信!——他没用来写信的那半边脑子在说,“我应该拿这家伙怎么办?”或者“怎么才能确保不把那女孩的名字搅进这一团糟里?”[5]464
坎皮恩将军不仅直接向自己讲话,而且似乎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分裂的影响。 另一种思想,不是他的意识和理性的思想,而是他无法控制的思想介入并直接质疑他。此外,像瓦伦汀一样,提金斯也意识到自己在内部对话中展开的双重自我和内心挣扎:他对自己喊着,“老天有眼!这是癫痫吗?”他祈祷着,“上帝保佑的圣人,救我出去吧!”他喊着,“不,这不是!我完全可以控制我的头脑。我最重要的头脑。”[5]494小说多处可见提金斯的内心矛盾、分裂的心态和永无止境的自我分析,这些自我分析以自我对话的方式表达出来。提金斯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双重性,同时用对话的方式对自己说话。
有时,人物还会考虑和评价不在场的其他人物的言语和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在人物的意识中形成冲突和对话。在第二部《再无队列》中,提金斯的妻子西尔维娅就经常和另一个自我以及已经死去了的康赛特神父进行多声部对话:
西尔维娅心中泛起种种情绪……在提金斯的身边,她对自己说:“会永远这么下去吗?”……她说:“神父!你曾经很喜欢克里斯托弗,让圣母帮助我克服吧。这会毁了他,也会毁了我。但是,噢,该死的,别这样!因为这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5]400
上述西尔维娅和康赛特神父之间的对话是在西尔维娅的脑海中发生,康赛特神父不仅不在现场,而且已经不在人世。但是,西尔维娅与死去的神父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对话,理所当然地考虑了他的思想和他对提金斯的立场,这样就并不需要神父的实际在场。这样的对话通常是在两个以上的意识之间发生:人物、另一个自我以及其他人物的视角。而且,多声部对话性叙事弥补了人物之间缺乏交流的缺陷,而这种想象的交流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对话,即主人公意识的多声部内心对话。
四、结语
福特小说《队列之末》的贡献不限于印象主义、时间转移、内聚焦叙事等十分现代的手法,还在于其呈现了对话性对立的多种声音、视角和观点,体现了人类思维和思想的对话本质。福特使小说人物摆脱了作者的控制和判断,并使他们的声音和意识完全独立。《队列之末》并不关注悬疑的情节,而是人物意识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叙述的外部事件的主观反应。通过对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对意义、自我分析和内省的本体追求,人物的声音和意识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呈现出来。对话的方式不是对白,也不是独白,而是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自我之间的内心对话来表达自我,充分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复合性。人物内心的多声部对话本质启发我们观察以其他意识作为镜像反映的自我,不仅在社会现实中也在自我意识中与“他者”展开充分对话,尊重他人的差异和个性,而不是将自己的动机、理由和感觉归因于他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