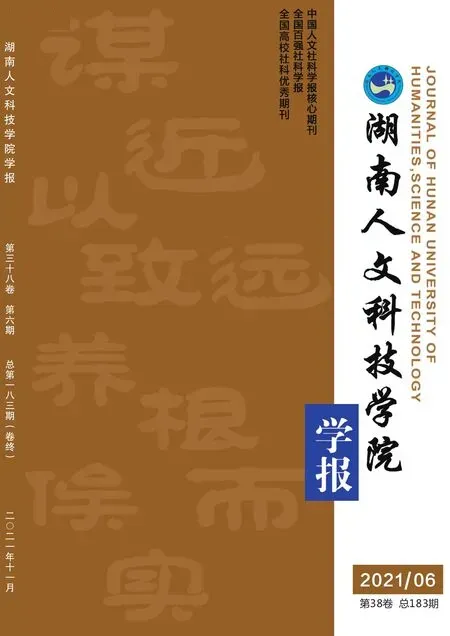论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对湘军的影响
范大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清王朝至道咸时期,已日益呈现出衰落之势,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面对危局,思想文化界一些学者受传统儒学“修齐治平”德治思想的影响,试图从学术层面探寻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的办法。于是,已独霸学坛百余年之久的汉学作为学界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被学界斥责为琐碎拘执、失道误国,造成社会道德沦落、人才匮乏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被压抑日久的宋明理学等学术思想开始复苏,出现所谓“理学中兴”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罗泽南先以“醇儒”之身坐馆授徒20余年,同时精研理学,著书立说;后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率徒编练团勇,倡办湘军,转战数省镇压太平天国。罗泽南是晚清理学和湖湘经世学者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治学严谨,尊崇宋儒之学,探其精微,得其奥义,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认识体悟,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并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罗泽南将其理学经世思想充分运用于文化教育与治军打仗,通过其与弟子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实践,成就了“理学名师”与“湘军之母”的名声,取得了“大小二百余战鲜有败绩”的骄人战绩。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对湘军的崛起与湖南社会文化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基本特征
罗泽南尊崇程朱理学,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的著作均作过深入的探究和剖析,著述颇丰。体现其理学经世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人极衍义》《西铭讲义》《周易本义衍言》《周易附说》《皇舆要览》等,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朱熹的《周易本义》等著作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尤其对理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大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并“将周、张、朱等人思想中的精微之处进一步挖掘出来,特别是对周敦颐的‘主静察几’之说、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进行了反复的申论”[1]。罗泽南在取各家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具有一定创意和特色理学思想。同时,罗泽南作为素有经世传统的湖湘学者,其理学思想又呈现出强烈的经世气息,并通过其著书授徒、投身军旅、创办湘军等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他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可以说,以儒学正统和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旨归,是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捍卫儒学正统,倡崇程朱理学
儒学发展到宋、明,出现了学术转型,理学成为思想文化的正统,被统治者奉为圭臬。但到清代中后期的乾嘉时期,以考据学为代表的汉学流行,而理学被压抑,士子或热衷研读心学,或醉心于词章。道咸时期,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汉学作为学界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于是,学术界“理学复兴”应运而起。罗泽南是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坚持捍卫儒学正统为己任,正学术、斥异学,大力倡崇程朱理学,猛烈批驳陆王心学。
素以“崇正学、辟异端、正人心、明圣教为己任”的罗泽南,针对其时学界俗学斑杂、风气不正的局面,认为匡时济世必先正学术,才能正人心,而正学术首先就要辨明正统。为此,他认为:“议淫邪遁之词,甚为难辨。知言之功,当自何始耶?曰:不消急要去辨别他底,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将圣贤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里精粗,毫无蒙蔽,则彼说来前,便能烛其病之所在”[2]285罗泽南与传统士人一样,极力推崇 “万世圣人”的孔子和“亚圣”孟子,但他对宋儒更为注重,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看作孔孟的继承人,直接传承了他们的“大中至正之道”,以为宋儒理学 “发尧舜之薪传,续孔孟之微脉,圣贤之道,益以大明于天下”[3]206其中,罗泽南对宋儒最推崇的是朱熹,认为“非朱子无以发;濂洛之蕴奥,非朱子无以明”“夫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传也”[4]267。
罗泽南认为,要坚持正统儒家的“大中至正之道”,就必须在辨明儒家正统的同时,找出异端学说的谬误所在,从而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他认为佛、老之学是杂学、俗学;佛老之学不绝而盛行天下,则必然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应坚决排斥。同时,为了防止宋、明以来流行的心学危害“儒学正统”,罗泽南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姚江学辨》开篇即言:“吾谓阳明《传习录》、《大学问》论学诸书,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日无善无恶。无善无恶,阳明所不常言也。其说本之告子,出之佛氏。常言之,则显入于异端而不得托于吾儒也。然而千言万语阐明致良知之旨,究皆发明无善无恶之旨,阴实尊崇夫外氏,阳欲篡位于儒宗也。”[4]209他认为“阳明悖古圣之明训,信外氏之邪说,谓性之本无善无恶,发用也可以为善、可以为恶。是则天下之为仁、为义、为忠臣、为孝子、为信友、为悌弟,皆非本体所固有,不过因乎意念之所动也;为奸、为宄、为盗贼、为寇攘、为篡逆,亦发用上所有也。圣如尧舜,于性何与?暴如赢杨,于性何伤?不将率天下之人沦三纲敦九法,至于人将相食而不止哉! ”[4]211
(二)传承传统理学思想,对程朱理学作出具有创意的阐释
罗泽南作为一位恪守程朱理学的思想家,一方面坚持儒学正统,极力尊崇程朱理学,传承程朱衣钵;另一方面,他又结合自己的治学体验,对程朱理学作出了具有创意的深入探究、发掘和阐释,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理气论方面,罗泽南继承了程朱理气论的基本思想内涵。“太极”“理”与“气”,是程朱理学中关于哲学世界观、本体论的基本范畴。罗泽南对朱熹之论“太极”以及“理”与“气”等哲学本体论范畴加以深入的阐发,并提出“天地人一太极” “理在气先,不离不杂”“气化万物,理为主宰”等思想观点。他认为:“天、地、人,一太极也。至哉!道乎无声无臭,纲维二五,根抵万化。至诚无息,天以诚而运也;至顺有常,地以诚而凝也。”[3]189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罗泽南在朱熹的理气观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气不离不杂”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格局,认为:“盖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气也者,所以载夫理者也。无理,气无所宰;无气,理无所附。二者不相杂,亦不相离者也。是故阴阳异位,道无往而不存也;动静殊时,道无往而不在也。散之万殊,统之一致也,非默契天地之化育,孰能识其微哉?”[3]190在“理”与“气”在哲学本体论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形成世界万物的问题上,罗泽南把“理”与“气”在天地万物中的具体作用概括为8个字,即“气化万物,理为主宰”。他认为:“天地之大,无非此理之所充周;古今之久,无非此理之所运量也。是以人生其中,莫不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即莫不得天地之理以成性。”[5]又言:“理在天地间,初无偏、全之分,有是气即有是理。气之清者,此理固无不存;气之浊者,此理亦无不在。惟其气有清浊之殊,故其理有明蔽之异。”[2]306并说明了气在具体物质成形中的作用:“天地之气,万有不齐。和风甘雨,其气清明;阴霾浊雾,其气昏暗;迅雷烈风,其气震荡;愆阳伏阴,其气偏戾。天时有不齐也,西北之地高俊,其气多刚劲;东南之地平衍,其气多柔弱。得山之气者,其人多雄健,其恶者为粗顽;得水之气者,其人多秀丽,其恶者为淫靡。故数里之间,其气多有不同,地势有不齐也。天地之气各殊,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俟矣。”[2]307
在心性论方面,罗泽南继承和发展了宋明理学的人性论思想,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并对“气质之性”的意蕴作了具有一定新意的阐发,提出了“心为身之主宰”和“心也者,理之次舍也”的思想观点。“把心性关系置于身、心、行、道这样一个更广的思维空间中考察,强调理为心性本体,让他的心性论与理气论顺利地建立起连接。”[6]然后,罗泽南又进而从天地人的关系将万事万物变化与人的身体结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他在《人极衍义》中说:“人身一天地也。得天地之气以成吾形,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气,其天之覆帱也乎;骨肉,其地之持载乎;声音,风雷之鼓荡乎;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发,草木之荣滋乎:经络,山川之条理乎;呼吸。昼夜之循环乎;寐兴,寒暑之往来乎;老幼生死,元会运世之递降乎。曰仁、曰礼,元亨之通乎;曰义、曰知,利贞之复乎。天地,一大人也;人,一小天地也。心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其量固未尝或隘也。盖天地人同一太极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极也,分之殊也。”[3]190
在人性论方面,罗泽南主张性善论。他综合了孟子性善论,在承袭宋儒理学把人性归诸于 “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 的基础上,深入阐发了其意蕴及二者的关系。他把人性之善恶、智愚、勇怯等归之于气性的差异,并认为应实行人为干预而求其变。其曰:“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与?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气禀之各异也。气有清有浊,斯人有智愚也;有纯有杂,斯人有贤否也;有强有弱,斯人有勇怯也。故上哲之资清而纯,下愚之资浊而杂,其中人,则毗阴、毗阳,或静、或躁之不同。气禀拘于生初,物欲蔽于后起,斯人之才遂至于千变万殊而不可纪极然。而物与人分明暗也,圣与凡分通塞也。暗者不可使之明,塞者犹可使之通。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者,变化之道,是在乎人为也。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3]191于此,罗泽南从儒家人性论的视角出发,在肯定人“性善”的前提下,解释和肯定了“气”与人为因素对人性的“善恶、贤愚、勇怯”的影响。
在道德论方面,罗泽南坚持传统的儒家道德观,竭力维护程朱理学伦理的纯正性,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批驳了阳明心学“以仁义礼智为表德” “天下无心外之物”和“良知”论观点,充分论述和深入阐发了“仁爱”“礼乐”“义利”等关系范畴。罗泽南认为“仁义礼智未发之中也,大本也”,而“阳明悖古圣之明训,信外氏之邪说,谓性之本无善无恶,发用也可以为善、可以为恶。是则天下之为仁、为义、为忠臣、为孝子、为信友、为悌弟,皆非本体所固有,不过因乎意念之所动也;为奸、为宄、为盗贼、为寇攘、为篡逆,亦发用上所有也。圣如尧舜,于性何与?暴如赢杨,于性何伤?不将率天下之人沦三纲敦九法,至于人将相食而不止哉”[4]211!
在认识论方面,罗泽南以“格物致知”作为基本方法论原则,将认识论与道德论结合起来,体现出其理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7]
(三)以经世之学充实程朱理学,并将其运用于教育、政治、军事实践
明末清初以来,湖南学界受船山思想影响,一直具有着浓厚的经世传统,在晚清由空疏流弊的“纯学术”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涌现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唐鉴、曾国藩、刘蓉、左宗棠等一大批经世派大家,以至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说:“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最盛”。罗泽南当时虽以塾师身份名声不显,但实则为其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几十年的教育、政治、军事实践中,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在注重以儒家道德和程朱理学思想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倡导经世实学并竭力躬行之,“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8]。罗泽南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之中,并通过其撰写的《皇舆要览》一书而集中体现。《皇舆要览》共9卷33篇,内容丰富,涵盖广博,纵论山川河流、水患水利、漕运盐政、少数民族防务及国内外形势,将罗泽南的理学经世思想予以充分展现。
罗泽南的经世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罗泽南虽曾长期坐馆授徒,却又密切关注社会时政。他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合理性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上展开的。罗泽南认为,君主的职责就是“代天理物”,应该像爱护父母一样爱护老百姓。如果君主勤政爱民,修已安民,以礼仪教化百姓,就能恢复其善良本性,老百姓也就会拥戴君主,遵守社会秩序;而如果君主安于享乐,不修德爱民,不勤政安民,那就会背弃天道,违背民意,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因此,君主就一定要修身养德,而为人臣者就应该勇于上疏进言。他说:“乾父坤母,化生万物;四海黎献,尽属天地之赤子。然天虽生此民,厚生正德,有非天之所能为者,则命此有德之君以统治之。故君行政以治民,实为代天理物,而有父母斯民之责。”[9]罗泽南还认为,在国家治理上既要注重“保民而王”,对民施仁政,行教化,但又不可废法度。而国家的运行管理还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因此,要举贤任能。他认为:“贤人登庸,天命以存;不肖在位,天命以亡。进退一世,人才以寅亮天工,典至巨,系至重也。是故五臣举,虞治盛;伊傅起,商道隆;吕周夹辅,王化大行;方召佐命,宣王中兴。是皆贤才之赞襄,开至治于千古。”[3]196此外,罗泽南还认为,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就必须使老百姓有安定的生活;而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就必须以封建土地制度作为切实保障。针对当时“天下之田,又多为富者所占” 的土地兼并严重状况,罗泽南提出了“复封建”“复井田”的主张,他认为“盖封建者,井田、学校之所由行也。不封建,则不能井田,贫富不均,养民之道失矣;不井田,则不能学校,庠序无法,教民之道失矣。”[3]197
罗泽南军事思想,是其经世思想的重要内容。罗泽南一生虽然直接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不长,但他非常重视军事,在当塾师的时候就注重训练门徒军事武备;以后投笔从戎,在组建湘勇练兵、统兵治军的过程中,将其理学经世思想完整地运用于军事,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儒将”。罗泽南军事思想内容丰富,颇具特色。他注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严肃军纪。他与其弟子率领的军队往往在行军作战之余,讲学论道,以儒家忠孝仁义之伦理道德教导军队士兵。此外,他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战争与思想政治的关系、战略战术、战备、军事形势与地理等问题,也都有深刻的理解和阐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战争理念与军事思想。例如,他认为:“兵也者,所以行天之讨者也。方命虐民,罔畏天威,以兵靖之,而后可以禁万民之乱。御戎之法,不在边锤,而在朝廷之政事也;战胜之道,不在杀戮,而在德威之素著也。是故佳兵者不祥,有德者无敌。圣王之征天下也,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用,除暴安民,不得已而用之,故战则必克也。不以好大勤远略,不以太平忘武功。”[3]199他还认为,战争性质直接影响战争胜负结果,仁义之师因为深得人心,必然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惟孟子之言,乃天理人心之至。义旗一麾,天下自然响应,盖大公无我之心,天下共知,我师未动,邻国之民,早有引领而望者,沛公宽大长者,遂能收人心于秦、项之余,况夫以纯王子心,行政王之政者哉!仁以胜暴,此战国时之第一著,亦古今之第一著,惜乎无有能用之者。”[2]278在战术上,罗泽南主张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曾国藩曾在奏稿中称:“罗泽南自与此贼接仗以来,专用以静制动之法,每交锋对垒,贼党放枪数次,大呼数次,而我军坚伏不动,如不敢战,往往以此取胜。”[10]此外,罗泽南还非常重视注重军事地理形势的研究,注重考察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和舆地制图,并在军事战争中加以适当运用。他说:“统筹天下之大局,黄河北条之水也,秦晋、燕赵之险凭之;大江南条之水也,巴蜀、荆襄、徐扬之险凭之。河水浑浊,操舟维艰,长江数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东南争战,必恃水陆之兼济。”[11]
罗泽南教育思想,是他在长期的为学治学、座馆授徒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罗泽南从4岁开始“受命读书”,19岁课馆授徒,在办团练之前,他长期作为塾师,培养了一批既遵循儒家伦理道德又有经世济世之志的学生。罗泽南教育思想包含为学治学、教书育人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他认为,为学治学一定要为“圣学”、为“正学”,而要为“圣学”、为“正学”就必须首先立志,即其所谓“人之为学,必先立志。志不立,虽以至易为之事,逡巡畏缩,废然而无所成。志一立,虽以至难为之事,鼓舞而不可御”[12]。在论及为学治学时,罗泽南还强调讲求经世之学。他说:“吾人为学,固当于身心下工夫,而于世务之繁琐、民情之隐微,亦必留心穷究,准古酌今,求个至是处,庶穷而一家一乡处之无不得其宜,达而天下国家治之无不得其要。此方是真实经济,有用学问。”[13]罗泽南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勇于探索,善于总结,教育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寓教于乐,并自编辅导讲义:《西铭讲义》和《小学韵语》。由于教学得法,效果良好,罗泽南日益成为湘中有影响的塾师名儒,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有志士子门徒,成为日后湘军名将的摇篮。
二、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的影响
以儒学正统和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旨归的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通过其长期座馆授徒、组建湘勇、统兵打仗以及成就湘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实践而熠熠生辉,在晚清的湖南乃至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湘军的影响至深,其影响的对象上至湘军将帅,下至普通士兵;影响的方面涉及湘军的组建训练、军队建制、军事理念、治军与行军打仗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
(一)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将帅及相关名臣的影响
罗泽南的学识渊博,是湘中有名望的塾师乡绅,教书授徒20余年,其弟子友人为数众多。曾国藩、刘蓉、郭松焘、胡林翼、左宗棠等“中兴名臣”都与其交往甚密,而罗门弟子更是遍及三湘,据他的好友刘蓉说:“从之游者数百人”。其中,因投身湘军而留名史册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李杏春、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朱宗程等,共达16人之多。这些后来成为湘军著名将领的他们之所以能“以书生拯大难、立勋名”,与其在不同程度上受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所言:“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罗泽南向弟子传授学问,与一般的塾师不同。他不仅授以弟子科业,而且将义理经世之学传之,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罗门弟子在罗泽南的影响下,以程朱理学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标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王鑫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得同邑罗罗山先生师事之”“日夜与讲明善复性、修己治人之道”,“每恨相从之晚也”[14]40-42。李续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从罗泽南游,“日与讲论正学,自以躬之所行,不逮所言”[15]。同年,师从罗泽南的钟近衡将自己每天的言行见闻记录下来并考察得失,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称许:“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则可望乎!”[16]谢邦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从罗泽南读书于朱氏别塾,“朝夕讲习,以圣贤之道相儆醒”[17]。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罗泽南最初兴办团练,他们就都毫不犹豫地追随罗泽南投身到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去了。也正是这一大批弟子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追随罗泽南左右,而后来又大多为官一方,他们训练民团,安抚百姓,兴办教育,推行洋务,为晚清“咸同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罗门弟子的影响,《清代名人传略》评价:“罗虽然是一位学者,却有经世之才,尤精于兵书战略。罗泽南诸如此类的成就与品质才干,在他多年教书的生涯中,也许已影响了他的学生。”[18]事实上,在后来与太平军的争斗中,罗泽南的弟子们平时在师门所学习积蓄的学识与经世才干,特别是军事才干得到了充分施展。如王鑫在罗泽南门下求学时就注重研究兵法,后来带兵时结合自己的体悟写出了《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等兵书。在对兵士的训练上,他注重明耻教育与军事教育的结合,认为“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19],“日教练各勇技击阵法”“至夜,则令读《孝经》、《四书》,相与讲明大义”[20]。他充分利用忠孝仁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来驱使士兵为其拼命,因此,王錱所统领的湘勇凶狠异常,少有败绩。又如,李续宾在罗泽南的影响下,也注重研习舆地学,“摩绘地图九百余纸” ,曾国藩见之,“自谓所藏皆不能及也”[21]。李续宾对兵法也深有研究,在带兵之前就著有《孙子兵法易解》。在罗泽南带兵期间,李续宾一直跟随其左右,深受其思想影响。“罗公善言易,攻战之暇日相与讲习讨论”, 续宾“于屈伸消长之机、进退存亡之道,颇能默契于心”[22]。因此,对于罗泽南的作战意图,李续宾总能全面领会。这些,为日后李续宾成为湘军名将打下了良好基础。罗泽南战死后李续宾接统其军,“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23]。在他的率领下湘军“益发扬而光大之”[24]。曾国藩曾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指李续宾)也。”[25]在罗泽南死后,罗氏弟子王鑫、蒋益澧、杨昌浚等深为左宗棠所器重。
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其弟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些弟子因战功成为地方大员后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先,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吏治进行了整顿。他们担任地方官员后,大多以整顿吏治为要务,兴利除弊。如蒋益澧在署理浙江巡抚时,“遴乡士之朴诚者,予以厚资,令微服赴郡县密考牧令政绩”。其次,积极倡导和推行团练。罗泽南及其弟子本身就是靠团练起家,因此对办团练极为重视,每攻克一地他们都要“召见士绅,慰免以忠义,出示令行团练法,以自相保卫”[26]。再次,积极兴办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罗泽南及其弟子在为官之后,极其重视恢复地方文化教育,注重弘扬儒家道德礼仪。积极兴办义学、书院,恢复科举。1853年罗泽南驻军衡州时,修复了石鼓书院。次年,又出资兴建湾州义学。李续宾与曾国藩、胡林翼共同出资兴建箴言书院。蒋益澧任浙江巡抚时“增书院,设义学,兴善堂”并修复贡院,补行乡试;其任广东巡抚时,又极力恢复广东地区乡试。罗泽南及其弟子每占领一地,都竭力宣传忠孝仁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1857年,王錱路过一陈姓村庄,见当地编辑的《崇仁志》上有理学、忠孝、仁义的目录,就对村民说:“尔辈今日尚知有此六字乎?尧、舜人皆可为,特患志不立耳。”[27]
罗泽南与曾国藩、刘蓉、郭松焘、胡林翼、左宗棠等一群有着共同学术旨趣的友人一起,不仅以经世实学著称于晚清,而且还积极从事军政文教事业,竭力为清王朝济时救弊,为所谓的“咸同中兴”尽心尽力,死而后已。正如梁启超所言:“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28]曾国藩与罗泽南家乡相近,少年时即仰慕其名,一起创办湘军,南北征战,对罗尤为倚重,对罗的过早阵亡甚为痛心,以挽悼之:“步趋薛胡,吾乡矜式;雍容裘带,儒将风流。”曾国藩所作的《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对罗泽南给予了高度评价,曰“公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叹仰,以为名将,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泽南与刘蓉同为湘乡究心圣贤、砥砺品性之人士,两人相互督促,并引以为知己。在《春日怀刘大仙霞》一诗中,泽南发抒二人惺惺相惜之意,“男儿莫受虚名累,七尺顽躯忍抛弃。叱咤风云生远心,酒酣拔剑蛟龙避。两地相思二月天,班超投笔谁少年?谁少年?默无语,读书之乐乐千古,篝灯独听潇潇雨。”[29]罗泽南与郭松焘、胡林翼、左宗棠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胡林翼武昌被太平军攻克告急时,罗泽南毅然率部从南昌急忙回援,以至命殒武昌。罗逝世后,郭松焘专为其撰写年谱。左宗棠在湖南组建“楚军”,就是以罗泽南弟子王鑫的老湘营为班底的。左宗棠不轻易服人,但对罗泽南却极为赞赏。
(二)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创建、训练及治军的影响
罗泽南在兴办团练、训练湘勇、初创湘军及其以后领兵打仗、治理湘军的过程中,始终以捍卫封建纲常礼教为旗号,以理学经世思想为精神灵魂,注重思想教育和意志磨砺,严肃军纪军风,从而练就了一支勇猛异常、“少有败绩”的湘军劲旅,成就了“湘军之母”“一代儒将”的名声。事实上,湘军将领中,大多有“儒将”而兼“悍将”之谓,这是士人出身的湘军将领最根本的人文特质。罗泽南、曾国藩、胡林翼、刘蓉、左宗棠、王鑫、李续宾、蒋益澧、杨昌浚等都是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满腹经纶,深明忠义,智勇双全,可谓文经武纬之才。曾国藩、罗泽南统领的湘勇以理学经世思想融合湘中地域血性文化精神,作为立军之本,大力倡导“以礼治军”,注重发挥精神文化的教育作用,将刚毅血性文化精神与“公诚道义”之儒学伦理融为一体,并升华为“湘勇精神”[30]186。
罗泽南兴办湘勇早于曾国藩,已是公论。罗泽南坐馆授徒时,即教授门生既习文,又习武。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起事初入湖南,罗泽南应湘乡知县朱孙诒之请组织编练湘勇时,招募的大都是能吃苦耐劳农民,而领兵的多为理学士子,此所谓湘军“选士人,领山农”之先例也。罗泽南以捍卫儒家道义和程朱理学为号召,常以封建理学、纲常名教以及湘文化与湘中地域血性文化对将士进行思想灌输和精神训导,整肃军队,严明军纪。他在带兵打仗的过程中,也常向士卒陈说忠孝节义,通过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湘军创立之初,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学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又言:“当湘军兴起,山农柔懦者亦颇畏远征,及援江西,士人轻死陷阵,叠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而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萧启江之伦,皆崇纪律,重廉耻。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益众。”[31]168正是罗泽南组编的这班乡勇人马,日后成为曾国藩办理团练、训练湘军的最初班底。因此,罗泽南“湘军之母”的称谓可谓实至名归。作为湘军早期的主要统领和曾国藩倚重的得力悍将,罗泽南及其弟子参与了对太平军的多次战斗,“师弟戮力,转战大江南北,师碚而弟子继之”[32]。罗泽南从军虽仅有短暂的4年,然其与弟子转战两湖、江西、安徽,挽危救急,历经大小200余战,克复20余城。在罗泽南武昌阵亡后,按罗泽南遗言,其所部主力由李续宾统领,再克武昌,后又回援江西,并参与安庆之战。在对太平军的战争后期,罗泽南弟子王鑫、蒋益澧、杨昌浚、刘典等将领深为左宗棠所倚重,为平定浙江和最后扫平太平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湘军组织结构与兵制的影响
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为指导创办湘勇,对湘军组建方式、组织结构、体制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尔纲曾经说:“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14]58湘军军制虽然最后是由曾国藩决定的,但罗泽南及其弟子在营制与训练方式、军事机制等方面的最初创造性贡献,可以说是世所公认的。正如王定安在《湘军记》中所说:“湘军初兴,王鑫、罗泽南皆讲步伐,谙战陈,深沟固垒,与贼相据。曾文正采其说立营制,楚师之强,莫与京矣。”[31]359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为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骑兵为棚。湘军之制起子陆师。湘军陆师营制,是1852年由朱孙治奉命募招湘勇时,与罗泽南、刘蓉、王鑫等人一起制定的,最初为每营360人。1853年底,曾国藩移驻衡阳后又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改定营制,规定湘军陆师每营加长夫120人,抬枪16人,成500人之数[33]。同时,还定出了湘军的军饷规制,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50两,办、幺银150两,夫价银60两,共计260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设置与办旗帜等,另补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它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9两、哨长6两、什长4两钱、亲兵护勇4两5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夹三两。如此,则奠定了湘军的军制。也因此,《清史稿》说:“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22]11949
自罗泽南创建湘勇始,以封建人际关系和乡土文化观念为纽带,来协调湘军内部关系和构建军队体制、运行机制。在创建湘军过程中,罗泽南、曾国藩鉴于清军内部“败不相救”的弊端,因而招募将士即以封建人际关系和乡土文化观念为纽带,通过同乡、邻里、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关系将其网罗在一起。统领由曾国藩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丁勇由什长挑选,形成以血缘、亲缘、地缘、学缘关系为基础的利害攸关、便于掌控的军队组织系统。曾国藩、罗泽南的同乡、友人、弟子与湘军其他将领相互之间姻亲关系就非常普遍。这种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对血缘姻亲关系、同乡关系、师友关系的认可和强化,使湘军将士行伦普遍一致、思想高度认同,造就了一支异常强悍的地方武装。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这支军队内部关系虽然也很复杂,也出现过像王鑫等个别将领难以统驭的现象,但总体说来,各统领、营、哨之间还是能首尾相顾、互相呼应的,很少发生见死不救的情况,也大都能服从曾国藩的调度。也正因为如此,湘军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充分展现出不同于清八旗子弟兵的强悍的战斗力[30]151-152。
三、结语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近代湖湘文化与湘中地域血性文化孕育出来的典型人物。尊崇程朱理学、捍卫封建纲常、重视思想教育、坚持忠义血性、倡导经世致用、热心文治武功,是罗泽南基本的文化品格及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精神内核。以儒学正统和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旨归,是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的基本特征。
他早年坐馆授徒20余年,培养出大批学徒,其中涌现出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著名湘军将领;同时精研理学,著书立说,撰写有《小学韵语》《人极衍义》《西铭讲义》《周易本义衍言》《周易附说》《皇舆要览》等著作。中年后,又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率徒编练团勇,倡办湘军,转战两湖、江西数省,救急挽危,历经大小200余战,克复20余城,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罗泽南以理学经世思想为导引,首兴湘勇,对湘军的创建、训练、治军及其内部组织结构与军制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赢得了“湘军之母”“湘军儒将”的称谓,也可谓名至实归。自罗泽南创建湘勇始,湘军即以封建人际关系和乡土文化观念为纽带,来协调湘军内部关系和构建军队体制、运行机制,形成以血缘、亲缘、地缘、学缘关系为基础的利害攸关、便于掌控的军队组织系统。罗泽南理学经世思想对曾国藩、刘蓉、郭松焘、胡林翼、左宗棠、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湘军将帅及相关名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晚清学术风气的转变与近世湖湘经世派文化的兴盛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