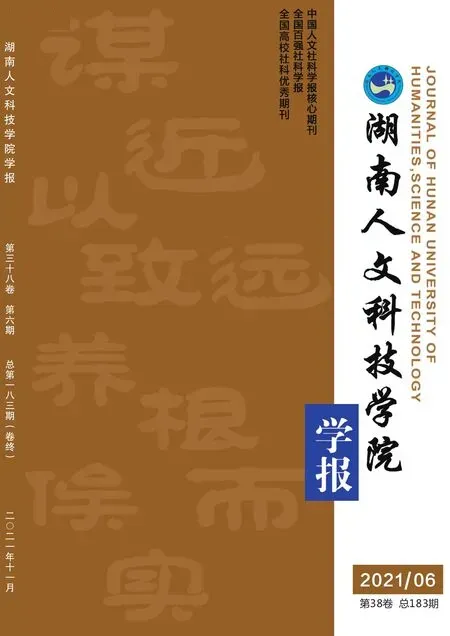“都市边缘人”:《阿毛姑娘》疾病叙事探究
王书婷,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疾病”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出现频率很高,它本身是一个属于医学领域的问题。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不仅指涉的是医学上的生理范畴,也跨指社会文化中畸形、病态的现象与问题[1]。近代以来,文学家们对病态身体的关注,尤其是女性作家对于该题材的独特书写与细腻体验,更彰显出了性别抗争的色彩。以丁玲为例,其早期小说都涉及到了肺结核或忧郁症等①,这种独特的疾病叙事大多以心理隐喻的方式,成为展示灵肉冲突的平台,直接指向了人物感伤苦闷的心理,从而揭示出五四青年们的“时代病”②。值得关注的是,疾病原本是“阴郁”“幽暗”的负面象征,而在《阿毛姑娘》中,肺病不再令人“气闷”,在主人公眼里反而被视为“一种多情的高雅”[2]。它似乎超越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那种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心境和环境的衬托,而将“身体的病态”视为“城里人”的一种时尚[3],一种高贵的文化身份象征。在丁玲的疾病书写史上,《阿毛姑娘》是她初期作品中一部典型的、却未被引起重视的小说,原因正在于主人公的疾病症状并未明晰地表露在读者眼前。因此,本文以阿毛“疾病情结”的产生作为切入点,以个案分析的形式,研究身处现代社会的“都市边缘女性”欲望意识觉醒及其文化身份隐喻,探讨“疾病”的美化功能,从而揭示出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都市边缘女性”的复杂性。
一、“过渡中的女性”欲望意识的萌发
和丁玲的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相比,《阿毛姑娘》的影响力远不及前者。然而它却体现出疾病书写的独特性,即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大胆描写。如果说前者以疾病叙事的方式,袒露了现代女性在灵肉冲突的爱情面前挣扎反抗的心灵困境,流露出的仍然是五四文学启蒙意识形态下,“莎菲们”坚守精神独立、渴望爱情自由的女性意识,那么《阿毛姑娘》的魅力则在于作家超越了之前观念层面的哲学式拷问,使得阿毛的觉醒比起梦珂、莎菲的焦灼具有了更为实在的身体内涵。它正视了生活在底层的乡村女性对物欲和情欲的热烈追求,真实地触碰到了“边缘女性”欲望心理的潜在发生[4]。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的少女嫁到城乡之郊后,隐藏在主人公理性意识之下的身体欲求逐渐被唤醒。与此同时,现代都市的引诱与“结核病”的刺激又加重了阿毛的病情,直至她精神崩溃、自杀而亡。
从荒凉偏僻的山谷嫁到城乡交界处的葛岭,阿毛不仅经历了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的变化,感知着因都市文明带来的心理变化与欲望醒觉。这种醒觉主要体现在物欲与爱欲两个方面。
小说一开始,阿毛是一个生活在荒凉偏僻山谷的淳朴少女,她具备中国传统社会所赋予女性的一系列美好品质。即使生活环境封闭、落后,在阿毛的眼中也是一个如世外桃源般保存着原始时代的朴质荒野的存在。当阿毛从偏僻的山谷来到城郊西湖边葛岭时,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不仅物质生活相比之前而言变得更为富足,阿毛还遇到了一个疼惜爱护她的丈夫。这个坚实纯朴、脸色微带红黑的少年会在阿毛梳头发时“替她擦一点油”[5]72,在阿毛做鞋时替她理线,偶尔进城还会买一些香粉香膏之类的东西讨她欢心。陆小二的爱抚使阿毛第一次体验到了生命原始欲望下男女之间的爱慕。爱欲与婚姻催发了阿毛身体里的欲望意识,刺激了她敏感、害羞、温婉的女性特质。爱情的滋养使阿毛“旺盛的生命得到了自然的生发,灵与肉在这里结合得最为完满”[6]。同时,城郊生活的另类体验又为她更加接近杭州都会生活提供了机会。
在和邻居三姐、阿招嫂的相处中,阿毛第一次从别人的口中感知到城市的繁华富丽,它简直像一个神话中的奇境,深深吸引着这个乡下女孩。当她小心翼翼地向陆小二吐露了想要进城看看的愿望时,其人生的悲剧和痛苦也随着这次城市之旅而展开。“城市生活的富丽繁华,给予她一种臆想的依据……使人迷醉地沉浮于其中,不知感到的是痛苦还是幸福。”[5]68灯红酒绿的都会生活、打扮时髦的都市男女和繁华富足的城市景观,都让她对比见证了自己原来生活的贫乏枯燥。充斥着爱欲与激情的都市文明,如同海面上突然来临的风暴,强烈地吹袭着阿毛淳朴安宁的灵魂,也燃起了她骚动不安的欲望。小说中的“疾病情结”[7]正来源于此。“新的生活,总是惹人去再等待那更新的。”[5]69初次的城市之旅只是为阿毛开启了发泄内在欲望的一个小小窗口,而与自己一向交好、出身类似的三姐竟嫁得一个军爷,尤其是那穿着皮大氅、戴着玲珑小手套的上海美人成了阿毛的邻居时,她们娉婷摩登的步法、腰肢扭动的姿态都让其欣然向往,她愤然觉得“为什么她们便该命不同?”[5]71那些不能实现的物质欲念以白日梦的形式频频出现在阿毛的精神世界里,“无情地撕裂着她的内心”[8]。
向往现代都市富裕华丽生活的物质欲望萌发之后,主人公的情爱意识也被进一步唤醒。阿毛丈夫的爱是“从本能冲动里生出的一种肉感的戏谑”[5]65,是原始的、质朴的,但这种爱却被一对都市恋人的爱情所改变。一开始阿毛是连那穿着皮领和高跟缎鞋、戴着玲珑小手套的美人,“都不知道这也正是属于她一样的女性”[5]75。当他们搬来做了阿毛的邻居之后,两人说说笑笑,并肩朝着山上走。这对恋人的笑声夹在鸟语中,夹在溪山的汩汩中,她感到仿佛“连路旁枯黄的小草,都笼盖着春的光辉”[5]83。这是主人公对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爱情的感受[9],对城里姑娘拥有的浪漫爱情的关注,幻化为阿毛心中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之爱。这次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使阿毛意识到其婚姻生活的悲哀——精神意义上的虚妄,也使得她从原始的出于男女本能的感情冲动中剥离出来,主动寻求那种“超乎物质的爱”[10]。
欲望的产生来自于那次看似庸常无奇的城市旅行,但这场旅行在阿毛心里引起了风暴般的变化。单从文本上看,这是素朴单纯的乡村女性,由于寻求那浮华喧嚣的城市生活无望被迫自杀的故事。然而丁玲对这个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切,从肯定“都市边缘女性”作为一个“觉醒了的人”,到对内在合理欲求与自我人格完善的追寻。这种个体欲望意识的追寻也符合“人的文学”一贯追求的理念。可以说,个体欲望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文明的、合理的、进步的现代意识③,它彰显了狂飙突进的“五四”之后重新发现“人”、肯定“人”的时代气息。作者正是通过这类底层乡村女性的觉醒,去体验她们的“人”的社会觉醒。
二、“肺病”的美化
长期以来的疾病书写史上,“病”已不止被视作生命个体的病痛体验,也被文学家们当作一种隐喻手段来运用。在思考疾病书写给患者本身带来肉体痛楚的同时,更应关注那些加在疾病之上的多重象征意义。由最初引起轰动的“莎菲”系列形象开始,我们发觉了丁玲笔下的身体疾病所呈现的“Modern Girl”特质:女性高雅的“结核病”与追求浪漫的精神姿态,不仅影射着都市安逸享乐的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情调,更映现着现代女性的现实生存处境。她们无法参与其中,投身时代革命的潮流,同时又不甘成为封建男权制度的附属品,所以只得病态地放纵内在的情欲,苦闷地挣扎在社会的边缘[11]。
《阿毛姑娘》中同样出现了一位患着肺病的年轻姑娘,她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常常趿着一双嫣红拖鞋,漫步到阿毛家的院坝边,或又谐和着高低音唱着一首诗歌。在阿毛的眼中,“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也是一种幸福,也可以非常满足的死去”[5]61。为何阿毛会欣羡这个患了肺病的女人呢?其中的缘由可以从“疾病的隐喻”[12]中得到答案。自19世纪以来,结核病就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优雅贵族色彩的疾病,苍白和消瘦成为理想女性美的典型症候④。而肺病女人的独特气质、身份地位,刚好符合阿毛潜意识里的一切想象。服饰(外部装饰)与肺病(内部装饰)双双构成她内在欲望释放的隐性转换机制,阿毛偷偷模仿患病姑娘走路姿态的行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据丁玲本人回忆,幼年丧父的她在母亲的影响下深受古典文学熏陶,尤其喜爱阅读《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小说,用她自己的话说,便是“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里面反应了我所处的社会与时代,我可以从那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启示”[13]。在对患病的城里女性进行描写时,不禁让人联想起林黛玉那“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14]的瘦弱体态,加之多愁善感、沉郁哀怨的细腻心思。这种弱不禁风的病态美与病态性格,似乎在年轻姑娘身上得到了较好的呈现,成为她更具中国古典女性东方美的一个表征。
鲁迅在《病后杂谈》里,赋予了疾病特殊的浪漫主义色彩:“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7]279这位所希望的是患上肺病,即使是吐血,也不能“一碗或几升”,而是“半口”,微妙之处正在于这半口血,倘若太多,“一个人的血,能有几次好吐?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15]。在这里,疾病不是可怕的灾难,而是因为多情才病,病因情生,这恰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审美倾向,对疾病的审美化书写也在丁玲笔下得到了延续。在她的小说中,肺结核是一个主要的身体疾病,《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阿毛姑娘》中皆有过关于肺病书写的例子。主人公们那病态身体和病态的感伤情调,既是五四知识青年时代病的映现,同时也是疾病审美化表达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文本里除了阿毛这个前景性故事,它还暗藏了另外作为背景性存在的两个都市女性的不同遭遇。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住在阿毛家左面小山上的、面色惨白的年轻女性,另一个则是居住在小洋房中的城里美人。她时常在半夜演奏悲凄的曲子,那歌调在弦上是“发出那样高亢的,激昂的,又非常委婉凄恻的声音”[5]99。而她们俩的经历在阿毛眼中是如此令人着迷、超凡脱俗。即使是生着病还要在深夜弹琴,这和鲁迅笔下的那位生着病也要人搀着恹恹地到阶前去看海棠的行为是极度相似的。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的疾病⑤。它带有罗曼蒂克的象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16]33。对疾病的审美化书写塑造出文弱、孤独、敏感、高雅的病者形象,渲染出一种伤感、凄凉、唯美的艺术氛围,这样的人物形象、这样的氛围正是20世纪初以来肺病的浪漫主义隐喻的直观体现。
小说中出现对肺病的浪漫主义美化书写,首先与它独特的病症分不开。在患者身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苍白消瘦的面颊、虚弱无力的体格和敏感多疑的气质。反复无常的病情加上长期的治疗过程,使结核病成为一种恒常的存在状态,正是这种特征使结核病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患了这种病的人,其行为往往也与“高雅”“风雅”等词相关。另一方面,在链霉素尚未发明的时代,肺结核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这种死亡又不是迅疾的、狰狞式的,而是愈发虚弱,逐渐走向衰亡。因此,这样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虚弱、敏感、颓废、哀怨等一系列特质,以及因注定死亡的结局而笼罩的某种神秘色彩,这也是结核病被作家们审美化书写的重要原因。
三、疾病的隐喻与城乡抉择的两难困境
阿毛最初是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保存着中国乡村女性“原始时代的朴质的荒野”[5]40。在出嫁之前,她对于城市的印象是模糊的,以为暂时做着一个“长久的客”,不自觉地从心理上与都市保留有一定的距离。在这里,健康的、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身体状态,隐喻着和谐质朴、宁静优美的传统的宗法制乡村社会。然而一次意外的城市之旅,打破了阿毛自然封闭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她不禁羡慕起肺病女人的生活和遭际。破败的、病态的身体正对应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现代都市文明。然而,当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价值观侵蚀着传统社会所代表的乡村文明时,阿毛原本健康活波的身体状态也被悄然改变,开始与疾病相纠缠。
如果将城里女性所患的肺病归为因受潮湿环境影响而导致的身体器质性病变,阿毛所得的疾病则与之不同。“头是异常的晕眩……大约是由于太少睡眠,太多思虑的缘故”[5]116,她的疾病属于精神性的臆想症和忧郁症。幻想造就的魅力与残酷的现实环境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矛盾冲突,对现代都市生活与灵肉一致浪漫爱情的希求,自始至终牵扯着疾病逐渐伸向主人公的心灵深处,直至外在身体的毁灭[17]。“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被破译的对象”[16]59,这些隐蔽的欲望被看作是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虚荣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城市布尔乔亚式的浪漫爱情生活的向往,导致了阿毛疾病的产生。“那如云的光泽的黑发,那粉嘟嘟的嫩脸……美人娉婷的步法,微微摇摆的腰肢”[5]69,正一点一点苦咬着她充满欲望的焦灼的心。阿毛愈发感到自己与这些城里人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她深深渴望却又无法触及的。
疾病之诱因,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来自患者看待世界以及他对待自己的方式。欲望意识的觉醒使阿毛一反被动的生存状态,不再沉溺于虚无的幻想之中。她开始主动把握起自己的命运,积极调动所有的智慧与心性,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并努力付诸于实践,想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改变现实处境,“似乎手里的工作一停止,那使她感到的极为焦躁的欲念,就会来苦恼她”[5]74。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封建观念下,阿毛对都市生活的热烈渴望又使她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她总幻想着也许小二某天做了军爷,或者从某处发了财,那样就能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然而陆小二除了从原始的冲动里生出一种肉感的鲁莽和戏谑外,并不能给予阿毛任何慰藉与可能。与此同时,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幻想:或许某一天会有另外一个爱她的男人突然出现,把她从小二那里夺去,促成她应享受一切的美梦。当最后自己想要当模特的愿望也被亲人残忍毁灭之时,她的疾病便走向了无法治愈的地步,将她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导致阿毛步入死亡的是肺病女人的离世,这给予她思想上的转变。当眼前所见的幸福瞬间化为泡影,自身始终不能尝着这甘味,她选择吞下火柴杆,以自杀行为结束了可怜的一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导致异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会过程。”[18]现代的历史是乡村逐渐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代表城市文明的机器大生产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乡土的自然经济秩序与文明。阿毛的主体欲望意识正是在城乡抉择的焦虑与二元对立中开始了朦胧地觉醒。正如研究者所言:“《阿毛姑娘》透露出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乡土文明的逼仄与挤压,乡村女性从物欲出发所迸发的一线精神光明,一点理想之光,以及合乎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欲望的清新。”[19]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阿毛的反抗是无力的。她只能选择以死亡来解决内在合理欲望与外部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冲突,从而达到对男权中心话语的消解。
回到文本,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抉择既是清醒的,又是矛盾的。有关现代都市的乌托邦想象已然落空,能唤起审美想象的乡村又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找不到一处合法空间可以释放其内在的欲望意识。疾病是透过人物外在形体说出的、被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感的特殊语言,它是一种自我表达[16]97。而丁玲对阿毛欲望心理和疾病遭遇的正视,更显示出现代女性存在的真实历史图景。这位从精神到躯体都浸透着反叛信念、流贯着模糊的自我意识的乡村女性的抗争,一方面是对实现个体生命本能的欲望意识、灵肉合一的理想爱情的执着追寻;另一方面则是对男权象征秩序、传统家庭及社会现实的颠覆背离,呈现出一个“都市边缘人”被迫感知现代文明,却又被残忍地拒斥在外,“回不去”又“进不来”的生存困境。
丁玲对疾病的另类书写延续了自五四以来的人文关怀,即剖析欲望者的精神本相,凸显欲望者的生命情绪[20]。这种独特的疾病叙事表现出现代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其潜意识里本能欲望的深层觉醒,以及与传统秩序、伦理观念相对立的精神自卫姿态。
注释:
①丁玲早期小说或多或少皆涉及到疾病书写,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里莎菲的肺病、《暑假中》承淑与嘉瑛的病态心理、《自杀日记》里伊萨的“疯疯癫癫”,以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里薇底的忧郁症等。参看张炯编:《丁玲全集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82页。
②“时代病”主要是指一种心理的疾病,然而这种心理疾病往往通过生理的疾病来显现。他们的身体都患有某种疾病,体质孱弱,性格忧郁,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而造成他们如此体质和心理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病态的社会。参看谭光辉:《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③对这种“现代意识”内涵的解读,参看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④在贵族已非权力而仅仅是一种象征的时代,结核病者的面容成了贵族面容的新模型,结核正是高雅、纤细、感性丰富的标志。参看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2页。
⑤龚古尔兄弟在作品《格维塞夫人》中,把肺病称作人类的“高尚的、高贵部位的疾病”。由肺病导致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更使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参看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