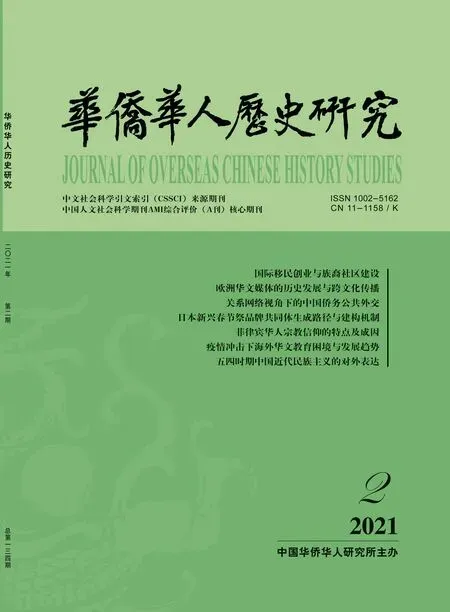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朱东芹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由于近代以来受西方国家长期殖民,菲律宾成为一个宗教氛围异常浓厚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菲律宾华人对宗教也表现出相当的热忱。宗教信仰对华人的观念和行为有着深刻影响,是深入认知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迄今为止,有关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中涉及到菲律宾:如李天锡对东南亚华人民间信仰传播的历史梳理,[1]张禹东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的构成、特征、变迁的理论分析,[2]其中均涉及到菲律宾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另一类是专门针对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前者如洪玉华和吴文焕等对宗教融合现象的探讨,[3]陈衍德对宗教信仰原因的探讨。[4]后者则具体到某一宗教,如天主教方面,陈孟利对天主教在华人社会传播历史的梳理,[5]施雪琴对近代天主教在菲律宾本土化过程中华侨皈依的探讨,[6]吕俊昌对西班牙统治时期华人皈信天主教动机的分析;[7]基督教方面,上官世璋对华人社会基督教早期发展史的探讨,[8]程露晞对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历史的梳理;[9]佛教方面,传印法师对佛教在菲律宾发展历史的梳理,[10]陈孟利对佛教寺庙现状的探讨,[11]胡沧泽对佛教在菲律宾发展情况的分析。[12]总的来说,目前有关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仍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资料主要源于历史文献,田野调查明显不足;内容涉及早期历史的居多,对现状的研究较为稀缺。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近几年多次赴菲律宾田野调查所获资料,对华人宗教信仰的现状及特点加以介绍和分析,探讨其成因,以深化相关研究。
一、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现状与特点
1975年菲律宾和中国建交前夕,马科斯总统为解决华侨效忠问题,放宽入籍政策,华侨在短期内大量加入菲律宾国籍,“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人社会”,当地化加速发展。此后,伴随代际更替,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趋势更加明显,而社会变迁也对菲律宾华人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菲律宾天主教信徒占总人口的79.7%,基督教①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正教即东正教)以及新教和其他一些小的教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基督教一般采狭义的说法,即指新教。本文均取此意,不再另作说明。(包括新教及其他独立教派)信徒占12.7%,伊斯兰教信徒占5.8%,其他宗教占0.8%,不信教或无神论者占1%。[13]整体而言,在今天的菲律宾主流社会,天主教是绝对的优势宗教;基督教居其次,具有一定实力;而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这同时也是当前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一)天主教居诸信仰之首
1565年,西班牙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天主教随即进入并迅速传播。针对华人的传教始于1579年。为了便于管控,政府通过给予税收、居留、迁移和通婚等特权的鼓励性政策,吸引华人皈信。[14]到1751年,已有约5万华人受洗,[15]但华人大量皈信是在二战之后。1948—1951年,大批西方传教士撤出中国,[16]其中一部分前往菲律宾,极大地充实了当地从事华人教务的神职人员队伍。由于回归中国无望,一些人决意扎根当地。1952年,专门服务于华人的堂区在宿务和怡朗建立,之后,此类堂区在菲律宾全国兴起,引发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天主教事工热潮:华人堂区和教务中心数量剧增,分布广泛,覆盖全国。②1951—1997年,菲各地新建天主教堂区及教务活动中心共31个,绝大部分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见菲华教务编委会:《菲华教务五十年(1949—1999)》,马尼拉:菲华教务编委会,1999年,第13~14页。华人事工兴起,中菲建交后华人当地化加速,伴随代际更替、华裔新生代的融合加快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天主教成为华人主要宗教信仰的局面。
目前,全菲华人天主教堂区共有19个,其中,6个在大马尼拉区,③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都市区(Metro Manila)由马尼拉、奎松、马卡蒂、加洛干等17个市和行政区构成。华人区位于马尼拉市,即小马尼拉。全菲华人神职人员共700多人,相对于较大的服务范围和较多的服务对象,神职人员总数偏少。[17]就信众而言,天主教在华人社会最具优势。著名华人学者吴文焕先生这样描述菲华宗教信仰:“年青人信仰天主教较多,也有受父母影响信仰佛教的。但总的趋势是:结婚百分百上教堂,信佛的也去;小孩子周岁也一定要上教堂洗礼。”[18]其他受访者也都表示,由于天主教是“国教”,所以华人信教首选天主教。虽然菲律宾没有针对华人宗教信仰的普查数据,但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数据能够提供佐证。如洪玉华在1995年、潘毓玲(Yu-Ling Pan)在2000年、章石芳和卢飞斌在2008年的调查中,华人信仰天主教的人数占比分别为70%、75%和62.2%,[19]居诸宗教信仰之首。从信仰的状态看,与主流社会大多数信徒为“名义上的天主教徒”[20]相似,华人信徒大多也是“名义上的”而非信仰意义上的信徒。光启学校①菲律宾著名华校,由离华赴菲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于1956年创办,以中国明晚期科学家、农学家、天主教徒徐光启之名命名。的校长陈孟利先生是已经接受圣职的神父,他这样谈及华人的天主教信仰:“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大部分人会信仰天主教。但很多教友是‘文化教友’(cultural catholic),也就是说,会在生活中有大事的时候去教堂,比如办结婚典礼,家里有人去世要做仪式,庆祝生日,为家人祈祷祝福等,就会去教堂,至于是不是每个主日真的都会去教堂‘望弥撒’,也不是大多数人都会去。”[21]可见,天主教信徒中虔诚的信仰者并不多。从教会的活动来看,由于信徒众多而神职人员偏少,加之华人教堂亦为社区教堂,需要服务包括华人在内的全体社区居民,因此,华人天主教会的工作主要在于日常的教务,其他社会活动如公益活动则较少组织。
(二)基督教呈加速发展势头
基督教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被禁止进入菲律宾,大规模传播是在1898年美国统治开始之后。由于天主教在菲律宾已有深厚根基,基督教将传教重心放在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群体上。1903年,圣公会②即“安立甘宗”(Anglicanism),属宗教改革新教三大教派之英国国教。教义多持守基本的新教信仰,但在礼仪、教制上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传统,如实行婴儿洗礼,实行主教管理制,被认为是“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或“最接近天主教”的教会。在华人区成立首家教会,初期信徒较少且教派背景多元。1929年,由于不适应圣公会的礼拜仪式,加之人际关系冲突,一些来自闽南的长老会③又称“归正宗”,属宗教改革新教三大教派之加尔文宗。由于实行长老制,由信徒推选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故名。礼仪上追求简朴,排除祭台和圣像等繁文缛节。信徒脱离圣公会,另组中华基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所。④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创办的本土教会,国内称聚会处、地方教会、小群,海外称聚会所、召会。与传统教会的差异主要包括:在组织上反宗派,主张每一市镇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各教会相互独立;在人员构成和管理上主张平等,不设牧师,信徒间互称兄弟姐妹;礼仪上坚持基要主义(对圣经的每一字句都绝对信仰),注重宣讲教义,不重礼拜仪式等。之后,这两个教会发展成为华社较有影响的基督教会。二战后,加强宣教,教会规模均有所扩大。1986年后,随着政局的宽松、华人经济的起飞以及华人融入的推进等,社会环境对华人更加有利,基督教会也进入加速发展期。
目前,华人基督教教派众多、堂会林立。就规模和实力而言,最大、最强者首推中华基督教会,拥有包括位于马尼拉华人区总部在内的遍布菲国的30个分支机构,以堂会和支会⑤一般先设立布道所或福音站,稍具规模后成立支会,支会在经济上能够自立时,就独立成为堂会。为主,其中,13个在大马尼拉区。[22]总部约有信徒2000~3000人,包括牧师在内的工作人员约30人;外省信徒约4000多人,牧师约70人;全国信徒共约7000人左右,为大型教会。[23]其次为基督徒聚会所,目前在全菲共有11个聚会所,其中,8个分布在大马尼拉区,华人区聚会所有长老6人,同工10多人,信徒几百人;全国共有长老和同工约100人,信徒约4500人,为中型的教会。[24]再次为华侨浸信会,全国共有约10个教会,其中2个在大马尼拉区,目前有3位牧师,信徒约500~600人,由于有人已移民外省或外国,经常参加仪式者仅100多人,属小型教会。[25]从宣教来看,基督教会普遍比较积极,除日常定期的布道会、门徒训练、见证分享会、探望等形式外,不定期的布道会也较为频繁,信徒个人传教也较为活跃。随着科技进步,各教会在宣教中借助电话、电视、电脑、平板电脑、投影、智能手机、同声传译器等电子设备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中华基督教会由于较有实力,除了开通福音专线电话外,还在当地有线电视台购买时段,转播基督教电视台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 TV)和好消息(GOOD TV)的节目,辅助传教。
(三)华人传统宗教渐趋式微
本文采用张禹东对“华人传统宗教”的界定,认为“源于中华文化系统,并且成为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形式”的宗教文化即华人传统宗教,具体包括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儒教①源自儒学(儒家思想),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儒教”,在印度尼西亚称“孔教”,在菲律宾并无此说法。等。[26]这些宗教信仰在近代随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成为华人慰藉情感、维系认同的重要媒介,在第一、二代华人中有较多信仰者。近些年,随着代际更替、融合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加速,华人传统宗教遭遇较大冲击。
2019年暑期,笔者在菲律宾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仍开放的民间信仰庙宇有供奉关帝的关夫子庙、供奉包公的包王府、供奉王爷的镇池宫和镇海宫、供奉保生大帝的宝泉庵、供奉顺正府大王公的青阳石鼓庙和供奉广泽尊王等的大千寺。除关夫子庙香火较旺、包王府在节日较多人进香、镇池宫有少数人进香外,其他庙宇均比较萧条,绝大多数门可罗雀。供奉白衣大将军、临水夫人、天封夫人妈、城隍爷等神祇的庙宇均已废弃。进香者以老年人居多,也有少数中年的新移民②主要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赴菲,以闽南人居多,多从事中国商品的经营。参见朱东芹:《菲律宾华侨华人新移民:历史、现状与前景》,贾益民等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228~258页。。民间信仰的颓势毋庸置疑。道教的情况也相似,在马尼拉华人区,除了极少数名为“观音宫”、“佛堂”而实为道观的场所犹存外,其他传统道观已不复存在,而这些开放的道观也殊少人气。
佛教总体情况也不乐观。目前,全菲寺庙共计37座,高度集中在马尼拉(21座),其余分散于群岛各地。[27]由于人才缺乏,仅少数寺庙有男众(和尚)或女众(尼姑)驻寺,大多由居士或菜姑管理。目前,全菲寺庙男众有20多位,其中又以信愿寺最多,有10多位;全菲女众有10多位、带发修行的菜姑10多位;共计40~50位。由于人数不多,所以到了寺庙法会的时候,需要相互借人。[28]就信众而言,根据2015年菲律宾人口普查数据,佛教徒26,346人,[29]占总人口的0.026%,实力非常弱小。华人约占总人口的1.5%~2%,据此则2015年华人约为151万~202万,佛教徒在华人中约为1.3%~1.7%,占比也相当小。就构成来看,目前佛教可分为传统佛教和新兴佛教两个体系。前者以传承经典教义为主旨,弘法也以法会、共修等传统方式为主,因内容和形式较“陈旧”,不为年青人接受。加之代际更替,前辈信徒凋零,信仰群体明显萎缩。菲岛寺庙多属此类,如信愿寺,尽管历史最久、软硬件最好,但近年来信众也明显减少,面临后继无人之危机。[30]后者提出人间佛教之理念,主张佛法服务于现实生活,借助文字、影音、艺术、素食禅茶等多种手段,通过文化、教育、慈善等实践弘扬佛法,较有成效。这种新兴佛教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菲律宾,以佛光山和慈济为代表,前者重文化和教育,后者重慈善,由于致力公益,加之形象展示、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都较为时尚和现代,因此较传统佛教更有活力。但从推广策略来看,新兴佛教将重点放在主流社会:佛光山通过办大学及向菲律宾贫民子弟提供教育机会,以改变菲律宾人对佛教的认知;慈济则深入菲律宾基层社区,开展各种公益项目,以实践传播佛教理念。因此,就现状而言,新兴佛教对主流社会的影响更大。
二、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特点的成因
宗教信仰变迁受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宗教属于文化的范畴,本文拟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对影响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变迁的因素加以解析,以厘清华人宗教信仰选择的复杂动机。文化变迁,即涵化,是指不同文化在接触中相互影响乃至借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美国学者埃费雷特·罗杰斯关注文化互动中创新的传播,他指出:对异文化中创新部分(新观念、新事物或新产品)的采用,取决于它在接受方文化中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等。[31]罗杰斯的观点对于我们考察菲律宾华人的宗教信仰选择具有参考意义,因为华人作为移民进入菲律宾,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移民后裔所承继的华人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宗教信仰亦然,是陌生而异质的,华人的选择其实就是在自身传统宗教信仰和主流社会主要宗教信仰之间,依据上述要点进行权衡、作出取舍。
(一)天主教成为华人主要信仰的原因
华人常以“入乡随俗”来解释对主流宗教的追随,但这个答案过于笼统。笔者认为,华人大多信仰天主教,主要是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是天主教地位的相对优越性,其“国教”地位对于作为移民和弱势群体的华人而言极具吸引力。因为信仰优势宗教可以获得相应资源和利益。早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就有华人为了特权而受洗,或者为了扩展人际关系网络以利事业发展而皈依,[32]这种功利性考虑延续至今。一位教会人士坦陈:“菲华社会,天主教的圣洗圣事,他们也接受,也让儿女们领受,可大多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他们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多次他们藉着孩子领洗,请有钱有势的人做代父、代母(教父教母),以便有助于生意来往。”[33]教会(包括天主教与基督教)还有一种优势资源——教育,这从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新生代的信仰倾向。由于教会学校办学质量较高,吸引了大量生源。①菲律宾马尼拉百阁公民学校校长林文诚先生表示:在选择学校时,一般华人家庭会就近选择,经济条件好的会选择最好的学校,大部分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办学质量高与教会组织严密、有向心力很有关系;此外,教会学校的优势还表现在英文教育办得好,这与它们资金雄厚,能请最好的老师有关。2021年1月19日笔者通过微信对林文诚先生的访谈。根据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②简称“菲华校联”,1993年由128所华校共同组建,为推动菲律宾华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导机构之一。的统计,在大马尼拉地区2018—2019年度仍然招生的40所华校中,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的共11所,其中8所为教会学校;在这11所学校中,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占11所学校学生总数的约69%,其中天主教学校学生约占40%,基督教学校学生约占29%。[34]教会学校虽然并不强求学生信教,但大量宗教知识的传播难免对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影响,不少人因此皈信。正如陈孟利神父所言:“我的父母信天主教,他们是为了在教堂结婚,所以去受了洗礼,但平常没什么活动,比如做礼拜都没有。我们这一代兄弟几个都在光启学校③从在校学生总数来看,光启学校在2005年以后历年仅次于中正学院位居第二;但从变化趋势来看,中正学院的学生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2006年度为6188人,2018—2019年度仅为4181人,同时期,光启生数分别为4152人和4051人,基本稳定。读书,这里有宗教课,所以我们这一代对宗教比较注重。菲律宾很多私立学校是教会办的,所以影响很大。”[35]而这种影响甚至会波及家长,现实中就有些家长本不信教,但因为送孩子上教会学校,开始了解宗教,最终信教了。[36]
二是本土化的天主教与华人传统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观念和制度上较为包容、灵活,世俗色彩较浓。华人传统宗教源自中国宗教,本身有着较强的人本主义倾向,主张重视人的价值、宗教服务于现实中的人。在中国,宗教对统治者来说,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即所谓“以神道设教”;对民众而言,是纾解内心困惑和满足现实愿望的媒介;中国宗教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信仰的纯正性,而是这种信仰所导致的社会效果。[37]可见,官方意在通过宗教更好地管控社会,民众则希望通过宗教寻求心理慰藉和趋利避祸,因此体现出较强的现世性甚或功利色彩,在观念和制度上对信徒要求相对宽松、灵活。因此,民间信仰以及佛教等传统宗教对于经典研习和仪式参与并无严格要求,在菲律宾华社亦然。虽然天主教本身较为传统,观念较保守,组织和制度较严谨,但近代传播到菲律宾后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得不适应当地国情民情——当时的菲律宾还未形成统一国家,社会形态以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部落或村社为主,超血缘的社会组织难以形成控制力;菲律宾地处热带,人民天性自由散漫,不太适应严格的组织制度约束——而呈现出包容、灵活、世俗的特点。施雪琴称之为“民俗天主教”,①从宗教角度看,菲律宾“民俗天主教”的成因在于:当时菲律宾的原始宗教处于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阶段,复杂的多神崇拜、习惯性的(已融入生活、生产之中)宗教仪式等传统难以根绝;传教士奇缺迫使教会普遍对菲律宾人实行集体归化;后续训导的缺乏等。参见施雪琴:《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1565—1898)》,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认为与罗马天主教相比,菲律宾的民俗天主教“不是一种信仰,而更像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融合了天主教信仰与本民族传统习俗的生活方式。从表现形式上看,罗马天主教是神圣的,而民俗天主教则是世俗的,正统天主教引导人们超越现实与追求‘彼岸’,而民俗天主教更多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中世俗的功利,如趋福避难、农业丰收与子孙繁衍等。”[38]可见,菲律宾民俗天主教与华人传统宗教在信仰实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对于华人来说,天主教易于适应,信仰阻力和压力较小。
三是天主教文化内涵的复杂程度(在此可理解为宗教参与的难度)不高。在这方面,天主教也与华人传统宗教类似,并没有很高的参与难度。就内容而言,天主教对于信徒读经典并无硬性要求,只需听神父布道,对是否听得懂不作追究,正因为如此,菲律宾天主教徒的“望弥撒”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对真理不求甚解甚至流于形式的做法。就形式而言,天主教虽然仪式众多,但并不强制要求信徒参加,且需信徒作为志愿者参与的公益活动少,不会对生活带来影响;相反,在菲律宾基督教志工活动多,虽然并不强求参与,但基督教会一般规模稍小,类似熟人社会,不参与活动可能会面对较大的外界压力,因此,相对而言,信仰天主教更为简单,投入成本更小,更易于参与。
四是人口、时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在文化的涵化中,人口(规模和分布)、时间(跨度)、距离(亲密接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39]华人的宗教信仰选择也受此影响。20世纪70年代,随着菲律宾经济的起飞,许多华人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考虑,迁出马尼拉华人聚居区,分散嵌入主流社区,与主流族群混居,这种长时段分散混居的状态更有利于被主流文化吸纳和型塑。
(二)基督教信徒明显增加的原因
在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近年来基督教会都比较活跃,一方面,一些原来的天主教信徒受到感召,转信基督教;另一方面,基督教对年青人颇有吸引力,吸纳了许多年青信徒参与,这些都促进了基督教的加速发展。在华人基督教会,信徒构成除了部分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外,以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初入社会的年青人居多,年轻化趋势较为突出,多数为近些年加入,其中不少为天主教信徒转变而来[40]。基督教之所以在吸收信徒上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主要归因于以下方面因素。
一是基督教在传教方面十分积极主动,更具效率和成绩。而这缘于二者的体制差异。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有统一的管理体系,罗马教廷采用主教制(教区制)管理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由罗马教廷、(区域或全国性)大主教区、(各国)教区和堂区构成的统一架构。[41]在各国,主教团与诸堂区形成隶属关系,本堂神父对教堂事务有管辖权。没有本堂神父的批准,不能开展工作。而基督教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教会间相互独立,有决策和行动自由,不受掣肘,更易于开展工作,效率也更高。[42]可见,在管理体制上,基督教拥有较大优势,正因如此,基督教的传教更为积极而有效,除了教会各种制度性宣教活动外,信徒个人参与传教也非常普遍,形成“全员传教”之形势。而天主教会则保持传统由神父负责传教,信徒并不介入,由于神父还要管理堂区事务,投入传教之精力就较为有限。同样,受惠于灵活的体制,基督教在组织社会活动方面自主且高效,这些活动以公益项目为主,既有针对华社也有针对主流社会的服务,是很好的辅助传教方式。近年来,基督教会吸收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主要在于教会借助举办语言培训班及福音团契等方式为新移民提供了实际帮助,正好解决了新移民进入华社后需要融入却不被接纳之难题。①新侨进入菲华社会后,一度与老侨关系势同水火。原因在于:经济上,新侨主要将拥有价格优势的中国商品引进菲市场,与老侨形成竞争,甚至产生巨大冲击,引发老侨不满;文化上,有些新侨言行举止不够文明,引发老侨批评。虽然新侨与老侨一样大多祖籍闽南,老侨社团也因后继无人需要补充新血,但由于对新侨的负面认知,在初期多持谨慎态度,较少吸纳新侨加入。因此,新侨实际处于移民之初亟需帮助却孤立无援之境地,基督教会的帮助可谓及时雨。而天主教会受体制和人力限制,由教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不多,虽然信徒个人也热心参与公益,但很少与传教相联系。所以,在传教方面,基督教会更具竞争力。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氛围进一步宽松,菲律宾在宗教文化上出现了突破天主教一家独大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正是在此背景下,基督教会在传教上积极主动,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取得了不俗成绩。
二是基督教作为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派别,在形象上较为清新,更受年青人欢迎。一方面,基督教主张“因信称义”、《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信徒皆为祭司,肯定人的作用和价值以及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些都与现代人的价值观相契合,易于得到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以加尔文宗“预定论”②“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只是“选民”,并非全部世人,由于“选民”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对自身的救赎无能为力。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预定论”给基督教徒内心带来的焦虑感刺激了他们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于是将勤勉、节俭、自律和创造财富当作一种神圣的天职,这也助力了基督教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为代表的基督教救赎观型塑了以勤勉、节俭、自律和创造世俗财富为神圣天职的新教伦理观,使得近代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美、英、德等国在经济上颇为成功,成为发达国家之翘楚,基督教也被视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符号、西方化的代名词,受到年青人青睐。近些年,菲律宾信仰人群向基督教的流动还受两个因素的微妙影响:一是信仰动机。在物质富足、精神需求增加时,人们会更看重对纯粹信仰的追求,相较于成为“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基督教无疑更具吸引力;二是高等教育。随着新生代受高等教育者增多,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易于让年青人对基督教产生亲近感。
(三)华裔新生代疏离传统宗教的原因
目前,华裔新生代多追随主流宗教,与传统宗教疏离,加之代际更替,传统宗教信仰普遍式微,民间信仰面临严重危机。其实,华人民间信仰极具包容性,庙宇基本都是多神共祀,祀神数量众多且背景各异,初衷在于满足信徒的多元化需求。按照宗教市场论③由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提出,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如供需原理)解析宗教现象,将宗教系统与世俗社会市场类比,认为“宗教市场”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供给者(教职人员)会竭力为消费者(信徒)奉献产品(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产品的丰富会导致多元和竞争,也会提升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参见魏德东:《宗教市场论:全新的理论范式》,《中国民族报》2006年1月24日。的观点,这里提供了丰富的宗教商品,在正常情况下,充足的供应应该带来市场的繁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随着社会变迁,一些神祇的职能已被时代淘汰,如保生大帝问诊施药、临水夫人助产扶育的职能被现代医学取代;多数神祇具备的断事祈福职能往往与迷信活动紧密联系,在人们教育水平提升后,便不再认同而舍弃。总之,“医学、科学、技术和教育取代了民间信仰作为人们寻求健康和财富的手段;专业书籍和自助书籍而不是祖先的庇佑,成为建立幸福之家的方法。”[43]可见,民间信仰的衰落是时代进步、代际更替、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必然结果。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似,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神祇构成庞杂,加之话语及仪式具神秘色彩,易于形成“落后”、“迷信”之印象,加之缺乏传道的手段和积极性,所以随时代进步而衰微也是必然。
传统佛教后继乏人,许多寺庙仅能勉力维持。以信愿寺为例,僧众要靠中国南安雪峰寺的支持,信众中几乎没有新生代华裔,要依靠20世纪90年代以后赴菲的新侨。[44]佛教式微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改变,弘法一直以传统的法事和共修为主,对年青人缺乏吸引力;教理深奥,弘法仅靠法师,传教范围有限,加之佛教并不主动对外传教,在竞争性宗教环境中不具优势;佛教对信徒读经并无要求,现实中虽有人意欲自学,却由于经典浩繁,义理艰深,自修困难,因此佛教不像基督教(仅一本经典《圣经》)可以通过自修形成信仰。[45]近些年,随着代际更替,老一辈信徒凋零,新生代没有替补跟进,所以目前寺庙只能靠新侨解燃眉之急,但新侨尚在创业期,受限于精力,参与较为随意,因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佛教后继无人之危机。
三、结语
在菲律宾,对于作为移民后裔和少数族群的华人来说,宗教不单是一种信仰,还承担了提供情感支持和维系族群认同的功能。从华人的信仰趋势可以看出,随着代际更替和融合推进地位,华裔新生代在宗教信仰上与主流社会趋同的形势还会继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会选择信仰在主流社会居优势地位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传统宗教信仰式微会进一步加剧,信仰中心的转移表明传统宗教作为华人族群边界标识的作用渐趋消解,信仰人群的流动也预示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和群体形象正在建构。
族群认同,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迄今为止,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种为“文化说”,侧重对族群显性特征即文化特质的梳理,强调族群是特定人群社会文化的载体,除血缘外,包括价值观和语言在内的文化特质是区分不同族群的主要依据。另一种为“边界说”,侧重对族群隐性特征即心理机制的考察,强调形成族群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界,而不是族群共同的血缘和共享的文化特质,而边界由族群互动过程中的自认与他认构成。[46]“边界说”并未否定文化特质对于辨识族群所起的客观作用,但更强调主观的自我和他者认同的决定性作用。“边界说”的观点对于我们考察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颇具参考意义,因为“认同”往往是地理上远离中心或社会上处于低位的族群最为关切的问题,由于地位边缘而弱势,在竞争性的社会中如何自处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边界说”对主观性认同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在现实中弱势族群的一种生存策略,即通过重构自身的族群边界,来优化生存环境。“边界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的视角,华人宗教信仰的中心由传统宗教信仰向主流社会主流宗教的转移,实际上反映了华人作为移民后裔、弱势群体的一种策略性选择:通过信仰上的趋同来模糊与主流族群的边界、减少差异性,以避免被差别化对待。正如有些华人所言:“要做一个真正的菲律宾人,就必须这么做(信仰他们的宗教)。”[47]当然,在现实中,这种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往往与代际更替叠加发挥作用。就现状而言,华人宗教信仰中心从传统宗教向主流宗教的转移还在进行之中,即便这一进程尚未完成,但传统宗教作为华人族群边界标识的作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成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出于文化的建构。[48]对于现代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满足人们宗教因素的需求如对纯粹信仰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人们非宗教因素如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就菲律宾华人而言,信仰人群从传统宗教向主流宗教的流动、由天主教向基督教的流动,即可视为一种构建新的宗教文化和群体形象的努力,其中基督教信徒表现最为突出。如前所述,在菲律宾,与华人传统宗教和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在教义、教规上更加保守、严苛,诸如要求读经查经以及参与较多的仪式和活动,会给世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此刻意提升难度目的就在于拉大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距离,塑造信仰的纯粹性。信仰基督教要面对诸多不便甚至困难,①对于年青华人而言,信仰基督教还可能引发代际冲突。主要表现在:新教不准拜偶像,而中国人有祖先崇拜,华人作为移民尤其重视慎终追远,家中常设祖先牌位,逢年过节也有祭祖仪式,由此造成信仰基督教的子女往往因此与父辈产生冲突。若非为纯粹追求信仰,一般人不会选择。在访谈中,许多基督教信徒谈及自己的信仰时也颇为自信。可见,华人基督教信徒正力图改变华人的文化“原型”、一种旧有的刻板印象:华人是拜鬼神的、多神教的、功利的投机者,同时,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文化形象:华人和菲律宾人一样,信仰主流宗教,是真正的信仰者。这种形象建构往往是通过“我群”优越于“他群”的话语表述来体现,如谈及天主教时称“我们是读圣经的,而他们不是”,而在基督教各教派间,通常也会强调自身的“优势”,比如信仰上更为专注(“以圣经为主,没其他多的活动”),组织上更为民主(“实行大会制,不是少数人决策”),规则上更为严谨(“违规者就开除了,无情可讲”),等等,[49]总之,都在突出自身信仰的纯粹性,试图建构一种以虔诚信仰为中心的新的宗教文化和群体形象。与天主教信徒相比,华人中基督教信徒尚属少数,为弱势群体,然而就信仰的纯粹性而言,与“名义上的天主教徒”相比,基督教信徒又具有优势,惟其如此,这一群体将在目前华人宗教文化和群体形象的建构中扮演积极角色。
[注释]
[1]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2]张禹东:《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增刊;《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世俗化与非世俗化: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的研究》,《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4期;《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等。
[3]Teresita Ang See(洪玉华),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Volume (Vol.1-5),Manila: 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 1990, 1997, 2004, 2013, 2018.
[4]陈衍德:《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
[5]ARI C.DY.SJ(陈孟利),“Building a Bridge: Catholic Christianity Meets Chinese-Filipino Culture”, Jesuit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 Inc., 2005.
[6]施雪琴:《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1565—1898)》,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
[7][32]吕俊昌:《西属菲律宾天主教与华人社会关系的延展与重构》,《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
[8]上官世璋:《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金禧年鉴1929—1979》,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1979年。
[9]陈露晞:《菲律宾华人基督教研究(1929—1975):以中华基督教会为基础》,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0]传印法师:《大乘信愿寺简介·附菲律宾佛教概况》,菲律宾大乘信愿寺,1989年。
[11]ARI C.DY, SJ(陈孟利),“Chinese Buddhism in Catholic Philippines”, ANVIL Publishing Inc.,2015.
[12]胡沧泽:《菲律宾的佛教与华侨华人》,《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1期。
[13]The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 “Largest Religious Groups (Philippines)”, http://www.thearda.com/internationalData/countries/Country_178_1.asp,2020年6月5日浏览。
[14][38]施雪琴:《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1565—1898)》,第98~101,131页。
[15]ARI C.DY.SJ(陈孟利),“Building a Bridge: Catholic Christianity Meets Chinese-Filipino Culture”, Manila:Jesuit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 Inc., 2005, pp.33-40.
[1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3~398页。
[17]2019年8月7日笔者在大马尼拉仙范市光启学校对陈孟利先生的访谈。
[18]2019年7月24日笔者在马尼拉太白大厦对吴文焕先生的访谈。
[19]TeresitaAng Se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Volume Ⅲ., Manila:Kaisa Para SaKaunlaran, Inc,2004, p.181;Yu-Ling Pa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o-Cultural Identity of Some Filipino-Chinese Adolescents in Metro Manila”, Master’s Thesis, Asian Social Institute, the Philippines, 2000,PP.65;章石芳、卢飞斌:《菲律宾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调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20]“菲教会指出教宗来访敦促我们不再只做名义上的天主教徒”,www.asianews.it/news-zh/32292.html,2014年9月30日。
[21]2019年8月7日笔者在大马尼拉仙范市光启学校对陈孟利先生的访谈。
[22]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八十五周年庆典纪念特刊》,[菲律宾]《联合日报》2014年7月12日。
[23]数据来自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2020年11月25日。
[24]数据来自菲律宾华侨基督徒聚会所,2020年11月25日。
[25]2019年7月23日笔者在马尼拉华侨浸信会对杨牧师的访谈。
[26]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
[27]ARI C.DY, SJ(陈孟利),Chinese Buddhism in Catholic Philippines, ANVIL Publishing Inc., 2015, p.25.
[28]2019年8月5日笔者在马尼拉信愿寺对当家门清法师、普学法师的访谈;2019年7月23日笔者在马尼拉普陀寺对住持道元法师的访谈;2019年8月6日笔者在马尼拉佛光山万年寺对当家觉林法师的访谈。
[29]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2015 Census of Population, Report No.2-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Manila: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7, p.63.
[30]2019年8月5日笔者在马尼拉华人区信愿寺对门清法师的访谈。
[31]参见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33]菲华教务编委会:《菲华教务五十年(1949—1999)》,菲华教务编委会,1999年,第15页。
[34]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菲律宾华文学校各校学生人数统计表(2000—2019)》,由百阁公民学校校长林文诚先生提供。
[35]2019年8月7日笔者在大马尼拉仙范市光启学校对陈孟利先生的访谈。
[36]2009年1月25日笔者在马尼拉对周女士的访谈。
[37][41]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99页。
[39]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碰撞与交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40]2019年8月7日笔者在大马尼拉仙范市光启学校对陈孟利先生的访谈;2019年7月23日笔者在马尼拉华侨浸信会对杨牧师的访谈。
[42]2019年8月7日笔者在大马尼拉仙范市光启学校对陈孟利先生的访谈。
[43]约瑟夫·谭穆尼:《华人社会的宗教市场》,方立天:《宗教社会科学(2008年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44]2019年8月5日笔者在马尼拉信愿寺对当家门清法师的访谈。
[45]2019年8月5日笔者在马尼拉信愿寺对普学法师的访谈。
[46]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2~346页。
[47]2013年7月30日笔者在马尼拉市黄帽子披萨店(Yellow Cap Pizza)对许先生的访谈。
[48]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0页。
[49]2019年7月21日至8月10日笔者在马尼拉华人区对基督教各教会人士之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