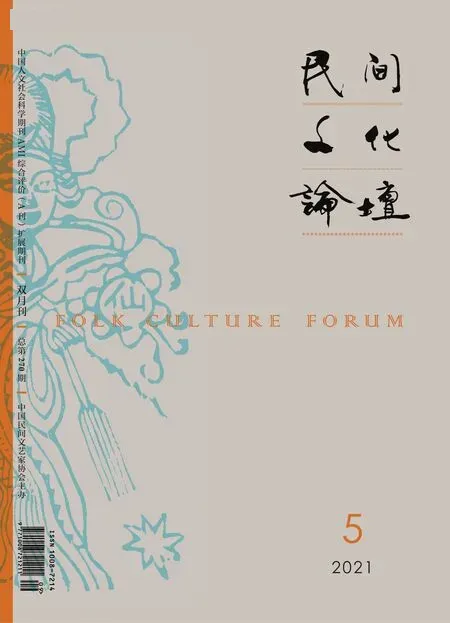“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亚民间文学研究
—— 兼评《东方民间文学》
吐孙阿依吐拉克
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项目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的最终成果——《东方民间文学》于2021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阐述了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印度、伊朗、阿拉伯、巴基斯坦、中亚、东南亚等地区以及希伯来(犹太)民间文学研究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为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民间文学作为单独一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编写。该部分概述了中亚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与叙事诗、歌谣以及辞令等文类,内容涉及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中亚五国的民间文学,给读者呈现了中亚民间文学的整体概貌。本文以《东方民间文学》为基础,讨论中亚民间文学及其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一、“中亚”及我国的中亚民间文学研究概况
“中亚”历来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地理划分,也是一个文化区域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地理范围。a[巴基斯坦]A.H.丹尼、[俄]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第368页。“中亚”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于1843年提出。“洪堡认为中亚的地理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前苏联学者认为中亚一词专指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b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学术界对“中亚”的界定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广义“中亚”的范围界定尚未达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联解体之前,即1978年在巴黎召开专家会议,根据气候和风俗,指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伊朗东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以及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a[巴基斯坦]A.H.丹尼、[俄]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芮传明译,第366—368页。相对而言,国内外学者对狭义“中亚”的范围日趋百喙如一,即认为“中亚”是以阿姆河及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主要包括当代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b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即“中亚五国”。我国相关词典对“中亚”的解释是:“狭义仅指中亚细亚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四个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南部。”c阮智富、郭忠新编著:《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狭义上中亚五国的界定逐渐被学界普遍接受。
从文化层面来讲,中亚是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区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d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亚民间文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枢纽,中国、印度、希腊、阿拉伯等几大文明在这里碰撞并交融,造就了中亚独特的多元文化。语言方面,除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一部分民族外,中亚大多数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同一个语族。这些民族历史上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等文字。e参见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概论》,《满语研究》,2013年第1期。从诸语言的亲疏度看,哈萨克语与吉尔吉斯语相近;乌兹别克语与维吾尔语相近;土库曼语与撒拉语相近。从语言沟通度看,这些语言在日常交际中彼此能够通话,但沟通程度有差异。f参见赵明鸣:《中亚五国语言及其使用情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7日,第4版。因此,这些语言的民间文学构成了中亚民间文学的主体。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中亚既有各国独特的文化特色,又是欧洲型、欧亚混合型和东方型文化的融合。g参见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0—231页。各国文学也长期在交融和渗透中发展,在自身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产生有机“共同体”,彼此共享一些文化遗产和文学作品,有时难以对各国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清晰的地理划分,尤其神话、史诗作品的源流问题。如《东方民间文学》所述:
如今的中亚民族,很多都是由一些源自漠北的原始部落和世居中亚的古代原始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长期以来,他们都以游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改宗伊斯兰教之前,这些民族中还都长期存在萨满信仰;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也大致相同。因此,在这些民族中流传的一些古老神话、传说、史诗,在结构、情节、母题等方面都具有很多共性。h同上,第232页。
有鉴于此,《东方民间文学》中,“中亚民间文学”以“中亚五国”的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展开了宏观描述和系统阐释。本文也沿用了此观点。
东方民间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方民间文学来讲,中亚民间文学同样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据何辉斌统计,从1901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翻译了31885册外国文学作品和1580册外国文学研究著作,出版了2391册国人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这三种作品在各大洲的分布比例为:欧洲和北美洲分别占69.85%和14.69%,亚洲则仅占13.31%。3万多册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中,中亚所占比例更小,吉尔吉斯斯坦5册、哈萨克斯坦2册、土库曼斯坦1册。文学研究类著作中,亚洲有153册,其中没有中亚五国的著作。国人撰写的2391册外国文学研究图书中,有125册涉及亚洲10个国家的文学,同样没有研究中亚五国文学的作品。i参见何辉斌:《中国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总貌的量化研究》,《东吴学术》,2015年第6期。我国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虽颇丰,但与其他领域相比,中亚文学的研究仍然极其薄弱,涉及中亚民间文学的更微乎其微。同样,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学者在各级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亚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有六十余篇,其中除了一些跨境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外,对中亚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寥寥无几,超越具体国别的整体研究少之又少。中亚民间文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仅限于少量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学科发展的需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从中可以推测,中亚民间文学研究较为滞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亚文学译介束缚了广大学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导致了中亚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单一、方向千篇一律。可以说,中亚民间文学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亟待研究的“一隅”,对其进行研究是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中亚关系迈向崭新的发展阶段,中亚研究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对中亚各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化,对中亚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幅增长。作为了解中亚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窗口,中亚民间文学的研究愈发凸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只有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亚民间文学》,其可谓这一研究领域的凤毛麟角。a参见多洛肯:《中亚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籑》,《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在《东方民间文学》的中亚民间文学部分,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勾勒出了中亚民间文学及其研究概况。
二、中亚民间文学主要体裁的研究
文类(genre)一词源于法语,根据《牛津文学术语词典》的解释,文类指写作的类型。文学文类是书面作品可辨认并公认的分类,它是通过一定的惯例使读者不把它与其他类别混用。bChris Baldick,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0.显然,此定义的出发点是书面文学。其实,文类要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人的讲述活动与文本制作过程决定的。
讲述者与听众的关系、讲述时间、地点、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造成文类界定的变化…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教科书中定位清晰的民间叙事文类……以往对于民间叙事的模式化分割遮蔽了背后真实存在的叙事关系与社会结构。文类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为具体的文本绑定带有客观真理性质的符号,而在于将语境中的讲述活动视为阐释社会文化表达的一种途径。c刘先福:《民间叙事文类的界定与转换——以查树源的“罕王叙事”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随着口头传统理论的日渐成熟,学者从民间文学研究实践出发,不断更新“文类”的界定:“传承人基于一种由集体传承的习惯性思维,所选用和享受的特定表述方式。”d[日]西村真志叶:《中国民间幻想故事的文体特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文类已“扩展到人类的言语交际的大背景,广渉一切艺术门类、传播媒体、甚至体现在书店的书籍陈列、电视节目收视指南、日常生活的交谈之中”e李玉平:《口头文学视野中的文类理论》,《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从这一角度来讲,“文类”已超出了文学体裁的阈限,发展成了一个跨学科的概念。
中亚民间文学包含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与叙事诗等常见的文类以及辞令、民间笑话、黑萨等比较独特的亚文类。同中国民间文学文类相比,中亚这些文类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国内学者已开展相关研究,其中史诗与叙事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中亚各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女天神创世》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的化身——乌迈(Umay)的创世女神意象与我国传统神话中的女娲有着诸多共性。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可比性较早就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并有了若干成果出版。
史诗和叙事诗a中亚各国的不同民族对史诗或叙事长诗有自己不同的称谓。吉尔吉斯人称史诗作品为“交毛克”(Jomuq);卡拉卡勒帕克、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土库曼人则都将长篇史诗称为“达斯坦”(dastan),其源于dastaˉn。波斯语乌兹别克人称宗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叙事诗为“仗纳麦”(jangnaˉma);中亚各地对史诗演唱艺人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如雅库特人称其为“奥隆霍特”,乌兹别克人称“达斯坦奇”,卡拉卡勒帕克、哈萨克人则称“吉饶”。20世纪前,吉尔吉斯人称玛纳斯演唱艺人为“交毛克奇”,现则称“玛纳斯奇”。参见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第242页。是中亚民间文学瑰宝中的绚丽奇葩,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文类。其最具代表性的有《乌古斯汗传》(也称《乌古斯可汗的传说》,Oghuznaˉma)、《先祖阔尔库特书》(Dede Qorqut)、《玛纳斯》(Manas)、《阿勒帕米西》等。同一部史诗的文本由于其口头性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原因会呈现出篇幅长短不一、艺术性有高有低、结构繁简不等的多种文本状态。比如以书面文本呈现的古老史诗《乌古斯汗传》,只有一百多行的篇幅,而史诗《玛纳斯》则是一部数十万行的口头长篇巨著。b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类型的本土命名和界定——语义学视角》,《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3期。《东方民间文学》中,中亚民间叙事长诗被分为英雄史诗、爱情叙事诗和“黑萨”c“黑萨”(qissä)一词源自阿拉伯语,表示“故事、传说、小说、轶事”之意。参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编:《阿拉伯语的qissa汉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5页。三类。“黑萨”是哈萨克民间文学中较为特殊的类别,是模仿阿拉伯、波斯文学题材创作的叙事长诗,其传奇色彩比较浓郁。
我国不少学者从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视角,对史诗《先祖阔尔库特书》进行了介绍和研究。魏李萍在她《<先祖阔尔库特书>手抄本译介研究史述评》一文中从史诗的手抄本、影印刊布本、转写本、译本等几个方面梳理了该史诗手抄本译介研究史d参见魏李萍:《〈先祖阔尔库特书〉手抄本译介研究史述评》,《民族翻译》,2017年第4期。;2017年,刘钊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祖阔尔库特书>形态句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转写、汉译、语法及索引)》,这是我国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基于Semih Tezcan和Hendrik Boeschoten合作刊布的《先祖阔尔库特书》(现收藏于德累斯顿图书馆的抄本)的转写本,转写并翻译原文,用共时研究法描写其形态句法特征,为广大民间文学和语言研究者提供了较新的研究方法和参考资源;金斯汉•穆哈泰在其《从<德尔色汗之子布哈什汗>看哈萨克族古典叙事组诗<阔尔库特父之书>——古典长诗<德尔色汗之子布哈什汗>浅析》一文中就该史诗在我国哈萨克族中流传的第一部《德尔色汗之子布哈什汗》,分析了哈萨克族民间史诗的“散文化”的叙事特点。《先祖阔尔库特书》主人公不是乌古斯可汗本人,但涉及乌古斯部族的事迹,故也有学者认为,《乌古斯可汗传》和《先祖阔尔库特书》可能是同源。e转引自陈浩:《〈乌古斯可汗传〉版本源流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作为中亚的邻国,我国历来与中亚有较多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和中亚各国共享着不少民间文学作品,比如《乌古斯可汗传》《玛纳斯》《阿勒帕米西》《少年阔孜与巴艳美人》等古老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我国西北地区也广为流传。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了对《乌古斯可汗传》的搜集、转写、翻译以及研究工作,早期学者有耿世民、郝关中、吐尔逊•阿尤甫和马坎等人。耿世民在 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乌古斯可汗传》的完整汉译。a参见陈浩:《〈乌古斯可汗传〉版本源流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1978年,翻译家郝关中等发表了《〈乌古斯传>译注》。阿不都克力木•热合曼、郎樱、张越、力提甫•托乎提、宋晓云、高一惠、马世才、岳燕云、陈岗龙以及陈浩等学者先后发表了相关论著。b参见米吉提•阿布拉:《维吾尔民间达斯坦〈乌古斯传〉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可以说,《乌古斯可汗传》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玛纳斯》在中亚是吉尔吉斯人创作篇幅最大的一部英雄史诗。这部史诗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民间也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起,胡振华、郎樱等老一辈学者在新疆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工作,搜集翻译了《玛纳斯》,并发表了诸多颇有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成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的《玛纳斯》,引起了学术界更广泛的关注。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学者长期致力于《玛纳斯》研究,为我国《玛纳斯》学的推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东方民间文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亮点,是哈萨克、吉尔吉斯、卡拉卡尔帕克、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民间较为活跃的民间文学文类——辞令的阐述。“辞令”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民间分别被称为“舍仙迪克索兹”(sheshendik söz)和“切切尼迪科索兹”(chechendik söz),意思是“辩士之言论”“雄辩的语言”。辞令有韵文和不带韵文两种形式,具有经验性和训诫性,有些辞令还有谜语的特征。从文类上看,辞令与民间格言、谚语、巴塔(Bata,即赞祝词)、哲理诗及机智人物故事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一些学者将这一文类归入对唱文类,也有学者将其归入机智人物故事。《东方民间文学》将“辞令”归类为民间歌谣的一种,指出“辞令在史诗等其他民间文学文类中也大量存在”c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第253—257页。。书中论述的亚文类辞令是对以往的民间文学文类划分的补充和拓展,给民间文学的文类研究提出了崭新的研究课题。
三、关于我国中亚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连接亚非欧大陆的人文交流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中亚五国居于亚洲腹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之组成部分,中亚民间文学研究属“一带一路”研究的范畴。
中亚民间文学反映的是中亚各国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以及不同时期中亚社会状态和时代精神,是我们认识中亚的重要途径。通过浩如瀚海的民间文学作品,认识并感受中亚的语言文化,能够增进我们对“近邻”中亚文化的认识和民俗民情的了解,促进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深入研究中亚民间文学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进展,促进我国与中亚的人文交流和学术对话,为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从学科建设来看,研究中亚民间文学也是对我国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补充。
然而,在东方民间文学研究中,我国对各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并不均衡。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埃及、印度等国家的民间文学在某些特殊领域里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民间文学研究相对薄弱,中亚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极其匮乏。a参见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导论”,第5—6页。从我国学者对中亚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国在《乌古斯汗传》《玛纳斯》《先祖阔尔库特书》等史诗,“阿凡提的故事”等幽默故事以及东干民间文学等方面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是,中亚民间文学的研究仍然缺乏“整体意识、对话意识和跨学科意识”b参见毛莉:《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14日,第1版。,研究方法也相对单一。对中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文类的研究仍然薄弱,尤其是辞令、黑萨、莱提法cLatfa一词源自阿拉伯语,在中亚民间文学中指机智人物故事。等较为独特的亚文类研究则几乎没有。
“东方民间文学,首先应着力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他们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趋同性。”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区域民间文学,是“通过分析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久远的历史接触关系,揭示其共同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显现其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有机整体”d陈岗龙:《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导论)》,陈岗龙、张文奕主编:《东方民间文学》,第5页。。作为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应超越中亚“一国民间文学”,探索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趋同性,关注其普遍性规律,从而深化区域性整体研究。中亚五国在语言上基本能够沟通,在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丰富各自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形成了各国共同的文化特质。因此,中亚五国彼此共享着很多的民间文学作品,且很难考证其起源。《东方民间文学》的“中亚民间文学”部分的撰写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将中亚五国作为一个“文化圈”,将其民间文学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通过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与叙事诗以及民间歌谣等的宏观阐释,展示了中亚民间文学的概貌。《东方民间文学》这本教材无疑是我国中亚民间文学研究乃至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创之作,将东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深化东方文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精神核心、文化心理与行为逻辑,对沟通民心发挥重要桥梁纽带作用。”e毛莉:《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14日,第1版。“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激励与支持、各领域之间的互动与推动,会为我国包括中亚民间文学在内的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开创新的发展契机。我们相信,中亚民间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其研究的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