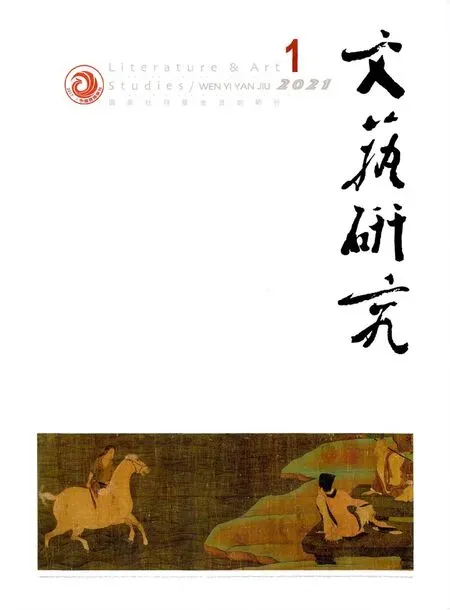《狮子吼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文化建设
谭桂林
据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介绍,《狮子吼月刊》创刊于1940年12月15日。刊物的版权页上注明主办者是广西省佛教会,由狮子吼月刊社编辑发行,桂林三户印刷社印刷,南方出版社负责销售。实际情况是,该刊的主编为巨赞法师,编辑与发行则由暮笳、道安两位法师负责。刊物的主要栏目有:社中座谈、佛学专著、通俗佛学讲座、现代佛教史料、名著介绍、书评、佛教岗位通讯网、佛教文艺以及读者之页等①。可能是由于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战事造成人员变动(该刊停刊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该刊名为月刊,但在第5期以后就开始合期出版,到了1941年12月15日第11、12期合刊后,就没有再出版。现代佛教期刊层出不穷,《狮子吼月刊》办刊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战争时期能够坚持一年,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奇迹。就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建设而言,《狮子吼月刊》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佛教刊物之一。首先,抗战时期创办的佛教期刊并不少,比较著名的如《人间佛教月刊》于1940年元月在浙江缙云城隍山创办,《觉音》1939年在香港创办,《佛学月刊》1939年1月在北平创办,《佛化评论》1940年6月在成都创办等,但只有《狮子吼月刊》一家是专门为抗战宣传而创办的。有意思的是,刊物创办时特地请欧阳渐撰写发刊词,这篇发刊词不长,谈及佛学的特点和学佛归趣在无余涅槃的心得。欧阳渐是现代佛学大师,其言虽然重要,但并非创办此刊物的主要任务,所以主编另外又发表了一个《代发刊词》。主办者在文中明确指出该刊的主要宗旨是用历史的眼光,系统整理全部教理,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建立一套新佛教的基本理论,同时针对敌伪的荒谬宣传,尽量发挥佛教的反侵略思想,在佛教的岗位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所以,该刊可谓自觉肩负起了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建设工作。其次,主编巨赞法师不仅是佛学家,而且是文学家;不仅是佛教徒,而且亲自组织了佛教界的抗战文化活动;不仅与佛教界的青年改革派互通声气,影响很大,而且与新文学家也多有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大批新文化界人士从京沪两地撤退到桂林,如夏衍、田汉、郭沫若、廖沫沙、欧阳予倩、端木蕻良、聂绀弩等新文学家都曾在桂林驻足,他们办刊物、搞演讲、组织爱国诗社漓江雅集等,使桂林一时间成为抗战文化建设的中心地带之一。巨赞来到桂林后,与这些新文学家过从甚密,也参加了漓江雅集的活动。这些联系,包括接受新文学家的建议,邀请他们撰稿等,使巨赞主持的佛教界抗战文化活动成为现代新文化界的抗战文化活动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
一
对大后方抗战文化建设而言,《狮子吼月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加强了佛教界与新文化界之间的联系。清末民初以来,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痛切地感到佛教法运衰颓,积极推动佛教自身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引入世界新潮来重新阐释佛教教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运动及其追随者与新文化的关系就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关系既有相互的影响,如太虚的弟子中不少人读过鲁迅、郁达夫等新文学家的作品和胡适等人的哲学、史学著作、尤其是禅宗史著作,也有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如太虚、大醒、芝峰、唐大圆等都曾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但那时的联系还只是间接的,影响主要来自阅读,而相互的思想交锋往往是隔空对话。太虚和鲁迅在厦门时曾有一面之缘,但在这次宴席上,双方没有直接的互动,太虚到来前佛教徒的夸张声势使鲁迅觉得可笑,虽然在席间他觉得太虚很随和地只讲家常,但先入为主的印象使得他不愿与太虚交谈,而太虚是主宾,也是宴席的中心人物,沉默的鲁迅给他的印象是傲然自得,新文学与新佛教领袖的直接互动也就失之交臂了②。《狮子吼月刊》的创办依靠天时地利,为佛教界与新文学界的直接交往搭起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推动这种交往的功臣当然是刊物主编巨赞法师。巨赞是现代佛教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1908年出生于江苏江阴,俗名潘楚桐,曾在上海大厦大学(即大夏大学) 学习,并结识田汉等新文学作家。1931年由太虚介绍到杭州灵隐寺依却非老和尚出家,1933年后曾到重庆汉藏教理院、南京支那内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等地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正在衡山讲学。“七七”事变后,巨赞深感国难当头,法运颓危,佛教界不能再安心于丛林清修,应对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有所贡献。正如他的《一九三七年冬题宁乡寒铁生余楼》之二诗云:“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③巨赞不仅寄语山林同道,而且身体力行,在衡山组织了佛教界首个“佛教青年服务团”。这个服务团在政治部指导下,和当时部队中的抗剧八队、电影一队一起,奔赴各地为抗战部队募款公演,后来又到长沙等地进行抗战宣传,为阵亡将士举办超荐法会。他们还在《阵中日报》的副刊上出版《佛青特刊》三期,宣传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工作。这些工作打破了佛教出家人不与世事的传统,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这位曾被田汉称为“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④的巨赞法师,在衡山成立佛教青年服务团以及后来去桂林办《狮子吼月刊》,都与新文学界朋友的联系与帮助有关。譬如他在筹划成立佛教青年服务团时,与当时撤退到衡山的田汉、冯乃超、鹿地亘等新文学家相遇。田汉是巨赞在大厦大学读书时就结识的朋友,正是田汉等人将巨赞引荐给当时在衡山主管部队文化教育工作的叶剑英,为巨赞后来成立的佛教青年服务团找到了政治上的依托与指导。在抗战宣传上,他们也有文字上的切磋。据巨赞回忆,他当时拟了一个有关佛教徒参与抗敌救国活动的宣言,准备在《觉音》杂志上发表,“可巧田汉先生和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等五人,也从桂林来了。我在上封寺会见了他。他说:宣言文字太漂亮了,恐怕一般佛教徒看不懂,纵然看得懂,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同情。最好多引用佛教经文,字句也要腐化一点。我们便请他斧正,他答应了”⑤。这段回忆说明了佛教界和新文学界之间的互动情况,巨赞是受新文化影响的佛教徒,所以他在写宣言时有意识地运用新文学的腔调,用词富有抒情性,善于鼓动宣传,但田汉则考虑到佛教界自身的保守倾向,反而建议巨赞字句要“腐化”些,多用佛经义理,这样才能引起佛教界的共鸣。田汉不仅能够提出这样切实的建议,而且爽快地答应修改宣言,可见他在佛理学养与古文修养上的自信。
巨赞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从事救亡工作,在佛教内部的人事关系上多有摩擦,一度曾想超脱纠纷赴印度修习佛学。对此,田汉曾写信去劝阻,信中说:“遽以挫折去今日佛法隳颓、斗争尖锐之印度,在某些朋友中,似反觉吾师道心之未坚,忘此间即是西天之语,以为如何?以汉所感,近来读各方谈佛之书报亦不在少,青年人而着僧衣者亦多,其于抗战之尽力,反不如师等在南岳衡长一带当时之成就。真能以不退转之精神,多少适应时地人事,继续为之必能蔚为风气,造福国家不少。其实际成就必不仅功利意义,或者释迦生于今日中国,亦将为此。”⑥可见,巨赞后来到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为佛教界抗日宣传效力,显然与田汉的劝导有关。正是因为与新文学家的互动,《狮子吼月刊》上经常发表新文学家的作品。据统计,其创刊号发表了夏衍的文章《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田汉的信件《复巨赞法师》,1941年第5、6、7期合刊发表了欧阳予倩的诗《如意歌》 《寄洪深并示寿昌兄》 《别意》 《老婢歌并序》等,1941年第8、9、10期合刊发表了田汉的文章《关于新佛教运动》等。巨赞是太虚新佛教运动积极的响应和推动者,田汉的《复巨赞法师》以及《关于新佛教运动》,都谈到自己对新佛教运动的看法,对运动的缺陷提出了批评与期望。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战前十数年日本政府曾暗中委派许多和尚借宗教交流之名到中国做间谍,勘察地形、了解时事,为侵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夏衍曾留学日本多年,对这种情况有较多了解,他的《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一文,就是要鞭挞部分日本佛教徒助纣为虐的行为。他把日本军国主义叫作“魔道”,把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徒称为“魔僧”。为了阻止战争,弘扬佛法正义,夏衍呼吁对日本人民作狮子吼,唤醒他们的良知,唤醒他们心中真正的佛的和平慈悲精神。巨赞和这些新文学家们也有诗作唱和,1942年,进步文化界曾为郭沫若组织庆生会,巨赞有《田寿昌嘱和柳亚子韵祝郭沫若五十大寿及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一诗唱和,诗云:“微服归来三岛哗,中原到处馥如花。从知沫水滋芳杜,应薄虞山醉苦茶。前日已闻温古史,今朝欣见颂名家。边关未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⑦诗中第一句指郭沫若从日本潜回国内参加抗战,第四句中的“虞山”指降清的钱谦益,因此“苦茶”指的是接受伪职的苦茶僧周作人,可见巨赞对新文学界的典故相当熟悉。田汉更是与巨赞法师交往多年,友谊深笃。据田汉《孩子的“行路难”》一文所述,当年田海男去印度,在佛教圣城寄来精美的菩提树叶,田汉就想到要把菩提叶寄赠给巨赞⑧。巨赞《一九四二年岁暮寄怀桂林田汉》诗云:“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⑨虽只有寥寥数语,但真情溢于字里行间。田汉给巨赞法师的书信,常交换自己对佛教、佛学的观感,其中一封信谈弘一法师:“昨云彬兄招饮,在其案头获见弘一法师涅槃瑞相及绝笔‘欣悲交集’,法悦之中对今日局面仍未免一抹悲悯之情,则知法师真情之至亦智之至也。”⑩对“欣悲交集”一语,当时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多从佛理的悲悯观和涅槃意识来理解,田汉把“悲”的内容引入对当时国家救亡时局的悲悯,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在这封信中,田汉还提到“夏衍兄在《法西斯细菌》剧中提出‘智识分子再出发’之口号,汉殊有同感”,在相互的私人信件中亲切地提到第三者,这些都可以证实巨赞与新文学家的精神联系,可以说,田汉和巨赞之间的这些信件,对研究抗战时期的佛教史以及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建设,无疑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
二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初,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强调文艺为抗敌前线和大后方的普通民众服务。民国以后,佛教界为了广宣流布和佛教教育,创办了不少刊物,这些刊物为提高佛教团体的整体文化水平和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刊物大多是专业性的,内容基本上是弘传佛法、阐析佛理,同时也记载一些著名高僧的活动行迹及相互唱和的诗文作品。抗战爆发唤醒全体国民投身救亡图存的斗争,而普通民众对国家大事从冷漠到热情的转变,更是抗战兴起后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这启示了久负爱国之志的巨赞,他觉得衰颓的佛教要想中兴,必须发动最基层的佛教徒加入救国运动之中。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应该让普通的佛教徒不仅能了解国家大势,而且能互通声气、互相鼓励。所以,他希望全国的佛教刊物都能交流各地佛教在抗战中的生存状况,及时反映佛教徒的抗战事迹。为实现这个目标,《狮子吼月刊》在创刊时,发表《为开展热烈的通讯员运动告各地读者》一文,呼吁大后方佛教徒开展通讯员运动。文章开宗明义就把佛教认定为全国抗战大局中的一个岗位,编者说:“作为全面抗战的一个部门,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岗位自然也有着够多的经验和教训。从三年前的‘九一八’(应为‘七七’事变——引者注) 那一天起,前仆后继的已经有过许多面向血腥的大乘行者的壮烈史实。关于这些,应当好好地记录起来,和其他岗位的工作者互相交换,互相配合。同时,为着培植新佛教运动的工作干部,为着促使抗战最后胜利的早日光临,更有建立佛教通讯网的必要。”⑪可见,《狮子吼月刊》的创刊倡导并促进了战时通讯员运动,为大后方抗战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这篇倡议书中,编者还设计了建立佛教通讯网的具体计划。《狮子吼月刊》积极培养青年僧徒从事通讯员工作,在刊物上发表抗战主题的通讯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狮子吼月刊》还带动了一些重要的佛教刊物积极投入到抗战通讯与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来。佛教徒写作的通讯与报告文学陆续发表,给现代佛教刊物带来了勃勃生气。在抗战爆发后,把抗战救国与救教联系起来,成为爱国佛教团体的共识。佛教刊物上发表的这些通讯与报告文学,真实记录了抗战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岗位——佛教——对抗战的积极投入,显示了民国以后现代佛教徒国民意识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通讯员运动,造就了抗战时期佛教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揭露日寇对中国佛教文物的掠夺与摧残。中国佛教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某些中国佛教的典籍文物甚至只能在日本才能看到,所以近代以来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尤其是民国前后,中国的佛教学者曾掀起一个赴日本高野修习密宗的热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加强了舆论战上的攻势,大力鼓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佛教势力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华北沦陷后,一些陆续创办的佛教刊物具有日本背景。它们宣扬中日之间佛教文化的同源性,并以此作为中日两国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友好相处的基础。由于东亚国家佛教文化传播甚广,佛教徒人数众多,日本侵略者用佛教作为侵略的幌子,有一定的欺骗性。而大后方的佛教刊物上登载的通讯,陆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佛教寺庙的占领,对佛教财物的掠夺,对佛教文物的摧毁,让佛教徒看到日本侵略者不仅不是佛教的保护者,反而是佛教的破坏者。由于这是来自佛教内部的揭露,其效果和影响力远超非佛教刊物。《狮子吼月刊》创刊之际,编辑部同人就表示,“在寂寞的佛教圈内,狮子吼将成为深入祖国广大原野的一支有力的笔部队,阐扬佛的正义,来打击敌寇汉奸的疯狂行为与荒谬理论,在焦土上树立佛教文化的堡垒,从荆棘中,另辟佛教新闻事业的新天地”⑫。从刊物对佛教通讯员运动的大力提倡和佛教抗战宣传方面所做的贡献来看,编辑部同人圆满实现了“笔部队”的宏图大志。
《狮子吼月刊》在倡导佛教通讯员运动的同时,也积极提供版面设立佛教文艺栏目,为投身抗战前线且爱好文学的青年僧人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青年僧人在抗战救援工作中,一边劳作,一边拿起笔来记叙前线的抗战见闻,既为抗战宣传做出了贡献,也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文字修养,对当年佛教界批判“不立文字”的教条,是一种正面呼应。在《狮子吼月刊》上,由于主编与新文学家的密切联系,常有一些非佛教徒作者的作品发表。虽然作者不是佛教徒,但由于发表园地是佛教刊物,作者在创作时往往精心运用佛教的文化典故与僧家意象来表达时代主题。如陆群的诗作《宝剑行——寄赠踏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士兵》,就质问“紧握着金刚宝剑”的日本士兵:“运用宝剑的威力,/残酷的毁灭了中国,/能不能搭救你们的日本?”诗人还希望日本士兵,“睁开自己的双眼”,“奋迅金刚宝剑,/大家对准这危害人类的恶魔,/截取它的头颅”⑬。金刚作为佛教文化名词,指的是护法降魔的力士。日本佛教盛行,侵华士兵中不少人即是佛教徒,既然拿着的是“金刚宝剑”,就应该遵从佛法的和平宗旨,发扬金刚的降魔意志,把降魔的金刚剑锋指向戕害百姓、扼杀和平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诗人的质问与希望,既显现出佛法的威严,也表达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心声。
当然,《狮子吼月刊》最突出的特色还是佛教徒对佛教团体中的抗日英烈的记述与歌颂。在这方面,主编巨赞不仅积极倡导,而且身体力行。理妙法师是牺牲在抗战前线的佛教徒,他曾参加佛教青年服务团,后来奉命赴湘北敌后工作,对于敌情的揭露、交通的破坏,积功甚多。他后来被俘,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最后被敌人挖眼割耳,悲壮牺牲。巨赞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回忆了理妙放弃北京广济寺养尊处优的生活,千辛万苦来参加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往事,以及他第一个报名参加敌后工作的英雄气概。最后,巨赞呼吁:“《涅槃经》上说:为着佛教牺牲在敌人魔掌下面的,命终生阿閦佛国。我相信我们的烈士,现在已经见佛闻法,得到解脱。僧青年同志们!理妙法师替人类打响了永生的晨钟,我们要严肃地纪念他,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各自建筑成佛之路!”⑭此外,暮笳的散文《行者之泪》以书信体的方式描写了佛家弟子明慧和空轮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明慧是一个牺牲在抗战前线的救护队员,从走进“卍”字救护队那天起,就没有离开自己在抗战事业中的“佛教岗位”,把时间花在抬担架、包扎、看护等事情上,即使在救护中遭遇伤员叫骂也心甘情愿。明慧后来受伤被日寇俘虏,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保守着高尚的节操。空轮是潜伏在敌后的我方情报工作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质,空轮不仅负重而且还要忍受同胞的鄙视。明慧和空轮的忍辱负重、坚贞不屈,都是现代公民的爱国激情和佛教徒金刚人格的完美结合。暮笳是成名的佛教徒,他将三封互相联系的书信编在一起,其中所叙事件具有一定的戏剧色彩,里面细微的心理描写、直接坦率的呼告,也都有力地加强了作品的抒情效果。
在中国佛教史上,为高僧大德立传是佛教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梁慧皎、唐道宣、宋赞宁、明如惺都曾编有同时代的高僧传。高僧传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也可以作为头陀修行的楷模,是佛教界弘法宣教的好教材。现代佛教界在高僧传的撰写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如震华的《东渡弘法高僧传》 《入华求法高僧传》《续比丘尼传》等,虚云的《增订佛祖道影》,法尊关于西藏佛教俱善派两位大师的传记《阿底峡尊者传》 和《宗喀巴大师传》,都颇具古代高僧传记的风范,而太虚的《人物志忆》,弘一的《南闽十年之梦影》,大醒的《清代诗僧八指头陀评传》,芝峰的《十五年来生活之片断》,蒋惟乔的《徐蔚如居士传》 《杨文会传》 《谛闲大师传》以及慧云的《照空和尚访问记》等,对自己的修行生活或同时代名僧的生平行迹也多有记叙,为现代佛教的历史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不过这些篇什大多为名僧或名居士所写,记叙的也都是名僧或名居士的事迹,广大普通僧伽的生活缺乏翔实的描写和表现。正是抗战的兴起和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建设,促使现代佛教文学开始关注下层僧侣的生活,尤其是他们中的抗战英烈。对基层普通僧侣抗战事迹的记载,其意义之重要,其价值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普通僧侣乃是佛教的基础,他们的生活、心理、情感显示着佛教生存的真实状态。正是透过这些记载、描写普通僧侣抗战生活的佛教文学,才可以看到佛教界参与抗战的历史全貌。而这类通讯与报告文学陆续发表在佛教刊物上,不仅给现代佛教刊物带来了勃勃生气,而且使佛教自身的改革显现出了时代的亮色。
三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族战争,中华民族各行各业无不踊跃加入,佛教虽然历来标榜沙门不敬王者、出家人不问世事,但在事关民族存亡之关键时刻,一向以金刚精神自许的佛教徒并没有置身事外。因此,不仅在激烈的抗日前线,有理妙、空轮、明慧这样勇于牺牲的佛家弟子,而且在大后方也集聚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佛教徒,为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由于佛教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哲学、历史、文学以及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传统⑮,因而佛教在大后方的文化建设上所做出的成绩尤其醒目。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佛教徒抗日英雄事迹的记载、宣传与褒扬,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佛教徒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界的讨论,显示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建设的多元化与包容性。在这方面,太虚大师迁至重庆缙云山办刊的《海潮音》无疑是佛教思想文化界的执牛耳者,而《狮子吼月刊》对《海潮音》的呼应及其在战时大后方思想文化建设中的独特贡献,也值得认真讨论。
战争期间,在生死攸关之际如何安身立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思考和抉择的问题。对佛教徒而言,是做一个逃到深山丛林中清修的自了汉,还是做投身世间、关心民瘼的现代公民,这种选择不仅关乎气节,而且是一种对身份的理解。在《狮子吼月刊》上,可以看到抗战中的佛教徒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以及他们在身份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勉励和认同感。王恩洋居士在《南游记》一文中,记叙了自己1940年冬去江津拜谒导师欧阳渐的经过。此类题目,如果没有战争,背景又是山川秀美的天府之国,一定会写成一篇清丽脱俗的游记。但在战时,作者的所见所想无不与时代、现实息息相关。有些细节是饶有意味的,如作者途中“遇一幼兵,与同行,吴姓,忘其名,恭敬朴诚,而富同情。与言极亲,举手为别,甚知礼也”。作者感慨地说:“风尘中宁无人哉。”在中国文学中,兵丁形象一直比较负面,“兵匪一家”是中国文学相关叙事中的一个经典范式。抗战军兴改变了人们对士兵的传统观感,即使在戒杀的佛教徒眼中,兵丁都已如此可亲可敬,可见时代精神对佛教徒的深刻影响。这篇游记叙战时的乱离之苦,也颇为感人。“途中遇童子三五成群,树下水边,甚自得者,语非川人,询之为抚婴院难童,皆自江浙来者,深慰其得所。”⑯作者还记叙了自己遇到抚婴院难童的病痛与死亡,表达了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思考。这种对社会苦难的关注,不仅是佛教徒悲悯情怀的流露,而且显示出佛教徒在民族抗战中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代以来,佛教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推动佛教的改革与复兴,但效果不甚显著,因为佛教历史悠久,保守势力根深蒂固,改革派承受的压力格外沉重。这也使得坚持改革的青年佛教徒往往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砥砺士气。《狮子吼月刊》主编巨赞一直追随太虚法师推动人间佛教运动,深深体味到改革的艰难。抗战军兴,他大力推动青年佛教徒走向抗战前线,坚守抗战大业中的“佛教岗位”,却不断遭到佛教界保守势力的挤压。那些与佛教联系密切的文化界人士了解巨赞的心境,纷纷用诗作唱和勉励巨赞。如万民一的《雨中怀巨赞上人》:“文化人中今有子,浑融墓畔久无僧。不离世觅菩提果,乃舍身为暗宅灯。竹屋禅谈容数与,雨山吟槛想孤凭。鲰生苦厄何时度,欲访祇园病未能。”⑰李焰生写有《赠巨赞上人》:“浑融墓畔久无僧,胜景南州被许称。万顷波澜看起落,一般尘法未规绳。艰难衣钵灵明见,寂寞鱼龙感慨增。世纲撄时思有著,新诗欲与证禅乘。”⑱欧阳予倩也作《再步巨赞大师原韵》:“中原豺虎正磨牙,浩劫虫沙未有涯。俚唱砭时宁避俗,微生随处可为家。喜培浓绿新成实,莫怨残春已谢花。抵掌何妨珍敝帚,听泉闲话不须茶。”⑲这些诗歌不仅表达了他们与巨赞的友谊,而且赞许巨赞在国难当头时舍身入世的精神和不受陈规陋习拘束的人格。在这些友人的鼓励下,巨赞放弃了逃世避嫌的打算,坚定了守住“佛教岗位”服务抗战的信念。他的《感赋》篇表示:“道高一尺魔千丈,吠怪憎贤古已然。尼父周游曾削迹,达摩面壁辍谈禅。精金岂却炉锤炼,大任须从穷饿肩。独倚江楼观万汇,春来无处不芳妍。”⑳他还有《汨罗张健甫先生以古风见赠雅健雄深未能和也勉成七律一章报之》一诗:“袈裟不掩伤时泪,每对中流发浩歌。衡岳云封惊夏雨,湘江风起皱春波。幸从八桂瞻文范,且喜三车蕴太和。酬答未能还奉约,山花争发可相过。”㉑此处的“衡岳云封惊夏雨,湘江风起皱春波”句,蕴含着巨赞推动佛教“下山”的故事,而“幸从八桂瞻文范,且喜三车蕴太和”,则记下了新文学家对巨赞的支持与引导。相对于国难民艰,个人的荣辱微不足道,而在抗战大业的洪流中,佛教改革终将顺势而下,随波而兴。所以,无论是“春来无处不芳妍”,还是“山花争发可相过”,都显示出巨赞对佛教改革及抗战胜利前景的信心。这些诗词唱酬,与过去佛教高层常见的文人雅集不同,它不是修禅说道的心得,也不是山居行脚的记趣,更不是品茶论艺的闲话,而是抗战时代大后方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个体的心事里卷舒着时代的风云。
在战争背景下,佛教外部的抗战文化建设深深影响了佛教自身的革新,而改革中的佛教徒不仅坚守自己的“佛教岗位”,而且也尝试积极主动地参与抗战文化建设。《狮子吼月刊》的各种栏目,都显示出编者参与大后方抗战文化建设的自觉与主动。如“佛会小品”栏目讨论信仰问题,主张“在有信仰的人,生死是没有问题的。为了信仰,倾其生命之力(生)、生命之血(死) 以赴之,所谓义无反顾。此精神,即是传道的精神,殉道的精神,有此精神,信仰问题看得重,生死问题倒看得轻了”。“儒家的见解和佛家的见解,有许多是不同。但对于生死问题,却有共同之点。此点就是,传道殉道的精神。儒家的现实,与佛家的理想,其要求,就是一个人生的究竟。此人生的究竟,可以包含了那‘生死问题’。但生死问题,却不能作人生究竟的说明。人生究竟是如何的,那问题才大啊!”㉒战争年代,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如何面对生死就成了人生最为迫切的问题。作者把信仰和殉道的精神联系起来,以佛教的智慧和气度赋予生死以信仰的力量与殉道的精神。
20世纪40年代初,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社会开始弥漫消极情绪,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正如胡风所言:“从武汉撤退开始,战争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候,‘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过程是艰苦的’,才渐渐由理论的语言变成了生活的实感。人民的情绪一方面由兴奋的状态转入了沉炼的状态,一方面由万烛齐燃的状态转入了明暗不同的状态,人民的意志一方面由勇往直前的状态转入了深入分析的状态,兴奋生活开始变为持续的日常生活了。”“在创作上也是这样的。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的强度或艺术力的强度呢?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㉓对于这种社会情绪和文学倾向,《狮子吼月刊》的负责人之一暮笳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在《培植青年的心》一文中指出,“眼前这个时代,真是波澜壮阔活泼多彩的,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可是扮着时代主角的青年,尤其是遭遇双重苦难(为佛法被歪曲地传布民间而受难,为祖国的空前外祸而受难) 的佛教青年,竟有许多在抗战逼近胜利的今日,却一天天消沉起来,甚至有点萎靡麻痹懈倦散漫”。“为什么会走向消沉的路上去?我们的答复是肯定而又简单的,是因为历史的现阶段给予青年太多的烦闷,我们要解决这一代青年内心的烦闷,只有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行程来加以细心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暮笳批判了当时几种企图引领青年的思想倾向,而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行程”的思潮明确地归之于马克思主义:“近一二十年来,德国有名的两位社会运动家的思想,却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上扫荡一切,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是谁也无视不了歪曲不了的,这个思想的最初形成,便是经过黑格尔的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合流,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是谁也无视不了歪曲不了的!人类社会的进化,经过正反合的相续变化,从数变进到质变,而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形成飞跃和突变,旧的一切都转化为新阶段的反对物,在新结的胎盘上仍然保存一部分适合新阶段诸条件的故物。人类历史的演进,就是沿着这个线索而向前推移。”暮笳还强调,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前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青年的心田,都应该是天风海涛波澜层叠的,而不是一个枯寂单调冷漠的死水池。年轻的中国,年轻的佛教,要求每个青年都有一颗健康的心,要求每个青年都能培植一颗健康的心”。当然,暮笳把培植青年的健康的心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并非由于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相信“这用佛法观点来看,也是完全对的”㉔。相信马克思主义与佛学思想具有相通之处,这并非暮笳的独创。恩格斯曾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 才是可能的。”㉕梁启超也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㉖。在暮笳之后,废名更表示过要写一部马克思主义佛学的论著。暮笳的贡献在于他把这种相通性引进到佛法的实践中,希望青年佛徒“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本师佛作,一切愿作,要在庄严而神圣的佛事中,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换一句话,就是参加在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㉗。
结 语
总体来看,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创办的刊物数以百千计,《狮子吼月刊》虽然在佛教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大后方林林总总的文化刊物中,还是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但即便如此,《狮子吼月刊》通过加强与新文化界之间的联系,努力向文化建设的中心区域靠近;通过记叙、描写和反映抗战前线普通僧徒的英雄事迹,坚守抗战事业中作为现代公民的“佛教岗位”;通过积极参与并引导思想文化界的讨论,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建设贡献了佛教的独特智慧;尤其是在对时代新潮的认知上,该刊超越了一般佛教徒乃至某些新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局限,敏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将引领青年走出烦闷的时代。这种边缘刊物所具有的远大志向与敏锐眼光,来自现代佛教文化与新文化精神的结合,一方面显示出佛教改革派受到抗战的鼓舞努力投身文化建设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建设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引领力量。
① 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目录索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太虚:《忆鲁迅先生的一面》,《海潮音》第24卷第7期,1943年7月1日;鲁迅:《两地书·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③⑥⑦⑨⑩ 朱哲主编:《巨赞法师全集》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7页,第1276页,第1353页,第1354页,第1277页。
④ 《田汉先生复巨赞法师》,《狮子吼月刊》第1期,1940年12月15日。
⑤ 巨赞:《奔走呼号一整年》,《觉音》第15期,1940年7月7日。
⑧ 田汉:《孩子的“行路难”——岩下纵谈之三》,(桂林) 《文学创作》第2卷第5期,1943年12月1日。
⑪ 编者:《为开展热烈的通讯员运动告各地读者》,《狮子吼月刊》第1期,1940年12月15日。
⑫ 狮子吼月刊社:《“一支有力的笔部队”》,《海潮音》第21卷第12期,1940年12月15日。
⑬ 陆群:《宝剑行——寄赠踏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士兵》,《狮子吼月刊》第3、4期合刊,1941年3月15日。
⑭ 巨赞:《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狮子吼月刊》第1期,1940年12月15日。
⑮ 严北溟曾指出:“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儒家艺术或道教艺术之类的特定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儒、道思想对文学艺术不发生影响,它们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是很大的,但并不像佛教那么集中和精深,没有出现过佛教艺术那样丰富多彩的特有风格和独立生命。”(严北溟:《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⑯ 王恩洋:《南游记》,《狮子吼月刊》第5、6、7期合刊,1941年6月15日。
⑰ 万民一:《雨中怀巨赞上人》,《狮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
⑱ 李焰生:《赠巨赞上人》,《狮子吼月刊》第8、9、10期合刊,1941年9月15日。
⑲ 欧阳予倩:《再步巨赞大师原韵》,《狮子吼月刊》第5、6、7期合刊,1941年6月15日。
⑳ 巨赞:《感赋》,《狮子吼月刊》第5、6、7期合刊,1941年6月15日。
㉑ 巨赞:《汨罗张健甫先生以古风见赠雅健雄深未能和也勉成七律一章报之》,《狮子吼月刊》第5、6、7期合刊,1941年6月15日。
㉒ 焰生:《佛会小品·生死问题》,《狮子吼月刊》第3、4期合刊,1941年3月15日。
㉓ 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㉔㉗ 暮笳:《培植青年的心》,《狮子吼月刊》第2期,1941年1月15日。
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8页。
㉖ 梁启超:《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饮冰室合集·专集》五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