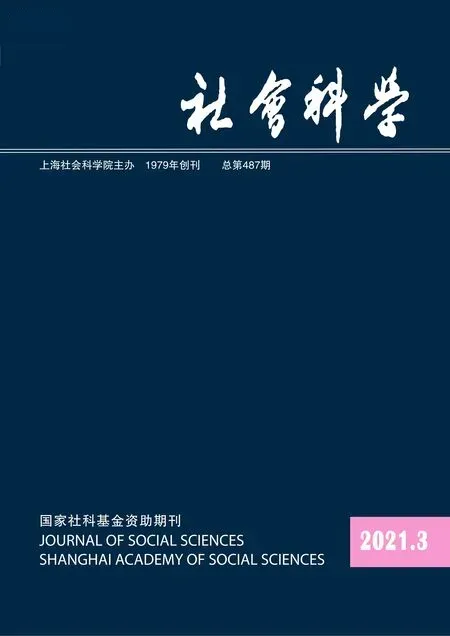对等视阈下外资安全审查的建构逻辑与制度实现*
张怀岭 邵和平
近年来,在美国、欧盟及其核心成员国等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和中美经贸摩擦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以“国家安全”抑或“公共秩序与安全”为由的、单边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日益成为公权力干预企业并购交易的重要法律工具。2017年以来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均对其既有的外资审查机制进行修订或者制定立法规划(1)胡子南:《欧盟首次推出FDI安全审查机制的影响及其应对》,《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简称“FIRRMA”),实现了近十年来首次对外资审查制度的重大修订(2)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https://home.treasury.gov/sites/default/files/2018-08/The-Foreign-Investment-Risk-Review-Modernization-Act-of-2018-FIRRMA_0.pdf, last accessed on 26 Nov.2019.。2019年2月14日欧洲议会审议通过了《建立外国对欧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简称“欧盟新框架条例”)(3)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 (EU) 2019/45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March 2019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Union,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0452, last accessed on 26 Nov.2019.。 实践中,美欧外资安全审查执法逐渐构成中国企业对美欧投资的主要法律障碍,并且成为我国2017年之后对美欧直接投资骤降的重要制度原因(4)张怀岭:《美欧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
面对复杂严峻的对外经贸局势,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及其历次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和法治保障并重,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坚持与世界融合和保持中国特色相统一,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坚持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在我国《反垄断法》确立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基础上,党和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审查的政策和法律法规(5)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2月发布《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简称“外资并购安审通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013)、第二次会议(2014)均提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2014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建议加快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立法工作进程;2015年1月商务部就《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外国投资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简称“自贸区外资安审通知”)率先在自贸试验区试点实施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措施;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制定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建立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对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和机制进行了概括性规定;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将“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作为完善对外商投资管理的核心保障措施。据此,我国统一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构建便有了法律依据。然而,《外商投资法》对于外资审查制度仅在第35条作了概括性规定。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2019年11月司法部关于《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并未对外资安全审查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进行具体规定。法律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同时也使得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执法部门行使审查权缺乏明确的指引和约束。那么,该如何实现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再平衡,如何完善以《外商投资法》为基础的、统一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法律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以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美国与欧盟核心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分析近年来其外资安全审查的法律改革和实践动向,在对等原则的视阈下,遵循“审查什么——如何审查——怎么救济”的逻辑思路,就完善我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相关制度(如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审查标准以及法律救济机制)等问题加以探讨,在域内谋求吸引外国投资与保障我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利益平衡措施,在域外尝试建构应对美欧等东道国政治驱动下针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无理的“安全审查”风险的保护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安全审查成为各国外商投资领域的新常态
对等原则,要求一国在依据特定(国际法)规则提出权利主张的情况下,也必须接受该规则的约束。该原则被各个主权国家广泛用于贸易反制措施中,在对方国家不遵守国际法时,限制该法在本国的适用性(6)Fabrizio Di Benedetto,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Law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uropean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October 1, 2017).Diritto del Commercio Internazionale, Forthcoming.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072214.。我国早期的《对外贸易法》《反补贴条例》等法律法规采用“对等限制”这一狭义理解。2019年《外商投资法》第40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规定构成了我国外商投资法领域对等原则的文本确认。在中美经贸摩擦及欧盟对中国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并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的背景下,美欧多国频繁调整其外资安全审查法律制度,强化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或地区投资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监管。统计表明,我国对美欧投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快速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464.9亿美元的峰值,同期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达到370亿欧元(7)卢进勇、李小永、李思静:《欧美国家外资安全审查:趋势、内容与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2期。。由于中国投资的骤增以及一些高科技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投资项目(如美的并购德国库卡)引发美欧东道国的不安与质疑,甚至被视为“史无前例”的威胁(8)Jonathan Masters and James McBri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U.S.National Security,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28, 2018,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foreign-investment-and-us-national-security (visited on August 28, 2019).。自2017年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欧直接投资均出现持续性的断崖式下跌。以2018年为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为53.9亿美元,而对欧直接投资总额仅为173亿欧元,相比2017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40%和60%。究其原因除了我国监管部门强化对我国企业非理性、高杠杆对外投资活动的监管之外,美欧等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强化也是导致中国企业投资骤降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十分明显(9)Lawrence Eaker and Sun Tao,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Is the EU Legal Regime About to Follow the US Model, 9 Frontiers L.China (2014), pp.42-63.。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对中东主权财富投资在美投资活动引发了国家安全担忧,作为立法回应,美国2007年颁布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巩固并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中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经贸实践中,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外资安全审查在不断强化(10)Vivek Tata, Target Boards and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13 S.C.J.Int’l L.& Bus.2016, p.80.。 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至2016年这八年间,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共审查了364宗并购交易,仅对其中两项交易采取了禁止措施(11)Patrick Griffin, CFIUS in the Age of Chinese Investment, 85 Fordham L.Rev.2017, p.1757.。但是,在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干预下,仅2018年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否决了两项针对中国投资者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并购交易。而即便在新加坡博通公司并购美国高通公司的交易中,美国监管部门阻止交易的理由是担心美国企业在5G技术领域丧失领先地位,而不是国家安全威胁。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的FIRRMA通过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延长审查期间、增强组织能力和资金保障以及增设“中国投资报告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活动的安全审查。
与美国法律修订遥相呼应,经德国、法国等成员国动议,在欧盟委员会2017年9月公布《关于制定建立外国对欧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的建议》(简称“外资条例草案”)(12)COM(2017)487 final, availabel at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7/EN/COM-2017-487-F1-EN-MAIN-PART-1.PDF (visited on September 10, 2019).短短十八个月后,欧盟立法机关便批准了《欧盟新框架条例》,并将自2020年10月11日起实施。由于《欧盟新框架条例》对于所有欧盟成员国均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欧盟成员国有义务在过渡期内通过颁布或者修订国内法来保障条例的实施。对于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者而言,欧盟外资安全审查首次呈现出一种以成员国审查机制为基础、欧盟委员会审查为辅助的“双轨制”审查格局(13)张怀岭:《欧盟双轨制外资安全审查改革:理念、制度与挑战》,《德国研究》2019年第2期。。从美欧各国新近的执法情况来看,东道国的投资安全审查已经构成阻碍中国企业对美欧等国投资的主要法律障碍,而这种不利影响可能超越美欧等东道国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
鉴于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基于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稳步实施的目的,有必要秉持对等原则,建构我国以《外商投资法》为基础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在对等的理念下,我国立法者应关注美欧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将政治因素法律化的本质,探索构建有针对性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规制理念,是一个(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在原则上以不同规制工具之间所具备的“功能性等价”为出发点。不同规制工具或不同的工具组合选择是规制功能实现所关注的核心问题(14)Vgl.Jens-Hinrich Binder, Regulierungsinstrumente und Regulierungsstrategien im Kapitalgesellschafts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2, S.50.。 而对等原则在外资审查机制建构中的功能如何检验?本文认为,检验对等原则这一规制工具是否有效的标准有两方面:一方面看对等原则在我国作为东道国对“引进来”的外资所开展的安全审查的实际管理效果;另一方面要看我国投资者“走出去”面对美欧等国的安全审查所导致的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效果。对等原则下的管理效果与应对效果,一内一外,既是继续扩大开放,消除外国投资者来华顾虑,回应美欧等国针对我国《外商投资法》相关制度不当指责的有效措施,也是加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有效途径。
二、当前美欧和我国外资安全审查的适用范围
外资安全审查的适用范围决定了我国国家公权力干预外资并购交易的深度与广度。无论是美国的FIRRMA,还是《欧盟新框架条例》抑或《德国对外经济条例》(AWV),这些外资审查规范立法抑或修法中的共同点是审查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审查触发门槛的一再降低。
(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及其扩张
传统上,美国外资安全审查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目标企业实施的“控制权取得交易”,即“由外国投资者实施或者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实施的、可能导致该外国投资者取得对某家美国企业控制力的所有交易”。这里的“交易”涵盖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并购、对企业所享有的可转化投票工具的并购或者转化、获取投票代理权、合并或者集中、设立合资企业以及使得承租人能够对涉及被租赁企业经营的所有问题进行决策的长期租赁等交易类型(15)Jingli Jiang and Gen Li, “CFIU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 or for Political Scrutiny”, Texas Journal of Oil, Gas and Energy Law, Vol.9, 2013, pp.67-100.。
美国立法者认为,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数量上的骤增、并购目标企业在战略行业上的集中以及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将对外投资“武器化”等,使美国有必要通过FIRRMA来应对因所谓中国特殊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而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16)Patrick Griffin, CFIUS in the Age of Chinese Investment, 85 Fordham L.Rev.2017, pp.1757-1760.。 尽管在立法过程中美国学界存在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权过宽的质疑,但是,该法最终依然将该委员会的审查权限从改革前的“控制权取得交易”,大幅度地扩大到除“被动投资”以外的所有并购交易类型,旨在防止中国企业利用改革前外资审查的缺口实施法律规避(17)刘岳川:《投资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及法律对策》,《政法论坛》2018年第6期。。 修订后的审查范围包括:控制权交易、基金投资交易、不动产交易、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敏感个人信息”的交易和破产交易等。具体措施:其一,所有导致外国投资者取得对一项美国企业控制的合并、兼并或者通过证券市场的并购,包括通过设立合资企业所实现的并购;其二,对以下不动产的购买、租赁或者取得使用权:(1)位于空港或海港区域内或者作为二者的功能区域;(2)临近美国的军事装置或其他设施、美国政府敏感资产;(3)有理由相信相关不动产会使得外国投资者有能力收集相关装置、设施或者资产上从事活动的情报;(4)可以以其他方式使得相关装置、设施或者资产受到监控。其三,外国投资者对下列领域非关联企业的投资:(1)拥有、经营、生产、供应“关键基础设施”或者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2)生产、设计、检测、制造、加工或者开发“关键技术”的企业;(3)持有或者收集美国公民个人敏感信息的企业,且这些信息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方式被滥用。其四,具有以下情形的其他投资:(1)可以导致外国投资者获取美国企业拥有的非公开关键技术信息的投资;(2)使得外国投资者获得美国企业董事会(或同等的业务领导机构)成员权或者观察员资格,或者取得对该机构成员或者观察员的任命权;(3)取得其他非以投票权形式参与(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美国公民个人敏感信息)美国企业决策的权利(18)Sec.1703 FIRRMA.。可见,改革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实现大幅扩张。
(二)《欧盟新框架条例》“双轨制”审查适用范围
1.欧盟成员国的基础性审查权
首先,欧盟赋权成员国各自构建外资审查机制,即“可以基于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考量,维持、修订或者新设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19)Sec.3(1) See Sec.9(2) COM(2017)487 final.。为了最大程度地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国内法方面的外资审查机制,《欧盟新框架条例》设定了“欧盟最低审查标准”,用强制性条款的形式对成员国层面的外资审查框架作了规定,对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透明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基本协调与信息报告制度进行了协调统一。鉴于欧盟各成员国既有的外资安全审查模式的差异(例如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自愿申报与强制申报、独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与非独立的并购控制机制共存),《欧盟新框架条例》并未对各成员国具体审查机构的设置作强制性规定,对此各成员国享有自由立法权。
其次,欧盟成员国各自安排基础审查机制。其中德国和英国的审查模式具有代表性:德国采取以联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简称“德国经济部”)为主导的独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英国传统上并不存在独立的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机制,而是由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在《2002年企业法》合并控制的法律框架下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包括国家安全、财政稳定以及媒体多元化等)对并购交易进行审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英国国务大臣享有对交易进行干预的最终决定权(20)Jonathan Parker and Adrian Majumdar, UK Merger Control, 2nd edition.Hart Publishing, 2016, p.34.。德国经济部根据《德国对外经济法》和《德国对外经济条例》的授权主导针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安全审查,并有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部门参与,安全与情报部门为审查工作提供咨询。所审查的交易范围内,立法区分“跨行业安全审查”与“特殊行业安全审查”两种类型。跨行业安全审查程序中,德国经济部有权审查非欧盟主体取得德国目标企业10%以上表决权(目标企业属于关键基础设施经营者、关键基础设施行业专用软件开发企业、从事法定电信监控措施的设备生产并且掌握相应技术知识的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的企业或者大众媒体企业)抑或25%及以上表决权(目标企业为其他企业)的并购交易。特殊行业安全审查程序中,德国经济部有权针对任何外国(包括其他欧盟成员国)主体对德国的军事装备、IT安全设备企业取得10%及以上投票权的并购交易进行审查。
最后,建立防止外资规避审查行为的法律措施。《欧盟新框架条例》授权成员国维持、修订或者新设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外资对审查机制以及审查决定的规避行为。例如,在对“非欧盟主体”的认定上,反规避措施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将依据其他欧盟成员国法律设立的企业所实施的并购行为也纳入审查范围,即实施并购的主体虽然属于欧盟内部,但是该主体却由一个欧盟外的投资者所有或者控制,那么其在欧盟内部所进行的投资仅是外资进入的一种人为的安排,仍然属于“非欧盟主体”。此立法模式借鉴了德国外资审查反滥用与反规避措施的相关内容:在德国,跨行业企业并购审查主要针对“非欧盟投资者”对德国境内目标企业所实施的并购行为,但为了防止投资者滥用规避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德国经济部有权对住所地位于欧盟的投资者所实施的对德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安全审查,特别是针对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基于规避审查的目的、滥用欧盟法赋予的主体资格,并采取了规避审查的行为。如交易的直接并购方,除了所涉及的并购交易之外,没有从事其他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活动,或者在欧盟范围内没有相应的营业场所、人员或者设备等来展现其持续性的存在。2018年7月,英国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国务大臣向议会提交了《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一项针对立法改革的咨询》(简称《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21)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vestment - A consultation on proposed legislative reforms, p.30, available 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national-security-and-investment-proposed-reforms., 建议通过专门立法构建一种独立于现行《2002年企业法》合并控制机制的“美国式”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其中,该立法建议将建立预防规避审查对象的措施(如资产并购中采用广义资产概念、股权并购中采用抽象的重大影响力或控制标准)作为新审查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2.欧盟委员会的辅助性审查权
欧盟委员会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主体,其审查权仅限于特定的投资类型。具体而言,如果欧盟委员会认为一项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对具有联盟利益的项目或计划产生影响,那么可以向接受此项外国直接投资的成员国发布“立场声明”。所谓“具有联盟利益的项目或计划”的具体范围由欧盟立法者通过概括性的义务性规范与清单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在范围上,“具有联盟利益项目或计划尤其包括那些涉及大量的或者大比例的由欧盟资助的项目或计划,或者欧盟立法所涉及的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关键投入中的项目或计划”。此外,作为新框架条例的组成部分,欧盟立法者将以附录清单的形式对具有联盟利益项目或计划进行列举。目前共涉及包括伽利略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哥白尼计划)等在内的八个项目或计划。同时,为了弥补穷尽性列举式的清单欠缺灵活性的缺陷,立法委托授权由欧盟委员会对具有联盟利益的项目或计划清单进行修订。
基于对特定交易表明立场的需要,欧盟委员会的辅助性审查权还可以要求该计划中或已完成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在的成员国提供必需的信息。成员国应当确保及时向欧盟委员会提供其所请求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1)外国投资者以及计划中或已完成的外国直接投资针对的目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包括其最终的控制人或者股东;(2)外国直接投资的标的;(3)外国投资者以及目标企业的产品、服务和商业运营;(4)外国投资者以及目标企业开展经营的成员国;(5)相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等(22)Sec.9(2) COM(2017)487 final.。
(三)我国外资安全审查机构设置与管辖权重构
1.现行审查机构设置:效率与安全的平衡
关于我国外商投资审查主体的机构设置和管辖权问题,《外商投资法》中并未直接加以规定。而此前商务部《外国投资法(草案)》中规定由国务院建立外国投资国家安全部级联席会议,承担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责。具体由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和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共同担任联席会议的召集单位,会同外国投资所涉及的相关部门具体实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申报即日起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务大厅接收”,从而接替商务部此前在外资安全审查中的窗口职责(23)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19年第4号),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904/t20190430_935337.html.。
基于对等原则,通过对美欧外资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和监管机制的比较考察,我国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构设置应当采取下列重构措施。其一,应当以“法律”确定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机构设置。相较于行政法规,以法律为基础可以保障机构设置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欧盟委员会以及德国经济部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权的基础性法律依据均是国会或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于2011年2月和2015年4月发布的《外资并购安审通知》和《自贸区外资安审通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建立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来承担并购的安全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牵头,并根据外资并购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和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审查工作。基于对等原则考量,我国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作为外资安全审查机构设置的条文依据,显然在法律渊源上比美欧的效力层级低。我们认为,基于我国扩大开放与投资者利益保障的需要,今后我国外商投资立法不宜再授权行政法规进行规定。其二,重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联席会议的组成与工作规则。在对等视阈下,“美国式”外国投资委员会日益成为国际上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主导性模式,我国的联席会议的牵头单位也宜确定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商务部中的一家,确保审查启动的效率。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应纳入司法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国防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整合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的职能,定位于外资安全审查的常设办事部门。为了保障联席会议能够充分履行法定职责,可借鉴美国FIRRMA的法案,为我国外商安全审查机构设立专项预算和编制保障,提供履行法定职责的财力和人力支持。
2.管辖权的重新界定: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对外商投资的界定决定了应受国家安全审查机关审查的交易范围,在公权力的配置方面即为安全审查机关的管辖权问题。在我国既有法律法规中,对“外商(国)投资”的立法界定较为宽泛,既涵盖了并购交易中常见的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形式,又包括绿地投资、协议安排等交易方式。如《外商投资法》中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下列情形:(一)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二)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三)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然而,哪些外商投资应当纳入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审查范围界定了经济自由与公权力干预的边界,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分别设定不同的审查门槛:其一,涉及军事及国防安全领域的投资。其二,其他敏感领域的外国投资,如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的投资。针对前者,不设定审查所必须满足的股权比例、资产比重等条件,一律应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针对后者,仅对导致外国投资者取得实际控制权的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遗憾的是,《外商投资法》并未对监管部门的审查范围以及监管权的触发条件进行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导致涉及外商投资交易审查行为的极大不确定性。如在永辉超市要约收购中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交易中,并购方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和目标公司均于2019年11月11日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该交易启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程序中的)特别审查的《特别审查告知书》。其中并购方永辉超市是否属于外商?其第一大股东牛奶有限公司是否享有控制权?触发国家发改委审查的原因是什么等法律问题的答案均充满不确定性。在历经八个多月后,该交易最终以永辉取消部分要约收购而收场。
在对等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参考美欧的立法模式,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确定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和监管权触发条件。首先,在审查范围上借鉴德国,明确区分构建“特殊行业安全审查”与“跨行业安全审查”的二元审查机制。一是对于特殊行业安全审查,针对涉及军事及国防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且无论股权及资产比例皆纳入审查范围。这也对等美国法新近修订后的监管模式。在特殊行业安全审查中应明确纳入涉及“敏感不动产”的投资,包括以购买、租赁等方式投资临近空港、海港、军事设施以及政府敏感设施的不动产。二是对于跨行业安全审查,则应侧重于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公民个人敏感数据”“大众媒体”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其次,在外商投资触发审查的门槛问题上,对比美国和欧盟立法模式,发现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不再将外国投资者取得对美国企业的“控制权”作为对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前提,可见美国的监管门槛放低;而欧盟《新框架条例》原则上将审查范围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即外国投资者至少获得目标企业10%的表决权的并购交易,同时通过反滥用机制保持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审查的制度可能性。可见,美国法监管模式从达到“控制权”监管向全面审查监管转变,原因主要是基于地缘经济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基于对等原则,我国外商投资立法一方面要维持与德国以及欧盟审查标准的对等性,构建二元审查机制;另一方面,也能对来自美国的外商投资于我国的行为加强安全审查,不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可将证券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和绿地投资形式纳入审查范围。
三、对等视阈下“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其法律表达
(一)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和构成要素
美欧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关于“国家安全”内涵及其立法表达一直是个立法难题。无论是美国外资审查机制中的“国家安全”标准,还是欧盟法所采用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审查标准,都属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其内涵需结合司法机关在个案裁判中的解释方能确定。
欧盟法中“公共秩序与安全”概念的内涵以及适用标准必须受到欧盟法院的审查。如何将“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审查标准具体化,从而保障类案审理的确定性,是欧盟以及成员国立法者共同面临的难题。其中,德国的立法模式比较典型,即采用“一般条款+非穷尽性列举”的规制模式来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标准的适用。首先,“一般条款”针对非欧盟成员国主体并购德国国内企业,或者通过获取表决权的方式实现对德国国内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参股行为,德国经济部有权对相关交易是否威胁德国的公共秩序与安全进行审查。其次,为了强化对外资(尤其是中资)在德并购活动的审查,2017年修订后的《德国对外经济条例》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在被并购的德国境内企业存在所列举五种情形之一的,即有可能构成对德国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威胁:(1)关键基础设施的经营者;(2)关键基础设施行业专用软件开发企业;(3)被委托从事《德国电信法》所规定的监控和信息共享措施,或者生产或者曾经生产过用于从事法定电信监控措施的设备并且掌握相应技术知识的企业;(4)提供云计算服务的企业;(5)拥有《社会法》所规定的电子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组件或服务许可的企业。欧盟立法者继承了德国的这一立法模式。《欧盟新框架条例》第4条认为下列领域涉及公共秩序与安全,应当作审查考虑:(1)实体的或虚拟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能源、交通、供水、健康、通信、媒体、数据处理或存储设施、太空、国防、选举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以及对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至关重要的土地和不动产;(2)关键技术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太空、国防、能源存储、量子技术与核能技术、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3)关键投入品的供应(如能源、原材料以及食品安全);(4)获取或者控制敏感信息的能力,尤其包括欧盟居民个人信息;(5)媒体的自由和多元化。
美国自1988年《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颁布以来,连同其1993年《伯德修正案》以及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均未对“国家安全”直接进行界定,而是一步步对这一概念要素化。美国FIRRMA进一步扩展和细化了对外资安全审查中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包括:(1)相关管辖交易是否涉及所谓的“特别关注国家”,即(以行动)显示出或者表示通过获得一项关键技术或者关键基础设施从而挑战美国在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中的领先地位;(2)外国政府或者外国主体以累积的方式对关键基础设施、能源资产、关键材料或者关键技术的控制或者在这些领域中新近的交易模式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3)外国投资者此前遵守美国法律法规的历史;(4)外国投资者通过对美国工商业活动的控制对美国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能力在质和量上的影响,包括必要的人力资源、产品、技术、材料和其他供给和服务;(5)相关交易多大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暴露美国公民可识别的信息、基因信息或者其他敏感数据,而外国政府或者其他主体可能以威胁国家安全的方式利用这些数据;(6)相关交易是否可能加剧或者导致新的网络数据脆弱性,或者会导致某一外国政府极大地取得针对美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的能力,包括所有旨在影响联邦选举结果的活动。对于美国扩张安全审查的范围,一些学者表达了担忧和质疑,认为以上因素的认定,不仅可能阻碍中国企业对美进行重要的投资,而且也会冲击友好国家对美投资,从而对美国企业的增长和成功起到反作用(24)Rachel H.Boyd, FIRRM: Buy American Products, Or Bye American Products, 19 WAKE FOREST J.BUS.& INTELL.PROP.L.103, 123 (2019), p.121.。
依照我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外商投资法》和现有行政法规将外商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影响”作为国家安全审查的一般标准。同时,辅之以列举的方式对安全审查的内容进行具体化。国务院办公厅《外资并购安审通知》规定:(1)并购交易对国防安全,包括对国防需要的国内产品生产能力、国内服务提供能力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影响。(2)并购交易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3)并购交易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4)并购交易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自贸区外资安审通知》除了将审查的对象从“并购交易”扩大为“外商投资”外,审查内容方面与上述规定相同。商务部《外国投资法(草案)》采取列举的规制模式,项目扩大至11项,且为“非穷尽性列举”。除了前述四项审查因素外,对外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3)对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我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4)对受进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扩散的影响;(5)对我国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影响;(6)对我国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影响;(7)对我国在能源、粮食和其他关键资源方面长期需求的影响;……(8)外国投资事项是否受外国政府控制;……(11)联席会议认为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
再看我国《外商投资法》关于外资安全审查标准的立法不足之处。其一,《外商投资法》在外商投资领域未对“国家安全”这一不确定性概念的内涵进行限定。较之于美国法和欧盟法,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基础上,未对“国家安全”要素化,极大地增加了执法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影响”“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等作为审查因素,既不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可预期的指引,也不能为监管部门合法履行职权提供指引和约束,实践中容易诱发审查权的滥用。其二,“国家安全”作为一般条款欠缺既有司法裁判支撑,而安全审查决定作为“最终决定”,排除了将这一抽象标准借由司法裁判实现的可能性。在对等视阈下,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标准构建,首先应当针对美国与欧盟立法中所列举之安全审查要素抽象出一般的审查标准,从而能够保障监管部门相对灵活地对外商投资所带来的新型安全风险进行及时应对。其次,制度设计上因应美欧立法的新发展,通过非穷尽列举来阐明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的具体范围,并对我国公民敏感个人信息的获取、网络安全、外国投资者与其政府的关系等领域加强针对性的经济政策因素考量。最后通过允许有限度的法律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来实现“国家安全”要素化后发生的审查错误的矫正问题。
(二)国别因素:投资者二元划分的工具
客观上,近年美国和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和保护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美欧外资安全审查有强烈的共性: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表现,甚至部分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条款”)是为中国投资者“量身定做”(25)廖凡:《欧盟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应对》,《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这种基于投资者国别而实施的歧视性待遇,导致美欧的外资审查监管部门将外国投资者划分为“中国投资者”和“其他外国投资者”两种类型,进而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参与的投资实施更加严苛的审查和监管。国别因素是东道国经济政策和政治目的法律化的产物。以德国为例,中国企业在德国所遭遇的监管异常强烈。仅在2017年,德国经济部启动了60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其中大约30项交易有中国投资者的参与,导致2017年中国企业对德直接投资占德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仅为约7%。美欧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的国别因素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
首先,美国外资审查制度中的“中国条款”态度表述强硬和直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引入“特别关注国家”概念。美国对将特定关键基础设施或者关键技术作为国家战略的国家进行特别关注,如中国政府因《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被作为特别关注国家,所以重点强化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行为的审查。其二,在界定“外国投资主体”时,将其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关投资是否在落实该国政府的战略等作为国家安全审查的考量因素。其三,广义界定“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将所有导致外国政府可能控制一家美国企业的交易,或者导致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控制了一家美国企业的交易,以及代表外国政府的实体控制了一家美国企业的交易等均界定为“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四,规定“中国投资报告制度”,即商务部定期向美国国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关于中国实体在美直接投资状况的详尽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1)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总量;(2)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按照交易额、行业、投资类型、政府与非政府投资进行分类;(3)由中国政府投资收购的美国企业名录;(4)受到中国法律司法管辖的美国企业附属机构的数量、雇员人数以及市值;(5)中国企业投资模式分析以及这些投资模式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设定的目标的吻合度;(6)可能对美国商务部合法、合理地收集中国在美投资数据构成障碍的情况。其五,规定“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特定铁路领域投资报告制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应当会同外国投资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国家安全报告,针对外国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在货运、公共铁路运输系统或者城际铁路系统的投资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评估。评估中应当分析这些投资的数量、类型以及如何对国家安全构成影响。
其次,欧盟及其成员国立法中“中国条款”的文本表达较为隐晦。欧盟立法者将外国投资者与第三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判定相关投资是否构成对公共秩序与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这种与政府间关系不仅表现为法律上的投资关系,而且包括事实上为投资者提供大量资助(26)Sec.4(2) COM(2017)487 final.。 依据《新框架条例》,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在判断一项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可能对公共秩序与安全构成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因素:外国投资者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由第三国的政府(包括国家机关和军队)控制,诸如通过所有权结构或者大量的融资支持……。可见,国别因素事实上会导致欧盟外资监管部门对第三国投资者进行了“二元”划分,即来自经济受到政府较强干预国家的外国投资者和其他第三国投资者。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欧盟这一立法的指向性虽然隐晦但相当明显。
我国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应遵循对等原则,进行对等限制。具体而言,在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引入相应的“美国条款”“欧盟条款”等投资者国别条款。为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判断特定外商投资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时将外国投资者的国别,尤其是外国投资者与来源国特定政党或者政府的关系纳入考量因素之中。通过二元划分,即将外国投资者区分为源自美国、欧盟的投资者和源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建立针对美国和欧盟对华投资的报告制度,将美欧所采取的歧视性审查立法和执法措施对等地应用于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中,为实现我国与美欧实质性对等的投资法律环境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对等视阈下外资安全审查救济机制的构建
外资安全审查是对投资与被投资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进行干预和限制。在民商事领域,任何政府干预都应当有合法的救济方式。我国《外商投资法》并未规定投资者如何针对外资安全审查措施进行法律救济,并且规定“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笔者对这一规定进行引申解读:一方面,此规定说明安全审查决定的性质不是司法判决,而是行政行为,但是对于安全审查决定不可复议,说明这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此规定也并未排除交易当事人对监管部门的决定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能性。虽然现行法律法规未规定当事人的任何行政或者司法救济机制,但是通过考察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国的外资审查救济的立法情况,以对等原则为指导,可以建构针对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决定的法律救济机制。
(一)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司法豁免及其例外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对管辖交易进行审查期间或审查终结后,可以依据对相关交易的风险评估情况,采取“中止交易”“将交易提交总统”“通过协议或者设定条件减少国家安全威胁”三种类型的措施。在FIRRMA颁布之前,美国法律并未对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总统的审查决定如何来救济进行规定,仅在《国防生产法案》中规定“总统所采取的行动及其结论不受司法审查”。实践中,该规定导致美国监管部门的决策过于政治化,缺乏司法制约。此弊端在美国监管部门针对华为并购美国3Com以及3Leaf公司的两项交易审查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在“罗尔斯公司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案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变。该案审理法院认为,尽管《国防生产法案》中规定“总统针对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决定而采取的措施和得出的结论”不应受到司法审查,但没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立法者旨在禁止宪法诉讼的审查。因此,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以总统所采取措施程序违法为由所提起的宪法诉讼的可诉性为对象,并认定美国政府剥夺了罗尔斯公司因交易完成而取得的财产利益,而这一剥夺行为缺乏正当程序。这意味着,法院有权对美国总统调查或者禁止威胁国家安全之外国投资的程序予以司法审查(27)758 F.3d 296 (D.C.Cir.2014), at 307.。基于这一判例,美国学界主张法院应当依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对外国投资审查决定实施有限度司法审查的呼声日益强烈。反对的观点则认为,该判例开启了司法干预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危险先例(28)Christopher M.Fitzpatrick, Where Ralls Went Wrong: CFIUS, the Courts, and the Balance of Liberty and Security, 101 Cornell Law Review (2016), p.1113.。 作为对这些争议的回应,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对“司法审查”进行了明确规定。原则上,美国总统依据该法采取的行动或者得出的结论不受司法审查。基于挑战总统采取的行动以及得出的结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仅限于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在此类民事诉讼中,如果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所持有的信息(包括机密或者其他法律所保护的信息)对于案件裁决是必需的,该信息应单方面和秘密地提交法院,法院应当对这些信息保密。
(二)欧盟外资安全审查决定的类型及其法律救济
《欧盟新框架条例》未直接规定安全审查决定的类型,但通过欧盟的“年度报告制度”要求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供以下信息:(1)已审查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进行中的审查;(2)作出禁止交易决定的审查;(3)作出附条件许可交易或者附缓解措施审查决定的交易;(4)已审查以及审查中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投资来源国以及标的额。根据这一规定,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结论往往采取“禁止交易”“附条件许可交易”“设缓解安全威胁措施允许交易”三种审查决定的类型。这与欧盟《并购条例》中所规定的决定类型相类似,并且可以涵盖成员国国内法上所规定的审查决定类型。以德国法为例,德国经济部依据德国《对外经济条例》的规定启动审查程序后,对其认为可能危害德国的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外国投资可以决定“禁止交易”或者“颁布附加条件”的行政命令。
针对监管部门的审查决定,《欧盟新框架条例》以强制性条款的形式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及欧盟内目标企业对成员国监管部门的决定享有法律救济的权利。法律救济机制的具体设置则由各成员国国内法进行规定。以德国为例,首先,法律性质上德国经济部禁止并购交易或者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对交易附加条件的措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对此,并购交易双方当事人有权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其次,由于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以非欧盟第三国对本国企业投资为规制对象,因此,原则上属于欧盟法“资本流动自由”的适用范围。如果间接并购主体由在欧盟境内设立的法律主体完成,在拟进行并购交易能够实现对目标企业“实质性影响”时,原则上也属于“设立自由”的适用范围。欧盟法院受理的前提是,原告的设立自由及资本流动自由受到侵害。因此,交易双方对欧盟成员国国内法院判决有异议,可以以“德国违反欧盟资本流动自由和设立自由之条约义务”为由向欧盟法院提起上诉(29)张怀岭:《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改革内容与法律应对》,《德国研究》2018年第3期。。 最后,无论是在特定并购交易主体针对德国经济部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还是针对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是否违反欧盟条约基本自由的抽象性审查中,欧盟成员国政府都要对于其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及法律措施符合欧盟公约所规定的资本流动自由及设立自由的法律义务承担说明与举证责任。但应注意的是,原告对欧盟成员国国内法及行政行为违反公约义务这一事实要件负有“辅助性的说明义务”,即原告必须对被告可能违反其欧盟公约义务的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举证。
此外,英国政府2018年公布的《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中建议,英国拟新建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应当受到适当、有力和透明的监督,并基于敏感信息保护的需要,拟建立一种特别上诉程序作为司法救济的程序措施。此上诉程序以司法审查原则为基础,仅对监管部门审查过程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由于在国家安全的事项上,政府享有决策权并对议会负责,原则上不应当由法院代替政府进行决策。因此,英国拟建立的安全审查救济机制对可申诉审查决定的类型、上诉理由、司法管辖权、上诉主体以及保密措施等进行规定。其中,司法管辖权上建议任何针对监管部门审查决定的上诉均由高等法院审理。
(三)我国外资安全审查法律救济机制建构
基于保障涉及国家安全敏感信息的原因,《外商投资法》排除当事人针对外资安全审查决定进行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的权利。然而,同样在对等原则视域下,观察美国法和欧盟及其成员国法(如德国、英国)的立法、执法、司法过程,即便监管部门审查决定的结论是最终的,依然赋予受到安全审查的交易方在程序上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这种有限度司法救济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作为经济规制法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性质上属于公权力对外国投资者抑或被投资者的民事权益(物权、股权和契约权利等财产权益)的法律限制或剥夺。在法理上,这些限权措施应当满足“比例原则”,对于行为限制的适合性、必要性与妥当性要进行说明与论证。审查机关作出的限权行为应当符合适合性要求,即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目的实现之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效果;还应当符合必要性要求,在存在多个适当的措施的情况下,应当选择对权利限制或者侵害最小的措施;最后符合妥当性要求,考察对权利的限制与其所实现的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合理的、适度的、成比例的、相称的、平衡的关系”。基于此,立法者必须考虑,完全排除权利主体针对安全审查决定的司法救济,是否走向阻碍经济贸易发展和阻滞资本流通的一面,是否存在其他损害更小的替代性限权措施。美国判例确认,限权措施的正当程序包括告知当事人限权措施内容、事实依据以及提供证据反驳的机会等内容(30)Jonathan Wakely and Andrew Indorf, Managing National Security Risk in an Open Economy: Reforming the Committee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9 Harv.Nat’l Sec.J.1 (2018), p.15.。 欧盟法中,由于成员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构成了对欧洲联盟基本自由的限制,所以欧盟监管部门的审查决定、以及作为基础的成员国国内法都属于欧盟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实践中,欧盟法院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判决中认定,成员国基于公共利益考量通过“黄金股份”而对资本流动自由和设立自由进行的法律限制违反了欧盟成员国的条约义务。我国为了维持《外商投资法》所追求的“投资促进”与“投资管理”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立法应当借鉴美欧立法与判例的经验,“有限度地”允许外国投资者针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决定寻求法律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另一方面,基于保护国家安全敏感信息的需要,美国法以及英国政府拟进行的立法均采取指定专属管辖的模式,而且在诉讼过程中采取特殊的保密措施。如英国拟立法规定,在诉讼所涉及的信息和材料公开后,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将适用所谓“保密资料审理程序”。这与英国2011年《恐怖主义预防与调查措施法》所采取的审理模式相类似。此外,司法机关的审查权应当仅限于形式审查,而不得对监管部门审查决定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其二,赋予外资安全审查当事人有限度的司法救济权,也是对等原则的要求。美国和欧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国,其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不容置疑。未来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反垄断法发展进步和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诸方面,美欧确有我们可学之处。客观上美欧的外资安全审查最新立法和司法判例有限度地认可监管部门安全审查决定的具有可诉性,我国立法不宜秉持国家安全的执法行为享有绝对豁免的权利。但基于对等原则的考量,为了避免在未来缔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应当通过指定专属管辖的司法救济方式,对审查行为的程序正当性问题加以救济。我们建议可诉范围仅允许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瑕疵导致的投资者利益损害,管辖上只能在指定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审理过程采取严格保密措施。而基于否定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基础性行政法规的目的提起抽象行政行为之诉,应当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
结 语
开放与安全的平衡,是各发达经济体外资审查机制改革中的核心考量。我国《外商投资法》也将“统筹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之一。作为外资管理核心制度的国家安全审查也应当保持与对外开放、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平衡。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近年来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革,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各类贸易限制或经济遏制甚至不可避免(31)张守文:《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的完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在对等原则视阈下,构建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外资安全审查联席会议的组成与工作方式,确定我国外资安全审查的适用范围和审查门槛,通过纳入投资者国别因素等具体化的措施,使“国家安全”审查标准不仅具有一般性,而且更加具有针对性内涵和具体适用标准。我国有限度地引入司法救济机制,将不断改革开放和保障国家安全在更深层次中达到发展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