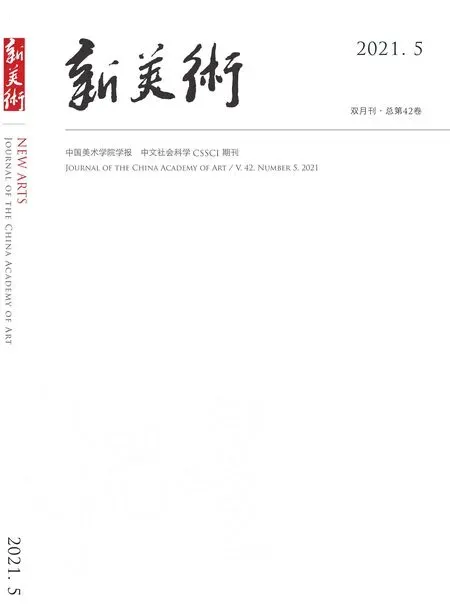《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析论 兼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续编诸问题
李 霏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六册,清道光年间朱善旂编集,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书高39 厘米,宽25.8 厘米,封题“敬吾心室钟鼎款识”,金镶玉装。据朱善旂自书题识,此稿本为道光年间续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产生的两部底稿之一,另一部经龚自珍、陈庆镛、吴荣光先后编纂,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吴荣光在粤刊刻为《筠清馆金石文字》(以下简称《筠清》)。稿本对于厘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续编史实及相关文本、《筠清》编纂过程,提供了一手文献和研究线索。
朱善旂(1800―1855),字大章,号建卿,浙江平湖人,朱为幹之子,嗣为朱为弼(1770―1840)长子,朱善楹、朱善卤兄。以“敬吾心室”为斋名。其父朱为弼,字右甫,号椒堂,一作茮堂,又号颐斋,是阮元抚浙期间最为重要的学术幕僚之一。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下简称《积古》)编定审释实出朱为弼手。朱善旂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官国子监助教,並署博士监丞,武英殿校理。自嘉庆甲戌年(1814)起,侍父游学京师。酷嗜金石文字,“精训诂鉴别鼎彝诸器,又能世其家学,一时好吉金家如陈颂南、吴子苾、何子贞、陈受卿,皆折衷于建卿。”1许乃普(1787—1866,字季鸿,号滇生)语,引自[清]潘衍桐编纂《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三,清光绪十七年浙江书局刻本,叶三十二正。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对于重新审视清代吉金著录文献,有一些值得补充讨论的问题。在迄今所见有关《积古》《筠清》研究中,皆未引用稿本中的内容。稿本因何而来,有哪些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与《筠清馆金石文字》有何异同?本文即以稿本为中心,对勘《筠清》,考察稿本的形成过程、文本层次及文献价值,兼论及清道光年间续编《积古》诸问题。
一 编纂缘起:续《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前有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二日朱为弼题识,原文写在茮堂自制笺纸上;次为朱善旂题识;次为《敬吾心室钟鼎款识自序》,朱善旂作于道光丙午年(1846)五月。稿本未分卷,以器别分类,依次著录钟、鼎、尊、卣、壶、盉、罍、爵、举、斝、觯、角、㱃、觚、彝、敦(□)、簠(瑚)、簋、甗、鬲、匜、豆、盘、铎、剑、削、戈、刺兵、玉刚卯、薰炉、鱼符、鬷等器物的铭文。是本所用稿纸样式不一,每一器类前有一至二叶的器类目录,用红格稿纸誊录器名,后以小字注明器藏某家或某拓本或某摹本。惟簠类器目首行顶格书写“经注经斋续钟鼎款识卷第八”十二字、鬲类器目首行顶格书写“经注经斋续钟鼎款识卷第”十一字,经注经斋乃朱为弼斋号。其他各类器目首行皆空出。正文书写在无栏格稿纸上,每器为一条目,著录格式如下:先写器名,次附注所据拓本或摹本来源,次铭文钩摹本,次释文,而后附考证。字迹多样,非出一手。少数器仅见器名,留出空白而未录入铭文、释文等项。此本行间多有校改、增补,批校间用蓝、朱、墨三色笔。综合分析,《敬吾心室钟鼎款识》尚未完全形成定稿。此本未见刻本,亦未见其他抄本。
卷首有朱善旂题识,详述稿本来历,今迻录如下:
道光乙未秋,阮太傅相国内用还朝,其时京师之好吉金者叶东卿封翁、陈寿卿太史,而吴荷屋京卿、吴子苾编修、陈颂南民部(庆镛)、何子贞编修同好此文,又皆太傅之门生。其时龚定盦(鞏祚)任祠部主事,而夙以博通名。于是荷屋丈欲为相国续《积古斋款识》,属定盦作释文,而徧属诸同好者广搜拓本且助之编籑。相国许之,遂各以拓本钩取备刻,予亦在襄事之列。其底稿共成两部,其一部即此五册是也。内中铭文,予属陶香楞(中桂)叔母舅钩之。其考释大半皆定盦作,予令子达十弟(善楹)书之,予为手校,并自书释文。其逐年增入,采之徐籀庄丈居多,彼本所无矣。
其又一部用太史纸,比此册长而较狭。所书考释皆定盦亲笔。各家虽有考释,皆未入此册内,何子贞、子毅偶注一二语,寥寥不成片段。即定盦亦未器器皆释。其铭文吴子苾出资倩好手精钩。及戊戌年相国予告还里,书尚未成,亦有由有也。盖定盦为人放浪不羁,长苦贫,草此书稿未及半,辄告吴荷翁及太傅,谓此书成可印数百部,交各督抚发首府、首县,定值情售。二公大怒,谓我岂以是市利耶!又定盦释“驶卣”,引段《说文》所引(庄述祖反戊为癸、反癸为戊臆说)之文,以非毁积古斋先大夫所释,相国甚不谓然,手批其册内驳之(今此纸尚存予箧中)。荷翁即取稿本交子苾(囗龚祠部处只丙申及丁酉半年,故龚不能竟其事),及子苾出守,转交颂南囗,公私碌碌,亦未遑多所增益。至庚子三月,吴荷屋丈来园展觐,得致仕罢官,即自圆明园令其郎心畬四兄到颂南民部宅取此稿本,径往粤中刊刻,名曰“筠清馆金石录”。至廿二年壬寅秋刻成。丙午传至都下,予始见之,共五册,较此无所增益,知暮年仓猝所成识者,惜之。其与此不同者,惟分商周时代及多序文与凡例耳。
此文阐明了稿本的编纂缘起——“续积古斋款识”产生了两部底稿,此为其一。这对于勾勒清代彝器款识著录之书的发展脉络,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尤其对考察续编《积古》的过程及考释编纂等细节,提供了重要补充。
细绎此文,道光十五年(1835)阮元回京任职以后,弟子吴荣光(1773―1843,号荷屋)2吴荣光,字伯荣,一字殿垣,号荷屋、可庵,晚号石云山人,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进士,由编修官擢御史。道光中任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后坐事降为福建布政使。倡议续编《积古》,并延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考释铭文,叶志诜(1779―1863,字东卿)、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陈庆镛(1795―1858,号颂南)、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朱善旂等人广泛搜罗拓本,“各以拓本钩取备刻”。至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时仍未编讫,成两部底稿。其一,吴式芬出资请工钩摹铭文,册中考释皆龚自珍亲笔,各家亦有考释,但未入册内,仅何绍基、何绍业偶作注解,书稿几经辗转,道光二十年(1840)吴荣光携至粤中,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成《筠清馆金石录》凡五卷。3《筠清馆金石录》,仅刻印款识部分五卷,“石”部未及刊刻,此书又被称为“筠清馆金石文字”“筠清馆金文”。第二种稿本藏朱善旂处,共五册,铭文由陶中桂钩摹,考释内容多出自龚自珍,由朱善楹誊录,经朱善旂手校。释文乃朱善旂自书。考释文字朱氏亦有增补,采徐同柏之说较多。由此可知,两部底稿的初衷是续编《积古》,乃汇聚诸家所藏拓本钩摹,并非吴荣光在《筠清》刻本凡例第一条所称“此书非续《积古斋钟鼎款识》,亦非续《金石萃编》,不过纪四十六年之所得”。
此文提示我们,应在道光年间彝器考释的历史情境中去认识该稿本的意义。道光十五年二月阮元以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八月入都。次年(1836)二月,吴荣光在湖南巡抚任上因事被命降四品卿至京候补,六月至京,与阮元过从最多,常为万柳堂之游,“半年杖履”“出游共车”。4张雪莲,〈从吴荣光《授经图卷》看阮元思想影响〉,载《岭南文史》2011年第1 期,第51 页。续编《积古》的正式着手,当在吴氏入都以后。此时的京师形成了以阮元为中心的金石考证群体,通过释读金文而考证经义。吴式芬、龚自珍、陈庆镛、吴荣光等常游于阮相国之门。同在都门的叶志诜、朱善旂、许瀚(1797―1866)、汪喜孙(1786―1847)、陈介祺等皆参与续编。是时,朱善旂、吴式芬、叶志诜、何绍基、陈庆镛均居住在京师宣南坊宅邸,龚自珍、许瀚亦寓居于宣南坊。吴、何、龚、陈之间常互观所藏金石古物。
梳理文献材料,续编期间,阮元与诸门生之间金石交游影响力较大的事件主要有二:一为吴荣光绘《授经图卷》(现藏佛山市博物馆)并请题,一为考释齐侯罍(即洹子孟姜壶,现藏上海博物馆)铭。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吴氏补授福建布政使离京,别后摹绘阮师像,于十八年三月绘就《授经图卷》,“图成,传诵至都,都中诸老题咏者十余人”。5《阮氏大理石屏》吴荃选跋语,引自洗宝干编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校注本》(下),佛山市图书馆整理,岳麓书社,2017年,第931页。该年十二月阮元有五古诗和吴氏韵。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吴氏以原品休致。五月南旋,道出扬州拜访恩师阮元,阮元“招游北固山、甘露寺,至焦山观《周鼎》《定陶鼎》《瘗鹤铭》《马殷铜鼓》”,6[清]吴荣光,〈吴荷屋自订年谱〉,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0 页。是时吴氏携《授经图卷》求师重题。阮元得在《积古》成书以后得齐侯罍,因其铭多达一百六十八字足证经史,将之视为家藏吉金第一重器。考证齐侯二罍,是阮氏致仕之前京师金石生活的重要议题。戊戌年(1838)初,阮元重新考释“齐侯罍”,曾致朱善旂札,索朱为弼嘉庆甲戌年(1814)所作齐侯罍释文。1838 至1839年间,又邀吴式芬、何绍基、陈庆镛、龚自珍、许瀚等考释,各家释文互有同异。据中国嘉德2008年春拍拍品《旧拓齐侯罍铭文及阮元书齐侯罍歌卷》,阮元书《后齐侯罍歌》赠吴式芬赴江西南安知府任,并附齐侯二罍拓片二幅,其跋语中提及欲将吴氏释文编入续款识:
子苾年老先生于此铭亦曾释之,与椒堂朱漕帅所释并存,且俟修入续款识也。时子苾出守江西属书此篇。又识。7中国嘉德2008 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Lot2696《旧拓齐侯罍铭文及阮元书齐侯罍歌卷》。《齐侯罍歌卷》,行书,纸本,216cm×24cm。钤印:“阮元”“节性斋老人”“阮元私印”“戊戌”“伯元父印”。据内容,阮元所书实为《后齐侯罍歌》,作于1838年。
考此卷书写时间,当在1838年七、八月间。经过各家考释,齐侯罍被阮元认定为“论语春秋在此罍”(见阮元撰《后齐侯罍歌》)。可知,将齐侯罍铭文、释文及考释予以著录,是续纂《积古》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光己亥年(1839)冬,阮元(1764―1849)在扬州题徐同柏(1775―1854)考释彝器款识的稿本,写道:“其中诸器有未见之文,且审解精确,今都中有续钟鼎款识之作,是册必多采择矣。”8[清]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所言“都中”续作,当即指吴荣光、吴式芬、陈庆镛等人共襄之事。己亥冬是阮元致仕归里的第二年,由此可知,续作当时仍未编讫。
关于《筠清》的编刻和成书过程,以及阮元、吴荣光与吴式芬、龚自珍、何绍基、何绍业金石交游等问题,目前还未见学者有深入研究。朱善旂的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今结合所知文献,略作钩稽。龚自珍为吴氏考释编纂,始自道光十七年春,缘于友人吴葆晋(1791―1860)与廖甡(1788―1870)的推荐。9《定庵遗著·与吴虹生书三》:“荷屋中丞驺从光临,面诿一切,雨中畅读吉金乐石,奇文异字,此皆阁下及廖鹿侪之赐,感何如也。”参见李敖主编,《龚自珍全集·盛世危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4 页。吴葆晋(1791—1860)字红生,号佶人,河南固始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江苏淮海道,署按察使。廖甡(1788—1870),字鹿侪,广东南海人。嘉庆丙子(1816)举人,丁丑(1817)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后迁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都水司郎中。道光十七至十八年间,吴荣光、阮元、吴式芬或因调任或致仕,先后离京,又吴荣光与龚自珍失和断交,致编纂前后时间跨度较大。《己亥杂诗》第七十九首,是龚氏对自己考释款识的感喟,诗中以淮安王刘安比喻吴氏,后悔自己接受了委托而为汇聚拓本、考释款识。尾注即提到吴氏写信请绝交一事,当时书稿已成十二卷,后转至何子贞处。10手扪千轴古琅玕,笃信男儿识字难。悔向侯王作宾客,廿篇鸿烈赠刘安。(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识,属予为之。予为聚拓本,穿穴群经,极谈古籀形义,为书十二卷。俄,布政书来,请绝交。书藏何子贞家。)见[清]龚自珍,《龚自珍诗选》,刘逸生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3 页。
关于龚氏为吴荣光编书一事,潘建国《新见清龚自珍己亥佚札考释》文中已有考。今仅就上图稿本中有助厘清编书史实的部分再加讨论。龚吴失和的原因,与两人对书稿著作权心存异议相关(龚有“来书付刻之举”),11潘建国,〈新见清龚自珍己亥佚札考释〉,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第147—150页。朱善旂的说法——书稿未及半而直言印书交各督抚发售,又考释古器“非毁”朱为弼先前所释——龚氏言语不羁且考释有自负之处触怒阮、吴二人,可资参考。
现存的一些书札资料表明,吴式芬在京期间,为编纂《筠清》亦花费了大量精力,包括考释、搜罗拓本、请工钩摹等。阮元也时常关注续编之作,给出自己的意见,并将阮氏家庙藏器拓本寄予吴氏。编书过程中,二人往还频繁。
1838年六月龚氏撰成十二册手稿,以器分类,并请阮元审阅。阮氏“草草阅过,中夹数签,无十分紧要语”,“又于齐侯器跋尾末亲笔增两语。又于齐侯第二器跋尾中亲笔增两语”。12〈与吴式芬笺〉(十二),引自孙文光《龚自珍集外文录》,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 期,第47 页。阮致吴式芬另一札中,言及已阅龚氏手稿,并询及册中有释文但尚未钩摹铭文的情况:
定庵送其为荷屋所订款识十二册来,阅之甚佳。再此十二册内尚多有释文,而无摹篆之油纸,将若之何?此询。13〈吴式芬藏名人书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 册,叶九。此承尚磊明先生录示。参见尚磊明,《从陶嘉书屋到双虞壶斋:吴式芬与道咸金石世界》,未刊稿。
吴荣光致何绍基札,言及底稿转移、托交何氏继续编纂,可与朱善旂的说法相参证:
……芸师来缄,传子苾之言,欲以金石文代送吾兄编纂,已承惠允,感不可言。又云托陈君庆镛同襄其事。是否必须两人,陈君台甫,便中示及,容再报谢。至定庵来书付刻之举,弟于定庵手稿,并未得见,惟闻稿未尽善,且定庵新交,非知弟者,欲以还之。子苾未出都时已致信,托其原璧归还,如子苾已出京,未见此信,即属小儿呈台端收览也。……仪徵师相属考证《积古斋款识》,谦而未就,今《筠清馆金石文》概蒙允许成书,感谢当何以报耶?专请台安。侍前乞叱名请安,并候子毅近祉,不具。子贞大兄年大人阁下。年愚弟吴荣光顿首,九月十九日。内人附笔请安。14〈吴荷屋中丞荣光手札〉一通。引自罗振玉撰述,《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二)》,辽宁教育出版社,第765—766 页。
吴荣光未见龚自珍手稿,但对之似乎并不满意。内言及子苾出都,则该札写于1838年九月十九日。由此可知,陈庆镛15陈庆镛(1785—1858),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给事中、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等。共襄其事,是出于阮元的请托。而此时吴氏已明确将书稿称为“筠清馆金石文”。
综上,《筠清》初由吴荣光、吴式芬二人出资组织编纂,龚任考释并于1838年六月“缴卷”,撰成手稿十二册。手稿曾藏何绍基家,不久即转至陈庆镛处,阮氏、吴氏请陈庆镛继续考释编纂。据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及余解组,已先得其十之八九,余亦邮索寄还。及余归里,适子苾守南安,途次尽出所有以补余之不足,而金文亦庶几备矣。”道光二十年(1840)吴荣光致仕后索稿归粤,又辑录了一部分吴式芬的藏拓,16是年九月吴荣光观吴式芬所辑钟鼎款识册,并题:“与子苾知三年,不谓钟鼎款识如许之富,欣幸观之。时道光庚子九月下九,为子苾六兄大人题,六十八叟弟荣光。”([清]许瀚,《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稿本,第一册,叶五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于1842年在粤刊成。《筠清》以商、周、汉时代先后为序,各时代按器形分类。正文体例为摹录款识、次释文、次考释,是仿阮著而作。根据朱善旂题识,其稿本中的考释文字逐年又有增补,采徐同柏之说较多。且在丙午年(1846)获睹《筠清》刻本之后,朱善旂对自己辑录的此部底稿又进行了一次批校。
该稿本未经刊刻,清末归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小校经阁收藏。解放后刘氏藏书捐献上海市文管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敬吾心室钟鼎款识》原稿本六册”,即在其列,见载于《刘晦之先生捐赠小校经阁藏书清册》。1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刘晦之先生捐赠小校经阁藏书清册》,封面字样是顾廷龙亲笔。参见宋路霞,《细说中国近代家族史书系·细说刘秉璋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32—135 页。朱善旂题识称稿本为五册,而归刘体智收藏时已分为六册,推测稿本自朱氏流出后可能经过重新编排。存疑俟考。
二 稿本的形成过程
《敬吾钟鼎》稿本的形成,大致经历了钩摹铭文、誊写龚自珍考释内容、誊写龚氏释文、批校、增补几个阶段。稿本的层次比较复杂,现试析如下。
(一)钩摹铭文及誊写龚自珍考释。分别由陶中桂、朱善楹完成。陶中桂,字香楞,生卒不详,是朱善旂之叔母舅,尝为朱为弼治印。18此据黄尝铭,《篆刻年历》,转引自乔晓军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二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19 页。朱善楹完成誊录龚释的时间,当在道光十八年秋之前。19“兮仲钟”条,释文旁有朱为弼手批“人当作父”,朱善旂注曰“此四字,先大夫乙未病后亲笔,戊戌秋间所书”。朱为弼批注当在誊录完稿之后。誊录龚释所依据的底本究为何本?朱善旂稿本中未交待,因材料不足,尚难考证。20根据龚吴二家往来书札,龚自珍曾手录考释文稿的副本,包括何绍基、何绍业二人后加的籤注。“去年呈教之二十七种考释一册,望扎东卿取回。付来手书,弟急欲读子贞子毅之籤,且欲录副本以自考。现在穷日之力录副,专俟此廿七种发回,则可以卒业。卒业后,尚有俗冗多端,寸阴尺玉,行色匆遽故也。力为催来,至感。弟于廿九日趋晤作别,即问子芯仁兄早安,巩祚顿首。廿六卯刻。吴印大人。”《与吴式芬笺》(十七),引自孙文光《龚自珍集外文录》,第48 页。今考该札当写于龚氏己亥去都之年1839年。疑即经阮元审阅后“中夹数签”的龚氏手书稿本。
(二)朱善旂手校朱善楹所录龚释,并手书铭文释文。并于少数器抄录叶志诜、吴式芬所作释文,如“周宂敦”条,朱善旂注曰“凡释文旁注皆叶氏所释”。
(三)朱善旂、朱为弼、陈庆镛手批。包括夹批、眉批、尾批、签批,内容含校勘异文、指正阙误等。稿本中见朱为弼批识四处,陈庆镛批识仅一处。朱为弼手批,如“周乙伯彝”(《筠清》作“周十月彝”)条有“飤下乃彝字,见王子申盞盖。为弼识”。“宵旅彝”条跋云:“此器余曾有拓本,宵字较此为肥,俟再觅之。为弼识。”“兮仲钟”条,释文旁有手批“人当作父”,又有“此四字,先大夫乙未病后亲笔,戊戌秋间所书”,则知为笔迹分别出朱为弼、朱善旂手。“王作姬娷盉”条,有“姬字下当是姊字,首一字盖阙”句,下有朱氏双行小字“此一行陈颂南给谏为民部时所书”。朱善旂的手批涉及考据辩证、记录见闻等,间加考跋。在校语中偶采素讷、叶志诜、吴式芬之说。表明自身观点者以“旂曰”“旂按”或“建卿记”批注于旁,以加按断,但此类批注较少。
(四)增补考释。采徐同柏之说较多。如“曐尊”,以红格稿纸抄录1846年“六月二十六日”徐释。依字迹判断,非朱氏自笔,当是他人誊录。另有若干篇考释直接以徐氏手稿本添入。此类续补当是朱善旂遵阮元之嘱而为——阮跋徐同柏款识考释稿本曰“是册必多采择”。
(五)增补古器及铭文考释。增补古器,例如在“伯彝”条前增“陈侯彝”(注曰“七十九字 潍县陈氏”)并手书释文,但阙铭文钩摹本。又于敦器类,增“杞伯每敦”等四器。于盘类,添入徐燮钧(字博兼,号阆宾,武进人)任陕西郿县县令时所得的“虢季子伯盘”。稿本中另见徐同柏考释“周叔囗㪟”的手稿,款署:“道光十九年己亥中秋,应建卿先生大著作教即政,徐同柏。”
(六)比勘《筠清》刻本,标注异文,或改、或删。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氏始得见《筠清》刻本,将之与自藏稿本中的龚释合勘,校出吴荣光刻书时更改之处,并以旁批或眉批的形式用朱笔标注。例如在“宂彝”考释文字勾删之处眉批:“此亦从荷屋丈所删。”
(七)添入考释器铭的若干信札资料。如张廷济(1768―1848)致朱为弼信札《获同里王氏所藏史颂盘》。诸如此类应为编纂过程中的往来书牍,陆续添入者。
(八)添入其他相关文本。如“兮仲钟”条,添入了铭文原拓本。朱为弼曾为嘉兴王子愚之子嘏斋(锡寿)作“宝盘斋”匾,今未见传世。册中“史颂盘”条,保留了朱氏为“古斋大兄”即王锡寿所题的“宝盘斋”小字手稿。
通过分析可知,《敬吾钟鼎》是在誊录龚释之后陆续增补修订而成。其中的龚氏考释内容,历经校勘、批识,或增添或勾删,远较《筠清》刻本详赡。上述第四至第八项的文本层次,可能相互交叉,并非准确的先后关系。后补器,据稿本仅在器目叶抄录了释文推定,似乎未最后定稿。
与《筠清》卷三著录“周毕中孙子敦”(图1)相对比,可对稿本的内容层次有更具体的认知,二者差异较明显。此器实为段簋,西周中期器,《集成》04208 收录,叶志诜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稿本“周毕中孙子敦”(图2)文本次序为:陶中桂钩摹铭文、朱善楹楷书誊录龚定盦考释、朱善旂手写龚释文并旁注叶志诜释——“释文旁注者系叶氏所释”、朱为弼手批——释文旁有两行批语,朱善旂小字注曰“此先大夫病时亲笔”、朱善旂据《筠清》刻本校改考释内容——“硃

图1 《筠清馆金石文字》“毕中孙子敦”,天津图书馆馆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采自中华古籍资源库(上)

图2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周毕中孙子敦”
三 稿本与《筠清馆金石文字》刻本比较
《筠清》刻本共收录44 家藏器拓本或摹本,凡267 器:商器67 件,周器172 件,秦器4 件,汉器21 件、唐器3 件。《筠清》中的考释内容多出龚自珍手,又龚氏、陈庆镛先后助编,“吴氏略不审核,使其画一”,故“卷中行文有简古平易之殊,且有一语而前后异释,一器而前后异说者”。杨树达(1885―1956)《读〈筠清馆金文〉》一文中,对此有评析。21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1954年,第280 页。另见姚华跋语,指出《筠清》不足有六:“摹刻未精;不明器之所在;文字多沿旧说之误;考据或得或失,而浅深不一家法;生金文盛时,所采亦仅如此;取材既不闳博,而真伪又少别择。”[清]吴荣光撰,龚橙校释并跋,姚华跋《筠清馆金石文字》,清道光二十二年吴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龚、陈二人的考释时有胜义,但总体而言失于穿凿貤缪,22黄宾虹指出此书中考释研究的不足:“中有金文之释,为龚自珍所纂定,自负其学,为能冥合仓籀之旨,而凿空貤谬,时或不免,此为西汉学者所言金文,尝或不通字例,未习旧艺而然。”引自赵志钧编,《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41 页。孙诒让(1848―1908)《古籀拾遗》、杨树达文中对之有匡正。需要说明的是,《敬吾钟鼎》稿本中朱善旂关于铭文考释的校语,同样也未免纰漏,主观臆断的成分较多。朱善旂较早参与续纂《积古》又亲睹《筠清》刻本,与阮元、吴荣光、吴式芬、陈庆镛、徐同柏等学者之间交往密切,其批校文字时而汇录了诸家观点,又不乏亲睹亲闻。因此,稿本为我们考察《筠清》的编刻过程及搨铭钩摹、考释等分工概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将稿本与《筠清》合勘,或可析出稿本对《筠清》的文献校勘价值。
(一)文本异同
续编《积古》而产生两部底稿,后各经纂辑,文本面貌遂有不同。《筠清》刻本依据的原始稿本今不知所在,据刻本比较上图所藏《敬吾钟鼎》稿本,可以总结出两部底稿的文本递变(表1)23本表内容依据:《敬吾钟鼎》稿本,龚自珍〈己亥杂诗〉,龚橙跋《筠清馆金石文字》,龚、何、吴之间相关信札,《筠清馆金石文字》稿本等。。

表1 两部底稿的文本递变
除去稿本中朱善旂陆续增入的徐同柏考释观点,即题识中所言“其逐年增入,采之徐籀庄丈居多,彼本所无矣”,稿本与《筠清》刻本之间的差异,分析朱氏手批内容可知大概。其校改、增补的层次如下:首先对龚释予以校订。以旁批的形式反映在稿本上,包括校订释文讹误、考释失当之处。第二,增补故实见闻。如器之流传、藏于某处等,内容多写在空白处。第三,道光二十六年以《筠清》刻本比勘自藏稿本的龚释,标注异文。此时朱善旂手批反映的是龚释某器中的语句在《筠清》成书时被删削或校改之处——即《筠清》刻本无而此稿本有的情况或《筠清》刻本对龚释的更改。下文于朱氏校订龚自珍考释、增补古器见闻类的批语中各举一例。
例一:虢叔钟,龚氏误以此本为张廷济藏器,实乃陈均、伊秉绶经藏后归钱塘瞿氏者。朱善旂在器名下注曰:“此钩本实伊墨卿丈所藏器,予昔年囗以致《筠清馆金石》亦误为张器。”在释文部分第八行第三字,手批“释文内多出一铸字,
此定盦麤心”。龚氏考释原文称“古人制器,一范不止铸一器”,朱校曰:“阮张伊三器各一范,定盦但观其大段同文,不细谛字之大小及行列不同。”该叶朱氏另有跋语:“己亥八月二十九日,余取阮张两拓本与此细校。此摹本,字形较小且鼓左皆六行,第独作七行,彼二本鼓左第一行天字止,第二皇字止,三止钟字,四止二字,五止其字,六止享字,且张本虽不及阮之精好,亦不如此之残剥,此摹的是又一本。”
道光己亥八月,旂至虎林,亲往张同甫二兄(应昌)处索观,摩挲竟日,手拓数纸,见此器完好并不残阙,惟多剥蚀又拓本不能清晰耳。钟重今权四十四斤,井与郑相近而同封,见夏松如考释中,足证旧读邢之讹。又杭人夏松如、徐问翁等皆有诗歌。丁酉岁刘燕庭观察之武林欲之,偿以三百缗,同甫因以为赠,既而悔之,属胡书农讲学作送钟还钟歌,遣使追数百里外索归。
(二)稿本对《筠清》的校勘价值
龚自珍十八通与吴式芬札(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写于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间,其中十五通均是为吴荣光编书过程中的通信。是时,吴式芬居京城宣武城南坊,龚自珍与其隔巷而居。札中龚称“日立课程为荷屋先生办书”“望付郭君手先钩摹于油纸”“此件望即付双钩”“送上唐鱼符搨本二种,乞钩出加考释”“筠清馆书为吾辈所定”“以笔代舌求教”“兹将本纸呈览,仍教之”,可见往来讨论频繁,正如其《己亥杂诗》第四十一首所言“忙杀奚童传拓本,一行翠墨一封书”。不仅如此,二人也时常晤面商讨,札记即见“欲携就左右求教”“日内颇有所得新义,愿走政”等语。龚所涉及的方面,不仅商榷考订铭文而已,还包括搜集拓本、勘校摹本等。32孙文光,《龚自珍集外文录》,第44—49页。龚为书稿出力最勤,并非吴荣光在刻本序言所称龚氏任“校订”。
民国版本学家杨钧(1881―1940)在《记古书》一文中,提到了《筠清》稿本:“《筠清馆金石文字》,余得见稿本,芜杂异常。成书之时,删去不少,其去取以何为准,余尚未明。大约先求凑多,后又求精也。”33杨钧,《草堂之灵》,张海军译,岳麓书社,2019年,第305 页。《敬吾钟鼎》中朱善旂手批,可为稽寻《筠清》稿本原貌、刻本去取的依据,提供一些参考。据稿本或可复原出龚定庵释文及考释的原始面貌。
1.龚定庵考释,而《筠清》未标明或托名他人者。
龚释内容由朱善楹手抄,据字迹即可分辨某器实为龚氏考释,而《筠清》刻本未标明者。又龚橙、34龚橙(1817—?),字公襄,后以字行,改字孝拱,号石匏,晚号半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龚自珍长子。许瀚、吴式芬、杨铎(1813―1879)、盛昱(1850―1899)均曾批校《筠清》刻本,考订其不足。综合诸家考校文字,可知铭文原为龚自珍所考释者远较刻本中标注“龚曰”“龚定盦云”者为多。如“虢叔钟”“毕中孙子敦”等等,实为龚氏考释,《筠清》刻本中未标明。朱氏稿本、龚橙及许瀚批校本的校语皆可为证。对吴氏删龚名之举,定庵长子龚橙颇有愤慨,云:“此多定自先礼部,吴氏有标龚曰,其余多经刊削似为己说者。”35龚橙跋语,见[清]吴荣光撰、龚橙校释并跋,姚华跋《筠清馆金石文字》,清道光二十二年吴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图3)龚橙在校释该书时,以“窃贼”称吴荣光。如《筠清》卷四“周申月望鼎”条,龚橙手批:“即如此释,荣光必不能解,何所见而欲窃之哉,此人殆有窃疾也。”36同注32,卷四,叶二十八正。“周父癸角”,许瀚曾批识:“定翁后说,定翁说讬之苾翁,不知何意。”37[清]吴荣光撰,吴式芬校注並录,许瀚批识《筠清馆金石文字》卷二 ,清道光二十二年吴氏刻本,叶五十二正。如许说无误,则可见《筠清》刻书时曾将部分龚释托名吴式芬。

图3 龚橙跋《筠清馆金石文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采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2.非吴式芬考释而托其名者。
《筠清》卷五“周兮中钟”条,吴式芬批语:
苾在京师亲见此钟,实是“前文人”,橅者因拓本剥蚀,误增损其笔画,作“省文父”,而反以释“前文人”为非者,云是鄙说,殊不可解。38同注33,卷五,叶二十四正。
3.《筠清》刻书时,删削龚所作考释者。
例如,“周十月戒田尊”(图4),稿本中存龚释: “《积古斋》此器文大同小异,释文未允,又改从肉之肦为从舟之,谨为正之如此。”此句旁有朱善旂手批:

图4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十月戒田尊”
吴荷屋丈刻筠清馆金石文,将此首一行删去,盖有见于释锡驶卣之所怒于阮太傅也。况《积古斋》“王主父丁尊”下,明明引“制名山大泽不以肦”云“古从舟之字隶每省从月”,特释文作字耳何。
再来看“齐侯罍”二器的著录。《筠清》刻本,于前器“齐侯罍”未采龚释,后器“齐侯中罍”采其说而略有更改,而《敬吾钟鼎》稿本中完整过录了龚所作释文及考释全篇,保留了龚释原貌。铭文中字,龚氏释为,认为是齐侯名,定器为壶。而阮元、朱为弼释之为罍,不以龚说为然。前器有手批:“若以为侯名,则臣尚称谥,君何以名?此书内无罍器,可增此器为一门。”此句别写于一纸签条上,黏贴于稿本“齐侯罍”条铭文钩摹本旁。析其笔迹,或为阮元手书(或为朱善旂编书时所摹录,俟考),即前引龚札中所言芸台相国“于齐侯器跋尾末亲笔增两语”。该纸左下角别有一行小字“此条难遵”,难以断定是何人笔迹。至于后器的考释内容,《筠清》刻本对龚文作了一处改动,稿本作“旧以此器为罍(因齐侯之名而误),今定为壶,彝可以赅之”,刻本作“或以此器为壶”,可见吴氏对龚说的肯定语气做了缓和处理。今检《筠清》刻本,确将二器单列为“罍”一类。
此外,稿本惟“商臤州鼎盖”条,铭文有双钩单钩二种,最为特殊(稿本中其他器铭均为单钩)。联系龚致吴式芬札所商讨的内容,41〈与吴式芬笺〉(六):“启者,求考兄、生字凡几见,示下。又弟以搨本校郭君双钩本,有一纸实不可用,欲剔去,求子毅重摹之。”引自孙文光《龚自珍集外文录》,第46 页。按此书兄、生字,即臤州鼎盖中铭文。原始的双钩之本,可能是摹工“郭君”所为。对照此类文本,对于考查《筠清》的成书问题,当有助益。
四 《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朱善旂编辑的另一部续《积古》之作
道咸年间,朱善旂另辑有一部稿本《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以下简称《敬吾彝器》),共收录商周秦汉四代器三百六十有四。42据册后朱之臻跋语:“以类相次,盘、钟、洗、鼎、尊、敦、簋、甗、甑、盉、匜、壶、彝、觯、爵、卣,为类者十六,汉器别出鼎、钟及鬲为类者三,原拓题记间用五色笔。”此书收录原拓,且多有当时稀见之品,留存了拓本资料,但收录伪铭颇多。除鼎(毛公鼎)仅录释文,43“鼎”条,朱善旂跋曰:“咸丰壬子夏,陈寿卿太史得于都门,秘不示人,但拓一纸寄陕藩吴子苾方伯式芬,甲寅夏苾翁来京,因借录其释文。”引自[清]朱善旂辑《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清光绪三十四年平湖朱氏景印本。余器皆以朱善旂所辑彝器原拓编入。拓本多经时人题识,朱善旂考释或有或无,多为移录他人之说。原拓题记间用五色笔。原稿在清末归端方(1861―1911)收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善旂从侄朱之榛借以石印,封面书笺“敬吾心室识篆图”,以二卷本传世。经分析,该书也属于《积古》的续作。此稿本与上图所藏稿本,同以“敬吾心室”斋号命名,但体例不同。因此,《敬吾彝器》同样是考察续编《积古》文献的重要材料。
稿本前有阮元隶书、汤金钊(1772―1856)楷书题书名(图5),戴熙(1801―1860)、查青华各绘《敬吾心室识篆图》一帧,李宗昉(1779―1846)、张廷济、叶志诜题识。张序中有“政余学古益进不懈,续辑古金文数百器,考释累数万言”语,叶氏提及朱为弼欲作《款识续编》而未果:“茮堂漕督为阮芸台相国编辑《款识》一书,考据赅博,远出薛尚功、王啸堂之上。……每欲为《款识》续编,以历官中外,公事驰驱,未竟其绪。”44[清]朱善旂辑,〈《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序〉。

图5 《敬吾心室彝器款识》阮元题字中国国家图书藏清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采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朱为弼何时开始有续编《积古》的计划?检其诗文集中较早提及纂辑“积古款识续编”“续款识”,见《蕉声馆诗集》卷五〈周散季㪟歌为程铁楼驾部作〉诗序:
铭虽见《款识》摹本,然锓刻传钞多失古意,此拓本甚完好。……嘉庆强圉单阏之岁为壮之月望日,直宿曹署,尘事少闲,因考誌数语,并系以诗。平生僻好在斯,每见古器必手拓,见拓本必手摹。此铭微带草篆体,具鸾翔凤翥之致,爱玩不能释,摹入《积古款识续编》,真鸿宝也。45[清]朱为弼,《蕉声馆诗集》卷五〈周散季㪟歌为程铁楼驾部作〉,清咸丰七年刻本,叶七正至叶八正。
析其义,此时朱为弼依拓本考释“散季㪟”铭并赋诗。因薛尚功《款识》以摹本入录,又经版刻传钞已失古意,朱氏欲将此拓本摹入《积古款识续编》。此云“强圉单阏”即嘉庆丁卯年(1807),考释赋诗时间在八月望日。可知至迟在此时——距《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刊成有三年,朱为弼已有续补其阙之意,远早于道光十六年吴荣光的续编提议。
综合以上分析,在《积古》刊行后,朱为弼陆续辑得数百种古器铭文作考释,拟成续编。
但辑书之事,因事缠未果。嗣子朱善旂承续其志,稿成名曰“敬吾心室彝器款识”,阮元、汤金钊为题书名。《敬吾彝器》册内“周叔㛗㪟”拓片上有朱善旂跋语:“此恐赝器,不可入《续款识》,因徐籀庄先生已为考释,姑存册内。善旂记。”46[清]朱善旂辑,《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清光绪三十四年平湖朱氏景印本。按:《敬吾心室钟鼎款识》《敬吾心室彝器款识》收录了徐同柏前后两次考释该器的手稿,分别作于1839年中秋日、十月初八日,后稿多识出二十七字。这也表明,《敬吾彝器》实由纂辑“款识续编”而来。
在《题史颂盘铭》诗序中,朱为弼也明确提到将器铭摹入《续款识》:
史颂盘铭十二字……奇古浑朴,周器也。余载古器物铭于《积古款识》,凡数百种,此盘未及录。其篆法与《款识》内史颂壶相似,殆一人之物也。梦庐以拓本见示,云是新篁里王氏子愚所藏……,因题断句,并摹入《续款识》中。47[清]朱为弼,《蕉声馆诗集》补遗卷一〈题史颂盘铭〉,清咸丰七年刻本,叶九。
按诗集编次,此诗作于嘉庆己巳年(1809)年之前。此时盘为新篁王几(字子愚,生卒年不详)收藏,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售归张廷济,现藏上海博物馆(《集成》10093)。该器《筠清》未著录。《敬吾钟鼎》稿本中存道光十八年元旦张廷济致朱为弼“椒堂大人政之”的《获同里王氏所藏史颂盘》手稿。《敬吾彝器》辑入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张廷济“拓奉建卿先生”的史颂盘铭原拓本。由此可见,朱善旂在《敬吾钟鼎》《敬吾彝器》中均续补了该盘相关资料。
“史颂盘”是两部稿本重出但《筠清》未录之器,可作为分析两部稿本关系的一个例子。两部稿本重出器,且《筠清》已著录的,《敬吾彝器》一般于器名下标注“筠清馆已采”,朱氏过录《筠清》考释内容,偶或增加自作考释,或请徐同柏作跋。
上海图书馆藏《敬吾钟鼎》所录器与《敬吾彝器》有同有异,限于篇幅,此不作析论。两本皆源出于续编《积古》,是可以肯定的。《敬吾彝器》皆据朱氏所藏拓本编入,其中很多器铭为《敬吾钟鼎》稿本所无,册中有多篇徐同柏手书题跋,作于1839―1841年间。简言之,《敬吾钟鼎》著录器中朱氏藏有拓本的,复被编入《敬吾彝器》,朱氏题记这部分拓本的文字,有些直接引用了先前稿本的编校内容。《敬吾彝器》的创稿时间当早于《敬吾钟鼎》,而编订完稿时间则晚于后者。48《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有关时间记录最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从《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中的拓本分析,其题记最晚时间在咸丰甲寅(1854)年。
五 《敬吾心室钟鼎款识》稿本的学术价值
(一)稿本揭示了续编《积古》诸作的源流关系,从金文文献史的角度审视,稿本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道光年间“续积古斋款识”可析为两大编纂系统。一为道咸年间朱善旂承其父朱为弼夙愿而作,1908年经朱之臻整理石印为《敬吾彝器》上下两册。二为道光十六年起吴荣光主事编纂,由龚自珍考释,产生两部底稿,后又各自吸收了其他学者的考释成果:一部经吴荣光刊刻为《筠清》五卷,一部即此《敬吾钟鼎》稿本。故三者均属于《积古》的续书,《筠清》与《敬吾钟鼎》是同出一源的关系,而《敬吾彝器》独成系统。
(二)稿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龚自珍考释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对校勘《筠清》亦有重要意义。据朱善楹手迹,可推定原为龚自珍考释而《筠清》未标名或托名他人的内容;据朱善旂朱笔手校部分—— “硃笔依荷屋丈刻时改,本非龚自改也”,可知《筠清》成书时所作取舍及删改缘由。其中少数几则已成佚文,尤其值得珍视。如从稿本可辑出龚考释齐侯罍的二则内容,有助于厘清各家考释该器的相关史事。据此,可以补充收录于《定庵遗著》中的《两齐侯壶释文》所阙。此类文本是探讨龚氏金文考释的直接材料。
(三)稿本揭示了朱善旂续纂《积古》的实践,对研究其抄书、校书、藏拓、释铭诸问题,提供了一手文献和研究线索。石印本《敬吾彝器》卷后朱之榛跋语中有云“喟世父心力所寓,存于今者止此”,依此判断,朱之榛亦未得见《敬吾钟鼎》原稿。而细读稿本恰可见朱善旂收藏、考释款识的心力所寓。稿本屡经批校和增补,对于研究朱善旂的金石考释经历及成就,具有重要价值。
(四)稿本考释内容源自龚自珍、徐同柏等,又采录吴式芬、叶志诜、素讷等人的释读,经朱为弼、朱善旂、陈庆镛批校,可视为众多金石学家考证成果的汇总。稿本中的书札原件及朱为弼手迹,朱善旂手批中的金石见闻,反映了道光年间张廷济、徐同柏、张应昌、王锡寿等嗜藏金石的学者与朱氏父子之间的金石交游,并成为考查道光末年金石兴趣、考证焦点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