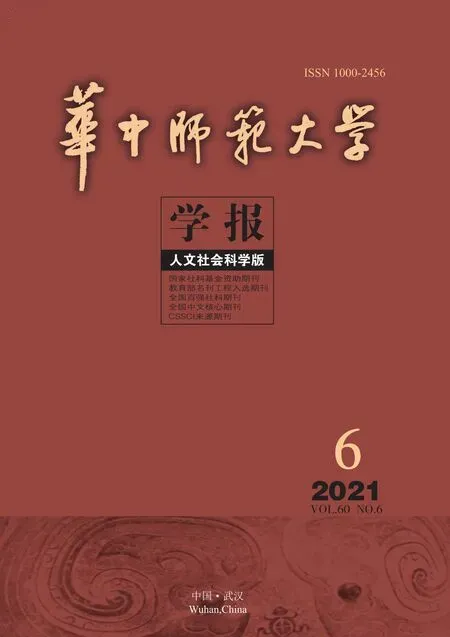明清百姓避役避比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
胡铁球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明中叶以来,随着官员的考核逐渐倾向于“赋役完纳”这一项,比限制度也在各地逐步形成。此制度一建立,便成为催课之法的核心,到清初,比限处于四大催课之法的首位①。正因为比限制度的重要性,梁方仲、瞿同祖两位先生早就关注到比限,只不过他们不叫“比限”而叫“期限”,虽着墨不多,但分限征收的特点已揭示得较为明晰②。此后的学者,除笔者外,仅是有意无意提及它,致使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设立比限制度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缓征”③,实际上则是为了逼迫老百姓执行赋役交纳的优先原则,即逼迫老百姓将所有收入最先用于赋役交纳,为此,出现了“三日一卯,五日一输”④的普遍现象。其弊端非常突出,赵廷臣言:“一月六卯,限勤期迫,四乡之民仆仆道路,公私咸误。”⑤所谓“一月六卯”,指一年内每月分设6限,需“五日一输”,致使老百姓不是在交纳赋役的路上,便是在衙门内办理纳税手续。
设限过密、比责严苛引起了交纳成本高昂、官员胥吏勒索加剧、市场混乱、高利贷盛行、包揽成风等众多社会问题,结果乡民因催比而破产、逃亡、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⑥。至于当役者,其处境更为艰难。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专比当役者,结果比粮长,粮长破产,比里长,里长破产,比排年,排年破产,比地保,地保破产,致使这些当役者“倾家荡产者相比”⑦,“不逃亡不死徙者几希”⑧。
面对如此困境,老百姓开始积极应对,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措施来避役避比。这些手段与措施又严重破坏了赋役制度,影响到国家赋役的征收,故政府也不断推出新的制度来强硬地回应百姓的应对措施。政府与百姓之间惨烈的博弈过程,集中体现了以比限制度为中心构建的催征体制对土地结构、乡村结构、基层组织结构的改造力度。诸如明清以来土地市场的分层性与复杂性,宗族势力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以及多层级包揽网络的形成,皆与赋役制度,尤其是比限制度息息相关。
一、百姓通过诡寄、花分等手段来避役避比
老百姓避役避比最常用的手段,是减少自己户下的地亩,使田亩数量不符合国家编派粮长、里长、柜头、解户等重役的标准,常用的方法有诡寄、花分、飞洒、影射等。役起田亩是明朝的惯例,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江县令刘时俊言:
前件看得吴中赋役,俱从田起。概县田荡额有壹百贰拾万顷,递查历年审役田册,贰拾亩以上至百千亩点拨轻重差役者,仅贰拾万顷内外,余俱奸民花分,势户受计,累有所偏重,而利有所独归。本县查知其奸,思厘其弊。先以保甲之法,挨圩逐户细查其名号、年岁、职役、生理、宅舍、田园、男女奴仆,置烟门册。又逐圩查坵数,逐坵查亩数,逐亩注管业之主,为田根册。然后归以万殊一本之法,以旧户册捏立之名,附于烟门册之的名。于是有昔无田而今有、昔少而今多者,有数拾名并一户者,不烦搜索而花诡自清,当役之田三倍于往昔矣。本县于点役之时,遂得稍加宽恤,如往年点北运以千亩,今以千贰百亩;往年点南运、收头各以四百亩,今以陆百亩;往年十九亩以上俱在点役之内,今叁拾亩以下概得空闲;往时生员不免,今各免一百亩,而田亩尚多,点拨不尽。⑨
据上述史料,明代吴江点役有明确的地亩限制,减少田亩数量便是避役的最佳方法,故当时的吴江县民为了避役,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花分和诡寄。
花分是指“化整为零”,即将自己的田亩通过私契的方式分于田少之户,或将己户分成数十户,使一些没有身份的地主因减少了自己户下的田亩而避免当役。不仅如此,花分后还容易避比逃税,如清康熙中期,戴兆佳言:“完粮一人一户,各地皆然,独台民狡猾异常,无论粮多粮少,喜分而不喜合。盖合则追呼易迫,分则完欠难稽,所以一人必拍为数十户,或字,或讳,或号,或堂名,或乳名,或排行,或混名,星罗棋布于各都各甲之中,腾那闪烁,挂欠不完,摘彼漏此,此为花分之弊。”⑩从“合则追呼易迫”来看,因花分使名义上户的税额急剧减少,从而避免了自己作为“大户”而被政府盯上的困境,降低了比责加重且频繁的风险,具有一定的避比功能。诡寄则与花分刚好相反,诡寄是指“化零为整”,即势家们通过接受投献的方式将无优免者的田地集于自己名下,或通过代纳乡民赋役,即私契的方式将这些民户的田地集于自己名下。诡寄的好处是,原来拥有大量田地的田主不仅不用当役,而且其田地的赋役交纳也由优免户代替,从而达到避役避比的目的。
从上述吴江县令刘时俊所言来看,对政府而言,花分、诡寄的直接后果是户甲不实、田亩不实。针对这两个不实,刘时俊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通过推行“保甲之法”“置烟门册”来消除户甲不实的弊端,弄清每户的丁口、财产和田亩实数,以便从容点役。二是通过推行“田根册”来消除田亩不实的弊端,弄清每坵田地的实际亩数和业主。随后又将烟门册与田根册互相核对,花分和诡寄的数目便会了然,从中可剥离出非优免田地与优免户。不管是花分还是诡寄,其田亩总数都不会变,不太会影响田赋征收,但极大地影响了役的编审,导致的恶果是徭役的轻重失度,编役标准下调,致使户不配役,赋役难以按额完成。但对于采取花分和诡寄的老百姓而言,则利益巨大。
明万历时期,“役”到底有多重,我们从刘时俊“筹集工程款”这一案例可窥见一二。刘时俊见“役”的买卖市场很大,故采取公开“量开免役之条”的方式,通过该市场运作来筹集梳浚河流的工程款,其言:
完助工银肆拾两,免北运一名,贰拾两免南运或收头壹名,完银多寡不等者,照役轻重免差。士民无不乐从,共计银柒千八百陆拾贰两叁钱陆分捌厘,此一项得数颇多。然各出意愿,本县初未尝强之也。盖不惯当役之人,驱就役如蹈汤火乙,请托之门一启,甲移之一,乙移之丙,每点一役,转累且数拾人。此数千金者,暗有所归,而尚不止此。
众所周知,诡寄的主要目的是免役而非故意逃脱正供,即使如此,在一县一年之中,“免役市场”的纯利至少达到了7862.368两,可见当时民众的避役之切以及“免役市场”之繁荣。
百姓通过诡寄可以避役,同时因其田产在受寄户名下,不需要完纳赋税,故诡寄还可以避比。诡寄的实质是通过田地转移而进行的一种包揽,这种包揽甚至不需要诡寄户付出任何成本,而包揽者则可以通过赋役完纳的“考成分数”来获利。所谓“考成分数”,指州县地方官完成赋役应纳额的80%或90%,便可考满升迁。如万历年间,范濂言:
诡寄之妨赋有二:其一,自贫儒偶躐科第,辄从县大夫干请书册,包揽亲戚、门生、故旧之田实其中。如本名者仅一百亩,浮至二千,该白银三百两,则令管数者日督寄户完纳,及有司比较结数,二百七十两已足九分,便置不比。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田二百亩矣,积以十计,则每县无白银田去二千矣,况十不足尽乎!又况所寄愈多,所侵愈甚乎!其二,自乡宦年久官尊,则三族之田悉入书册。其间玩法子侄,及妻族内亲,如俗所称老婆舅之类,辄谓有司无可奈何乡宦,而乡宦又无可奈何我们,于是动辄欺赖,仅与管数人雇倩代杖,迁延岁月而已。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银一千余者。夫一官以千计,则十官以万计矣,况又不止十乎!
在松江府,一介“贫儒”只要中了功名,便立即接受诡寄田土,如果自家的田土只有一百亩,通过受寄可以浮增至两千亩。“贫儒”向寄户收取白银300两,按90%考满交纳,贫儒只需代寄户向官府交银270两,可从中牟利30两,而寄户在此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失,而且还可以免比,故趋之若鹜,于是诡寄之风愈演愈烈,故有“贫儒以册规为膏火”之说。
正因为诡寄既可避役又可免比,还不需要成本,不管是贫民还是富民,都争相诡寄,而拥有优免权的身份地主会充分利用其优免权,在免役、免比的市场上逐利。乾隆《江南通志》载:“贫户苦累不堪,将本名田地寄籍于豪强户下,以免差徭,而诡寄之弊生矣。”非止贫民如此,富户亦如是,黄印记载了无锡地区的情况:“前明绅户免役,富民之田多诡寄于绅户,于是贫民独出其力,以代大户之劳,最为一代弊政。”官绅的族人、姻亲、门生、故旧及一般贫民以田土假造为券(私契),诡寄于官绅名下,以为“避役之窟”。避役的目的是为了避比,故潘月山总结明清比限的弊端时说:“且比卯之时,每有民人托名宦属,藐法抗比。更有一种无品子衿,包揽过卯。”而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时俊言:“诡寄之难于清查者,以受寄系缙绅之家故也。”据此,诡寄多是在宗族内展开,明清宗族势力的形成应与之有关。
当然,诡寄的对象不仅是有身份的地主,凡是有优免权的人户,皆是诡寄的对象。嘉靖《宁波府志》载:“何言乎诡寄?多田之家或诡入于乡宦举监,或诡入于生员吏承,或诡入于坊长里长,或诡入于灶户贫甲,或以文职立寄庄,或以军职立寄庄,或以军人立寄庄。夫乡宦于各县占产寄庄,犹可言也,而本县寄庄何为者哉;军官占产寄庄,犹可言也,而军人寄庄何为者哉。率不过巧为花分,以邻国为壑耳。”据此,明代嘉靖年间诡寄的对象有乡宦举监、生员吏承、坊长里长、灶户贫甲、文职、军官、军人共七类人。这些人要么有优免权(免役)和免比的特权,要么具有“藐法抗比”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特别关注“患里”诡寄“富里”的现象。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富里”“患里”的问题在浙江地区已经非常突出了,政府不得不出台“升里并里法”来解决该问题。天启《海盐县图经》载:“嘉靖三十年按院林有行升里并里事例,以从民便。如一都三都七都十四都西北区,此富里也,听其将一里升为二里;如十三都十六都十四都东南区,此皆沿海患里也,听其将两图并为一图,仍不许增减原额里数。如此则法可变通,利垂永久。”可见,浙江曾通过“升里并里法”来解决各里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效果似乎不是很好。到万历初期,福建巡抚庞尚鹏言:“查得按属各州县编审均徭,俱随各甲内原额丁田,挨年编派,其法初未尝不善。但奸民欲避重就轻,往往诡寄粮多甲下。而宦豪之家,又花分子户,频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轻重愈失其平。”因为“升里并里法”仅能暂时让各里处于平衡状态,随着“患里”诡寄“富里”不断推进,这种平衡会马上被打破。由于这种情况很普遍,成为后来均田均役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历九年(1581),浙江推行“均田均役法”,究其原因,就有“患里”诡寄“富里”这一条:“盖往因里甲不限田故,奸民竟将田地诡寄富里,以致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户无立锥,且充数役。贫民不甘,往往苦扳大户,或将吏书装头,或捏重情骗准,经年累月烦渎官府。吏书因而陷害,大户亦复丧家。今若里有定额,则诡寄者无所容;丁产适均,则编役者无偏累;照田认役,则里长不审而自定;有产当差,则富家充役有何难;赋役得均,则贫民安生而息讼。”均田均役是从“以户配役”向“以田配役”的变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嘉靖三十年(1551)的“升里并里法”到万历九年(1581)的“均田均役法”,时间跨度为30年,可见解决“患里”诡寄“富里”问题的艰难,且即使“均田均役法”推行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故清代又有新一轮“均田均役法”的推行。
编审徭役,县之大政,而花分、诡寄的害处就在于紊乱编役,故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之道。嘉靖三十年(1551)推行“升里并里法”,万历九年(1581)推行“均田均役法”,万历中期刘时俊的“保甲之法”“烟户册”“田根册”的配套推行,其主要目的皆是为了解决花分、诡寄的弊端以及由此而凸显的优免制度的危害。虽然上述措施取得积极效果,但只要优免、比限等制度存在,这些弊端是无法根除的。不仅如此,因避役避比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民间百姓在花分、诡寄的基础上又生出了许多新的手段,如飞洒、影射、虚悬等,这些手段皆互相关联。

何谓“影射”?嘉靖《宁波府志》载:“又有弊者,则专货书手,悉以田归书手,户粮亦随之,书手乃径豁其田,而粮则于十年之中岁洒合勺于一里百户之内,渐以消豁,此以影射为奸者也。”据此,“豁”乃免除之义,而所谓“影射”,是指有田之家通过贿赂册书(书手),将自己的田粮归于册书户下,而册书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这些田的赋税暗暗摊派到自己所管一里百户之内,如此,有田之家不仅可以避役,还可以免于交纳赋税,从而可以免比。相对于有田之家而言,影射的实质是将赋税包于册书的一种方式,而册书包税却不纳于官,反而将税洒入他户,实属“干没”。又万历《漳州府志》载:“白兑之家本属影射,令还业主,各收米入户办纳。”白兑之家为包揽之家,因“业主”害怕进城纳税,更怕比责等环节的勒索,故将自己名下的田地过户给白兑之家,由白兑之家包纳己粮。册书与白兑之家包揽赋税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将他人之田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而包揽赋税,故影射的词义应是“蒙混、冒充”,即假冒他人纳税。
当然,针对影射之弊,政府也有应对措施。如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浦江令须之彦推行了“里长自填”与“三联串票”相配套的措施以防影射:“征粮分十限,设长单,里长自填,免算胥之扰。粮由三联互照,防影射之奸,于是夙逋尽完,沈困顿苏。”之所以“里长自填”与“三联串票”相配套的措施能防影射,原因在于其堵死了册书将己粮洒入他户的舞弊空间。
何谓“虚悬”?嘉靖《宁波府志》载:“何言乎虚悬?赵甲有田而开与钱乙,钱乙复开与孙丙,孙丙复开与李丁,李丁复开与赵甲。李丁有开,赵甲不收,则并田与粮而没之矣。”据此,某田经过不断过户,最后从地册上消失,该田之粮便“虚悬”了。此处“虚悬”的词义应是“无着落”。嘉靖《宁波府志》又载:“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飞洒、诡寄、虚悬诸弊。故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册乃无田,其轻重多寡皆非的数,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嘉靖《宁波府志》又载:“然飞洒者,损人以裕己者也。诡寄者,避重而就轻者也。至虚悬则一切欺隐以负国课耳。”万历《漳州府志》载:“本户有粮而无田,业户有田而无粮,谓之虚悬。”对比上述三则材料,虚悬是指“欺隐”,欺隐的方法是“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册乃无田”,与“本户有粮而无田,业户有田而无粮”的含义相同,依然指田粮无法落实,落实了也难以有效征收,还是“无着落”。又万历中期,刘时俊言:“江南苦役重,民就役如赴汤蹈火、入陷阱也。拥田者规避百端,窜入贵有力家,莫可踪迹,号铁脚诡寄。又或捏立名号幻出不穷,一户花分成数十矣。至若田圩册被私家瘦匿不入官,诸胥遂因缘为奸,飞洒、影射,每以游粮附诡户,号称虚装,核之,则户为乌有子虚,载册亩如飘絮不着地。”这里的“虚装”应与“虚悬”含义相同,是当地民户与册书联合作弊,即通过虚设户头的方式,将自己的田亩假托于虚户名下,从而达到避役避比的目的。影射、虚悬与花分、诡寄最大的不同是,花分、诡寄不影响田赋征收,而影射、虚悬则使得部分田地不在册籍上,即使在册籍上,也因其“虚名”而无法征收。
当然,面对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弊端,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方法是清赋,如用烟门册来清查各户人丁、资产等数额,用田根册来清查各户田亩实数,甚至通过攒造鱼鳞图册来解决田亩不实的问题。这种清赋的行为经常在各地推行,效果在短期内非常显著。如康熙二十年(1681),曹文珽为浙江台州太平县令,一到任便询问赋役难完的症结,结果发现问题集中在“户甲不实”上。民国《台州府志》载:
士民多言地方之积困,由于钱粮之多逋;钱粮之多逋,由于户甲之不实;户甲之不实,由于经界之不明。善良之家或一田而两赋,奸猾之辈或漏赋而管田,由是箠楚恒及于无辜,催科莫诘于诡骗,下滋赔累,上频檄催。且有一人分作数十户者,苦于应接之艰难。亦有一户丛集数十人者,便于彼此之推托。故每年各有带征旧粮,分日挨比,号冤痛哭于县庭者,昼夜靡宁,请其详立稽查之法。时适值编审,文珽撒去旧日图册户籍,令民各先自具田地实数,准其除虚挂之累,宥匿漏之愆,候履亩勘明后,与自具之数不符者,置之重罪不宥。阅两月,毫号俱齐,虚者悉除,漏者悉出,无一人敢以虚数报者。
据曹文珽调查,在当时的浙江台州太平县,花分的结果是“一人分作数十户者”,诡寄的结果是“一户丛集数十人者”,结果“图册户籍”紊乱,出现了“一田两赋”“漏赋”“虚挂”等弊端,赋役难以征收,故比责更苛。为了清理上述积弊,曹文珽推行了废除“旧日图册户籍”,建立新的“图册户籍”,不久“虚者悉除,漏者悉出”,有力遏制了花分、诡寄之弊。
不管是“升里并里法”还是清赋,皆是治标不治本,只要“以户配役”制度存在,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弊端总会层出不穷,无法根治。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弊端,必须推行“以田配役”。而均田均役法、摊丁入亩、顺庄法等,皆是“以田配役”的变革,如均田均役法,在很多地方已经将役的负担股份化,每亩地都有相应的役费负担,史称“以田配役”。潘月山言:“里长不尽独当一年,盖因以田配役。里役百分,分为十甲。甲役十分,每甲值卯一年。甲中人户,田数多寡不一,即派役多寡不同。照役分卯,有数人朋充一卯者,有一人管充二三卯者。一年之内每里长一分,应值三十六日。”在“以田配役”制度下,诡寄、花分、飞洒已经在躲避充当重役方面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而摊丁入亩是“以田配役”的进一步深化,当役摊入田亩中后,花分、诡寄、飞洒等舞弊手段能从避役中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顺庄法是在摊丁入亩的基础上推行的,更加注重对“的户”的征收,且必须在“户甲实”的基础上推行,故对诡寄、花分、飞洒甚至影射、虚悬等弊端的遏制也非常明显。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以田配役”仅能遏制“躲避充当重役”的各种手段,而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手段,既可以“躲避充当重役”又可以“躲避比责”,故只要比限制度存在不合理,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弊端依然有存在的市场。故“以田配役”推行后,在比限过密的时期,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弊端依然大规模存在。当然,民间避役避比的智慧不止停留在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上面,最体现民间智慧的是业主通过土地市场摆脱与政府的联系,游离于赋役之外,其中最典型的是“一田多主”。
二、百姓通过土地市场转移赋役负担来避役避比
由于当役应比而破家者比比皆是,所以乡民穷尽其智慧来避比,但乡民要绕开“比”,必须绕开“役”,甚至要绕开交纳赋役。要达到上述目的,最佳的途径是以田租的方式把赋役从租赋中分割出去,最典型的方法是“一田多主”,其中至少有一主可“无粮差”。如嘉靖年间,福建“柳江以西,一田二主,其得业带米收租者,谓之大租田;以业主之田私相贸易,无米而录小税者,谓之粪土田,粪土之价视大租田十倍,以无粮差故也”。所谓“得业带米收租者”是指全部包揽国家赋役的大租主,国家的地籍以及各类赋役册籍、票单上皆登其户名,小租主则超然于赋役之外。
总之,在“一田二主”的模式下,登记在官方册籍的是大租主,而小税主(小租主)则游离在地籍之外,如万历《漳州府志》载,万历元年(1573)以前,“漳州受田之家,其名有三。一曰大租主,共此一田,出少银买租,办纳粮差。一曰小税主,出多银买税,免纳粮差。一曰佃户,出力代耕,租税皆其办纳”。据此,小税主通过土地多层交易,变成了纯粹食租地主,“免纳粮差”,官方地籍、实征册等一切赋役册籍、票单上面皆没有他们的名字。那么小税主是如何游离出去的?万历《漳州府志》又载:
隆庆五年(1571),本府知府罗,议一袪宿弊以正田赋。漳州所属如长泰等县田惟一主,惟龙溪、南靖、平和等县,一田而有三主之名。一曰大租,一曰小租,一曰佃户。如每田十亩带米九斗六升三合,值银八十两,年收租谷五十石。大租者只用出银二十两,买得年科租谷一十石,虽出银少而办纳粮差皆其人也。小租者则用银五六十两,买得年科租谷二十石,虽出银多而一应粮差不预焉。至于佃户则是代为出力耕收,年分稻谷二十石,是谓一田三主。
此外,又有白兑之名,如大租人将粮差不自办纳,就于十石租内存留三四石自享安逸,抽出五六石带米九斗六升三合,白兑与积惯豪霸棍徒代为办纳。夫以九斗六升三合之米,岁纳本折色、机兵、驿传米、人丁银等项,该银一两二钱有零。若以十石租论之,约值银二两五钱,亦自足办。惟白兑之家止得租五六石,值银愈少,而欲其办纳粮差,其可得乎!况此辈止是苟贪目前小利,不顾身家后患,一遇稻谷到手,则便荡费,何有存留输纳,及至追征杖并,终年不完一二,钱粮逋负,词讼日兴,皆此之由。
据上述史料,至少在隆庆时,福建一些州县通过市场不同层级的交易,将税粮纳入土地交易中,如有田10亩,值银80两,可产谷50石,其中佃户劳动力值谷20石,余下的30石租谷值银80两,每石谷值银2.667两,小租主用银60两,按正常市值应购得谷22.5石,但实际上其年收租仅要了20石,出让租谷2.5石用于交税,而大租主用银20两,按正常市值应购得谷7.5石,但实际获得谷10石,但其需交赋税9.63斗米,按2石谷折1石米计算,需交税1.926石谷,不过这是正额税,加上各种役费的摊派与耗费,实际上要交银1.2两有余,而当时谷价是每石0.25两,银1.2两值谷4.8石,而1.2两有余该值谷5石左右。如此算来,大租主用银20两实际上只买到了年收租5石谷左右,表面上显然吃了大亏,但其所拥有的地权则在官府各地册籍票单中得到了确认,而小租主只是在民间私契中得到承认,有一定风险,这样就使得上述交易变得合理了。总之,通过土地市场交易,小租主已经游离于政府地籍管理之外,完全不纳粮差,这是第一类游离于政府田赋交纳之外的人群。据此,从某种层面讲,大租主也是包揽户,其包揽了小租主的税粮。
由于很多大租主不擅长与政府打交道,在纳税过程易受到各类人员勒索,于是他们又将负担国家赋役部分的租谷通过土地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包揽之家(白兑之家)。康熙《漳州府志》载:
惟是漳民受田者,往往惮输赋税,而潜割本户米,配租若干石,以贱售之,其买者亦利以贱得之,当大造年辄收米入户,一切粮差皆其出办。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买田契劵大率记田若干亩,岁带某户大租谷若干石而已——原注)。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私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米兑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劵,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
结合万历《漳州府志》和康熙《漳州府志》所载,福建许多州县的包揽是通过土地贸易形式进行的,如白兑之家要包揽10亩田的赋役,需大租主通过土地交易,将10亩田过户给白兑之家,白兑之家成了国家地籍等赋役册籍票单上登载的户,拥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其包揽也就合法化了。不过,这个土地交易过户过程却是“无贸本交易”,仅是白兑之家与大租主互相协商,以租的形式确定交纳国家的赋役数额,从万历《漳州府志》所载来看,一般占整个租谷的20%左右,即10亩田6石租谷,其实这与前述诡寄是一个性质。经过大租主将田过户给白兑之家,大租主成为第二类游离于政府田赋交纳之外的人群。
由于土地交易带有长期性,这种包揽也就长期化了,甚至需一代一代相传。然而,在租额固定不变而国家赋役数额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大租主或白兑之家的收益越来越少,甚至要亏本。于是白兑之家向大租主要求增加租额而大租主向小租主要求增加租额的情况就变得频繁起来,导致诉讼不断。若白兑之家、大租主增加租额的请求失败,必然会导致赋役逋负愈来愈严重,地方官员不得不强力介入。如隆万之际,福建南靖县知县曾球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办法就是政府强力介入土地市场。万历《漳州府志》载:
近该南靖县知县曾球,欲将本县大租粮米革归小租输纳,原无价买者,则不必贴,如有价买者,着令小租之家贴还。如小租之家不愿出贴,大租之人能照原价与小租承买者,亦从其便。白兑之家本属影射,令还业主,各收米入户办纳,是亦深知时弊,切于为民相应准行。但人有贫富差等,田有上中下则,若以此法行之,富民并上则、中则之田,亦易为力。若行之贫户,并下则之田,则恐人情未便。
今合酌量适中,如以十亩之田为率,原该价银八十两,今则以银配田,出银六十两者,则给与七亩五分;出银二十两者,则给与二亩五分;无银出者,则不必给。此则不论田则高下,只照价银分田则,田因银为多寡,无出贴承买之烦,粮因田而办纳,无有粮无田之病。及照漳州,又有利卖价多而推粮数少,以致本户有粮而无田,业户有田而无粮,谓之虚悬。其典卖田地俱不税契,照亩过割,历造黄册钱粮虚数则有,及至追征实在则无。
通行议呈抚按行分守道参政阴复议,得均平之法,莫善于丈量,其次则在于清查。今丈量难得其人,且非一时所能干理。合行该府,除长泰县已经丈量、南靖县见该知县曾球查理外,其龙溪、漳浦、平和、海澄四县,即行各该正官秉今大造黄册,顺带清查。令各户将实在事产另造小册,明开本户实在田产若干顷亩,坐落某地名,载官民米若干,或自耕种纳粮,或系佃户某人认佃,每年纳租若干,或田主一人自收,或大租主某人分收若干,小租主某人分收若干,逐一查审明白。
如系田主一人收租者,粮差自办无事更张外,其有大租主、小租主分收者,斟酌民情土俗,善为区处。或大租并归小租,或少租并归多租,或照租分米各自办纳。大要粮出于租,必使租粮相配,田主相管,轻重适均,粮额无失。
备造实征文册,查照征纳,用垂永久。其白兑冒顶者,示谕自首改正,免究前罪。如仍通同隐蔽,许里长、知因人等首告,从重问罪,田产入官。虚悬粮米者,责令得业人户照亩收割;崩陷难修复者,查勘新垦田地抵补;典卖不税契者,责限三个月之内赴县验税,姑与免罪,如隐匿过限查出,依律究问,追价入官。务使积弊一洗,田赋均平,粮差易于征纳,小民不至偏累等因转呈抚按,详允行府,通行各县,遵照施行。
上述史料皆是讲官府如何处置小税主、大租主、白兑之家三者的纳税关系。知县曾球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是“将本县大租粮米革归小租输纳”;第二种是“以银配田”,即根据小税主、大租主所出价银分割田亩数,依据各自田亩数各纳各的税额;第三种是将租额归并于一户,由一户办纳,或依据租额分割税额各自办纳。不管是何种办法,其最终目的是“大要粮出于租,必使租粮相配,田主相管,轻重适均,粮额无失”,也就是说不逋负税粮即可。另外,在讨论因民间土地买卖造成税粮逋负问题时,让我们进一步认知了何谓虚悬和影射。所谓“虚悬”就是指“本户有粮而无田,业户有田而无粮”,而小税主属于“业户有田而无粮”,至于白兑之家则属影射。白兑之家为地方政府所痛恨,因为他们是造成税粮逋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即白兑之家的存在减少了官吏的勒索空间,因为白兑之家身份背景深厚:“白兑之家所承领者,非势豪则大户,表里为奸,深根固蒂,非严刑峻法,莫肯归还原主。”
当然,在福建,以白兑之家的方式包揽赋役,不仅存在于龙溪、南靖、平和等县,云霄厅以及长泰、诏安、海澄等县皆有记载。如在云霄厅,“纳粮之弊,历代多有,而明为甚。有白兑置田收租,不自办纳粮差,兑与积惯代为办纳,号曰白兑”。在长泰县,“其间典卖包纳,亦同田粮白兑等弊”。在诏安县,“大抵诏属所困苦者,田则浮粮虚悬,及白兑揽纳诸弊,皆缘里书相倚为奸,不可穷诘”。又言:“置田收租之人,不自办纳粮差,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瞻,以其余租带米兑与积惯代为办纳,号为白兑,往往逋负官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泰县的“典卖包纳”形同“白兑包揽”,而在海澄县,似乎更强调田与租分离造成的困境,与上述万历《漳州府志》和康熙《漳州府志》所载一田多主的弊端中强调租与赋税的分离有别。崇祯《海澄县志》载:
盖受田者惮输赋于官,潜割本户米,配租若干,售之他人,其直稍平,置者以贱得之,收米入户,一切粮差皆其出纳。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关,是曰田主。其得租者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买田契劵大率记田若干亩,转某宅大租岁若干而已——原注),流转成习,久之,田与租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私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给,以其余租带米兑与积棍代为办纳,虽有契劵而无资本,名曰白兑,往往逋负公家,构讼连绵。
据上述史料,在海澄县,田产经过了三次推收过户,第一次田主买田过户,第二次田主以“潜割本户米,配租若干,售之他人”的方式,将田过户给大租主,第三次大租主“以余租带米”的方式将田过户给白兑之家,这便是“租与赋税的分离”过程。经过三次推收过户,田主、大租主的户名皆不会出现在官府的册籍上,他们皆与纳税无关,而官府册籍上其所拥有的田产属白兑之家。
白兑包揽钱粮的方式,不仅存在于福建,而且还广泛存在于广东,且其操作模式,两省大同小异。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载:
禁白兑。巡按御史戴璟访得潮州府人民多白兑田土,有田十亩而带粮四五石者,其富者幸其免粮而乐与之,其贫者幸其无价而乐受之。及后,贫困不堪,乃又将前田捏作轻粮,骗卖多价,粮无下落。又多方告俵,利在兑田之家,而害归买田之主,故大户有田数顷而无粮输官,此乃饶平一县之极弊也。
据上述史料,“白兑田土”的基本特点是“有田无粮,有粮无田”,而这种白兑包揽,在戴璟眼里与诡寄等无异:“巡按御史戴璟曰:访得南番、东莞、新会、香山、顺德等县,往往产去税存,输纳无备……其究也,飞洒、诡寄不可方物……今之大户势豪,有田无粮者十而五六。”隆庆《潮阳县志》对于潮州府的白兑包揽记载较为详细,嘉靖二十五年(1546),潮阳知县刘景韶言:
查得虚粮来历,原有巅末可据,盖有田则有粮,有粮必有田,是粮出于田之中,不可谓之虚也。……询之耆老,访之士夫,佥谓贴银无价之弊,不出飞洒、诡寄之律,是皆造册之奸巧,实非虚粮之根因也。盖当造册催收之时,富民之避重就轻者,推其粮米,贴以田银而兑之于人,贫民之贪财苟得者,利其田银,受其粮米,而收之入户,于是有无田而有粮者,有田少而粮多者,此贴银无价之说所由起也。又其甚者,则串同造册里书,将其所兑之米,裂为升合,飞洒各户,彼既脱累身之祸,人多受无影之灾。又有破家荡产之子,临此推收之际,故意觅财利己,托辞产去粮存,冒收白兑之米,告俵得业之家,虽云奸弊多端,终非虚粮比类。盖人户以册籍为定,税粮因田亩而科……彼之所谓贴银,所谓无价,所谓诡寄,所谓飞洒者,不过窜东就西,出此入彼。
据上述史料,所谓“贴银无价”,是指有田之家不愿自己交纳赋役,将应纳税额从租银中抽出来,交予愿意承担国家税额的人户,这便是“贴银”;不过,要合法包揽,则需要通过过户这一环节,有田之家无偿将土地过户给白兑之家,这便是“无价”,也就是说,土地过户了,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土地买卖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还需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并纳税的契约。这种买田契劵的内容“大率记田若干亩,转某宅大租岁若干而已”,其实质内涵便是“利其田银,受其粮米,而收之入户”。在知县刘景韶眼里,“贴银无价”和诡寄、飞洒是同一个意思,但具体操作不同,“贴银无价”是指白兑包揽,所以白兑之家并非都有势豪大户的背景,其中包含了贫民(其他文献称之为“兜收积棍”)、破家之子等人户,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不管是大租主还是白兑之家,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包揽行为,尤其是白兑之家更是“积惯揽纳户”,应是“歇家”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白兑之家与田户之间签有“契劵”,也就是说在官府的文档中,白兑之家是“田主”,是“主户”,这或许是“田主歇家”和“主户歇家”的来源之一。实际上,在福建漳州等地,最后真正向官府服役及交纳赋役的多是白兑之家,如康熙《平和县志》载:“一田旧有三主,其弊始于南靖粪土大租之说。买田者为田主,买租者为租主,其田原载粮米,租主全不收,人户只将田租之内抽出三分,付与兑米人户代办条差,而兑米之人名曰白兑,递年取租纳官,谓之米主,由来久矣。”显然,在官方的赋役册籍上,所谓的田产,很多是记于白兑之家,造成了有田无粮、有粮无田的局面。
另外,广西出现的田主歇家,与福建、广东的白兑之家性质类似。“田主歇家”在材料中,一会儿称“田主人”,一会儿称“田主歇家”,一会儿称“保家”。从“田主”两字来看,在官方册籍上登载户主应是“歇家”,他们一般为城居。至少到嘉靖中期,田主歇家在广西已经非常普遍,成为广西地区赋役征收的一大弊端。如嘉靖时期,郭应聘言广西南宁:
乡村小民所以不敢入城见官者,非小民之本心也,皆由附郭田主歇家及熟识之人,或包收其钱粮而未纳者,或揽当其差役而多派者,惟恐原户得知情弊,非彼之利矣。故每见村民入城,则多般吓害,串令吏书杂出小票,催取远年丁粮余银、房价、丧礼、土兵、马价及肨襖、铎木、各色水脚等项,不问是否本户差役,混称某里告贴,东拘西唤,使村民身无所容,复求田主人等代为用钱使释。间有倔强敢于赴官者,官不加察,亦曰此户之人果素躲避粮差者,辄监候追并。村愚之民,谁为辨诉之!苦盖万状矣!父兄子侄,有来奔告者,其被吓害如前,不得已仍凂田主人等到官保认,揭债赔偿,方得脱身。回村不数日,而债主、保家纷纷至矣。致使村人视公门如鬼阈,终其身不敢复向官司一诉。无名索骗,以一科十,惟田主歇家而无少违焉,此地方之通弊,而宣化(今邕宁县)一县为尤甚者。民如之何,不逃且盗也。
据上述史料,歇家是以田主的身份包揽乡民,与福建、广东白兑之家的包揽方式完全一致。田主歇家之所以能够包揽,是因为乡民怕进城交纳赋役。这种害怕源于城里书役衙役曾长期勒索乡民,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一旦欠税,比责起来往往要人的性命,于是乡民为了避免这些危害,便将赋役包于城居的田主歇家。田主歇家之所以能够吓住进城乡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与吏书衙役串通一气,且吏书衙役唱黑脸,而田主歇家唱红脸,互相配合,乡民不得不落入其圈套,只得“用钱使释”。若诉之官司,其苦万状,陷阱愈多,随之恐吓勒索,遍及亲属,失败的总是乡民,最终弄得个“揭债赔偿”。一旦欠债,债主、保家(田主歇家)纷纷上门讨债,弄得鸡犬不宁,结果在乡民眼里“公门如鬼阈”,乡民再也不敢入城见官,于是赋役交纳唯歇家马首是瞻,而歇家由此“无名索骗,以一科十”,成为铁定的包揽者。
三、百姓通过户的整合来应对比限中的各类问题
期限过密,则误工费时,且交纳成本极高,尤其对于普通人户,一旦将赋役分割为4限以上,就会出现每限交纳的赋役数目零碎化,这种零碎化往往导致交纳成本大于应纳数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基层民众开始将数户或数十户整合为一户,将应交赋役的数额扩大,从而减少交纳成本。虽然整合户的过程也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但只要整合的成本低于己户交纳成本,这种情况就会大规模出现。据笔者目力所见,户的整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徽州地区的“甲首户”
自万历以来,南直隶多数地区实行一月3限制,年30限,由于限期过密,零星花户交税成本过高,于是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当时征税对象皆以甲为单位,称之为“户长”或“甲首户”。目前,方志与遗存实物都反映出,万历以后,安徽地区是以甲为纳税单位。首先,看方志是如何记载的。万历《合肥县志》记载了“总由”与“门由”两种纳税通知单的格式与内容。“总由”发给里长,其开写了里长户、甲首户、十甲及畸零寄中户、本里名下绝户等四种类型的户,每类户下分别有实在田地塘若干,应纳秋粮、夏粮、免粮若干,共该丁银、粮银、兑军若干,“总由”不分限。“门由”发给户长,其开写了户长、门丁、各门等三种类型的户,每类户下分别开写实在田地塘若干,应纳秋粮、夏粮、免粮若干,共该丁银、粮银、兑军正耗米若干,分10限交纳税粮。从万历《合肥县志》记载的“总由”与“门由”来看,政府直接征税的对象是里长与户长,而户长实际上就是甲首户,即每甲立一户长,从纳税通知单的发放来看,户长是政府真正的征税对象。
其次,从遗存实物来看,徽州休宁县也是以甲首户为征税对象的。如目前遗存的一张残缺的“休宁县催征万历叁拾玖年(1611)税粮条编(长单)”,即当时的纳税通知单。此纳税通知单是发给“七都三图捌甲程晟”的,这个程晟应是一个甲首户,理由有二:一是该长单的开头便写有“今以本甲丁米麦,算派税粮条编”;二是程晟户有成丁三十丁,如此多的成丁,当是甲首户。因资料珍贵,现将该长单的详细内容录文如下:
休宁县催征万历叁拾玖年税粮条编(长单)
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为立长单,以便稽查,以清弊源事。今以本甲丁米麦,算派税粮条编,银数壹则,分作拾月征比,先壹日将纳数填入长单,候本县对单查簿,有能依限完纳,不必赴县应比,如一二限能完者,定行奖赏,敢有违限拖欠,枷号严比不恕,须至单者。
计开
万历叁拾玖年派征税粮条编科则。
一、税粮
麦,每石派银叁钱壹分伍厘伍毫叁丝陆忽柒微陆廛玖渺玖漠。
米,每石派银肆钱柒分壹厘叁毫壹丝捌忽叁微陆渺肆漠。
一、条编
成丁,每丁派银壹钱壹分肆厘柒丝壹忽陆微柒廛伍渺伍漠。
米,每石征银伍钱柒分叁毫伍丝捌忽叁微柒廛柒渺陆漠。
内徭费优免,每丁免银陆分贰厘陆毫叁丝柒忽壹廛肆渺。
免米,每石免银叁钱壹分叁厘壹毫捌丝伍忽柒廛。
七都三图捌甲程晟
田地山塘
麦,捌石肆斗壹升肆合陆勺该征夏税银贰两陆钱伍分五厘壹毫,
米,拾玖石肆斗捌升壹合壹勺该征秋粮银玖两壹钱捌分壹厘陆毫,
该征条编银拾壹两壹钱壹分壹厘叁毫。
成丁叁拾丁,该征条编银叁两肆钱贰分壹厘捌毫。
以上共派征税粮条编银,内除优免银,仍实征银贰拾陆两叁钱陆分玖厘捌毫,分作叁拾限,每限征银:
二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三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四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五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六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七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八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九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十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十一月 一限 票完银 二限 票完银 三限 票完银
上述纳税通知单,其首开事由,即推行长单的原因、目的以及赋役完欠的奖罚规定,次开科则,包括税粮、丁、徭役、优免派征科则,再开程晟户应纳麦、米、条鞭、丁银各项数额以及总额,最后开写一月3限,年10限,总30限。从事由的奖罚规定来看,甲首户不一定要按这30限一限一限地完纳,可以分作一次或两次完纳。只要提前完纳本户条鞭银的各项赋役就有奖励,拖欠就要处罚。总之在此长单中,政府已经没有把程晟纯粹看作排年,而把其看作户的意图更为明显。
休宁县负责赋役征收的是甲首户,至于甲首户内部如何征收,政府没有任何规定。但是黄忠鑫收集了数份有关赋役征收的合同,其中有几份涉及在比限制度下的甲首户运作方式,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休宁十二都一图二、三甲预备早完钱粮合同,其内容如下:
立合同人二甲里长汪文新、三甲里长汪文谏,为预备早完钱粮以便应役事。切思里役须有二、三甲之分,而钱粮实原一家之事。今蒙县主比并钱粮甚急,奈因数甲难催,应貱不便,故以本家汪氏两甲钱粮及有产东数甲下钱粮并收本甲首钱粮,嘀议预备早纳。其夏麦秋粮,硬在六月完纳;其条编,硬在七月完纳。自议合同之后,皆要体心遵议完纳,违者甘罚银一两,贮众公用。仍依此议为准,今恐无凭,立此合同一样两张,各执一张存照。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四日,立合同人:汪文新、汪文谏,户丁汪延昌、汪文相、汪邦相、汪文杰、汪文诚、汪文谦、汪文蔚、汪应鲤、汪应钟、汪延冕、汪延昂、汪文诏、汪文诲、汪文元、汪文谅、汪应鉴、汪应凤,代书汪文志。
查道光《休宁县志》,祝世禄万历十七年(1589)任休宁县令,万历二十四年(1596)卸任,故合同中的县主指祝世禄。因祝世禄追比钱粮甚急,规定夏麦秋粮必须在六月以前完纳,条鞭银必须在七月以前完纳,期限定得密且紧,致使汪氏家族所在二甲、三甲难以按惯例应付。为了适应新的比限制度,作为负责赋役完纳的二、三甲里长汪文新、汪文谏希望得到家族的支持,不仅要求家族内部成员及时完纳二、三甲的钱粮,而且还要积极完纳一图“东数甲”属于本族成员产业的钱粮,为此制定家族内部完纳钱粮的处罚规定,规定没有及时完纳本户名下钱粮的户丁,罚银1两。在这份合同中,可以看到,汪文新、汪文谏属里长户或甲户,而二、三甲的其他各户叫“户丁(门丁)”,还有一个“代书汪文志”也不在“户丁”内,共20户在此合同中,皆为汪姓,应属于同一宗族,而合同亦称“里役须有二、三甲之分,而钱粮实原一家之事”,可见这是一个占据两个甲的家族。笔者认为,在图甲重组与调整过程中,尤其是均田均役法推行过程中,甲这个单位开始与宗族合并或关联,是户与赋役征收单位相互整合的结果。
休宁十二都一图二、三甲之所以要立“预备早完钱粮合同”,目的是为了能够及时足额完成国家赋役征收任务,是政府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表现,这也是明代徽州休宁县遗存至今的赋役合同的共同特点,如天启三年(1623)二月休宁九都一图设立平济会及会簿议约称:
九都一图立议约。里排郑积盈、程世和、陈世芳、陈泰茂、汪辰祖、陈衡俊、陈梁、陈世明。今因国课催限甚紧,奈因百家人户藐法坐抗,缓以致拖延愆期。本图钱粮浩大,理合照卯上纳,矧今县主督比甚严,现役责并奚愖。今各排年共立平济义会,每甲出银二两,官等兑,朋助均济,轮流交领,预备济急,应卯上纳。其银今付二甲现役程世和收领,每年加一分二厘钱起息,至次年二月十一日,本利一并兑出,付下轮现役收领,换次贮蓄,永为定规。会众面议:递年钱粮以三月十五日为期,各甲俱要一齐磨图完纳。如一排不完者,各排齐出催促,立要即完,不许容情,如违抗拒,呈县究治。如是,齐完国课,共乐雍熙。今恐无凭,立此会议,永远存照。
众议:若各排年之人致期钱粮未完,不得将会内银坐抵。若本县开卯之日,现里预将银两代众克貱,各甲管年者,约二月十一日将前貱银补还现里,以便应会。如抗拒迟延,众排坐催速完,如违,定罚银一两入会。再批。
查道光《休宁县志》,侯安国天启二年(1622)任休宁县令,天启五年(1625)卸任,故这里的县主指侯安国。因侯安国督比甚严,且追比方式是排年(甲首户)轮流应比,一旦出现欠纳的情况,各排年的生命与家产都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自救,他们开始组建“平济会”,以便事先筹备足够的钱粮来应对频频而至的“比卯”,即合同所载“朋助均济,轮流交领,预备济急,应卯上纳”。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比限制度带来的困扰,九都一图的八个排年规定了“平济会”的组织和运营方式。首先,规定每甲出银2两,共银16两,就是为了解决纳银时暂时短缺的问题,但轮役完了以后,必须补足原来的银两及其利息。依此类推,“平济会”保证了每个现役手里除了从各户收取赋役外,还有16两机动银两来应对突发事件,保证能够顺利地足额完成本限的赋役交纳,以避免被血比或高利贷的盘剥。其次,面对欠缴拖延等情况,采取联合催征方式,原先是谁轮役谁催征,而“平济会”则强调“如一排不完者,各排齐出催促,立要即完,不许容情,如违抗拒,呈县究治”,显然是利益相关者组成了联盟,试图依靠集体力量来完成国家赋役征收的任务。
万历时,也有人以合同的形式来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休宁五都四图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订立的合同,即是针对“本图新增人户,居住星散,一时难以催完”的问题,经由十排年的共同商议,形成“每甲出银三两,斗共为三十两之数,以为预防充貱之备”的约定。实际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体现了以里为单位征收赋役的困境。
上述两份合同,实际上代表两种不同的里甲运作方式,前者是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后者是以里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这两种里甲运作方式都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然而,因自万历均田均役法推行以来,甲与宗族渐渐开始高度关联,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成为里甲运作方式的主要趋势。清初的“滚单落甲法”便是这一趋势的结果,而徽州休宁县在天启初以里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显然不合这一趋势。故到天启七年(1627),新任知县朱陛便顺从民俗,变以里为单位为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如天启七年(1627)二月休宁十九都一图十排年钱粮缴纳合同展现了这一变化的前因后果:
十九都一图立合同十甲里排吴仕荣、曹信森、洪宗保、程连、程中和、程子南、巴天盛、程源、程宝善、程高三等,切有本图钱粮,旧例俱属现年征收上纳,至于临卯缺限,独责该里,以致各排逸享安乐,无责比之忧,有兜侵之望。往往沿袭故套,各相拖延,偏累现役赔貱,深为陋规。今际县主朱爷莅任,仁政廉明,厘革夙弊,裒均苦乐,明示晓谕,各纳各甲,花户拖欠,许本甲带比。良法美政,便民利国,普县俱已遵行。各排恐例不能永久,后有变更。身等现役,会集十排,面立合墨十张,到县请印。各排自纳,务期始终如一,俾十甲均沾利益,永远遵行。嗣后如有恃势阻扰者,显系希图侵渔国课,徇私害公。一家抗拒,九家共攻呈治,仍照此墨为据。现年亦不得以私票兜收别甲钱粮,碍法不行。所有先后代过各排充貱钱粮,各轮现役先将各甲充过数目清算,开卯时,即代纳还,其甲方行上纳。今恐久后无凭,立此合墨十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如以路远,往纳未便,许将银倾销真纹,付现年顺纳,将官票缴还,不得稽误。再批。
查道光《休宁县志》,朱陛天启六年(1626)任休宁县令,崇祯四年(1631)卸任,故合同中的“县主朱爷”指朱陛。在前任县令侯安国推行以里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的运作模式下,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各甲是由不同家族(宗族)组成的,而家族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故当别甲轮役当里长时,便互相挖坑。由于追比“独责该里”在前,各甲“无责比之忧”在后,故“兜侵之望”实难避免。朱陛上任后,又变回了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这一改变,实际上对各排年来说有救命救家之功效。因为以甲为单位负责赋役征收,能够调动家族力量来保证赋役及时足额完纳。而以里为单位负责赋役征收,别甲不要说配合,不故意坑蒙已属最好情况,故排年、里长被责比和垫赔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各排年甚怕政策反复,希望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各排自纳”的政策贯彻到底,务期始终如一地推行,不能人息政亡。
除此之外,合同内容还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嗣后如有恃势阻扰者,显系希图侵渔国课,徇私害公”;二是“一家抗拒,九家共攻呈治,仍照此墨为据”;三是“所有先后代过各排充貱钱粮……即代纳还,其甲方行上纳”;四是“如以路远,往纳未便,许将银倾销真纹,付现年顺纳”。这四点说了四个问题,第一、二点是阻止意图恢复以里为单位负责赋役征收的行为,坚决维护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的新政;第二点用家代替甲或排年,说明每一甲便是一个家族,甲与家族已经合二为一,体现了户的整合过程;第三点说明在以往以里为单位负责赋役征收的政策下,各排年代别甲垫赔是一种普遍现象;第四点明确了包揽的合法性,以甲为单位交予现年代纳是可以的,但不允许要求各甲都这样做。
总之,隆万之际,合肥县开始将“甲首或排年”称为“户长”,“户长”之下称为“门丁”,“门丁”之下称为“各门”,体现了里甲制度内部户的整合过程。徽州休宁县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十九年(1611)皆实行以甲为单位负责赋役征收的运作模式,且其甲与家族已经合二为一,到天启三年(1623)时改为以里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的运作模式。但因一里之中有十家,家族之间存在竞争,故在没有“平济会”这样协作组织的里中,问题很多,最后又不得不顺应民俗,改为以甲为单位来负责赋役征收的运作模式。而这种运作模式更适合比限制度下的里甲制度,实际上反映了里甲制度崩溃、改造、变动的过程。这种演变与运作模式在南方地区体现得非常明显,清初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徽州地区的“排年总户”都体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二)山西的“股头制”
山西定襄县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改革以前,该县赋役征收实行“股头包揽制”,实际上就是将一个宗族的人户整合在一户名下,故又称“门头”。万历《定襄县志》载:

据上述史料,民间以“宗支”为单位,形成自己的纳税单位,整个宗支由一人总管,轮流应比,而其他人户“自以银付股头代纳后,便可免于追呼”,这便是利益所在。由于这种“股头包揽制”在山西民间推行很广泛,后来演变为介于“甲”与“花户”之间的一种官方正式的“役”。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西安泽县张文耀言:“惟先年傕收钱粮,各里设有总老并甲老等以董其事,总老专任,甲老副之,厥后甲老废弛,势难兼顾,是以诸事掣肘。耀等生长斯邑,稔悉四十年前一应杂费不及今日三分之一,催粮则总老、甲老、股头相转而行,官民称便。”直到民国,股头包揽钱粮在山西依然存在,1940年,《榆次县厘定征收钱粮章程》载:“钱粮按照街村属地征收,应由街村长副负责办理,所有从前都甲属人办法及递年、股头、屯头等名目,嗣后一概免除。”
“股头”在山西其他地方多称“门头”“总户”,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介于甲与花户之间的一个纳税单位,如光绪初年,襄垣知县李汝霖言:“自今年上忙起,按八十一保均分二十八里,务各近在一处。每里分为十甲,每甲举甲长一人。开征后,里总催甲长,甲长催门头,门头催花户,一气联络,不日即可周遍,花户亦无遗漏。”二是相当于“里甲制度”的甲,如康熙十年(1671),长垣知县宗琮言:“邑征收旧例,每季各里签报百长一人,凡一里之正项杂项俱责成之。往者杂派四出,往往一季未终,百长之皮骨已尽。侯痛革从前陋规,正供而外,丝毫不以累民。杂项既除,并去百长名色,止用门头十长,设柜征收,令花户手封自投,其奸猾不急公者,着本里十长开报。均田均役,各户各税,公私两便焉。”从“门头十长”“本里十长”来看,门头相当于甲。乾隆八年(1743),李高为绛州知州,“创设滚单,照钱粮分数,挨次办纳,不用门头候比,遂尽革里长经收”。这里的门头依然相当于甲。山西长治县也设有门头之役,如“革各里大门头之役”,这里的门头还是相当于甲。门头在山西有些地方也称为“总户”,如山西兴县,“昔分小户,而今混开总户者,不可枚举也”;山西霍州,“每里立甲,每甲设立总户头,催办地粮等项”;山西阳曲县,“每都十甲,每甲设立总户头,催办地粮”。总之,从“股头”到“门头”的历史演变,反映了里甲制度内部户的整合过程,其性质与徽州地区的“甲首户”或“排年总户”以及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类似。
(三)各地的“总户”
在比限制度下,零星小户因其交纳的数额仅有数钱甚至数文,又将这些微小的数额依限再分成数份或数十份交纳,这不仅大大增加交纳成本,甚至细小到无法称量。清雍正以后,清政府推行上下忙两限制,但从遗存的上下忙串票来看,每户交纳银两数超过2两以上者甚少,1两以下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真正的花户每年所纳赋役数额多在2两以下,而自万历到雍正各地推行比限制多是一年10限以上。
在上述比限制度下,合户交纳成为常态,这也得到了政府鼓励。如目前遗存的一张“崇祯五年(1632)六月许成儒将税寄在许六户下完纳的合同”称,许成儒新置买的田产一亩六分七厘,计粮八升九合三勺四抄五撮,推入本族许六、德富名下供解,“所有递年编粮、辽饷,照依官则由票并加耗上官,议定递年清明交付本管许世兴上纳,不致迟误”。显然,这种合同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和鼓励。
又晚明时期,佘自强言:“人之贫富,难以悬揣。自当照田地多寡定之□□,然粮多之家多买吏书户首,飞洒各家,反作零星小户,而痴愚小户,则户首等多并其父子兄弟之粮为一门,反成大家矣。”“多并其父子兄弟之粮为一门”,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比限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政府对这种行为并不制止,而是鼓励。如万历与康熙年间的均田均役,曾推行过“并田并户”的改革。所谓“并田并户”,其中就有鼓励家族或宗族内部整合成一图或一甲。这一点,康熙二十四年(1685),袁国梓在《均田均役条议》中谈得更清楚:
一、并田。凡田地,大约零星置买,分属各图,钱粮既分头完纳,差徭又各处奔驰,甚为民困。今将一己之田,尽收一图,如田多者尽图汇收,田少者尽甲收户,或少至数亩、二十亩不足一甲者,各就弟男子侄亲族共成一甲,务使人自供田合成图甲,则百姓完粮既便,亦不苦差役分扰,庶粮徭易值矣。
……
一、并户。从来立户之弊,患于子户花分,或父兄已故而仍旧鬼名,或殷实田多而捏析名号,户既纷繁,以致征比花户之法难行。今必令并田之时,一人止立一户,业户务须的名,则户少易稽,而征比不烦,一洗花诡之积习。
一、革粮见。先奉宪行革现年、粮长名色,然名虽去而实犹存,或改称柱头,或设当分名色,是欲去粮见而仍移祸于图首、甲首也。今并田并户,则正项钱粮花户各自输纳,凡有杂办差徭,照田承值,可无按甲轮当、挨年催办之事,庶不至以一甲而支十甲之费,以十年而并一年之累,则粮见实可以顿除,歇家包揽之弊亦从此永杜矣。
袁国梓是针对浙江谈的,从“并田”条来看,浙江鼓励各户按家族或宗族整合为甲、为图。从“并户”条来看,浙江鼓励大户将子户整合到自己户下,最终达到“户少易稽”的目的,通过并户的措施来消除“征比花户之法难行”的问题。从“革粮见”条来看,其改革目的是消除中间组织粮长、里长、歇家,实行“花户各自输纳”,从而进一步取消“按甲轮当、挨年催办之事”,废除里甲轮当服役制度。
浙江自万历九年(1581)开始大规模推行均田均役法,到康熙中期时又一次大规模推行。尤其是康熙中期,全国推行一月3限、年30限的比限制度,需要将户的单位扩大来应对分限过密的问题,于是浙江地区出现了“总户”概念。如嘉庆《武义县志》载:“旧志……岁分十限,月分十日,班递统之见役,各房统之值年,而众多之户,分房赴比……然寄庄,海内在在有之,皆立名于册,官得比征,赋无积逋。武人则异是矣,不自立户,附于原主,有通户皆寄庄而己无升合者,有附于总户而混以避税者,种种情弊,乃为逋粮之薮,盖受寄尽出篓户之家。”从“旧志”以及“一月三限”制来看,这里谈的应是明末清初武义县的情形;从“众多之户,分房赴比”以及“附于总户”来看,武义当时推行的是总户催征制,且总户是以宗族为单位。又雍正五年(1727),浙江海宁县推行顺庄滚催法时,发现很多诡寄户不在保甲册内,保甲册内只有总户名,“又总户诡名完纳者,俱将本人正实名号、应分完若干之处,照数填明,毋许隐匿,从前有未入保甲册者,止令补入,免究前罪”。笔者认为,这些总户与广东、福建地区类似,皆是一个家族或宗族名号,之所以如此,与康熙年间过密的比限制度相关。
总户之名号,在全国各地皆有,如万历十年(1582),河南商水知县张德崇防推收之弊的措施是:“责令里书细加磨算,务使门总合户总,户总合排总,排总合里总,里总合县总,则有推无收之弊无自而生,虽百年之久,可保无失额之患。”从“门总合户总,户总合排总”来看,政府是鼓励家族或宗族自我整合成甲成图。明末,邹维琏言其家乡江西新昌县:“盖由易知单册不行,官册只载总户完欠,不列花户粮数,官府只比见年催里,不比管粮本丁,痛痒不切,谁不玩视。且愚民无单,不知当纳之分数,官府无册,不知散丁之欠数,官民常在混沌中。完欠一淆,比较不清,所以良民不免于受殃,顽民正乐于逋负,于是诸奸乘之大胆干没,罪委民欠,卒为官累。”这里的“总户”与“见年催里”是一个概念,“花户”与“管粮本丁”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万历末至崇祯年间,江西新昌县只催比总户,唯总户是问,从而产生了花户不纳粮或拖欠粮的问题。康熙二十四年(1685),安徽贵池知县赵衍在任时,“贵池向多积逋,其弊由于总户催科者,莫得其人,乃为按户清注,俾实田,办实赋,民深便之”。四川苍溪县,“雍正二年(1724),有总户收花户粮银数十两,酒醉遗失道路”。道光六年(1826),陶澍言江苏:“至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每于开征之始,兜收花户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这里明确指出,总户实为同姓一家族集合而成。民国四年(1915),上海宝山县知事茹庆琛言:“旧制每图以十户合成一联,以百亩编成一户,有余不足协軿支配,由县饬发印单,会集同图业户议定后,填明单内,另派总户督率,各联户共同办理。”这里的总户是以10户100亩为单位编一总户,大约是以甲为单位编定总户,而“旧制”当是指清代。上述总户,要么是以宗族为单位构成,要么是以里、甲为单位构成。除比限制度外,总户与里甲组织、宗族的关联极深。
当然,最能反映宗族与里甲制度关联密切的是广东、福建,关于这一点,刘志伟、陈支平、刘永华等皆有深入论述,只不过他们没有将这个问题与比限制度相关联。广东、福建的“粮户归宗”也形成于设限最密的康熙中期,绝非偶然。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清楚,此不赘述。
结语
明清百姓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手段来避役避比,这些手段概括起来有四种方式。一是将土地化零为整,即无优免户将自己土地诡寄在优免户下或包揽户下,从而达到避役避比的目的,这需要通过土地过户这一环节来完成。二是将土地化整为零,由于役起于田亩,田亩越多,役的负担越重,于是土地多的人户,将自己的田花分到田少之户,使自己名下的土地减少,从而达到避役避比的目的,这也需要通过土地过户这一环节来完成。三是将己户田地过户于册书名下,而册书包揽赋役时,常将己粮洒入他户,甚而不把这些田地放入册籍中,形成影射、虚悬等弊端。四是通过贿赂册书的方式,将己户虚悬,即变成虚户,隐藏在国家册籍之外,从而达到避役避比的目的。
通过土地市场将赋役负担转移给他户等方式来避役避比,一般也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田租的方式把赋役从租赋中分割出去,转移到他户身上,其最典型是“一田多主”。在同一块田地上,小租主购买土地时候多出银少收租,将地租收益之中的纳税部分出让给大租主。这种出让是通过土地推收的方式进行的。大租主则是少出银多收租,其租中则包含纳税的部分。这样,在国家册籍登记的田主是大租主,要负责整块田地的赋役交纳,小租主则脱离于国家册籍之外,不需要交纳赋役。二是大租主将含在地租中的纳税部分无偿出让给白兑之家。这种出让也是通过土地推收方式进行的。白兑之家被登记在国家的册籍,正式成为田主,这样一来,大租主也脱离于国家册籍之外,不必负担赋役。通过上述一连串土地市场的交易过程,小租主、大租主皆脱离于国家册籍之外,不承担赋役交纳之责,而本身无田的白兑之家就成为国家册籍上的田主。白兑之家这种包揽方式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一带,而在广西等地则叫田主歇家。
在比限制度下,零星小户因其交纳的数额仅有数钱甚至数文,再将这些微小的数额依限再分成数份或数十份交纳,这不仅大大增加交纳成本,甚至细小到无法称量。面对这些问题,各地采取了将户扩大的方式来应对比限,其方式主要有三。一是安徽地区的“甲首户”。在徽州地区,主要按家族或宗族为单位,整合成一甲或数甲的方式来应对比限,史称“甲户”或“甲首户”;在安徽合肥地区则叫“户长”“甲首户”。“户长”之下叫“门丁”,“门丁”之下叫“各门”,也就是说在甲首户之下,按宗族中的“房支”整合成门丁,而门丁之下的各门应是指花户,合肥地区是按“各门(花户)→门丁(房支)→户长(甲首户)”的结构模式进行整合。由此,户的概念变得异常复杂。二是山西地区的“股头制”。将各宗支整合为一户,便叫“股头”,“股头”之下便是“门头”,“门头”之下是“各门”,山西地区按“各门→门头→股头”的结构模式进行整合。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革除“股头制”的事例来看,政府希望按各门之户来征税,把门称为“花户”,把发给花户的纳税通知单称为“门单”。但这个改革并没有成功,后来山西基本上是按门头来征税。门头相对于里甲制度来言,有两个概念,其一指甲长,这种门头一般叫“总户”;其二指介于甲与花户之间一个征税单位。三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的“总户”。户的结构模式是“总户→子户→爪户”,其特色是“粮户归宗”。
总之,明清时期避役避比的手段对明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推动了土地市场的复杂化。将上述前两种避役避比的手段进行对比考察,便会发现,不管是诡寄、花分、飞洒、影射等,还是大租主将赋役包于白兑之家,大多数都是通过土地过户这一环节来实现的,即通过土地市场来达到包揽目的。虽然很多土地过户并没有真正进行过买卖交易,但政府一方却认定已经发生了地权转移和业主更换,而诡寄、花分、飞洒、影射、白兑等真过户假买卖的行为,刺激了地权的分层与分割,使得明清土地市场出现极为复杂的面相。总之,地权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应该受到了上述舞弊手段的影响。
其二是推动了赋役制度的变革,包括赋役征收与赋役册籍制度两个方面。就政府方面而言,上述前两种避役避比的手段造成了大户变小户、小户变大户以及有田无粮、有粮无田的局面,对赋役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破坏。大户变小户、小户变大户后,徭役佥派无法有效推行,有田无粮、有粮无田后,赋役征收无法有效推行。针对上述问题,政府要么采取清赋的方法,于是出现了烟户册、田根册、图册户籍等五花八门的册籍,甚至重造鱼鳞图册;要么采取从“以户配役”变为“以田配役”的方式,而这里又包含了升里并里法、保甲法、均田均役法、摊丁入亩、顺庄法等变革。但不管哪种解决方式,只要设限过密的制度存在,上述避役避比的手段总会层出不穷,无法根治。
其三推动了乡村内部包揽网络的形成。上述前两种避役避比的手段几乎都是利用优免制度与以户配役的漏洞,进行变相的包揽,皆是在户与土地这两个决定赋役数额的因素上做文章。从实质上看,这属于乡村内部损人利己的行为,且几乎都是乡村内部的一种包揽行为,大大促进了乡村内部包揽网络的形成:通过诡寄形成了优免户的包揽圈,主要由乡绅等构成;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形成了册书的包揽圈;通过白兑之家、田主歇家等形成了地方势力的包揽圈,包括势豪大户、兜收积棍等;通过户的整合逐步形成了宗族内部的包揽圈。这些包揽圈叠加起来,便会构成一张巨大的乡村内部包揽网络。
其四推动宗族势力的发展。如诡寄,受寄对象多是族人、姻亲、门生、故旧之田,甚至有的乡绅将一族的田全部收入自己户名之下,由自己代纳赋役,这些行为显然可以加强一族的内部团结和归属感。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明清时期出过生员、举人、进士以及官员的宗族以及有军户等优免户的宗族,其宗族组织发展相对于没有优免户的宗族更为完善和严密。虽然诡寄不是唯一原因,但其影响不可小觑。至于通过户的整合来应对比限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这个户的整合皆是在宗族内部进行,致使一族之人常常共同面对困境和解决问题,这直接推动了宗族的内部整合与凝聚。明清宗族的长足发展,应该与比限制度的推行有着深切的关系。
注释
②参见梁方仲:《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20-221页。
③[明]陆深:《俨山外集》卷1《传疑录上》,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页下。
④光绪《嘉兴府志》卷22《田赋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2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第574页下。
⑤[清]赵廷臣:《定催征之法疏》,[清]徐栋:《牧令书》卷11《赋役》,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99页上。
⑥参见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9-140页。
⑦[明]刘光济:《差役疏》,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25《艺文》,见《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8页上。
⑧[清]佟彭年:《议差粮里催轮回文》,[清]徐栋:《牧令书》卷11《赋役》,见《官箴书集成》(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01页下-202页上。
⑩[清]戴兆佳:《天台治略》卷1《一件严饬编造以杜混淆事》,见《官箴书集成》(第4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30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