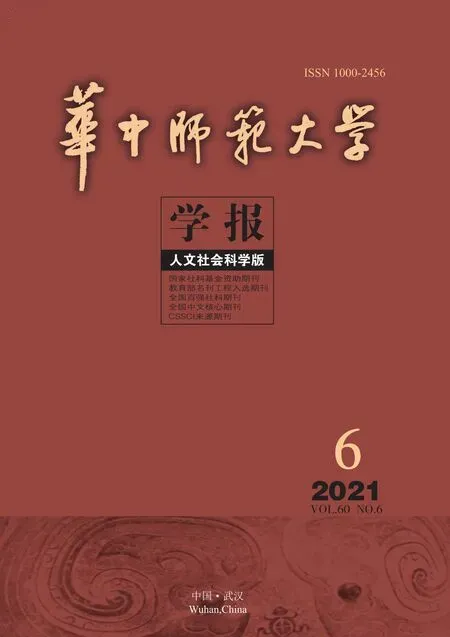“疫情补贴”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经济?
——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对比分析
王 胜 赵浩权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2020年初,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灾难突然席卷全球,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肺炎认定为全球“大流行病”,前所未有的形势变化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毁灭性打击。世界银行6月8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提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其防控措施带来的经济“停摆”,全球经济将在2020年陷入严重收缩,预计人均收入降低3.6%。报告预计,由于内需、供应、贸易和金融严重中断,202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收缩7%,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脆弱性也将被外来冲击放大,IMF预计新兴经济体2020年GDP增速为-1.1%,是近几十年的首次负增长。除实体经济外,金融行业也受到来自疫情的巨大冲击,由于疫情对实体行业的冲击以及投资者的恐慌心理,上证指数从2020年初的3115点降低到3月末的2660点,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从2月初的29551点降低至3月末的18592点,期间3月甚至触发4次股市熔断机制,VIX指数一度上升至历史最高位的82.69,股市崩盘速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由于出行限制、抵制人群接触与停工停学等原因,全球72亿人口都切身体会到因防控疫情而抵制人群接触对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在重大危机面前,市场难以自行调整,必须依靠和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面对消费、就业、产出大幅下滑的压力,一些政府选择实施应对新形势的经济刺激计划,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与美国均在3月先后推出了对受疫情影响的人群发放紧急救助资金即“疫情补贴”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对于美国发放的1200美元“疫情补贴”,根据美国阿斯彭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大多数领取者将补贴用于支付账单和购买生活必需品,短时间内迅速花费了大部分资金,这也凸显了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除刺激消费外,为刺激投资增长,美国还同时使用货币与利率两种政策工具,推出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再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零。
以上事实让我们认识到,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挑战,货币政策需要更积极地跟随形势进行调整,面对消费、产出严重萎缩以及失业率上行压力,需要积极的财政刺激方案推动经济回暖。中国政府也推出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的补贴政策,如武汉市向2020届毕业生发放1400元就业补贴,南京、江西、济南等地发放多种文旅消费券等政策,以支持企业和居民渡过难关,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相比之下,我国的补贴受众人群与补贴力度仍然较小。而在疫情危机下,政府干预力度决定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通过财政补贴减少因需求降低导致的就业影响十分重要①。其他国家发放“疫情补贴”的刺激计划是否值得中国采纳?在新环境下的积极货币政策措施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在疫情冲击后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选择与政策措施的经济影响,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在当今新形势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全球疫情持续升温,更多国家采取“封闭”政策带来的贸易停滞,以及疫情影响的全球统一性,本文建立了一个封闭经济DSGE模型,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货币持有量(Money in Utility)以着重考虑疫情前后家庭对自身实际货币余额的偏好,同时加入抵押担保约束以表现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与利率相比,货币供应量对产出没有任何短期影响,这与目前一些学者的理论研究不符②。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传统的MIU模型将货币加入家庭的预算约束,货币供给的增加在当期直接提高家庭财富,这与现实中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调控市场中的货币而使得政策传导滞后的情形不同。而当期提升家庭财富的政策效果与现实中为刺激消费重振经济提供救助资金财政补贴的情形一致,因此将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提升对经济的短期影响理解为“疫情补贴”的形式可能更加贴合模型设定。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将货币供应对家庭部门“疫情补贴”式的短期影响纳入NK-DSGE模型中,对比分析了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政策措施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差异,以研究“疫情补贴”在危机后的相对作用,还模拟了疫情发生后消费、产出、劳动供给大幅下滑的实际情形下两种措施的政策效果变化差异;第二,模拟了疫情恶化后宏观经济在两种货币政策下受到的影响,对比了经济进一步衰退后实行两种货币政策下的经济稳定性;第三,通过反事实实验对现有的货币政策规则具体参数进行小幅调整,对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调整、改进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研究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选择与调整。灵活的规则性货币政策近年来成为学术界货币政策分析的热点,而规则性货币政策主要分为McCallum提出的以基础货币作为政策工具调整经济的数量型货币政策③,以及Taylor提出的以调整短期名义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的价格型货币政策④。实际上,学术界对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而学者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利率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等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Laurens和Maino通过VAR模型发现单独的利率政策在实现通胀稳定目标时,相对于货币供应政策的效果是不显著的⑤。Koivu等认为利率还没有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相关模型中过于强调短期利率的泰勒规则并不合适⑥。胡志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现状主要是由当前经济金融体制决定的,因此具有行政色彩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⑦。盛天翔和范从来的状态空间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后的数量型工具对经济的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工具⑧。当央行注重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时,刘喜和等的研究表明此时数量型规则的效果强于价格型⑨。
然而由于传导滞后性、可控性与受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等缺陷,随着国际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推进,近年来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效。Galí和Monacelli的研究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引起的福利损失低于数量型政策⑩。Zhang在封闭经济DSGE模型中比较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认为在管理宏观经济方面,价格型规则比数量型规则更有效。马文涛在其基础上将模型拓展为开放经济,引入了贸易顺差、金融加速器等因素,结果也表明价格型工具优于数量型工具。王君斌等分别使用SVAR和DSGE模型,均得到价格型工具更优的结论。
因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都存在一定缺陷,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混合型货币政策是利率市场化之前过渡时期的最优选择。岳超云和牛霖琳的研究发现在利率规则中加入货币因素能带来模型对数据解释能力的显著提升。Liu和Zhang、张杰平、王曦等的研究都认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优于单一的数量型或价格型规则。卞志村和胡恒强指出我国在利率市场化还未完成的现阶段,央行应该在不放弃数量型工具的同时,逐渐增加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比例。伍戈和连飞的研究也表明实施混合型的货币政策规则要比单一的政策规则更能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实际上,学术界对于不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没有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不同的经济环境以及不同的冲击来源会使得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出现差异。在面临不同来源的经济波动时,两种货币政策各有优劣。面临不同的经济环境,在经济萧条时期,央行更希望促进经济发展,此时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效;在经济高涨时期,央行更希望稳定经济波动,则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效。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学术界对中国最优货币政策选择仍没有定论,但是大多都强调了货币政策因外部环境、经济形势变化做出调整的重要性。虽然我国货币政策总体需要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但是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明显表现出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特征。在面临重大危机时,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否会提升?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调整?目前没有文献在疫情带来经济严重衰退的新形势下对比分析中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选择,回答以上问题不仅能丰富在特殊情形下货币政策的研究,对于现阶段经济提振、产业复苏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采用严谨的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对比分析疫情冲击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疫情恶化冲击下的经济稳定性。
三、理论模型
(一)耐心家庭部门
假设家庭部门个体完全同质,通过购买国内债券Bt实现跨期消费平滑,通过选择消费Ct和劳动供给Nt以及持有实际货币余额mt来追求期望效用现值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形式如下:
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实际货币余额mt,其满足mt=Mt/Pt,表示家庭在t期末持有的名义货币余额,并在t+1期使用。效用函数中的β为家庭部门的主观贴现因子,v反映了其消费习惯程度,ξt、φt与ψ分别是家庭的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偏好与货币需求参数,η是劳动的Frisch弹性的倒数。家庭预算约束如下:
PtCt+Bt+Mt=WtNt+(1+it-1)Bt-1+Mt-1+Tt
(1)
其中,Pt为消费价格指数,Wt是耐心居民的名义工资,it表示本国债券的名义净收益率。Tt是家庭部门得到的政府转移支付。Bt是家庭部门所持有债券的总额。因此,家庭部门就是在给定的市场价格水平和各种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最优的变量集{Ct,Nt,Bt,mt}来实现其效用函数最大化。
(二)企业家部门
和家庭部门不同,企业家的耐心程度较低,因此企业家部门可以直接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有代表性企业家的效用函数具体如下:
效用函数中的βe表示企业家部门的主观贴现因子,因为比家庭部门更加不耐心,因此βe<β。与家庭部门相同,v反映了其消费习惯程度,ξt是企业家的消费需求,η是劳动的Frisch弹性的倒数。除了预算约束条件,企业家部门还需要考虑资本积累方程和抵押担保约束,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2)
(3)
(4)
对于企业家的抵押担保约束,由于侯成琪和刘颖发现相比外部融资溢价的价格型金融摩擦,抵押约束机制的数量型金融摩擦设定对中国信贷市场更贴合,因此本文借鉴Kiyotaki和Moore与Liu等的设定,企业家的借贷合约执行需要一定成本,即债权人清算时仅能变现θ比例的资产,而此参数的上升意味着抵押担保约束的放宽,即后文提到的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企业家的最优决策就是在给定的市场价格和各种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决策变量集合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三)最终品厂商部门
假设经济中有一个代表性的完全竞争的最终品厂商,使用生产技术生产最终品Yt如下:
其中,Yt(j)表示第j个中间品厂商生产的中间品,σ表示不同中间品的替代弹性。在给定生产技术下,最终品厂商将最终品价格Pt和中间品价格Pt(j)视为给定,选择中间品数量Yt(j),以最大化其利润。基于以上设定,我们容易得到中间品Yt(j)的需求函数以及总价格水平指数的决定形式,如下所示:
(四)中间品厂商部门
假定经济中有一定数量的垄断竞争的中间品厂商,都使用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中间品Yt(j),即:
Yt(j)=AtKt-1(j)αNt(j)1-α
其中,Kt-1(j)表示中间品厂商j的资本需求;Nt(j)为劳动需求;At为所有中间品厂商共用的技术变量,其变化形式满足一阶自回归AR(1)过程:
本文考虑经济中名义刚性的存在,假设中间品厂商定价策略满足Calvo的交错定价机制,即每一期任一厂商有θp的概率无法调整价格,剩下的厂商可以将当期价格设置为最优价格同时,为了消除稳态下的垄断扭曲,假定政府对厂商的边际成本给予τ=1/σ的补贴,因此其利润函数为:
其中vt,t+j=u′(Ct+j)/u′(Ct),运用拉格朗日法可以得到最优价格设定:

(五)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主要研究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因此考虑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进行比较以给出政策建议。
1.数量型货币政策
(5)

2.价格型货币政策
央行将名义利率it作为政策工具,参考王胜等,黄志刚和郭桂霞的设定,在封闭经济下,央行采取同时盯住消费价格通胀、产出缺口的利率规则,具体如下:
(6)

(六)市场出清
商品市场出清:
要素出清条件:

四、参数校准
由于国内关于两种货币政策分析的文献较多,本部分直接参考其他文献进行参数校准。参考王曦等将家庭和企业家的时间贴现率分别设置为β=0.993和βe=0.98。按惯例将消费需求参数设定为ξ=1。参考郭豫媚等将消费偏好的惯性参数取值为v=0.7,将资本调整成本参数设置为常用取值即κ=2.5。参考Chang等将效用函数中劳动与实际货币余额参数分别设定为φ=1,ψ=0.06,劳动力的Frisch弹性倒数为η=2。由于我国消费GDP占比与投资GDP占比非常接近,将资本折旧率与资本生产份额参数设置为δ=0.05,α=0.5。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将企业的抵押担保率设置为θ=0.6。国内中间品厂商的价格黏性参数取值为常用值θp=0.75。将生产技术滞后系数设定为ρA=0.9。参考Zhang将数量型货币政策滞后参数取值为ρm=0.8,货币供应增速对预期通胀反应积极,取值为ρπ=1.0,对产出反应较低,取值为ρY=0.5。参考王胜等将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胀与产出盯住系数取值为θπ=1.6,θY=0.35。
五、数值模拟
本部分我们将主要利用脉冲响应来估算在当下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不同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通过对理论模型的模拟,我们发现提高名义货币供给的扩张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降低名义利率的扩张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都是利好影响,这符合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经济理论。但在消费需求、劳动供给大幅下降的疫情期间,选择更为高效的政策措施对于货币当局而言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外部环境变化时,比较不同货币政策的经济刺激效益更具现实意义。
此外,由于全球确诊人数突破千万后疫情仍然不断扩散,且即便疫苗面世后我国仍有多地出现新增案例,不仅疫情冲击短期内难以缓和,甚至存在出现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探究后期疫情恶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比较不同货币政策下经济的波动情况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经济急剧下滑、复工复产需求提升的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目标权重是否要随形势而动需要严谨的经济理论和数值分析证据支撑。综上所述,本部分我们主要考虑三种情形:(1)在疫情冲击下产出、消费、劳动供给等宏观经济状况大幅萎缩的现实情形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分析;(2)在疫情进一步恶化时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分析;(3)疫情形势下对于货币政策规则调整的反事实实验。
(一)宏观经济状况大幅萎缩时货币政策措施的经济影响
1.疫情冲击前经济影响
图1为正常情况下对货币供给增速提供2个标准差正向冲击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对名义利率提供1个标准差负向冲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脉冲响应。
从图1可以看到,对货币供给增速提供2个标准差正向冲击与对名义利率提供1个标准差负向冲击对经济的正向刺激效果较为接近,在两种货币政策下冲击都使产出提高2%左右,消费提高0.3%左右,投资提高6%左右。

图1 疫情冲击前两种政策措施的经济影响
在货币当局实施政策措施时,刺激效果随目标变量迅速传递到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数量型货币政策表现为家庭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迅速上升,这使短期内的消费与债券购买迅速上升,企业家通过债券融资带来资本存量与投资的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表现为名义利率迅速下降,短期内释放家庭存款使得消费迅速增加,同时企业家的融资成本随低利率而下降,带来资本存量与投资的提高。两种政策都直接导致产出的上升,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使得劳动供给随之提高。这也带来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从而导致了通胀的短期上涨。
在带来产出、消费与投资上涨相近幅度的基础上,似乎数量型货币政策略胜一筹:一方面,在带来消费均上涨0.3%的同时,尽管带来了更高的通胀水平,数量型货币政策下的政策措施对产出、投资的刺激作用略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实际工资与劳动供给的正向影响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尽管各变量回归稳态的时间相近,但是对于产出、消费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刺激作用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维持得更久,具体体现为这些变量的波动下降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平缓。
2.疫情冲击后经济影响
(1)疫情冲击后宏观经济衰退情况
疫情期间因出行限制加上大部分商家关闭门店,消费需求大大下滑,且大部分企业全面停工,劳动供给也大幅下降。消费需求与工作时长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社会消费水平大幅下滑,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悲观预期使得投资下降,带来整体产出的衰退。图2为中国几种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率季度情况。

图2 宏观变量增长率变化
从图2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城镇投资在疫情冲击前均保持5%以上的增长率,然而2020年第一季度均大幅下滑为负增长,第二季度GDP略有回升,但消费与投资增长率仍然为负。此外,人民币贷款总额在冲击后增长率不降反升,增长率由此前的2%左右提高至4.6%。
本文认为,贷款总额逆势增长源于我国的市场机制:中小企业占我国总体产出相当大的部分,但是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缺陷,突发的疫情让中小企业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根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对995家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的问卷调查,58.05%的企业营收预计下降20%以上,超过2/3的企业资金维持能力不超过2个月。一旦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引发的不良贷款、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冲击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为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税收、补贴等政策举措,包括减免中小企业房租费用、降低税费、“五险一金”的减免缓缴安排以及提供贷款支持等,舒缓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使得贷款总额略有提高。
尽管商业贷款所受影响不大,总体经济因疫情影响仍然遭受巨大冲击。为了反映宏观经济遭受的冲击大小,图3描述了几种宏观经济变量的水平值变化与其疫情前增速外推水平的差异大小。
从图3可以看到,除贷款总额相比冲击前外推水平略有提高之外,产出、消费与投资均相对出现大规模下降,相对于冲击前的经济增速外推水平,疫情毫无疑问带来了经济增长稳态的波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进入了10余年的衰退调整期,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造成的影响更严重,尽管疫苗已经面世,但是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疫情再次抬头的情况,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而恢复产能的问题将持续更长时间,因此为考虑经济衰退的长期性,本文接下来将在宏观经济的稳态衰退下进行模拟。

图3 几种宏观经济变量轨迹模拟对比(2018Q1=100)
此次疫情波及全球,使得各国社会生产与消费投资暂时停摆,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时受到抑制。而疫情带来的波动主要源于人与人断绝接触带来的供给端劳动供给、消费能力下降与需求端消费意愿的下降,因此本文将考虑经济中消费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带来的影响。
此外,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在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政策执行方面将有针对性地向小微和民营企业加大倾斜,通过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投放提高资金支持的质效,并且对因为疫情影响出现借贷、还款困难的企业给予贷款支持以及展期或续贷,以缓解迫在眉睫的融资与还款付息压力。基于前文贷款总额的逆势增长,本文假设其主要源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为了在模型中模拟这一政策扶持端的影响,具体体现为政府为缓解中小企业困难考虑放宽企业融资约束,放松抵押担保约束,带来贷款水平的相对提升。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根据疫情冲击主要源头与实际数据的变化调整消费需求参数、劳动供给参数与抵押担保约束参数以反映整体宏观经济的衰退。经过多组参数调试,为与实际数据相匹配以拟合经济的衰退,最终将消费需求参数降低为ξ=0.55,劳动供给参数提高为φ=1.05,抵押担保约束参数提高为θ=0.72,分别代表停产停工足不出户后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劳动供给下降与政府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扶持。疫情冲击后参数调整导致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大幅下降,所得经济中的主要变量(产出、消费、投资与信贷)降幅与前文实际数据相对冲击前增速外推水平的降幅比较吻合,此调整能够拟合疫情发生后经济大幅衰退的实际情形。表1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前后稳态值的变化。

表1 疫情冲击前后宏观经济稳态变化
从表1可以看到,调整消费需求、劳动供给以及抵押担保约束参数后,除产出与投资降幅略有差异以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稳态变化均与实际数据的模拟较为贴合。关于劳动供给,虽然中国2020年6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较2019年末仅上升1.38%,但疫情对于劳动供给的冲击不能只看失业率,且调查失业率会存在明显的抽样误差,因指标口径、未充分就业等原因,真实的失业率应更高,疫情期间会更为明显。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的报告,受工作场所关闭、企业裁员与消费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估计疫情使得今年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14%。鉴于中国在防疫工作上的严谨负责态度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对复工复产以及消费行为更加严格的管控使得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损失高于全球平均值更加合理,因此近20%的劳动供给降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2)经济衰退后货币政策效果对比
疫情冲击导致经济状况大幅收缩,最直接表现为消费与劳动供给的大幅下降,进而带来投资与产出的下滑,参数调整后的经济情况变化基本逻辑与现实情况相符。本文这一部分将在此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比较两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图4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政策措施效果对比。
从图4可以看到,在提供同样大小货币政策冲击的情况下,疫情冲击前政策效果接近的两种货币政策在疫情冲击后的政策效果产生了明显差异: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在疫情冲击前后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在雪中送炭的“疫情补贴”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刺激效果显著提升,相对于基准情形,消费刺激提升了约0.1%,产出与投资刺激提升约1%,政策效果更优。

图4 疫情冲击后两种政策措施的经济影响
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在疫情冲击后对货币供给增速的冲击导致家庭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提升,但是上升幅度小于疫情冲击前的提升效果,然而冲击后带来的经济刺激效果有明显提升:疫情冲击后消费、劳动供给与产出大幅下滑的环境下,提供“疫情补贴”使得家庭预算约束中的货币余额提高,对消费、投资等刺激效果更优。在因疫情出行困难、工作停滞与收入大幅下滑后,居民因预算约束与消费不便等原因导致消费大幅收缩,直接提高家庭货币余额的“疫情补贴”可以良好刺激消费需求,甚至导致长时期压抑消费后的“报复性消费”。从结果看,直接性的货币补贴对经济的各方面均有良好的刺激作用,在疫情冲击后的影响更为明显,对刺激经济回暖有较好的效果。
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在疫情冲击前后几乎没有差异:各变量的增幅与回归稳态的时间几乎相同,而消费提升后在短期内的下降幅度甚至更高。在疫情导致消费需求、劳动供给大幅下降时,对外部环境和未来收入风险担忧的居民急需实质型的补贴,而对债券的需求无明显提高。没有收入来源使得居民对货币余额和未来稳定收入来源的需求更高,在此情况下更偏好于安全资产,将现有货币余额用于提高消费并不符合大部分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的观念,此时降低名义利率并不会对经济产生更优的刺激作用。
从结果看,降低名义利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措施在疫情前后的经济影响几乎一致,而提供“疫情补贴”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措施在疫情冲击后的经济衰退期间的政策效果更好,对刺激经济回暖有较好的效果。
(二)疫情恶化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
全球疫情短期内难以结束。从国内看,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考察组曾在3月称“中国疫情二次爆发是大概率事件”,而从疫情基本控制后,北京、新疆、大连先后再次突增确诊病例的现实,除了加大疫情防控力度以外,国内应当做好疫情二次爆发可能的准备。从全球来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全球疫情的发展仍处于上升期,而其中西方国家对疫情的轻视态度与第三世界国家对疫情防控的能力不足都加剧了疫情扩散的可能,即便中国目前能完全防控,也难以在全球独善其身。
基于上述现实背景,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做到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疫情的长期存在以及疫情恶化的情况。本部分将重点探究疫情恶化时宏观经济影响与货币政策的选择。结合前文所述,疫情恶化后,将从需求和供给端对经济造成影响,同时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以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为检验疫情特殊时期货币政策在长期的稳定性,在疫情冲击后分别考虑来自消费需求、劳动供给与抵押担保约束的三种冲击以代表疫情恶化的外部环境变化,并比较两种货币政策下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探究疫情恶化时的经济影响,因此外部环境设定为疫情冲击后,即产出、消费与投资大幅下滑时的情形。各变量的稳态值分别取值为疫情冲击后的校准值:ξ=0.55,φ=1.05,θ=0.72。
1.负向消费需求冲击
从图5可以看到,面临负向的消费需求冲击,在两种货币政策下的消费均下降0.5%左右,但是对于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影响,两种货币政策的反应有所不同。

图5 负向消费需求冲击的经济影响
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虽然负向消费需求冲击导致消费出现下降,但由于短期内投资大幅提高,最终使得产出不降反增,同时短期内实际工资下降幅度远低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而劳动供给也出现上升。这是由于家庭对货币余额持有存在偏好,而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对货币余额的偏好相对上升,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对货币供给增长的预期为零,因此家庭选择缩减消费,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以提高货币余额持有应对将来的疫情风险。此外,对于企业家而言,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短期内投资的大幅上升,使得资本存量持续上升,劳动供给与资本、投资的增长导致了产出的上升。尽管产出略有上升,但实际工资和资本回报的下降导致厂商边际成本的下降,带来了通胀水平的下降。
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下,负向的消费需求冲击直接导致了消费与投资的下降,进而带来产出的下滑,劳动供给与实际工资出现大幅下降。由于家庭对货币余额的偏好以及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对货币供给增长的预期,货币余额增长预期带来劳动供给偏好下降。此外,劳动供给大幅下滑带来的产能下降导致企业家的收入下降,进而带来投资下滑,资本存量缓慢上升,在消费规模下降的同时最终导致产出缩减。与疫情前后的政策冲击情形相同,数量型货币政策为刺激经济增加了货币供给,牺牲了通货膨胀的稳定,表现为面临冲击通胀水平的波动明显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
可以看到在负向消费需求冲击下,似乎价格型货币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在各经济变量波动更小的同时,还带来了产出、投资与劳动供给的提升。这主要源于家庭部门对货币余额持有的偏好,以及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对货币供给增加的预期使得其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下的劳动供给变化方向相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部分只模拟了消费需求的负向冲击,在实际的疫情恶化冲击下,劳动供给也必然大幅下滑,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劳动供给逆势提高的情形难以实现。
2.负向劳动供给冲击
从图6可以看到,面临负向的劳动供给冲击,两种货币政策下劳动供给均下降0.5%左右,但应对冲击的反应截然不同,体现为各自的货币政策工具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的变化差异。在不同的政策反应下,负向劳动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图6 负向劳动供给冲击的经济影响
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在劳动供给下降带来的闲暇增加导致消费短期内略有上升,但之后由于工资收入的降低使得消费与货币余额持有迅速下降。负向劳动供给冲击带来的产能下降使得企业家的资本存量与投资立刻下降,两种影响联合直接导致产出的下降。价格型货币政策下,由于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给予了较高的权重,面对持续的产出缺口与正通货膨胀率,货币当局权衡决定持续提高名义利率以稳定通胀。
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下,消费、劳动供给、投资与产出等都在负向劳动供给冲击下出现了下滑,但是在货币供给持续提高的刺激作用下,大部分变量都在3期以内回归到了稳态值,甚至消费在冲击出现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增长态势,体现为消费由冲击当期的下降到冲击后15期上升0.2%左右。数量型货币政策下,产出缺口与通胀水平的下降导致货币供给增速上升,但是为刺激经济复苏,持续的货币供给增长分担了由劳动带来的消费提升作用,使得产出的劳动份额下降,导致实际工资与通胀水平波动较大。
面临负向的劳动供给冲击,可以看到相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更佳,具体表现为各变量的下降恢复稳态的时间缩短,以及短期内对消费、投资与产出的正向影响更高。但是为了经济企稳,数量型货币政策牺牲了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表现为通胀水平下降0.4%左右。
3.正向抵押担保约束冲击
从图7可以看到,面对正向抵押担保约束冲击,企业家的融资约束下降,更多的融资使得企业家的收入提高,进而带来投资与资本存量的上升。但是面临冲击,两种货币政策下的宏观经济变量影响大有不同。

图7 正向抵押担保约束冲击的经济影响
在价格型货币政策下,企业家放宽融资约束带来的投资上涨导致产出和通胀的提高,为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货币当局提高了名义利率。由于企业家贷款规模的提高以及名义利率的上调,家庭部门的消费与货币余额持有下降以购买企业家发行的债券,在消费下降与投资上升的共同作用下,产出略有上升,而劳动供给与实际工资没有显著变化。
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下,由于名义利率在当期略有下降,以及家庭持有货币余额略有降低,家庭部门选择增加消费以弥补货币余额降低的效用损失,消费在短期内有所提高。此外,在企业家抵押约束放松带来投资与资本存量大幅提高下,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产出上涨0.4%左右。为支撑更高水平的消费,在货币余额持有下降的情况下,家庭的劳动供给提高,因其上涨幅度低于产出上涨幅度,实际工资提高并带动通胀水平的上升。在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的上涨与通胀水平的上升导致货币供给增速下降,实际货币余额略有降低。
与负向消费需求冲击和劳动供给冲击不同的是,在前两种冲击下,无论采取哪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而在正向抵押担保约束冲击下,只有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价格型货币政策下的经济波动幅度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恶化时,政府放宽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减少企业压力,促进企业扩大融资规模以带动投资、产出的回暖,根本目的在于扶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从扶持目的来看,通过提高名义利率以稳定经济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反而降低了政策实施效果,而牺牲通胀稳定换取产出、投资、消费与劳动供给上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则更加符合当下情形的需求。
4.福利损失对比
由前文结果,仅从脉冲响应来看难以判断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新形势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因此本部分借鉴Woodford与刘斌关于央行福利损失函数的设定:
央行希望同时降低通胀与产出的波动,假定中央银行与家庭有相同的时间偏好β,λ代表央行对于产出波动关注的相对份额,值越大代表央行越倾向于减少产出的波动。本文给出λ的三个取值:0.5、1与2,分别代表央行对产出波动关注的不同权重水平。表2表示了当n取20时,在两种货币政策下,外生冲击(消费需求冲击、劳动供给冲击与抵押担保约束冲击)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情况。

表2 三种货币政策规则下福利损失
数量规则与价格规则下的福利损失都主要来源于消费需求冲击。随λ提高,根据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加总比值可以看到,数量型规则的福利损失相对更多来源于通胀水平的波动,而价格型规则更多来源于产出水平的波动。从福利损失的水平加总来看,无论λ取值位于哪个区间,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都更高,并且随央行对产出波动的关注度提高,二者的差距不断扩大。
结合前文的结果,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疫情冲击后的政策措施效果相对下降,并且在疫情恶化冲击后产生了更高的福利损失,同时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而降低抵押担保约束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而相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福利损失上表现更优的同时,避免了产出水平更大幅度的衰退。总而言之,无论是疫情冲击后的货币政策效果,还是疫情恶化冲击后的经济波动水平与经济提振效果,数量型货币政策都表现更优。
(三)货币政策调整反事实实验
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对各国经济、民生带来不容忽视的冲击,在此等特殊形势下,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应当完全遵循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更加灵活适度,为使经济面临“二次冲击”时拥有更大的抵抗能力和更大的回旋空间,可适当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调整以在面对疫情冲击时降低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幅度。
由前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牺牲通胀稳定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上的政策效果更好,并且在疫情恶化时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上取得更优的成果。参考Zhang,本部分将进行在疫情冲击后对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适度调整的反事实实验。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相对利率规则产出波动更低,通胀波动相对更高,本部分将同时假设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增速分别更盯住产出缺口与更盯住通胀水平,并模拟比较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差异。调整具体体现为(5)式中通胀水平盯住系数分别调整为ρπ=0.8,1.2,产出缺口盯住系数分别调整为ρY=0.7,0.3。根据前文结果,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疫情恶化对经济带来的负向冲击而非政府的被动扶持措施,因此本部分仅考虑疫情恶化后直接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负向消费需求冲击与劳动供给冲击。为对比分析政策规则调整前后面对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表3表示了三种模型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差异。

表3 货币政策规则调整前后福利损失
基准模型与更盯住产出缺口的模型在冲击后的福利损失比较接近,并随央行对产出缺口的重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反应更加积极可以相对降低福利损失水平。而无论λ位于哪个区间,更盯住通胀水平的货币政策在冲击下都相对于基准模型造成了更高的福利损失水平。
因此从结果来看,在疫情肆虐带来消费、劳动供给收缩,经济严重衰退的特殊时期,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整应该相机而行:在货币当局倾向于尽快提振经济、复苏产出与投资时,货币政策工具应当对通胀水平反应更积极;在货币当局倾向于稳定经济波动、降低福利损失时,货币政策工具应当维持常态或者对产出缺口反应更积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借鉴主流的经济学模型,探究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降息政策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货币供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效果。其中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措施在当期提高家庭财富,与现实中提供“疫情补贴”的政策相符,模型中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措施的模拟可以为此类“疫情补贴”措施提供参考。本文还特别对比了在疫情恶化时,消费需求与劳动需求下降以及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两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企稳效果。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疫情冲击前,尽管降低利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提供“疫情补贴”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与产出的刺激效果相近,但是在疫情冲击后,消费、产出等宏观经济指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两类政策效果出现了明显差异: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几乎没有改变,甚至短期内消费下滑幅度更大;而数量型货币政策通过“疫情补贴”的方式抓住了经济衰退时期居民对实际货币余额的偏好,使得消费、投资、产出与劳动供给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尽管造成了更高的通胀水平。
第二,在疫情恶化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劳动供给的下降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综合三种冲击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牺牲通胀稳定的基础上全方位提高了经济的政策反应,结合经济提振效果与福利损失结果,在新形势下数量型货币政策表现更优。
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甚至存在二次爆发可能的今天,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更为重要,同时在疫情导致的消费、就业收缩,产出大幅衰退的经济颓靡期间,中国面临的外部疫情风险与内部经济复苏压力使货币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本文针对疫情冲击下降低利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提供“疫情补贴”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的对比研究,不仅量化比较了特殊形势下刺激经济的政策实施效果,这对货币当局后续针对疫情的货币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对居民提供“疫情补贴”等经济刺激政策在疫情冲击下效果显著提高,值得中国货币当局借鉴,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期间,其对经济的刺激提升效果相对传统的基于泰勒规则式的降息政策更优,但是鉴于对通胀造成的波动,补贴措施需要逐步稳定推进以防范风险。其次,货币政策的设定应当考虑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疫情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的企稳效果表现相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好。再次,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规则参数设定的反事实实验,我们发现在疫情期间,通过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水平的盯住系数并且降低产出缺口的盯住系数,在疫情恶化后消费需求与劳动供给冲击下经济的衰退有所减缓。但是带来产出、消费与劳动供给相对提升的同时,也因为带来更高产出波动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因此,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发展相机抉择,根据经济形势积极调整货币政策的设定与政策实施,通过宏观调控刺激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
注释
①朱军、张淑翠、李建强:《健康损失的通货膨胀、就业影响与最优财政补贴政策——基于两部门和产业链的DSGE框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朱军、张淑翠、李建强:《突发疫情的经济影响与财政干预政策评估》,《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3期。
②⑤B. J.Laurens and R. Maino, “China: Strengthening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F Working Papers, No.14, 2007, pp. 1-51.
③B. T.McCallum, “Robustness Properties of a Rule for Monetary Policy,”Carnegie-RochesterConferenceSeriesonPubilcPolicy, vol. 29, 1988, pp. 173-203.
④J.Taylor, “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Carnegie-RochesterConferenceSeriesonPubilcPolicy, vol. 39, 1993, pp. 195-214.
⑥T.Koivu, A. Mehrotra and R. Nuutilainen, “An Analysis of Chinese Money and Prices Using a McCallum-Type Rule,”JournalofChineseEconomicandBusinessStudies, vol. 7, no. 2, 2009, pp. 219-235.
⑦胡志鹏:《中国货币政策的价格型调控条件是否成熟?——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⑧盛天翔、范从来:《信贷调控: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国际金融研究》2012年第5期。
⑨刘喜和、李良健、高明宽:《不确定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稳健性比较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第7期。
⑩J. Galí and T. Monacelli, “Monetary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 vol. 72, no. 3, 2005, pp. 707-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