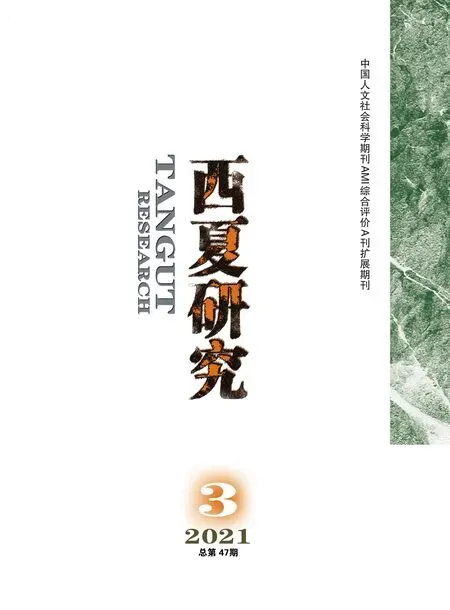西夏社会的借贷自由与债务负担
——《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的制度透视
□张映晖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一部在旧律令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的律令集合,它即是一部反映政权意志的法律文本,又是一部集中体现11—12 世纪西夏社会普遍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的百科全书,其编纂体例大体仿照唐朝“以类相从”的模式。[1]2150
《天盛律令》的“催索债利门”集中规定了民间借贷的主体资格、借贷契约形式以及债务负担的程序与偿债措施等内容①。已有学者对“催索债利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史金波结合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贷粮契对《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中的契约制定制度、最高利率、债务清偿、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述论[2]208-249。赵彦龙在契约制度的文化背景下结合出土的西夏契约文书对“催索债利门”中的借贷制度、违约责任、借贷利率等进行了考察[3]105-111。邵方从西夏“民间契约的书写格式”、“官私放贷利率”、“违反契约的处罚规定”等方面对“催索债利门”中的各项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4]95-98。于光建从“债权保障”的角度分别从“契约担保”、“刑事处罚”、“同借者连带赔偿”等六个方面对“催索债利门”中的各项制度做了剖析[5]108-126。对“催索债利门”中的各条规定进行整合以后,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从借贷契约成立到借贷契约履行,从偿债的责任认定到偿债的具体措施都有明确的规定。对比同时期宋朝的借贷案例,讨论西夏民间借贷秩序,尝试挖掘这些制度产生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社会基础,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催债索利与借贷自由的西夏视野
从《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的内容来看,西夏政府注重保护商事主体的意思自由,主体之间的借贷遵循自愿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商事主体的范围方面,也体现在借贷契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与同时期的宋朝相比较,西夏法律对商事主体的资格限制较为宽松,贵族、僧侣、官僚以及庶民都可以参与私人借贷活动。“因负债不还给,十缗以下有官罚五缗钱……”[6]188说明官员也可以是借贷者。此外,西夏的贵族和僧侣是粮食出贷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224,而且部分官僚也参与了放私债取利的活动[7]3902。同时期的宋朝,法律规定在任官员不能参与商事活动。《宋刑统・杂律》:“监临官于部内放债者,请计利以受所监临财物论。”[8]413放债收利属于官员的非法所得。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出举债负》也有类似的规定,“诸命官举债而约于任所偿者,计本过利五十贯,徒二年”[9]902-903。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社会中的“卑幼”在不经过自家“尊长”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参与借贷活动。虽然西夏政府尝试禁止这种社会现象,“催索债利门”中明确“卑幼”私自借贷属于“不应做”的范畴[6]191,甚至受到“十三杖”的惩罚[6]190,但另一些规定似乎纵容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同居饮食中家长父母、兄弟等不知,子、女、媳、孙、兄弟擅自借贷官私畜、谷、钱、物有利息时,……借债者自当负担”[6]190-191。同样,类似于奴仆的“诸人所属私人”,不能私自借债,但是在有“执主者”的情况下,是可以借债的[6]190。相对比而言,宋朝在法律上反复强调,“卑幼”在不经过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私举公私财物”是无效的[8]205、412。《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多个判决例能说明这一点,“业未分而私立契盗卖”一案中,在祖父去世“服尚未满”的情形下,行为人私自“立契盗卖田产”,买主明知而交易,“法官”认定该买卖为“违法典卖”,“用钱不追,业还主”[10]303;“母在与兄弟有分”一案中,“法官”提到,“未有父母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可典田者”,判决“钱没官,业还主”[10]301。相对来说,“催索债利门”中对商事活动主体资格限制宽松,这更容易促成借贷和买卖关系的成立。
在借贷活动中,契约双方的自由意愿一般通过纸质载体(例如书面契约)来体现,作为日后双方在契约履行过程中的证据。“催索债利门”中明确规定,诸人在发生类似买卖、借债等“牵连”时,“各自自愿,可立文据”,“于买价、钱量及语情等当计量……官私交取者当令明白,记于文书上。以后有悔语者时……”[6]189“人口、田宅、畜物”等交易活动更是如此,法律要求必须签订书面契约,规定“诸人将使军、奴仆、田地、房舍等典当、出卖于他处时,当为契约”[6]390。从西夏契约文书上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份正式的契约文书上都有“本心服”的字样[2]211,表示契约的签订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催索债利门”将“诬指”他人欠债的行为等同于“枉法贪赃”[6]190,也就是在非出于对方本意的情况下尝试占有对方的财产。同样,西夏法律也禁止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进行借债。“诸人于官私处借债,本人不在,文书中未有,不允有名为于其处索债。”[6]190在田宅的买卖、典当等方面,西夏律令对于中原“亲邻之法”作了一定的“变通”,侧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从当时南宋的一份判决书来看,“亲邻之法”在法律实践中得到落实,当时的“法官”援引了一条法令:“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丝麻以上亲者,以帐取问……”只要没有“别户田间隔”且不超过法定的期间,“亲邻”可以优先“执赎”[10]309。对于类似的情形,《天盛律令・租地门》规定:“诸人卖自属私地时,当卖情愿处,不许地边相接者谓‘我边接’而强买之、不令卖情愿处及行贿等。违律时庶人十三杖,有官罚马一,所取贿亦当还之。”[6]495杜建录先生指出,“这里西夏限制土地买卖中的‘亲邻权’,当从防止强买的角度规定”[11]48,《嵬名法宝达卖地文契》中“‘他人先召有服,房亲后召’反映了西夏在土地买卖中先问四邻,后问房亲”[11]32。从“防止强买”的角度来看,“西夏限制土地买卖中的‘亲邻权’”,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交易当事人的交易自由。
二、催索债利与债务负担的西夏方案
上述“契约自由”的实现不仅仅依赖西夏政府颁行的法律制度,还以契约双方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为前提。《天盛律令》规定,在债务人到期不能如约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不能“强力”用债务人的屋舍、畜物和田地等财产来抵债。在借贷活动中,行为人如果违反这种规定,那么其可能面临着“本利债量减算”的后果。[6]191
(一)催索债利过程中的官方介入
按照《天盛律令》的规定,法律注意区分债务人“负债不还”的不同情形。分别是“赖债不还”和“无所还债”。对于第一种情形,“不还债”被看作是一种“犯罪”,“诸人对负债人当催索……因负债不还给……若违律时,使与不还债相同判断”[6]188。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西夏政府有关部门寻求救济,政府“当以强力(对债务人)搜取问讯”,根据不同情形,分别给予债务人不同程度的惩罚,债的“本和利”依然应当还给债权人。对于第二种情况,主要指债务人在契约约定的日期未能还本付利时,则视情形判定。在这里,西夏政府对于借贷过高利息的规定有时候决定着债务的到期日,因为超过最高利息的数额不受法律保护。例如,有借贷契约这样约定,“天庆寅年正月二十九日立契约者梁功铁,今从普渡寺中持粮人梁任麻等处借十石麦,十石大麦,自二月一日始,一月有一斗二升利,至本利相等时还,日期过时按官法罚交十石麦,心服”[2]210。结合《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的规定以及一些借贷文书可以发现,“本利相等”可以看作是西夏政府认可的对于债务人欠债不还的惩罚标准之一。例如,有粮食借贷契约中约定,“日过时,一石还两石”[6]211,也有贷物契中约定,“……借贷七千七百卷[计],期限同月十五日当聚集还。过期时一[计]还二计数,共还一万五千四百卷”[2]248。“催索债利门”中多次提到,私人借贷的利息超过“本”以后,“应告于有司”[6]188-189,这在法律上限制了债权人牟取暴利的行为,“利息上限”也成为西夏政府干预民间借贷活动的“临界点”。
(二)催索债利的顺位与连带责任
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西夏法律规定,应该给债务人三次宽限期,到期仍不能还债,则债权人可以申请政府代为“催索债利”。在偿债的顺位上,分别是“借债者(债务人)”、“同去借者(类似担保人)”和“持主者(委托人)”②。“催索债利门”规定:“借债者不能还时,当催促同去借者。同去借者亦不能还,则不允其二种人之妻子、媳、未嫁女等还债价,可令出力典债。若妻子、媳比所典钱少,及确无有可出典者,现持主者当还债。”[6]189在提到“卑幼”私自借贷官私钱物时,再次明确了偿债的顺位,在家长不负担的情况下,“借债者自当负担。其人不能,则同去借者、执主者当负担”[6]191。这里的“执主者”与上述“持主者”的身份相同。但是,“催索债利门”中反复提到的“持主者”似乎在西夏的借贷契约中无法找到。从西夏的借贷契约上可以看到,契约的尾部先后列明“立契约者(债务人)”、若干“同借者”以及若干“知人”[2]210-215。按照史金波先生的研究,“所有粮食借贷契约的契尾第一个签名的是借贷者”,“为了保证本利的归还,债主除要求借贷者本人签字画押以外,还要求家属或至亲签字画押”,也就是上述“同去借者”,“同借者类似担保人,当直接借贷者发生无力还债、死亡、逃亡等意外时有借贷连带责任,负责偿还”,最后面“知人”的作用“仅仅证明契约行为,不负契约实施的连带责任”。[2]236-240结合唐宋的借贷契约内容、宋朝的相关规定以及宋代的契约纠纷能够发现,上文的“持主者”也就是西夏借贷契约以及买卖契约中的“知人”,与唐宋私契中的“见知人”同义[11]350-351。“见知人”在商事实践中可能承担着“牙人”的职能。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重叠”一案中,行为人将田宅先后典卖给两个买主,发生纠纷以后,按照契约内容,“法官”追问身兼“牙人”和“见知人”身份的王安然,结合其他证据证实了其中一份契约的真实性[10]302。在“买主伪契包并”案中,买主伪造契约试图吞并他人田产,官府认定,契约上没有家主“知押”及牙人的“证见”,遂认为此契约无效[10]305-306。“母在与兄弟有分”案中,“法官”认定“牙人”败坏某家不肖子弟,促成交易,“勘杖六十,仍旧召保,如魏峻监钱不足,照条监牙保人均备”[10]301-302。从宋代律令中可以发现,“牙人”和“见知人”不仅仅承担着上述“撮合”以及“见证”契约成立的作用,在契约的履行过程中还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元祐五年(1090),户部言:‘抵当财产……若有折欠,出卖不敷,如本主并保人填纳不足者,勒元检估吏人、牙人均补。’”[7]10865-10866绍熙二年(1191),宋廷规定:“在法:违欠茶、盐钱物,止合估欠人并牙保人物产折还,即无监系亲戚填还,及妻已改嫁,尚行追理之文。……人户欠负客旅及店铺价钱……有已经估籍家产,偿还不足,依旧监系牙保等……”[12]6695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牙保”、“见知人”或“执主者”于债权人承担的可能不仅仅是有限的偿还责任,应该和债务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三)债务负担过程中的个体识别
在债务负担方面,“催索债利门”的相关规定突出个人责任。在债务人与“家长父母、兄弟等”家庭成员同居饮食的状态下,卑幼不经过家长同意私自借贷,“家长同意负担则当还,不同意则可不还。借债者自当负担”[6]191。同样的道理,“诸人所属私人(奴仆)”也不能用“头监(主人)畜物中还债”[6]190。按照上述还债顺位,如果“借债者”和“同去借者”不能还债,则不能向两者的家人索债,但是可让他们的家人“出力典债”,这里的家人包括“妻子、媳、未嫁女”等[6]189,这里不包括“借债者”和“同去借者”的父母。“出典工门”中明确规定,“诸人不许因官私债典父母”[6]390。与执主者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相区别,执主者的家人对于债务仅仅承担有限的担保责任,以“消费”所借贷钱粮为限。“执主者不能时,其持主人有借分食前借债时,则其家中人当出力,未分食取债人时,则勿令家门入。”[6]189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西夏法令的规定,债务主体“同去借者”、“执主者”与“借债者”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上述“卑幼”私自举债情形中,在“同去借者”与“执主者”不能负担的情况下,两者“出工抵债”仅仅限于“分食”所借钱粮的情形。这体现的是一种“过错责任”,“分食”也说明“同去借者”和“执主者”有贪利之心。宋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宋刑统》“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指出:“如是卑幼骨肉蒙昧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其卑幼及牙保引致人等,并当重断,钱业各还两主,其钱已经卑幼破用,无可征偿者,不在更于家主尊长处征理之限。”[8]206这条规定虽然没有进一步明确“卑幼破用”钱财以后的偿债程序,但是可以推断出后果,家主不助还债,卑幼和牙人应当承担非法举债的责任。
(四)作为终极措施的出工抵债
在偿债的方法上,《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规定的“出工抵债”颇具特色。查阅中原宋朝的法典可以发现,宋朝开国之初,在债务人无所还债的情况下可以“役身折酬”,与西夏律令中规定的“出工抵债”具有相似性。但是,《宋刑统》中规定“出工抵债”的主体是“户内男口”[8]412,《天盛律令》“催索债利门”中规定的可出工抵债的主体包括借债者、同去借债者以及执主者并他们的妻子、儿媳和未嫁女等[6]189。显然,西夏的男丁和成年女性都可以“出工抵债”。这与西夏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有关,“全民皆兵的制度”使得“人人能斗击,无复民兵之别”[13]193-194,女性也是军队的一员[14]118-122,自然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力。《天盛律令》“弃守大城门”规定:“守大城者,当使军士、正军、辅主、寨妇等众人依所定聚集而住……”[6]197这里提到的“寨妇”就是女性。出工抵债者大多为失去田宅、牲畜等财产的贫民,以自己的劳动及所得偿还债务,“典押出力人类似债务奴隶,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奴隶,典押出力人偿清债务后可离去,借贷方也可以出钱赎回典押人”[15]44。从律令的内容中也可以发现,债务人及担保人等“出工抵债”的计量方法依据“盗偿还工价”之法进行。《天盛律令》“盗赔偿返还门”对此有详细的规定,用以将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劳动量折算为财产[6]174。考察宋朝后来的一些规定,政府明确催索实践中禁止通过“质当人口”的手段来典债。宋至道二年(996)闰七月,宋太宗下诏:“江、浙、福建民负人钱没入男女者还其家,敢匿者治罪。”[16]99《庆元条法事类》“出举债负”明确强调:“诸以债负质当人口,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9]902上述偿债方法上的差别、债务负担的机制以及借贷自由的制度设计可能是由西夏独特的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状况决定的。
三、催索债利与西夏社会的立体透视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西夏政府似乎在保护借贷主体的意思自由方面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但是,与同时期宋朝进行制度上的对比,其残存的半奴隶制形式的“出工抵债”又令人颇为费解。同时,在卑幼私自举债情形下,责任承担的个体识别似乎又与夏仁宗(曾以“天盛”作为年号)的“儒学情结”存在一定的对立,因为儒家相对注重整体的亲伦关系。其实,这些看似“另类”的制度设计决定于西夏特殊的自然地理、土地所有制以及人口状况。
首先,西夏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粮食相对匮乏,这也导致了部分民众需要采取“贷粮”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贵族、官僚以及僧侣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成为出贷生活资料的主要群体。反映在契约制度上,体现为参与商事活动的主体较宋朝来说更为广泛。虽然,按照《宋史》的记载,西夏“甘、凉之间”以及“兴、灵”两州皆引河水灌溉,“岁无旱涝之虞”[16]14028,但是这四个州的面积只占全境的一小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7]11129按照吴天墀先生的研究,就西夏全域来说,“农作物种植的面积不大,收成远远不够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13]156,再加上“频繁的气象灾害”经常引起饥荒,这成为西夏“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除官方的救济(例如赈济、贷粮于他国、榷场贸易等)[17]118-120之外,在市场上进行借贷也成为部分贫苦民众维持生活的手段。根据史金波先生的研究,“黑水城出土的粮食借贷契约数量最多,有110 多号,300 多件,约占全部契约的2/3,不仅数量大,类型也多,比敦煌石室所出粮食借贷契约多”[2]245。其中的贷粮食者“实际上是缺乏种子或口粮不得已而举债的贫困者”,而在出贷者群体中,有皇族、国师等,而且利息都很高[2]223-225。由于“党项贵族大土地占有制是西夏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皇族对于佛教的重视又使得佛寺和僧侣占有大量的田产,除此以外,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很少[15]1-15。根据吴天墀先生的论述,“西夏统治阶级对于扩大农耕土地增加农业收益很感兴趣,在谅祚统治初期的国相没藏讹庞,凭借武力侵耕宋朝麟州西界屈野河外的肥沃土地,‘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把所占的耕地,‘宴然以为己田’”[13]160。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的贵族、官僚和僧侣掌握着大量的生活资料,民众在缺粮的时候只能向这些富户借粮。可以说,达官贵族的牟利心理与广大贫困民众的谋生需求推动了西夏民间借贷的“繁荣”。
其次,区别于同时期宋朝的财产制度,西夏的卑幼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财”,这一点在契约制度和催索债利的实践中体现为卑幼不经过家长的同意可以“擅自借贷”,家长也可以不助还债。在“别籍异财”的风尚下,责任承担过程中的“个体识别”亦在情理之中。如上文指出的,在同时期的宋朝境内,法律禁止卑幼私自参与商事活动,最直接的原因是“父母在,无私财”[10]367,卑幼不能在尊长在世的时候分家析产,这种制度设立的出发点是,父母与子女在“同居共爨”的生活状态下,“均其贫富,养其孝悌”[10]278-279。从宋朝律令的规定也可以发现,“别籍异财”属于“十恶”之一[8]11,宋太祖在开国之初更是明确,“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7]231。相对来说,在西夏社会中,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别籍异财”[6]390。《天盛律令》“出典工门”规定:“诸人父母不情愿,不许强谓‘我另往别住’,若违时徒一年。父母情愿,则罪勿治。”[6]390“罪则不同门”规定:“诸人父母不情愿,不许强以谓我分居另食,若违律时徒一年,父母情愿则勿治罪。”[6]609从“谋逆门”中也可以看到,犯“谋逆”之罪者,其部分同居亲属和不同居亲属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祖父母、父母、兄弟等“非同居”亲属的财产“勿没收”[6]111。这说明,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祖父母、父母与子孙“非同居”的情况。这种现象从一些出土的西夏户籍文书中也可以推断出,按照史金波先生的研究,黑水城出土的户籍文书表明,当时该地户均人口数较少,“可能当时男子结婚后分家另过”[2]80。分家析产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尊长对于卑幼的借贷行为不一定要承担责任,财产仍然由家庭所有,债务人家资尽偿的情况下,“出工抵债”对于债务人和“同去借者”是不得已的手段,但是对于“执主者”来说,也是基于“过错促成交易”的一种变相惩罚,其家属仅仅在“分食债利”的情况下承担责任。
最后,西夏以畜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民族成分以及不均匀的人口分布使得“出工抵债”成为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与同时期的宋朝主要“以农业为主”不同,“畜牧业是党项羌族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西夏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144-155。这一点在刑罚内容上也有所体现,一些重大的犯罪诸如十恶中的“背叛”、“恶毒”、“不道”等,《天盛律令》规定,将行为人的亲戚“入牧农主中”,强制其从事畜牧和农业劳动[6]115-119。相对而言,西夏农业生产不发达,且“居民中的汉人一般都是农业劳动者,大多数党项羌和吐蕃、回鹘人民则以畜牧业为主”[13]161。又由于西夏的农耕牧区很有限,按照杜建录先生的研究,“西夏除了沿边山界以外,无论是河套平原还是河西走廊,实际上都是沙漠绿洲”,“荒漠与半荒漠约占西夏全境的4/5 以上”[18]37,剩下的适宜放牧和耕种的地区很少,这些地区也是“官僚贵族和军队”集聚地。贵族和官僚占有大量生活资料,“在贵族地主土地上进行生产的主要是人身依附性很强的农奴”[15]9,普通民众很容易破产进而“出工抵债”。对于当时的宋朝来说,“以一家一户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生产”需要社会劳动力的增加[19]27。从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五代战乱以后,宋朝为恢复生产采取了一些发展人口的举措[20]474-476,劳动人口增多的同时,垦田面积也扩大了”[19]67-71,更为尊重自由的生产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以债负质当人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此外,过于多的破产民众也可能成为西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出工抵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结语
西夏的“借贷自由”与西夏社会生活资料分配的不均匀紧密相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部分人将多余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以后,伴随着货币的出现,“高利贷资本”就产生了[21]437。但是,无限制的利率将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政府对于借贷利率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着社会矛盾。在西夏社会中,有限的农耕和牧区、繁重的赋役、频繁的战争以及不时降临的天灾更加拉大了贫者与富者之间差距。其中,西夏按照每个“租户家主”的财产规模纳税[15]18,繁重的赋役可能促使一些家庭进行“分家析产”,以此可减轻一定的税负。在这种财产所有制下,债务负担的过程中倾向于一种“个人责任”。对于极度贫困者来说,“出工抵债”似乎是偿还债务的唯一手段。
注释:
①在E・И・克恰诺夫翻译的《西夏法典》中,这一门类的标题被翻译为“追缴债息”。见E・И・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E・И・克恰诺夫将“持主人”翻译为“委托人”。见E・И・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其职能可能类似于中原唐代借贷契约尾部的“知见人”,见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