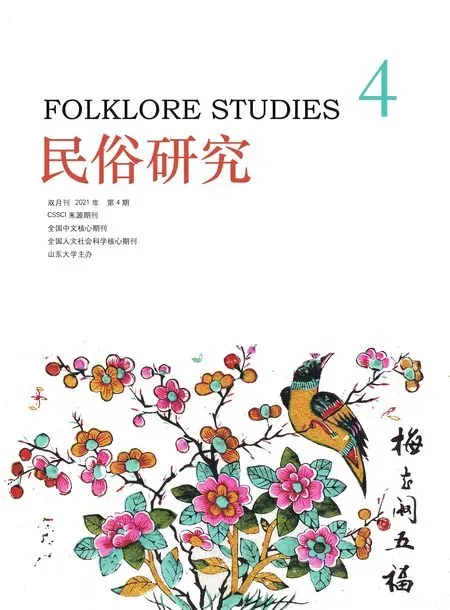地方社会的世界性:藏戏、遗产和博物馆
张 帆
一、导言:遗产研究中的地方社会
对遗产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进路。其一为遗产研究(heritage studies),或曰文化遗产学,是研究、保护和利用人类创造的遗存的学问。(1)参见孙华:《遗产与遗产保护学——以文化遗产学的学科范畴为中心》,《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12期;王运良:《中国“文化遗产学”研究文献综述》,《东南文化》2011年第5期;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贺云翱:《文化遗产学初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其二为批判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或曰反思性遗产研究,是通过分析遗产与记忆以及地方之间的关系,来反思身份认同和价值生产的过程,揭示遗产和政治以及权力的关系。(2)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Barbro Klein, “Cultural Heritage, the Swedish Folklife Sphere, and the Others”, Cultural Analysis, no. 5(2006), pp.57-80; George Yúdice, The Expediency of Culture: Uses of Culture in the Global Er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 Trigger,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o. 19(1984), pp.355-370.这两种进路的研究显示,遗产在形式上虽然是保存地方传统,实质上却和国家行政、市场运作、全球化的经验以及现代性的境况紧密相关。
首先,遗产被理解为“生产过去与未来的技术”,通过将记忆物化(materialized)或者客体化(objectified),构建过去和当下的联系,形成遗产政治。(3)[英]迈克尔·罗兰:《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52-153页;P.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1989, no. 26, pp.7-24; K. Wals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通过“遗产”构造出新的历史记忆,将过去的属于精英阶层的财产和代际传递关系,转化成了现代的属于大众领域的政治和文化现实,成为民族国家共享的“过去”,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4)Valdimar Tr. 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l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20; 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215页。由民族国家的想象构成的国际秩序,进一步强化着民族国家的现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不在一个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民族国家疆域内的遗存,就不具有作为遗产地位的延续性。(5)[英]迈克尔·罗兰:《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54页。而在中国,具体的遗产实践是按照行政区划一层层展开落实的,围绕遗产产生的义务和资源都严格对应于国家、省、市、县的行政级别和区划,遗产工程因之被纳入地方行政体系(6)陈进国:《信俗主义:民间信仰与遗产性记忆的塑造》,《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Chen Zhiqin, “For Whom to Conser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Dislocated Agency of Folk Belief Practitione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ocal Culture”, Asian Ethnology, vol.74,no.2(2015), pp.307-334.,其坐落的地方社会也随之被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整体叙事中。
其次,虽然遗产的概念和实践是沿着国家、文化等的边界展开,强化了国家间和文化间的差异,但与此同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对遗产进行定义所依赖的哲学资源几乎都有着现代的、以欧美为中心的源头。(7)例如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以及怀旧(nostalgia)心态等(参见Rodney 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28-31; Regina Bendix,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被视为遗产的去地方化以及随之而生成“现代历史心性”(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过程。(8)David C.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7,no.4(2001), pp.319-338.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定义遗产时的共同价值观和不同地方各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间,常常发生冲突。(9)[英]迈克尔·罗兰:《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55-58页。随着“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的兴起,博物馆和节庆逐渐和文旅产业相结合,成为地方、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界遗产”也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名牌商标。(10)Rodney 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84-94.在遗产被“品牌化”(branding)的过程中,地方社会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景观。(11)M. Rectnanus, “Globalization: Incorporating the Museum”, in Sharon Macdonald(ed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p.381-397; Manon Istasse, “Affects and Senses in a World Heritage Site: People-House Relations in the Medina of Fez”, in Christoph Brumann and David Berliner(eds.), World Heritage on the Grou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6, pp.37-59.
这些研究表明,如何厘清地方社会与国家、市场、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和定义遗产的基础。地方社会常常被想象为民间、基层、普通、日常的(12)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因此,对于地方节庆或庙宇的研究,常常呈现为对“小传统”的研究。(13)雷德菲尔德提出大、小传统(great and little tradition)的区分,以研究不同于部落社会的文明社会,他认为乡民社会是文明社会的局部(part-societies),大传统是文化精英创造的,而小传统是乡民依之生活的。这两个传统之间存在互动和交融。对这两个传统的研究才构成完整的对文明社会的研究。参见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随着地方节庆和庙宇逐渐成为遗产,对其遗产化过程的研究为了缓解国家和社会、传统与地方、科学与迷信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入了多元行动者的视角,强调地方的能动性。例如,高丙中指出,遗产是一种政治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双名制,在寺庙及其民间实践被转化为遗产的过程中,政府、学界和民间共同参与。(14)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再如,陈进国指出,在中国当下的“遗产锦标赛”中,对于历史性和本真性的追求已经逐渐转变为官民共建的民间文化再生产运动,在其中党政机构、地方民俗团体、学者专家以及大众媒体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5)陈进国:《信俗主义:民间信仰与遗产性记忆的塑造》,《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5期。但是,这些研究本质上还是沿着官方和民间、国家和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二分展开分析,更重要的是,将地方转化为政治博弈中的行动者,虽然赋予了地方社会一定的“行动力”,却遮蔽了地方社会的“想象力”,即对由人与非人构成的世界的差异及联系的认识。而如何理解和定义遗产,涉及一整套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如果要超越二分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必须反思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欧美知识传统,何以成为塑造全球现实的普世性知识(16)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英]迈克尔·罗兰:《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汤芸、张原编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92页。,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地方社会自身出发,呈现地方社会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因此,本文基于笔者2019-2020年在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对藏戏的遗产化过程的民族志田野调查,重新思考地方传统在被“遗产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全球化、国家、市场的角色和意义。本文指出,遗产化并不简单是现代性在传统地区的扩张,也不仅仅是全球资本和国家权力在底层社区的渗透,而是地方社会的世界性在时空层面的重新拓展。本文进一步指出,重新思考地方的意义,看到地方社会的世界性,对反思和理解由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等概念所构造的“现代社会”的概念和现实至关重要。
地方社会的世界性,首先是指将地方社会看作是具有世界性的,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并且始终在组织和拓展内外、上下联系,而不是将地方社会视为全球的局部或者国家的基层,因而易于将遗产化所构造的地方与外部的关联看作是被动的,将地方的现实视为终将卷入全球现代性的,将地方的思想认为是局部的、在遗产化过程中将被现代普世世界观清洗或者启蒙的。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论述“地方性”(local)的时候,展示出每一种地方性知识都具有解释世界的普遍性(1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61-368页。,因此人类学是在村庄中研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18)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22.。不过,格尔兹对于地方性的讨论是建立在“理想型”的基础上,出于建立类型以比较的目的,他没有充分展开地方与外界的时空关联。但是,如果把地方的历史展开拉长,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或早或晚参与了世界体系的形成。(19)cf.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mmanuel M. Wallerstein, “What Are We Bounding, and Whom, When We Bound Social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vol.62,no.4(1995), pp.839-856; Immanuel M.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ré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的世界性也强调每个地方社会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意义体系、关系和结构。
更重要的是,世界性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人群构成的世界,也包括非人的存在。正如王铭铭指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在构造“社区”概念时,受到了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重视人,而轻视物及物所构成的环境。以社区概念为基础进行的遗产研究,易于忽视地方社会的世界观,看不到其中包含的对于人、物、神诸体系及其关系的认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完整的社区应该包含人、物、神诸存在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社区研究应该是对“广义人文关系”的研究。(20)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对社区研究局限性的反思,有其深刻的哲学思考。近年来,对造物和自然的关注回归学术视野,“本体论转向”的浪潮冲击着人文社科诸领域,不断反思和重置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本体论之关系。(21)Martin Holbraad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王铭铭:《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地球”(global)是自然科学家的产物,“社会”(society)是社会科学家的造物,这两者都不是完整的世界。如果回到社会最原初的意义上,社会意味着“联系”(association),这种联系从来都不局限于人类。在拉图尔看来,人对于神明的皈依,对于人群的依附,对于不可控的宇宙的依赖,都参与建构狭义的社会,而广义的世界包括一切形式的“联系”。(22)Bruno Latour, “Whose Cosmos, which Cosmopolitics? Comments on the Peace Terms of Ulrich Beck”, Common Knowledge, vol.10,no.3 (2004), pp.450-462.
从世界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地方及其传统的遗产化,非遗展演构成众多不同形式的地方展演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性(sociality)的展现。涂尔干指出,社会性是一种道德力,使在同一分类范畴中的人相互具有责任和义务,组织起道德秩序。从日常到超常的“集体欢腾”是社会的基础,赋予社会以节奏,使人在世俗的无聊沉闷以及神圣的激情狂乱之间转换,以维持道德力。(23)[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不过,正如费孝通所批评的,涂尔干“把社会太抽象的看成一个普遍永恒的实体。因之在理论上还有一个弱点。他把感觉和观念分得很清楚”,对此费孝通认为,“人不是一面镜子,客观有什么,主观映出什么来。人是一段生活”。(24)费孝通:“序”,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费孝通对于涂尔干的反思指出,涂尔干的讨论基于对神圣和世俗的绝对二分,相应地就出现了对于社会和个体、观念和感觉、物质和道德的二分,在这样的二分中,社会成为外在的、超越的、自成一体的存在,人的生活被湮灭,成为摆动在圣俗之间、映照主客的机械存在。而世界性的视角对地方中心性以及广义联系的强调,将社会的超越性转化为内在性,弥合了观念和感觉、物质和道德的断裂,揭示出社会性是内在于个体和地方的,生活本身也同样呈现道德秩序。在这个意义上,遗产化不简单是国家权力或者文化产业自上而下或者由内至外进入地方的过程,恰恰相反,以寺庙为中心的仪式和以博物馆为舞台的表演,节庆中的藏戏和作为非遗的藏戏,都是地方社会性的表达和显现,建构着地方的时空和道德秩序。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首先介绍田野地点理塘,从历史、神话、传说、地景、宇宙观等方面来展现地方世界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中的开合和关联;继而介绍藏戏传入理塘并成为地方总体节庆的一部分的过程,将藏戏表演视为社会性的展现,即在表演中不断“显现”地方世界的上下、内外联系,以及与人、自然以及超自然存在的关系;然后介绍藏戏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变化过程——成为非遗、走上舞台、进入媒体等,将这些变化放入地方的世界性拓展中,来理解全球化和现代性、国家和市场等概念和现实在地方世界中的展开方式和关系格局;进而讨论非遗表演、文化政治以及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遗产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和新空间,是显现地方社会性的不同方式,参与构建地方世界的人、物、神的意义、关系和等级。“新”与“变”并非沿着传统和现代、地方和国家、神圣和世俗等概念上的对立而展开,而是地方的世界性的转化和拓展。
二、理塘藏戏:地方社会中的遗产
(一)理塘的世界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下辖8个区、25个乡(镇)。在文化上,理塘属于康巴藏区,94%的人口是藏族,以牧业为主。在地理上,理塘地处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横断山脉中段,沙鲁里山纵贯南北,是藏彝走廊通道的组成部分。(25)理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塘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2页。在东西方向上,理塘是汉藏的通道;在南北方向上,理塘连接多民族的青海和云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高城”,恰恰是四方通衢。理塘的世界性,在这四面八方的联系中纵横开合。
理塘县治所在,现在称为高城镇,根据《理塘县志》记载,其建制最早可以追溯至元至元九年(1272),置李唐州,归云南丽江路管辖,治所李唐城(现高城镇)。(26)理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塘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5页。理塘再次闪亮登场是在1580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在理塘建立长青春科尔寺,意为弥勒法轮洲,也常常被称为理塘寺,此寺后来成为康区最重要的格鲁派寺庙之一。1578年,第三世达赖喇嘛应蒙古俺达汉(1507-1583年)之邀,于青海仰华寺相见,弘扬教法并寻求联合,并在此后来到康区弘扬格鲁教法,在丽江萨达木王(即丽江木氏土司)的支持下,于1580年在理塘建寺。(27)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2006年,第241-42页。
理塘寺成为当地历史记忆的起点,在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第三世达赖喇嘛建寺的传说,都强调了建寺原因在于理塘地形地势之殊胜吉祥,正如在理塘寺藏戏开场的扎西雪巴的唱词中所展现的:
看男声如吹金色长号一样洪亮
看女声如吹金色唢呐一样悠扬
听到这歌词,远望(理塘寺)如同建在象鼻上,(两侧)吉祥之水流淌
愿上师法体安康的吉祥颂词
愿家乡幸福平安的吉祥颂词
愿大地丰产无灾的吉祥颂词
以理塘寺为中心,理塘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各有一座神山:西面波拉山(’bumrari),北面囊色山(rnamsrasri),东面玛卿波拉山(rmachen‘bumrari),南面索如山(sori)。这四座神山中,有两座都和第三世达赖喇嘛相关:东面的玛钦波拉,据说第三世达赖喇嘛从青海来到理塘时,青海最大的神山阿尼玛卿(也称玛卿波拉)护佑其后(28)阿尼玛卿的不同名称,参见才贝:《阿尼玛卿山神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66-67页。据其传记记载,第三世达赖喇嘛在去青海的路上就受到了玛卿波拉山神的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2006年,第232页)。,在理塘驻扎,成为玛卿波拉;南面的索如,直译即蒙古山,据说追随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来的还有蒙古军队,在此驻扎,化为神山。
理塘寺不仅是当地时间的起点,也是当地空间的中心。在当地人眼中,理塘寺及其周围八个村落,构成了一副以寺庙为中心八村环拱的“八瓣莲花”之景象,四座神山环绕四周又形成一个坛城结构。现在的高城镇基本是以这八个村落为基础。八村中,据说最早的是车马村,此村地位特殊,与寺庙成南北轴线,其中还有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年)的诞生地,构成现在理塘古镇的核心,政府办公大楼以及新的地标建筑“格萨尔广场”也紧邻其右。德西一村位于寺庙西侧,二村和三村顺次向南排布。德西三个村子形成的时间比较晚,据说最初是乞讨和流亡者聚集之地,靠寺庙施食存活下来,颇成规模。于是,出生于此的理塘寺寺主第二世香根活佛阿旺洛绒丁真嘉措(1909-1949年)赐名“德西”,即幸福之意。后来很多外来人口,诸如汉族的木匠以及掉队士兵等,也大都落户德西村,因此理塘烈士陵园即坐落在此村西部。替然宁巴村位于寺庙东侧,紧邻寺庙大门。替然宁巴即老街子之意,此村据说曾经是山陕商人聚集之地,商铺林立,形成街市,被称为“老街子”。
从理塘的史志和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理塘虽然被困于海拔四千米的贫瘠山谷,是刚刚脱贫的落后地区,却并非是封闭被动的。民族区域常常被看作是沉默的、被动的边缘,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29)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Liu Shao-hua,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mily T. Yeh and Chris Coggins (eds.), 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然而,假如把时空线拉长,理塘的世界在时空上囊括了从南边丽江而来的土司和官员,从西边藏文明的核心拉萨而来的藏戏,从北边蒙古俺答汗汗庭坐落之处青海而来的山神,从东边山陕一带来的商卒走贩。理塘接纳着乞讨流浪者,也留宿工匠手艺人,供奉着不同的神仙,也恭迎各界政要。理塘并不是边缘局部的,而是拥有世界性的,其世界在迎来送往中伸缩自如。
(二)显灵的遗产
1.“显”灵、节庆与社会
理塘的世界不仅在历史中展开,也在仪式和节庆中显现。山口昌男(Masao Yamaguchi)指出,日语概念mitate,通常被翻译为“显”,强调物扩展出自身物质形态所展现的时空之外的特性,指涉更大的社会性和超社会性联系,是种“征引艺术”(art of citation)。表演也具有征引性,例如,在日本的歌舞伎表演场中,演员认为表演的是浓墨重彩的行头,而非行头包裹的人,因为表演(theater)是神迹的展示,而神借助衣饰显灵,灵使演员做出各种动作。(30)Masao Yamaguchi, “The Poetics of Exhibition in Japanese Culture”,in Ivan Karp and Steven 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58-59.在这个意义上,表演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空间维度,将人的空间拓展至神的空间。王铭铭也指出,汉文中有“显”的概念,与“隐”相对,节庆和神堂是“化隐为显”的过程。神堂的塑像和壁画基本是围绕主神“显灵”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具象化,和历史过程中的特定道德秩序相关。在汉文中,节庆常常被称为“社”或者“会”,在这个过程中,物(作为祭品的食物、作为供品的宝物)和表演(娱神的戏剧)显现了活生生的社会,参与者也感受到了社会的力量。(31)王铭铭:《显与隐:文化展示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文化展示》,《博物院》2020年第4期。
在藏文明中,尤其是在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哲学中,虽然人在此世的生活是朝向彼岸的,但是,中观派对于性空的讨论并不建立在否定缘起的基础上,换言之,还是肯定了“世俗谛”的存在,肯定了现象世界虽然不实有,但存有,物(dngospo)和人,是延续业果流转的“所依处”(rten),不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状态或者过程。(32)参见[美]伊丽莎白·纳珀:《藏传佛教中观哲学》,刘宇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变化和无常,没有永恒存在之物,不管是人还是物,寺庙还是博物馆,其意义都不是持有而是流转,不是保存而是显现。在藏区地方社会中,寺庙与节庆正是社会显现与生命流转的场所,既具“显现”意义上的拓展当下的时空维度的征引性,能够激发参与者的强烈感受,同时,其征引体系不仅包括“大传统”中的经典和神明,也包括“小传统”中的精灵和鬼怪。
理塘的节庆和仪式众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除了藏历新年,就是夏季的“耍坝子”,官方称呼是“夏安居”(dbyarskyid),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佛教节日,为了避免在雨季出门踩踏生灵,僧人们闭门不出直至雨季结束。(33)Robert E. Buswell and Donald S. Lopez, 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60.在西藏,夏安居结束之时,人们会给僧人们布施,并以各种方式来庆祝。在理塘,夏安居的庆祝和祭山神的活动慢慢融合,形成了每年以“六月日皎节”(drugpa’iriskyid)为核心的耍坝子。耍坝子期间,理塘僧俗官民都会在草原上扎帐篷,短则一个礼拜,长至月余,祭山、赛马、藏戏、歌舞,日常生活被悬置,社会性则化隐为显,地方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在祭祀、戏剧、竞技中被浓墨重彩地夸张呈现,人的空间也由此拓展至历史、神话以及神明的世界。
2.作为节庆的祭祀、竞技与表演
1947年,贺觉非(1910-1982年)在《理化县志稿》中记载:
六月初三日跑马会,是日黎明,堪布即率全体僧众,遍祀各山神,焚柏诵经,延至正午,始达跑马场,在治东里许□溪支幕,观者茹堵,县长莅场,先与堪布等互上喀带,旋跑马开始。马在前跑,道之左设箭靶,中者下马趋拜,由县长堪布赐予喀带以宠之,中的殊不足奇,在观其夭矫之态耳[…]幕里歌舞又其余事矣。堪布率众诵经,斯须而去。游人亦收幕,渐归县属。四乡亦各有跑马会。(34)贺觉非:《理化县志稿》,理塘县档案馆藏,1945年。
贺觉非记载的藏历六月初三的仪式活动,其程序和内容和今天相差无几:凌晨开始,理塘寺的僧人在寺庙诵经,之后在堪布的带领下骑马祭山神。从西面的波拉山开始,按照顺时针依次在每个山上诵此山神的经文以安抚山神、焚烧柏枝以趋祟、撒风马树经幡以求福佑。这一圈祭祀下来,就从凌晨到了午后。午后僧俗众人在县城西面的东嘎坝上支起帐篷。中间的巨大白色帐篷“星螺环”是跳藏戏的场所。其他人的帐篷以之为核心,环拱其周。在堪布的主持下,僧人们吹起法号、诵经、辩经、布施、进食。之后就开始跳藏戏和赛马。理塘县各村以及县属各乡都有自己的祭山赛马仪式,最早从五月份开始,最晚的一直到八月份。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贺觉非所记载的有最高级僧俗官员出席的县治祭山赛马。
贺觉非记载了帐幕内的歌舞表演,却没有提到藏戏表演。其原因在于,1946年,在贺觉非记录下跑马祭山仪式的前一年,藏戏刚刚从拉萨被系统引入理塘。根据高城镇藏戏团扑巴(35)文中田野受访对象的名字均为化名。团长的说法:
1941年,第二世香根活佛和他的亲兄弟管家等去拉萨,共花五年的时间学习了觉木隆派藏戏,1946年把觉木隆派的藏戏传统带回理塘。在觉木隆派藏戏传入理塘之前,1940年5月,理塘寺仁增多吉、索朗、向秋等僧人在寺内组织20多位僧人排练并演出《卓瓦桑姆》和《诺桑法王》。当时拉章寺也有一个藏戏团,排演过《朗萨姑娘》《志美更登》《卓瓦桑姆》等传统剧目。1947年理塘寺和拉章寺两个剧团合并,之后每年藏历5月11日“香根日皎节”那天,第二世香根活佛出生的村子德西村就牵头准备去神山燔柴供施、焚香祭神的所有备用东西。转山煨桑回来之后,在“东嘎坝”演出藏戏,持续10天。表演的时候有不同音调,语调,曲调,男音,女音,哀歌,赞歌,角色和顺序。理塘藏戏是先跳雅隆扎西雪巴,然后猎人唱腔,第三王朝,第四祈祷等结尾。一直以来大部分是僧人演出加上几个在家人,藏戏的内容和佛法因果关系融入在一起,行善断恶,和平和谐,团结,众生平等。(36)访谈对象:朴巴;访谈人:张帆;访谈时间:2019年6月20日;访谈地点:理塘德西村活动中心。
这段叙述把理塘藏戏的源头追溯至拉萨的觉木隆藏戏。觉木隆藏戏是藏戏的一个流派,发端于拉萨以西的觉木隆(37)觉木隆巴(skyor mo lung ba)藏戏流派的起源常常被追溯到唐东杰布,不过,目前影响藏区的觉木隆巴事实上是1913年以重建为名开启的,在重建过程中有过多方面革新。参见桑吉东智:《觉木隆巴的前世今生》,《中国藏学》2015第3期。,觉木隆巴戏班是西藏地方政府布达拉宫内务机关直接管理的,每年在雪顿节期间献演(38)17世纪,西藏地方政府甘丹颇章建立,在其支持下,出现了大量职业、半职业戏班,并形成不同藏戏流派,例如蓝面藏戏迥巴派、江嘎尔派、香巴派、觉木隆派等等。到18世纪中叶,地方政府开始组织雪顿节中的活动和表演,藏戏成为固定表演。参见高翔:《“觉木隆”职业藏戏及唱腔音乐研究——以西藏藏剧团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8-29页。。在拉萨,雪顿节是在夏安居结束之时,民众为僧人们布施酸奶的活动,后来活动内容逐渐增多,藏戏表演成为固定节目。除了在雪顿节的官方演出,很多职业戏班常常在庙会和集市等场合登台,或者在达官贵人的庄园里献艺。(39)高翔:《“觉木隆”职业藏戏及唱腔音乐研究——以西藏藏剧团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3-34页。
从拉萨引入藏戏并非偶然。理塘寺和拉萨色拉寺是祖寺和子寺的关系,也就是说,直至民国时期,理塘寺的僧人都要到色拉寺学习取得学位,借此和拉萨的高僧以及大寺形成稳固的师徒和供施关系,从而和拉萨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形成联盟。民国时期的理塘是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社会,因此活佛的游历和行走是地方的世界性拓展的重要过程。第二世香根活佛在拉萨学习期间,看到了觉木隆藏戏,随后派人去学习并带回理塘。藏戏表演于是被纳入庆祝活佛诞辰的“香根日皎节”,后来又逐渐成为六月日皎节的组成部分。这一仪式活动形成之时,贺觉非已经离开理塘,无缘观看。
3.节庆中的地方世界
德西村不仅作为祭山和藏戏活动的组织者以及主要布施者,而且高城镇藏戏团的成员几乎全是僧籍为德西村的僧人。德西村的僧人每每讲到理塘寺,都会自然地说“我们寺庙”,其密切关系可见一斑。理塘藏戏团由40到50个僧人构成,有三个管事,分别是德西三个村子的代表,来负责组织各种相关的仪式和演出,五年一届,由寺庙安排。每年的藏戏表演以及藏戏表演前的转山煨桑仪式的举办也都是德西村主导。由此,寺庙和村庄历史上的供施关系以及在坛城结构中的护佑关系得到再现。
地方的边界及其与更大区域的联系也在仪式中被呈现。地方的边界在骑马绕界祭祀的过程中,变得清晰。理塘的“牛场娃”们能轻松向我指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旷阔山头中,哪些草场归理塘所属,哪些是其他地区的,必然和每年一次的绕山密不可分。王明珂指出,在羌寨里,每个寨子有自己的草山和林场,都界限分明,各村各寨的山神菩萨与各种庙子,就是界限的维护者,定期祭庙子或山神的活动,正是确认本家族、本寨、本村与本沟在资源分享体系中的地位。(40)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4-54页。在理塘,接受供养的山神大部分是外来的,例如有着蒙古渊源的索如神山,有着青海联系的玛卿波拉神山,这些神山既区分着理塘的边界,也让理塘和更大的区域联系起来。
祭祀山神之后,僧众们来到东嘎坝,诵经煨桑,击鼓鸣锣,表演藏戏。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和宇宙秩序也显现出来。藏戏的情节常常借助国王-大臣、贵族-乞丐、丈夫-妻子,神仙/动物-人等人物展开,通过冲突不断显现地方社会的伦理边界。丑角常常以乞丐、渔夫、猎人等低等级的身份出现,通过颠覆性别和地位的语言及动作,引起哄堂大笑,从反向确认道德秩序。
按照扑巴的说法,山里居有“鲁”,是类似于龙王的神衹,掌管世间雨水,雨季将近结束之时,僧人们通过祭山诵经来震慑鲁,并通过藏戏表演来娱乐鲁,会使雨季顺利结束,一年风调雨顺。正如扎西雪巴中的美好祝愿所表达的:“愿大地丰产无灾的吉祥颂词。”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指出,对于“鲁(龙-蛇-神)”的信仰,普遍存在于前佛教时期的萨满信仰中。(41)[法]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520-521页。在西藏,“鲁(klu)/地下-赞(btsan)/中空-拉(lha)/天界”的垂直宇宙结构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被逐渐融合,但在民间信仰中,依然影响深远。(42)谢继胜:《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在猎人唱腔中,垂直宇宙结构被重现:
猎人头顶上的发髻,
是大成就者唐东杰布的造型,
大成就者唐东杰布,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额头上的日月,
是照亮世间无明的日月,
照亮世间无明的日月,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上面仙界的服装,
彩虹般的大神婆罗门,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下面鲁界的服装,
聚财宝的水中龙王,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上穿的服装,
是来自赞界的服装,
大平原上愤怒的赞神,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下身的果子,
是如意果树结出的果子,
如意果树结的果子,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猎人身周的璎珞,
是大宝金刚手的造型,
大宝金刚手,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
这一段唱词,既在描述作为表演者的猎人装扮,也在呈现表演者置身其间的宇宙。表演者们不断召唤三界主管神灵以及佛的化现大宝金刚手,将其请入理塘的世界,或者说,将理塘人的世界拓展至神的世界。额上日月,身贯三界,金刚护佑——世界在这场仪式中重生。
在这场祭山、赛马、唱戏构成的节庆中,理塘与不同文明区域以及政治中心的联系被展现,理塘的历史和神话被重现,寺庙与村庄、村民与山水的关系被呈现,理塘的伦理边界和道德秩序被显现,理塘的世界在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许中被展开。
(三)具加持力的非遗
1.国家、政治与两支戏团的诞生
扑巴在谈话中坚持使用理塘“高城镇藏戏团”的称呼,以区别于理塘“甲洼藏戏团”。甲洼是理塘下属的一个乡,在高城镇东南三十公里,甲洼藏戏团的成员基本都是甲洼乡的村民。这支偏安一隅的戏团,却在2018年代表理塘荣获甘孜州藏戏非遗传承人的名号,被政府签约为游客表演,每个月3000元的工资,相当于当地基层公务员的收入。
甲洼藏戏团的建立者崇西活佛解释说:
藏戏从最开始就是老百姓的歌舞,唐东杰布修建铁桥创立藏戏都是为了老百姓。14世纪,西藏很多地方有自己的王(甲波),在文化发达的地方,王就会邀请翻译家(罗扎娃)到自己的王国,以印度的史诗传说为蓝本,以王的丰功伟绩为核心,创作剧本。这就是八大藏戏的来源。王从百姓中挑选演员来演出和传唱藏戏,这和寺庙里跳神不一样,跳神是僧人的仪式,依据的不是剧本,是经(朵)和咒(哈)。藏戏和寺庙无关,依据的是翻译家的剧本,是王和百姓之间的欢庆。
旧社会的时候,香根喇嘛的前世,在40年代就建立过藏戏团,后来丢了。理塘寺也建立过,也丢了。我小的时候经常看藏戏,特别喜欢,脑袋里就记下了。1985年,我开始组织老百姓恢复藏戏。(43)访谈对象:崇西活佛;访谈人:张帆;访谈时间:2019年6月18日;访谈地点:甲洼乡崇西活佛宅邸。
高城镇藏戏团主要由德西村的僧人构成,因此在扑巴的叙述中,藏戏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方式;而甲洼藏戏团主要由甲洼乡的村民构成,所以崇西活佛在讲述中强调藏戏的民间性。这两个藏戏团的表演主体虽然有僧俗之分,前者的表演和仪式相关,后者的表演以娱乐为主,事实上,这两个藏戏团具有同样的传统且有师承关系。
理塘寺的藏戏表演在1959年之后就停止,后来很多僧人还俗,藏戏表演中断了20年。1979年,理塘县政府召集了部分还在世的藏戏表演者,组建了“高城公社业余藏戏团”,归属县文化馆,在各个乡村巡演,做文艺宣传。(44)理塘县档案馆、文化馆《关于正式成立县藏戏团的报告》(1982)及其批复《理府发〔83〕29号》。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藏戏团因为没有编制、经费和补贴,逐渐停演。(45)理塘县档案馆,理府发〔1991〕60号。1985年,崇西活佛做理塘寺的堪布,在其出生地甲洼招募人员组建藏戏团,并动员僧人藏戏表演者到甲洼教授藏戏。
现在高城镇藏戏团的戏师平措告诉我,他也曾经指导过甲洼的藏戏表演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宗教政策逐渐放宽,德西村的僧人们也开始重拾旧业,在村民的支持下复兴了寺庙的藏戏。于是就出现了两个藏戏团并存的局面。
甲洼藏戏团初创时,因为村民都不是职业演员,只是在每年耍坝子、藏历新年等场合进行小规模的自娱自乐的表演。而高城镇藏戏团复建之后,成为每年祭山活动的中心,极具影响力。近几年,甲洼藏戏团的发展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在成为非遗之后,地方政府修建了“藏戏传习所”,并在2019年改为藏戏博物馆。甲洼藏戏团的影响力随之不断扩大,两支戏团之间开始出现竞争与张力。
2.去魅与复魅的博物馆
藏戏博物馆坐落在德西村的一座两层的藏房里,德西村属于理塘古城的一部分,毗邻理塘寺,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旅游区。博物馆的一层设计为表演大厅,中间是高起的舞台,周围是卡座。理塘的旅游旺季常常和村民耍坝子的季节同步,所以,当高城镇藏戏团的僧人们在草原上为村民们跳藏戏的时候,甲洼藏戏团的演员们则在这方舞台上为游客们表演。因为舞台表演的需要,藏戏团要把以往六七天的戏压缩到一两个小时之内,甚至是片段式的一次15至20分钟的表演。不过也因为具有可展示性,戏团有了外出表演的机会,到过巴塘、成都甚至上海。
博物馆二层被装修为理塘藏戏的介绍长廊,用图片和文字介绍了理塘藏戏的历史以及甲洼藏戏团的演员。博物馆的介绍从唐东杰布开始。学者们指出,藏戏的起源融合了西藏吐蕃时期的宫廷表演、卫藏地区的民间歌舞以及印度的佛教戏剧(46)Isabelle Henrion-Dourcy, “rNgon-pa’i ’don…: A Few Thoughts on the Preliminary Section of a-Lce Lha-Mo Performances in Central Tibet”, Études Mongoles Et Sibériennes, Centrasiatiques Et Tibétaines, no. 46(2015), pp.1-18.,不过在西藏,藏戏被广泛认为是唐东杰布(1361?-1485)创造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唐东杰布,并没有发明藏戏的历史记载;不过,作为有神通的大成就者,他据说活了125岁,须发皆白(47)Cyrus Stearns, King of the Empty Plain: The Tibetan Irion-Bridge Builder Tangtong Gyalpo. Ithaca, NY :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7, pp.23-24.。据说他在修建铁桥利益众生的过程中,请了六个声音优美的姑娘,通过表演筹集建桥资金。姑娘们的表演惊若天人,所以大家称之为“神仙姐妹”(alcelhamo),这就是藏戏的起源。正如甲洼藏戏团在猎人唱腔中所唱的:“猎人头顶上的发髻,是大成就者唐东杰布的造型,大成就者唐东杰布,请看看我们这些猎人吧。”理塘藏戏中,扎西雪巴表演中的黄色面具以及猎人唱腔表演中的蓝色面具,也都是白髻白须,以此来纪念这位藏戏的创立者。博物馆对于唐东杰布的介绍兼顾了学术传统和地方传统中对于藏戏起源的解释。
在二层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藏戏表演的面具,制作略显粗糙的是理塘的面具,制作精良的则是从拉萨买来的。在藏戏中,人的角色不需要面具,而动物和恶魔是需要戴面具的。理塘人认为魔的面具会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例如,一位僧人认为自己演了女魔而得了痛风。因此,不跳藏戏的时候,面具都是锁起来的,尤其是女魔的面具;在演出时,女魔的面具也会被盖上白布,直到出场时才拿下白布。而在博物馆里,面具被赤裸裸地展示着,旁边还摆放着蜡制牦牛和人,这使整个空间显得诡异可怖,村民们不怎么到博物馆里参观,大部分来此参观的都是外来游客以及到访官员。
山口昌男指出,日语概念mono,常常被翻译为“物”,其原始意义指不可见的世界与可见世界之间的连接,以可见的物质形态显现不可见的宇宙图式。例如,在日本的能剧中,常常存在一个萨满角色,这个角色能够“阅读”各种物的意义从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神鬼。(48)Masao Yamaguchi, “The Poetics of Exhibi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Lavine (eds.),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62-63.在这个意义上,物具有征引性。在博物馆展示中,物的征引性被抹除了,时空以及关联不再通过展演被显示于当下,而是通过在当下的展演中对物重新命名和分类,构造新的时空与关联。理塘的博物馆,一方面,在汉藏双语的文字介绍中、在外来游客和到访官员的光顾中,博物馆空间显现着地方世界不断构造的新意义、关联和等级;另一方面,其内部展示的物对当地人而言,依然具有强烈的征引性——面具依然激发恐惧,佛像前面会堆满供养的钱,博物馆的院子里还能见到放生的鸡。
3.镜头中的非遗表演
在县宣传部的推荐下,甲洼藏戏团参演了影片《寻找罗麦》并于2018年上映。这是一部中法合拍的影片,主要情节发生在巴黎和北京,藏戏团作为一种精神救赎出场,使主角度过了丧友之痛。
贝里(Chris Berry)指出,包括《寻找罗麦》在内的一系列华语藏地影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升温的“西藏热”的映照,其中的藏区都是被“他者化的”。(49)Chris Berry, “Pristine Tibet? the Anthropocene and Brand Tibet in Chinese Cinema”, in Kwai-Cheung Lo and Jessica Yeung (eds.), Chinese Shock of the Anthropocene: Image, Music and Text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19, pp.249-66.从这个角度来看,《寻找罗麦》中的理塘确实被浪漫化和符号化,始终是一片白茫茫,呈现出纯洁的意向,出场的人物不是着红袍的僧人就是披戏服的藏戏演员,被平面化为救赎的符号。亚当斯(Vincanne Adams)以现代性的隐喻来分析拉萨KTV中的表演,她指出,表演成为一种生产差异的过程,在其中,正宗的他者——藏、汉、英——被演绎、差异被生产。(50)Vincanne Adams, “Karaoke as Modern Lhasa, Tibet: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0, no. 4(1996), pp.510-546.如果将《寻找罗麦》也视为一个现代性的隐喻,那么,镜头中的表演,不断合成着法国与中国、内地与藏地之间双重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世俗与神圣等的二元对立。
不过,无论是对“他者化”的思考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只是从地方被“再现”(荧幕和KTV)的方式中来观看世界,而没有真正看到被再现的地方。电影里藏戏团跳的剧目《卓玛》,是团长登巴以藏戏《诺桑王子》为蓝本做得改编。僧人们对甲洼藏戏团随意更改藏戏颇有微词。不过,对于僧人而言,表演的“本真性”无足轻重,不能随意改动的原因在于,藏戏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手段,更改对佛法是不敬的,对自身的福报也是不好的。而对村民们来说,表演更像是一场仪式,在场意味着被加持(51)桑吉东智:《乡民与戏剧:再论阿吉拉姆的研究》,《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因此,在场比入戏更重要,他们不仅常常即兴发挥,而且常常在演戏的过程中彼此聊天,心不在焉,游离在表演和情节之外。
加持,是一种朝向神圣性的行动,也是一种赋予力量的过程,既体现在社区的风调雨顺和兴旺丰产,也体现在个体的健康、财富和声望。在这个意义上,藏戏确实带来加持。政府和甲洼藏戏团签了合同,藏戏团的演员们成了当地人艳羡的“吃皇粮的”。因此,当登巴向我展示藏戏团和影片主创的合照时,他频频谈及“由县领导推荐的”“北京来的导演”。在他看来,参与国际电影拍摄并不意味着搭上了驶向现代的诺亚方舟,由电影所构造的向上和向外的联结,使他在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中从“能人”变为“名人”。登巴曾经出家,后来还俗,通晓藏文并在寺庙受过系统绘画训练。在藏戏成为“非遗”之前,他主要经营一家传统藏式墙面装饰的作坊。现在,他关停了作坊,投入到戏团的管理中,常常带领戏团外出巡演,有时还能和地方政要握手言谈。他制作的面具,被藏戏博物馆征集为展品,和来自拉萨艺人的面具一起被高悬于博物馆,广被观瞻。
不仅团长登巴一下从村落能人跃升为地方名人,丑角次仁也一下成了当地的明星。丑角虽然不是主角,却是不可缺少的,且极易出彩。次仁年过半百,妻子身有残疾不能自理,两个儿子尚未成年,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但是,次仁天性幽默,不仅擅长用夸张的动作展现荒谬,还擅长即兴发挥,把时下流行的笑话段子加入表演中,有时还会加几句汉语和场下的汉族游客互动,常常引得哄堂大笑。他的表演在得到视察领导的赞赏后,他一夜之间成了古镇的明星。
藏戏演员们津津乐道于和明星一起演戏、在康巴卫视的节目、在成都报刊上的报道、在巴塘和上海的演出。在成都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藏人聚集的武侯祠附近,这之外的区域被他们描述为混乱无序却又充满诱惑的地方。他们充满好奇却又步步为营地出走,因为回到家乡这些外出的经历是一生的谈资。电影和藏戏,仪式和表演,剧本和戏本,是建立超地方性联结的方式,都使他们参与到了与更大世界的联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他者化和现代性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如果将地方作为世界的局部,那么,他者化意味着地方作为弱势一方被想象、观看和呈现,现代性呈现为对于“地方性”的清理,或者说,从地方所蕴含的混杂中不断制造边界和差异的过程;如果将世界看作是内在于地方的,那么,他者化意味着一种内外关系,现代性则呈现为地方世界的一次次扩张,一次次突破边界将差异纳入自身的过程。
三、结论:文化政治、世界性与遗产
本文在对藏戏及其遗产化的讨论中,尝试展现理塘的世界性及其拓展。藏戏于20世纪40年代从西藏传入理塘的过程,是理塘与拉萨关系的一种显现,也是以寺庙为中心的地方社会关系的显现。与此同时,寺庙的建设和历史无不与外在的权力中心相关联——达赖喇嘛、蒙古汉王、云南土司、民国官员等等;节庆中的仪式、竞技和表演展现着地方世界中与自然(神山、草坝)以及超自然存在(龙神、山神、佛)的关联。在建国后的国家建设阶段,藏戏经历了改革,被并入文化馆系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暂停,直至20世纪80年代逐渐复兴。复兴后的藏戏,一方面在僧人们的仪式性表演中,依然显现着地方世界的历史和神话、宇宙观念和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随着藏戏的非遗化和地方旅游经济的兴起,村民们的非遗展演走进博物馆、走上舞台、走入媒体,显现着地方世界构造出的新的意义、联系和秩序。
很多研究倾向于关注遗产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即非遗表演背后的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及其不断经历商议和重构的过程(52)S. Macdonald, “Museum Europe: Negotiating Heritage”, Anthropolog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Cultures, vol. 17, no. 2(2008), pp.47-65;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World Heritage and Cultural Economics”, in Ivan karp et al. eds., 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61-202.。例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指出,苗族强调“民族”和“传统”的表演呈现为一种悖论:一方面,苗族尝试从少数民族、女性、农村等结构性差异中逃离出来,加入中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们的努力使得少数民族、女性、农村在现代性中进一步被视为贫穷落后的他者。(53)Louisa Schei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这正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政治。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将表演看作政治的神话,致力于戳破神话揭示权力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地方的理论主体性;将政治看作神话的展演,则有助于呈现地方对于政治和权力的解释,以神话的形象,而非科学的话语。从比较古典学和神话学出发,各种文化中——印欧、波利尼西亚诸岛、美洲印第安部落以及非洲——都存在“陌生人-王”(stranger-king)这样的结构,这种结构指向一种普遍的权力理论,即,支配是社会本质的自动表达,权力在社会之外。在此,萨林斯强调,“陌生人-王”不是简单的支配、剥削和压迫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结构,此结构是文化范畴及其关系的展开,它既是政治,也是全部的社会生活,是社会的宇宙秩序。(54)Marshall Sahlins, “The Stranger-King Or Dumézil among the Fijians”,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 16, no. 3(1981), pp.107-132.
同样研究海外藏人社会的藏戏,卡考斯基(Marcia Calkowski)指出,作为行动体系的文化,自身也是有结构的:藏文化中有一种“驱祟”(exorcism)的结构:息(zhi):平息、安抚;增(rgyas):通过允诺财富、权力和地位来劝慰;旺(dbang):显现力量而降伏;灭(drag):驱除或转化。这四步结构不仅体现在各种驱祟仪式中,呼应于藏戏表演的不同阶段,也用于消除政治纠纷的“社会戏剧”。(55)Marcia S. Calkowski, “A Day at the Tibetan Opera: Actualized Performance and Spectacular Discours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8, no. 4(1991), pp.643-657.卡考斯基的研究表明,从表演到仪式、从政治到文化、从传统到现代,是往复式的结构转化,而不是单向的社会进步。
因此,本文指出,藏戏遗产化的过程是理塘调整上下内外关系的过程,以容纳由现代性、国家以及资本等概念制造的新的差异性范畴。成为非遗和“赐予喀带”类似,其表演并不简单是浮于表面的“文化政治”,以地方作为中心,这恰恰是地方的世界沿同心圆向外向上的拓展。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派遣的县长,在地方的世界里被视为继蒙古大汗、云南土司、拉萨地方政府等之后新的“陌生人-王”,表征着理塘世界的超地方性,参与其中的是僧人,祭山赛马中县长和寺庙堪布互献哈达。如今,这种“超地方性”被重新展现为“理塘-成都-中国-国际”这样的同心圆,移动于其中的是村民,旅游旺季政府官员和藏戏演员们亲切握手。从“拉萨-理塘-民国”的世界转化为“理塘-成都-中国-国际”的世界的过程中,作为联系节点的僧人、官员、精英们也呈现出新的关系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两个戏团及其表演的三个方式——仪式性的耍坝子、遗产化的表演以及商业化的展示,并非简单地从神圣到世俗、从传统到现代、从民间到官方的线形替代过程,而是多线并存不断转化的过程。
正如导言所论,世界性概念有助于重新思考地方社会与现代性和全球化、国家和市场的角色和意义。本文尝试从地方世界的伸缩开合出发来重新理解现代性,不是简单把现代性作为一个不可逆的时间线,将地方的世界线性化,在这个时间线上安排地方和国家、仪式和表演、少数与多数、边缘和中心,而是把传统、现代、国家、市场、仪式、表演等等作为地方的世界的变量,将其空间化,看地方的世界如何藉着这些变量而展开。
更重要的是,世界性的视角有助于拓展“社会”的内涵。不论是涂尔干二分的社会观还是费孝通生活的社会观,都很难真正为非人的存在留下一席之地,而自然与超自然的存在是构成地方世界社会生活和宇宙秩序的基础。这些存在常常是文化展演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却又是现代社会观影响之下,遗产化过程中无处安置的元素。正如开篇所言,只有返回“社会”一词的原初意义,即,联系,将作为“自成一体的实在”而存在的社会,转化为作为由点及面纵横开合的过程而存在的社会,才能在由点及面的过程中,将人、自然、超自然的各种存在纳入分析,才能在纵横开合的过程中,呈现历史性形成的意义、关系和结构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