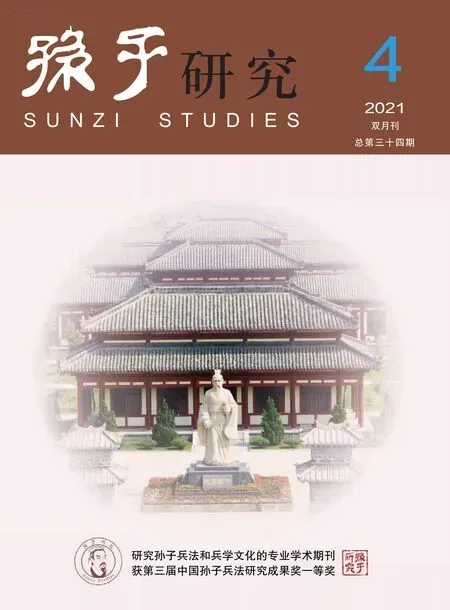欧阳修对《孙子兵法》的学习与运用
吴名岗
欧阳修是文学家、史学家,但他同时又是国家的重要官员,既担任过为皇帝决策把关的谏院主管,又担任过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副使之职。他关心国家安全,忠于职守,学习并运用《孙子兵法》,就当时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朝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做了大量的实际性工作。探讨这些史实,我们不仅可以学习欧阳修严谨治学的精神,而且可以了解北宋时期先贤学习和实践《孙子兵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孙子兵法》的理解,所以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一、利用编纂《崇文书目》之便学习《孙子兵法》
景祐元年(1034),28 岁的欧阳修“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书目》,到庆历元年(1041)完成。这期间,他为《易类》和《兵家类》30 种书撰写了简短的“叙释”。由此,他接触到各种《孙子》注本,并对《孙子兵法》产生了兴趣。其中,尤其是他的诗友梅尧臣所作《孙子注》,更加深了他对《孙子兵法》及其作者孙武的认识,从而写下了著名的《孙子后序》。
他在《崇文总目叙释·兵学类》中说:“《周礼·夏官》:司马掌军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书》之《洪范》:‘八曰师。’《易》之《系辞》:‘取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然而,“《司马之法》本之礼仪,后世没行焉。惟孙武之书,法术大详”〔1〕。这样,他不但通晓兵法,还了解了军事历史,认识到《司马法》后世已无人实行,惟有《孙子兵法》因“法术大详”,后人多能运用。
欧阳修深入学习《孙子兵法》,对各家的注解做了认真的比较,以从中探求孙子的本意及后人的心得。他在《孙子后序》中说:“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孙子’。……三家之注,皞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2〕如杜牧注《谋攻篇》“修橹轒 ”之“橹”曰:“橹,即今之所谓彭排。……陈皞曰:‘杜称橹为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当用此樐字。’”〔3〕陈皞指出了杜牧的错误,“彭排”是盾牌,《孙子兵法》中的“橹”与“轒
”连在一起,说明“橹”不是一般的盾牌,而是建在轒 车上有挡箭作用的大盾。再如,杜牧注“少则能逃之”说:“兵不敌,且避其锋,当俟隙,便奋决求胜。言能者,谓能忍忿受耻,敌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战也。”对此,陈皞曰:“此说非也。但敌人兵倍于我,则宜避之,以骄其志,用为后图,非为忍忿受耻。”〔4〕又如,杜牧注“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说:“恃我之强,不知敌不可伐者,一胜一负。”陈皞曰:“杜说乃是出兵无名,而伐无罪,所以败也。非一胜一负之义。”〔5〕陈皞对杜牧的批评是对的。孙子的观点,胜负在于自己一方,“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孙子兵法·形篇》)。既然“敌不可伐”,就是敌不可胜,自然伐者败,伐者无胜算,不会“一胜一负”。欧阳修注意到了这些,说陈皞“其说时时攻牧之短”,就是对陈皞的肯定。其实,欧阳修对《孙子兵法》也有自己的理解,认为“注者虽多而少当也”〔6〕。
由于时代不同,注家的经历不同,所以大家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也不可能相同,这并不奇怪。例如,欧阳修的朋友、著名诗人梅尧臣,他对曹操和杜牧的注解就不大认可。欧阳修在《圣俞会饮》诗中说:“诗工镵刻露天骨,将论纵横轻玉钤。遗编最爱孙武说,往往曹杜遭夷芟。”〔7〕就指出了梅注删除曹操和杜牧注解的事实。但是,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欧阳修学习、研究《孙子兵法》之细致与深入,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高深造诣。
二、“胜败系人谋,得失由庙算”
欧阳修开始运用《孙子兵法》的时间,难以考证,但从其著作中最早涉及《孙子兵法》的有关内容,可以推见其注意运用《孙子兵法》的时间。从现有文献看,欧阳修最早言及《孙子兵法》运用的是他作于康定元年(1040)的《送任处士归太原》诗,是年欧阳修34 岁。
《送任处士归太原》题下有小序说:“时天兵方讨赵元昊。”〔8〕赵元昊本是处于西夏的地方藩臣,宝元二年(1039)派人到京城,通告西夏独立,希望朝廷承认这一分裂行为,一时震惊全国。
当时,大多数官员主张兴师问罪。仁宗于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元昊。由于是在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战,宋军接连失败。元昊进攻金明寨(今陕西安南寨)得手后,派人与延州(今延安)知州范雍联系,表示愿与宋廷和谈。范雍信以为真,当即上疏朝廷,并放松了延州的防御。康定元年正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鄜延路副总管刘平、石元孙奉命前往增援。刘、石军到达三川口(延安市西北)时,遭遇早已驻守的西夏军队的包围。西夏军以逸待劳,刘、石军只好苦战,双方伤亡惨重。于是,刘平下令宋军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元昊派人劝降,刘平拒绝投降。这时,本该前来救援的宋军竟然逃走。刘、石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致失败,刘平、石元孙被俘。
三川口失败,北宋朝廷再谋征伐西夏。在这一背景下,欧阳修写下了《送任处士归太原》这首重要的诗作。这不是一首普通的送别之诗,而是借机向朝廷进献讨伐西夏的策略诗。诗中,诗人运用《孙子兵法》提醒朝廷应“采奇谋”以攻敌。全诗如下:
一虏动边陲,用兵三十万。天威岂不严,贼首犹未献。
自古王者师,有征而不战。胜败系人谋,得失由庙算。
是以天子明,咨询务周遍。直欲采奇谋,不为人品限。
公车百千辈,下不遗仆贱。况于儒学者,延纳宜无间。
如何任生来,三月不得见?方兹急士时,论策岂宜慢!
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闭户不求闻,忽来谁所荐。
人贤故当用,举缪不加谴。赏罚两无文,是非奚以辨?
遂令拂衣归,安使来者劝?嗟吾笔与舌,非职不敢谏。〔9〕
诗的第一至四句,写出了边疆的用兵形势。
诗的第五至十二句是欧阳修自叙自己的用兵主张。他根据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提出了“有征而不战”的主张,说胜败的关键在于“人谋”,在于“庙算”。这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宋军的失败不是兵力弱,也不是将士不力战,而是“人谋”不到位,“庙算”不准确。“庙算”出自《孙子兵法·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所以,要战胜敌人,必须用“奇谋”。用奇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仅能战胜敌人,而且伤亡小,代价低。要用“奇谋”,首先要广采“奇谋”,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士的意见。如此,便引出了这位从太原到汴梁献策的任处士三月而不被接见的故事。
诗的第十三句至末尾,是叙述任处士到京城献策、朝廷不置可否、三个月没人置问、气得任处士愤而回太原的事实和欧阳修就此事对朝廷的批评;并且,他说自己当时不在谏职,有意见也无法提。
全诗表露了欧阳修对国家大事的极端关心,表明他对《孙子兵法》已烂熟于胸。所以,欧阳修写这首诗的目的,除了表示对任处士的理解和慰藉,也有向朝廷献计献策的意思。
虽然任处士没被朝廷接见,欧阳修的诗也不知是否传到决策者耳中,但西部边疆的战事,确实是靠出“奇谋”取胜的。夏军围延州,身为鄜延路钤辖的许怀德“遽还,夜遣裨将以步骑千余人,出奇不意击之,斩首二百级,遂解延州”之围〔10〕。许怀德偷袭元昊得手,西夏军战败,被迫撤离,边疆遂得以暂安。
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之后,爱而用之。他在任谏官之时,多次引《孙子兵法》为据,论人议事,上疏皇帝。他在庆历二年的《准诏言事上书》中说:
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闻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不敢妄动,今一旦发起狂谋者,其意何在?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故敢启其贪心,伺隙而动尔。今若敕励诸将,选兵秣马,疾入西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则吾军威大振,而虏计沮矣。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今诇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欲并二国之力,窥我河北、陕西。若使二虏并寇,则难以力支。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则虏势减半,不能独举。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元昊地狭,贼兵不多,向来攻我,传闻北虏常有助兵。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而元昊骤然被击,必求助于北虏。北虏分兵助昊,则可牵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则二国有隙,自相疑贰。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我能先期大举,则元昊仓皇自救不暇,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是破其素定之约,乖其克日之期。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胜,常有轻视诸将之心,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方经营于河朔,必谓我师不能西出。今乘其骄怠,正是疾驱急击之时。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此取胜之上策也。〔11〕650-651
当北宋面临西夏和契丹有可能联合攻击之时,欧阳修极力主张出兵西界,痛击西夏,其理论根据就是孙子的“伐谋”“伐交”之策。文中说到的“亲而离之”“出其不意”,亦都是《孙子兵法》谋略思想。
四、“将者,国之司命”
欧阳修不仅学习、研究《孙子兵法》,而且注意在军事实践中加以运用。
庆历三年(1043),他任职谏院。谏院是专门负责监督皇帝行政、对皇帝施政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机关。欧阳修知谏院,即多次引用《孙子兵法》论列政事,向宋仁宗提出自己在军事上的意见和建议。
就在这年,西夏元昊点集兵马,准备反叛。然而,这时驻守在今山西运城的“河东都署”将帅都不知兵。欧阳修上书《论赵振不可将兵劄子》说:
伏见河东都部署眀镐,虽是材臣,未谙战阵。副部署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结,沽买声誉,所以不因功业,擢至将帅。前在延州,遂至败误,虽行责降,不及期年,却授兵权,全无报效。其人少壮,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战斗,一旦临事,必误国家。臣闻:将者,国之司命。〔12〕
这是说,将帅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之司命”,即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如此重任,绝不可轻易授人,并以此作为“赵振不可为将”的理论根据。欧阳修所论是正确的,更何况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前在延州,遂至败误”,且是“老病”之辈,怎么能为将呢?此处所引,系《孙子兵法·作战篇》的内容,原文为:“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将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孙武以“道、天、地、将、法”作为预测战争胜负的条件。其中,“道”主要取决于国君的决策,“天、地、法”则全在将帅的利用和掌握,可见将帅在战争中有决定性作用。战争的胜负关系国家的存亡,所以孙子说将是“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而欧阳修则直接说“将者,国之司命也”。
在《论军中选将劄子》中,欧阳修又说:
臣伏见国家自西鄙用兵,累经败失……今军帅暗懦非其人,禁兵骄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然未有于用兵之时而反忘武备如今日者。兵法曰:“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辈当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卫天子,如当今之事势,而以民之司命,国之安危系此数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轻侮?〔13〕
欧阳修再次用《孙子兵法》阐述将帅乃百姓性命和国家安危之所系、不可不认真择取可用之人的道理。
庆历三年,欧阳修在《论李昭亮不可将兵劄子》说:“臣窃见朝廷作事常患因循,应急则草草且行,才过便不复留 意。”〔14〕意思是说,凡事没有预先准备,像事关国家安全的用兵问题,没有将才储备,有了战事只好让像李昭亮这样朝廷上下都知其“不堪为将帅”且又被“四夷所笑”的人为将。一旦误事,悔之无及!为国家计,为天下百姓计,欧阳修进一步请求仁宗:“宜作先时之备。《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为社稷之计,深思而行之,则天下幸 甚。”〔15〕将才的任用是战争最重要的准备,有些在平时很会来事的将官,特别是那些贪腐的将官,战斗真正打起来是很容易误事的,有的甚至叛国投敌。对此,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人才储备,到时候是会吃大亏的。
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16〕。麟州在今陕西神木一带,是与西夏对垒的前线重要州郡。通过前往靠近麟州的山西调研后,欧阳修上书说:“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于策为便。”“由是(麟)州得存。”〔17〕欧阳修保住了麟州,保住了西北的安全,也解决了向麟州转运大量军需粮草的问题,为国家安全立了大功。
欧阳修从河东回来后,正赶上保州兵乱。富弼为宣抚使,在平息兵乱时,“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隶州郡”。他怕日后生变,又使人欲同日诛杀这二千人。欧阳修与富弼相遇于内黄县,半夜无人之际,富弼把这事告诉了欧阳修。“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18〕“富弼醒悟而止。”〔19〕这样,不仅救了两千人的性命,也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震荡。
五、“必用先起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任枢密副使。第二年“参知政事”,协助宰相韩琦处理国家大事。他“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20〕8352。欧阳修深入调查研究,在“知彼知己”上下功夫,“考”天下军事实际情况,对一些重要数据都能具体掌握。不管到哪里,他不用问当地官员,都能了解具体情况,在军事和战备方面做了不少弥补漏缺的工作。
治平二年(1065)正月,欧阳修向英宗提出了自己的战略建议《言西边事宜第一状》。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修运用《孙子兵法》分析敌情我情,总结教训,提出了对西夏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战略主张。
他首先分析敌情,认为西夏“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21〕,因此其“必为边患”。而宋军在韩琦、范仲淹对西北边境的经营下,“人谋渐得,武备渐修”,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若其果叛,未必不为中国利也”。据此,他提出了彻底消灭西夏,将其赶出黄河以南,“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22〕的上、中、下三策。接着,他又总结了过去宋军失利的原因。他认为,《孙子兵法·虚实篇》早就强调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而当时北宋对西夏的情形正好相反,是敌合而我分。他说:
(宋军)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23〕
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我守而敌攻。欧阳修指出,要改变这一局面,“必用先起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24〕。也就是说:要转守为攻,先发制人,合众出击。
欧阳修说:
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别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无不困之虏矣。〔25〕
其实,这一计策正是当年孙武与伍子胥献给吴王阖庐的疲楚之计。《左传·昭公三十年》载,伍子胥对吴王阖庐说:
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26〕
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孙子兵法》与《左传》有深入之研究。文中论及的“开阖变化,有正有奇”“见形应变,因敌制胜”等,都是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具体应用。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欧阳修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全面执行,但其对北宋当时军事工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军事上的正确认识,无疑来自《孙子兵法》。欧阳修正确的军事思想,如重视将帅的选拔与培养,提出战场上要“先起制人”,重视主动进攻,反对消极分散的保守等,在当时都是符合实际的。当时的北宋朝廷如能听取他的意见,采取恰当而符合实际的军事策略,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北宋王朝也许兴盛的时间可以长些。
【注释】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93~1894 页
〔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6 页。
〔3〕曹操等注:《孙子兵法》,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 页。
〔4〕曹操等注:《孙子兵法》,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 页。
〔5〕曹操等注:《孙子兵法》,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 页。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6 页。
〔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 页。
〔8〕〔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 页。
〔10〕脱脱等撰:《宋史》第九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417 页。
〔1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0~651 页。
〔1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11 页。
〔1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20 页。
〔1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50 页。
〔1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51 页。
〔16〕〔17〕〔18〕〔19〕脱脱等撰:《宋史》第九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350 页。
〔20〕脱脱等撰:《宋史》第九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352 页。
〔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1 页。
〔22〕〔2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2 页。
〔24〕〔2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3 页。
〔26〕左丘明:《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