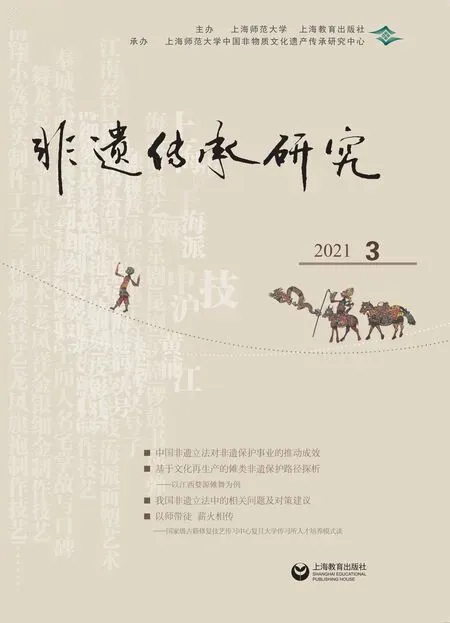择一行爱一行:两次生命的起点
——山西古交市非遗项目“岔口道情戏”自然传人王谷唤访谈
采访人:闫慧芳 受访人:王谷唤
“岔口道情戏”自然传人王谷唤,是目前山西省古交市岔口道情剧团中最为年长的,也是岔口村第一批学习道情戏的人。作为当地的道情戏名角,他深悉道情戏的起源发展与传承脉络,为道情戏的传承与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谷唤痴迷于道情戏,奉献于道情戏,从第二批学徒开始,他负责传授唱腔与表演技艺;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保留下了珍贵的道具箱,并集齐各方力量记录和整理了几十本道情戏的剧本。随着非遗保护的不断推广与深入,“岔口道情戏”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本土民众也逐渐意识到非遗传承的意义与价值。2009年,岔口道情戏成为古交市第一批非遗项目,王谷唤徒弟冯玉娃被列为古交市非遗项目“岔口道情戏”代表性传承人。
在这次自然传人口述史访谈中,笔者着重以自然传人主体的学艺史和生活史为切入点。通过访谈认知口述对象,把握自然传人的人物个性,捕捉其记忆深刻的经历和体验,从而为自然传人建立文化档案,让自然传人能够在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从咂手锣到学唱道情戏
闫:“岔口道情戏”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在当地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据了解,您是岔口道情剧团中最为年长的,也是岔口村第一批学习道情戏的。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道情戏的?
王:我193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五,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不幸夭折了。从小家贫,没上过几年学。8岁才开始上学,只念了两三个冬天。夏天没功夫念,因为要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儿。在我10岁的时候,村里就有道情戏了,还有专门的道情房。我是11岁不上学的,白天劳动完,到了晚上闲下来的时候就和同伴们跑去道情房看他们排练、汇演。每次我都是守在演员身边,把脑袋凑过去,偷偷地将看到的、听到的记在心里。因为年纪小,有时候也不太能听懂师傅讲的东西。起初,我对乐师手里的手锣尤其感兴趣,总是想过去敲一下。乐师听到后从炕上下来,二话不说就往我脑袋上敲几下,接着又上炕继续排练去了。唉,于是“摔给两逼斗(按:“逼斗”指巴掌),揉上两眼眼”就成了家常便饭。像这样因为淘气被打的次数,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了。
后来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和乐师说别打这孩子了,看他真的是“爱见”这手锣,要不让他试试吧。再加上当时班子里学手锣的学徒总是拿不下来,听到师傅让我试试的话后,乐师也就同意了。他们排练“红场”的时候就让我咂手锣,令他们意外的是,我一咂居然都能对在他们的点上。师傅惊喜地说道:“这是一个‘苗苗儿’,孩子愿意学的话咱们就带上吧。”师傅问我是否愿意,我马上就回答愿意。但是,师傅告诉我还必须得到父母的允许才可以。开始的时候,父母并不同意我去学,担心我因为年龄小,吃不了这份苦。我记得父亲还吓唬我,如果我跟上戏班子了,以后就是戏班子的人了。但我当时也没有害怕,依然坚持要去学。父母拿我没办法,慢慢便答应了。
13岁那一年的冬天,我正式进入了道情班子,最初学习的就是咂手锣。当时我是班子里年纪最小的,他们都比我大七八岁。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也确实是因为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才敢在父母的反对下坚持要学。
闫:您是从咂手锣开始学习道情戏的。您当时拜师学艺的时候有拜师仪式吗?如今,您唱道情很有名气,从咂手锣到学唱道情戏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我们那时已经没有拜师仪式了,但是在出去演出前,师傅(当时也是班主)会给班子里的所有人下跪,和我们说“这次去演出就靠大家伙儿了”,这不是简单的下跪,这一跪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们所有人一切都要听班主的。
我拜师、进团,只排了一个腊月的戏,正月就出台。我第一次出台是去娄烦(按:指太原娄烦县)演出,正月和二月两个月,开春了我们就回来了。在娄烦,我的手锣是很出名的,看戏的人经常说:“看外(按:“外”指“个”)孩儿,人倒不大,耍得可是不赖啊。”咂手锣我一直做到十八九岁,好天气还好说,遇上那坏天气,手指头冻得都要掉下来了。看着人家舞台上唱道情戏的演员唱完就可以回去烤火,我心想,他们可以唱,我咋不能唱了?我也能学啊。于是,我就开始边咂手锣边偷偷地往心里记他们的唱词。后来有一次,唱小丑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上台演出,我就主动提出我上去顶,开始班主还不太相信,但是没办法,就让我上去演了。这次演出后,就经常让我帮着顶一下这个,帮着顶一下那个了。后来,咂手锣和唱道情轮换着来,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
从那个时候开始唱道情戏,一直到现在,一辈子都在干这行。多次演出后,不论是在当地还是娄烦一带,一说到我的名字,爱看戏的人基本都知道。
二、痴迷于道情戏
闫:道情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历史悠久,表演形式丰富,极具地方色彩。岔口道情戏发展至今,颇受欢迎,这一地方戏曲最初是如何流传到岔口一带的呢?
王:小时候,我听师傅聊到过,道情戏的发源地在陕西。道情戏这个剧种是道人发明的,也就是道人念教的道歌,后来传到民间,民间唤为“道情戏”。有段时间,道情戏被认为是迷信。
首先,企业的资金结构不合理,地方性债务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市场变化能力较弱,并且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中低区段,经营模式过于粗糙。并且大型国有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多数偏重于大规模的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进行融资,这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杠杆率较大[2]。
我们村的师傅是从娄烦请过来的。当时正赶上古交南龙沟村七月里闹红火,师傅在那里带着道情班子唱戏。我们村里有俩人去南龙沟看戏,边看边和南龙沟村的人说,这戏种真是不赖啊!对方问,你们想学吗?这里就有个师傅,你们要是想学,就让师傅跟你们去。这俩人直接就答应下来了,把师傅从南龙沟带回了村里。回村后,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只要愿意学都可以跟着师傅学。
就这样,从1949年的冬天开始,岔口村的道情戏出世了,道情戏班子也开始成立了。
闫:您是1938年出生,13岁时正式进入了道情班子,也就是说1951年开始学习道情戏的。您说“过去道情戏被认为是迷信传统”,那么岔口道情戏是否经历过传承的中断?
王:岔口村的道情戏从1949年冬天出世,一直唱到了1966年,然后就停止了,没有人唱了。道情戏当时被认为是迷信,村里的红卫兵商议要烧掉道情戏的道具箱。因为我当时任贫协主任一职,红卫兵的连长提前找我商议烧箱子的事情,我一听就急了:“疯了吗?以后村里的年轻人再想继续,没有道具怎么办?大家伙儿摊钱也摊不起啊!”当年置办这些道具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在过去,出去演出挣的都是米,只能是用卖米的钱来买牛,再把牛卖到煤窑,这样才攒够钱到省城去买服装和道具。道具箱子就是这样置办回来的,所以我很不愿意毁掉这些箱子。于是,我就偷偷做了个决定,把道具箱子悄悄地藏起来,放在库里不再出露了。
那段历史结束后,道情戏又出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老一辈的不能继续唱了,因为他们装扮出来不像那回事了,也不好看了,所以就叫年轻人来学,我们负责教。当时是农业社时期,招了一批孩子挣上工分学道情戏。孩子们都特别愿意学,因为他们都不想在大冬天又冻又饿地去地里干活儿。教了40天左右就出戏了,正月里到娄烦演出。娄烦人爱道情戏,师傅又是娄烦的,所以道情戏在娄烦一带很受欢迎。
闫:道具箱能够被保留下来,多亏了您当时的这一举动。岔口道情戏有了物,又有了人,这中间离不开您对道情戏的真爱。听说,您说过“我13岁就开始学上道情戏了,一辈子就喜欢这个,你就不要拦着我唱道情戏了,我要活到老唱到老”。您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琐事等是否对您的这一爱好产生了影响?
王:我是21岁结婚成家的。刚开始,我爱人的家人不支持我们在一起,觉得我是唱戏的,当时民间总说“王八戏子”。但是我爱人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和我在一起,她觉得我有一门技艺,凭本事吃饭,跟着我不会吃苦。
我原本有6个孩子,其中5个女儿和1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但是,儿子18岁那年遭遇事故离开了我们。中年丧子,我整整躺了一年,这一年里我什么都不想去想,什么都不想去干。后来剧团里的几个人来开导我:“谷唤啊,你不能就这样躺着了,你躺着咱们的道情戏怎么办,孩子们还等着呢。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起来吧,一起把咱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道情戏撑下去。”几次的劝说,让我爬了起来,这次是道情戏救了我,我又重新开始唱道情戏。
闫:兴趣、天赋、信念,使您在道情戏中得到新生。通过与您的交谈,我深深地体会到,您将道情戏视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了道情戏,您付出了很多,但也收获了很多,几十年如一日,依然痴迷于道情戏。现在,岔口道情戏成为当地的非遗项目,这对您而言,也是一种坚持的回报吧。
王:回想过往,其实我就是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实际上,过去我们的路很艰辛,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了道具箱,这么多年里也不断地新换了服装、道具。眼看着一切都齐全了,但是,2016年正月从娄烦演出回来的那天晚上,道具箱被偷了,我们的心血没了。后来我们几个老演员商议,决定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和村里做生意的老板拉赞助。没想到,对方一听我们的来意,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出钱为村里道情戏剧团重新置办了道具箱。但是好景不长,2017年9月的一个晚上,道具箱又被偷了,这次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去开口请求帮助了,就这样,道情戏剧团没办法再去演出。后来,还是之前那位老板听说了道具箱丢失的事情,主动找到我们,并出钱置办了最好的、最齐全的道具箱。
经历了两次道具箱丢失的风波,剧团的人开会商量要派专人好好看住这些宝贝,也一定要把“岔口道情戏”热热闹闹地传承下去。
三、传承之“变与不变”
闫:“岔口道情戏”发展至今,与过去相比,如今的传承有了哪些变化?
王:过去,“岔口道情戏”都是师傅口传身授,没有本子。排戏的时候,首先是师傅和学徒一起围坐在道情房的炕上,师傅会教每一个学徒每一场戏的唱词,等到学徒们在炕上都会念词了,就下地排练动作。师傅在地上念着调儿,边唱边摆动作,我们叫这是“黑场”,也就是“黑拉儿”;“黑场”结束后开始“红场”,也就是把乐器加上,等到“黑场”和“红场”都熟悉了,这场戏就算是排完了,然后就开始排下一场戏。现在则变成了口传和书写。剧团会带上一个专门写的人,师傅念,这个人都写下来,然后演员们就各自拿上属于自己角色的词来学。当今人们的文化层次提高了,演艺人员有了这样的变化,也很正常,当然,道情戏的核心没有变化。
道情戏传承有序,谱系清晰,演员有了新变。“岔口道情戏”到现在已经是第六批了,我是第一批学的。第一、第二批道情戏学徒都是男性,第三批开始也招收女性,但是这批闺女们,学会以后唱了三年就出嫁了,演员凑不齐了,导致无法演出。第四、第五批的时候还是有闺女们想学,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还是继续教了,可是演员凑不齐无法演出的情况再次发生。眼看着道情戏剧团越来越办不起来,所以从第六批开始不得不改变了收徒方式,只收男性和儿媳(按:已婚女性)。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不愿意学的儿媳们,我们就会给她们做思想工作,她们也逐渐接受了道情戏。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会说“王八戏子”,一般不会让学唱戏、响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学习这些了。
记得以前我们演出的时候,台下看戏的人觉得我们唱得或者演得精彩的时候,他们从台下扔上来烟或者钱,这是一种台上台下互动的方式,我们台上的演员遇到这样的情况,表演也都会更卖力。而现在,年轻人大都喜欢上网、看电影、看电视等,都没有多少人喜欢看道情戏了。
闫: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剧团年轻成员大都进城打工谋生,春节期间才返回家乡;同时,道情戏的演出具有节日性,只有春节和村节演出才更为频繁。现在还有人主动来学习“岔口道情戏”吗?
王:现在,老百姓也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特别是春节和村节期间,剧团成员会自发组织起来,义务在本村演出。因此,“岔口道情戏”才能一直传承下来。
现在选演员也是和过去一样,主要看个人意愿,而且农村剧团和国家剧团在选人上也是有区别的。这个人只要愿意,如果嗓子不行,就换到武场,武场不行就换到文场,就这样来回调换。
我有两个女儿是第六批跟着学道情戏的,虽然她们是闺女,但是女儿和女婿为了方便照顾我们老人,儿子走后,他们就搬来岔口村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也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住在我身边的缘故,所以也就收女儿为徒了。“岔口道情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规矩:花戏原则。比如我虽为女儿们的师傅,但还是有讲究的,作为父亲,我不能教她们道情戏中的花戏,她们需要向其他的师傅拜师学习。
闫:虽年事已高,但您的嗓音依旧这般铿锵有力,浑厚自然,动作也是灵活自如。对于“岔口道情戏”,您热爱着,坚持着,是位朴实的文化传承者,非遗传承的初心不变,实属珍贵。请问您对“岔口道情戏”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王:我从小没读多少书,也没什么文化,但就是一辈子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道情戏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站起来了,我不希望“岔口道情戏”就这样中断了。现在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把我一生学到的全部教给孩子们,给他们置办好演出道具,尽力帮助孩子们把道情戏继续传承下去。我想,我的过往经历无非就是择一行爱一行,秉承这份热情和坚持。非遗发展也应当如此吧。
——蓝田上许村道情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