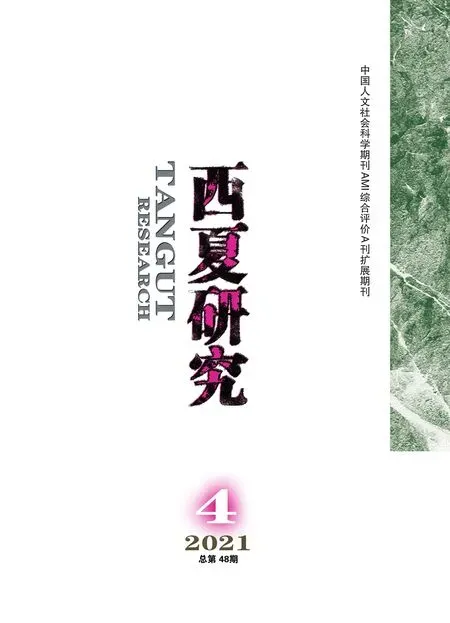西夏文献史的基石:近年来的新成果
□[英]彼得·科尼基 著 侯 凤 译
19世纪晚期,在中国发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铭文和钱币上的文字开始激起欧洲东方学者的兴趣。这些文字于1882年被戴维理亚确定为西夏文,但事实上,在本世纪(19世纪)早期西方汉学家不知情的时候,一位名叫张澍的中国学者就已经确定这种文字为西夏文①[1][2]。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北部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法国人毛利瑟对其中一份(一部西夏译本《妙法莲华经》的手稿,并包含少量汉字注释)进行了解读,并于1904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②[1]。1908年,沙俄帝国军队科兹洛夫上校挖掘了黑水城遗址,并在那里发现了两千多部西夏文献和残片,所有这些文献和残片现收藏于圣彼得堡科学院东方研究所③[3]。随后的几十年里,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等的挖掘工作使更多的西夏文献重现于世。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拜寺沟的一座宝塔上发生的破坏行为意外地揭开了一个隐藏书库的存在,这是对西夏语料库的一个重要补充④[4]。因此,在今天,西夏文献不仅可以在俄国圣彼得堡找到,而且可以在中国的多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很多地方找到。它们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扩充了《宋史》记录的西夏史的分量,而且佐证了11—12世纪中国边疆书籍文化的繁荣。
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俄罗斯学者主导着西夏研究领域,特别是尹凤阁(A.I.Ivanov)和聂历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很遗憾,他们都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被枪杀。之后是索弗罗诺夫(M.V.Sofronov)、克恰诺夫(E.I.Kychanov)和克平(Ksenia Keping)(英语写作Kepping)。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西田龙雄(Nishida Tatsuo),英国图书馆的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美国的邓如萍(Ruth Dunnell)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学者,特别是史金波和聂鸿音也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作出重大和实质性的贡献,西夏研究可以说是蓬勃发展。⑤
近年来,西夏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主要收藏地西夏文献影印本的出版发行,这使得还原(鲜活的)西夏历史成为可能⑥[5]。由此圣彼得堡、伦敦、巴黎和中国的许多独特的西夏文本首次被广泛使用开来,促成了笔者的这篇文章。这些文献成果如下。
(1)史金波、陈育宁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总20卷(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这套书中包含了各种中国藏西夏书籍和手稿的影印本。完整的内容清单可参阅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http://www.lib.cam.ac.uk/mulu/fh98017321751.html.)。
(2)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共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7)。这套书中包含了现收藏于圣彼得堡的科兹洛夫藏品。完整的内容清单可参阅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黑水城网站(http://www.lib.cam.ac.uk/mulu/heishui.html.)。
(3)吴芳思、谢玉杰编:《英藏黑水城文献》,共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包含黑水城出土、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斯坦因藏品的一部分)。
(4)李伟、郭恩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包含了敦煌出土,现收藏于巴黎的伯希和藏品的一部分。这是这四部影印本中唯一一部将西夏文翻译成汉文并在中国佛教经典中识别底本的,这无疑是由于法国藏品规模较小才使其具有可行性,这也给不认识西夏文的使用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下面的行文中我将这些文献分别简称为《中藏》、《俄藏》、《英藏》和《法藏》。
到目前为止,这些发现都是从11世纪和12世纪开始的,因为西夏是于1038年建立、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这些文献中一些文本是中文的,但是大部分是西夏文的。西夏文字于1036年创制并使用,至少部分是为了促进佛教文本在西夏的翻译⑦[6][7]。在日本、韩国和越南,与汉文文本的接触并没有激起任何类似的民间方言文本的搜索或翻译的冲动,这本身是值得注意的。可以提出哪些解释?一种解释是,西夏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其他文字,特别是回鹘文和藏文,因此,他们开始书写西夏文并不是由汉文决定的,尽管西夏文与汉文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许多佛教文本被翻译成西夏文,实际上不是从中文原文本翻译而来,而是从梵文、藏文和回鹘文的文本翻译而来⑧[8][9]。第二种解释应该是政治背景。宋并没有像唐一样主宰东亚,也没有在文化上威慑到他们的邻居。因此,西夏对宋的态度往往是勉强的,有时是公开的反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邓如萍将西夏文的创制描述如下,“这是一个具有战略色彩的事件,用以彰显文化主张,满足战略需要,并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即使采取的是以汉字为参照的文字体系,而不是在语言学上更适合(党项人)的藏文字母,这个决策也是政治性的”⑨[10]。在这种情况下创制的西夏文字被用来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如法典,以及翻译佛教和其他文献。这足以证明西夏文字在民间传播的驱动力。然而,应该强调的是,西夏文献远非纯西夏文,因为大量的文本也是由西夏人用汉文印刷的。
这四套影印本中的复本包括许多残片和短小的文献,也有完整的作品,文本的多样性是惊人的:在语言和文字方面,有些是中文的,有些是西夏文的,还有一些是双语的。有些文本是写本,也有许多是刻本;有些是用雕版印刷的,有些是活字印刷。这些文本包括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活字印刷的文本。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早在1958年,藤枝晃(Fujieda Akira)就将京都大学的西夏文《华严经》确定为活字印刷产品,这些发现由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于1974年公开。⑩[11][12][13][14][15]然而,新的发现表明,在韩国半岛上有任何活字印刷的证据之前,西夏人已经广泛并熟练地使用了活字印刷。这些活字印刷版本包括西夏译本《华严经》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些译本是在拜寺沟方塔发现的,虽然没有注明日期,但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字印刷书籍,他们的复本被收入《中藏》7—8卷和14—15卷。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认为这种活字印刷是木活字,其实其中一些可能是泥活字。孙寿岭最近进行的实验似乎表明,泥活字是能够产生类似于已经发现的西夏文本的○1[16]。如果这是正确的,这将使它成为11世纪宋朝毕昇活字印刷技术使用的唯一存世印本。
西夏尊崇佛教,懂汉文的西夏皇帝努力获取汉文佛经。为了获得《开宝藏》的副本(5057卷,公元983年雕印完毕),他向北宋派遣使团赎经,有时他们贡献马匹作为印经的费用,有时是宋朝无偿赐给,现有文献中可查到的11世纪西夏向宋赎经的记载有六次○12[17]。西夏成立了译经和释经场,到11世纪末,佛经的翻译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一部元朝1312年刻印的西夏典籍中,其中一个文本的前言提到,西夏共译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显然这是译经史上一个惊人的创举○13[17]。另一方面,西夏人也出版了许多汉文的佛教文本。一位中文名字是智光的西夏和尚用汉文写的一篇文章被列入典籍,这是一篇题为《密咒圆音往生集》的密咒○14。人们可能会认为,佛教文本的西夏版本和汉文版本的受众是不同的,汉文版本是给受过教育的僧伽的,西夏文版本是给平民百姓的,但并不一定是这样。克平指出,只有西夏人发行了汉文佛教典籍的本族语言译本,而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辽契丹人或金女真人都没有这样做○15[18]。这可能需要一些修改,因为用回鹘文翻译的佛教典籍的数量现在已是相当可观○16[19]。然而,确实是有数量相当的佛教文本是用西夏文翻译并刻印的,这足以让我们称之为《西夏文大藏经》○17[20]。个别的译经中有详细的题款,以识别在位的西夏皇帝和皇后、译经者和编经者以及该译本译自何种语言。除此之外,这些题款使我们有可能确定一些并未给出确切日期的译本的翻译时间。克恰诺夫专门对藏于圣彼得堡的文本的题款进行了研究,确认了160多名“供养人”的姓名,他们是经文抄写的出资者;127名抄经者的姓名,包括一名女性和三名被推断为汉人的人;10名刻印师和14名编经者的姓名,其中一名被确认曾在书籍活字印刷部门工作○18[21][22]。
佛教文献的西夏译本涵盖了大量的版式,可能但不一定反映当时宋朝的常规版式。在经文的结尾处,有用金粉抄写在深蓝色纸上的非常美观的字体,看起来非常奢华,也有配有精美插图的手抄经卷。在日本、朝鲜也有大量类似的传世版本。除此之外,还有活字版印本,有些活字印本的每一页空白处都会有木刻,这说明有一些不太成熟的读者群曾经读过这些文本,但是在其他地方现存的文献中很少有相似的文本,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中藏》第16卷中《妙法莲华经》的复本。
西夏的翻译绝不仅限于佛教文本。到目前为止,其他的文本还包括《论语》(两个不同版本)的刻印译本、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几部军事著作和《贞观政要》的一部分,以及《孟子》和《孝经》的手抄译本○19[23][24][25]。其中许多已列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卷。还有更多的,《宋史》中对于西夏的记载提到了西夏人对于早期词典《尔雅》、《四言杂字》和《孝经》的翻译○20[26]。现存西夏文本《孙子兵法》刻本残页包含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和其他版本的文本有相当明显的差异○21[27]。克平把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翻译风格,如佛教文本,描述为“逐字对译”,意思是每个汉字都被翻译成西夏文;这并不意味着忽视西夏语的句法,相反,正如克平所说,译者也被原文吓到了○2。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孙子兵法》或诸葛亮(181—234)的《将苑》的翻译。《将苑》的写本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克平曾对其进行考释,后来是高奕瑞(Galambos)○23[28][29][30]。这两部作品的译者似乎都秉承了对汉语的解释性翻译,把抽象的表达转化为较为具体的表达,省略或者改编暗喻和其他可能对于汉人读者来说较为熟悉但对西夏读者来说不那么熟悉的表达形式,扩展了汉语地名,以表明这些地名是属于城市名、河名还是国名。然而,正如高奕瑞所表明的那样,该翻译是从与所有现存版本不同的中文文本中进行的,现存版本都是较晚的,因此需要谨慎:克平确定的一些差异可能已在译者使用的中文文本中找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夏是存在双语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很难解释诸如骨勒茂才所编并于1190年刻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这类字典的发行了,它提供了西夏字和汉字的解释以及发音指南㉔。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解释的双语词典。现存的刻印复本说明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木刻版本,同时也证明这部字典很受欢迎。它的形式清楚地表明,它不仅是为了让西夏人使用,而且也是为了让讲汉语的人使用,这提出了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即在西夏讲汉语的那些人可能是谁。多个版本的出现表明在西夏既有讲西夏语的人,他们渴望认识汉语;也有讲汉语的人,他们希望理解西夏文。
迄今为止发现的大部分文本要么是汉文文本的西夏译本,要么是西夏发行的汉文文本。尽管一些西夏文的法典被列入《俄藏黑水城文献》,但是西夏文编纂的文本非常少,这是令人惊讶的,也是令人费解的。有可能西夏的书籍以佛教文本为主导,也有可能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文献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而且这一结论似乎更有可能,因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发现都来自寺庙或与佛教相关。
现存的西夏文文本向我们表明,西夏人特别致力于刻印,而且在朝鲜之前,就比任何东亚社会都更热衷于活字印刷。他们一方面在进行着汉文文本的翻译工作,同时他们也在用汉文刻印这些文本。因此,西夏人为其他东亚社会提供了一个反例,以回应中原文本文化,特别是《开宝藏》这一佛教经典的刻印。西夏的书籍业是独特的,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译自Peter Kornicki.Stepstowardsa History of the Tangut Book:Some Recent Publications[J].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2,(2012):83-91.)
注释:
①参见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初探》第313—316页,聂洪音《过去数十年的西夏学》第329页。
②参见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初探》,在第362页,他提供了带有汉字注释的《妙法莲华经》影印本的前两页的复本。
③参见克恰诺夫《文海宝韵:该书及其命运》。克恰诺夫的文章中包含西夏研究的历史。科兹洛夫是一个探险家,既不懂汉文也不懂西夏文。
④细节见宁夏文物考古所的《拜寺沟西夏方塔》。
⑤在下面的网站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西夏学研究目录,它包含了许多多语种的最新研究。http://en.wikibooks.org/wiki/Bibliography_of_Tangut_Studies,which includes many recent items in avariety of languages.http://en.wikibooks.org/wiki/Bibliography_of_Tangut_Studies
⑥有关这本书的历史的一手珍贵资料见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西夏书籍业》。
⑦有关该文献及其来源请参阅鲁光东《西夏文字的结构》和《西夏学札记——论西夏文的创造》。
⑧参见克恰诺夫《西夏译经史》第377页,西夏文佛教译本通常都会确认该译本的源语言;西田龙雄所编圣彼得堡和伦敦藏西夏佛教译本目录确认了源语言,见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卷3—59页。
⑨参见邓如萍《白高大夏国》第37页。
⑩参见罗丰《西夏方塔出土文献》、戴仁《西夏印刷书籍》、傅路德《关于西夏之活字印刷》、藤枝晃《关于西夏文经——石、木和泥——现存最古的活字本》
⑪孙寿岭2007的这篇文章里包含一张他仿印成功的照片,还有罗泰的详细注释。见参考文献[16]。
⑫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59—63页。
⑬同上,66页。译者注:根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举世闻名的《大藏经》先后经历了许多朝代,花费了近一千年的时间,共译出六千多卷,成为佛教史上的盛事。西夏仅用半个多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就译出了三千多卷佛经,平均每年译出六七十卷。因此作者说这是惊人的创举。
⑭关于汉文文本,参见俄藏黑水城文献1—7卷;此典籍中西夏人做的文章为T.#1956,46:1007-1013.译者注:在作者所给的编号中没有找到该文,经搜索,该文在俄藏4,tk271,第359—363页。
⑮参见克平《克平最后的文章和文献》,第30—31页。译者注:作者在这里将西夏、辽、金和日本、朝鲜、越南人并列提出进行对比,显然是将我国的西夏、辽、金少数民族政权视为独立的国家了,而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⑯参见艾宏展《回鹘佛教文献》。
⑰参见克恰诺夫《西夏译经史》第385—386页。该西夏文本曾在格林斯蒂德《西夏文大藏经》中重新影印。
⑱有关这些可确认的西夏译者,见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有关这些题款信息见克恰诺夫《唐古特佛教书籍:供养人、抄经人和编经人》。
⑲参见克罗克罗夫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语译汉文经典》、西田龙雄的《关于西夏语译〈论语〉》、克恰诺夫的《西夏国史纲》第276页。
⑳参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95页。
㉑关于影印本和俄语翻译见克平《〈孙子〉的西夏语译本》。
㉒参见克平、龚煌城《诸葛亮〈将苑〉的番文译本》,载于《克平最后的文章和文献》,第12—23页;高奕瑞《西夏语译〈将苑〉》;高奕瑞《西夏的北邻》;平田昌司《孙子》,第215—228页。
㉓参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卷,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