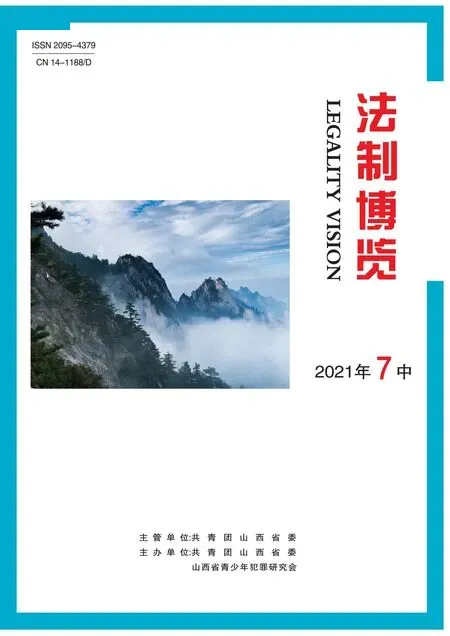环境权基本问题辨析
陈俊丽 黄 伟 布 多
(1.西藏大学,西藏 拉萨 850000;2.西藏技师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3.西藏大学环境研究中心,西藏 拉萨 850000)
环境权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后,一直处于环境法领域被讨论和争议的焦点。赞成环境权的人有之,依据环境权的人权属性、人格权属性或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等,或积极探索构建环境权获得宪法、民法保障的可行路径,或另起炉灶尝试构建以环境权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的理论体系;否定环境权的人亦大有人在,搬出环境权内容模糊、主客体不确定,可操作性较差,设立环境权的必要性不够,设立环境权的宣示意义大于其法律意义等理由,指出某些问题是目前社会发展条件下难以克服的,因此证明环境权从应然权利转化为法律权利或实有权利是不可能的。
对环境权的定义、权利主体、客体、内容等没有哪一项大家能统一认识,这对权利的形成无疑是不利的。据笔者分析大部分学者均是期望能建立起以环境权为基石环境法体系大厦,因此期望构建的环境权理论能够符合已有的环境法体系,在构建我国的环境权理论体系时,多从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出发来提取环境权的法律依据、环境权的主客体、环境权的内容,囿于这种固定思维的限制,学者们所构建的环境权的理论体系是泛化的,难以明确界定的,而这也就影响了环境权的司法实践,这也正是环境权否定者据以抵制的理由。大部分学者很难跳出这种限制,纯粹从环境权的应有之意去构建环境权的理论框架。另外大部分学者均是法学出身,而并不了解环境知识,这也影响学者对环境权性质及内容的判断以及环境法学术语的正确运用。
一、环境权是什么
把环境利益设定为保护好环境之后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到哪些利益或益处。但是杨朝霞认为环境权的权利客体为环境利益,并仅把清洁空气、洁净水源、自然通风、适足采光等一类的利益作为环境利益[1]。这样的环境利益仅包含了一个方面,未把其他的环境利益包含在内。笔者依据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包括开发利用环境行为和静态享用环境行为,静态享用环境的行为赵英杰等称之为本能性环境利用行为[2],如呼吸新鲜空气、直饮天然水源。静态享用环境的行为由于人的享用又会带来健康的身体和精神性利益,如愉悦、舒适的情感体验。开发利用环境行为是基于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是对物的处分和收益,显然属于财产权的内容。对一定质量的环境的静态享用可以促进人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精神性利益,也就是说健康的身体和精神性利益有赖于权利主体对良好环境的静态享用,而静态享用是人之为人不学自会的一项技能,如呼吸空气,饮用水源,享受日光,但是一定质量的环境是我们创设环境权追求的目的,一定质量的环境有助于我们获得相应的利益——健康的身体、精神性利益,这些是我们追求良好环境质量附带来的额外的好处,而我们环境权创设的最初目的不是在这些附带来的利益,而是良好状态的环境。另外有学者将环境权分为经济性权利和生态性权利。经济性权利我们已把它划定为财产权,暂且不予讨论。从陈泉生在《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一文中,将生态性权利解释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等[3],结合上文将创设环境权的目的,发现这里所说的生态性权利亦不是我们所说的环境权。我们所说的环境权是指对良好环境的享用权。
二、环境权是否可以个体享有
有的学者以环境的整体性来说明环境利益的不可分割特性[4],否认环境权的个体化。其实从环境的特点来看,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从范围来说环境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宇宙环境、地球环境等,小的有室内环境等。虽然环境利益是整体的,不可能计算分割到每个人的环境利益是多少,但是只要能确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静态享用一定质量的环境就足够了,并且笔者也并不打算从环境利益的角度创设环境权。另外据学者说地球环境是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客观利益,与其他人没有关系[4],笔者以为此种说法亦不完全正确。虽然我们所欲获得的良好状态的环境有自然的功劳,但其他人的活动也会或好或坏、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的环境,继而影响到我们可以获得的环境利益。因而现当代环境问题的发生可能不仅仅只是自然引起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或者人为引起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单一方面原因,可能更多的是二者复合的结果。这部分笔者仅仅从学理的角度分析环境权私法化的条件是具备的,至于从实践层面实现司法化则是不置可否的,需要下文分析。
三、创设环境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新型的并且可以为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但是目前由于没有我国立法方面的确切规定,环境权还是一项应有权利、道德性权利或习惯性权利,所以要想将环境权上升为一项法律权利,必须对环境权创设的正当性、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环境权的正当性基于环境利益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有学者将其作为第三代人权,并认为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5]。针对目前学者构建的过于泛化的环境权理论是无法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沿着上文的思路尝试对环境权的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以人对良好环境的静态享用为核心内容来构造环境权的理论体系。对良好环境的静态享用只可能为人所享有,所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不能算作环境权的权利主体。目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非常推崇自然体本身的价值,但自然体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对它的利益进行法律保护还停留在争议阶段而未进入实践层面,因此自然体目前也不可能成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而当代自然人和后代人均可以实质性地享受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把环境权的权利主体设定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权的客体设定为良好状态的环境,环境权的内容即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对良好状态环境的静态享用。所以对环境权的保障,只需用保持良好状态的环境即可,当代人和后代人可本能地享用。良好状态的环境具有主观性,但是有学者建议可通过环境基准值的研究,用可感知的数据对良好状态的环境定量描述[6]。这个问题可通过基础研究解决,但对于环境问题的综合效应,每个排污者都符合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综合效应就是有可能出现环境质量下降的状况,如北方取暖季,若每家每户争议符合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但还是出现雾霾现象,这种情况下,侵害他人环境权的加害人就无法找到,就无法实现环境权的救济。仅此一方面就证明创设环境权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是指非此不足以保护该利益,若环境侵权中侵害到他人的财产、健康、人身等传统权利,通过对此类环境侵权设定一些特殊的适用原则或规则,如现行环境法对环境侵权设置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等均是普通民事责任的变通规定;对环境侵害只损害到生态环境的,则可使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类似的制度,由此看来,并非只有通过环境权的创设才可以达到环境利益的实现。因此创设环境权的可能性低,必要性不够。
通过本文分析,环境权是一种新型权利,以追求良好环境为目的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因为环境责任主体无法明确确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环境侵害,环境责任主体无法确定,司法救济则难以实现,基于此,环境权亟需明确立法,以期得到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