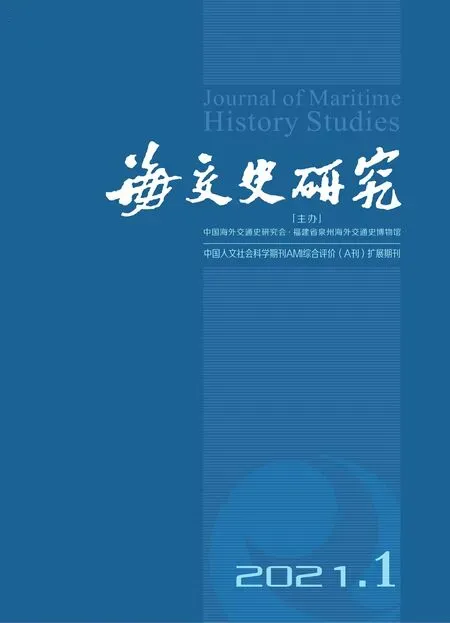《海国图志》出版之初的西人评介*
张坤 田喻
《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思想家魏源编辑的一部关于世界知识的作品。该书的主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着鸦片战争后饱尝丧权辱国之痛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集体心声,曾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各界。作为一部图书汇编,该书第一版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期搜集并编译的西人著述(后来命名《四洲志》出版),兼采中文文献中的相关著述,而魏源也在第一卷加入了自己的编纂主旨。随着资料搜集日广,该书的体量也逐渐增加,从1842年的五十卷本到1847年的六十卷本,再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魏源的编纂最终占据了该书的大半。作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和魏源看到的世界究竟如何?近几年台湾学者苏精先生已有相关论著予以揭示:通过还原《澳门月报》的英文资料来源,作者发现,由于翻译水准的局限,林则徐得到的关于世界的知识错漏百出。(1)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但对于《海国图志》所介绍知识的真实价值,学界还缺乏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评判。近来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取的1850年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海国图志·日本》译介本,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比较的视角。实际上,《海国图志》在初版几年后即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先是德裔英国在华传教士郭实腊(Karl F.A.Gützlaff),再是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时任港督汉文参赞的英国人威妥玛。二人先后在广州的西人报纸《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上发文,前者主要对该书做了介绍和评论,而后者则对其中的一卷《东南洋·日本》进行了译介,从中可以发现同时期西人对该书的认识。以下便以上述两个文本为中心,对《海国图志》出版之初西人的认识进行探究。
一、郭实腊对《海国图志》的介绍
郭实腊,又名郭士猎,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后曾长期在华活动。先后任过英国鸦片商人翻译、英国驻华监督机构翻译,参与过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丛报》的五大撰稿人之一。他著述颇丰,除了英、荷、德语等著作外,也有中文著译60多种,是近代史上极其重要却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其对《海国图志》的介绍在原文中不具名,通过翻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为报纸整理的索引,可以确知其出自郭实腊笔下。(2)“Communicated for the Repository by a Correspondent”, Vol.XVI, September1847,No.9,Chinese Repository,pp.416-425;List of Articles,Vol.XXI,p.xxiv.见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卷,第421页;第21卷,第322页。
该文发表于1847年9月,分卷介绍了《海国图志》的内容。从文章的开篇我们可以得知,在华西人得到的关于该书出版的信息是1844年:“在林则徐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魏源又搜集了京城资料,加上自己的写作,编成《海国图志》1844年夏出版。……我们从未在广州的书店看到这部书,所看到的惟一一部经一位朋友从上海带来。”(3)Vol.XVI, September1847,No.9,Chinese Repository,pp.416-425.见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422页。此外,该书经他们翻阅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到一位法国人手中并带回欧洲了。其装帧,“为雅致的八开本,12册,我们怀疑是金属活字印刷,其外观与通常中国人的书很不一样。”(4)Vol.XVI, September1847,No.9,Chinese Repository,pp.416-425.见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423页。这一说法促使我们重新关注《海国图志》的版本问题。学界一度认定1844年刊本是该书的最早刊本,后经吴泽、黄丽镛撰文明确了五十卷本的存在,并依据魏源在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本做序及相关诗文记录,参以清人旁证,尤其孙殿起在《贩书偶记》中“《海国图志》五十卷,附图一卷,邵阳魏源撰,道光二十二年刊木活字本”的记载,将该书成书时间从1844年前推到1842年。(5)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魏源史学研究之二》,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18—119页。郭实腊的评论似乎支持这项早已被学界淘汰了的陈说。
但仔细考察则不然。其一,上文只是就一般的了解提到该书的出版,并未带有考证的目的,对早期刊本信息不明是极有可能的。其二,上文提到其刊本“疑为金属活字印刷,其外观与通常中国人的书很不一样”,与孙殿起在《贩书偶记》所记1842年五十五卷本为木活字本不同,后者正是“通常中国人的书”外观。因此《中国丛报》所说的1844年的刊本极有可能是1842年五十卷本的再版。洪九来根据版本目录文献所载和自己所见,列出了《海国图志》的先后19个版本,其中最早的当属1842年木活字刊本和1844年古微堂聚珍本(20册)。上文所提版本显然不是1844年古微堂聚珍本,因为它是八开本,12册。其三,进一步的佐证来自威妥玛译介《海国图志·日本》的序言:“以下作品被翻译的章节包括60卷,比1842年出版的第一版增加了十卷。”(6)Preface of Japan,A Chapter from the Hai Kuoh Tu Chi海国图志,or Illustrated Notice of Countries Beyond the Sea.Translated by Thomas Francis Wade, Assistant Chinese Secretary, Hongkong: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1850.在介绍“《武备志》摘录之二”时,特别指出“这项内容没有出现在海国图志第一版中”,(7)Translated by Thomas Francis Wade,Assistant Chinese Secretary,Japan:A Chapter from the Hai Kuoh Tu Chi海国图志,or Illustrated Notice of Countries Beyond the Sea.Hongkong: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1850(以下简称“译文”),p.19.其原文“又曰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短水草塞罅漏而已,费工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其船底平不能破浪……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竖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见[清]魏源:《海国图志》,古微堂,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以下简称“原文”),第7页。也即再次明确他看的是第60卷本《海国图志》,也为《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首刊于1842年提供了新的证据。
郭实腊在文章中分卷介绍了《海国图志》的内容,夹杂了他的评论,并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介绍书籍的成文基础时,充分关注到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所搜集的与外国相关的资料,故在通篇基本上撇开魏源,主要谈林则徐的眼界和认识水平。郭实腊对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起因充满着偏见,在肯定林则徐才华的同时,认为他在禁烟的过程中“表现出卑鄙、残忍、无情、固执和不懂外交首要原则,将他的国家推向一场鲁莽的战争”。这一偏见在涉及海防内容的介绍时突出地反映出来。
首先,他看到了该书在中国书籍编纂史上的开创性地位,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同类著作与此相当”,称这是一部“关于外国事务的文摘,政治、历史、统计数据的、宗教等等”,并简单提及其所引用的资料;也没有忽略魏源编著该书的主旨:师夷长技以制夷。(8)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423页。这一评价与当前我国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海国图志》开创晚清典志体史书新局面,形成了以“综合体”编纂典志体史书的新思路。(9)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舒习龙:《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62页。
文章认为该书值得肯定的内容有:“越南、暹罗和缅甸的地理报告杂集里有很多有趣的描述,各种各样关于这些国家的评论是我们以前从未在其他书中见到的,可从其中摘录。如果有人想知道过去千百年来中国与南亚这些国家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感想,这部分内容很有优势”“对中印交往的历史的介绍提供了很多新知识”“婆罗洲在6、7世纪即向中国进贡。对这个大岛早已进入较高文明的假设证据,看起来是有史实依据的”“第12卷书日本是原始收藏,内容丰富,我们的出版者对此所知甚少”“他引用了一些记录证明基督教,或该国的信条(称作大秦和弗林之类)进入中国很早”“考虑到钦差大臣工作的繁杂,他仍愿意在业余时间处理这么多完全与自己的工作无关的事情,我们必须敬佩他的勤奋。他的政治主张不成体系……为了推进他国家的发展……十分值得称赞;但同时反复灌输对发明家的一贯嫉恨,比讥讽更甚”“最早由佛教徒传授的古代地理方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10)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424、425、427、428页。这些认识体现出当时的西人对历史上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知识贫乏,所见之处多是新知,故而感觉有趣。
相比之下,文中对作品的批评甚至是嘲讽更多。在评论书中关于海防的建议时,郭实腊尖锐的指出:“问题在于,如何去获得——我们将它交给高级官员去解决,他们会发现这很难,就是林的建议也不像纸上看起来那么可行。这一章紧跟着的一章是描述中国应该发动战争。我们更应该喜欢维持和平的文章,很遗憾,作者费了很大力气将大部分章节用来讲述不可实现的‘乌托邦’,那里的人们明智到不需要以剑来解决纷争。”这显示出对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存在偏见的郭实腊完全不谙魏源以《筹海篇》为总纲,痛斥投降派的谬论、总结御侮抗敌策略的宗旨。魏源首先从议守、议战与议款三个方面总结御侮抗敌的纲领,尤其强调了“守”在战争中的重要性。(11)张爱芳:《论魏源<海国图志>的编纂特点》,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57页。其宗旨在御侮图强,而非该郭实腊所说的好战。
在介绍书中的地图时,他写道:“整本书是模仿我们制作的地图,然后是最拙劣的蒙古帝国全图——忽必烈汗统治时期的,中国海岸轮廓,最后是世界古代地图——因为这是一千多年前画的。”关于马尼拉和其时被荷、英占领的印度尼西亚群岛,批评作者“并不准确地熟悉。如果他咨询一位福建的普通水手,他应该能够防止混淆名字。”其实,五十卷本《海国图志》所收录的地图包括沿海全图1幅(选自陈伦炯《海国见闻录》),历史沿革地图9幅(其中“元经世大典地理图”选自《永乐大典》),东西两半球图各1幅,亚细亚洲、利未亚州、欧罗巴洲、墨利加洲图各1幅,世界各国图则有日本、安南、英吉利、俄罗斯、弥利坚等共7幅,另附图里琛《异域录》中俄罗斯地图1幅。历史沿革图外诸图多受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万国全图》、南怀仁和蒋友仁所绘的《坤舆全图》等所绘世界地图的影响。这是郭实腊所批评的“模仿”的理由,被认为“拙劣”是指《永乐大典》中的元朝地图,而将世界地图揶揄为“世界古代地图”显然过于夸张。此外,相较于西人殖民活动的开展,五十卷本《海国图志》中东南亚地图的“不准确”是显然的。实际上,百卷本《海国图志》及时补充了最新的地图学成就,其世界地图部分临摹“香港英夷公司所呈《大宪图》”。(12)钮仲勋:《<海国图志>对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贡献》,载《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郭实腊注意到有不少于6卷书介绍印度,编排不当,充满错误,大部分来自外国人的记载,全部是讲罂粟这一破坏性的植物。关于亚洲土耳其的记载则非常贫乏。他指出林则徐对阿拉伯和波斯没有正确的认识,嘲讽道:“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属于西印度。我们也不想被告知,印度是他们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西部边疆的介绍,在谈到阿富汗、喀什米尔和叶尔羌(莎车)时,由于“疏于调查”,里面“充满了想象的内容”。(13)吴承志也指出其错误“……以素丹为西印度,哈里发为阿富汗,木乃奚为介碱海及里海之间,地形俱不合。又富浪,天方所在,仅具于图,不著于篇,失罗子、兀林、乞里弯,并图亦不具,阅者茫然”。见吴承志:《读<海国图志·元代北方疆域考>》,转引自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魏源史学研究之二》,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28页。这段评论显示出东西方地理称谓的差异性,作者的先入为主是显然的;而当其批评魏源对土耳其、中国西部边疆知识的“贫乏”“疏于调查”时,所依赖的知识则是英国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殖民活动中形成的。
在介绍欧洲、非洲部分时,颇多不满:1.林则徐称非洲为利比亚(Libya),“所知不比一位西方学生多”,混淆古老的迦太基为北非伊斯兰教地区。2.对书中详述了奴隶贸易以及当地王公的地位表示不解,对其所列举的热带国家、河流以及风俗,表示不能证实,也不能赞同。文中“提到阿基米德和一些刚去世的大人物,非常有趣”。3.第24卷欧洲部分“整册书妙语连珠,仍有许多谬论,大多是人为的”,将德意志及其属国完全搞混了,将该国的公爵、王子和无数的统治者分为25个区或像蒙古一样的部落。4.没有写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5.第31和32卷是丹麦、瑞士和普鲁士,最后一个国家被和他的公国及分散的各省混淆在一起。6.作为附录,介绍了北土耳其,错漏百出。7.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资源、贸易、殖民地等有公正的介绍,却“间或有些嫉妒的评论”,讽刺编者知识陈旧,“像中世纪的政治家一样对他们讲论”。8.对俄罗斯的介绍显示出编者不熟悉该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影响。
这些批评不无道理,联系到五十卷本《海国图志》相关内容的资料来源,非洲部分主要来源于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以及由清人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整理的《海录》,王大海《海岛逸志》等作品,其中因认识模糊而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在名称上,《四洲志》原本将非洲(Africa)译为“阿未利加洲”,这是比较贴近的;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改写作“利未加洲”和“利未亚洲”。郭实腊以为是将“利比亚”一国来称谓整个非洲,显然是误会了。欧洲部分主要来源于林则徐组织翻译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些内容的客观性得到了认可,而涉及普鲁士、北土耳其(即土耳其欧洲部分)和俄罗斯的介绍则多有批评。原文中《俄罗斯纪要》,是根据所翻译编辑《澳门新闻纸》中的内容,并加上林则徐的按语和评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所编译各国地理方位出现紊乱、各国历史事件产生讹误,也是不争的事实。(14)[清]林则徐著,张曼评注:《四洲志》,《<四洲志>评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至于介绍美里哥(美洲)和美利坚,“都转录自汉文出版物,毫无趣味,缺少关于这一伟大共和国的确切知识”。而对南美的介绍多有疏漏,充分注意了矿产资源。关于南美洲通往南极的海域,文章惊讶于编者用宝贵的篇幅来讲述“海豹和鲸鱼之类夏天偶尔进入这片海域嬉戏”。这里所说的“汉文出版物”主要指郭实腊本人编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他所倡议成立的“益智会”旗下的汉译本西学作品。显然,在郭实腊看来,这些摘录自时人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本身并无瑕疵,但林则徐对内容的选择令其感到困惑。
他认为第43卷对世界各地宗教的介绍简单又不正确。第47、48、49卷关于西方政治、辩论、理论和报纸的介绍看不出有什么可供中国借鉴的伟大思想,“整部作品包含的不过是夷人性格的描述”“尽管地理学是最有趣的部分,但仍有历史、神话和错误的内容大量占据篇幅”。但最后作者表示,尽管该书错漏百出,仍很高兴的看到“林这么一位杰出的人已参与讨论外国的事情。他的榜样已影响了很多同僚,读者会高兴地听说,很多满族高官开始学习地理学。这是一个更好事情的开端,尽管开头并不起眼”(15)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424—428页。。郭实腊将书中的功过是非全部指向林则徐,因魏源的编纂补充工作比例尚小,故被忽略了。
上述评论中充满着郭实腊作为最早创办中文刊物的在华西人的骄傲和自负,但他显然发现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联系到第二版《海国图志》对他的作品《万国地理全集》的辑录,他的上述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威妥玛译介《海国图志·日本》
威妥玛(1818—1895),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官。汉学方面,他以威妥玛拼音而著称,更是英国汉语译员计划的实际主持者。1867年,相继编写出版了诸如《语言自迩集》《文件自迩集》《寻津录》《登瀛篇》等一系列汉学教材。《海国图志·日本》的译介在1850年出版,当时他正担任港督兼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助理汉文秘书。全文38页,不足2万字,为一薄薄的小册子,以英文书写,有时为表述方便而插入个别汉语词汇。全书分序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其中序言6页,主要介绍了文章写作的缘起,对《海国图志》一书及其作者魏源的简单介绍,并整体性地谈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若干问题;正文是对《海国图志·日本》(16)即《海国图志》卷12,《东南洋》,“海岛国五·日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十卷刊本。可知原本1842年五十卷本中第十二卷是日本,至扩充为六十卷后,后版第十二卷扩充为“东南洋”,而“日本”只是其中的第五部分。的翻译,共32页,以现代学术论文的形式安排了脚注,用以说明资料来源或需要补充和拓展、订正或存疑等具有联系性的相关内容。脚注内容丰富,充满了学术性,从其中对汉语字形的关注、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名物制度极尽其详的介绍以及对相关中文典籍的溯源和对照来看,该文既是一本翻译学术作品,又可作为同时期西方汉语学习者的教程,具有显著的汉学普及功能。
该文的源起,正是由于郭实腊的《海国图志》书评。由于看到评论中提到的“第12卷书日本是原始编纂,内容丰富,我们的出版者对此所知甚少”,威妥玛特地将该部分找来进行译介。与郭实腊不同的是,他所看到的《海国图志》是刊刻于1847年的六十卷本,他在序言中清楚地说:“以下被翻译的章节所属作品包括六十卷,有十卷被增加到1842年发表的第一版里。”
与郭实腊相同的是,他对《海国图志》的学术价值也颇不以为然,甚至对前者所肯定的《日本》这一卷也持否定看法:“整本书的撰写说明中国人完全不适合完成这一编辑工作。他没有自己的评论或信息,而是满足于从《明史》、《武备志》、俞正燮《癸巳类藁》中各章节的历史编纂、陈伦烔《海国闻见录》对某些国家的某些方面的说明、南怀仁《坤舆图说》中的世界地理、由当朝或皇帝授权编写的《皇清通考四裔门》《澳门纪略》《万国地理全图集》和《蓴乡赘笔》(17)《蓴乡赘笔》又作《莼乡赘笔》,清人董含著。但魏源《海国图志》中误作《蓴卿赘笔》(目前尚未在别处看到这种写法),但威妥玛竟能按照《莼乡赘笔》来翻译:SHUN-HIANG CHUI-PIH,应与其中文老师的知识背景有关。。对明史的引用占据了文章的近一半,但我们从中几乎得不到关于日本的知识。这几乎都是摘录上述历史书中关于‘倭夷’在1547—1586年间对中国和朝鲜侵略时期的海盗谱系。” 他承认该卷是原始编纂,但“令人担心的是其中包含的有用知识,不足以应付英国人带来的麻烦,因为全书中很少内容是没有被欧洲学者更新和更完整叙述的”。
根据威妥玛对日本这部分的解读,他关注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旨使作品尤其关注日本在明朝时期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事迹——这是为了提醒国人,疏于军事知识(威妥玛称目前仍然如此)使中国内陆曾被少数“夷人”占领,从而祸国殃民。进一步评论道:“最近的经历显示,中国人在三百年里不管在陆军还是海军方面都无进步。政府重文轻武,使得传统的武术知识不会在学生中传习。从1368年明朝建立时起,中国的战争已经主要是防御性的……对弓箭手的检阅继续进行,仿佛他们和炮兵训练一样都是保卫国家的主要力量。”也读出了作品中的天朝心态:“这些部分的后面声称中国最先发明了船只和航海,并由于允许日本人对这些技术的改良,从而成为中国的阴险敌人。”
威妥玛在序言部分简单介绍了所译介内容,关注到一些过时的信息:“第7部分某种程度上是对第5段核心内容的重整,在记载朝鲜、日本和中国南部的相关地位上存在严重的概念错误。它注意到每年从日本进口2 500吨铜以供应四省的铸币,这是本朝初期的情况。根据最近的一本统计著作(参见第27页的注释),这个数字只有上述的不足四分之一。”也注意到了魏源潜在的反对基督教的态度:“第8部分摘自《澳门纪略》第10部分,宣扬日本人对天主教和它的传播者葡萄牙人的极端敌意;根据第9部分,他们被排斥是因为他们的信条,但却是在信仰新教的荷兰人的帮助下。书中好几处谈论信仰基督教的恶果。”此外,对魏源认为可资借鉴的日本以高薪养廉的做法予以肯定,但感慨于“这一评论的智慧在120年前做出,至今尚未传到清朝:中国官吏的薪俸长期以来与他的支出不成比例;上级的无限需索,这关系到他的职位是否能坐稳”(18)Preface of Japan,A Chapter from the Hai Kuoh Tu Chi海国图志,or Illustrated Notice of Countries Beyond the Sea.Translated by Thomas Francis Wade,Assistant Chinese Secretary,Hongkong: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1850.。
威妥玛在翻译这章内容时,与前文作者不同,由于专注于一部分的内容,并且长期研习中文经典和语言文字,他充分注意到魏源所辑录的各类作品原文。在正文中,以所辑录作品名称将内容分为10节。而对于所辑录作品,或在正文小标题下的括号内加以说明,或通过注释来进行解释。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对《海国图志》所辑录作品进行介绍
一种情况是在正文小标题下的括号内,对《海国图志》所辑录作品做简短介绍。如:“《武备志》摘录……该书有300多卷,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的战术和兵法。我有一小本,1843年出版,显然是宏大卷集中的一个缩略本,其中并未记录下列节录内容,看来是出自当代史学家之手。”《武备志》成书于1621年,是明代茅元仪的作品。书中阐发了明朝大陆国家意识下的武备思想,认为明帝国之大患在北虏,次为女真诸部,其次为日本,又次为西番,再次为海外诸国,更次为安南,最次为朝鲜。(19)赵凤翔、关增建:《17—18世纪中日陆海观念研究——以中日两部兵书<武备志>和<海国兵谈>为例》,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4页。魏源此处辑录的主要是其中的日本考。从目前的版本研究可知,《武备志》的确有道光木活字刊本,但目前尚未发现威妥玛所见的这种缩略本。(20)乔娜:《<武备志>版本流传考》,载《清史论丛》2016年第1期,第298页。
“辑录自《万国地理全图集》……这部分在第一个版本中没有,也不确定作者何时写的。作者是康熙年间人,下面和最后一部分章节被选录。”威妥玛这里说作者是康熙年间人,令人费解。魏源并未指明该书作者,学界目前基本认定这实际上就是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集》。以往学界认为该书是郭实腊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地理类文章的汇集,最近据庄钦永考证,这实际上是郭实腊的另一部著述,由香港福汉会刊行。初刻本出版于1844年6月或之前,修补本则大概是在1848年上半年,两者相隔约4年。经过对读,他确认魏源《海国图志》中所收录《万国地理全图集》正是来源于郭实腊的汉文世界地理著述《万国地理全集》。(21)庄钦永:《有关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若干考证》,载《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7年第2期,第17—43页。
“辑录自《蒪卿赘笔》(SHUN-HIANG CHUI-PIH)——乡,村庄,印刷为卿King,是官名,《海国图志》的第一、二版本中都有。莼(蒪)是一种水草,据说只在江苏某一地有,因而名之为‘莼乡’。《莼乡赘笔》是江苏华亭人董含的作品,作者在乾隆年间(1735—1795,此处应为1736—1795)名噪一时。全文收于同时期杂集《说铃》,查考原文后发现《海国图志》中辑录的部分有缺憾。”(22)原文页六、七、九、十二;译文p.15、19、24、29、31。这段介绍符合目前学界的相关认知,由于《说铃》这一杂集总的学术价值不高,《蒪卿赘笔》(《莼乡赘笔》)也较少为学术界所关注。
另一种做法是通过页下注对《海国图志》所辑录作品进行介绍。如: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记录在外国的见闻,1730年面世。作者年轻时陪同他的父亲几次出海远航,他父亲看来是一位海军军官,之后他本人也担当了重要的海防官职。”陈伦炯, 福建同安人, 其父陈昂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随施琅平定台湾, 之后“琅又使搜捕余党, 出入东、西洋五年”, 官至广东副都统。陈氏少从其父, 泛舟海上, 熟闻海道, 及年长, 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及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等职。《海国闻见录》初刊行于雍正八年(1730)。(23)原文页八,译文,p.21;王耀:《清代<海国闻见录>海图图系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第112页。威妥玛这里的说明大致无误。
“南怀仁《坤舆图说》”——“南怀仁是欧洲人,他的著作在清初被编纂。”(24)原文页九,译文,p.25。《坤舆图说》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撰写,为解说其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而作。该书刊于康熙甲寅(1674),分上下二卷。上卷介绍天文及自然地理知识,下卷为各大洲各国风土人情名胜等。(25)崔广社:《<四库全书总目·坤舆图说>提要补说》,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年第1期,第53—54页。
对魏源所辑录的作品做进一步地追索显示了威妥玛的汉学家特质,不满足于简单将字面信息翻译清楚,而是做进一步地文献追索。
(二)以西文纪年来对应中文纪年
关于中文纪年和西文纪年的互参,目前所知最早应是麦都思1829年所著《东西史记和合》。1832 年马儒翰编写的《英华通书》(TheAnglo-ChineseKalendarandRegister)及《通书附册》(ACompaniontotheAnglo-ChineseKalendar)(26)The Canton Register, 1832, Vol.5, No.9.,专门对东西方纪年进行整理和对应。威妥玛对《海国图志·日本》的中文纪年也注意了与西历的对应,但和今天的记录相比显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从威妥玛在正文和注释中涉及的一些纪年的转换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错误。正文中,如:“洪武二年(1368,按:应为1369)遣使颁诏书,且诘之。二十年(1386)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永乐初(1401,按:应为1403),始通表贡……十七年(1418,按:应为1420),辽东总兵官刘江大破之于望海堝……正统四年、八年(1459—1463,按:应为1439—1443),倭船四十艘,连寇台州、海宁……嘉靖二十七年(1547,按:应为1548),巡抚朱纨乃严为申禁。”(27)原文页一至二,译文,pp.2-4。这里出现了多处东西纪年对应的误差。
“俞正燮《癸巳类稿》摘录。癸巳年(1713?)我找不到这本书和作者的信息。他大概是本朝作者,但‘癸巳年’也许是1713、1733或1833年。很自然地设想,辑录的内容按照作品所属年代的顺序,既然在它后面的看来是1730年,认为其在1713年应当不错,亦即康熙五十二年。”(28)原文页七,译文,p.19。俞正燮(1775—1840)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富有思想的朴学家,《癸巳类稿》是成书于道光十三年(1833),收文249篇,其卷8、卷9为边疆地理类著述。(29)于石:《俞正燮著作结集考辨》,载《古籍研究》2004年第2期,第259页;黄成金:《俞正燮的史学》,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2页。这里威妥玛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注释中,如:“咸亨,唐高宗部分统治时间,在他统治时期年号有13个。基督教在这个时期应该已经由聂斯脱里派传到了中国,即654—678年。”(30)原文页一,译文,p.1。(按:李治在位时间应为650—683)以中西文纪年对照来介绍历史知识,这在今天历史学界几成共识,尤其是涉及到古代史、不同国家的历史情况时。这体现了日后成为汉学家的威妥玛对学术规范性的关注及东西方比较眼光的初具。
在技术更新的新形势下,数字地形测图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形测图,在城市测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分析,明确其是在传统的地形测图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实现对地形测图技术的更新。从某种角度而言,将数字地形测图应用到城市测量中,能够使城市各区域的地形地貌有效地展现出来,为日后城市的科学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本文在研究中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综合分析,重点阐述了其在城市测量中的应用。
三、威妥玛译文注释的汉学普及功能
威妥玛对《海国图志·日本》的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汉学普及。其时他担任香港总督文翰的助理汉文参赞,正在孜孜以求地学习中文,并因当时英国在华人员急于了解中国情况以及汉语人才的缺乏而积极传播汉学知识。故此,威妥玛在译文的正文基本采取意译。如“大治甲兵,缮舟舰”,威妥玛译为:整饬好陆上军队,准备好他的舰队。(31)原文页五,译文,p.13。“朝鲜居天地之艮方”,威妥玛将其译为“朝鲜在中国的东北方”,在注释中解释了“‘天地’,应当也指中华帝国”(32)原文页六,译文,p.21。。
只有少量涉及中国官职、书籍、计量单位之类的词汇会用拼音直译。更多的情况下,他虽然对中文中的历史事物采取了意译的方式,仍在注释中注明中文原文及其读音,再配合相关解释。有些解释追溯到中国古老的经典和文集,有些则辅以威妥玛个人的学术见解。其注释少则一两行,多则十余行,颇显用功之勤。应当说,正文的翻译是极少存在错误的,这对一位学习中文只有八年的英国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注释就另当别论了,虽然其中涉及的名物制度对今天的中国人也是一项挑战。仔细辨别,就会发现威妥玛在注释中存在一定的错误,既有读音方面的,又有释义方面的;有的错误是时代的原因,有的则源于威妥玛的跨文化隔阂和汉学功力。以下就详细介绍这些注释的内容。
(一)对中国名物制度或日本习俗的简单阐释
倭(马礼逊《华英字典》第11734页)的解释,日本人;当读wei时,指外表柔顺。
畿(马礼逊《华英字典》第5274页),一般指皇帝的统治区域,方圆1 000里,见《诗经》之《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33)原文:“日本,古倭奴国”,见页一;译文,p.1。里,旧制计量单位。
世宗,君主死后的庙号,其统治年号为嘉靖。(34)原文:“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见页二;译文,p.4。
胡惟庸,是明朝刚建立时的一位引人探究的宰相,以煽动叛乱罪被夺官,约在1379年被杀头。(35)原文:“会胡惟庸谋逆,借日本为助”,见页一;译文,p.2。
巡按(马礼逊《华英字典》第9048、2837页),派往各地巡回复核特定案件的御史。(36)原文:“三十六年十月初……宗宪……即命指挥夏正往……命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指挥,军官,相当于上校或旅长。见页四;译文p.4。
江夏侯,是江夏的侯爵;信国公即信国公爵。(37)原文:“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信国公汤和往浙江”,见页一;译文,p.2。
郊庙,即坛(马礼逊《华英字典》第5587、7592页)。郊是城外的荒地。(38)原文:“帝为告谢郊庙”,页五;译文,p.12。
邀追,1.“邀”如上文“邀击”;2.不是通常所谓的“邀请”,而是“诱使并等待”。冈萨维斯(Gonsalves)“有‘强邀而杀之’”,接下来引用《佩文韵府》《左传》《汉书》《兵书》进行论证并注明汉字字形。(39)“邀追”(1)“邀”如上文“邀击”(2)邀击,不是通常所谓的“邀请”,而是“诱使并等待”。冈萨维斯Gonsalves“有‘强邀而杀之’”(3)将邀而杀之esperous-o e matou-o.“In the Shang Mang,[His disciple]sent several persons to wait for him by the way”,but the 《佩文韵府》, 第17卷,shews that it is a synonym of yau要(4)要 in this,as alson in three other passages quoted from the Tso Chuen《左传》,Han-shu《汉书》and Ping-shu《兵书》,in which it is either linked with kih 击,or divided simply by an(5)rh而,the power of which particle to mean ut as well as et,is worthy of notice, as is also the translation from hope to expectation, of which the Portuguese esperar is likewise capable.From the latter meaning of the word is of course derived that employed in the text.(译文,p.17)“官皆世官世禄,遵汉制,以刺史千石为名,……衔官者乡保也,岁给赡养五十金”——“汉制”,在《佩文韵府》第一部分第10章;“石”[注明汉字字形]的意思:1.石头,引用了一部关于汉朝的著作如下:“武帝任命‘刺史’分掌各地狱讼,章帝更改其名为‘牧’”,他的级别是200石[古代读shi]谷。“五十金”[金,注明汉字字形],此处没有确定的数目的含义。(40)原文:“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为吾军之邀追”,页七;译文,p.17。石,旧制计量单位。
罗盘,以《易经》上的八个符号指示方向。(41)原文:“其南隔一洋,日本国属之对马岛,顺风一夜可抵。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者”,页十,译文,p.26。
弥耶谷,即天皇,是博学的皇帝,绝类精神和世俗的事务;将军是军事首长,表面上是皇帝的副手或军官。参见《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Vol.IX.p.305.(42)原文:“国王居长崎之东北,陆程近一月,地名弥耶谷,译曰京”,页八;译文,p.21。
吾妻镜,我妻子的镜子。此名寓意作者意在记录家庭琐事,无异于外国事情。(43)原文:“然君长授受次序,仅见于日本僧tian然所纪,有《吾妻镜》一书”,页九;译文,p.25。
崇德,是清朝第一位君主父亲统治时期,1644年篡夺明朝政权。(44)原文:“崇德四年,日本岛主令平智连……”,页十;译文,p.26。
(士农工商)这四类人民在中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排除了优伶、贱民、奴仆和皂吏至三代。(45)原文:“士民共计二千万丁,至于士农匠商,种种过人”,页十一;译文,p.30。
监国,当明朝最后一位君主1643年上吊而死,皇室中的一位朱姓被冠以鲁王头衔摄政。他往福建,那时满族入侵者尚未到达,在顺治七或八年在那里被杀。(46)原文:“鲁监国航海时,其臣阮进欲乞师日本”,页十二;译文,p.31。
由上可见,威妥玛对中国名物制度的解释一方面来自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国一览》和同时期的其他汉学家的解释;另一方面来自对中国的传统经典(如《易经》)、工具书(如《佩文韵府》)和史书(如《左传》)的释读,显示了其汉学根基非浅。而其对“对马岛”位置的解释,则完全站在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将日本地名转为英文再对应到中文的阐释中。
(二)对原文相关事件的补充和拓展
“洪武二年,遣使颁诏书”——“使”,这只是《明史》的一个摘要,原文对前往日本的使团记载有趣。当时日本国王梁怀由于怨恨之前元朝蒙古人施加的侮辱后,打算处死中国使者。此处威妥玛进一步阅读《明史》以补充说明。
“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福建16城驻防,浙江57城。前者有军队15 000人,分驻四处海防……。这里威妥玛参阅的资料是《明史》和卫三畏的《大中国志》(MiddleKingdom)原文第209页的“人口统计表”。
“永乐初,始通表贡。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谕其王捕之。王发兵捕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献。”——皇帝将他们释放给使团根据日本法律处理。他在回程将他们带至宁波,将其释放。参见《明史》第322章。
“自是频入贡,亦频献所获海寇,且表言岛上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这是1416年的事,当时新抓到了一些海寇。皇帝力排众议,没有立即将他们杀头……威妥玛这里并未给出资料来源。
“后又夺纨官,罗织其擅杀罪,纨自杀”——《防海备览》……朱纨的记录驳斥了对他的指控,禁令的存在使得这些被抓获的人无法逃脱海盗的指控,如果他们遵守法律就不会被抓;他坚持他们有罪应被杀头。他失败了,成了阴谋的牺牲品,如文本所示。朱纨的事迹有众多史料可循,对朱纨之死也有众多说法。此处威妥玛仅进一步引用了《防海备览》的记录。该书是清人薛传源所撰,共十卷,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和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
“索之急,则以危言吓将吏。俾之剿,兵将出,又以好言绐之走。”——自“将吏”至“兵将出”这部分不见于《明史》。我相信应当是“告诉他们军队将来消灭他们以恐吓他们”,或(如《明史》所云)“告之以好言‘吾将以准时偿还’”。这里显示出威妥玛亲自核对了《明史》原文,并按照其理解予以阐释。
“若直倭丧其资”——“资”(见《华英字典》第11236页),意思是财富、钱等,但参考《防海备览》,上述所引,说明他们要为国家处理的货物,被没收后回国无法交代。并且不能回到日本,在岛上驻扎,怒而变身海盗,并为弥补遭中国人欺骗带来的损失。威妥玛参照《防海备览》交代了倭寇的一个来源。
“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游击,在当朝是军官,一位满族将军。沈惟敬与日本有利益关系,已计划让皇帝将一位公主嫁给日本国王……。沈惟敬作为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中对日和谈首席代表,在当时身陷“和亲”传闻,一度遭到褫官处分。对此,兵部尚书石星上奏称其未涉此事,指出这是反对议和的朝中诸臣及朝鲜君臣的有意陷害,石星的意见最终获得了明神宗的允准,沈惟敬后来继续以原来的“游击”职衔奔走于东亚三国。(47)郑洁西、陈曙鹏:《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92页。威妥玛显然难以从一两则资料洞悉其真相。
“国饶铜,我朝鼓铸所资自滇铜而外,兼市洋铜”——在清朝成文法的增订版(1826年印刷)中,指出云南必须每年送5 836 220斤铜到北京;贵州每年送4 391 914斤白铅和473 238斤黑铅;湖南250 000斤黑铅,用于铸币。……一旦从日本进口铜,数量应当已经足够需要了。……据说铸币此前就很少了,现在的实质价值低于标准的百分之六七十。1846年,朱嶟强烈反对弛禁鸦片者,上了一篇长奏折论述存储铜钱以保值……(48)原文页一、二、六、十;译文,pp.2、3、4、5、15、27-28。斤,旧制计量单位。威妥玛此前曾翻译过朱嶟反对鸦片贸易的一个奏折,从中了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管理和货币体系。(49)Chinese currency and revenue,Vol.XVI,June,1847,No.6,pp.273-291,见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6卷,第277—297页。这段阐释显然是建立在对这份奏折翻译的基础上。
威妥玛对《海国图志·日本》所记录的相关事件的补充和拓展显示了威妥玛对中国明以来直至清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知识的把握。其内容涉及对日关系、海防、官场斗争和腐败问题、人口统计、铸币数量及铜的进口等方面,完全没有停留于对原文的简单翻译,这显示了威妥玛的汉学研究更多是为了解清朝的情报。他在翻译该书的同年还出版了《中华帝国政府及其状况》(NoteontheConditionandGovernmentoftheChineseEmpirein1849)小册子,主要依据当时发行的《京报》来介绍中国的情况,这为上述其对中国各类情况的介绍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基础,(50)Thomas Francis Wade,Note on the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49,Hongkong: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1850.也为其日后从日汉学生的培养以及参与中英交涉问题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三)注释中存疑之处
一类是威妥玛认为原文中存在错误的情况。如:
“故使我军士或愚而杀贼,或疑而杀良。”——“这里似乎是印刷错误”。这里威妥玛限于中文水平感觉文义不通,故做此论。
“或附蓬而飞跃,即雷震而风靡矣。”——“‘附蓬’(《华英字典》第2405、8730页),附,靠近;蓬,船上用于遮阳避雨的篷子;根据老师们的高见,应是别的写法[按:即“篷”]。蓬,是指一艘船,该文本应是写错了。”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威妥玛是在中文教师的协助下解读相关内容的。此处认识大概不差,但古文中通假字的使用非常普遍,威妥玛和他中文老师似乎多虑了。
“今有六十六州,各有国主。”——“怀疑印刷错误。”
“李言恭撰《日本纪国》书土俗颇详……若日本所属之对马岛,与朝鲜仅隔一洋,顺风一宿可抵”——“上述是对相关段落的自由翻译,这对一个外国地理学家造成某些困惑……错误由于从朝鲜南行到日本群岛的模糊概念……”(51)原文页六、七、九、十;译文,p.18、18、24、26。威妥玛对中国地理知识的准确性表示了怀疑。
另一类是威妥玛受限于当时的汉学水平,形成的错误解释。如:
“巡抚御史周亮,闽产也。”威妥玛翻译的时候去掉了“巡抚”二字,应是不理解当时“御史”是“巡抚”的加衔。“御史,从其头衔可见,负责特定区域的监察工作。见马礼逊《中国一瞥》(ViewofChina, 90页)巡使和巡抚的区别,看不出来。”这说明威妥玛并不了解在明朝属于临时性差使的“巡抚御史”在清代被沿用之后,逐渐演变为固定官职。
“先是国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都司”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少校,或海军中的指挥。“巡视”和“副使”是有军衔的平民。“巡视副使”即“巡视海道副使”,全称“提刑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这里威妥玛错误地认为是两个官职,另外对这一职务定位为“有军衔的平民”也不对,其官职在都司之上。(52)原文页二,译文,p.5。
“荷兰据有台湾,置揆一王,亦不复东”——“东”,原文并未充分解释是否台湾岛以东,或者,日本岛以东。这显示出作者可能不知道两国之间的相对位置。(53)原文页七,译文,p.20。这里,显示出威妥玛没有古汉语“名为动用”的概念;其称台湾和日本为两个国家,虽然知道台湾在清朝版图内。
“郑芝龙者,闽人也”——“郑芝龙”,郑克塽、郑成功(以国姓爷著称)的爷爷。他死于北京的监狱。荷兰人在30年的统治后,于1662年被驱逐,台湾岛于1683年被交到中国政府手中。[见《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Vol.II.P.415](54)原文页七,译文,p.20。威妥玛显然把郑氏的辈分搞错了,把郑成功和郑克塽的父子关系错当成兄弟。
“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劳动者“沮溺”(《华英字典》第10806、8003页),长沮和桀溺是两个有美德和能力的人,厌恶当时的恶政,隐居到乡村。他们在耕地的时候遇到路过的孔夫子,当后者问他渡口时,给了他一个粗鲁的答复。他们的粗鲁如此成为典故,他们的名字被连写在文本中,用来指仅从事耕耘稼穑者。(55)原文页六,译文,p.18。威妥玛这里对隐士的解释不全面,没能解读出隐士对当代政治的消极批判。也许是受限于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的理解。
“阮抵日本。其国初闻有藏经往,喜甚,及闻湛微名,大惊。曰:‘此僧复来,则速死耳。’因不受敕,护经而归。”——这句在董含的《说铃》里没有。威妥玛这里混淆了,董含的《莼乡赘笔》收入清人吴震方编纂的文集《说铃》。(56)原文页十二,译文,p.31。
综观威妥玛在注释中存在的各类错误,有的因其自身汉语理解能力的不足,将没有错误的当作有错误的来标记,有的是怀疑原文中存在理解和印刷的错误,从而特地指出来。第一类情况在明朝的官制、徭役、人物身份等解释中可以体现出来,是其汉学知识仍未娴熟的写照;第二类情况在威妥玛比照中英关于日本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较有代表性,显示了其文化优越感,尤其在明知道台湾在清朝版图内却称台湾和日本为两个国家,带有西方的偏见和殖民倾向。
结语
从《海国图志》在西人中的反响来看,至迟于1847年,该书已得到了在华西人的关注,并由此引发西人带有比较视野的评价。总体上,郭实腊对《海国图志》中的西学知识评价较低,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海国图志》所辑录某些作品非最新成果,且存在认识模糊的问题;二是受林则徐最初组织翻译时的译者水平所限,其中出现了错误的转述;第三,郭实腊本人即是当时向中国人提供世界知识者。这些评论也间接引起了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关注,其1850年对《海国图志·日本》的译介延续了相似的认识,但该译本作为一篇汉学读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1.该译本提供了当时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认识程度,其翻译和注释虽有多处错误,但译介也颇为用力,并进一步细化了1847年郭实腊评价中的某些话题。2.译文体现了英国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质疑和阐释,显示了治学的严谨;其中西纪年相对应的做法,虽受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而带有误差,但延续了麦都思以来在华西人鲜明的历史比较的眼光。3.译本为中国版本学界在孤证之下形成的《海国图志》最早版本出现在1842年说提供了又一重要证据,为这个已经沉默了的旧话题提供进一步探讨的可能。
此外,以往学界论及西人对《海国图志》的关注主要在两条史料,其一:《遐迩贯珍》1854年载一文考证《海国图志》所载阿丹国:“《唐书》言大食国本波斯别名,此为谬误,大食即阿腊比阿,为回教本国。稽《文献通考》大食在唐永徽中遣使朝贡,云其国在波斯之西,此言甚合。或又名天方,此择字义佳者以称其国,所传天方教即回回教无疑。《文献通考》又载大食有摩河末通,而智众立为主,即明史所称回教之祖马哈麻德也。”原文是英人艾约瑟考证大食、大秦国号的学术文章,此段文字中,英人艾约瑟对大食的国名进行了考证,认为《海国图志》中的阿丹国即是古代的大食,并且对《唐书》《文献通考》等权威典籍中关于大食的记载进行考证。另清末《申报》所载一文盛赞俄国人好学,并称:“犹忆光绪十三年,江阴缪王主政佑孙,奉命游历彼国,有颗利李甫者,出所译满文通鉴及蒙古各杂说就正,自言将译皇朝《圣武记》,又欲译《海国图志》。”(57)[英]艾约瑟:《大食大秦国考》,载《遐逸贯珍》第十号,1854年;《阅昨日本报纪俄国崇儒事为之引申其说》,载《申报》1896年10月19日。转引自刘勇:《<海国图志>研究》,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8页。这两则史料所涉及西人对《海国图志》的关注较本文所论显然晚出,本文盖可刷新这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