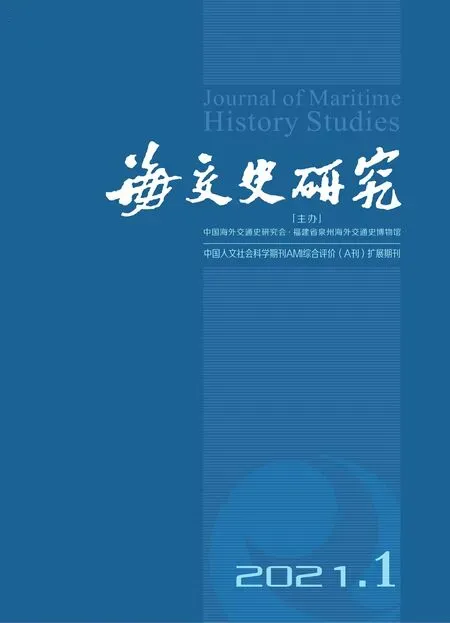区域性的国际交往与东方外交圈的形成*
陈奉林
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相互交往交流的历史,人类的交往也伴随着其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至今仍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交往不同于其他动物交往之处,在于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和物质文明成果可在短期内实现共享,缩短后进者与先进者之间的距离,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性,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变动过程。长期以来,从区域性的国际交往和国家外交活动的角度观察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不多,即便有一些成果也往往由于视野的狭窄与整体思路的缺乏,或者由于对不同民族、国家与文化交往的认识不够,或者由个人兴趣、基础与其他条件所限,不能作出整体性地、连续性地研究。从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崭新形势来看,无论从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不同文明交往与互鉴的角度,都应该推进这一研究,以获得对国家间交往的本质与属性的深层次认识。
一、丝绸之路开启的世界贸易网络
丝绸之路作为联结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的贸易网络,在东方历史上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发展与共生,铸成人类历史的伟大辉煌。它时间悠久,范围广阔,在空间上联结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和非洲,贸易的商品不仅有丝绸和瓷器,还有动物、植物、手工业品与人口,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间的交往是与丝绸之路分不开的,单纯的经济学观点或政治学的观点是无法解释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所涵盖的丰富内容的。对于丝绸之路开启的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已有学者进行过认真研究,曾予以高度评价。日本学者在《欧亚文明与丝绸之路》中这样写道:“它是联结悠久的古代至近代不同文化与风情的东西方世界的交通要道,是众多民族历史上最大而宏伟的古代通道。”(1)[日]児島建次郎、山田勝久、森谷公俊:《ユーラシア文明とシルクロード:ペルシア帝国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謎》,雄山閣,2016年,第174页。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通线,这样的商业贸易与港口城市,才有东西方国家的交流与进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开辟交通贸易的作用功不可没,有人把它看作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动脉”(2)[日]児島建次郎、山田勝久、森谷公俊:《ユーラシア文明とシルクロード:ペルシア帝国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謎》,第174页。。
自汉代起,我国的海上交往已经到达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从事着国家间文明的交流与构建。当时日本列岛小国众多,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3)《汉书》卷28,《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58页。这说明中日之间已经有了国家间正式的交往。无论是国家间的政治交往还是经济交往,对于双方都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双方进行联系的纽带与持久的动力。进入隋唐时期,日本、朝鲜、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频繁,海上贸易网推动着双方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东方海上交通线的开辟,给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僧俗往还带来了极大便利,各国互动影响进一步加深,也把中国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圆仁是日本入唐求法的高僧,在唐朝生活近十年,到过中国南北方许多地方,对中国社会有长期而详细的观察。从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知,在837年入唐的首次航行中,四艘船只载员651人,从博多港出发后遇到了台风,第三船中的140人中仅有20余人生还。遣唐使成员除了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外,还有留学僧、请益僧、翻译、船师、射手、阴阳师、医生、乐师、杂役等。(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在古代,海上航行充满了艰难险阻,可谓九死一生。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文明的交流与构建,创造着人类的历史。
在南亚,自汉代起中国就与印度洋北岸国家建立了海上政治、经济联系,商贸往来与使者往还不断。《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商船已经到达印度次大陆东南海岸的黄支国,带去黄金、杂缯等中国商品,这表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的航线已经开辟。唐宋以来,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天文导航、水文导航及指南针知识的掌握,中国的商船已经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最远可达印度洋和波斯湾沿岸各国。据成书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的阿拉伯作家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载:“中国人也曾航抵波斯湾。……甚至在巴格达城建立之前,中国船已到达了乌波拉。”该书还记载道,中国商船排水量大,远距离航行航行能力强,“应该承认中国人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中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我们认为阿曼人、中国人,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无法考证的民族,都积极地参与了南海沿岸各国间重大的交易活动”(5)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26页。。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材料也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这条航路为后来的航海以及东西方交通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东方国家的古史材料异常丰富。古代阿拉伯作家马斯欧迪在《黄金草原》中这样记载:“(黄巢之乱)以前,中国商船已通达阿曼地区、巴林沿岸地区,乃至澳波位、巴士拉诸港。同时,这些地方的商船也直接通往中国诸港。”(6)《中国印度见闻录》,注释2,第138页。现在有必要加深对东方国家区域性国际交流的认识,尤其对历史上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市场的互动研究。有学者指出:“中国和印度在这两千多年来建立了一种相互来往、相互帮助、相互交融和相互激荡的关系,使得它们成为全世界的两大繁荣、发达的农业强国。一方面,它们的国民总收入大概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和它们开展贸易。中国的丝绸(其中有一部分是印度出产)和印度的棉布长期占领欧洲市场。等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觉醒,意识到要发展本国经济的时候,他们发现国产的粗糙的呢绒无法和进口丝绸、棉布竞争,因而通过种种法令,不允许女人穿丝绸、棉布,甚至不允许使用丝绸、棉布裹尸葬人,以保护本土的毛纺工业。”(7)[印]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3页。人员的往来,商品的交换以及文化的互动给中国和印度社会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著名学者谭中先生把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国家看作是冲破“民族国”藩篱的典范。
我们强调近代以前东方人开辟的航线,是为了把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贸易的整体网络进行观察,重新思考与审视世界历史研究中以近代西方航海和扩张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分析视野。有材料显示,唐末以后中国的船舶技术已经超过了国外,到宋元时期中国海船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印度之间的航线,中外商客往来便利,受到各国商客欢迎。(8)金秋鹏:《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力量的支持,国家力量已经参与到对外交往当中,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才能建造出载重量巨大的商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造船技术进步,以及国家对交流交往交错重要性的认识。唐宋时期留下的许多文献都反映出当时国家对对外交流重视的情况。在看待近代以前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北印度洋贸易网关联的作用上,西方人往往忽视古代东方国家航海及贸易网络的作用,严重低估它的作用,因此也就造成了许多研究上的局限。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东方本土资源与史观,重新研究和评估它的价值。
在北方欧亚大陆交通贸易方面,早在汉代以前东西方就已经建立了联系,正史材料留下许多珍贵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由东方商人开辟的欧亚大陆贸易网络不仅适应了社会本身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都有发展贸易的内在需求。在促进东西方国家联系方面,经济力量是最为持久而强大的力量,没有哪一种力量比它更为持久有力,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中国大量输出的是陶瓷器。(9)[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大航海時代のセラミック·アドベンチャー》,东京:ぎょうせい,1989年,第43页。日本学者铃木治在《欧亚东西交涉史论考》中说:“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交流。”(10)[日]鈴木治:《ユーラシア東西交渉史論攷》,东京:国書刊行会,1974年,第292页。此语可谓通人之言,一语道出丝绸之路的本质特征,也是对丝绸之路属性的根本性认识。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不仅有东方的丝绸、陶瓷、香料等被输出到西方,给那里的社会生活增添了多样性,也有西方的商品输入到东方市场,融入到社会大众生活的许多方面,实现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任何外来文明的引入都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来完成的,丝绸之路无疑是它的载体。明代的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越,必先会通”的卓越思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对待外来文明方面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海陆丝绸之路不仅贯穿了东西欧亚大陆,而且真正发挥了联结南北的功能。(11)[日]平山郁夫監修、長澤和俊執筆:《海のシルクロード:神秘の南海航路》,东京:講談社,2005年,第16页。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东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本学界把丝绸之路分为绿洲之路、横贯中亚的草原之路和经由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南北方贸易网上活跃的不仅是华商,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粟特人、波斯人、叙利亚人。(12)[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講談社,2007年,第69页。
不仅是东方学者重视丝绸之路的影响作用,差不多每个时代都留下影响一时的作品,就是西方也同样有不凡的研究。如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赫德逊写道:“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无论从埃及经海路或是经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的陆路,都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13)[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李申、王遵仲、张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页。无论从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从促进社会变迁方面,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社会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我国学者指出:“汉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14)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1—2页。它像一张巨网,将东方与西方联结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贸易的力量在打造着世界,创造着新的世界历史。在克服了来自自然的、社会的以及技术上的诸多限制之后,人类的文明交往已经向更高文明的层次跃进。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多,不仅丝绸之路沿线各主要城市出现活跃的商品交易,即使是一些穷乡僻壤商品化程度较之过去也有相应的发展。西方商贾为了贸易来到东方,从事玉石、珍珠、犀角、琥珀、玛瑙、香料、药品、兵器、银器、毛织品,以及黑丝、毛毡等各种商品交易。(15)[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6页。自从人类脱离了最初的野蛮与残暴之后,自觉的文明交往已经成为国家关系的主流,虽然也发生战争,但战争已经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了。
对于丝绸之路开启世界贸易网络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因为它给商人带来的不仅是丰厚的商业利润,使他们不顾常常发生海难的巨大风险,从事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更为重要的是使东西方各自在相互交流中获得了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重大变迁。对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认真地探讨过。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不仅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欧亚非三个大陆的道路,同时也强调其规模之大,差不多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与它有关。(16)[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2—3页。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也异常的深刻。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日本始终对外部世界文明抱以巨大的热情与无限的憧憬。我国学者指出:“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17)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前言,第3页。确实,丝绸之路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不同一般,也有别于其他商业贸易与交通,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全方位演进的动态过程,有人把它看作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18)[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3页。这个观察极有力度,是对丝绸之路本质特征透彻考察所得。它有草原之路、绿洲之路与海上之路三大网络,如果把它作为网络来理解的话,决不只是联结东西,从南北的视角来看也是很重要的。(19)[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第65页。多年来丝绸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视,引起研究,除了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外,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也极为密切,它的理念与精神正是当今世界应该发扬光大的。
必须指出,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东西方交流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大众生活,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促进了物种交流与生产力发展。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织品、纸张、茶叶,从波斯、地中海输出的有金银器皿、玻璃制品、乳香、药品、绒毯,从东南亚、南亚印度输出胡椒、香木、宝石、珊瑚、象牙、犀角、龟甲和蓝靛;在北方,从俄国、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输出毛皮、人参和鹿角等。(20)[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第69页。古代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说:“西班牙有一个大型银矿和一个质量低劣的汞矿,从那里向所有穆斯林和不信基督的地区出口,那里也出口藏红花和姜块。麝香、樟脑、沉香、琥珀和藏红花等5种主要香料都来自印度及其毗邻地区,唯有藏红花和琥珀也出产自僧祇人中的希赫尔和西班牙。至于香料植物,在那里共计算到25种。”参见[古阿拉伯]马苏第著:《黄金草原》,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丝绸之路推动的东西方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更为巨大,东方人开辟的世界贸易网络已经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欧洲地中海地区联结成相互关联互动的经济网络,尽管它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性经济网络,但它至少可以说是区域性的经济网络,在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作出极高的评价,日本学者也同样有精辟的论断。他们在《欧亚文明与丝绸之路》一书中总结出丝绸之路的三大重要意义,即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化和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21)[日]児島建次郎、山田勝久、森谷公俊:《ユーラシア文明とシルクロード:ペルシア帝国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謎》,第190—191页。这个结论并非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众多学者的共识,突出的是区域性、洲际性交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真正反映了对丝绸之路本质的根本性认识。他们关注经营西域的意义。张骞“凿空”西域意义重大,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使中国认识到一个迥异于自己的全新世界,进入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新阶段。自此以后,汉朝成功地远征了大宛,在西域大显威力,东西贸易开始兴盛起来。(22)[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23页。余英时曾经指出,中国与西域诸国、印度、罗马等国家的交往,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中亚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后果。(23)[美]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可谓见道之论。
如果把国家间的交往作为一个具体的交往力看待,实际上它已经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当中,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多种力量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国际交往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人类相互交往的历史很早。自太古时代起,人类就有了相互间的交通往来,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孤立于外界的民族。(24)[日]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谢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20页。各国间的外交活动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唐宋时期,中外通商朝贡甚盛,中国使节往来南海及僧侣求法于印度者,不绝于途。(25)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页。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把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联系起来,其意义远远超过经济范围而向其他领域发展延伸。仅从文化交流而言,往来这条路上的有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惠超等求法高僧,也有耶律楚材、长春真人、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26)[日]児島建次郎、山田勝久、森谷公俊:《ユーラシア文明とシルクロード:ペルシア帝国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謎》,第190页。他们努力了解外面世界,把外面新鲜的东西带回国内;他们所作的翻译、引进工作影响了几代人,推动了世界文化传播,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与生活。文明的交往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在交往中人们越来越感到相互依存,正是这些区域性的国际交往不断加深扩大,从而才有后来世界性的国际交往。
二、东方传统国际秩序下的国家交往
与欧洲国家关系相比,东西方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无论社会经济基础,还是外交思想与行为方式都是如此。东方地理环境特殊,地域广袤,腹地纵深,拥有一个较之西方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深深地影响了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很早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出现地区性稳定的核心力量。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已经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创造了国家关系新形态,各国向具有较多联系的社会转变,交往的内容与形式发生深刻的变化,活动范围也大大拓展。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层次十分明显。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发展总是有先有后,不可能同步发展,整齐划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日本小国众多,“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还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27)《后汉书》卷85,《倭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21页。这些都是中国与日本早期交往的珍贵材料,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意义。日本东洋史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在评论中国对周边各国的影响时写道:“从东亚整体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28)[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0页。中国对周边的影响绝不是简单的位移,也不是武力施加,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是中外相互需求的结果。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日本与朝鲜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从纪元一世纪就开始了,四五世纪大体完成。(29)[日]佐伯有清:《古代の東アジアと日本》,东京:教育社,1977年,第23页。在东方国家关系体系内,它们之间有着东方特色的交往方式与内容。对外交往最初只是在相邻国家间进行,后来不断扩大,走向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交往。与西方相比,东方国家关系长期相对稳定,不像西方那样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存在区域性的国际秩序,中国王朝以礼仪、礼义和礼治主义作为形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为“天朝礼治体系”(30)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前言,第1页。。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历来关系密切,“只有在‘天朝礼治体系’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朝鲜王朝内部礼治体系的建立才取得了充分的条件。又可以说,只有朝鲜等邻邦在内部推行礼治主义体系,以中国的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区域秩序的宏观架构”(31)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71—72页。。到宋代,由于造船技术进步和国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换的商品种类繁多。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许多国家都有记载,如东南亚的占城国“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月又来贡。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3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2,“占城国”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7页。。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政治、经济上的往来。蒲甘国就是今天的缅甸古国,在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曾入贡”(33)《岭外代答校注》卷2,“蒲甘国”条,第84页。。《岭外代答》对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记载:“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34)《岭外代答校注》卷3,“大秦国”条,第95页。遣使、入贡、奉表、奉正朔等概念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常用概念,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就是依靠这些途径来维系的。
自唐宋以来,中国对外交流不断加深,交往的国家不断增多,对外影响具有了很强的力度。在东亚,日本、朝鲜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包括儒学、汉字、文物典章制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进入7世纪以后,东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隋唐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自汉帝国崩溃以来近400年分裂的历史,中国复归统一。朝鲜在经过长期分裂后由新罗结束了分裂的历史;日本开始形成体系性的国家机构,7世纪末和8世纪初“倭”的称谓也为“日本”所取代了。(35)[日]唐代史研究会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年,第357页。以后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消化。对于南亚的交往,古籍记载:“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36)《岭外代答校注》卷2,“故临国”条,第90—91页。这些都是东方国家富有朝气,气象不凡的表现。有目的的国家间交往形成的交往力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中、日、朝三国联系密切,同时也与东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构成具有东方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联系紧密的西太平洋贸易网络,可视为区域性的国际体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指出:“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并非初见于宋代。”(37)[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册),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
在东方,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其他地区不曾有的独特现象。从本质上说,东方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就决定了它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冒险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交往。东方国家关系虽然不平等,也不靠一纸条约来维持,但它却是长期和平、互利与联系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关系,为东方各国提供了一套社会秩序与规范,具有某些乡土味特征。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同。”(38)[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学科出版社,2010年,第4页。尽管这种关系不平等,但并不影响各国间的往来交流,在前近代时期不可能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权与平等,也不可能逾越当时条件限制产生近代的国家观念。宫崎市定认为,亚洲史就是一种乡土史。(39)[日]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绪论,第9页。在东方市场贸易中,阿拉伯商人崇尚交易中公平、公正与互惠原则,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交流。伊斯兰法律重视西洋中世正常价格的等价交换原则,在唐宋时期的大都市与海港城市,伊斯兰商人经营高利贷收取巨额利润的实例是很多的。(40)[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Ⅲ·海上の道》,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1页。
以区域的视角看待东方各国的交往,可以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之外获得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在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41)[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页。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相对较低,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贯穿于所有的朝代,即便是同一个朝代不同时期对国外市场的认识与需求也是不同的,有很大的差异,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进入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国家对外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宋代对外贸易已经占到国库收入的20%以上,与国外市场发生多方面的联系。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到:“宋朝时,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制造业产品和贸易,国家新财富的主体也是来自这两个经济部门。这种经济状况已经与如今的现代国家十分相似了。南宋时期,商业税和工业税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所能征收到的土地税。”(42)[美]罗兹·墨菲著:《东亚史》,林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144—145页。宋代社会经济与国家关系都发生重大变化,内藤湖南提出“唐宋社会变革”论是有其充分事实根据的。
根据《厄里特里亚海航行记》可知,公元1世纪罗马商人就已经来到中国南海从事贸易活动了,将东方市场的商品带到欧洲。根据日本东洋史、南海史学家藤田丰八考证,自公元2世纪中叶起,中国与西方已经有海上直接交通,到了3世纪已经很频繁了。(43)[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何健民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4页。宋代留下的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也给我们看待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诸蕃志》是宋代赵汝适的作品,从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众多,超过50个,其范围东起日本、菲律宾,南到印度尼西亚各岛,西达中亚、西亚、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无论对外认识还是交往范围都比以前深入得多。由于地理之便,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许多商品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输入到对方市场。三佛齐即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唐朝天祐年间始通中国,至宋代“贡使络绎”(44)[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三佛齐国”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页。。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其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漆器和瓷器,这些商品被销往东亚和印度等地,甚至远销到非洲东岸。(45)[美]罗兹·墨菲:《东亚史》,第144页。由于造船技术进步和国家力量投入到对外贸易当中,东方国家间的商贸交流更加有力直接,促使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不断发展、成熟和扩大。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以前,东方国家已经与外部进行跨国家、跨区域的国际性交往,形成西太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并且这两个贸易网形成密切的联系与互动,“阿剌伯人之海运,更为发达,彼等逐渐东进其航路,遂将波斯湾至中国海间之航运,完全收归其掌握。在西历九世纪之中叶,广东之外国贸易,尤为繁盛。约有几万之阿剌伯商人,不绝来往于广东”(46)[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鍊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38页。。海上交通的发展与扩大,对各国意义重大,不仅加快了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在代谢中不断向前发展,出现许多新的港口城市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缔造出新的文明中心,对外发生辐射作用。“由唐而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47)[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第17页。
关于东方国家内部的相互联系,许多材料中都有具体的记载,桑原骘藏写道:“唐代中叶以后,大食人(即回教徒)盛向中国南部诸港通商。”(48)[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第47页。他对海上往来和外蕃商客写得具体真实:“中国唐代与摩诃末教国(大食)间海上通商,曾盛极一时。”(49)[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第64页。东南亚地区商业贸易网络早已建立起来了。这里不仅有勃固、阿瑜陀耶、金边、会安、北大年、文莱、亚齐、万丹、望加锡等贸易中心,拥有远远多于欧洲任何城市的大量人口,更为重要的是形成巨大的世界贸易中心——马六甲港,它们成为东南亚经济生活、政治权力和文化创新中心。(50)[澳]安东尼·瑞德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 扩张与危机),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仅马六甲一地,就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常常听到的语言有84种,交易的商品有丁香、豆蔻、檀香、瓷器、麝香以及金子、白丝等。市场管理是经济市场化的重要标志,马六甲对外商征收6%的商税。(51)[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东南亚丰富的天赋资源吸引了各国来进行贸易交流,仅1604—1635年日本来东南亚的商船就有近300艘之多。因此,我们可以说东方人开辟的市场与海上商业网络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对后来历史都有影响:“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52)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19页。这样的看法符合当时东方社会的真实情况,符合欧洲人东来初期对东方社会的适应情况。
由于天时、地利等条件,东南亚地区历来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不仅有许多天然良港,交通发达便利,而且有丰富的天赋资源,成为东西商贾汇聚之地,历来受到东西方商人重视。自14世纪以来,它和爪哇控制着东南亚的贸易路线,与印度、波斯、东非和地中海贸易网相连,构成当时最大的贸易体系。(53)[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的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广州:广东出版集团,2014年,第64页。有大量材料表明,近代以前南海地区是世界贸易的重要之源,也是国际商人聚集的重要地区。“考我国与南海诸国之通商,为时颇古,秦时之番禺(今之广州)已成南海贸易之中心地,商贾云集,各种异货珍品,远近会聚,复因诸蕃商,对华货物,竞相贸易,故冒涉重洋,咸驶来华,而与国人交易焉。后竟有诡称贡使,以图利者,其市易之利,可想见矣。当时华商之往贾者,亦甚多。至汉代,益臻频繁。”(54)[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上),译者序,第1页。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到西太平洋贸易网的竞争与建设当中,摆脱了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摒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老生常谈,代之以义利兼顾与利己利人的经商理念,开启了一代风气,展现出中国商人与东方市场的崭新气象。
元朝的建立把中外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使东方和欧洲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也把东方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元朝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它打通的东西方直接交流的意义重大。“蒙古大征服的结果,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得以普及,连结各地的经济活动十分发达。在金帝国的华北地区,建立起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蒙古帝国强盛的西元十三世纪,在地中海世界,掌握黑海与东地中海贸易权的威尼斯出现了欧洲最早的银行。从威尼斯越过阿尔卑斯山,资本主义的经营形态扩展到了西欧地区。这也是因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才有可能发生的事。”(57)[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2013年,第195页。我国学者在探讨元代的东西交流时,写到:“蒙古军队征服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地区,使蒙古势力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相连。……这样,在古代世界东西交流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其亚洲陆地终点,均在蒙古政权的控制之下。……所以,元代中国与西亚之间的海陆联系之频繁程度,远逾前代。”刘迎胜:《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我国也有学者持这样的看法:“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要是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纪旧大陆范围的‘全球史’,乃至于后来时代欧洲——它之受惠于当日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明显要越过与它相向的另一极——的历史,也就一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58)[美]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代序,第10页。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东方社会发生的诸多重大变化,不仅对本地区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发生的重大影响。必须指出,元朝的武力征服也给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与伤痛。
元朝不仅继承了宋代的海外贸易网络与管理经验,还任用外国人管理对外贸易。蒲寿庚是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人,降元后受到重用在福建、广东市舶司任职。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对唐、宋、元时期中国与海外通商交流情况有详细的研究,展示了一幅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地区交通贸易的清晰图景,映现出中外交流与东方外交活跃的情况。早在8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已与中国海上交通,到达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与文化传播。“阿剌伯人之来华也,多自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抵今之广东。”(59)[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页。在中国广州,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设“蕃坊”,由外国人自行管理,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如果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中国政府是不予干预的,说明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宽容,也说明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说到历史上的中外交流,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而对海上交流以及海洋沟通东西的作用似乎关注不够,也就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网中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东方内部的市场与交流模式认识不够。已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中,遵守市场原则的正是中国人,他们用公平竞争的办法将中国产品提供给世界市场;他们按照利润原则,受价格信号的指引,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纵横海上贸易上百年。”(60)骆昭东:《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中详细地考察了阿拉伯人东来经商与旅居的情况,认为自8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人来到东方为止的八百年间,为阿拉伯人在世界贸易最为活跃的时代,特别是在8世纪以后,“彼等对于从海上与印度及中国方面之通商事业,尤注力焉”(61)[日]桑原骘藏:《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冯攸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页。。由于当时唐朝国力兴盛,政治稳定,国内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港口,在交州、扬州、泉州、广州等诸多贸易港口当中,“当推广州最为繁昌”(62)[日]桑原骘藏:《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第3页。。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因从事东西方贸易而成为富商者大有人在。他们称得上是富商巨贾,服饰皆绫罗绸缎,器用金银器皿,家资数百万贯。在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形成面积广阔的贸易市场,15—16世纪由于商品生产的展开和银市场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的交易活动取得快速发展。(63)[日]唐代史研究会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汲古書院,1979年,第15页。稳定的国际关系推动了中国、东南亚、印度以及西亚地区的社会发展,使它们有条件为世界贡献了东方古典文明。在东方各国的交往中,阿拉伯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活跃于西起摩洛哥、印度洋、南海至日本的广阔海域,而且独占东方贸易数世纪之久,直至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为止。(64)[日]桑原骘藏:《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第13页。这样的评断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三、东方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各部落、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不论规模大小还是时间长短,也不论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都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与痛苦的回忆,即使今天战争的威胁也没有远离人们的视野。历史上曾发生多少次战争,有的时间过于久远已经无可稽考,但大的战争已经被历史记录下来。检讨东方历史上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一套社会秩序与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历史上的一些战争有过论述,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专攻战略历史的保罗·肯尼迪一再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个国家已经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65)[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序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页。他说的是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对于理解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应该指出,和平与稳定是东方社会的常态。与欧洲相比,东方国家之间战争爆发的频率小得多,这可能与东方国际关系核心力量的长期稳定有关,也与农业文明的特性特点有关。在东亚,有几场战争影响了历史进程。发生在663年8月的白村江战役,是东亚第一场国际性战争。战争是以唐朝、新罗为一方,日本、百济为另一方来展开的。日本在战争中投入的战船有400艘。在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发生的事情一般都具有国际性质,绝不是单纯的某一国家的事情。百济与日本自四世纪即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六世纪以后两国继续维持军事同盟关系。(66)[日]遠山美都男:《白村江:古代東アジア大戦の謎》,东京:講談社,1997年,第69页。长期以来,一直吸收大陆文明的日本为什么要与唐朝发生战争呢?这与日本经过五、六世纪的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有关,也与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关,试图实现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当时新罗和百济正在争夺伽耶地区,日本支持百济占领伽耶。新罗对伽耶的占领使自己的国土直接与百济接壤,国境纷争成为新的问题。(67)[日]遠山美都男:《白村江:古代東アジア大戦の謎》,第70页。
白村江战役的结果是日本失败。《新唐书》记载,刘仁轨率兵“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68)《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83页。。唐朝与新罗联军取得了白村江对日之战的胜利。“白村江之战在两国关系中投下了一片阴影。两国交兵和倭人败绩,显然严重损害了倭人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引起了中国王朝对倭人的怀疑。”(69)沈仁安:《日本起源考》,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白村江战役的失败对日本影响很大,国内一片惶恐,深惧唐朝在战后进攻日本,从而在九州岛一线修栅筑城,紧张设防。(70)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与唐朝、新罗联军进行战争就意味着灭亡的危机,日本外交的大失策,也是其外交的大污点。(71)[日]関裕二:《古代日本人と朝鮮半島》,PHP研究所,2018年,第274页。经过战争,日本痛感自己的力量不足,只好在东亚的角落里好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于这次战争,日本学者多有检讨,认为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古代最大的对外失败战争,对国家、社会、文化以及对外观都发生很大影响。(72)[日]森公章:《“白村江”以後:国家危機と東アジア外交》,东京:講談社,1998年,第12页。可以说,自663年白村江战役到1274年元日战争爆发的600余年时间里,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在近代以前,称得上具有国际性战争的还有1592年和1597年发生的壬辰战争。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通过《刀狩令》《太閤检地》以及多种措施加强了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积累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的野心随之膨胀起来。1592年正式发布出征朝鲜令。当时日本拟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兵力多达158 700人。(73)[日]中野等:《文禄·慶長の役》,东京: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32页。以此观之,此次投入战争的军队规模是空前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侵略朝鲜进而达到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目的。4月13日,小西行长的军队包围釜山城,壬辰战争正式爆发。《明史》载,日军“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清正等遂偪王京。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74)《明史》卷322,《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358页。据说,当时从釜山登陆的日本军力非常强大,上陆一个月就攻占了朝鲜国都汉城,咸镜道和平壤也都陷于日本之手。为了抗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中国明朝派出了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总指挥官,李如松为军务提督的强大阵容。12月23日,李如松统帅的明军队43 000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新义州和安州。在朝鲜战场上,明朝军队会同朝鲜李朝军队和义兵从三面包围了被小西行长占领的平壤城,消灭日本军队1600人。(75)[日]中野等:《文禄·慶長の役》,东京:吉川弘文館,2008年,第98—99页。
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壬辰战争仍然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战争对交战三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一场东亚史上史无前例的国际战争,战后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76)鄭杜煕、李璟珣編著,小幡倫裕訳:《壬辰戦争: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东京:明石書店,2008年,第21页。有人指出,战争意味着日本在东亚国际舞台上作为大国而登场,朝鲜已经被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如果中国和日本两大强国再次发生战争的话,朝鲜半岛必将再次成为战场。(77)鄭杜煕、李璟珣編著,小幡倫裕訳:《壬辰戦争: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第24页。自此以后,日本出现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开始挑战中国明朝的大国地位。16世纪,东亚地区的各国形势已经发生不小的变化。从日本而言,已经完成了国内的统一,政治、经济、军事都有一定的发展,对中国明朝的国际地位有了最初的挑战。《明史》卷322“日本传”载,丰臣秀吉的狂妄计划是:“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极为明显,也十分庞大,不仅要侵略中国、朝鲜,也要把印度囊括在它的亚洲帝国的版图内。(78)鄭杜煕、李璟珣編著,小幡倫裕訳:《壬辰戦争: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第33页。侵朝战争的初战胜利和汉城陷落后朝鲜国王出奔,使丰臣秀吉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刺激了他侵略明朝的欲望,打算把天皇移居北京,他本人入居宁波府,完成征服南亚印度的扩张计划。参见中野等:《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6年,第379页。《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57页)载:(丰臣秀吉)“欲侵中国,灭朝鲜,……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们还对服务供应链以及供应链在服务业中应用的战略(strategy)、质量(qua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契约(contract)、创新(innovation)、优化(optimization)、选择(selection)以及服务(service)管理与基于价格(price)利益分割等问题给予了较高的关注。新时期,消费者需求已经从传统的商品质量需求转向全供应链服务质量的需求,加之产品服务化和服务制造业相结合的市场发展趋势,构建运作高效、质量稳定的服务供应链逐渐成了众多服务主导型企业发展的战略抉择。
日本表现出的侵略野心对整个东亚来说是凶多吉少,明代一些文臣对其已有洞见。它的侵略野心虽然未能实现,但对后来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影响。国际形势出现了不稳定。出兵朝鲜之前,丰臣秀吉在日本国内做了充分准备,声势浩大。无论从国际关系史还是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壬辰战争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壬辰战争不仅是中、朝、日三国最高权力者的介入,一场经济、军事和技术的较量,同时也在陆地上和海洋上进行,东亚三国真正地使用了铁炮技术。(79)鄭杜煕、李璟珣編著,小幡倫裕訳:《壬辰戦争:16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第32页。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程度上它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战争,在东亚历史和东方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有人认为明朝主导的15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已经解体。(80)[日]池享編:《天下統一と朝鮮侵略》,东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第14页。为了防止日本再次侵略朝鲜,中国明朝着手建立以东北为重点,以朝鲜为后盾的海防防援体系。战争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进行的,朝鲜承受了战争的巨大损失,留下了太多的伤痕,至今成为朝鲜人的惨痛回忆。从明朝方面而言,它虽然是地区大国,但它在许多方面出现发展缓慢甚至衰败的情况,已经缺乏积极的进取精神。
进入近代以后,导致东亚发展格局重大变化的中日甲午战争另当别论。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除了少数几场有影响的战争外,大多时间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度过的,所以有学者提出“为什么稳定能够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常态”这一命题。(81)[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页。当然这与东亚地区长期存在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有关,与存在一个强大的文明中心——中国有关。在东亚,中国长期主导地区国际秩序,既定的秩序不容挑战。中国的国力越强盛,整个地区的形势与国际关系就更加稳定;中国内部分裂与动荡直接影响周边各国与地区形势。按照中国学者的分析,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存在“天朝礼治体系”,周边国家被纳入到这个秩序中来,寻找各自的位置和最佳的利益交汇点。中国历代王朝以“天朝礼治体系”的规则来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建立一种相安无事的国际关系。必须指出,这种关系依靠的是一定的国力,无国力支撑的国际关系是脆弱的,无法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建立在合法性权威和强大物质力量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朝贡制度,为东亚提供了一整套社会秩序和规范。”(82)[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第2页。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与规范是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稳定总比动荡与动乱好。从另一个角度看,东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所具有的超强稳定也使东亚社会迟迟不能向更高一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相对于欧洲,东方社会的历史确实耐人寻味。它不仅战争次数相对较少,而且社会长期稳定甚至出现所谓的“超稳定”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东方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和“天朝礼治体系”之外,也与东方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有关。有人把东方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的是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和均势政治,却充满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东亚朝贡体系主张形式上的不平等和明确的等级制度,却塑造了长达数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83)[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第3页。这样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注意,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与极大关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内部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王权过于强大,政治缺少应有的弹性。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小农占多数的社会,凭借已有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力量,从事社会农业生产,社会的流动性极小,加上由各级官僚、军队组成庞大的国家机器,思想上和政治上追求大一统,实现了对社会一体化的强控制。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正如斯塔夫里阿斯指出的:“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8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两者相较,差异判然有别。必须指出,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多,但国内战争与王朝更替造成的社会灾难性后果极为恐怖,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漫漫2000余年的专制传统的国家因改朝换代造成的破坏可能比任何国家都严重得多,同时它也具有强大的社会修复功能,几十年后就像投向水潭的一颗石子引起一阵波澜之后很快又复归平静。
与东方相比,西方社会分裂与动荡严重得多,分裂的时间也长得多。比如在中世纪的德国,有二百多个大小邦国,两千多个骑士领地造成无法估量的混乱局面,强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为争夺帝国最高权力展开了无休止的斗争。(85)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不仅如此,各国货币不统一,度量衡也各有不同,直到近代德国才完成统一的任务,长期分裂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发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西方社会不仅战争频仍,就是发展程度也逊于东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评论道:“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8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1页。这是近代以前欧洲社会的一幅图景与缩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欧洲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分裂,不是一个偶然的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分裂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87)[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9页。他还指出:“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不同,与莫卧儿人不久后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也不同,从来没有过各部分共同拥戴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与此相反,欧洲是各种小王国、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88)[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4页。
仅仅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东西方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社会结构与制度当中去理解和思考。欧洲在进入近代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对外寻找市场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的重大需求,为争夺市场与财富奔走世界各地,因此为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发生的战争较以前空前地增多了。东方大国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缺乏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那样的强烈的创业动机。东方许多国家信奉佛教,其本身就缺乏基督教那样的强大扩张力量。“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佛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8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页。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从礼治的视角来解释东亚社会的长稳定问题,提出了“礼治稳定说”。这个学说认为:“传统东亚秩序礼治的统合性原则规范是所谓‘天下礼’。通过中央国家的推行,天下礼得以普遍实施,传统东亚秩序因此有序运转、平稳发展。”(90)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7页。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个社会过于稳定,承平日久,就会产生惰性,变革的因素减少,社会效能减弱,这也是东方社会的重要特征。
研究东方社会的长稳定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东方社会长稳定,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出现许多港口城市与贸易中心,为什么迟迟不能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演进,完成制度创新,以至于出现黑格尔等人提出的千百年来东方社会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极端观点。任何社会在几百年间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只不过是变化大小而已,绝对不变是不可能的。必须指出,长稳定与非变化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社会是神秘的、静态的与不变的,这样的观点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中广泛流行,也可以说是他们落后的亚洲观与东方观。对于东方社会的长稳定,必须以大范围、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过于短暂的观察是不能把握其社会变迁的。东方社会长期处于渐变的过程当中,不同于近代时期欧洲工业社会的巨变与灾变。我们强调社会长稳定,主要是基于对东方社会渐变的考虑,并不否认自身存在的一些创新性不足等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过于缓慢,几千年基本上处于没有变化的循环当中。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写到:“两千多年来,东亚社会很少发生大变化。东亚人不喜欢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变化是破坏性的(很显然,的确如此),……人们往往容易重视过去,确认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来。”(91)[美]罗兹·墨菲:《东亚史》,第13页。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忽视了农业社会是在生生不已的过程中发生变迁的基本事实。同样是封建社会,唐宋不同于秦汉,明清也有别于唐宋,近年国内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绝对的数量与持续的时间来说,东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多,西方国家间的战争不少,甚至持续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战争大有其例,例如持续了百余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堪称世界战争史之最,这样的长时间战争在东方极为少见。自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频繁与范围广大,引起军事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形成有影响的军事历史科学,为西方军事历史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尤其重大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变化以及造成以后新的国家间矛盾在很长时间里无法解决,可能会引起另一场战争危机。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话,以其解释西方国家的历史也许是合适的,但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对比古史材料,可以看到东西方社会的不同以及战争的密集程度。远的不说,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欧洲人发动的(当然也包括东方的日本),给世界带来无比巨大的损失。如此惨烈的国际战争给各国造成永久的痛苦回忆,正如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所言:“1900年以后的100年,毫无疑问,是近现代史上最血腥的100年。这100年比起先前的任何时代,无论从相对意义上还是绝对意义上来说,都要残暴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惨遭杀害的人数,比起之前任何一次具有相似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中丧生的人数,都要多得多。”(92)[英]尼尔·弗格森:《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上册),喻春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引言,第4页。现代技术进步使战争的伤亡空前地增大。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蓄意大屠杀。(93)[英]尼尔·弗格森:《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上册),引言,第4页。对比东西方战争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即东方国家的和平时间远远长于战争时间,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与交往中度过的。有材料表明,1368—1841年,在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之间只发生过两场征服性战争,而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在1300—1850年至少进行了46次战争,瑞典在此期间也参加了32场战争。(94)[美]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第103—104页。对比东西方国家间的战争极有意义,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应该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四、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也是最早形成人类文明交往的地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不仅影响了过去,也在影响塑造着未来。按照近代以来人们的一般看法,东方是指地中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面积4 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总数的60%以上,孕育了独自生成、自成一体的区域交流文明,形成具有东方浓郁特色的外交圈和文化圈。在东方,存在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对外交往圈基本上也是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大起来的,形成伊斯兰外交圈、印度外交圈和中国儒家文明外交圈,同时三大文明圈之间也有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与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在考察东方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地理因素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大体说来,在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高原以东形成了东亚外交圈,在很大程度上它独立发展,农耕经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外交思想与外交行为过于早熟。它独立发展并非孤立发展,通过陆上和海上与世界保持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联系,创造出东方外交制度与实践的典范。
在东方,几个重要的外交圈应予特别的重视。一是东亚——东南亚外交圈。这里不仅很早形成了中国这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而且与周边各国建立了国家间联系,推动了区域性的整体发展。中国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较早发生与周边文明的勃兴,形成了东亚世界,发挥了东亚中心的作用。(95)[日]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はしがき”,东京:岩波書店,1993年。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了官方联系,民间交往比此更早。“中国与南海之海上交通,有史之初应已有之。”(96)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强调指出:“与其他的地区历史相比,亚洲的历史自最久远的古代开始,就留存着不少相当明确的历史资料。”(97)[日]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绪论,第3页。确实,东方各国不仅有丰富的外交活动、外交思想,还留下相当完备的历史资料。我国正史《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魏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 《元史》 《明史》等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详细的记载,具有重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这些具体而完备的历史材料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外交圈。它不仅与东亚、东南亚有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也与西亚、非洲、欧洲建立商业贸易关系,印度的东西海岸早就有欧洲商人的活动。印度在我国史书中称为“身毒”和“天竺”,我国与它交往甚早。中国与印度交通,不会晚于汉代。《后汉书》“天竺传”对印度与汉朝关系有这样的记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缴外来献。”(98)《后汉书》卷88,《天竺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2页。印度不仅与中国有使节往来,与其他国家关系也同样密切。宋人周去非记载:“故临国(今印度西南部奎隆)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99)《岭外代答校注》卷3,“故临国”条,第90—91页。值得注意的是,南亚对外交往已经形成三个重要区域,即从红海—阿拉伯半岛、波斯湾至印度的西南端,从印度的西南海岸至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和爪哇岛,从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印度群岛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大港口。(100)[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第245页。大量的古籍材料表明,印度与外面的联系是以多种形式展开的,尤其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和东南亚影响至深至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三是中东西亚外交圈。因地利之便,它处在东西交通的纽带地位,发挥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经过多年征战形成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帝国,直至1258年为西征的蒙古军所灭。忽鲁谟斯是波斯湾东岸的重要贸易港,汇集了东西方商人与商品。1272年马可波罗到达这个商港,看到这里有许多驾船而来的印度商人,该港口交易的商品有香料、丝绸、黄金、象牙、马匹等。(101)[德]廉亚明、普塔克:《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姚继德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各国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之后,实现了与西方国家的远距离交往,从而形成跨区域的洲际性的国际交往。商业贸易是国际交往的重要方面,也是外交活动的内容。根据学者以往的研究,在埃及、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古代的陶瓷,足以说明这些陶瓷是由东方运输到西亚中东和西方的。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探访东西文明的连接点》中说,中国制造出陶瓷是在比埃及更遥远的公元前二千年后半期,通过海路销往世界各地的。汉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中亚关系逐步加深,中国的许多物产被运往这些地区。(102)[日]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东京:岩波書店,1969年,第164页。海陆丝绸之路把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形成人类交往史上的灿烂篇章,使各国的交流互动大放异彩,共同受惠于交流交汇的总体利益格局。
东方国家形成政治统一的时间很早,在对外交往中形成几个交往圈,人们习惯于称它为“四大文明交往圈”。我国学者已经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中国,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皇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在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由于中国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使得中国古代外交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宏、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103)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前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自唐代以后,中国对外交往具有了很强的力度,促进了东西方更为直接的交流,显示对外交往的宏大气魄。大量的东方古史材料所反映出的东西交流与东方外交,无疑是与东方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在数千年里绵延不断,给世界留下了珍贵遗产,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说得好:“最重要的是,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它,我们将会虚弱无力;……也许,特别是由于亚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当代亚洲人又重视其历史,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规划未来。这些都是研究亚洲历史的重要实际理由。”(104)[美]罗兹·墨菲:《亚洲史》,林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0页。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这也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