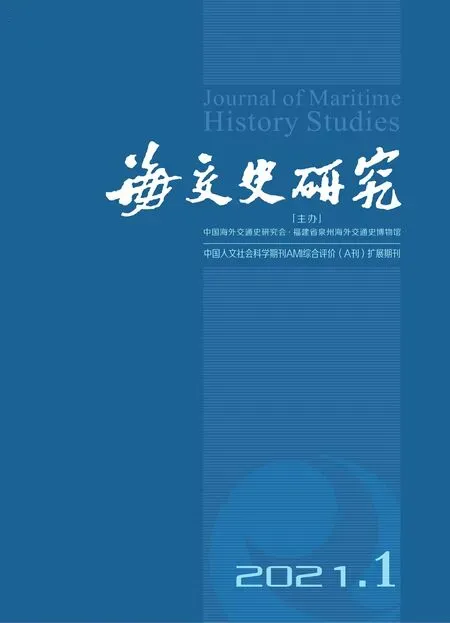清代前期沙船业的沿海贸易活动*
——以上海商船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范金民 陈昱希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清廷宣布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次年,上海县城小东门外设立江海大关,统辖吴淞、刘河等处22个海口分关。从此,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尤其是北洋航线,商品贸易获得合法地位,流通格局和规模迥异于前,沿海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各地地域商人纷纷以上海为据点,展开商业竞争,上海由此迅速崛起。
有关上海航运业史的探讨,学界研究成果已经极为丰夥,其中松浦章全面探讨上海沙船及其运输活动的著作、资料集和系列论文,萧国亮论述鸦片战争前上海沙船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辛元欧考察上海沙船的型制,郭松义和邓亦兵考察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等成果,最值得注意。(1)[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台北:乐学书局,2007年。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辛元欧:《上海沙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郭松义:《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载《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邓亦兵:《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然而论者的重点集中在清代中后期,内容上主要是沙船的型制、沙船运输业及其沿海贸易活动、沙船运输业的劳资关系、沙船活动的盛衰等,而于清代前中期上海作为航运业中心时期船商的情形、上海城市活跃的航业势力等还殊少着笔,有关情形还不甚清晰,进出上海港的物资以大豆为主,其背景也不甚明了。
笔者曾先后撰文,考察过清代前期上海作为航业中心的兴起、上海的航业船商、刘家港的豆船字号、福建商人及广东潮州商人的沿海贸易活动,(2)范金民:《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载《史林》2007年第3期;《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清代中期上海成为航运业中心之原因探讨》,载《安徽史学》2103年第1期;《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贸易》,载《明清论丛》第14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9月;《清代潮州商人沿海贸易活动述略》,载《历史教学》2016年第8期。但尚未对江浙商人的沿海贸易活动作系统考察。今主要依据相关资料尤其是松浦章搜辑的资料,在其研究的基础上,作专门探讨。拾遗补缺,以期能深化清代沿海贸易史和商人活动史的研究。
一、上海商船会馆的设置
在上海经营的船商,有共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商人会馆,也是上海现存时代最早的会馆遗址。会馆座落于南市马家厂,列于民国《上海县续志》“会馆公所”条之首。文谓:
商船会馆在马家厂,康熙五十四年沙船众商公建,崇奉天后。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南台,并铸钟鼎。同治元年借驻西兵,撤防后制造局僦居于内,阅五年迁出,殿厅适圮毁。七年重修。光绪十六年飓风损戏台,重修。十七、十八两年继续大修。天后宫未改建时,有司岁祀于此举行。二十年以天后护漕有功,钦颁“泽被东瀛”额。常年经费由船号商抽缴庙捐,并以租息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傤之用。泥夫每多争竞,遴夫头以资督率。会馆事延董主之,办事处称商船公局,在会馆之左,督理水手伤亡之承善堂附设焉。光绪三十三年复附设商船小学校。(3)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第1页。
是记叙述了商船会馆自始建到历次修葺的过程,包括修筑人的身份,会馆经费来源、功能、管理、用途、奉祀神灵,以及会馆的附属设施等,较为全面,但过于简略,不够翔实。
若依据此处记载,结合商船会馆的相关碑文,可以大致勾勒出商船会馆的基本情形: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上海的沙船号众商共建会馆。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1814),无锡海商铸钟鼎,崇明海商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船号商共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成为建筑巨观。同治元年(1862),借驻西兵,撤防后又由制造局租住,五年后方迁出,但殿厅圮毁。七年,众号商集资兴修。当时由沈晓沧主持馆务,竣工后由郁正卿经理。为时不长,遭风雨剥蚀,会馆屋宇倾斜,因停止南宫捐款,经费无着落,会馆得不到及时修葺。光绪十六年(1891)七月飓风大作,戏台头亭渗漏,同人花费洋银744元重修。十七年三月,同人继续筹款,修理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费豆规银1876两。次年九月,更易戏台新梁,又费豆规银891两。经过数年间的一再修葺,会馆稍复旧观。二十年,沙船号商陈丰记献助天后镀金点翠金银冠二顶、包金银项圈连锁二事,号商顺祥源献助点铜宝塔四座。同年,因天后佑护漕运官粮有功,钦颁“泽被东瀛”匾额。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设商船小学校。会馆大殿崇奉航海保护神天后,乾隆中期重修后,南、北两厅分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和福山太尉褚大神,官方每年祭祀天后的活动就在馆中举行。会馆所需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捐,馆产租息所入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以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泥夫每年争竞,馆方遴选夫头以资督率。道光后期会馆重修后,“会馆事务悉归号商经理”,会馆延请董事主持馆务。最初延请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状元苏州人石韫玉主理馆务,后来先后聘请张兰亭、陆春晖、沈雒宜、吴沐庄、金侍香、周心宇、金梅岑、沈晓沧、江馨山、沈庆甫、郁正卿、朱佩韩、潘子楼、王宗寿等地方名流主理。会馆办事处称商船公局,在会馆之左,办理水手伤亡的承善堂也设在其地。光绪十七、十八年大修会馆时,捐款者是佛店、铜锡店、广货店、绳索店、纸店、铁店、洋布店、颜料店、桐油店、砖灰行、漆作、水木作、石作、锡匠、木行、树行等,而未见沙船字号。(4)《重修商船会馆碑》,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商船会馆各号商捐助祭器碑》,光绪二十年二月,载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6—202页。如此大修未见沙船号捐款踪影,或许说明其时沙船业已很不景气,沙船主在商船会馆中已无甚地位。
明清时期商人建立同乡组织会馆,起自明代万历年间,各地商人在上海开展经营活动者,各建有地域组织。一地工商业同行建立同业组织公所,兴起于清代初年,但无论会馆还是公所,尚未有如上海商船会馆这样汇集在一地的各地商人建立的同业组织。商船会馆兼具异地商人会馆和一地同业公所的共有特征,充分展示出清代上海航运业隆盛发达的特殊性,颇具重要地位。
碑文中提到的石韫玉(1756—1837),字执如,一字琢如,号琢堂,又号竹堂,晚号独学老人,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五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山东按察使。嘉庆十年或十二年因事被劾革职,仁宗念其川省军营劳绩,赏给编修,以足疾乞归,有《独学庐诗文集》传世。道光十七年卒,年八十二。(5)陶澍撰墓志铭,载[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95,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6372—6373页;《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62—5963页。石韫玉为宦近20年,归乡时无田可耕,先是就养儿子浙江官衙,嘉庆十六年佐幕两江总督勒保,后主讲金陵、扬州、苏州等地书院,里居22年,墓志及传记均未提及其主理商船会馆事。其主理商船会馆,当在嘉庆十年之后,具体则很可能在嘉庆中期,时间也不会很长。
碑文中未曾提及名字的商船会馆总董有郁彭年。据民国《上海郁氏家谱》序记载,郁氏先祖为嘉定县南翔乡里人,四世祖宰荣公次子莲塘公,经商上海,遂入籍。卷2《世纪》载,彭年字尧封,号竹泉,系上海东乔家滨郁氏六世孙,生于嘉庆元年(1796),卒于咸丰二年(1852),经营沙船行号,任“商船会馆总董”。卷6《六世祖考竹泉公行状》又称他少壮经商,承继父业,创办森盛沙船字号,家有大船80余号,“承办海运漕水各号商,必推公为领衔,创立商船会馆,举为总董”。从时代和年纪推算,沙船主在道光初年朝廷海运漕粮中出了大力,在道光后期大事重建会馆,作为领衔者的郁彭年被同行推为会馆总董。于此同时,会馆的董理也由乡绅转为沙船字号主本身。
由商船会馆碑和郁氏家谱所记,可知会馆原来聘请地方名流主理馆务,而道光后期上海开埠贸易后,改由沙船号商自行经理。前述嘉庆中期状元功名的官员苏州人石韫玉应聘主理馆务,正好印证了这一点。道光四年,名士包世臣力主漕粮海运时,议及商船会馆的馆务管理时说:“沙船自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予尝问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千百分之一。”(6)[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光绪十四年刻本,第2页。包世臣所言,与商船会馆碑文所称大致吻合。
据沈宝采《忍庵恕退之斋日记》记,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绅士则郁泰峰、经芳洲纬、郭鬯庵长祖、王叔彝庆勋……王桐村承荣”;二十五日,“今早即拜王永杜桐村于咸瓜街……此为船商之最著者”。(7)上海图书馆编辑:《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9、240页。王永盛号王承荣是船商之最著者,商船会馆总董恐已转由其出任。由同治元年六月李鸿章《上海一口豆石请仍归华商装运片》所称“据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称”,王承荣是船商的领衔人。同治二年三月,上海船号商会馆司月,有王永盛、郁森盛、沈生义、彭宝泰、郭万丰、蒋济川、蒋汇川、合记、丰记、安吉、久大、源记等。(8)《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115丁表,同治十一年,上海博物馆藏。郁泰峰即森盛号主彭年之弟松年,字万枝,号泰峰,生于嘉庆四年,卒于同治四年,家谱记他“佐理兄营沙船字号”。可见其时沙船业领袖郁氏仍为会馆总董,兼任司月,但会馆总董在咸丰二年郁彭年去世后,转由王承荣担任。尽管如此,郁氏一直在商船会馆事务中发挥作用。碑文中屡次述及的郁正卿,是郁氏七世孙,名熙绳,字亦泉,号正卿,即为彭年次子,生于道光十三年,卒于光绪六年,在同治七年会馆修复后总馆务,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接任王承荣而来。由家谱记载,生于道光二十五年卒于光绪二十年的郁氏七世孙熙咸,号砺卿,兆年次子,曾为会馆总司帐,光绪十八年会馆重修时就以“经帐司事”署名;生于咸丰九年卒于民国六年的八世孙颐倍,号仲芬,正卿之子,曾任会馆议董,元培号福芝,熙浩长子,曾任会馆文案和海运局文案。郁氏在商船会馆中始终居有重要席位。
会馆其他董事记载较多者,有陈丰记。经元善《趋庭记述》卷2《资政公补遗轶事》载,沪南有陈有德沙船字号,与经纬所开元记钱庄往来已久,创业者无后,继侄为嗣,道光某年漂没沙船不少,“陈号揭欠各庄会票拾余万两”。(9)[清]经元善:《趋庭记述》,《资政公补遗轶事》,载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咸丰五年,沈宝采记录上海船商24家名单时,有第16家,陈有德芝芳,南仓街。后有陈增钧,字佑申,继承父业经营沙船,“赖以生活者,恒在三百人以上”。光绪八年山西大饥,输银三千两;光绪二十年黄河告灾,输银三千两,“皆匿名捐助”。(10)民国《上海县志》卷15,《人物》。光绪十八年会馆重修时,陈丰记列名司月众号商,并捐助豆规银100两。光绪二十年,号商陈丰记东号敬助会馆镀金点翠全银冠贰顶,重48两。(11)《商船会馆各号商捐助祭器碑》,“光绪二十年二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01页。两,与下文的厘、豪、忽、斤、钱、分为旧制计量单位。同时捐助祭器的只有号商顺祥源。据《中外日报》载,光绪二十四年,陈丰记号之朱元泰沙船,往返牛庄载运豆货。二十五年,陈丰记之金协裕沙船,由牛庄载货返沪;陈丰记号之朱源泰沙船,满装油豆各货,由营口返沪;陈丰记之沈恒翔等沙船,由牛庄返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陈丰记之朱源泰、金协裕、和长源沙船,每年均由牛庄装货返沪。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该报报道,南市商船会馆与徽宁会馆为占夺涨地涉讼公庭,“兹经思恭堂董胡广文德景邀同铁路帮办潘芸荪观察,与商船会馆董陈丰记,商船号主及久大号主李绅董,邀同朱森庭明府订期会勘”。光绪二十七年该报报道载明“商船董陈丰记主陈牾”。(12)上引《中外日报》的报道,均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所附资料,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由这些报道,可知光绪中后期,会馆总董是仍然经营沙船运输业名声最为显赫的陈丰记主人。
上海在开埠前后,豆业既是航运业中比重最重的行业,也是全上海各业中的领袖行业,因而金融流通有专用银两,称豆规银,含纯银九八成,价值尺度略低于库平银,以109两6钱合库平银100两。市面米麦行店所用斗斛即置于上海县城隍庙三穗堂的庙斛,以及道光年间开始用的漕斛,也以通用豆规银的海斛来较准,庙斛专量由北运南之豆粮,1石当海斛9斗,容量较海斛为略小。(13)参见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风俗》,第8—9页。石、斗、斛,与下文的升为旧制计量单位。上海豆业交易的发达和金融市场的度量标准的确立,商船会馆当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各地沙船业商人的北洋贸易
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14)明人《再陈海运疏》,载乾隆《崇明县志》卷19,《艺文志》,第46页。明后期开始活跃于上海以北的北洋航线。道光初年海运漕粮时,按照上海地方文献的说法,在沿海航行的船舶有四种:江苏及上海的船商惯走北洋者,为沙船;船商多由浙江宁波到上海贸易者,能行南北洋,为蜑船;直隶天津及山东一带南行专走北洋者,为卫船;福建船商走南北洋者,为三不象船。(15)同治《上海县志》卷7,《田赋下·海运》,第22页。商船会馆汇拢了在北洋航线上从事贸易的各地航业商人,各地商人以商船会馆为联络集议之所,较为活跃的地域沙船航商大体如次。
(一)江苏船商
1.苏松太通海商。嘉庆初年包世臣说,北洋航线上的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四文”。(16)[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第2页。其拥有的“大号沙船,造价盈万,中号亦需数千”。(17)[清]齐学裘:《见闻续笔》卷2,《禀复魏元煜制军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09页。同时期的无锡人钱泳也说:“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如履平地。”(18)[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四《水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8页。崇明地方志书也描述,其时县民习海道,“东乡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余艘”。(19)民国《崇明县志》卷4,《地理志·风俗》,第2页。同治时,王韬说:“沪之巨商不以积粟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驶至关东运贩油、酒、豆饼等货,每岁往返三四次。”(20)[清]王韬:《瀛壖杂志》卷1,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2页。船主开设船号,是为了揽载客商货物运输,而豆船字号主要是外地客商,特别是山东客商在刘河镇的字号力量最雄。豆船字号如无自有船只,就需向沙船主租赁船只,或者委托沙船主提供船只运输。因此,豆船字号与船商,前者主要从事商品贩运,后者主要提供运输服务,是一种商业运输的合作关系。在乾隆十七年竖立的《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中,具名的东省(即山东、关东)豆船字号范利吉第31家,江省(即江南省)豆船字号江天春、罗聚和等多达59家,江省字号最为繁夥。(21)此碑现存太仓浏河镇天妃宫纪念馆,参见范金民:《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载《史林》2007年第3期。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活跃在上海的沙船字号主,大多来自于上海、南汇、宝山、太仓、常熟、崇明、通州、海门一带。依据嘉庆年间金端表辑的《刘河镇记略》所载,康熙开海后,刘河镇“帆樯林立,江海流通”,先有安徽商人金姓赍资本到刘河创造海船,又有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继起而为海商,胶州则有海商开设中和、利吉字号,莱阳则有海商开设吉顺字号,从事海船运输的,则有吕四的高、姚、包、赵诸大户,其余小户与奉东各口之商贩“如云而起矣”。(22)[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17—18页。豆船字号商家大业大,资本雄厚。如康熙后期的著名海商张与可,或名张羽可,开设元隆海船牙行,家大业多,自有洋船数十只,以百家姓为号,立意置立海船百只,曾经五船同时出海,或一次性出海洋船十几只,出海时以官兵为后盾,有绿营营船保护。行内分工细密,人手众多,有管事之人,料理之人,管帐之人,管船之人,卖货之人,各司其职。(23)[清]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2,《驳勘张元隆船只有无在外逗遛檄为奏闻事》,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8册,第527—529页。类似张与可这种身家的大船商,据人研究,在乾隆、嘉庆年间的上海,主要有“朱王沈郁”四大家。(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9页。这四大家族船商,在清中后期的上海大多常可见到。如前所述,嘉庆十九年无锡海商为商船会馆铸钟鼎,崇明海商为商船会馆建两面看楼。此类船商,大约有船数艘至数十艘,一船造价即达七八千两银,财力看来确实雄厚。常熟人郑光祖《一斑录》载,常熟白茆海口在张墅东十里,“有张用和者,其家素以泛海为业,每至关山东(原注:关东山海关东牛庄等处、山东胶州等处)往来生理。嘉庆二年有船名恒利不归,丧资不少。后道光三年九月又有一船,名祥泰,已达牛庄销货,又置办豆饼、羊皮、水梨等物,回过成山角,遭飓风倒拖太平篮。”(25)[清]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一》,“漂泊异域”条,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17页。是其时实有其人的船商。道光、咸丰年间清廷动用沙船字号海运漕粮,作出重大贡献的上海郁(同发)家、王(文瑞)家、毛(招勋)家、朱(增慎)家,崇明施(彦士)家,蒋炳、陈廷芳、陈鹤、陈荷、季兆缙、季存霖等,都是实力雄厚的大沙船主。(26)参见拙文《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上海开埠前,据人研究,“商业以沙卫船商号为巨擘,豆业更为历史之中心。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惟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全盛时期,计有沙卫船二千数百艘”。(27)陈子彝:《上海百年史料初稿》未刊稿,转引自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其中财力特别雄厚,为航业“商人之领袖”者,就在太仓、上海等港口出任保税行商。如泰兴之季姓者,世代从事关东贸易,其舅万姓住居刘河,季姓即以万复隆投充保税行商。又有昆山之徐姓、杭州之郑姓,“俱以刘地之富家巨室相善,一徐恒豫,一郑复兴,投充保税”。外加在刘河的宁波吴姓,此四姓连名互保,地邻出结,为广大豆船字号提供纳税担保,极为便利。(28)[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18页。熟悉海运事务的当地人,往往充任豆船字号的管理者。如刘河人洪声,颇有声望,执一不二,与牙行商等素所熟悉,就受托代管豆船字号,包括登州帮的永兴、合兴,胶州帮的吉顺、正义、义成,徽州帮的德盛、诚和,海宁的金长和,关东的叶隆昌、黄颐庆,上海的唐永裕、赵泰源,多达12家。因管理事务繁杂,洪声虽大权独揽,调度出入之宜,但仍需聘用太仓金端表、潘端植和徽州闵建侯和三人为帮伙。(29)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122—123页。从船户、字号,到保税行、代管人、帮伙,刘河镇豆粮交易的管理措置配套齐备,分工明确,慎密细致,交易事务相当顺畅便利。
2.江苏海州青口镇船商。青口镇隶属江苏海州赣榆县,接壤山东,滨临海洋,既是淮安门户,又是“商民船只出入往来”的海口要津。(30)漕运总督张大有奏,雍正六年九月十三日,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第349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青口的广袤腹地是豆麦重要产区,青口成为江淮大地豆麦南输江南的重要窗口,青口沿海又擅鱼盐之利,出咸鱼、海米、蛰皮之类海产品,因而当地商人和华北、苏北和江南各地商人汇集于青口周围的上林集和欢墩埠集等集镇。康熙年间开海后,青口“有力者皆置海舶,载豆货由秦望山东出莺游门,顺流扬帆,直抵苏州,并载江南货物回青,贸迁之利最为便民”。(31)嘉庆《赣榆县志》卷1,《坊镇》,第40—41、42页。青口商人于是大力经营江苏沿海豆石业,运抵太仓刘河镇发售,被时人称为两口之间的对渡贸易。这种对渡贸易,官方只允许沿海的赣榆一县所出豆石由青口直接对渡到刘河口输入江南,而其他广袤地区的商品仍应由运河南下,到淮安榷关纳税,但事实上海州全州乃至淮安府属不少地区的豆粮,都不迂远走运河而是直接由海道掺入对渡贸易之中,而青口等地商人就在南北两个口岸开设豆船字号。赣榆地方志书称,开海后,青口成为“水陆商贾会集之区,居庐万家,迄东而西六七里,皆夹河而居”“峨舸大艑往来南北,废著者赢利三倍,市廛甚盛益兴,游手空食之民仰余沥其间者以数千计,称便利矣”。(32)光绪《赣榆县志》卷2,《风俗》,第19、20页。里,与下文的丈、尺为旧制计量单位。山东、山西、江南各地商贾从而贸迁于此,烟火万家。船户和商贾分别建有天后宫,商贾所建天后宫“较宏敞”。(33)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9,《祀典考·赣榆县·天后宫》,第7页。前述乾隆十七年《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中具名的59家“江省商人”,当有不少来自青口。乾、嘉之际,淮安榷关监督刘朴称,青口有豆行73家,油坊13家,腹地安东、海州、沭阳等州县的黄豆、豆饼均从青口出口,山东、山西、江南及青口本镇大贾杂货、布匹铺户51家,以及山东周村布客恒祥各字号8家,所有南来货物,均由此运往山东售销。(34)淮关监督刘朴《咨覆江督苏抚文》,载《续纂淮关统志》卷11,《文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350—351页。嘉、道间,包世臣称:“海州三属,集镇百数,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大。海沭各镇所用布匹、纸张等物,皆由青口转贩。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大,油与豆饼,皆属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来往,不问可知。”(35)[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3,《农三·青口议》,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8—99页。嘉、道年间,嘉定人郁瑞春,就在青口镇开展经营活动,赣榆县人徐经为其撰墓志铭,中称:“青口,沙河入海口也,海道由秦望山东出莺游门,直指太仓州刘家河口。海宇升平,永弛守禁,自江苏迤北濒海居民,例得僦沙船捆载货物,候风潮汐往市他省,视车牛挽运,简利傍蓰,以故青口虽江苏边邑,实为江北都会。吾邑饶于赀而蕲赢羡者,转游北地,以北产输送上海,易南物以给北氓。”墓主体察物理,恒中机要,在青口为人主管业务20余年。(36)[清]徐经:《皇清诰封奉直大夫布政司经历加二级国子监生啸农郁君(瑞春)墓志铭》,载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嘉定博物馆编:《嘉定碑刻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02页。道光中叶两淮盐场改行票盐后,富商大侩麇集青口,自夏至秋,直至秋粮上市,“吴越燕齐海舶衔尾而至,百货杂遝,金钱浩穰。于是宫室车舆日用服食之需,赛神会饮俳优倡乐之事,竞鹜侈丽,以为娱观耳目”,赣榆县东之民以海谋生,“豆以造油,其滓为饼,利以为业者,四境相望,行贩取赢,往往致富”。(37)光绪《赣榆县志》卷2,《风俗》,第6页。青口镇更为殷阜胜地,“闾阎扑地,尘雾幕空,交衢杂五方之人,哄市臭千钧之鲍,东来贿迁,盖无日无之”。(38)光绪《赣榆县志》卷3,《集镇》,第17页。豆粮出口地青口的繁盛,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岸刘河镇的豆粮交易的繁盛景象。
嘉庆十八年刘河淤塞,豆船转口停泊上海,青口镇字号商人乃与徽州商人公议发起饼油山货公积金。道光二年以4 000千钱在大东门外契当住房一所,建为祝其公所,奉祀关帝和天后。三年后加价4 000千钱,转当为买,在上海县衙备案。道光十三年,生意兴盛,公所提取公积金4 000千钱归青口放赈。咸丰兵燹,公所被焚,内部管理混乱,帐册散失。直到光绪十五年才经整顿,恢复管理。(39)《青口客商起饼油山货积建公所碑》,光绪元年;《上海县为祝其公所事务归南庄值年告示碑》,光绪十二年十二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04—305、306—307页。可见嘉、道时期为青口商人的全盛时期,咸丰战乱后即渐趋衰落。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一年中,据《中外日报》报道,北洋沿线各口岸抵达上海南市的沙船共为728只,而由青口到者最多,达221只,由莱阳到者其次,为219只,两口沙船占总数的60%以上。(40)参见[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第135—136页。在清代比例最重的豆粮对渡贸易中,青口商人当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3.江苏淮扬船商。该帮船商在上海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公所。光绪二十六年淮扬公所同人联名控告船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陈某某、朱书万等44人。(41)《松江府为禁船行管帮私收埠规告示碑》,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73—75页。
(二)山东、关东船商
雍正十一年(1734),新任两江总督赵弘恩,即与山东巡抚商定,山东所属各地豆货:“查明某某府州所属豆货来江可由内河行走,某某府州所属豆货不便经由内河必须从海洋运贩,除由内河行走者听其自便外,其由海运者,即令彼省地方海口各官查明何处商客、系何船户,开具姓名年貌、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货数目、出口年月日,径行详咨江省海关,并一面详明东省抚宪移咨江省,江省并海关于进口时查验明白,咨复东省,互相稽察。……如有东省豆船到岸,立即令其入口。……如是,则东省豆货出口入口俱有照对,不必禁其海运,而偷漏之弊庶乎可免矣。”(42)[清]赵弘恩:《玉华堂集·两江檄稿》卷下,《为密行咨商事》,景印雍正本,第21—22页。山东大部以及关东全部豆货都由海运南下,因而山东、关东商人凭藉地利之便,大力从事北洋贸易。
山东船商在上海活动较早。据碑文载,早在顺治时,山东商人即联合关东商人,两帮集资在上海县城西置义田50余亩,以为葬埋公地。(43)《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道光五年七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页。亩,旧制计量单位。康熙开海不久,山东、关东、山西海商和安徽、浙江海宁以及江苏上海、崇明、昆山和苏北青口、通州、泰州等地商人,就纷纷在刘河设立豆货、杂货字号,即金端表《刘河镇记略》所说“东省、徽籍以及通属各商设有长庄字号”。山东胶州先有海商开设中和、利吉字号,登州府莱阳则有海商开设吉顺字号,莱州府潍县(原作汇,疑误——作者)则有恒利。后来仅山东登州帮商人就设有永兴、合兴等十六七家字号,胶州帮商人更设有吉顺、正义、义成等字号20余家,徽州帮有德盛、诚和等字号,海宁商人有金长和字号,关东商人有叶隆昌、黄颐庆等字号,上海商人有唐永裕、赵泰源等字号。(44)[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17、19、23页。在各省商人中,常年到太仓的,“惟关、山东商船居多”。(45)[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22页。当时定例,南下的山东、关东以及江苏赣榆县青口镇等地豆船,必须在太仓刘河口收泊,定制青口豆货可以对渡刘河镇粜卖,但屡开屡禁,直到乾隆五年再次恢复趋于稳定。其间豆船字号在刘河镇开张极为兴盛。乾隆十七年,多达范利吉、许复兴等31家。山东豆船字号,不但在刘河数量众多,而且实力最为雄厚。当时字号将交易所得银两定期解往苏州存贮,为了确保驶往苏州城的标船的安全,山东豆船字号禀报镇洋县,通详江苏各大宪,从布政司衙门申领了鸟枪、火药、兵器,又特意从山东老家聘请来拳棒教师,专程押运,其中尤以山东登州、胶州的两帮字号实力最为雄厚,“立钱票船四只,以八为期”,打出“奉宪护送”的旗号,保护标银,其气派和声势为当时民间商业运输所罕见。(46)[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19—20页。按照地方文献的说法,“乾隆二十年之后,刘口之船益多”“自此以后,商民乐业,船如蜂拥而来,行号日增”。(47)[清]金端表:《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第21、22页。前述道光初年的《刘河镇记略》中提到,由人代为经营管理的山东字号有永兴、合兴、吉顺、正义、义成等号。
这些山东的豆船字号,嘉庆年间起,当与来自其他地方的豆船字号一样,先后转移到了上海,在商船会馆的旗帜下,与各地豆船字号主展开商业竞争。道光七年,商船集议山东关东各口贸易规条,在规条上作出承诺的,有(山)西帮商人胡升恒等4号,胶帮商人孙丰聚等6号,登帮商人初元丰等7号,文莱帮商人王元兴等5号,诸城帮商人陈广盛等2号,共计24号商行。(48)《上海县西帮商行集议规条碑》,道光七年,载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9年,第484页。单就数量而言,其时山东商人占有绝对优势。道光五年,山东登州府方爱仁,济南府孟广钰,沂州府宋鸿志等广记、永春、六吉、益顺等商号联衔清理,丈量地亩为25亩多,呈文备案,上海县立碑保护。(49)《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道光五年七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4页。道光二十六年,山东商人广记、六吉等21家,又联名创建会馆,并先在宝山县境内购置田22亩备造登莱公所,南市公估局等首先输助银3 000两,怡顺昌等3家捐银万余两,众商捐银6万多两。鸦片战争爆发,中经太平天国,山东商人大多避难航海而归,势力大损。光绪后期,山东商帮在上海贸易者复归众多,前往清理义地,地亩数基本仍前。(50)《山东至道义堂条规》,光绪三十年稿本。《山东至道义堂条规·禀为清理义冢求请过户承粮事》载:“窃商等查上海县西门外,向有山东义冢一区,计承粮地五十余亩。后因兵燹,各商回籍,司事星散,地粮均无人问,即为他人代管。近年商等在沪贸易人多,前往清理。”自光绪二十九年起建造山东会馆,于三十二年完工。会馆落成,制定规则50条,对会馆运营作出详尽具体规定。会馆创办时,捐款者有关税帮、公估帮、洋货帮、杂货帮、祥字帮、黄县帮、沙河帮、福绸帮、丝业帮、铁货帮、孤山帮、仁川帮、营口帮、崴口帮、银钱帮、周村帮、青岛帮、即墨帮、胶州帮、元釜山帮、潍县帮、洋杂货帮,共22个地域帮或行业帮,商号多达91家。其中关税帮商号最多,为15家。后来捐款者中又有涛雒帮。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有谦祥益等280余家商号捐款。(51)宣统《山东至道堂征信录》,转引自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80—890页。到光绪时,山东人自称在上海经商已二百余年。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商人建立会馆,到三十二年完工。(52)《创修山东会馆碑》,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95—196页。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家”,一时之间集至“数万之谱”,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力。(53)《鲁人之大奋发》,载《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第6页;《山东河南绸业公所助饷启事》,载《申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1版;分别转引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次印刷本,第636、638页。诚然,由上述帮别以及捐款的商号,可知晚清时期航商在山东商帮中的势力已相当弱小,其地位已无足轻重。
(三)浙江宁波船商
宁波商人是鸦片战争后上海人数最多、实力最为雄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域商帮,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又以买办、金融、轮运、成衣、木业制造乃至进出口业等最为出名,其实观其形成和初起,宁波商人是因从事沿海运输起家并日臻发达的。在清代前期的上海和沿海商品流通中,宁波商人从事船运业极为活跃。宁波地方文献称:“航业为岛民所特长,南北运客载货之海舶,邑人多营之。”(54)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第十六》,“风俗·航业”,第50页。后人追溯,开埠前,上海著名的沙船字号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惟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55)陈子彝:《上海百年史料初稿·沙卫船商号为上海商业巨擘》,第5页。浙江按察使段光清记,咸丰四年,由镇海出口,只走北洋的宁波北号商船有一百七八十号,其规模,“北号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余号,中商一家七八号,小商一家二三号”。(56)[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1页。这些专门从事北洋贸易的宁波商船,自然也会在上海停泊,在商船会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咸丰、同治年间,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帆船航运业也达到了极盛。《申报》称,“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数百号,每年统计进口沙宁船何止六七八千”(57)《申报》光绪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光绪中,宁波人自称:“吾郡□图之利,以北洋商舶为最钜。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航天万里,上下交资。”(58)[清]杨鸿元:《甬东天后宫碑铭》,转见于《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62页。北洋航运是关系宁波经济最大者。宁波的三个天后宫,一为闽人所建,一为南洋商舶所建,而其中由北洋商舶所建者,“规模宏敞,视东门外旧庙有过之”,始建于道光三十年,落成于咸丰三年,费钱十万千钱,“户捐者什一,船捐者什九”,主要由船商捐款建成,(59)[清]杨鸿元:《甬东天后宫碑铭》,转见于《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63页。直到其时,船商还是宁波商人的中坚。同治五年(1866),上海的宁波船户始创兰盆会,到光绪三十三年助款加入四明公所。(60)《头摆渡码头百官船户兰盆会助款入四明公所碑》,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60页。光绪后期,宁波帮中之内河小轮业成立永安会,举办同业斋醮,捐款者有90余人,宣统二年(1910)并入四明公所。(61)《内河小轮业永安会入四明公所碑》,宣统二年,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06—408页。这些航业人员单独成立同业公所,可见宁波航业在上海的实力。
(四)其他地域船商
在上海活跃的海商,江苏和山东、关东三大支商人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地域商人。如徽州商,如前所述,依据嘉庆年间金端表辑的《刘河镇记略》所载,康熙开海后,刘河镇“帆樯林立,江海流通”,先有安徽商人金姓赍资本到刘河创造海船,后有徽州帮的德盛、诚和等字号,说明活跃在江南的徽商,在航运业中也不乏其身影,而且创业较早。乾隆时有江文彬,世居歙县,高祖开始迁到苏州。其父国正,“尝置洋船若干艘,估客雇船出洋则收其直”,是大船主。后因沙船运输遇风漂没,反遭官员勒索而得病丧身。但到江文彬“中年以后复致饶给”,姻族亲党“待以举火者恒数十家,负之者或累数千家”,家大业大,看来仍是从事沙船运输的大业主。(62)[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37,《江慎斋墓志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405、406页。再如浙江商人,康熙开海后,海宁商人在太仓有金长和字号。如山西商人,道光初年,上海有西帮商人胡升恒等4号,也有一定实力。
在上海的船商和从事油、豆、豆饼业交易的店家、行家、经纪人,就在商船会馆等同业组织内开展活动。而各地海商或海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上海的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萃秀堂又称东园,在上海县庙豫园,建于道光年间。咸丰三年受战火遭损。十年,驻扎西兵,残毁尤甚。同治七年承粮管业,地基广达十余亩。同年大加修葺,禀县给谕,勒石保护,“以萃秀为二十一业之领袖”。萃秀堂外有三穗堂、仰山堂、格思堂和神尺堂四间议事厅。堂中亭榭池沼,回廊曲折,均极园林之胜,而大假山层峦叠嶂,尤为县中独有之境。光绪三十二年,与米业合组之豆米业小学校分设于此。堂馆所需经费于代客买卖时抽取货捐,豆油每石银1厘8毫,豆饼每片银2毫8忽,后因轮船盛行,沙船锐减,捐数寥寥,于是同业每月捐银1两。公所原由司月轮管,清末推举董事一人会同6家司月办事。(63)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第6页。
船商与豆业议价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俗称豆市,在豆市街万瑞弄。原来租用市房,光绪七年购屋,改建对照厅6间。(64)民国《上海县续志》卷3,《建置下·会馆公所》,第6—7页。
总体而言,清代以太仓刘河和上海商船会馆为经营场所,专营北洋商业航运的商人,群体实力最为雄厚者,地位最为突出者,毫无疑问是苏松太通为主体的江苏商人,其次是山东、关东商人,浙江宁波、海宁商人,安徽和山西等地商人也有一定实力。
三、江浙商人的北洋航运贸易实例
清前期,上海集中了江南所产棉布和百货,山东、关东盛产大豆和瓜子等货,从而北洋航线形成南布和北豆的大规模对流贸易盛况。康熙二十三年,礼部称,“今海禁已开,各省人民海上行走者甚多”。清代前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贸易,极为兴盛。雍正四年,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报,山东青、登、莱三府沿海地方,“土性硗瘦,种豆之处十居六七,每年江苏、天津等处客商载货来东,率多买豆,由内洋运回,售于腐店、油坊,兼以制饼肥田,所用甚广。……而本地山路崎岖,车运艰难,不能载往他郡销售,全赖出海流通,民间正藉此项粜籴,上之以办国课,下之以资日用”。(65)山东巡抚陈世倌奏,雍正四年八月四日,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1978年,第409页。稍后,山东巡抚岳濬又奏报:“查豆船一项,由东省贩运江南者尚少,惟江南贩货来东,发卖之后即买青、白二豆带回江省者拾居陆柒。”(66)山东巡抚岳濬奏,雍正十二年八月初八日,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78页。康熙后期山东胶州地方文献也称:“胶滨于海,故三江两浙八闽之商咸以其货舽浮舶泛而来。”(67)道光《胶州志》卷39,《考三·金石》,“重修小桥堤岸记文”,第30页。关东豆粮最大的出口是锦州,为五方杂处之区,“鼓枻飞樯,经营其地者多旅,惟江浙、福建两帮颇称盛焉”。雍正三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两帮商人建成天后宫。(68)《乾隆二十八年安澜郎补天碑》,载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78页。乾隆十六年,山海关监督御史高诚奏,锦州“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惟视其收成之丰歉以定税银之多寡”。(69)山海关监督御史高诚奏,乾隆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1982年,第399页。后来,锦州南向海运贸易更加兴旺。锦州城西南70里的天桥厂海口,俗呼西海口,为帆船商港,“向系闽、广、江、浙等省沙、鸟等船前来贸易之区,铺户较多,是为极要”(70)盛京将军庆祺金州副都统希拉布:《奏沿海布置情形折》,咸丰八年五月初十日,载贾植等:《筹办夷务始末》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34页。,“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口输入。其出口货,先惟油、粮,以大豆为大宗”(71)民国《锦县志略》卷13,《交通·商港·天桥厂海口》,第4页。。对于北洋航线上的这种贸易盛况,既有研究多从沿海贸易角度着力,而于上海航运中心角度关注不多。今主要利用松浦章先生等人搜辑的资料,佐以其它相关材料,胪列相关事例如次,以充实航运内容。
1.康熙三十三年,上海船主吴圣山、舵工、总管、水手、船客共14人,八月十八日由上海县开船,因途中遇到强盗,延至九月五日抵达山东胶州。在该地买进腌猪后,十一月二十日归航卖货,洋中遭风,漂到日本。(72)《华夷变态》卷22,东京东洋文库,1958年,第1711—1713页。
2.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六日,上海县沙船主张元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两,前往辽东贸易。(73)[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4册,第12页。
3.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华亭县船户张永升,揽装茶叶布碗等货由上海开船,前往关东贸易,到通州廖家嘴,九月十八日遭海盗抢劫。该船有舵工水手23人,系福建籍贯,又有水手2人系宁波人,搭船福建人余廷文等9人,客商王熙安、邹吉、王文卿、孙三合、赵直、施元生等6人。所需照票由上海牙行张御科即张羽可即张元隆领取。(74)[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第14—16页。
4.雍正十年,宝山县船户顾洪顺等15人,坐驾沙船一只,于雍正十年六月二十日,在刘河装载杂货,往山东发卖,于九月十六日出口,十月十二日在通州吕四场放洋,十五日陡遇大风,后漂到日本德岛。(75)《历代宝案》第2集第19卷,台北:台湾大学印行,1972年,第2167页。
5.南通州夏一周等16人,皆是亲戚,“常以船为各处商人之所雇,往来山东地方,受雇贳为生,而无身役矣”“年年到山东,装载货物往来”。雍正十年正月二十日,徽州商人吴仁则雇其所驾之船,装载棉花253包,自南通州开船前往关东;正月二十九日到山东莱阳县卸下;二月二十八日自莱阳发船;三月二十八日转到关东南金州地方,又有苏州府所管太仓州商人周豹文雇其船,装炭380担,五月十八日自南金州开船;六月十七日到山东宝定府所管天津卫卸下,而后又有商人徐梦祥也雇其船,到山东大山口海丰县,买大枣287石1斗装载,十月十二日自海丰县发船;返航之际,十四日在大洋中猝遇恶风,漂到朝鲜全罗道(王尔)岛郡。(76)《备边司誊录》第9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41—43页。
6.乾隆十四年,镇洋县商人许世泰等14人,坐驾沙船一只,于十月初九日由镇洋出口,前往山东胶州,装载黄豆及紫草梗36包、豆油22篓,十一月十八日胶州出口,后遭风漂到日本伊江地方。(77)《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89页。
7.乾隆十四年,崇明县船户顾君如等8人,往山东装载白豆、毛猪等物,十一月十八日在彼地开洋,遭风漂到琉球胜连地方。(78)《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52页。
8.乾隆十四年,通州船户彭世恒等12人连同客商2人,往山东胶州装载白豆、盐猪、紫草等物,从彼地出口,仍赴苏州府,十一月十九日遭西北风,后漂到琉球胜连地方。(79)《历代宝案》第2集第30卷,第2554页;《船户吴永盛等飘至琉球残件》,载《明清史料》庚编第4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339—340页。
9.乾隆十四年,苏州府常熟县船户陶寿及商人17人,在江南装载生葁,到天津卫发卖,转往关东大庄河口买黄豆,前到山东登州府放洋,十一月二十二日漂到日本永良部岛。(80)《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89页。
10.乾隆十四年,镇洋县船户邓福临坐驾沙船一只,前到关东西锦州买黄豆、瓜子,转到山东放洋,遭风,十一月二十四日漂到日本德岛。(81)《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88页。
11.乾隆十四年,常熟县商人白世芸雇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人的船,“载几担豆子,要到江南去卖,故此在他船上”,十一月二十九日漂着在日本奄美大岛。(82)《白姓官话》,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第53页。
12.乾隆十四年,常熟县船户沈惠等11人连同常熟商人1人,装载青鱼往关东南锦州买豆,转到山东,放洋遭风,十二月间漂到日本德岛。(83)《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88页。
13.乾隆十四年,镇洋县商人船户张常盛等28人,驾沙船一只,在刘河口开船,往山东胶州买豆、猪、豆油、紫草等物,十二月十八日由胶州开船,遭风漂到日本运天地方。(84)《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580页。
14.乾隆十四年,苏州府常熟县船户瞿张顺等13人,十一月初七日由山东开船,欲往苏州府刘河贸易,行到洋中遭风,后到胶州,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漂到日本长崎。(85)《历代宝案》第2集第31卷,第2622页。
15.乾隆十七年,通州船户崔长顺及商人共计23人,十月初七日由通州吕四场出港,前往胶州,装载客货,十一月二十一日从胶州出港,要往苏州府交卸货物。二十三日遭风,后来漂到琉球八重山地方。(86)《历代宝案》第2集第34卷,第2710页。
16.乾隆二十七年,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孙合兴船19人,连同客商三人,其中赵禹廷与潘长官是苏州府人,于德铨是绍兴府人,六月二十四日自家离发,七月初二日“在上海县装载货物”,九月二十五日至山东石岛,猝遇狂风,十月二日漂到朝鲜古群山。(87)《备边司謄录》第13册,第819页,载[日]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っぃて》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7辑,1984年,第56页。
17.常州府无锡县人孙如松,一向在通州、崇明一带帮驾海船为业,积有工资。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央萧仁官作保银130两,向丹阳县人沈盛赁沙船揽载客货。船上原有舵工郭上林,又雇仇献章写账,曹蚊、朱七、张连昌做水手。闻得海阳岛装青鱼,是按股分鱼,颇有利息。次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海阳岛揽载宁波客人翁秉奇青鱼十五万个,讲明二八分鱼,运往关东锦州发卖。五月初五日到复州阻风,遇见素相熟识之南通州人陈二南,搭船回家。适乏盘费,向陈二南件银十六两。五月十二日到锦州,投汪永茂鱼行。因鱼贱难卖,翁秉奇与仇献章商议,将鱼雇车装出口外塔子沟、三座塔各地方销卖。闰七月回锦州。(88)《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8辑,1984年,第667—668页。
18.乾隆三十四年,通州吕四场44号商船船户姚恒顺等14人,十月二十四日从太仓州镇洋县装载南货出口,十二月初六日到山东胶州口停泊,在胶揽装腌猪等货,十二月十二日开洋,要往镇洋县刘河口交卸,次日在洋遇风,漂到琉球国八重山地方。(89)《历代宝案》第2集第54卷,第3265页。
19.乾隆三十九年,太仓崇明县杨难等10人,八月二十七日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方,换买黄豆,同月十四日回到定山地方,大洋中猝遇西北风,十一月初五日漂到朝鲜。(90)《备边司誊录》第15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59—60页。
20.太仓州崇明县船商共15人,其中船户1人,船工1人,水手11人,住在苏州府的客商唐友凡与朱于龙2人,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六日自崇明县开船,往天津府买枣子1 000石、鲤鱼千余担,十月十八日还向本乡,中途遭风,飘到朝鲜。(91)《备边司誊录》第15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67—68页。
21.乾隆四十九年,苏州府元和县商船船户蒋隆顺等20人连同福建莆田县客商5人,闰三月二十二日,为本省镇江府黄姓客商所雇,装载生姜,四月三十日前到直隶天津府交卸。又揽得天津府郝姓客商,六月十八日前到关东牛庄县装载粮米,八月初五日回到天津府交卸。又揽得山东登州府黄县石姓客商装香末包,十月十五日去到黄县交卸。在那里过年后,又揽得黄县霍姓客商,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到关东装载粮米,三月十八日回到黄县交卸。“原客催原船”,五月十八日前到关东装载粮米,六月十二日往到山东武定府利津县交卸。又“本客在该地雇本船”,七月二十六日前到关东装载粮米,九月初七日回到天津府交卸。又将本船雇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商人游华利等,连客商共计25人,十月二十三日往到山东武定府海丰县装载枣子,要到浙江宁波府交卸。十一月二十日前到关东小平岛候风,十二月初八日开洋,忽遭狂风,漂到琉球国属岛太平山地方。(92)《历代宝案》第2集第73卷,第3709—3710页。
22.乾隆六十年四月,江苏通州张子华船载运客货开往关东,途中遭风沉没。(93)《乾隆嘉庆案件批底·惨死无尸等事》,抄本一册。
23.嘉庆四年,南通州吕四场舵工等7人,带了住在苏州的宋姓人的二百两银子,于十二月十八日放船,往山东莱阳府买黄豆,二日后遭风漂流。(94)《备边司誊录》第19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03—104页。
24.嘉庆五年,通州549号商船沈发泰等10人,十一月间在上海装载纸货,要到山东地方贸易,十二月十五日在山东开船,十七日遭风,次年正月初八日漂到琉球国大岛地方。(95)《历代宝案》第2集第92卷,第4479页。
25.嘉庆五年,通州舵工唐明山等6人,十二月十八日放船,往山东省莱阳府买黄豆,二十日遭风,漂到朝鲜在远岛。(96)《备边司誊录》第192册,载[日]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っぃて》下,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8辑,1985年,第34—35页。
26.嘉庆六年,通州613号季长义船,十一月二十八日放洋,遇西北风,漂到日本纪州。(97)[日]松浦章:《清代沿海商船の纪州漂着にっぃて》,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20辑,1987年,第49页。
27.嘉庆九年,太仓州宝山县叶合盛船船户傅鉴周和同县舵工朱盛章及水手19人,有客商上海人王培照,七月十六日在上海吴淞口,装载了徽州府茶商冯有达的茶叶835包,八月初一日止泊天津。卸下茶包,因约载客商上海县人王培照的红枣,转向山东武定府海丰县,装枣260担,十月二十一日回船,要回本乡。在海人遭风,漂到朝鲜。(98)《备边司誊录》第19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06—109页;参见《礼部题本》,载《明清史料》庚编第五本,第473页。
28.嘉庆十二年,南通县舵工龚风来船共16人,其中舵工1人,水手15人,12人是南通州人,2人是宝山县人,崇明县和镇洋县人各1人,应元和县彭际兴商船之雇,九月十二日在上海载篁竹发船,十八日到南通州,十月初三日自南通吕四港口再次发船向山东胶州。初五日遇大风,后漂流到朝鲜。(99)《备边司誊录》第20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22—125页。
29.嘉庆十三年,镇洋县俞富南等17人,八月十七日上洋出口等风,九月十一日开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貔子窝,在永丰店贸易,装载恒昌号高粱580石。十月二十六日放洋。二十八日遭风,次年三月一日漂到琉球国德岛地方。(100)《历代宝案》第2集第107卷,第5014页。
30.嘉庆十三年,通州船主庄蔚廷等20人,装载纸木等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县吴淞口出口,要到山东、青口贸易。因风不顺,在洋损坏篷舵锚绳,十一月二十八日漂到琉球山南地方。(101)《历代宝案》第2集第107卷,第5012页。
31.嘉庆十三年,镇洋县舵工水手陈仲林等13人,十月初五日,自江南往关东金州。十一月初七日载黄豆还向江南,遭风漂到朝鲜小落月岛。船中所载黄豆360石外,又有海参400斤。(102)《备边司誊录》第20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13页。
32.嘉庆十三年,崇明县郁长发船舵工水手11人,“于李裕昌行保禀,往山东生利”,于十一月初六日放洋,遇风漂到日本。该船舵工水手绝大部分是崇明县人,2人是上海等县人,可装米22包,当时装载子花19包、花衣3包等,至山东“莱州府办油、豆、猪肉等,并买花合桃腌等物”。(103)《江南商话》,载[日]松浦章:《文化五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郁长发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四》,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8、16、18页。
33.嘉庆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宁波船头严性被坐17人从上海开船,装纸前往关东,买黍,雇水手一人,共18人,十月二日回船。(104)《长崎文献丛书》第1集第4卷,《续长崎实录大成》,长崎:长崎文献社,1974年,第209页。
34.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商人朱大昌,雇得通州吕泗彭洪庆船,共12人,行到关东皮子窝客载豆子750仓石,五月十二日南返,二十三日在海上出事。(105)《各司誊录》第7册,载[日]松浦章:《清代江南沙船航运业史研究》,第125、129页。
35.嘉庆二十五年,崇明县施绍修船共17人,往山东装豆,于十一月初八日在石岛放洋,至十二日遭风,漂到日本。(106)[日]松浦章:《清代沿海商船の纪州漂着にっぃて》,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20辑,1987年,第50页。
36.道光元年九月六日,太仓州崇明县船头朱聚南,乘坐12人,装载棉花前往山东,交易油渣,十二月初一日归航,于洋中遭风,漂到日本萨摩国阿久根村一带海面。(107)[日]松浦章:《17—19世纪における漂着中国船资料よりみた清代海上贸易史の研究》,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第3—4页。
37.道光三年,镇江府丹阳县潘明显14人,正月二十日,于赣榆县青口浦买豆饼,二月二十四日往上海县发卖豆饼。八月初十往关东大庄河,收买青豆975包。十月初九日,要回上海县。开洋后遇大风。(108)《备边司誊录》第21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50—151页。
38.道光六年,通州人舵工王群芳等,驾苏州府元和县蒋全泰船14人,八月三十日由吴淞口出口,到永泰沙装载货物,要到山东莱阳县交卸。十月初二日由该沙开船,在洋遇风,十二月二十三日漂到琉球奇界岛地方。(109)《历代宝案》第2集第144卷,第5991页。
39.道光六年,苏州府元和县蒋元利商船,十一月十六日由江南放洋往北贸易,即往山东装豆饼、豆油、豆,遇逢西北风盛大,遇难飘到日本土佐。(110)《送舟周录》,载[日]松浦章编著:《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蒋元利资料》,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第8页。
40.道光六年,苏州府昆山县昆字27号陈福利商船(船主陈继松,并不在船)20人,十一月在上海县装载货物,要到山东胶州口交卸。初十日出口,到达崇明。十六日崇明放洋,在洋遇风,十二月二十三日漂到琉球国归仁地方。所载物品主要是各色纸、糖果、板笋、麻布、扣布、白糖、药材、书籍、蜜饯、茶叶等。(111)《历代宝案》第2集第144卷,第5994页。
41.道光七年春,南通州蒋元利船舵工王玉堂代驾彭耀曾共计16名,往北地贸易,装载生姜、纸、棉花、木、竹及零星窑货,途中遇风,漂到城南浦户港。(112)《送舟周录》自叙,载[日]松浦章编著:《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蒋元利资料》,第5—6、111页。(船主蒋炳,船有十九只,曰蒋元亨,曰蒋元利,曰蒋元贞,曰蒋恒生,曰蒋泰生,曰蒋肇生,曰蒋聿生,曰蒋太生,曰蒋德生,曰蒋天生,曰蒋同生,曰蒋宁泰,曰蒋荣泰,曰蒋复泰,曰蒋震泰,曰蒋全泰,曰蒋福安,曰蒋福康,曰蒋大昌。外有两只,装木贸易,蒋福源、蒋福来。船工都是江苏人,如靖江县一人、上海县二人,其余均为通州吕四场等处人。)
42.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苏州船主袁翼天袁万利号商船14人,持上海森盛号主郁竹泉信书,从上海出口,前往关东,十八日在关东铁岭关前往牛庄,装载沈汶泰的豆货,二十二十日遭风。该船有舵工、二舵、耆民、水手11人,都住上海和吕泗。(113)《各司誊录》第7册,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航运业史研究》,第131—133页。
43.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苏州元和县船户诸元茂船,从上海吴淞口放洋,往牛庄装豆。接近岑山时遭遇大风。舵工、水手共13人,全是元和县人(坐客是元吉号的吴乐山)。(114)《各司誊录》第7册,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航运业史研究》,第137、139页。
44.道光二十五年,海州赣榆县商人许振宽等8人,坐驾范复兴牌照商船,十月初六日在青口开船,即日抵于浙江,买载花生、青饼等项,二十日在该地开船,要回本籍,在洋遭风,漂到琉球与那国洋面。(115)《历代宝案》第2集第182卷,第7519页。
45.道光二十七年,周乾太商船,揽装上海三益等号布、纸等货往牛庄交卸,九月初八日驶至黑连沙尾洋面,猝遇盗船,劫去货物。(116)江苏巡抚陆建瀛题,转引自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1辑,第3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76种,1983年,第211页。
46.道光二十七年,崇明县瞿元亨商船,由上海装运吉祥庆等字号布匹、棉花、制钱等货往牛庄交卸,九月十一日驶至佘山对西黑沙潋头东南洋面,被盗船劫去货物。(117)江苏巡抚陆建瀛题,转引自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1辑,第3册,第222页。
47.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通州吕泗船舵工宗寿桃等11人,驾驶海州赣榆县船商孙同德船,为山东商人装货,从吴淞口开船,二十四日在通州候风,十一月十一日往山东,遭遇大风,漂到朝鲜。(118)《各司誊录》第9册,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航运业史研究》,第140—143页。
48.咸丰四年,昆山县、上海和崇明县舵工马得华和耆民、副舵共23人,装载漕粮到天津交卸,回到烟台,装山东聊城乌枣客商郭德章、杜佩珍等8人之货,十二月初一日开船,遇风漂流。(119)《备边司誊录》第24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72—174页。
49.咸丰四年,崇明县船主陆载岩等11人,驾驶本县竺格顺牌照船一只,十月初三日装载棉花、棉布等件,在新开港放洋。二十六日到山东莱阳县贸易,置买菜油、花生、麦面等件。十一月十九日该处开船,二十四日遇风,漂到琉球国叶壁山地方。(120)《历代宝案》第2集第197卷,第8243页。
50.咸丰四年,南通州海门县沙太寿船11人,其中舵工、舵副1人、水手9人,装豆饼、豆油,十一月二十日即墨县金口开洋,洋中遇飓风,漂到日本折生迫港。(121)《漂流小唐船一件》,载[日]松浦章编著:《安政二·三年漂流小唐船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八》,关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第181页。
51.咸丰五年,崇明县宋福盛之344号商船19人,在山东买豆4 400石,十一月十九日从右石岛开洋,遇风破损,次年正月十四日漂到日本。(122)《漂流小唐船一件》,载[日]松浦章编著:《安政二·三年漂流小唐船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八》,第181页。
52.咸丰八年,上海县人赵汝林等21名,驾了船主郁泰峰的孙寿福船号的船,往奉天府装了王子骥、周萃涛两人所管的价银数千两的黄豆、小米、芝麻、瓜子、猪肉、牛油、胡桃油等物,转回江南,十月二十三日到山东后山,忽遇大风漂流。该船船号孙寿福,船主郁恭峰。答:“担数写在票上,价银为数千两,便子王子骥、周萃涛两人所管。”(123)《备边司誊录》第25册,载[日]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78—179页。
上列52例,除不明海运者地籍的2例外,太仓州16例,南通州14例,苏州府9例,松江府4例,常州、海州和宁波各2例,镇江府丹阳县1例。毫无疑问,集中在长江出海口周围各地。此外,松浦章先生统计了1644—1885年240余年间的240例漂到朝鲜半岛的中国船,据其统计,可知来自江苏82例,山东72例,福建34例,关东30例,浙江9例,广东数例,直隶、山西零星几例,江苏最多。江苏省中,来自太仓州25例,南通州23例,松江府16例,苏州府13例,镇江府4例,常州武进县1例。两类统计相当吻合。很明显,从事北洋航业的商人,在各地域商人中江苏商人最多,而绝大部分又来自于苏、松、太、通地区。其次是山东商人,再次是福建商人和关东商人。(124)[日]松浦章:《李朝时代における漂着中国船の一资料》,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15辑,1982年3月。上列海难事例,印证了乾隆年间太仓《海商碑》所记,以上海为南端的北洋航线,主要是由江苏、山东、关东沿海商人经营的,也印证了嘉庆时人关于沙船商势力最大者是崇明、太仓、南通等地人的说法。船工也是如此。如例5南通州船工夏一周等16人,“皆是亲戚,同居一邑之内”。例25通州舵工唐明山等6人,均是南通州吕四场人。例27嘉庆十年太仓州傅鉴周等21人,均是太仓州宝山县人。例28南通州舵工龚凤来等16人,“都是江南省人,而十二人苏州府所属南通州人,二人太仓州所属宝山县,一人崇明县人,一人镇洋县人”“各自为商,同往一处”。例31镇洋县陈仲林等13人,“都是太仓州镇洋县人”。例39苏州府元和县蒋元利商船,船工是靖江县1人、上海县2人,其余均为通州吕四场等处人。例42,舵工和水手11人,都住上海和吕四。例48,昆山县舵工马得华等23人,8人来自上海县,15人来自崇明县。例52上海县赵汝林等21人,“都是江南省松江府上海县民家”。
商船前往的目的地,在已明确的50例中,前往山东特别是胶州者最多,为27例,占全部事例的一半以上;前往关东者17例,占全部事例的三分之一。前往这两个地区的商船,都是购买货物。前往天津者4例,是为卸货。由北向南者2例,也是购货后返程。如此则呈现出货物流向的特点,关东、山东豆货等商品源源南下,而江南少量商品经由天津入口输向华北。清代江浙商人北洋贸易活动以关东和山东为商品采购地,而以天津为南方商品的卸货地,这与福建、广东商人的北洋贸易的商品流向是相同的。
上述航向,有时并非直航贯穿全过程,也不以一个地点为目的地,而是因为采购商品的需要,或应商客的要求,往往先后辗转几个地方。如例5,南通周姓船只,原来常应各地商人雇请,往来山东地方装载货物,雍正十年却应徽州商人雇请,在南通装载棉花,到山东莱阳县卸下,再转到关东。在关东又装上太仓州商人的炭货,到天津卸下,又应商人徐梦祥雇请,到山东海丰县装大枣然后返航。例27,傅鉴周和同县舵工朱盛章船,嘉庆十年七月载有客商上海人王培照,七月十六日在上海吴淞口,有上海商人王培照装载了徽州府茶商冯有达的茶叶835包,开到天津卸下茶包,又转向山东武定府海丰县,装运王培照所买枣子260担,开船要回本乡。例21更为繁复。苏州府元和县蒋隆顺船,本已搭载了福建莆田县客商5人,后又应镇江府黄姓客商所雇装载生姜,到直隶天津府交卸。在天津,揽得天津府郝姓客商,前往关东牛庄县装载粮米,回到天津府交卸。在天津,再次揽得山东登州府黄县石姓客商装香末包,运到黄县交卸。在黄县,又揽得当地霍姓客商前往关东装载粮米,再次回到黄县交卸。然后应原客再次雇请,再次前往关东装载粮米,运到山东武定府利津县交卸。在那里,第三次应原客雇请,前往关东装载粮米,回到天津府交卸。而后又应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商人游华利等雇请,前往山东武定府海丰县装载枣子,拟南运到浙江宁波府交卸。前后9个月中,先后应福建莆田、江苏镇江、天津、山东登州府黄县商人8次雇请,数次往返于关东、山东洋面。
往返北洋航线的江浙商船,所载商品相当单一清晰。南下的称“北货”,基本是大宗商品饼豆类粮食,在关东是豆类粮食豆饼豆油瓜子等货,在山东是豆粮、枣子、花生和腌猪等;北上的称“南货”,主要是棉花和布匹,间有书籍、纸张、棉布、麻布、茶叶、糖果、板笋、白糖、药材、蜜饯等。后者看似种类多于前者,其实从商品价值而言,远少于前者,所以后者还需投放银钱等通货。这种不等值的商品交换,基本上体现为南输豆粮而北输银钱的流通格局。
上述52例,船户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沙船号主所有的船,另一类是船户自有之船。前者如第4例,华亭县船户张永升的船,是大沙船主张羽可即张元隆号的船。第44例,海州赣榆县商人许振宽等8人,驾驶的是沙船主范复兴牌照的船。第49例,崇明县船主陆载岩等11人,驾驶的是本县竺格顺牌照船。第50例,上海县人赵汝林等21人,所驾之船是上海大沙船主郁泰峰的船。例52,上海县赵汝林等21人,所驾之船主是大沙船主郁泰峰的孙寿福船号的船,船主有“有五十余船,不能出海”。
沿海运输之船分两大类,一类是船户自有之船,一类是船户撑驾沙船字号主的船。若船户以自有之船直接经营商品,赚取的是商业利润;若为客商代运商品,获得的则是“水脚”即运费,与船工按成分配运输所得。上述大多数事例是船户揽接客商货物运输,获取运输费用。如是沙船字号主的船,又分两种情形,一是沙船字号主经营航运贸易,所获利润归沙船主所有,船户和船工所获只是工资报酬;二是沙船揽运客货,所获“水脚”由沙船主和船户及船工按比例分得。例25,舵工唐明山等称,赵源发是船户,“故在家”。例31,舵工水手陈仲林等驾船,“张御是船主,故家不来”。例43,苏州元和县船户诸元茂船,船主为诸名善,据船户说,“与我们共业”“船主在家,得利二分”。显然,船主以船只作为投资,所获利润占比较小;船户和船工以人力作投资,所获利润占比较大。例27,船户是傅鉴周,舵工是同县人朱盛章等,船户是叶合盛。例48,昆山等地舵工,撑驾船主龚润甫之船,装载漕粮到天津交卸,回到烟台,装载山东聊城乌枣客商郭德章、杜佩珍等8人之货返航。
船商从事沿海贸易,须由保载行开出保票,以负法律责任,而既有研究从未述及。道光初年,包世臣说,上海沙船十一表,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尤多大户,立别宅于上海,亲议买卖”。又有保载行八家,“并非领帖船埠,专为庄客包税,兼及觅船,并不于水脚内抽分行用”。沙船主财大气粗,“骄逸成性,视保载行内经手人不殊奴隶”。(125)[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3,《海运十宜》,光绪十四年刻本,第21页。同时人齐学裘也说:“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五百余文。”(126)[清]齐学裘:《见闻续笔》卷2,《海运南漕议》,《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05页。这种保税行,就是专为豆船字号包税,兼为庄客雇写船只,雇船时先付部分运费水脚。这种保税行,显然就是前述刘河镇上为豆船字号包纳税额的牙行。上列例32,崇明县郁长发船启航前,就按惯行做法,即“于李裕昌保禀,往山东生利”。上海豆业有保载行,海船须由牙行保禀开出保票,结合康熙后期张元隆经营事例和嘉庆中期郁长发船事例,可知上海的豆业经营手续和形式,与太仓是相同的。
船户代客运输,客商则不必随船押运。嘉、道时期,不少人力主海运漕粮,包世臣描述,“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夥押载,从不闻有欺骗”。(127)[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第2—3页。齐学裘说:“关东豆货往来每年数百万石,并无客夥押载,从未闻有欺骗。”谢占壬也说:“商家货物从无用人押运,惟以揽载票据为凭,定明上漏下湿,缺数潮霉,船户照数赔偿。”(128)[清]谢占壬:《海运提要·防弊清源》,载《清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1157页。他们均认为船商揽载运输,客商并不押载,而全凭行票店信,从无商业纠纷。而道光五年河南巡抚歙县人程祖洛则说:“臣同乡贩运茶叶赴京暨关东售卖,向系装运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船户水手素习海洋水性,兼能预知风信。每船押送客商不过一人,开洋后其行泊悉听之船户。”(129)[清]程祖洛:《覆奏海运疏》,载《清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三》,第1171页。例28,南通州舵工龚凤来等16人,应元和县彭际兴商船之雇,“各自为商,同往一处”。船票开明18人,“船户彭祭兴,在家不来,王尧先有病,代送其子春林,陈瑞康有病不来”。随船带有两封信,一封是寓居上海县的山东胶州商人黄琼付同乡商人周肇西者,一封是南通州商人刘云洲付书其子者。该船欲往山东,傅致书信后,装载黄豆、青豆等粮。胶州商人黄琼,委托彭际兴船到山东装载豆石,大约言明代为购买事宜。上述贸易事例,很多事例只见舵工、水手,而无客商随船记录,也说明客商并不一定随船押载,然而上述事例,又有不少与客商随船同行。细细观察这些随船客商,通常并非整船包运,而只是搭船随行,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搭乘同一艘船开展经营活动。如例18、21、25例最为明显。如此说来,客商是否随船同行,全凭运输量的大小和方便与否而定,客商不必随船押运,但小额和散商经营,往往随船而行,以就其便。
至于运价,道光初年清廷试行海运时,曾经讨论过。包世臣、齐学裘等人谓,民间海商运输,“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四百文”,因此主张官运漕粮,若以苏石计算,付以运价每石7钱,以六八串钱给付,合制钱394文。(130)[清]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衢一勺》卷1,《海运南漕议》,第2页;[清]齐学裘:《见闻续笔》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10页。而上例31,镇洋县舵工水手陈仲林等自江南往关东金州装运黄豆360石,“每一石船贳钱七钱五分贰”。此次贩运,以“江南十斗,关东二十六斗为一石”计算,关石是苏石的二点六倍,则苏石每石运费为银2钱8分9厘2毫。关石与苏石之比,上例43,元和县船户诸元茂船又谓,“元和县豆价以苏斗,每石价银二两。牛庄豆价以牛斗,每石价银二两五钱。牛庄豆一石到江南卸作二石四斗二升”。(131)《各司誊录》第7册,转引自[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第113页。此例牛庄豆价合苏石每石银1两零3分3厘。如以此二例计算运价,约占豆价的则苏石每石为28%。无论如何,均比时人所说要低。清前期的北洋贸易,因为运输发达,运输量大,运费相当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