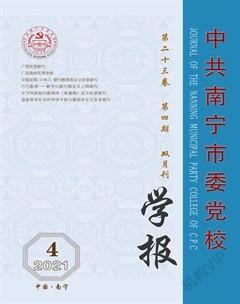法理视角下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正当性和现实性分析
邝达
[摘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正当性可解构为三个维度:一是目的正当,即制度构建应指向某种公共利益的目的;二是手段正当,即制度构建应沿着法治路径推进;三是程序正当,即制度构建应遵循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对此,本文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现实性包括:第一,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覆盖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可行性基础;第二,现有相关地方立法为从国家层面立法提供了有效“样本”;第三,国外相关的法律保护模式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理视角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 正当性 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21)04-0048-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1.04.0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传承并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知识,属于传统知识的范畴。目前,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已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也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中医药传统知识虽然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其他知识相比,具有特殊的属性和发展规律。2017年颁行的《中医药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簡称《意见》)发布,其中第十四项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上述法律和政策表明,我国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已是势在必行,因此,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理论研究仍然需要向纵深化和精细化推进。笔者在检索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关于讨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现实性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稀少,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本文阐述该问题。
二、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分析
“正当性”是法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贯穿法学学术史的一条线索,但是“正当性”这一概念十分复杂,不仅词义难以明晰,而且涉及诸多密切相关的概念。韦伯在系统阐述正当性命题时,认为构成正当性的来源的因素是传统、情感、价值理性以及实在法[1]161。同时,韦伯基于经验事实的维度,提出三种正当统治模型,即传统型统治、克里斯马型统治以及法理型统治[1]396,传统、情感以及实在法构成证立上述三种统治模型的正当性的决定因素。然而,人们却无法根据韦伯的论述确定基于价值理性的正当统治模型。对此,韦伯指出,在没有统一的价值理性的情况下,统治秩序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具有合法律性。[1]162换言之,在韦伯的理论视野中,正当性的获致建立在合法律性的基础之上。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则对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的阐释路径不以为然,他认为正当性与合法律性有别。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当性具有事实之维和规范之维,前者指政治秩序在事实上得以遵守,后者指政治秩序之所以得以遵守,是因为人们的承认。在此基础上,兼具正当性和合法律性的政治秩序方可实现公平正义,进而达致社会安定[2]。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探究法律制度构建的问题时,应当首先证立其正当性。
从哈贝马斯的理论可知,正当性包摄着制度的生成、运作和调整,制度正当性的证立应遵循符合公平正义等价值取向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信任的进路。具体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之上,正当性可以解构为三个维度,一是目的正当,即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构建应指向某种公共利益的目的;二是手段正当,即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构建应沿着法治路径,依法、有效地推进;三是程序正当,即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
(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目的正当性
一般说来,知识产权法的目的可以划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就前者而言,知识产权法因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而保障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就后者而言,知识产权法通过保障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知识产品的生产,促进知识产品的利用,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法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不特定多数人之利益[3],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目的亦然。从直接目的来看,知识产权法是为了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利益;从最终目的来看,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利益。
基于此,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指向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保证中医药传统知识可持续性地传承、使用与创新,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中医药传统知识经历了数千年的形成、流传与发展,已成为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象征与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成果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传统性是其特征之一。然而,在笔者看来,“传统”只表明其来源,并不能粗糙地将之与落后等同。诚然,由知识话语的视角观之,随着近代中华民族危机而引发的西化思潮以及科学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医药在近代话语知识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或者低效的话语状态,但是中医药传统知识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优势,是中医药科研创新的源泉。以药物市场为例,治疗疟疾的青蒿素、治疗代谢性疾病的黄连素等,皆是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研制的。此外,《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明,无论是个体的生存,抑或是社会的发展,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亦如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是不可或缺的。单一的知识体系会使人类目光狭隘、故步自封,进而失去创新的活力和动能,与之相反,多元的知识体系将会为世界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时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前所未有,世界各国至今尚未研制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全球正在面临极其严峻的公共健康危机。在此背景下,2020年1月至8月,国家卫健委相继发布了八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以下简称《诊疗方案》),而在第三版至第八版的《诊疗方案》中,中医药诊疗方案皆被纳入其中,主要用于对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救治。由此观之,受益于文化多样性,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能够在多元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制订中西医协同救治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化解中国的公共健康危机。
第二,维护和实现人权的需要。《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发展权利宣言》等诸多关于人权的国际文书中的相关条款都表明,从发展中国家、传统社区或部族的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维护和实现的视角来考量传统知识保护问题是重要的研究进路。首先,从健康权的视角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作为中华民族长期传承并持续发展的医药学知识体系,在维护中华民族甚至人类健康的领域已做出不容置疑的贡献。此外,由于中医药治疗方案所需费用较为低廉,因而其可最大程度地满足大多数患者的医疗需求,从而为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提供保障;其次,从发展权的视角来看,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财产属性,属于非物质形态的经济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化的基石。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制度化的保护,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消弭我国公共健康危机、捍卫公民健康权提供物质基础。
(二)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手段正当性
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西方国家强势主导之下、立足于西方国家价值观而构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其保护对象一般是现代知识,即建立在西方式的思想和实践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多数认同的、具有主流优势的知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属于舶来品,西方语境下的知识产权理论与实践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我国《中医药法》第八条规定,要“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但是由于中医药传统知识内部存在多种形态,而不同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形态获得或被授予知识产权的条件迥异,笔者在此难以详述,仅就专利保护问题为例展开阐述。根据现行专利制度,中医药传统知识成为专利制度的保护对象应满足如下前置性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然而,多数传统药方或是载于中医药典籍之上,或是被用于临床实践之中而丧失新颖性特征;其次,所谓“创造性”是指请求获得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必须和与之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其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中医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秉持固本培元之理念,遵循辨证论治之思路,认为病毒和细菌变化多端,故而中医的治疗思路不在于探究致病因素,而在于考察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症状,然后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以帮助患者增强自身免疫力,从而借由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有效地对抗病毒和细菌。换言之,传统中药药方和药品的疗效缺乏精确和稳定的数据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医药的诊断和治疗是建立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与具体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无法借由现代化学药品审查中的生理、生化、病理等关键指标的方式对传统中药配方及药品的创造性特征进行量化评估;最后,按照专利法的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客体应当具备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实用性的标准要求该专利权客体以产业应用为前提,并且可以产生实际利益。由于传统中医药的诊断和治疗无法形成稳定和量化的方案,故而传统中医药将因难以形成产业标准化的制造和使用而缺乏工业应用性。因此,在现有专利制度框架内,中医药传统知识在获得或被授予专利权方面将面临诸多障碍。
由此观之,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对象方面略显僵化和滞后,未能覆盖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针对这个问题,《意见》第十四项表明未来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推进,即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以《中医药法》为基础,以“保护条例”为中心,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体系。
(三)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程序正当性
哈贝马斯采取商谈模式的程序主义进路来建构法律的正当性,他提出,法律获致规范意义的途径,非是经由法律本身的形式,亦非经由法律的道德内容,而是经由立法程序。[4]进言之,现代立法程序中具有的交涉性是法律正当性的关键来源。所谓的“交涉性”是指立法决策的参与者依据法律程序规范,进行充分的辩论与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获致参涉各方皆能认同的结果。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六条亦规定立法应当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付诸公议。立法程序中的交涉因立法决策参与者的多元利益立场必然存在诸多交锋,但是交涉性的立法程序机制通过为上述持有不同利益立场的立法决策参与者在讨论关于法律草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上提供了有序平等、温和理性对话的平台,进而让彼此的分歧与争端消弭于立法过程之中,最终使法律法规草案获得多数人的認同,表达多数人的正当意志。这正是“正当性应该根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也是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原则之贯彻。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到,由于主观维度和客观维度的条件制约,立法者最终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不圆满性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立法过程的正当性与立法结果的正当性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即立法过程的正当性证立了立法结果的正当性。因此,我国应通过程序性层面的合法性来进一步强化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正当性,即我国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应在公民的直接民主参与和代表制的间接民主决策的机制之下,遵循法定程序,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三、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现实性分析
关于正当性的证成分析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内在的价值基础。除此之外,如今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被盗用、篡改甚至流失的困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构建具有在现实性维度的紧迫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构建的实然条件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覆盖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可行性基础
当我们从历史维度研究法律时,可以发现:从实质上说,法律是以历史经验来应对现实问题的。[5]归根结底,中医药传统知识与一般的知识产权的客体同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促使人们诉诸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依托现行知识产权立法模式来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作为世界各国用以分配知识权利的主要机制之一,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和与其交往的其他社会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产权的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立性,某些方面在现实中可能会导致传统知识的流失,而其他方面则具有解决问题的潜在可能性。”[6]在如今这个时代,知识产品生产和利用速率呈上升趋势,新的知识形态也在不断生成。我们知道,法律规范的滞后性导致其适用的时空场域具有相对性,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或许无法规制新的知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大厦面临“推翻重来”式重构。在笔者看来,目前社会范围内要求完整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呼声呼唤着知识产权理念和制度的创新,此种创新可以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之下通过完善立法技术的方式实现,而不必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造成根本性破坏。既然我国尚未确立全新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法律保护模式,那么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应是当前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最适切的制度工具。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催生出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即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客体呈现扩张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产权制度并未故步自封,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法律体系,这意味着将中医药传统知识纳入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是可行的。
(二)现有的相关地方立法从实践维度为我国从国家层面立法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提供了有效“样本”
自1982年《宪法》和2000年《立法法》颁行以来,我国的立法体制在纵向上可划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级,而在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地方立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法律制度的构建以现实社会的需求为导向,故而当前各地在不抵触上位法的前提下,基于本地的实际需求和文化特色,以地方立法形式制定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地方性法规。然而,我国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领域缺乏明晰的顶层制度设计,因此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而碎片化保护具有“治标不治本”的缺陷,即虽然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缺乏基础性、系统性、长期性的整体保护方案。换言之,仅靠地方立法难以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全覆盖式保护,我国应在国家层面推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我国可以借由自下而上的地方立法经验作为切入点和“试验田”,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设计提供实践“样本”。同时,通过对地方立法思路和内容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中央可以克服地方立法分散化、碎片化的缺陷,整体性地配置立法资源,进而周全地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
(三)国外相关法律保护模式对我国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目前,国外针对本国传统医药知识的法律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综合立法模式,即将传统医药知识归入传统知识范畴,并针对传统知识进行统一的立法规制与保护,代表国家有秘鲁、菲律宾等国;一种是专门立法模式,即针对本国传统医药知识进行特别立法,如泰国的《保护和促进传统泰医药智力成果法案》就是作为该种模式的立法典范被国际社会广泛提及。该法案作为保护与利用泰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典型立法对涉及泰国传统医药知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将泰国传统医药知识区分为国家处方或文献、私人处方或文献以及普通处方或普通文献,从而满足多维的保护需求。[7]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及职权分配。[8]由此观之,专门立法模式可较为准确地界定、解构专门的法律概念群的内涵,详细地规定特定保护的基本原则、主要规则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针对性和保护力度较强、效用较显著。在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以综合性立法的形式对传统知识进行规制与保护的情况下,为尽快化解中医药传统知识被篡改、盗用甚至失落的危险,我国采用专门立法模式是适宜而有效的。《意见》的第十四项亦表明我国倾向于采用专门立法模式,即针对中医传统知识进行特别法律规制。此外,中华民族在生产和传承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概念群,因此我国在制定“保护条例”的过程中应当廓清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内涵和外延,进而界定法律保护范围,从而明确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管理机构和职权配置等内容。
四、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和知识信息逐渐成为极其重要的经济资源,对国际竞争的成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创造和世代传承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在今天已然成为我国的关键知识产权资源,并将成为新时代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的构建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利益。同时,在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制度研究,仔细梳理中医药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断为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3]冯晓青,周贺微.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研究[J].学海,2019(01):188-195.
[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67.
[5]赵立行.法律史的反思:法律的历史维度[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01):138-146.
[6]David R. Downes.How ntellectual Property Could Be a Tool to Protect Traditional Knowledge[J].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 Law,2000(25):253.
[7]甄思圆,李海燕,刘扬.国际传统知识保护模式分析及对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启示[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8,42(04):1-5.
[8]董作军,黄文龙.泰国传統医药保护及对我国中医药保护的启示[J].中国新药杂志,2008(14):1278-1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