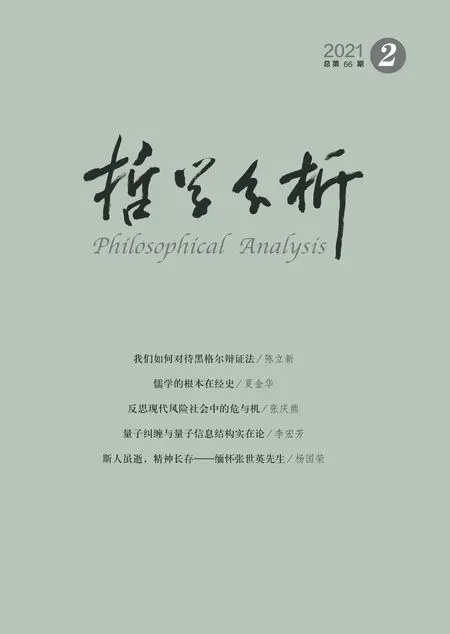哲学与大脑:作为非还原性神经哲学的世界—大脑关系
——格奥尔格·诺赫夫教授访谈
陈向群 [加]格奥尔格·诺赫夫
格奥尔格·诺赫夫(Georg Northoff)是国际知名的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现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心灵健康研究所心灵、脑影像与神经伦理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他长期关注心灵和大脑问题,善于从神经科学、哲学和精神病学的跨学科综合视角来研究心灵问题,从而将心灵和意识问题从单纯的哲学议题转为神经科学和哲学的跨学科综合议题。诺赫夫教授已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包括《大脑哲学》( Philosophy of Brain,2004)、《解锁大脑:第一卷:解码/第二卷:意识》(Unlocking the Brain: Volume 1:Coding/Volume 2:Consciousness,2013)、《留心大脑:通往哲学与神经科学之路》( Minding the Brain: A Guide to Philosophy & Neuroscience,2014)、《神经哲学与健康心智:基于不正常大脑的研究》( Neuro-philosophy and Healthy Mind: Learning from the Unwell Brain,2016)①该书繁体中文译本为:《病脑启示:神经哲学与健康心智》,陈向群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版。、《自 发 的 大 脑:从 心 身 问题 向 世 界 — 大 脑 问 题 的 转 变 》( The Spontaneous Brain: From the Mind-Body to the World-Brain Problem,2018)等。本访谈主要是与诺赫夫教授探讨他的神经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非还原性神经哲学理论的世界—大脑关系(world-brain relationship)”,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解答心灵的本质和实在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陈向群(以下简称“陈”):据我所知,您的研究主要涉及神经科学、哲学和精神病学,您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说自己是一个神经科学家、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为何你认为这三个学科是相互交叉关联的,且可以展开对话?
格奥尔格·诺赫夫(以下简称“诺赫夫”):非常谢谢您来访谈我。事实上,当你回顾哲学史时,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此外,20世纪和现在的物理学都深刻地触及了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只有20世纪哲学中的某些渗透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沿着概念逻辑维度与观察经验维度的分界线,构想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分裂。我认为自己是站在早期哲学和20世纪物理学前辈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20世纪哲学与科学二分法的肩膀上。我们目前所缺乏的是一种系统和有效的方法,去将概念逻辑和观察经验的维度联系起来,从而更广泛地将哲学和科学联系起来。这确实是我的主要目标之一。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方法论,例如非还原性的,已经在我早期的《大脑哲学》( 2004)一书中阐述了,并且在我的代表作《留心大脑》( 2014)( 特别是第4章)中作了更详细的阐述。简言之,我主张一种方法论策略,我将其命名为“概念—事实迭代性”(concept-fact iterativity),作为哲学概念和经验数据事实之间连续的方法论和迭代运动。从历史上看,这种“概念—事实迭代性”是站在康德的肩上,康德认为“没有直觉的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你可以把我的“概念—事实迭代性”的方法看作在方法论上概念与事实/直觉之间的系统关系的发展。很明显,你可以在我的各类神经哲学著作中看到这种方法,特别是在《解锁大脑》( 2014年版第二卷)和《自发的大脑》( 2018)中。因此,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设想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方法,这是首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构建一个健全的跨学科对话。这是我们哲学和物理学的前辈们在直觉(而非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非常多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方法论的范畴,我认为用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来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似乎是必要的。遵循康德的座右铭,我们认识论的局限性会导致我们仅仅以经验或概念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因此,我希望,我的经验主义背景可以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哲学家,就如我所说的那样,哲学也会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神经科学家。
陈:所以,在您看来,神经哲学这个新概念源于神经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对话?然而,我们都知道,神经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研究,而哲学是关于概念的研究;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思辨的。为何看上去概念相反的两者可以联系起来?
诺赫夫:如上所述,哲学是关于概念领域,而神经科学是关于观察领域。但如康德早已指出的那样,两者都不能孤立地被构思。当我研究神经科学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概念性的问题出现了这么多。例如,当我们讨论如何研究自我的心理和神经机制的实验范式时,我们立刻进入了概念领域: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一个自我必须满足的标准?当前关于自我的解释与不同时期哲学对自我的理解如何相联系?等等。如康德所说,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我们需要概念来指导实证研究。去问问物理学家,他们对此了解得太多了……好的科学需要理论和概念工作,否则最终就不是好的科学。同样地,这也适用于两极的另外一端。如上所述,哲学的纯概念特征是20世纪西方哲学较新近出现的概念,在哲学和科学紧密联系之前……概念和观察领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连续的。由此,概念自然流入观察;反之,观察自然流入概念。因此,有一个连续体,一个概念—观测的连续体,两端是纯粹的概念性和纯粹的观测性,它是混合了概念和观测的连续体/关系。我们可以位于这个连续体上,或者更靠近概念端,或者更靠近观测端。
陈:您特别提到了两种神经哲学概念,即还原性的神经哲学和非还原性的神经哲学。可否在具体介绍下两者的不同?哲学和神经科学在它们之中又有何不同的关系?
诺赫夫:神经哲学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它可以用还原与非还原的方式来理解,这是一种关于概念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方法论描述。从我的关于概念—事实的迭代性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倾向于一种非还原方法。然后我们可以区分狭义的和广义的神经哲学,它们是关于大脑的见解和模型。狭义的神经哲学以一种纯经验的方式来构想大脑,同样地,神经科学也在构想它。相比之下,广义的神经哲学认为大脑不仅是一个经验的,而且还具有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背景,这相当于我的早期著作(Philosophy of Brain,2004)中所说的“大脑哲学”。我同意丘奇兰德(P.M.Churchland)的还原性狭义神经哲学是一个死胡同的观点,这是我10到20年前就已经说过的,对于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哲学见解。还原性神经哲学意味着哲学的还原性,它倾向于将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概念还原为大脑的经验事实,这相当于概念—事实的减少,甚至是概念—事实的消除。非还原性神经哲学通过提供方法论的工具来系统地研究依赖性和相互制约性,反对概念—事实的还原,这相当于以概念—事实的迭代性作为一种非还原性方法论策略。因此,站在哲学和神经科学历史的肩膀上,广义的非还原性神经哲学有一个相当光明的未来,因为它允许提出新的问题,如用世界—大脑问题取代传统的心身问题。再者,为了发展和应用广义的非还原性神经哲学,我站在叔本华和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前辈的肩膀上充当神经哲学的“前卫”,我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背景下来构思我们的大脑。
陈:就如你回答上面问题时所说的,哲学和神经科学在还原性神经哲学与非还原性神经哲学中有不同关系(还原和迭代),那么,除此之外,哲学和神经科学还有没有其他关系?
诺赫夫:是的,您可以假设这两个领域之间是并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和神经科学基本上是不同的,没有任何相互作用。哲学是关于概念逻辑领域,而神经科学是关于经验观察领域。它们涵盖了两个不同的逻辑空间:理性的逻辑空间和自然的逻辑空间。两者既不相互干扰也不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逻辑空间的二分法,进而导致了哲学和神经科学的二元性。声称站在维特根斯坦的肩膀上的贝内特(Max Bennett)和哈克(Peter Hacker)强烈建议采用这种平行模式。我认为,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狭隘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塞拉斯(Wilfried Sellars)和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都试图通过结合康德式的先验方法——先验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来克服这两个逻辑空间的平行性 。
陈:您在《自发的大脑》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世界—大脑关系,什么是世界—大脑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看作一种非还原性的神经哲学理论?
诺赫夫:的确,这是一本关于非还原性神经哲学的书。总的来说,神经科学和哲学在大脑和意识方面的相遇,使我们对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心身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让我简要介绍以下这本书的推理思路。在书中,我不打算提供一个关于心身问题的答案。相反,我的目标是通过质疑心身问题的前提来质疑和化解(而不是回答和解决)心身问题,这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先验的方法论。这样的预设包含于心灵的可能存在,只有预设了心灵,人们才能提出它与身体可能的关系的问题,即心身问题。与此相反,如果不再以心灵为前提,那么关于它与身体的关系问题(心身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我们不能提出关于某个事物(如身体)与某个不可能的事物(如心灵)的关系问题。然而,另一个通常默认的前提是,心灵表现出与意识等精神特征的必要关系,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因为心灵应该解释精神特征的本体基础。而这本身就预设了心灵和精神特征的区别:精神的特征是意识、自我等,而心灵则是它们所谓的潜在本体(或形而上学)基础。这种区别意味着,除了心灵之外的任何其他都可能为精神特征提供本体论基础。此外,这种区别还意味着,对心灵的排斥(作为本体论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对精神特征的排斥,心灵的缺失与精神特征的存在是完全相容的。基于各种经验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证据,我认为,世界与大脑的关系(从本体论而非经验意义上来理解)必然与意识等精神特征相关,可以作为它们潜在的本体论基础。因此,世界与大脑的关系可以取代传统认为的心灵在精神特征中所扮演的本体论角色。现在,考虑到心灵是心身问题的前提,用“世界—大脑”关系取代“心灵”在其精神特征中的作用,意味着“心身问题”变得没有意义并因此得以解决,甚至提出“心灵与身体关系”问题也变得无意义,因为不再有“心灵”。我们可以用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来解决(本体论、经验、概念)存在和实在问题,例如,精神特征的本体论基础。因此,我并没有提供一个解决心身问题的答案,而是透过假设世界—大脑关系来取代它作为精神特征更合理的本体论基础。然后,我们可以谈论世界—大脑问题,正如我所希望的,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本体论框架来讨论诸如意识之类的精神特征(正如我在2018年的书中所讨论的),以及诸如自我和人格同一性(我目前正在研究)之类的其他精神特征 。
陈:什么是自发的大脑模型,它与主动性大脑模型和被动性大脑模型有何不同?你说哲学家康德也提到过这个概念是吗?
诺赫夫:是的,这确实是《自发的大脑》第一章所说的。虽然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涉及,但它是以哲学史为基础的。目前神经科学中的大脑模型是基于过去哲学中的心灵模型。让我详细说明一下。
神经科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大脑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自发活动,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外部刺激的神经活动。这显然为反对纯粹基于刺激反应的被动大脑模型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这种大脑模型可以与洛克和休谟,以及过去和最近行为主义提出的心灵概念相一致。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引入认知功能来使这种模型复杂化,但即使这样,它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型,只是中间夹有认知功能。因此,这种模型也有点属于大脑的被动模型。不同于休谟,康德认为,我们的心灵表现出内在的自发性。显然,这与观察大脑本身内在的自发活动相符合。因此,我提出一个大脑的主动模型,它类似于康德式的大脑模型。然而,经验现实告诉我们,在大脑的神经活动中,与外部刺激相关的反应和自发活动两者不能被清楚地分开。什么是自发的?什么是外部诱发的?我们不太清楚,也不可能把两者分开。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相互作用——非线性和动态的,在默认情况下,或许以一种必要的方式使神经活动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能分离。因此,我说的是大脑的频谱模型(spectrum model of brain),它是对休谟的被动模型和康德主动模型的经验性回答。因此,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哲学思维模式是如何帮助我们发展现在的大脑模型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检验我所提出的大脑频谱模型的经验合理性。这可以看作对西方哲学中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的二分法的回答,即主动与被动的关系问题。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旧的哲学问题伪装成神经科学出现了……在西方世界,我们称之为“新瓶装旧酒”。
陈:在世界—大脑关系中,您认为大脑和世界之间是一种时空关系,为何大脑内的时空能够与世界中的时空联系起来?它们又是以何种方式相联系的?
诺赫夫:是的,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一句话,我的目标是找出主观性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如何来的。因此,我认为像自我和意识这样的精神特征是一种更基本和更广泛的主观性范例。鉴于我的本体论框架,我提出世界如何与大脑相联系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即世界—大脑关系。这样的话,大脑的神经元活动就可以转化为精神活动。我所说的世界—大脑关系是什么意思?它与意识等精神特征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它们的关系是本体论的,具体地说,是时空的关系,时空构成了世界和大脑的关系,从而使意识成为可能。大脑在时空上嵌套于世界,就像较小的俄罗斯玩偶或中国水晶球嵌套在下一个较大的之中,以此类推。因此,嵌套在这里被理解为本体论和时空意义的。从时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世界—大脑关系是神经—精神转换的必要本体(和经验)条件。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关于精神特征和它们的神经基础问题通常不是以这种方式构建的。我们通常不寻求神经—精神的转换,而是精神特征的神经相关性,比如意识的神经相关性。从方法上,这就预设了从精神到神经的方向性。现在我把它颠倒过来,因为我更喜欢从神经(最终是神经—生态的)开始到精神。只有当预设了后一个方向性时,我们才能提出神经—精神转换的问题,而如果从方法上预设从精神到神经的方向性,这个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这听起来似乎更奇怪。然而,考虑一下其他学科,如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他们关注的是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状态A如何转换为状态B。为了使这种转换成为可能,A和B必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因为没有这些特征,A就不能转变成B。这就是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说的神经和精神特征的“共同货币”(common currency),因为它必须是神经—精神转变的基础。乐观地来看,我会说,神经和精神特征的“共同货币”应该是我们探寻精神特征或主观性的神经(本体论)基础。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假设时空动力特征(temporo-spatial dynamics)提供了神经和精神特征的“共同货币”。神经特征显示了时空动力特征,正如我假设的那样,它转化并体现在意识时间和空间的主观体验中。“时空性”就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识流”和胡塞尔的预存(protention)、呈现(presentation)和保留(retention)概念。为了从意识和自我(以及其他精神特征)的精神层面上把握和解释这种时空性,我们需要第一人称的描述。而为了将第一人称的时空性与大脑的时空动力特征联系起来,我们需要第一人称的神经科学,后者(以及你所指出的相关概念)因此是一种研究时空动力假设的方法论工具,它提供了神经和精神特征的“共同货币”。而且,正如我所假设的,发现并识别“共同货币”将提供一个一致的,在本体论和经验(以及认识论)中可行的意识概念。
陈:您在上个问题里提到了“共同货币”和“镶嵌性”,可否具体再解释下这两个概念?
诺赫夫:想象一下水,它可以是冰冻的、液态的和蒸汽状的。一种化学物质(H2O或水)怎么可能转变成这样不同的状态?唯一可能的是,他们一定分享了一些东西,如我所说的“共同货币”。这同样适用于神经和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神经状态如何可能转变成精神状态?为什么我们会经历一种特殊的现象状态或意识,而不是感知神经状态?在我看来,类似于水的不同状态,神经状态也可以转变成精神状态,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只有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共同货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如水的情况,正是H2O这样的共享特性或“共同货币”,水才能在不同状态之间相互转换。我现在假设水的化学式,即H2O,在神经—精神转换的情况下是时空动力模式:水存在冰冻状态和液体状态,类似地,时空动力模式存在神经和精神状态。因此,时空动力模式提供了迄今为止缺失的神经和精神/现象状态的“共同货币”,这是我在2018年的书中的主要主张。
什么是嵌套?看看那些俄罗斯娃娃。较小的玩偶嵌套在下一个较大的玩偶中,而下一个较大的玩偶又包含在下一个较大的玩偶中,依此类推。不同的俄罗斯娃娃在空间尺度上表现出不同,但在基本形状上却有相似之处,中国传统中美丽的水晶球也是如此。同样的,关于不同的时间尺度,它们也在彼此相互嵌套,我称之为时间嵌套。现在,这同样适用于意识、大脑和世界的关系:意识可能作为一个较小的俄罗斯玩偶嵌套在大脑这个较大的俄罗斯玩偶中,而它们又嵌套在世界中形成一个最大的俄罗斯娃娃。因此,时空嵌套是我的一个本体论概念,是时空本体论的一个特征,它描述了时空中的存在和实在。与此同时,存在一种被称之为的大脑无标度活动(scale free activity)可以从经验上来检验这种镶嵌性。事实上,我们和其他各种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大脑的无标度活动程度,即其神经活动的时空嵌套性与意识直接相关。
陈:就如你所认为的,世界和大脑的时空关联是我们具有意识的关键,那么,在一些不正常的大脑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病人,他们大脑与世界之间是否同样存在着时空关联呢?
诺赫夫: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神经生态(neuro-ecological)方法如何理解精神失常(mental disorder)的。精神失常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经验论上都是世界—大脑关系的失常。这些病人的大脑表现出异常,但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脑神经功能强烈地依赖于环境的变化,例如,在生活和神经发育方面的环境变化。同样地,世界依赖性也适用于症状本身。精神病患者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体验到他们的症状,而他们体验到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和他们的症状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详述了哲学、现象学中的另一条历史线,它解释了我们自己、时间和空间、身体以及世界的经验结构。因此,我们在大脑和精神疾病的症状中看到了世界依赖的必要性,它们是世界—大脑关系的紊乱,更确切地说,是神经—生态的紊乱(而不是神经或神经认知紊乱)。这不仅在理论上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还导致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用于治疗的新想法。
陈:您将世界—大脑关系理论看作一种时空意识理论(Spatiotempor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TTC),它与其他形式的意识理论如信息整合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IIT)和全局神经工作场理论(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 Theory,GNWT)有什么不同?
诺赫夫:注意,我并没有说IIT或GNWT是错误的,它们都描述了意识的特定方面及其潜在的神经元关联。然而,我说他们漏掉了一些东西,正如维克多·拉姆(Victor Lamme)最近所说的“缺失的成分”,它存在于时空动力模式以及所塑造的独特神经活动中,即自发、预刺激和刺激诱导的活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大脑神经活动的时空动力模式表现为意识,也就是现象学家所说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时空动力模式因而提供了神经和精神活动的“共同货币”。因此,我假设TTC,即时空意识理论,提供了一个比IIT和GNWT更大和更全面的意识观。如果我是对的,TTC的时空动力方法应该可以预测IIT和GNWT的时间—空间动力方法。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研究阶段,初步结果是令人期待的。
陈:我们都知道,意识问题也是心灵哲学所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而世界—大脑关系作为神经哲学理论从大脑与世界的时空关联视角来解释意识问题,心灵哲学和神经哲学是什么关系?
诺赫夫:对我来说,心灵哲学是关于对心灵的概念、本体、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灵哲学可以通过广义的非还原性神经哲学加以补充,正如我2018年的书中所说,这会导致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如果认真考虑我的建议,人们最终会用我在之前的一本书(Philosophy of Brain, 2004)中所描述的“大脑哲学”来取代心灵哲学。大脑哲学将在概念、本体和认识论方面来理解大脑,然后通过非还原性神经哲学及其具体的跨学科方法论策略将其与经验数据联系起来。对我来说,认知科学哲学就像是科学哲学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认知科学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认知科学所预设的心智和认知模式。我想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神经科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来讨论我们通常在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中所默认的(较为初级的)大脑模型。
陈:我们都知道,当代认知科学对意识的解释同样强调身体、大脑与外界环境的互动性,如具身(embodied)认知、嵌入(embedded)认知、生成(enacted)认知、延展(extended)认知等理论,可否说世界—大脑关系对意识的时空解释与这些理论是一样的?
诺赫夫:确实,我认为意识不在大脑中,它是大脑和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特征。这会立即让我们联想到4E(embodied,embedded,enacted,extended)认知的背景。那么,我的观点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让我想到了另外两个假设,它是我们在解释心灵问题所提出的。笛卡尔认为我们心灵的存在和实在与我们所生活和观察的世界是不同的,因此,心灵的概念必然与世界相隔离,否则,他就无法再区分心灵与世界。由于像意识这样的精神特征被认为必然依赖于心灵,它们继承了心灵与世界隔离的概念。为了在这种世界孤立(world-isolated)假设的基础上解释心灵与世界的关系,人们可以追求不同的策略。麦克道威尔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策略,他把思维的概念能力和理性理解为“人的第二天性”,并将其整合到一个可以称之为“自然概念扩展的逻辑空间”中。另一种解释心灵与世界关系的策略是你提到的4E。现在大部分世界孤立的观点是与身体和世界相关的,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尝试,但它并不能克服它最初的先天缺陷,即,通过隔离心灵和世界的关系来定义心灵。简单地说,就是首先把世界从心灵中排除(当定义它的时候),然后试图把世界带回心灵中。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必要的基础上被排除在外的东西,例如心灵定义中的世界,不能通过后门带入,因为这不能弥补最初的先天缺陷。换言之,我们需要比4E更激进的东西来克服我们对心灵的定义中的先天缺陷(将世界排除在外)。重要的是,当我谈到世界时,我指的不是理性概念中的高阶认知世界,也不是现象学方法中的意识世界,我指的是独立于我们的理性、意识或其他的世界。
回顾康德、胡塞尔等人,人们现在可能倾向于认为,这种心灵孤立(mindisolated)的世界观可能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接近和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是与将其与我们自身关联起来。大脑通过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方式,使我们与世界相关联,这相当于我所说的世界—大脑关系(区别于大脑将自己强加给世界的大脑—世界关系)。加上我对前两个前提(世界孤立和心灵孤立)的否定,我认为,在本体论意义上构建的世界—大脑关系,可以克服对精神特征的定义中排除世界的先天缺陷。为了充分理解我的观点,需要在我对心灵解释中构思第三个默认的前提。我们通常假定属性(精神或物理)作为存在和实在的基本单位,这相当于我所说的“基于元素的本体论”(element-based ontology)。心灵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本体论,因为它是由实体或属性所解释的。然而,这却忽略其他比主流哲学发展得更为成熟的本体论。这些替代的本体论强调过程、关系和转换的优先性,而不是元素和属性,它们可以追溯到卡西尔、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柏格森和当今的结构实在论。在我对世界—大脑关系的描述中,我预设了这样一种基于关系的本体论(relation-based ontology),即结构实在论,它是世界和大脑的关系,是一个部分(如大脑)与整个(如世界)的整合或联结,由此构成并提供可能的精神特征(意识)的必要本体论条件。因此,我认为精神特征在本体论上是基于关系的,而不是基于要素的,因为它们可以追溯到世界—大脑关系。正如我所希望的,这清楚地表明我比4E更激进,精神特征因此必然是内在联系的,也是神经—生态的。
陈:您在《自发的大脑》的最后一章指出,我们应该用世界—大脑问题来取代心身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诺赫夫:对的。在哥白尼前(pre-Copernican)的地心说中,我们站在地球内部的视角(viewpoint)使得我们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围绕它旋转。而当哥白尼站在地球以外位置来观察时,情况就改变了。地球可能只是宇宙中众多行星中的一个,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这就产生了一种日心世界观,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随后的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同样的,我预设了一个从大脑之外的视角,取代了从大脑内部观察的当前视角。大脑、意识甚至世界的神经中心观由此被一种神经生态观所取代,大脑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来适应大脑。我们可以考虑大脑如何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并积极地与之联结或参与其持续的时空动态中。例如,当我们听音乐时,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用脚或手指敲击音乐的节奏,我们的大脑因此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使我们与世界的持续节奏保持一致,即时空关联性。正如我那本2018年的书中所说的,这种时空关联性是意识和精神特征的中心。这一观点取代了目前大脑和意识的神经中心观,取而代之的是神经生态观。意识和其他精神特征由此可以追溯到世界—大脑关系作为它们的基本必要条件和本体论基础。心身关系问题则转化为世界与大脑的关系问题,即世界—大脑问题。正如我所说,只有假设哥白尼后(post-Copernican)的大脑之外的视角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观点使得我们去考虑新的哲学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我目前正在研究类似的哥白尼前后(pre-post-Copernican)时代的自我和人格同一性(personality identity)概念的转变。
陈:同样地,在书中你还说到,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对于神经哲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如天文学内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一样,将会引发神经哲学领域的一场哥白尼革命是吗?
诺赫夫:是的,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用一种精神特征的生态中心观来取代目前对大脑和心灵的神经中心主义,它建立在世界—大脑关系的基础上,并作为其潜在的不充分本体论条件,即意识的本体潜在性(ontological predisposition of consciousness, OPC)。这可以在经验方面即神经方面,由意识的神经前提(neural predisposition of consciousness, NPC)来补充,这是潜在意识的必要非充分的神经条件。NPC在临床领域内非常重要,但它在我们处于昏迷或手术麻醉的状态会消失。如果不将我们从大脑内部的视角转移到大脑外部的视角,我们将无法认识大脑和意识的生态中心模型,而保持当前的神经中心模型。正如我所说,这也对其他的哲学概念,如自我和人格同一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概念也需要以生态或更好的神经生态方式来理解。因此,非还原性的神经哲学,采用哥白尼后而非哥白尼前的观点,也可以为传统哲学问题,如心身问题、自我、人格同一性等,提出新的见解而铺平道路。
陈:如果说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是神经哲学领域的一场哥白尼革命,我们是否同样可以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讲的“范式”概念来理解?这就是说,世界—大脑问题取代心身问题是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神经哲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
诺赫夫:是的,事实上,我想说的是范式的转变。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神经科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连续性。简言之,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实践中隐含的模式和理论,这也包括对方法策略及其有效性的反思。哥白尼革命及其视角的转移,正是两种不同视角的方法论策略的比较,且这两种方法论具有不同的认识论意义。
因此,如果你想作出区分的话,关于哥白尼革命作为方法论策略的讨论是科学哲学的一部分,而它是在神经科学中被实践和隐含预设的。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导致了神经科学中不同的实验范式和研究策略,这与哥白尼的数学形式化使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实验范式和发现成为可能的方式差不多。
陈:我注意到,您在今天的讲座里还提到庄子和莱布尼茨对于时间的观点,它们与世界—大脑关系所说的时间有什么关系?
诺赫夫:时间对我至关重要。时间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神经科学家通常把它理解为时间和空间内对特定点的感知和认知事件。然而,人们也可以从时间的构成来理解时间。莱布尼茨和道家的庄子都提出了这样一种更具建构性的时间观。在这里,世界的特点是时间的不断建构、时间的流逝或时间性。想象一条河,有连续的水流,水流构成或本身就是时间,这里的时间本质上是动态的,即动态的时间。动态时间是在世界内部和大脑自身内连续构建的,然而,这种动态时间的范围显然比嵌套在世界时间内的大脑时间范围大得更多,扩展得更多。在我们关于莱布尼茨和庄子时间的论文中比较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时间概念,并区分了不同的时间层次,这是东西方时间概念的美丽融合。我们认为,庄子可以为莱布尼茨的时间概念提供补充。
需注意的是,这种动态的时间观在现象学中早就被提出了。胡塞尔以惊人的细节阐述了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注意、呈现、保持);海德格尔描述了存在的时间以及我们的时间如何与世界的时间联系在一起。而我的目标是将意识现象学层面(胡塞尔:基于意识的时间)和意识的存在层面(海德格尔:基于存在的时间)基础上的动态时间模型连接到神经元(基于大脑的时间)和最终本体论(基于世界的时间)层面。这样的动态时间黏合了本体论、神经元、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世界—大脑关系因此为动态时间所塑造,具体地说就是,世界、大脑、意识不同层次的时间是如何相互关联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庄子和莱布尼茨感兴趣。现象学是我在哲学上的最初起点,但是,正如我现在看到的,它需要与世界的本体相融合。不同于海德格尔和萨特,现象学不是基于意识或存在,因为它必须与心智相区分,也就是说,独立于我们对世界及其存在和实在的具体研究方式,即本体论。
陈向群:谢谢诺赫夫教授接受我的访问,通过您的解答,我们更加理解了大脑和哲学的交叉研究对于意识问题的意义,我们可以期待,在以世界—大脑关系为代表的非还原性神经哲学理论框架下,人类的意识谜团终究会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