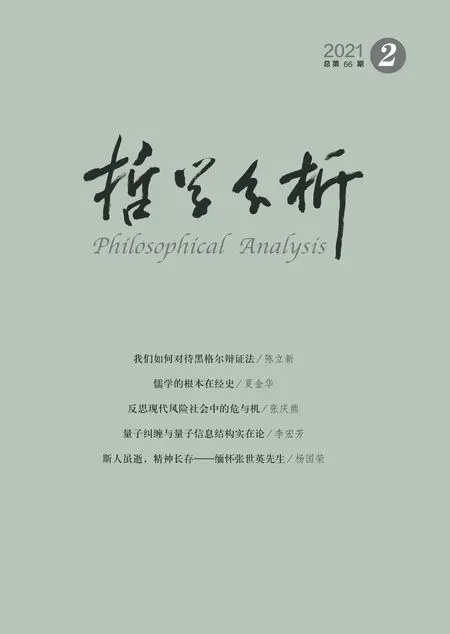论《逻辑哲学论》的简单性原则
张志平
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追求完美写作形式的维特根斯坦崇尚的是简单性原则。①有关简单性,维特根斯坦用的是“einfach”一词,英译者翻译为“neat”(干净的、整洁的,名词为neatness),似乎不妥(参见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p.125)。事实上,“einfach”在德语中有“容易、普通、简便、朴实、简单”等含义,张申府先生把它翻译为“简单”更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参见路·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从本文的分析看,在《逻辑哲学论》中,“简单”既有简洁、精炼、简约的意思,也有朴实无华、不复杂、容易明白的意思,还有不说无意义的废话、不使用没有意谓的概念或多余的词汇的意思。有关简单性原则,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多次提及。在5.4541中,他说:“对逻辑难题(Probleme)的解决必须是简单的(einfach),因其确立了简单性标准。人们总觉得,必定有一个问题(Fragen)领域;在其中,问题的答案——先天——就是对称的(symmetrisch),并联结成一个封闭而规则的结构。这一领域就是命题‘简单性乃真理之标志’(simplex sigillum veri)在其中有效的领域。”①有关《逻辑哲学论》的引文翻译,本文参考了德英对照本中的英译和张申府先生的中译,同时据德语作出笔者认为更准确的重译。由于《逻辑哲学论》中的引文都有编码,可以很方便地查阅、对照,本文就只在正文中标注引文编号,不再加脚注。德英对照本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中译参见路·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5.5563中,他又说:“我们在此应指出的那最简单的东西(Jenes Einfachste),不是对真理的比拟(Gleichnis),而是完全的真理本身。”从中可见,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真理和逻辑都必须是或者说本身就是简单的。简单性原则发挥到极致也就意味着除了必需之外没有多余。由此,简单性原则也就与“奥卡姆剃刀”关联起来。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也两次提到“奥卡姆剃刀”。在3.328中,他说:“如果一个记号(Zeichen)不是必需的,那么,它就是缺乏意谓的(bedeutungslos)。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的意思(Sinn)。”在5.47321中,他又说:“当然,作为准则(Regel),奥卡姆剃刀原则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其实践上的成功被证明为正确的:它的意思是,不必要的记号单元并没有意谓。满足同一目的的诸记号在逻辑上是等值的,而不满足任何目的的诸记号在逻辑上都是缺乏意谓的(bedeutungslos)。”从中可见,就“奥卡姆剃刀”有助于剔除无意义并因此是多余或不必要的符号或概念而言,它也为简单性作出了贡献。②在《逻辑哲学论》中,记号(das Zeichen)与符号(das Symbol)不同——记号是语词的物理属性(如形状或发音),而符号是语词的意义。所以,符号就是有意谓的记号。不过,有些记号虽然没有意谓,但我们可能误以为其有意谓,并因此会把它们当成符号;同一记号在不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意谓,并因此是不同的符号,但我们可能由于它是同一记号而误以为它也是同一符号,并因此产生思想混乱。因此,“奥卡姆剃刀”既可以说是对没有意谓的记号的剔除,也可以说是对没有意义的符号的剔除——虽然“没有意义的符号”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也可以说是对思想混乱的剔除。
维特根斯坦对简单性原则的推崇,在蒙克的评价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谈及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时,蒙克说:“如果此书有一个可能多余的词,它的美就会被毁掉。”紧接着,蒙克就认为这话也同样适用于维特根斯坦。他说:“维特根斯坦无疑会赞同并接受这种对作品之美的诉求。用《逻辑哲学论》那种稀疏的散文风格,他将把罗素在此倡导的无装饰(austere)的审美观带到新的高度。”③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Inc., 1990, p.46.的确,仅从结构和外观上看,《逻辑哲学论》一书就具有一种简单性的写作风格——全书惜墨如金,只有7个主命题,每个主命题下不同层级的子命题也都像格言警句一样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不过,对写作《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来说,简单性不仅仅是一种写作风格,它还体现在其对世界存在的思考及其哲学追求或哲学理念中。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分析简单性原则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体现,剖析维特根斯坦基于简单性原则所表达出来的“形而上学”及其哲学追求,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最后阐释简单性原则本身对哲学的意义。
一、世界本质的简单性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首先是从简单性入手切入对世界存在及其本质的思考的。在他看来,对象乃是构成世界的终极要素,而“对象(Der Gegenstand)是简单的”(2.02)。原因在于“诸对象是构成世界的实体(Substanz),所以,它们不可能是复合的”(2.021),因为“实体就是独立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存在的东西”(2.024)。在此,维特根斯坦对实体的理解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单子。在莱布尼兹那里,作为实体的单子只有没有部分、不可分,才能独立不依,并有资格被称为实体。不过,维特根斯坦更多是从逻辑上把对象定义为简单的,或者说,对象的简单性只是其根据实体定义所分析出来的结论。
虽然简单对象作为实体是构成世界的终极要素,但世界并不仅仅是诸简单对象的单纯总和(Die Gesamtheit)。那样的话,世界的结构、秩序、对象的运动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无从谈起。相反,世界乃是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那么,维特根斯坦是如何从构成世界的终极要素的简单对象过渡到世界乃是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总和呢?这就需要对简单对象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作为实体,简单对象既是内容又是形式(2.025)。作为内容,每个简单对象都具有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并因此是独一无二的(5.5303)、实存的且不变的(2.0271),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简单对象的现实性;作为形式,每个简单对象又都具有由其本质所规定的、与其他简单对象结合成不同原子事实的诸种可能性,并因此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简单对象的潜能。维特根斯坦说:“对象出现在原子事实中的可能性就是该对象的形式”(2.0141)。就此而言,对象就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并且,对象的内容决定着其形式,或者说,对象的现实性决定着它与其他对象建立关系并构成原子事实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事物能够出现在原子事实中,那么,这种可能性必定已经存在于事物当中”(2.0121),并且,“成为原子事实的构成部分,乃是事物的本质所在”(2.011)。
由于每个简单对象的内容都先天地决定着它与其他简单对象结合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构成一种原子事实,而不同的原子事实的“组合”复又构成更复杂的事态,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诸对象蕴含着所有事态(Sachlagen)的可能性”(2.014)。由此可见,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世界归根结底是由所有简单对象的内容及形式所共同决定的;仅就此而言,世界从根本上讲就是简单的。
不过,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简单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作为主体的自我;世界和自我的关系就在于,世界并不是康德意义上超越的自在之物的世界,而是通过我而呈现出来的世界。既然世界只能通过我才呈现出来,所以,我就是世界的界限。只不过,维特根斯坦所理解的“我”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作为人类的我,而是类似于胡塞尔现象学经过先验还原发现的先验自我。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自我并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心理学所探讨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它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5.641)这样的我通过逻辑性的语言理解、描述世界,世界也只是通过逻辑性的语言才被我所理解和认识,所以“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这样的我作为灵魂也像简单对象一样是简单的,否则,就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说:“的确,一个复合的灵魂也就不再是一个灵魂。”(5.5421)
在此,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就在于:首先,如果对象是简单的,它就不能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感性对象,如桌子、树木、高山等,因为这些事物都是复合的,甚至也不能是诸如分子这样由原子构成的超感性对象;因为这些超感性对象理论上也是无限可分的,但它们必须像数学上的点那样没有部分,但又不同于数学上的点,因为数学上的点除了在坐标轴上的位置不同外,是完全同质的,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每个作为实体的简单对象都与其他简单对象存在着质的差异,更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单子。但是,与封闭的单子不同,每个简单对象又先天蕴涵着与其他特定的简单对象结合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构成一种原子事实。但如此一来,我们就根本无法说出他所谓的简单对象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简单对象也就无法通过语言的命名而进入到我们的思想或命题中。汉斯·斯鲁格就说:“他(即维特根斯坦)最终返回如下观念,即一定存在着绝对的简单对象。这又将我们带回到我们是否能识别它们的问题。对于我们,什么时候到达最终的分析层次有客观标志吗?它们会是什么?”①汉斯·斯鲁格:《维特根斯坦》,张学广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其次,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作为实体的简单对象与简单对象先天结合的可能性构成了原子事实,但我们通常的主谓命题意指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实体与实体的结合,而是实体与属性的结合,如“雪是白的”,或者说,它所表达的是种和属之间的归属关系,如“雪是(属于)白的东西”。由此,由作为实体的诸对象的结合构成的原子事实,如何与表征实体与属性或种属关系的基本命题具有互换性或同构性就成为问题。至于特定的简单对象与简单对象相互结合的先天的逻辑可能性从何而来,维特根斯坦对此也并未作出论证,而只是好像在凭直觉进行断言似的,由此,逻辑就成了世界的命运,即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其作为逻辑上的可能性必然已经存在而言,都是“命中注定的”了。更进一步讲,虽然某个简单对象与其他特定的简单对象彼此结合的可能性已经先天存在于对象的本质当中,并由此为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规定了一个可能性境域,但是,什么样的可能性能过渡到现实性或从现实性复又变成可能性,过渡或回归的原因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从维特根斯坦的结论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答案。对此,他的回答是:“所有的发生(Geschehen)和如此这般的存在(So-Seins)都是偶然的(zufӓllig)。”(6.41)那么,使其成为偶然的原因又何在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其原因不在世界之中,否则原因本身也将是偶然的(6.41)。由此,他就把现实世界以及其中事物的实存和事件的发生归于某种超乎世界之外的不可思议者。再次,由简单对象构成的简单事实即原子事实在何种程度上是简单的,维特根斯坦对此也未给出任何说明。他并没有说原子事实是由两个还是多个简单对象构成的,而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原子事实就是由诸多对象结合而成的”(2.01),但问题是,两个以上的对象所结合成的原子事实是否可以被分解为诸多的简单事实呢?如果可能,是事实上的可能还是逻辑上的可能?如果不可能,是事实上的不可能还是逻辑上的不可能?由于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很难给出一个原子事实或简单对象的例子,所以,蒙克才会说:“维特根斯坦既不能举出基本命题或原子事实的例子,也不能说出‘简单对象’是什么;但是,他觉得,假如语言和世界的结构允许一个对另一个作出映射,那么,正是对此进行分析的可能性要求有这样的东西存在。”①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p.129.很显然,简单对象和原子事实只是其对世界的存在结构进行分析或作出“形而上学”思考得以可能的逻辑前提,也因此是他的一种逻辑预设。早在《1914—1916年笔记》中,他就说:“我们意识到简单对象(der einfachen Gegenstӓnde)——先验地——作为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存在。”②Ludwig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1916, G.H.von Wright and G.E.M.Anscombe (eds.), G.E.M.Anscombe(trans.),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9, p.60.
最后,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自我具有语言,不构成世界的部分,是世界的界限,是非复合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只有构成世界的事实和事态才是命题的对象,并因此是可说的。对这种悖论,维特根斯坦也许只能通过采取某种反讽的姿态来加以化解,如把自己的哲学命题本身也当成无意义的加以丢 弃。
二、命题形式的简单性
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也是通过一个极简的表达式加以描述的,那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在于,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真值函数的普遍形式(Form)是:这就是普遍的命题形式”(6),另一方面又说“普遍的命题形式就是命题的本质(Das Wesen)”(5.471),而“指出(angeben)命题的本质就是指出所有描述(aller Beschreibung)的本质,也就是指出世界的本质”(5.4711)。很显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命题的普遍形式、命题的本质、描述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拥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并因此能彼此“映射成像”。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接下来对此加以解释,由此就可看出,它与维特根斯坦对世界的理解是完全同构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命题在思想中形成事态的逻辑图像。命题可分为复合命题和基本命题。前者由后者构成,而后者又由名称构成。名称是对简单对象的命名,所以,名称也是最简单的、不能再进行界定的符号。维特根斯坦说:“名称是简单记号:我用单个字母(‘x’‘y’‘z’)来表示它们”(4.24);“一个名称不能通过定义而被进一步解析:它是一个原始符号”(3.26)。由名称构成的基本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图像,并因此也是最简单的。他说:“最简单的命题,即基本命题(Elementarrsatz),断定原子事实的实存(das Bestehen)”(4.21);“如果基本命题为真,那么,原子事实就实存;如果基本命题为假,那么,原子事实就不实存”(4.25)。如果要从逻辑上把所有的基本命题归于同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就可以表示为:;其中P是基本命题变元,则表示P的全部取值。在此情况下,()也就是P的真值函数。复合命题由基本命题构成。类似地,如果要从逻辑上把所有的复合命题归于同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就可以表示为;其中,ξ作为变元代表任意一个或一组复合命题,则表示ξ的全部取值。换句话说,()也就是ξ的真值函数。由于ξ是由诸多基本命题构成的,所以,()最终也是诸多基本命题的真值函数。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诸基本命题的真值函数。(一个基本命题则是其自身的真值函数。)”(5)从P到ξ,一方面意味着命题由简单到复杂的递推性过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即都是命题。当命题为真时,其所指的就是逻辑上可能且实存的事实;当命题为假时,其所指的就是逻辑上可能却非实存的事态。由于世界就是由所有实存的事实和逻辑上可能却非实存的事态构成的,所以,要指出世界的本质,命题的普遍形式就必须把所有的真命题和假命题都涵盖其中。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N()这样的逻辑运算。其中,N是Negation(否定)的意思,是对的值的否定。维特根斯坦说:“N()乃是对命题变元ξ的一切值的否定(Negation)。”(5.502)具体来说,在都为真的情况下,通过N(),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反的假命题。通常情况下,真命题构成的集合都是有限的,通过N()运算得到的假命题也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构成世界的部分的逻辑图像。如果我们有一个足够充分而复杂的命题或无限的命题系列,只要它对整个实存世界作出语言描述,并构成整个实存世界的逻辑图像,那么,通过N()得到的无限的否定命题系列就会对整个非实存但却可能的世界作出描述,并构成整个可能世界的逻辑图像。由此可见,作为命题的普遍形式也就指出了包括可能世界和实存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本质;与此同时,它也排除了逻辑上不可能的“世界”。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所有真的基本命题都被给出,结果就是对世界的完全描述。通过给出所有的基本命题,并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得到了完全的描述。”(4.26)很显然一方面完美体现了维特根斯坦所追求的“简单性乃真理之标准”,另一方面也构成其极简的“形而上学”。不过,与诸如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尼采的“权力意志”等对世界本质作出具体规定的形而上学很不一样对世界的性质到底如何并没有任何的言说。对此,维特根斯坦的解释是:“我们为理解逻辑所需的‘经验’(Erfahrung)并不是某物有如此这般的表现,而是某物存在(ist):但是,这恰恰不是什么经验。逻辑先于一切经验——即对某物是如此的经验。它先于如何(Wie),但不先于什么(Was)。”(5.552)在此,维特根斯坦区分了世界的如何和什么。世界的什么,即世界的存在或非存在,是可以通过逻辑而得到先天的界定或揭示的,而世界的如何,即世界的具体属性,如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等,则是逻辑命题根本不触及的。故而,对于他来说,从本质上讲,世界仅仅是由实存事态和可能事态构成的,也唯有这一点才与纯粹空洞的普遍的命题形式相对应,并与逻辑相关。那么,世界的本质和命题的本质为何会在逻辑上建立这种同一性关系呢?原因就在于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我。一方面,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1.1)是我的世界(5.62),另一方面作为“命题总和”的语言(4.001)是唯有我才懂得的语言(5.62),正是“我”构成了两者之间具有同一性的中介。基于此,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语言与世界的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意味着语言和世界共有某种逻辑结构;命题性语言是逻辑的,世界也同样如此。维特根斯坦说:“逻辑布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5.61)由此可见,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自我也同时是逻辑性的自我,或者说,是意识到语言和世界之逻辑性的自我,而这样的自我也只能是哲学性的自我。
在此,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就在于,首先,如前所述,既然作为实体的简单对象只是他的一种逻辑预设,就实际的生活世界而言,我们根本找不到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要对找不到的简单对象进行命名,除非我们承认这样的命名是纯粹空洞的,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命名不可能,那么,对事实进行描述的命题以及由命题的总和构成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而这与我们的常识恰恰是违背的。其次,在日常语言中,名称既有专名,也有类名,而类名中既有种名,也有属名,那么,给简单对象命名,是给个体的专名,还是给类的种名或属名呢?维特根斯坦对此语焉不详。事实上,他也排斥这样的区分。他说:“在逻辑中没有并列,也不能有分类(Klassifikation)。在逻辑中,不能有一般(Allgemeineres)和特殊(Spezielleres)之分。”(5.454)但是,如果每个名称都是专名,语言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作为专名的名称的数量将远远超乎人类记忆力的容纳范围,这样的语言充其量只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思辨”中。即使这样的语言可能,大多数的描述性命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有实质性内容的命题中,一般与一般或个别与一般的结合很常见,而个别与个别的结合却很罕见。例如,在“雪是白的”中,“雪”和“白”或“白的东西”都属于一般性的类名,在“这棵树是绿色的”中,即使“这棵树”特指眼前如此这般的树,从而是专名,姑且不论其可用来指任何一棵眼前的树的一般性意义,“绿色”或“绿色的东西”也是一般性的类名,而不可能是特指眼前这棵树的叶子上如此这般的绿色的专名。更何况,由于树的绿色也是深浅不一的,即使绿色特指这棵树的绿色,它也不是专名,不是意指眼前特定的某一点、某一块或某一片绿色,而是意指树叶上深浅不一的绿色的同一性。事实上,没有一般性,就不可能有语言,也就不会有命题。专名与专名结合的命题也是有的,例如,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如“张三是张三”,但这样的命题,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是”虽然不是名称,但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甚至张三也可以作为名称用到不同个体身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这种情况毕竟是缺乏意义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少用到。还有描述个体与个体关系的命题,如“张三打李四”,但在这样的命题中“打”一词也已经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而并非个别动作的专名,因为在“打”的过程中,“打”的动作也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而“打”只是意谓所有这些动作在本质上的同一性。不仅如此,像“张三是人”“张三怀疑李四”这样的命题并非属于同一类型,如果不考虑其中的差异,维特根斯坦对命题的逻辑思考就要么违背了语言的日常使用,要么自成一统而无关乎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再次,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并非纯粹的演绎逻辑,而是哲学性的描述性逻辑——“在哲学上没有演绎,它是纯粹描述的”,即它对世界的本质仍有所言说,所以,把对世界是“什么”的认识与对世界是“如何”的经验加以割裂,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带上神秘色彩。换句话说,如果“逻辑先于一切经验——即对某物是如此的经验”(5.552),那么,作为思想者的他就能够超越于事实性的经验世界而与世界本质建立一种先天性的认知关系。由于他由此发现的世界本质又先天地规定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态,如此一来,作为思想者的他似乎就处在“上帝”的位置或拥有“上帝”的视角,其性质恰恰如斯宾诺莎断言“神即自然”一样。但是,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世界本质的逻辑思考不需要感性经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像“可能性”“现实性”“原子事实”这样的范畴,甚至“世界”概念本身,都只不过是根据日常的感性经验所抽象或提炼出来的,或者说,是其从日常经验“悟到”的。当然, 就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的真假独立于经验事实的是否实存而言,逻辑的确是先验的(transcendental) (6.13),但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量命题并非“一无所说”的逻辑命题(6.121),而是有所言说的断言式的描述性命题,如“我们为自己画出事实的图像(Bilder der Tatsachen)”(2.1),而他的图像说也是源于他受汽车事故与法庭上呈示的事故模型之间“映射成像”关系的启发。①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p.118.最后,如果他的“真值函数的普遍形式(Form)是(6),它既描述了命题的本质,也描述了世界的本质,很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对语言与世界所共有的逻辑形式的言说,但是这恰恰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即命题与世界之间共有的逻辑形式只能显示而不能言说。类似地,像“命题是实在的一幅图像”(4.01)这样的命题用语言来描述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悖论,因为它似乎是站在语言和实在的关系之外来看待两者的关系的,但这从逻辑上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悖论,所以,维特根斯坦才会自嘲地认为,他自己在书中所表述的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unsinnig),并最终应该像梯子一样被超越或扔掉(6.54)。
三、哲学思考的简单性
有关哲学,《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是这样理解的:“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澄清,哲学不是学说,而是一种活动”(4.112);“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是晦涩的和模糊的:哲学的任务就是使思想清楚,并为其划界”(4.112);“哲学的正确方法确实应当如此,即:除了能说的,即与哲学无关的自然科学命题外,什么也不说”(6.53)。从中可见,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存在的意义就类似于管道疏通工,其目的仅在于对语言管道进行疏通、修理,以使自然科学性质的言说更加流畅和清晰;至于哲学本身,则没有独属于自身的理论目的,除了辅助自然科学之外,哲学并不提出自己的学说,因为超乎自然科学命题的言说都是无意义的。不过,早在1913年的《逻辑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却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哲学上没有演绎;它是纯粹描述性的。‘哲学’这个词永远应该指某种超乎自然科学或低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与自然科学并列的东西(这在《逻辑哲学论》4.111节中也提到过)。哲学并不提供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确证也不能驳倒科学的研究。哲学是由逻辑和形而上学构成的,逻辑是其基础。”①路·维特根什坦:《名理论》,第89页。其中的《逻辑笔记》是由陈启伟先生翻译的。很显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笔记》中与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哲学的理解存在着矛盾,因为在前者中,哲学是纯粹描述性的,必然要有所言说,而且这种言说还要在自然科学之外通过逻辑分析确立自己的形而上学,由此哲学就不是辅助性的或低于自然科学的,而是有着自己存在的独立目的与意义,甚或高于自然科学。事实上,这样的矛盾在《逻辑哲学论》中始终存在,因为维特根斯坦毕竟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按照“哲学的正确方法”从事哲学,而是在自然科学之外,通过这样的表达式确立了自己极简的“形而上学”。
除了体现在其所确立的极简的“形而上学”中之外,简单性原则在维特根斯坦上述哲学理念和哲学追求中的体现还在于:首先,为了使思想获得清晰性和确定性,有必要对语言进行批判,澄清语言的表面逻辑和内在逻辑,用“奥卡姆剃刀”剃除词语的歧义性和模糊性,把原本复杂的日常语言改造为简单的理想语言,以使表达更精确,逻辑更严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思想的混乱是由同一个语词用法的多样性引起的,例如,德语的ist就既是系词,又表示相等和存在,等等(3.323);“为了避免这类错误,我们就必须使用一种排除了这类错误的记号语言,即不用同一记号(Zeichen)表示不同的符号(Symbolen),也不用表面上相似的方式使用具有不同意指模式的记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受逻辑语法——逻辑句法——支配的记号语言”(3.325)。很显然,维特根斯坦在此试图建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记号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对象的同一性,我用记号的同一性来表示,而不是借助于等号。对象的差异性则用记号的差异性来表示”(5.53)。也就是说,要用同一记号表示同一对象,用不同记号表示不同对象;用不同记号表示同一对象,为表明它们表示同一对象又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乃是多此一举。更何况,“说两个东西是同一的,这是胡说,而说一个东西与自身等同又等于什么都没说”(5.5303)。其次,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大多数哲学命题并非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并因此需要通过指出它们的无意义性而加以剃除;经过这样的剃除,哲学臃肿的身材就变苗条了,而思想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简洁和清晰。他说:“一直以来,有关哲学论题所写下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非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无法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着重指出(feststellen)它们的无意义性(Unsinnigkeit)。”(4.003)这些命题和问题之所以无意义,除了与哲学家混淆了语言的表面逻辑和真正逻辑,与语言的不完善性有关,还与哲学家的越界思考即对不可说者的言说有关。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可说的东西属于事实世界,因为语言就是对事实世界的“映射成像”;事实世界原则上具有可经验性,所以,我们能够对描述事实的命题作出或真或假的判断,从而使命题获得自身真值上的确定性。反过来说,凡是超出事实世界的东西就都是不可言说或不可思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我们又可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逻辑上就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言说的不可说者,如命题和事实所共有的逻辑形式。这是因为,“为了能够描述(darstellen)逻辑形式,我们必须能够把我们自己连同命题一道置于逻辑之外,即置于世界之外”(4.12)。也就是说,要描述两者共同的逻辑形式,我们必须既超越于语言也超越于世界,但这在逻辑上就像要画出圆的正方形一样是不可能的。另一类是逻辑上可说,但对其言说没有真假可言的不可说者,如绝对的善恶、意志、人生的绝对价值、绝对的美丑、死亡、灵魂不朽、世界存在的原因,等等。在此,说它们不可说,并不意味着人们根本对它们不说或不能说。相反,从古至今,人们就相关话题一直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只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于这种言说超越了事实世界,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假,从中也就得不到任何确定性或真知识。正因如此,维特根斯坦说:“伦理学,如果真有的话,也是超自然的,而我们的语词只会表达事实。”①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Occasions,1912—1951, James C.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 (ed.),Hackt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3, p.40.不过,这第二类不可说者虽然不可说,但对我们并非无关紧要。维特根斯坦说:“我的全部倾向,并且,我相信,所有曾试图就伦理或宗教进行写作或谈论的人的倾向,就是冲破语言的边界。要冲破我们的牢狱之墙,那是完全、绝对地没有希望的。伦理学,就其根源于想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说点什么的愿望而言,不可能是科学。它之所说绝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它见证着人类心灵的一种倾向;对此倾向,我个人禁不住要抱有深深的敬意,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嘲笑它。”①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Occasions,1912—1951, James C.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 (ed.),Hackt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3, p.44.维特根斯坦为何不会嘲笑这种倾向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体现出人之为人所具有的追问究竟的高贵秉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言说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会通过我们的追求、行动、信念或信仰显示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左右我们的情绪或情感,带给我们幸福或痛苦,并因此塑造我们自己的存在。在有关宗教的讲演中,针对有人相信最后的审判,维特根斯坦就说:“追问他是不够的。他或许会说他有证明。但是,他拥有你或许会称其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东西。它会显示出来,但不是通过推理或诉诸日常的信念理由,而毋宁是通过调控他一生的所有作为。”②L.Wittgenstein, 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 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 Cyril Barrett (e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54.可见,对不可说的东西,如果我们就有关它的言说的真假进行争论或追问其真值如何,那将是徒劳的和无意义的,并因此需要动用“奥卡姆的剃刀”剃除;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重要的不是这类言说的真值如何,而是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何,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那种无谓的追问和争论中摆脱出来,并通过自己的生活和行动显示出自我对不可说者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自我生活的意义。以基督教信仰为例,维特根斯坦就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信仰是否是真的,而在于在应对难以承受和无意义的生存时,它是否给人们提供了某种帮助。③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p.122.
在此,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在于:首先,当他为了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而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用同一记号来表示同一对象的可能性问题。如果对象是纯粹的逻辑对象,那么,逻辑对象作为抽象的同一性用同一的记号表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这种理想语言要像日常语言那样具有实质性的所指,问题就出现了——同一对象如何获取?如果同一对象是个体,那么,由于个体数目的无穷无尽,这样非但没有剃除多余的词语,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词语,使语言变得臃肿无比;如果同一对象是一般,那么,一般由于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的集合,个体的差异性也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对一般的涵义的理解或者使其发生变异,同一记号要维持自身的同一性也因此会变得十分困难,这就像人们对“人是什么”会有不同的理解一样。其次,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除了可说者即自然科学命题外什么也不说,另一方面《逻辑哲学论》本身却说了许多非自然科学命题的东西。很显然,他终究未能用“奥卡姆剃刀”完全剃除掉他所谓“无意义”的哲学命题,而只是让大家把它们像梯子一样扔掉。最后,他在全书的结尾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人必须保持沉默”(7),这句对思想本身发出“简单性”要求的“绝对命令”本身也是极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似乎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就意味着不论对不可说的东西的言说对于人的实践生活有怎样的效果,人们也都不必去争论,而是必须保持沉默。事实上,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是一回事,对有关不可说的东西的言说的真假保持沉默是一回事,对这种言说产生的实践效果如何保持沉默又是另一回事。这三者并不能画上等号。就第一层含义而言,由于对不可说的东西的言说不具有确定性,所以,为了逻辑上的自洽和免于在认识论上被质疑,人们就必须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就第二层含义而言,在人们对不可说的东西有所言说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也需要对这类言说的真假保持沉默或不去争论其真假,因为它们本身就没有真假可言,争论其真假完全是搞错了方向。但是,就第三层含义而言,由于这类言说很可能五花八门,虽然没有真假,但对人的实践生活会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对其实践合理性如何也同样保持沉默,那么人在价值追求上就会陷入到虚无主义当中,似乎凡是存在的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此人就会把价值平面化,并因此丧失批判意识,对任何一种人生观、价值观都采取听之任之的随意态度。基于此,我们说,对于有关不可说的东西(如伦理、宗教、美学)的言说,虽然人们不应该去争论其真假,但也应该争论其实践合理性,哪怕这种合理性并非绝对的合理性,而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
四、 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简单性原则乃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因为哲学从一诞生起,就带有还原论的倾向,即在多中寻求一、在变化性中寻找确定性、在时间性中寻求永恒性、在复杂性中寻求简单性。这样的探寻都是通过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加以透析、过滤、简化来达到使世界变得充满秩序,并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目的的。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划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潜能与现实理论,还是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康德的现象与本体界的划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权力意志”等,都是通过其极简的核心性概念或结构性理论试图提纲挈领地让世界的本质对我们变得清晰可见,且不论这样的本质是世界的自在本质还是有哲学家主观性介入的诠释性本 质。
前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简单性原则抱有同样执着的信念。他说:“哲学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结构,这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它是最终的事情,独立于你所能辨识出的一切经验,就确实应该彻底简单(gӓnzlich einfach)——哲学解开我们思维中的结,因而其结果必须是简单的,但是哲学化不得不像哲学解开的结一样复杂。”①Ludwig Wittgenstein, Zettel, G.E.M 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 (ed.), G.E.M.Anscombe (tra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81.很显然,维特根斯坦对之前已经以简单性为原则的哲学的简单性仍不满意,而他最终选择以这样一个极简的命题形式达到对世界本质逻辑性的形而上学思考。对于维特根斯坦坚持简单性原则的原因,斯鲁格给出的解释是:“要否定存在着最终的分析元素,便意味着世界是非限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知识也是不确实和非限定的。但是,‘世界有固定的结构’。对他来说,这显然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分析过程必须结束于最终的简单物,在这一点上过程是有限的。即使分析无限持续下去,我们仍会争辩说:‘它将结束于简单对象。’”②汉斯·斯鲁格:《维特根斯坦》,第54页。斯鲁格的这种解释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有限性原则。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如果追溯动力因的过程是无穷尽的,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有关存在原因的确定性认识;只有当我们的追溯到了第一推动者那里戛然而止,即遵循有限性原则——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是结束于简单物的简单性原则,我们才能最终认识运动的根本原因。
到了《哲学研究》阶段,维特根斯坦在反思语言的日常用法时,意识到从用法上讲“简单性”本身并不简单,并因此对简单性概念本身提出了批判。他说:“我们是以大量不同而又有着不同关联的方式使用‘复合的’(因而还有‘简单的’)一词的。(棋盘上方块的颜色是简单的,还是由纯白和纯黄组成的?白色是简单的,还是由彩虹的七色组成的?长度2厘米是简单的,还是由两个1厘米组成的?但为什么不是由正的3厘米和负的1厘米组成的?)对于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即‘这棵树的视觉形象是复合的吗?其组成部分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那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复合’。(当然,这并非一个答案,而是对问题的拒绝)。”③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E.M.Anscombe, P.M.S.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trans.),Revised 4th edition by P.M.S.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 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pp.26—27.他又说:“我们看见复合之物(如一把椅子)的组成部分。我们说椅背是椅子的一部分,但椅背本身又是由不同的木块组成的,反而椅腿是它简单的组成部分。我们也看见一个整体在变化(被拆毁),而其组成部分却保持不变。这些就是我们绘制实在图画的素材。”①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p.33.从中可见,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来说,《逻辑哲学论》中预设的简单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瓦解的,即这样的对象要么仍会被解析为复合对象,要么就根本不可能;反过来说,即使可能的话,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简单性。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变化,斯鲁格说:“与《逻辑哲学论》‘对象是简单的’学说形成强烈的对比,维特根斯坦现在断言,不存在绝对简单性或绝对复合性这类事物。当我们称某物简单或复合时,我们这样称呼总是关联着某一标准或尺度。‘如果我对某人说‘我现在眼前看到的东西是复合的’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他就有理由问我:你说‘复合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什么都可以这样说!”②汉斯·斯鲁格:《维特根斯坦》,第59页。
维特根斯坦在简单性原则上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也是哲学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一个缩影。现代性哲学重视同一性、统一性、基础性、绝对性、秩序性、一元性,而忽视差异性、多样性、去中心性、相对性、无序性、多元性等。这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仍抱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将世界的秩序与结构理想化,却离存在和生活的现实相去甚远。不过,后现代性哲学由于离地面太近,过于微观,看到了太多的变化与差异,又面临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也许,只有认识到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辩证统一,保持两者之间合理的张力,才不会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偏执一端,哲学思考也才能更贴近事情的真相,为人的生活实践贡献更多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