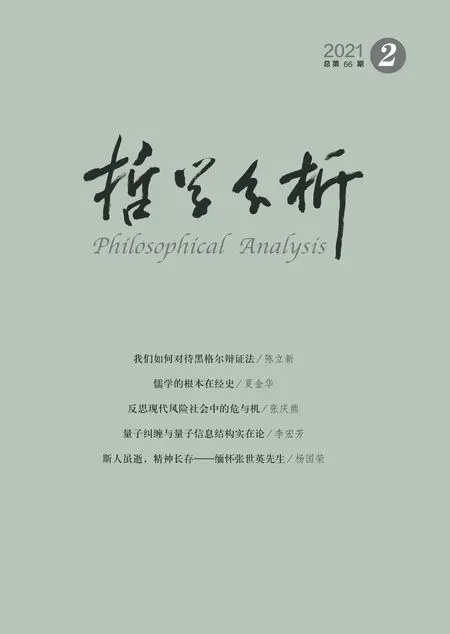如何理解贫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田书为
18、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得到了高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也引发了普遍化的贫困问题,整个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加剧。这样的社会现实,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在黑格尔那里,贫困成为阻碍现代社会走向国家阶段进而实现伦理的最后阻碍;在马克思那里,贫困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并蕴含着超越现代社会历史局限性的内在力量。很明显,他们对贫困问题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不同。厘清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把握黑格尔、马克思思想的特点,求解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本质,超越当代世界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价 值。
一、黑格尔视野中的贫困
首先要指出的是,贫困概念不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范畴,贫困问题也不是黑格尔关注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涉及贫困现象,不过《哲学全书》中几乎没有讨论过贫困问题,而是指出:“由于我在我的法[哲学]的原理中发挥了哲学的这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比起对其他部分来可以说得更简略些”①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根据《黑格尔全集》 (历史考证版),这句话在1817年版《哲学全书》中并不存在,在那里,黑格尔只用了400节和401节两段,就引出了“法”的内容。②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13,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0, S.224.不过,在1827年版《哲学全书》中,黑格尔加上了这句话,并指出,“法[哲学]的原理”就是“(Berlin 1821)”③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19,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9, S.354.,即《法哲学原理》。1830年版《哲学全书》则对此句进行了完整保留。④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0,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2, S.481.所以,黑格尔似乎认为,《法哲学原理》已经解决并消化了贫困问题,而且贫困问题也构不成“客观精神”的重要环节,所以之后无需赘述。实际上,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只是从“警察和同业公会”阶段开始,才逐步涉及贫困问题,而且篇幅极为有限。至于到了“国家”阶段之后,虽然也有提及,但贫困问题的“曝光率”还不如之前。这样的文本排布,确实能够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黑格尔没有构建系统的贫困理论。
即便如此,贫困问题对于黑格尔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5页。“苦恼”在于贫困问题不易解决,这一点显而易见。至于“重要”,则在于,社会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将使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陷入相互分裂,作为特殊性的个体,将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实体性本质;作为普遍性的实体,将由于缺乏个体特殊性的充分延伸而愈发空虚。诺瓦科维奇(Andreja Novakovic)的说法或许更加清晰,他认为:“黑格尔将这个世界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方面,高尚的方面,追求荣誉、权力、承认;市民的部分,追求财富利润……黑格尔认为,利己主义的驱动创造财富,并以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为终点,尽管个体在创造这种财富时对公众利益完全漠不关心。这样,整个社会,包括对更高程度的‘教化’的渴求,也都最终受惠于这种‘基础性’的经济活动。”⑥Andreja Novakovic, Hegel on Second Nature in Ethic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94.遗憾的是,贫困的负面意义恰恰在于,使这种“基础性”的经济活动难以为继,所以它最终阻碍的不仅是贫困者充分张扬个性并满足特殊欲求,更是整个社会“高尚的方面”的真正建构,也就是“国家”的实现。所以,不得不承认,贫困问题事关重大,决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问题。
《法哲学原理》和《哲学全书》都是黑格尔生前出版的著作,至于他生前未出版的《法哲学讲义》,其实包含着很多对贫困问题的精彩阐释。所谓的《法哲学讲义》,是指1817年以后,黑格尔讲授法哲学课程时的讲义,不同年份内容很不相同,主要由他的学生整理记录。《法哲学原理》最初不过是黑格尔讲授法哲学课程时自己使用的讲稿①参见邓安庆:《黑格尔〈法哲学〉版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真正上课时,黑格尔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很多发挥。对一些贫困现象的扩展描写,及其背后根源的深入挖掘,甚至黑格尔贫困思想的变化,只能从不同年份的《法哲学讲义》而非《法哲学原理》中才能发现。不过,《法哲学讲义》的大部分内容,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伊尔廷(Ilting)系统出版,《黑格尔全集》 (历史考证版)对这部分内容的编辑出版,也是到了2015年才完成。伊尔廷曾指出,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应当与他的法哲学讲演录联合起来看。但只要这方面的全部材料还根本未曾出版或出版不足,那么就几乎不存在这种联合的可能性”②卡尔—海因茨·伊尔廷:《〈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评论版“导论”》,载邓安庆主编,《黑格尔的正义论与后习俗理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贫困思想的全貌,在他逝世之后几乎被尘封了半个世纪,国内外学界或许是在最近几十年,甚至最近几年,才拥有认知和把握它的可能。
那么,黑格尔究竟如何理解贫困?黑格尔总体上认为,贫困问题的核心是精神贫困,即“贱民精神”,而这一核心的外化,将导致社会中底层劳动阶级脱离分工体系而遭遇极端的物质贫困,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黑格尔反思贫困问题的基本维度。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市民社会,以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为基础,赋予个体平等的发展机遇和自我实现的可能。随着市民社会原则的不断展开,市民由于自然条件和能力素质的差异,处于社会分工体系的不同环节,从社会普遍财富中获得不同的特殊财富,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且财富分配的差异会不断扩大,最终使市民分为财富所有量差异很大的两个阶级:“富有者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③“富有者阶级”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245节中专门使用的术语,“底层劳动阶级”是本文根据《法哲学原理》第243节中“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一语及其前后文概括而来(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44—245页)。。不过,如哈德曼(Michael O.Hardimon)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并不为这种社会不平等所困扰。相反,黑格尔认为,为表达天赋、技能和努力的不平等提供场所,是市民社会的适当职能之一”④Michael O.Hardimon, Hegel’s Social Philosophy: The Project of Reconcil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7.。黑格尔真正在意的是,在面对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时,市民社会中两个阶级产生“贱民精神”⑤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26,2,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5, S.994.。富有者阶级认为,自己不必遵循市民社会原则,认为自己拥有超越“法”的力量,有权力随意剥夺他人的财产,不再自食其力;底层劳动阶级,也认为自己不必遵循市民社会原则,认为市民社会原则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所以干脆好逸恶劳。西佩(Ludwig Siep)对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有非常清晰的概括:“早期工业化的大生产,导致了在资本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广大群众的愈发贫困之间,形成了不断尖锐的阶级对立”,这导致的“不仅是贫困的贱民,还有富人的狂妄,及其对法律和权利忠诚的轻蔑”①Luwig Siep, Ak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Hegels,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S.72.。此时,两个阶级都处于精神贫困的状态,因为他们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44页。,彻底阻断了自身通往“国家”阶段的路径,毕竟在黑格尔那里,个体在精神层面意识到他与共同体利益的同一性,是伦理实现的根本标志。
当然,黑格尔没有仅在意识层面探究贫困问题,他同样关心精神贫困外化的物质后果。精神上的贫困(“贱民精神”)使底层劳动阶级,脱离了市民社会的分工体系,“生活水平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③同上。,最终处于物质上的极端贫困状态,精神层面的贫困被现实化了,它是市民社会走向分裂的现实表现,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无法统一具体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黑格尔说出了那句名言:“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④同上书,第245页。所以,这里所谓的“贫困”,根本上指在社会中泛滥的精神贫困(“贱民精神”),其次是指底层劳动阶级抛弃市民社会原则后身处的极端物质贫困。中译本《法哲学原理》第244节里的一句话:“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⑤同上书,第244页。,存在严重误译。因为,根据这样的翻译方式,底层劳动阶级被抛出社会分工体系的这个物质因素,似乎成了“贱民精神”得以产生的原因。但已如前述,这与黑格尔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其症结在于,中译本把原文中“damit”⑥G.W.F.Hegel-Gesammelte Werke, Band 14,1,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9, S.194.译为“从而”表达因果关系,而实际上“damit”在这里表达并列关系,应译为“同时”。整句话应当译为:“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同时,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相比之下,英译版把“damit”译为“and”表并列的方式,更贴合黑格尔的原初想法。⑦G.W.F.Hegel, Outline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M.Knox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8,p.221.
其实,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贱民精神”在富有者阶级那里也必然发生外化,只不过,其外化的结果与影响,黑格尔少有提及。应当承认,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理论不足。所以,黑格尔关心的精神贫困,是社会中两个阶级共有的;至于他关心的物质贫困,只是脱离分工体系的那部分群体遭遇的。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的反思
相比于黑格尔,贫困概念是马克思从始至终都使用的范畴,贫困问题也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关心的问题,而且在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马克思用不同的术语体系,表达着自己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遭遇着“普遍的不公正……表明人的完全丧失”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这里,所谓“普遍的不公正”“人的完全丧失”本质上描述的都是阶级对立与工人阶级极度贫困的社会现象。到了《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使用“异化劳动”②同上书,第157页。这一范畴,指出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概述工人阶级贫困境遇的社会基础。至于《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又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出发理解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产生、发展与消灭,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源于资产阶级对它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里,则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工人阶级日益贫困、资产阶级日益富裕的经济根源,等等。应该说,面对现代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面对社会中两大阶级的尖锐矛盾,马克思始终用一系列复杂变化的理论框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并尝试寻求超越的路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贫困问题的讨论,往往被包裹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中,这很自然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马克思形成了复杂而丰富的贫困思想。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同样认为贫困问题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不过对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解很不相同,归根到底,这是由二者哲学理念之差异导致。黑格尔之所以认为精神贫困是贫困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精神贫困现实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另一方面,更是由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使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乃至“主观精神”经过“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的演进,本质上都是“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在《哲学全书》“精神哲学”部分的“绪论”中,黑格尔指出:“精神的一切行动只是对于它自身的一种把握,而最真实的科学的目的只是:精神在一切天上和地上的事物中认识它自身。”③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第2页。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黑格尔而言是“客观精神”的发展环节。在“法”这一阶段中,黑格尔指出,“精神在其自身自为地存在着的自由的直接性里个别的精神……他是人(Person),即对这个自由的自知”①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第317页。。的确,“人”是客观精神中活跃着的因素,具有主观能动性,但这仅是“精神”运动的组成部分,体现为“人”对自身实体本质的漫长“自知”过程。若用《精神现象学》中的语言概括,这个过程将表现为“意识的各个形态”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页。,而非对象化的物质活动领域经历的不同阶段。所以,黑格尔理解的,本质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当然,黑格尔不是不在意人的外部对象,只不过,外部对象没有独立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因为,“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③同上书,第60页。。按照这样的思路,作为市民社会中人思想认识领域的重要特征,精神贫困(“贱民精神”)自然被黑格尔视为贫困问题的核心。
与黑格尔针锋相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尝试确立“感性的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前提性意义,进而超越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黑格尔则“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⑤同上书,第201页。。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一个观点,即历史的起点并非黑格尔式的抽象概念,而是“感性的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⑥同上书,第194页。。应该说,费尔巴哈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努力把具体的人从黑格尔庞大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⑦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洪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页。。否则,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只能是从属性的,只能是绝对精神展开的一个环节,只能是某一主词的宾词,属人的东西只能经由外在的设定才能真正属人。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造,上帝和人虽然仍是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不过,主词和宾词所标识的,不再是本质和属性,而是存在和本质。这意味着,人是上帝的本质,在人的认知能力之外,无法存在一个超验的上帝,上帝只能以人的方式对人存在,“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⑧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页。。那么,在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革命之后,如何理解“人”?“感性”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费尔巴哈的“感性”,包含“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不仅指人肉体上的欲求和需要,也指“感情、感觉、同情心和爱情”①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前者具有基础性、前提性意义。应该说,这一点总体上被马克思继承下来。
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一些想法,但他认为,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的实践领域出发,才能赋予“感性的人”以具体规定,才能真正认清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更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在此,马克思表达出至少两层含义。第一,“感性”的人,即“现实中的个人”是具体的,在物质生产及其交往关系中才拥有其现实性,若像费尔巴哈一样,仅从认知能力对之予以界定,“感性”的人仍旧只具有黑格尔式的抽象意义;第二,人类的精神活动,本质上是物质活动的主观呈现,是生产实践的思想产物。所以,精神贫困的性质、特点,本质上也要由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贫困,即物质贫困的性质、特点决定。另外,马克思还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③同上书,第525页。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自身不是独立的,它依托于物质生产活动,所以思维观念的改变要在变革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精神贫困,作为人们思想观念的阶段性特点,也要在消灭物质贫困的基础上,才能被消灭,而不能如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般,仅在精神领域内部,寻求改变人们思想认知模式的路径。到此,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指出,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主观产物,物质贫困才是贫困问题的核心。
随着唯物史观的逐步确立,马克思已经能够对黑格尔贫困思想反映出的世界观进行更加清晰的概括。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清晰地概括出黑格尔哲学理念的本质,“把逻辑范畴看作一切事物的实体……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④同上书,第600页。。的确,在黑格尔的贫困思想中,逻辑范畴的演绎发展,统摄着历史的现实进程,与其说黑格尔在通过逻辑解释历史,倒不如说在让历史服务逻辑。关于这一点,从黑格尔对待贫困问题的方式上,就可轻易发现。阿维纳瑞(S.Avineri)认为,贫困问题是黑格尔“唯一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任其悬而未决的地方”⑤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与之类似,鲁达(Frank Ruda)也声称,“尽管黑格尔讨论了一系列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他也清楚地指认,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①Frank Ruda, “That Which Makes Itself: Hegel, Rabble and Consequences”, in Hegel’s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 Critical Guide, David Jame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62.。这并不奇怪,毕竟,黑格尔的哲学观使他过分专注于精神贫困,而无力细致审视物质贫困的来龙去脉。可更遗憾的是,他心知肚明,贫困问题的加剧会致使其伦理构建的崩溃,却不去努力解决现代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是在《哲学全书》中,十分不坦诚地把这一困境略去了。很显然,黑格尔之目的,仅是逻辑上的自圆其说,此举是其客观唯心主义思路的延续。马克思不无讽刺地指出,黑格尔式“历史的哲学仅仅是……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至此,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沿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路径,不仅无法真正理解贫困问题,也无法树立处理贫困问题的严谨态度。
三、马克思视野中的贫困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观的反思,使马克思立足物质生产领域,从“感性的人”出发,认真审视被诸意识形态遮蔽的现实,重思现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继续探析贫困问题的本质内涵。此时,马克思不仅把物质贫困视为贫困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现代社会,以及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内涵的理解,已经与黑格尔发生了根本性不同。
就物质贫困而言,黑格尔关心的仅是市民脱离社会分工后的极度贫困状态,至于“底层劳动阶级”的不幸处境,则是先天注定、难以改变,且如哈德曼所言,在道义上不容置疑。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这种观点予以概括,“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同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的节省、勤劳、道德等等有关,而决不是由个人在流通中互相对立时发生的经济关系即交往关系本身造成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因为,据黑格尔所言,现代社会已经依托市民社会原则赋予了个体发挥自身才能的平等机遇。但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细致考察,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的流通领域虽然遵循着等价交换,可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基础上,“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④魏小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哲学与伦理——以MEGA2中马克思文本为基础的阅读与理解》,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9期。。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始至终都没有为其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遇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所以,马克思并不是没有看到个体的自然差异,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承认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的确客观存在。只是,现代社会底层劳动阶级的形成并非个人天赋的“命中注定”,而是物质生产结构导致的历史必然。马克思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重新规定了黑格尔“富有者阶级”和“底层劳动阶级”指称的社会群体,用“资产阶级社会”概念规定了“现代社会”,进而宣示了现代社会阶级压迫的实质。所以,马克思关心的物质贫困,是在阶级压迫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方式及其深层矛盾。至于黑格尔眼中物质贫困的承担者,马克思则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它总体属于社会的反动力量,基本沦为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帮凶。
就精神贫困而言,黑格尔关心的是市民对市民社会原则的反叛。马克思则立足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对工人阶级物质贫困的揭示,指出利己主义观念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精神贫困的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这里的“私有制”指的是使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拥有更多的物,是所有人一切行为的唯一精神追求。受到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每个人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把社会中的他人视为手段和工具,才能满足自身对物的需要。于是,人对拥有物的无限渴望,只有通过强烈的利己主义精神才能真正实现。“绝对的贫困”,即社会成员精神层面的贫困,也就随即获得了利己主义的规定。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那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代社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个体都是“利己主义的人”④同上书,第322页。。很明显,与黑格尔类似,马克思也认为精神贫困同时存在于两个阶级。不过,虽然同样遭遇精神贫困,资产阶级在物质领域得到的却是富庶和浓厚的满足感。资产阶级必然维护精神贫困及其所有制基础,成为“保守的一方”,渲染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对现实社会的统摄作用。通过意识形态的欺诈,遮蔽工人阶级科学理解社会生产方式的精神路径,使工人阶级在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的悲剧中不断徘徊。工人阶级起初或许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但最终将成为“破坏的一方”⑤同上书,第261页。。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日益窘迫,在物质领域愈发的贫困匮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必将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观念,形成阶级意识,通过阶级革命,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精神贫困赖以形成的所有制基础,彻底解决困扰现代社会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问题。①参见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72—173页。所以,马克思真正关心的,是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的精神贫困。
在黑格尔那里,贫困问题是无解的,是一个被刻意抛弃的难题。这不仅因为黑格尔自身的思想局限,更是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贫困非但没有被扼制的迹象,反而在不断地蔓延,黑格尔从中没有发现破解贫困问题的可能。面对如斯情景,马克思显得更有勇气,仍立志为解决贫困问题奋斗终生。这固然与马克思的人格品性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在其贫困理论真正形成前,马克思受到了历史现实与社会思想语境的双重影响。
首先,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工人阶级的人口数量和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历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曾指出,通过对不同方面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1790年至1830年的英国历史中,“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②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与之类似,恩格斯也通过对英国社会的一系列经验观察,更加概括地指出:工人已经“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75页。。不仅在英国,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在逐步增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抗也在日益加剧,两个阶级的矛盾正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已经超出国界而走向联合。这样的社会现实,促使马克思日益坚信,工人阶级内部蕴含着改变自身贫困境遇、变革社会现实的强大精神和物质力量,它的利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以,马克思逐渐自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强调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从理论的高度细致考察现代社会贫困的形成、发展与消灭过程。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认知方式,这种思想语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马克思。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指出,斯密“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变了限制性的、歧视性的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穷人应该永远穷下去的态度”④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分配正义简史》,吴万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实际上比我们想象到的要小得多……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⑤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所以,社会底层群体在精神层面表现出的懒惰狭隘、实践层面表现出的能力匮乏,与其说是生而注定,不如说是社会使然。很明显,这种观点与整个柏拉图传统、中世纪理念,甚至一些启蒙思想家,都针锋相对。如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指出,在柏拉图那里,“自然差异准确地说是分工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分工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允许本质上不同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①Gertrude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54.。到了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人的先天差异由上帝赋予,贫困本就该存在,社会也本就该分为不同的等级。对于一些启蒙思想家,他们更多的是在政治意义上,或“应然”的彼岸世界中,肯定人的自由平等,黑格尔自不待言,费希特作为较早论证分配正义理念的哲学家,亦是如此。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指出,“一旦某人不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一切人都必须……并根据公民契约,从自己的财产中分出一部分给这个人,直到他能够生活下去”②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4页。。能够看出,费希特也承认个体彼此的平等地位,并希望以此为基础,使个体平等的生存权利现实化。但是,判定个体间地位平等的标准,不是个体在经济领域拥有平等的生产能力,而是他们在政治层面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
相比之下,斯密则立足于此岸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强调“感性的人”之间现实的、具体的自由平等,肯定“感性的人”生产能力的同一性。实现自由平等的依据,既不在人类社会之外,也不在政治领域之中,而在“感性的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弗莱施哈克尔称斯密为“单枪匹马”毫不过分。应当承认,这种观点影响深远,甚至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消灭货币和资本,重建自由平等的善良构想,恐怕也得益于斯密早已奠定的基本理念。至于马克思,或许并不直接,但至少在两方面意义上间接继承了斯密的某些想法:第一,在本体论层面上,个体拥有摆脱贫困的政治权利,不等于在物质层面获得了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因为,“活下去”的物质标准可以很低,个体应该也能够在经济生产领域,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第二,在方法论层面上,贫困既然不是上帝意志,而是经济制度的人为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阶级“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页。,那么就完全可以通过人为变革经济制度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这使马克思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前景充满信心。
当然,无论考察社会历史的具体现象,或审视斯密开创的思想语境,马克思最终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他虽然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壮大,却也谨慎地指出,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机才成熟,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毕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另外,斯密式的观念虽然有启发性,但马克思也批判性地指出,在本体论层面,剥离了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生产能力的同一性是抽象而无意义的,人的自由平等固然要在经济领域实现,不过要依靠社会关系的逐步变革;在方法论层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固然要被扬弃,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则要被继承,只有如此,才能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上解决贫困问题。到此,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待贫困的基本态度,已经较为清晰地初步展现。黑格尔虽然早于马克思分析贫困问题,却囿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终不得果。马克思则跳出既有范式,回归历史,澄清了贫困问题的逻辑实质。当然,要想真正理解二者贫困思想的差异,至少还要在“贫困如何产生”“如何摆脱贫困”等问题框架下,对他们的文本细节展开深入分析,而这或许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探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