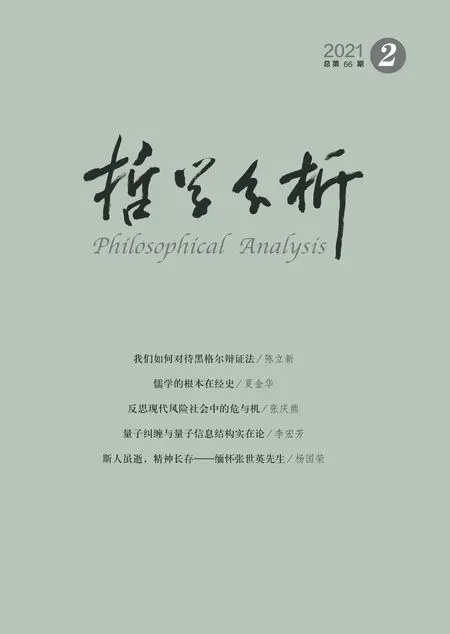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
陈立新
本文的题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使用的一个追问,其义一目了然。当今的哲学研究者大都高度认可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辩证法思想的宏富内容和思想意义。问题在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是不是现成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现成地享用?黑格尔之后的很多阐释者,透过其艰涩思辨的文本,试图从他的智慧体系中获得滋养,“从绝对者的领域的最高监督以及著名的辩证法的无所不通的威力那里给自己弄到一些什么东西”①参见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 Ⅰ),管士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8页注70。,擘画了思想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伽达默尔颇得要领地指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黑格尔所阐发的社会现实之中。在思想史上受到如此这般持续关注的实情表明:黑格尔的读者参与了其辩证法意义的生成,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不可避免地在读者的阅读和使用中呈现出来。正是这样,马克思这一追问的有效性可谓历久弥新。吴晓明教授的新著《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基于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革命的主旨与意义的深切领悟,把视线指向现实生活世界,独具匠心地阐述了马克思经由黑格尔的哲学深思而切中时代深处的思想成就。我们就此可知,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在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参与时代问题中才展露出蓬勃的生机和广阔的前景,马克思毫无疑问在思想史上建树了一座解读黑格尔哲学、直抵黑格尔辩证法真谛的思想路 标。
一、卢卡奇在存在论上的失守与教训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拯救和改造了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遗产,有着引导读者把握和体会黑格尔辩证法意义的优先性。推而论之,在马克思之后,讨论黑格尔哲学(包括其辩证法)的意义,不能绕开马克思先期在存在论意义上实施的改造;探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包括其辩证法),不能无视黑格尔思想的真正影响。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性遭遇中,卢卡奇最早感受到并最先在实践中处理这种关系。我们从卢卡奇这一范例中可以获得弥足珍贵的启 示。
卢卡奇非常明白,解决资本时代的生存困境,只有具备了成熟的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才能承担并完成如此重任。卢卡奇不仅高度认同马克思的理论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判断,而且还特别强调理论掌握群众的“方法”尤其重要,只有方法得当,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从而转变为“革命工具”。为了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唯有依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武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卢卡奇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对读,这一思路符合思想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无疑是合理的、恰当的。卢卡奇究竟是如何展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呢?
在卢卡奇看来,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例,我们提炼了卢卡奇在这方面的三种观点。其一,“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卢卡奇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是直接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黑格尔自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坚持不懈地继续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同时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诸如此类的表述,表明卢卡奇无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异质性,把马克思等同于黑格尔。其二,认同并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看作“死狗”的告诫。卢卡奇觉得,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马克思这一态度,连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也未能奏效,以至于黑格尔思想中富有价值的方面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用。为了贯彻马克思的这一要求,卢卡奇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提出要摧毁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死’的建筑”,“把黑格尔思想在方法论上富有成果的东西作为对现在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拯救出来”,剥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成果,使之“能够再次成为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力量”。其三,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卢卡奇指出,“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但是,黑格尔没有认识到“历史的真正动力”,马克思在如何对待现实这个问题上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用现实的实践活动终止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神话”。不过,在深究黑格尔陷入“概念神话”的原因时,卢卡奇居然认为,黑格尔在构造哲学体系的时候,历史动力表现得不是十分清楚,以至于黑格尔“不得不把民族及其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从而选择了“民族精神”的神话。①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3、43—44、67—68页。
从这些归纳可以看出,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理解和判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左右摇摆和不确定性。由之而来的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判断与阐扬,还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吸收,卢卡奇都未能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程度。他念兹在兹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一事,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实现。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卢卡奇孤身一人能够完成如此宏愿,但从哲学上澄清其何以犯错则十分重要和迫切。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存在论原则上的差异,是否承认马克思在存在论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否能够把握马克思的存在论创制。像卢卡奇那样,夷平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存在论分殊,想当然地以黑格尔为凭借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这就在哲学立场上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只有在存在论根基处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资源的利用才能毫无遮蔽地与我们照 面。
卢卡奇后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承认犯了一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只是这篇“序言”意识到对象化“事实上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卢卡奇才开始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卢卡奇明言,这种区分“完全动摇了那种构成《历史与阶级意识》特点的东西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差距是如何造成的呢?还是卢卡奇本人道破了真相:“这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①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9、34页。使用黑格尔主义的眼镜,试图以“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卢卡奇并没有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境域中进行理论思考。“卢卡奇对黑格尔将对象化和异化混同在总体上不加批判,这决不是偶然的,尽管事实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理论成就呈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所深知的著作中(例如,《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的原始导言),而不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还没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②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 (上),郑一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这就是说,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存在论境域上表现出严重的偏差。正是这样,卢卡奇不仅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体论根基,而且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遗产——社会—历史现实观,以至于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和建设落入主观主义窠臼之中。③参见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8、178、299页。
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独具匠心地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作为劳动者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对象化是一切劳动之共性,没有对象化的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产品反过来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沦为产品的奴隶,那么,这样的劳动对象化就是异化。所以,对象化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异化是劳动的否定方面。在马克思以前及其同时代,绝大多数批判仅仅止步于指责异化作为劳动过程的否定性质。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异化默认为永恒的“人类状况”,默认“有害的”“造孽的”异化劳动成为天经地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东西却有了形式上的合理性,现实生活中最关乎本质的东西却在这类文化哀婉式的批判中遭到了遮蔽。这是以激进的表达形式走向为现实异化进行粉饰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区分对象化和异化基础上开展的批判,切中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道说了生活世界之实情,由此展开的批判才能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之中,开启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现实道路。就此而言,在发现和阐明社会现实这一标志着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新原则的关节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相遇关乎问题之根本,我们在此毫无例外地感受到一种本质上的关联。这正是马克思在新的存在论境域中透视黑格尔辩证法所达到的积极成果。
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卢卡奇把深厚的历史意识与真诚的现实关切相结合,最敏锐地领悟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联并力图在最关乎本质的方面予以建设和推进,最深刻地阐述了辩证方法之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性意义,却令人惋惜地在存在论原则上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失守。卢卡奇作为一个特点突出且富有说服力的案例,彰显了前述马克思追问的现实针对性——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是一种余兴或旁出,而是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判明并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存在论)基础则是所有工作的前提。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申出具有巨大历史感的社会现实领域,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被揭示出来的最大成果,更是辩证法被马克思的存在论创制所贯通之后稳固确立起来的基本境域。据此,我们顺理成章地聚焦于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哲学语境中,“否定性”与“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息息相关。这三个概念的动态连接大体上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构成,毋宁说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 词。
第一,“绝对主体”意味着黑格尔的哲学立场。
所谓绝对,简单地说就是“无对”,就是指只可能与自身相关的性质;所谓与自身相关,是指绝对从自身出发,经过自己的异在又回到自身。黑格尔对此有着精到的阐述:“精神已向我们表明,它既不仅是自我意识退回到它的纯粹内在性里,也不是自我意识单纯地沉没到实体和它的无差别性里,而是自我的这种运动:自我外在化它自己并自己沉没到它的实体里,同样作为主体,这自我从实体(超拔)出来而深入到自己,并且以实体为对象和内容,而又扬弃对象性和内容的这个差别。”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1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实体即主体”论断:“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进而言之,作为实体,主体既包含“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着“作为知识之对象”的那种直接性,从而主体还有一个“树立对立面”的本质要求。唯有在这种意义上组建的“自身的同一性”或“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自身等同性”则不具备如此之品质。①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0—11页。绝对真理既然必定拥有如此这般的品质,那么,它作为主体的活动,决不能在自身理性之外假借形式或权力来证明自身。换言之,理性自身有着足够的力量和内涵而自我支 撑。
第二,“自我活动”是绝对主体的基本存在性质。
依照“实体即主体”的哲学立场,精神的活动一定不会假求于外的某种力量,理性自身具有“活力”。理性不像有限行动那样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去创造一切、统摄一切,这就是理性的“无限的素质”。理性自己供给自己的营养和参照,不需要从给定根据中获得营养和活动的对象,理性就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理性是“实体”,还有着“无限的形式”去推动这些内容。只是由于理性并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理性是自己预设的唯一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并自我授权地在自然和精神宇宙中开展这一目标,使之从内在源泉到外在特征都能够由潜在性变为现实性。这就是唯有理性才具有的“无限的权力”,是真正的、永恒的、绝对的权力。理性正是因为拥有如此这般的内在品质,便能够成为世界的“灵魂”和“共性”。②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明白,“实体作为主体,本身就具有最初的内在必然性,必然把自己表现为它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即把自己表现为精神。只有完成了的对象性的表现才同时是实体回复到自身的过程,或者是实体变成自我〔或主体〕的过程”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269页。。就此可以发掘精神作为“绝对主体”之“自我活动”的两个内在的建设性向度。一方面,精神的自我把捉:“精神不仅知道它自在地或按其绝对的内容说是怎样的,也不仅知道它自为地按其无内容的形式说或从自我意识方面看是怎样的,而且知道它自在和自为地是怎样的。”④同上书,第262页。这就是说,精神不仅知道自己,而且知道自身的否定亦即自身的“界限”。另一方面,精神基于“内在的冲力”的自我造就——精神不仅不惜“牺牲自己”而扬弃自身的主观性,而且必定要扬弃对象的片面性,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同一,从而重建自身为绝对主体,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使之成为真理。⑤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0页。
从精神“自我活动”之要义来看,精神只有作为自己回到自己的变化过程才真正是精神。这就是说,精神在它的异在本身里也就在它自己本身,精神是“依靠自身”的存在,是“自为存在”,亦即是自由的存在。既是这样,精神就要使一切外在之物都变成“为我而存在”之物。“那种在精神中作为他物而继续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未被消化,或者是死物;如果精神让这种东西作为外物存在于自身里面,那么精神就是不自由的。”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4页。精神的“自我活动”既然本质重要地蕴涵着“为我而存在”的必然要求,实质上表达了精神以建构或设定为内涵的创造性。
第三,“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性质和展开方式。
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不单纯是思维过程,而是概念本身或绝对理念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辩证法构成了世界的自发的自我发展。这是因为“绝对主体”作为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乃是世界的主宰和真形相。于是,事物通过变为它的对立面,解决矛盾而发展为综合,达到更高的存在状态。这是一个不断开展直至达到完善的过程。所以,“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②黑格尔:《小逻辑》,第177页。。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一般的否定性或否定的东西直接进入到实体之中,改造实体性,使之成为活动的主体性。于是,辩证法不仅把否定的东西确定为推动的原则,而且还把它理解为“自身”(Selbst)。这样的辩证法当然就被命名为“否定性”的辩证法:“如果这个否定性首先只表现为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那么它同样也是实体对它自己的不同一性。看起来似乎是在实体以外进行的,似乎是一种指向着实体的活动,事实上就是实体自己的行动,实体因此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4页。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也把‘思辨辩证法’径直称为‘方法’。用‘方法’这个名称,它既不是指一个表象工具,也不仅仅是指哲学探讨的一个特殊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为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④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7页。这里的“生产过程”用语,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蕴涵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切中肯綮的评 价。
从黑格尔本人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把握其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及其存在方式。值得深思的是,从“实体即主体”之自我活动的展开过程中确立辩证法的实体性的内容,呈现并说明“事情的活生生的本质”,黑格尔切入问题的思考深度、深邃的历史意识、关注现实的思想指向,皆无与伦比,令人敬佩。这样的成就,固然与黑格尔个人的卓越才华分不开,但根本动因仍是超越个人并引领个人的现实力量。黑格尔就富有洞见地提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与现实的和解,理解和把握现实。马克思更明确地概括为:“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因此,我们站立在黑格尔宏伟严密的哲学体系面前,需要透过黑格尔用于搭建哲学体系的逻辑“脚手架”,把辩证法这颗“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时,就指出其“伟大之处”:“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②同上书,第205页。抓住人的自我生成,抓住现实生活过程,这就是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之中。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的伟力就不言而喻地呈现出来。正是这样,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这一论断中提炼表达这样一个判断:黑格尔无比深刻的辩证法乃是社会现实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三、辩证法的革命性改造与创造性推进
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我们已经阐述,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不是现成地呈现出来的,而是需要剥离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在崭新的存在论境域中才能得以澄明。必须承认,这项创举首先要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合理对待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同时展露了唯物辩证法的要义。
其一,用“实在主体”置换“绝对主体”。
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的设计,“辩证法是绝对主体之主体性的生产过程,并且是作为绝对主体的‘必然行为’的过程”④海德格尔:《路标》,第506页。。黑格尔把思辨方法看作实体之为主体的内在运动,并随着绝对精神主宰世界而同时成为世界的“灵魂”,作为实体和主体的绝对精神能够认识和把握这一过程。不消说,辩证法就是“实体即主体”原则实际展开的运动过程,也就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过程;只要没有这种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就根本不会有辩证法。这就是思辨辩证法的思辨逻辑。一旦费尔巴哈拉开了批判绝对精神的帷幕,“绝对主体”的瓦解就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这里的问题在于:当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被证明是神秘化的思辨幻觉而已然需要解构的时候,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否获得实质性的保留?这种保留工作是在什么样的本体论基础上进行的?①参见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第84、86、89页。
马克思独具慧眼地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被形而上学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现实生活过程。这就在新的存在论原则高度洞穿了近代哲学所持守的意识内在性本体论原则的秘密。正是这样,马克思从“劳动”与“人的自我产生”的本质关联中批判地阐释和彰显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要义时,就用现实感性的“实在主体”承载和重启辩证法的“自我活动”之特质,实现了对于“绝对主体”的格式塔式转换。在马克思理论思考的语境中,“实在主体”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统一。作为“现实的人”,“实在主体”是有血有肉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从事现实活动的、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现实的人”的基本构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作为“现实的人类”,“实在主体”乃是特定的、既与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是既定的社会,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结合马克思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相对立、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的特意提醒,毋宁说,“实在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而不是关于社会的抽象规定或知性范畴。这样的“实在主体”,毫无疑问才是现实地发挥作用的真正的“自我活动者”。
其二,开启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道路。
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黑格尔在论述历史理性的开展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成就。黑格尔说:“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不消说,黑格尔清晰可见地关注那些有着“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个人。这些个人虽然是人类芸芸众生中影响“极为有限”的一员,但他们是“社会的特殊单位”,总是“从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和意见来献身于一种事业”,从而构建了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因为如此这般高度重视人的热情的能动作用,黑格尔在哲学上深切表达了追求自己切身利益的人类感性世界,让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实生活过程展露在人们的眼前。当然,黑格尔不会无原则地关注人们的需要、热情和才能,他把“人类的热情”与绝对理念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不过是表明绝对理念是“原则”和“最后的目的”,人的热情和激情则是“原则”的“实行”和“实现”。换言之,在人类历史广阔的画面上展示出的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戏剧”和表演,莫不是绝对理念利用人的热情作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而已。这正是“理性的狡计”。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13、23—24、28 页。这表明,黑格尔虽然深刻辩证地揭示了富有内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但用厚实的思辨逻辑构造把社会现实严密地遮蔽起来。
马克思高度认同并充分吸收黑格尔关于哲学把握社会现实的相关思考,创造性地阐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把哲学关注现实的原则落到实处。马克思毫不妥协地针对黑格尔哲学原则实现了存在论原则的根本转变,走上一条面向现实生活过程、讲述现实生活故事的思想道路:透过繁芜丛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抓住人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形成了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的基本方法;坚持物质生产或经济发展乃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又同时强调社会上层建筑对于物质生产的反作用;坚持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发现并概括了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又肯定东方社会应当探索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诸如此类的基本观点证明:马克思已然在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中阐发辩证法的真谛,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原本就是具有必然联系的理论学说。可以相信,经过马克思的努力,辩证法走向现实生活世界,已经成为保持自身的生命线。正是这样,卢卡奇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归结为“辩证法的决定性的因素”,把“改变现实”当作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革命辩证法”。
其三,拒绝“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作为真实的主体(抽象思维是其现实运行方式),是正常的状态,一切不同于抽象思维的对象化都是不正常的,是应该予以扬弃的异化。“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这就是把对象化等同于异化,扬弃异化就是克服对象;而且,不仅要扬弃真正的异化,也要扬弃一切的对象化。只是对象的“对象性的性质”,对自我意识说来成为一种障碍和异化,对象复归于自我意识就是人的本质复归于人本身;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人也就成了一个“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虚假的实证主义”。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206、212页。就黑格尔把对象化看成思维自身发展的必要环节来说,这是对对象化的肯定或实证的研究。然而,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肯定对象化也就肯定了异化,自觉不自觉地为真正的异化如私有财产进行辩护,这是“非批判”的缺陷。这一批判外观下所包裹的非批判的态度,意味着认识社会现实的不彻底性。黑格尔之后那些形式主义地运用辩证法、痴迷于游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空乏议论,正是从此获得了一个哲学方法论上的重要凭借。实证主义理念恰好是典型的代表。
实证主义对于黑格尔的批判,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叛离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在主导理念上对于当代哲学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实证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不过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高到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水平之上而已”。②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52页。按照实证主义的理论取向来看,一切真正的人类知识都包含在科学——当然是指知性科学——的范围之内,唯有科学才是真正知识的唯一来源,唯有科学方法才能造福于人类的生活。从此出发,所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都主张,哲学可以在科学范围内,在诠释科学和服务科学的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凡是科学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哲学必须满足于让其永无答案,哲学不能声称具有可以获得科学无法获得的知识的手段。深究起来,实证主义赖以立足的经验证实原则,根据在于依赖自然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通常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胜任的科学家从同样的证据出发,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例如,“物理学思维的主要前提假设,就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持有的;而对物理学问题科学地进行思想,也就是按照它们去进行思想”③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问题在于,“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3页。。这就暴露了实证主义在主导观念上的限度,以及实证主义理念的适用范围。然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固守自己的哲学信条,漠视现实生活的多样化,脱离生活实际,最终沦为事实上的非批判的、无立场的、单向度的理论说教,成为发轫于批判黑格尔却终止于分享黑格尔哲学原则的实例,成为当代思想对待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突出和醒目的反证。
从存在基础上把生活与科学分开,马克思把这种做法斥为谎言。解构实证主义不切实际的教条,让科学实现其服务人类生活的本务,依然是当代人生存实践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揭露黑格尔哲学“虚假的实证主义”以及“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有助于充分发挥其辩证法的建设性意义,深化理解马克思“实在主体”辩证法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