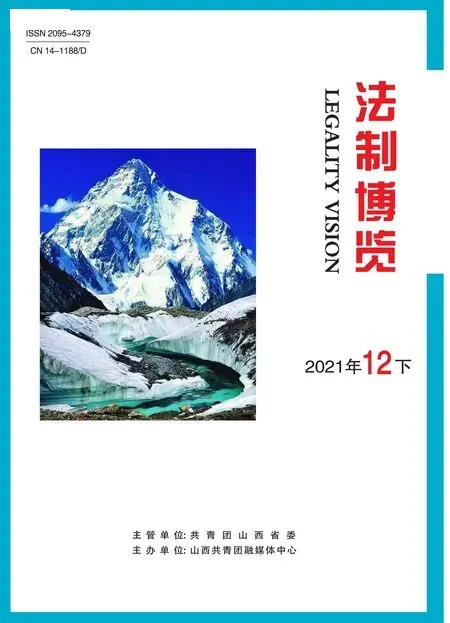关于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的思考
武志芹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检察院,山西 太原 030013)
一、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内容
(一)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发展历程
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方式,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而在上述法定四大领域后出现的“等”字,则为检察机关之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预留了空间。2018年我国新出台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规定了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在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依法对上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我国新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至此,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形成了“4+2”法定领域的格局。
除法律规定的上述领域外,公益诉讼还存在“等”字的探索范围,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积极主动作为,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大胆创新,为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使“等”外领域探索成为检察战“疫”中的新亮点。[1]2020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为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指明了方向。
当然,在其他涉及公益损害的领域,例如产品及工程质量、高铁沿线安全等公共安全,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辟除网络谣言等互联网公益保护,国防和军事利益保护等方面,各地检察机关也在持续探索当中。
(二)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具体探索方向
1.安全领域:例如安全生产与作业、公共电梯检验及维护、加油站扫码支付风险、市政窨井盖毁损缺失等危害公共安全方面,可开展预防性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工作。
2.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依据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并结合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等规定,可对辖区内古文物、古文化遗址、传统古村落等方面开展文物保护现状监督工作。特别提到的是,在将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界定为新领域之前,文物保护类案件是按照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的案件办理,目前则将该领域单独作为新领域案件的范围之一。
3.互联网、通信领域:例如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骚扰电话、垃圾信息等互联网、通信领域损害公益的情况进行监督。办理该领域案件可通过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的沟通联系,在线索获取、调查取证、委托鉴定方面获取便利条件。
4.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例如对于商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校园周边开设成年人性用品商店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进行监督。
5.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护:例如对盲道设置不规范,车辆、经营者占用盲道的情况进行排查,保障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同时关注老年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存在的困难,通过办理赡养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解决老年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问题。
6.其他领域:除上述领域外,对于涉及扶贫领域、国防军事领域、违反我国《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在冥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等行为,也可作为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
二、“等”外领域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等”外领域的扩大以至检察权的扩张加深了行政机关抵触情绪、加大了公益诉讼办案阻力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之初,受案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法定的四大领域内,后又新增了英烈保护领域和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再之后发展到安全生产等新领域。而办案程序从法定领域案件层报省院批准到新领域案件层报省院批准,再到新领域案件有典型案例在先的,可以备案代替审批。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公益诉讼检察权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事实上,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字延伸,加深了行政机关本就存在的抵触情绪,加大了案件办理的难度和阻力。尤其在我国新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中新增“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的,应当在七日内将《立案决定书》送达行政机关”的规定,更加剧了行政机关的紧张情绪和抗拒程度。
一方面,行政机关各个职能部门是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行政管理的第一线,依法行使各项行政权,而检察权对多个领域的扩张会使行政权遭到弱化;另一方面,立案后无论是进行磋商还是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均是以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致使公益受到侵害作为前提条件,如此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难免会因怕被纪委监委追责而产生抵触情绪。基于上述原因,导致实践中在一些职责不明、边界模糊的案件中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从而影响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质效。
(二)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界限标准不明
目前,公益诉讼“等”外领域并非全部被法定化,例如我国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正式以法律授权的形式为检察机关办理安全生产领域的案件提供了直接依据,但有些新领域的提出并未被立法确认,而是被当作一项司法政策提出。并且在上述列举的新领域后也有一个“等”字,这就为受案范围的再次无限延伸提供了空间。上述情况容易造成各地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案件时界限标准不明,对“等”外理解会无限扩大,使得检察权过度干预行政权,违背了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
公益诉讼新领域的提出只是以列举方式说明案件范围,并未对新领域案件规定核心内涵和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地区办理“等”外公益诉讼案件,其立案标准不甚严格,未能综合考虑公共利益受损的严重程度、侵害行为违法性的严重程度、社会影响、保护必要性等因素,出于完成考核指标的目的,盲目追求办案数量,对于一些非普遍性、轻微损害公益甚至是有侵害公益可能性的案件进行立案办理,不仅损害了检察机关的权威性,还会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未能实现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一起、警示一片,教育、纠正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三、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等”外案件探索的建议
(一)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需遵循谦抑性原则,审慎行使检察权
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不作为来促进依法行政,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归根结底是一种司法监督权,行政机关是公益的第一顺位捍卫者,检察机关不能代位行使行政权,这也是检察建议内容更着重于强调对行政机关的督促履职而非指导行政机关提出具体行政措施的原因。因此,办理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案件也要始终围绕公益保护这一核心目的,保持检察权的谦抑性原则,防止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做到检察监督不缺位也不越位。
对于行政机关的抵触情绪,检察机关也要主动出击,积极沟通,消除行政机关的顾虑,使其了解到公益诉讼是督促履职之诉而不是追责之诉,制发检察建议或磋商函是为了督促并帮助行政机关解决公益损害问题,而非起诉追责,双方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公益,从而在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拓展上,信任并支持检察机关,形成保护“等”外公益的合力。在办案过程中,还可以采取公开听证、圆桌会议等方式,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的方式,推动问题在诉前阶段得到有效解决。同时要加强与人大、党委、政府的沟通联系,争取工作理解和支持,为开展公益诉“等”外领域探索打造良好的工作局面。
(二)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应当遵循积极、稳妥原则,防止对“等”外理解的无限扩大
最高检将办理公益诉讼“等”外案件的原则,由“稳妥、积极”调整为“积极、稳妥”。积极优先于稳妥作为第一顺位的原则,意味着检察机关办理“等”外案件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去主动监督,同时注重办案程序和办案规范,严格按照要求,履行审批和备案手续,把握检察监督权的边界,与行政机关加强团结协作,形成共同保护两益的工作合力。
基层检察机关作为办案的中坚力量,要把握好办理新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标准,结合地区实际,从行业、区域、群体等方面加强分析研判,综合考量公共利益受损的严重程度、侵害行为违法性严重程度、社会影响、保护必要性、是否有其他适格主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等因素,[2]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等”外公益被侵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此外,建议最高检加快对公益诉讼“等”外案件受案范围的司法解释工作,为检察机关办理“等”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统一标准、细化规则,更好地依法行使检察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