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为什么会转向马克思主义
李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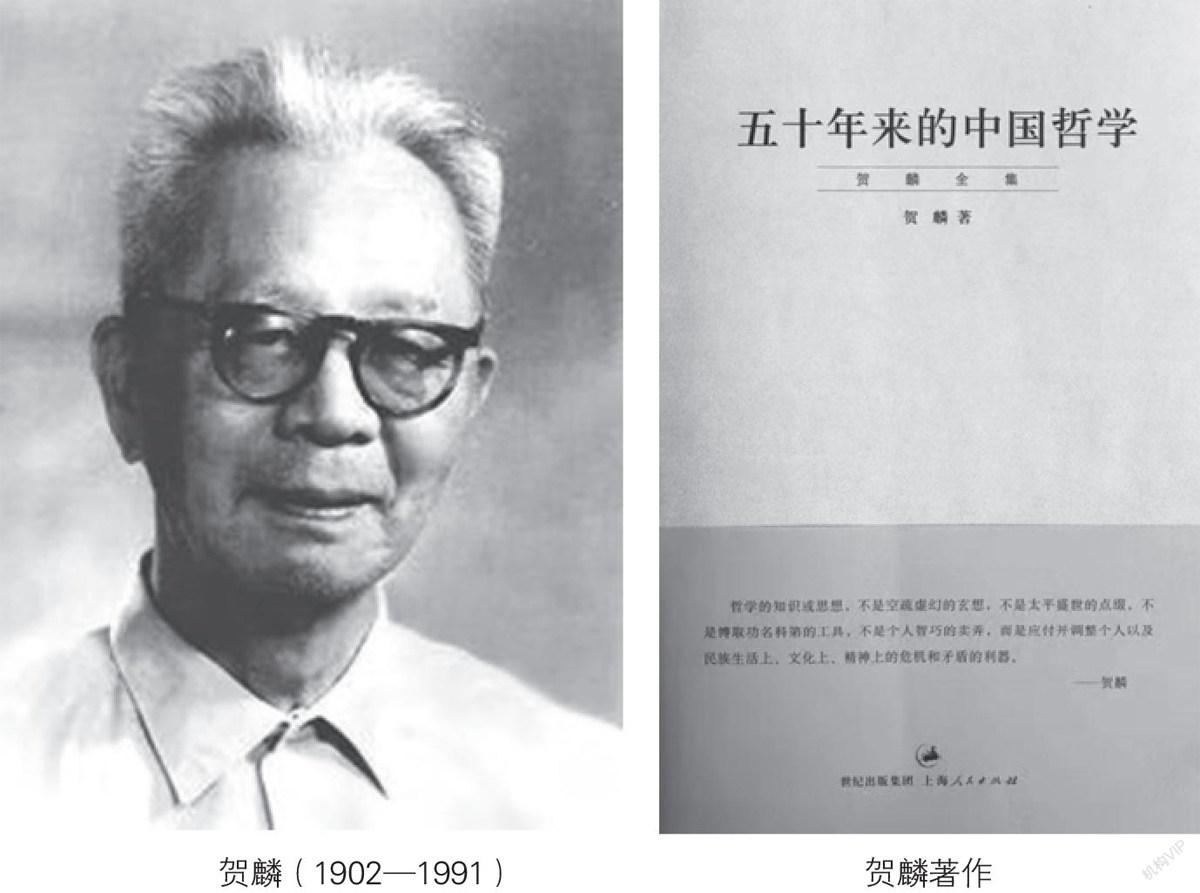
贺麟(1902—1991),四川金堂人,是现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198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对贺麟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贺麟在哲学思想、黑格尔哲学研究、翻译西方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方面的地位及贡献。他与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各创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精通黑格尔哲学,论述遍及黑格尔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翻译的《小逻辑》,学术界公认为继严复的《天演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中文译本;他在中国较早倡导中西文化研究。在哲学这块土地上,贺麟辛勤地耕耘了一生。这期间,虽说步履艰难,但最后终于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贺麟面临要留在内地,还是随蒋介石政权南迁的抉择。对此他在《我和胡适的交往》中有所说明: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知道共产党也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
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计。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去香港,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圍城期间,南京方面曾3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有一天,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汪子嵩来找他,对他说:“地下党城工部托我转告贺先生,城工部负责人的意见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我们认为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经过反复、郑重地考虑,他三次拒绝了南京政府请他离开北平飞往南京的要求,决定留下来,迎接解放。据他的女儿回忆,“院里的伯伯叔叔们也都没有走,整个北大的教授们绝大部分也没有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历史开始新的一页。
二、通过土改的社会实践真切认识到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旧中国留下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吻合的。让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土改就是期望通过这一实践来改造其思想,以此争取知识分子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并借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土改运动的开展。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以不同方式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冯友兰参与了北京郊区的土改,梁漱溟考察了四川的土改,贺麟参与了陕西土改。他们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出土改对他们的教育意义。贺麟通过参加土地改革、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转向唯物主义。
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土地改革作为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在那篇文章里阐述了他的思想,认为土改的社会实践,使其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认识到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他说:“静观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连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很肤浅、表面、外在;而深入参加实践斗争,不惟对变革现实尽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除增进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外,又复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这次的新经验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过去多年来脱离实践的书本生活,不知错过了多少伟大的实践斗争的场面,也就错过了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帮助我否定了“静观世界”的唯心论观点,而真切认识到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他的女儿后来回忆父亲时写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调查体验。唯心论只讲概念,不接触实际,而只有通过实践得到的思想才真正有力量。过去以为唯心论注重思想,唯物论不重思想,现在看到共产党的辩证唯物论也非常注重思想”。后来他又参加了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亦叫“洗澡”。他说他是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来检查自己的。虽然那时对自我批判和群众的批判,有些人上纲过高,但是他还是以改造自己,适应新社会的态度来对待,还是实事求是,自己想通了的才承认。1957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周谷城、胡绳、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费孝通、王方名、黄顺基等10人,并共进午餐,饭后又谈到3点多钟。贺麟根据同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说:“过去我对于唯物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以为它有些骛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重向内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时,于是我又以为唯物论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却是唯心论。因为我总以为只有唯心论才重思想,唯心论者认思想创造世界,认没有思想就没有存在,没有知就没有行,认要改造世界,先须改造思想,甚至有许多唯心论者只求改造思想,不愿改造世界。……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我才开始认识到唯物论与搞通思想不可分”。他最后总结说:我现在才明白了,何以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何以无产阶级真正觉醒起来,必然会寻找到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贺麟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敢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公开检查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这种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三、《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蕴
改革开放以后,贺麟以前所未有的畅快心情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他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治学历程,撰文、编书、讲学、带研究生、对外学术交流、出国访问等,度过了充实、祥和的晚年。他所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
1986年,贺麟将旧作《当代中国哲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特别说明:“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新版将孙中山的知行说定位为“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最高最新最进步的成就”;同时将思想谱系连接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将后者作为知行哲学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贺麟所做的思想谱系的变动,亦即砍断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联系,而将孙中山直接与毛泽东连接在一起。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内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先秦诸子在现代的面貌。贺麟接通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认识论思想的联系,在现实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对于贺麟的一生,任继愈先生在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序言中有一段很中肯的文字,他说:“如果深入地了解贺麟先生的为人与办学,会发现他是旧中国成长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影响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少数的专家,而他思想深处更多的是儒家入世、救世的倾向,往往被忽视。他的治学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见诸实行;他讲学偏重在西方哲学,而用心却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满足于讲论的义理之学,他还要付诸实践,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变革。可惜他所操之术和他的善良愿望未能吻合,以致走了弯路。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算找到了最终归宿,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虽说步履艰难,但是立足坚实,当初不轻信,既信了就不动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贺先生身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以上这段文字,算作对贺麟哲学思想的结语;更是告诉我们贺麟先生也与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也希望通过学术建国的思想和行动来为中国进步贡献自己的学识。他的《文化与人生》就是一部这样的书,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由中国当前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贺麟将治学的重点转向西方哲学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撰写和翻译西方哲学,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贺麟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可以说是其介绍西方现代哲学的代表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贺麟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记录,80年代经作者重新进行审阅和修改而成;下篇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上下两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本演讲集,贺麟不仅介绍了西方对我国有影响的哲学家,如柏格森、詹姆斯、杜威、罗素等,而且也介绍了在我国影响不大的哲学家,如爱默生、怀特海、桑提耶纳、布兰夏尔德等,足见贺麟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工夫之深。正如周谷城在该书的序中说:“这本讲演集大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补充读本”。尤其是下篇,在分析批判方面,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特别是于对实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方面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还未有中译本,贺先生便直接从德文本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分析评论西方哲学。当然,这次讲演集出版,这些引文均对照马恩有关著作的中译本作了统一,但指出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反映了贺先生在1949年以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哲学研究的热忱,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贺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其三个原因:首先,热切地关注国家的命运是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动力。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其次,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黑格尔研究专家又有“幸运”一面: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因此新中国关于黑格尔的研究与翻译尚有一席学术之地。这也被认为是贺麟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的内在关联因素之一。黑格尔及之后的马克思提出的哲学理论都完全可以解决客观条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对立及冲突。贺麟曾认为,“就作介绍工作的人来说,不介绍黑格尔使人懂得,不好;介绍黑格尔使人懂得了,不批判黑格尔,进而提高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也不好。就读者来说,读不懂黑格尔,不好;读得懂黑格尔不能批判,作了黑格尔唯心论的俘虏也不好。这就是我深切感到的介绍黑格尔哲学的矛盾”。黑格尔的哲学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论之源。最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及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这些契合点及互补处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随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贺麟的学生洪汉鼎指出:“在我看来,贺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位大哲学家。贺先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同时又是研究阳明学、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尔的理论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王陽明心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综上所述,贺麟一生的最大两个成就,一是用文化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即他提出的儒学宗教化、艺术化和哲学化。二是他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精湛的研究和翻译,使“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传入中国,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在哲学史的思想渊源的发掘与进一步的研究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贺麟人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