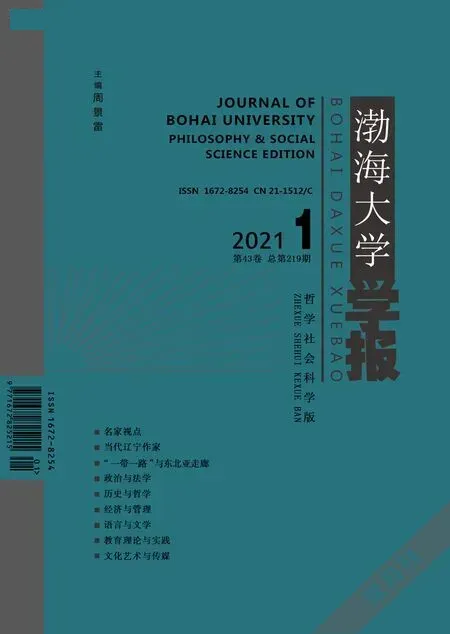文化资本现实处境的艺术传达
——评苏兰朵的小说
马 婷(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万州 404000)
苏兰朵是辽宁省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经常发表在各类文学期刊上,也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白熊》和长篇小说《声色》。她的中篇小说《歌唱家》《雪凤图》和《诗经》等,写出了消费社会中文学、文化资本的尴尬与困境,很有启示性。
一、资本的逻辑:“认贼作父”也正常
《歌唱家》把一个“认贼作父”的故事讲得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甚至让读者认为按照资本的逻辑,必然会如此。王春生偷了杨十月父亲浩良的名字,打着歌唱家浩良的牌子走穴,赚点小钱。杨十月侦破案情后,居然与王春生一起盗用了浩良的名字,去更有排场的地方唱其父的成名曲《十月金秋飘果香》。有了杨十月保驾护航,王春生再也不怕被人发现自己是假的了,唱得更加自信,更“是”浩良了,简直比浩良本人还像浩良。完成从抓小偷到伙同小偷一起偷的转变的根本是:钱,资本。资本作为一种强大的可以裹挟一切的力量,冲击了曾经牢固的血缘关系。在资本的场域中,血缘父子亲情也风雨飘摇。杨十月对父亲有心结,责怪名声在外的父亲没有借助袁浩的关系帮天赋不错的自己进入音乐学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利用已经老迈无用的父亲的名字就能赚钱的机会,杨十月紧紧地抓住了,让父亲的名字充分发挥它的余热,照亮了杨十月一家的好日子,也让杨十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小说《歌唱家》中,父亲这种因确定的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名称也可以如符号一样,能指与其所指断裂开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也称符面,所指对应的是概念,也称符意。在符号系统中,符号并非与外在世界相对应,而是自足的,只由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决定。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最初是任意的,但一旦确定下来,就约定俗成。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两面,是可以分离的,而且能指一般要大于所指。父亲,血亲关系,本是人类最坚实的关联,已经成了飘浮的能指;父亲之所以失去了其对应的所指(生身之父),在于资本这个强势的“/”将符号的两面割裂了开来,“认贼作父”也就顺理成章了。
资本侵袭的不仅仅是曾经牢不可破的亲缘关系,甚至坚固的文艺堡垒也被资本侵占,不得不容忍资本登堂入室,坐拥一席。浩良不仅仅是个名字,更是一个聚集了稀缺文化资本的符号。这个符号稀缺,可交换价值显赫。王春生偷的不是有形的钱财,是更为稀有的文化资本——名声。俗语说“物以稀为贵”,恰好对应经济学上的基本价值规律,资源稀缺才好交换。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符号,稀缺性更为明显。旧时,文艺作品只能以现场演出的形式活跃在少数人生活中;而大众媒体时代,浩良借助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活跃于众多普通人的心目中。比较恒河沙数般的物质财富和众多过耳即忘的政治话语,流行歌曲当然是稀缺的,可以穿越时空留在人们心头,响在耳畔。
甚至“浩良”这个艺名本身也是蹭他的大名鼎鼎的师父袁浩的名声资本得来的:“浩是袁浩的浩,良是善良的良。”[1]浩良这个名字让杨石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有了漂亮的舞蹈演员妻子,可以把奶粉当井水喝,试图做一个能把政策语录融进日常言谈的政治过硬的艺术领袖,但他只是一个果农,靠着天赋和机缘走到了他那个阶层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境地。他回首往事,终于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不愿意靠着浩良的名字走得更远,是因为他意识到浩良的成功与逝去的恋人红霞密不可分,而自己对红霞亏欠得那么多,竟然没有去祭拜过她。幡然醒悟时,“他对着黑暗的空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真实,而歌唱家浩良的人生,就像个梦。他终于哭了出来。声音翻山越岭,从他的喉咙里奔跑出来,嘶哑,苍凉。这声音不属于浩良”[1](29)。显然,这个声音是杨石柱的,即浩良的前身。此时,他在见假浩良之前,似乎也不愿意再去在乎这个名字的归属。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且能指可以脱离所指独立存在。浩良这个符号的能指本来对应的所指是曾经的歌唱家袁浩微末之时收的徒弟,一个后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唱歌的果农,后来的所指对应王春生这个会唱歌的知青。“浩良”对应着谁都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及其影响力更重要。王春生就在真的“浩良”居住的养老院里正大光明地扮演着浩良的角色,享受着养老院负责人和彩霞的崇拜和优待。“浩良不属于他王春生,浩良也同样不属于杨石柱。浩良本就是个历史误会”[1](43)。
“物以稀为贵”是经济学上的一项基本价值规律。相对人类难填的欲壑而言,资源是有限的。资本虽是劳动的积累,但从形式上看,稀缺性也是资本成为资本的条件。如果商品物质像水和阳光那样容易得到,没什么交换价值也就不会成为资本。所以,文化资本也符合资本的基本属性即稀缺性。名声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其稀缺性不言而喻。当稀缺性与一定的权力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名声也由于拥有一定的符号资本而表现为一定的优越感。杨十月因为父亲是歌唱家,自觉其文化身份高人一等,因而有些融入不了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比如他面对妻子一家的生活时的看法:“黄丽的家曾经给了他温暖,让他短暂地忘掉了这些不快乐,但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岳父母家的那种快乐不属于他,他无法在那个粗陶的花盆里生根。他们一家三口在岳父母家过周末的时候,看着黄丽和儿子被岳父逗得哈哈大笑,他常常会心生羡慕。”[1](27)即使在杨十月的父亲已经不再活跃在舞台上,工薪阶层的他仍然保持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文化资本是会承袭的,世上没有公平的起跑线,杨十月沾了父亲的光,无论过去还是当下。
如果说《歌唱家》是“认贼作父”,那么苏兰朵的另一中篇小说《白马银枪》也有明显的“认父”的痕迹,造成后者的主人公也要“寻父”的根源在于政治对文化场域的侵袭。吕彤想要买回家传的京剧行头白马银枪时,却被人半道“截胡”买走了,买家是一个名为白胜堂的著名京剧演员。而后吕彤多方打听发现,买家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自己外公倾心培养的徒弟,也正是他告发了自己的外公、外婆,导致外公被下放黑龙江偏远农场,外婆被批斗惨死,母亲也拒绝父亲再进家门而改嫁自己的养父。这里导致父子血缘关系断裂的根源在于特殊的年代,父亲由于涉世不深非常想参演样板戏而被部队军代表诱导,说了一些外婆抽鸦片止痛、因身体不好雇佣奶妈的事,正是这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被当成了外公一家的罪状。从叙事的内容来看,吕彤身世之谜的揭示完全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他为了买房子而卖掉母亲心爱的京剧行头白马银枪,也不会引出后来他一心要补偿母亲而决定一定要买回这套行头,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身世之谜。如果没有白马银枪,吕彤会一直活在母亲和养父为他编织的谎言之中,无法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对其母、逝去的养父以及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说到底吕彤的亲生父亲白胜堂之所以犯了错,归根结底在于政治资本对文化领域的侵袭。在那个贫苦工农翻身做主的年代,政治身份比舞台功底重要得多,尽管他扎实的舞台功底无人能出其右,但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接受来自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强势因素的介入,这也是造成父子关系断裂的根由。换句话说,“文化场”无法独善其身,不得不任由更为强势的力量来支配。
相对于现代西方原子化的个体之间的关联,建立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化更注重家庭和血缘姻亲关系,更容易形成熟人社会网络,同时也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耕读传家,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尤其稳固,这都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资本更具可继承性。尽管如此,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是以其强大的介入能力,主宰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如杨十月的“认贼作父”和白胜堂的“见利忘亲”,这些都提醒我们要对文化场域的自治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障。
二、社会资本对文化资本的侵袭:赢者通吃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界喊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艺术一方面可以不必作为政治的附庸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另一方面获得自由也意味着无所依傍被边缘化,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作家、诗人再不像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样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人们对诗人、作家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前,更关注的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成功人士。当然,文艺界也涌现出了众多知名人士,凭借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本家”。《歌唱家》中的浩良凭一首《十月金秋飘果香》而名扬四海,得益于名师指点,更在于这首歌生逢其时。可以在1978年于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国庆晚会中演出,不仅在于杨石柱歌唱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首时代需要的好歌、大歌”[1](35)。由此可见,文艺领域的名声和地位不仅仅在于其专业水平,也在于时代和社会的召唤。
艺术不为政治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相应的庇护。“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艺术可以独立自主了,然而,这个理想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海洋中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浩良因政治需要而成为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当市场经济大潮来临时,他也因逐渐失去了政治的庇护而被慢慢遗忘。要恢复过去的辉煌,还要靠大众传媒的影响。杨十月“把父亲曾视若珍宝的各种奖状、奖杯、荣誉证书都翻了出来,摆在一块红布上一一拍照,然后以浩良的名字注册了QQ、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把照片传上去。在头像的位置,他放上了一张王春生的演出照”[1](18)。借着这些材料,他可以重拾浩良先前的崇拜者的回忆,可以借助电视台、电台、报纸等众多大众传媒的力量,继续扩大浩良的影响。
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文化并非圣洁领域。教育和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合谋,将文化产品转换成符号权力,掩盖不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力分配等级,使社会成员相信其自然和合法性。由此看来,文化有其独立逻辑,但最终未脱离社会权力的影响。”[2]艺术领域并非是自治的,也会受权力场的支配,王春生这样的舞台表演者们也不甘心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正常情况下都会积极地与大众媒体、赞助商和审查机构联合,吸引社会关注并追求经济利益,或者向赞助商和市场妥协以换取收益和社会声誉。然而一些文艺场内的“纯”艺术家如杨石柱或袁浩,在面对资本的强势入侵时,会激烈反对,如杨石柱一开始就义愤填膺地要抓住冒名顶替的人,也坚决反对杨十月的做法,后来却只能隐忍退让,不参与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最激烈的反抗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受到他律原则前所未有的危害,林林总总的权力关系伸向自主的文学艺术生产,企图使后者沦为外部势力的附属物”[2](590)。
《诗经》也讲述了一个文化“向钱看”的故事,用形象的方式诠释了文学艺术领域的沦陷。某市诗歌协会打算筹备一次诗歌大赛,但缺乏资金,需要赞助。以养宠物起家的崔启发成为潜在的赞助者之一,对他来说拿出十几万来并非难事,但以“启发猫粮”杯命名本次大赛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来诗歌协会筹措不到款项,不得不向崔启发妥协,在各方博弈中根本没写过诗也不懂诗的崔启发竟然被推举为“诗协”副主席。起初,著名诗人兼诗协副主席闻杨在崔启发眼中是一个略显神秘而高尚的人物。但当诗歌协会缺乏资金时,闻杨也只能向钱投降。闻杨曾经因以“启发猫粮”冠名诗歌大赛拂袖而去,后来因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回来向崔启发道歉,笑脸相迎。极要面子的崔启发在闻杨拂袖而去时丢了面子,后来他用坚实的金钱赢回了面子。在诗歌协会主席和著名诗人面前,也从略带仰视的姿态转变为高高在上的金主姿态,在一众文化人面前经常上演拍桌子走人的戏码。在硬邦邦的资本面前,文化头衔也不得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崔启发成为诗歌协会主席的这个决定一出来,涉世未深的崔启发的雇员袁红丽一脸惊愕,而曾经因诗人的身份对崔启发并不看重的闻杨,也只能默认,以不发一言来保持最后的尊严。这类赤裸裸的交换,对于将海子视为“精神之父”的闻杨来说,再难堪也只能接受,至少比毫无底线的主席高宝玉多保留了一份矜持。因为出了钱,崔启发可以肆无忌惮地要求诗歌协会给他的秘书袁红丽出一本诗集或者给“内定个奖”。尽管崔启发以雇主的名义处处为难大学中文毕业生袁红丽,贬低她的人格,摧残她的尊严,但他仍不满足,还要用金钱来折断更高级的文化人的腰。
面对崔启发们的文化跃层,曾经对文学艺术充满热爱和崇敬之情的袁红丽们彻底失望了,也隐喻曾经默默坚守文学的纯净和高贵的人都被更有力度的能量收编了,诗歌协会高贵而虚伪的面纱也荡然无存了。袁红丽离开了那个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城市,回来后穿衣风格、处世态度大变。她的衣饰隐含着她的转变:曾经她是单纯的刚毕业不久的女生,只身色彩单调的衣服,因为崔启发和闻杨对诗歌协会的所作所为,她去北京漂了半年,变成了衣饰夸张的女生,夸张到翠绿色的紧身小棉袄配桃红色的阔腿裤,“姿态妖娆”地和几个年轻男子聊天,放声大笑。
文化掮客小五劝崔启发出钱理由,道出了文化也是一种当之无愧的资本,也需要奋力争取才能得到。而且,有了诗歌协会头衔的文化人可以骑着自行车与宣传部长吃饭,上报纸、上电视也都触手可及了,这些都让崔启发心动不已。崔启发们如此春风得意,赢者是否真的能够通吃?还好小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结局如何要由读者自己书写。小说中只是用一系列小插曲来暗示崔启发们的“原罪”“出来混总有一天是要还的”。他因猫舍发家,因此可以有机会获得诗歌协会副主席的符号,但也因猫舍扰民被投诉,而且很有可能在他风光无限的主席台上被控诉。也许这些都不会发生,一切都要由读者和这个社会来续写。正因为结局不明,小说的批判力并没有减弱,反而留下了更多令人思索的空间。
小说《雪凤图》从名字看,也透露出其内容和文化密切相关。《雪凤图》是小说中的核心物件,是引出喻小凤和喻美君真实关系的线索。喻美君因为贪图享乐和一点“温暖”,做了范德明的情妇。范是一个身材矮小、年龄不小、小有成就的精明的古董商人。喻美君觉得她在范德明的心中是被珍视的,觉得除了他之外再不会有人给她这种感觉。喻美君的姑姑喻小凤孤身一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坚决不同意喻美君的选择。为了让侄女看清范德明的真面目,她给了美君一幅古画《雪凤图》,让她托范德明卖出去。范德明故意欺骗喻美君说那幅画是假的,以低价买下然后高价卖出。喻美君因此看清了范德明的真面目,也通过追问画作的来历知道,原来画是自己姑姑的亲密爱人,一位高明的当代画家的仿作,因为技艺高超且没有真迹可对比,完全可以在市场上以假乱真。这位画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是自己“姑姑”和画家的爱情结晶。姑姑当年因为爱和画家远走高飞,尽管画家身患绝症,喻小凤还是坚持以未婚的身份生下了她和画家的女儿。画家离世后喻小凤母亲不忍自己女儿未婚生育,命她将孩子养在其哥哥名下,于是喻美君成了自己亲妈的侄女。小说中的《雪凤图》是揭开尘封的历史的关键证物,也是衡量人心的标尺。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范德明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是地道的“渣男”。《雪凤图》虽是文明的结晶,其真假并不重要,其文化意义和价值也不重要,其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才重要。在资本的场域中,它是一幅画,更是凝聚资本的载体。在喻小凤那里,《雪凤图》是爱的见证;在喻美君那里,雪凤图更多的是衡量爱的分量的试金石。曾经的喻美君和范德明的“温情”也被资本这把强势的刀劈得黯然神伤。而喻小凤手中的另一幅高仿画作更是给了她们母女以莫大的底气去追求自己要想的人,这也是金钱给予的底气。《雪凤图》从另一个层面讲述了文化在这个商业社会存在的作用,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几乎无人在意,只有画作的真伪和其拍卖价格才是关注的焦点。文化在资本面前,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是可以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是资本获得利益的工具。
科幻小说《白熊》中的白熊看起来也像一个可以引出一系列隐藏故事的线索,但实际上与前面两篇小说略有不同。白熊是小说中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的名字,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不仅小说中的主人公陈木不知晓,就连岛上最年长的土著居民也都不知道。陈木后来在电视中听到,白熊即将灭绝,进而读者可以猜测白熊岛名称的来历和寓意。陈木以写作为生,他的未婚妻是软件设计师,可以设计出很流行的软件。两人在一次欢爱的过程中,陈木脱离了未婚妻的软件设计的程序,流落到了白熊岛上,再也回不去他曾经熟悉的那个文明世界了。在岛上他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一个名为玫瑰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可以感受他以为是天然的阳光和沙滩,并经历真实肌肤接触的性爱。然而一个因飞机失事落在岛上的摄影师威廉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摄影师要陈木以岛上的人物为原型写小说,陈木答应了并且离开了白熊岛。小说写成后,岛上的生活场景被摄影师当作房产模型售卖,陈木觉得自己被骗了,岛上居民的隐私和权力被侵犯,但威廉的话让陈木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威廉更清高更重感情,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人。随后,陈木发现他以为是真实存在的“白熊”岛,也不过是资本裹挟下的一个可以给人“真实体验”的虚拟网络软件。这篇小说揭示出更可怕的真理:资本不仅支配着现实生活,甚至现实生活本身也是由其构建的,每个人都不过是资本操纵之下的提线木偶!
弗洛伊德说,文学是“白日梦”,从这个角度讲文学是虚构的,但文学也是真实的,是人的无意识的流露,是本能的升华,文学叙述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人在意识深处的难以察觉但又真切关注的问题。这几篇小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强势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面对相对弱势的文化资本的渗透和影响,显示着自己的强力意志。人类最牢固的姻亲血缘关系,在强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面前,显得尤为薄弱。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怎样维护自身曾经维护的独立性与神圣地位,也是文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总体而言,苏兰朵小说的叙事模式和题材丰富多样,但其表层叙事也都隐含着相对统一的深层结构,即决定情节发展甚至割断亲情、爱情的因素多为经济和政治等强势力量。用语言学的话来说,即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作为活跃的辽宁作家,苏兰朵的这些小说也许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资本大潮冲击下的焦虑的无意识的呈现。“文化场域”是各方博弈的阵地,需要去争夺,为自己划出一道适度自治的边界,才能捍卫其独立空间,体现出文化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