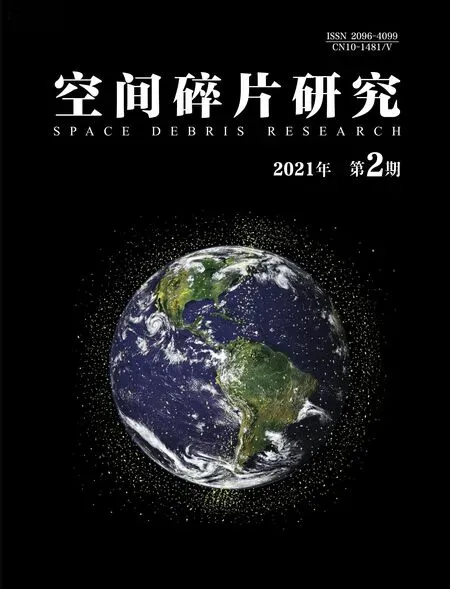《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对空间碎片损害责任的适用路径探析
谢金钗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1 引言
人类对外空活动的探索永无止境,空间碎片便随之产生与爆发。外空活动中空间碎片所造成的损害在实践中频频出现。例如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多家航天商业公司均设置了大规模的星座计划,SpaceX公司在2018年甚至完成了21次发射任务,截止到2020年12月,SpaceX公司已经发射将近千颗卫星。而如此大规模的卫星可能发生碰撞导致空间碎片产生,在其失效后也将成为新的空间碎片,在这样空间碎片造成的损害后果中,责任构成尤为重要。虽然空间碎片所应对的不法行为责任并未有明确的专门依据,但其产生的损害责任却可以被纳入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下称 《国家责任草案》)的适用范畴。虽然国际条约草案本身并非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由于其在国际法实践中通常为国际法主体在相关国际法规则存在缺失或内容模糊等问题时所援引,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因此,确有必要考虑将其作为法律依据的补充适用于空间碎片法律框架,甚至更广阔而言至外层空间法律关系,以弥补现行外层空间法律规则的不足。本文所指草案,是指提交制定主体审议,交由各国表决签字的条约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原型。
但草案在空间碎片,甚至外层空间法被适用与援引也具有一定难度。这是由于草案并非正式有效的国际法规范,当事方难以援引,甚至于国际法院援引其时也需要复杂而费力的论证。但另一方面,草案之所以称为草案,是因为其未来极有可能演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对外层空间法的构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外层空间法领域内的草案,作为各国际法主体初步达成一致的产物,具有较之国际条约更易修改的特征,发挥着协调外层空间活动的作用,使得各国在外层空间法领域能够绕过难以谈判的僵局,充分考虑客观技术限制所致之不确定性、各政治实体的立场以及各国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探究草案在空间碎片损害责任的适用路径确有必要。而本文将以200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例,探究草案在空间碎片损害责任的适用路径。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可以作为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还有司法判例和公法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原则之补充资料。但由于草案并非有效的国际条约,因此在外层空间法领域将草案加以适用的国际法路径可以是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考虑至空间碎片损害责任,乃至外层空间法领域对一般法律原则的理论研究缺乏从而导致上述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内涵与外延均难以明确[1],同时司法实践中对一般法律原则的独立适用热情不高[2],因此本文主要考虑 《国家责任草案》以习惯国际法地位在空间碎片损害责任领域适用。
2 草案在空间碎片损害责任中的适用路径设想
受限于科技发展,空间碎片相关立法的实践历程较短,相关国际案例并不多见,但草案作为习惯国际法在其他领域得以适用的案例并非少数,例如1997年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的匈牙利诉斯洛伐克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将 《国家责任草案》第25条危急情况视为习惯国际法[3],但并未作出详细论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在美国安然资本和贸易资源公司诉阿根廷案中认为,《国家责任草案》第25条危急情况为国际习惯法[4];同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在美国铁路发展公司诉危地马拉案也表示,将 《国家责任草案》直接作为国际习惯法予以适用[5]。甚至也有学者表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 《国家责任草案》条款,受到各国广泛的支持,尽管并未是普遍意义上的支持。《国家责任草案》的部分规则有些已经是习惯国际法了[6]。
习惯国际法系 《国际法院规约》所明文规定的国际法渊源之一,甚至早于国际条约出现在国际法渊源之中。《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项(丑)款把习惯国际法定义为 “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as evidence of general practice accepted as law)。传统认为,要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必须查明是否存在一项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惯例,即习惯国际法的论证需满足二要素—— “一般惯例”与“法律确信”,且两个构成要素中的每一要素必须单独予以确定。“一般惯例”包括国家惯例,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惯例也有助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或表述,但有关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即必须足够普遍并具有代表性,还必须是一贯的。“法律确信”意味着有关惯例的采用必须带有一种法律权利或义务感[7]。
举例而言,空间碎片可能成为人造卫星与轨道空间站的潜在杀手,即使只有100μm的碎片也可能足以如子弹一般穿透宇航员的航天服,造成人员伤亡与设备严重损毁,不难想象,空间碎片损害责任领域产生的责任从数量到影响程度都是巨大的,因此国家会极力寻找解除行为不法性的事由从而不予承担责任。其中,《国家责任草案》第25条规定的危急情况是很多国家在此时的选择。例如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近海海域上空开展军事侦察活动,但其飞行途中,违反安全飞行规则,突然转向并撞向中国飞机,致使中国飞机坠毁。随后,该侦察机擅自进入中国领空,降落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而美方曾以危难、紧急避险等事由解释擅自进入并降落中国领空不法行为的不法性[8]。若运用传统二要素论证 《国家责任草案》第25条危急情况为习惯国际法,需要从一般惯例与法律确信分别论证。从一般惯例看,空间碎片损害责任有关危急情况的国际实践几乎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国家在援引草案中危急情况条款时可参考其他领域案例。如果其他国际法分支领域案例足以证明草案规定的危急情况为习惯国际法,空间碎片损害责任对应的外层空间法作为国际法的分支,也可参照适用这些案例。在其他领域,一些国家援引过危急情况,若干国际法庭也对它进行了审理,危急情况已在原则上获得接受,或至少未被驳回。例如在1832年英国与葡萄牙的争端,英国承认危急情况是解除不法性的事由[9]。在1837年的“卡罗琳号”事件,英国和美国政府在交函中也承认危急情况可允许双方进入领土[10]。再如,1997年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的匈牙利诉斯洛伐克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11],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审理的美国安然资本和贸易资源公司诉阿根廷案[4]等。从法律确信看,法律确信的证据也并不少见,例如在1893年的 “俄罗斯海狗”争议事件,俄国政府发布了法令承认危急情况可禁止在公海的某一地区捕掠海狗[11]。因此,国家可以援引上述一般惯例与法律确信的证据,证明 《国家责任草案》的部分条款在外层空间法可以习惯国际法的路径予以适用。
3 草案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于空间碎片损害责任的问题
草案在外层空间法领域可以习惯国际法路径适用,但该路径下也存在问题,有些问题甚至难以解决。若草案在外层空间法领域通过习惯国际法路径适用,难以满足习惯国际法的传统二要素论证要求,也因此容易出现“决断”的情形,即直接认定草案构成习惯国际法,并未对认定依据、如何认定作出论证。
传统认为,习惯国际法的论证需满足二要素,一般惯例与法律确信。但在外层空间法领域,传统二要素对习惯国际法论证是苛责的,甚至难以实现的。这就是草案在外层空间法以习惯国际法路径予以适用的第一个问题。原因在于,第一,外层空间法虽从1957年人类进入空间时代即开始发展,但外层空间活动的国家实践仍有限,自然不必说可以作为外层空间法一般惯例的国家实践。虽然可以借助其他国际法领域的国家实践予以论证,但外层空间法毕竟属于新兴领域,习惯国际法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国家、国际组织有关外层空间法的实践缺乏,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也相对有限,法律确信同样也难以得到确认。第二,这与国际空间法本身的发展和适用特征密不可分。随着技术的发展,外层空间活动日新月异,外层空间的原则与规则因而持续动态发展,在具体案件中认定草案的习惯国际法地位是极富有挑战性的。因此,传统二要素反倒成为草案在外层空间法领域作为习惯国际法得以适用的最大问题之一。
这样的问题在外层空间法司法实践中不仅难以解决,甚至会孕育出新的问题——不经过传统二要素严格推理过程而直接认定草案是一项习惯法规则,更确切地说,在外层空间法领域以习惯国际法的地位适用 《国家责任草案》缺乏论证材料与依据,但出于对案件适用的迫切需求,司法实践可能会在未经推敲与论证情况下直接认定《国家责任草案》为习惯国际法从而加以适用,即便 “决断”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此处并非否定 “外层司法造法”的趋势,而是认为司法实践中对习惯国际法的论证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论证态度。
这样的问题在其他领域也并非少见。斯蒂芬·塔尔蒙 (Stefan Talmon)曾指出,“国际法院认定习惯国际法的主要方法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决断 (assertion),即在认定草案为习惯国际法时,并未基于大量而具体的证据考察,也并未进行严谨的演绎或归纳过程,而直接又简单地认定其属于习惯国际法,抑或满足习惯国际法二要素的条件[12]。譬如匈牙利诉斯洛伐克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国际法院在未对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的证据进行调查和认定的情况下,即认定 《国家责任草案》第33条危急状况为习惯国际法[3]。又如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的两个案例——美国安然资本和贸易资源公司诉阿根廷案认为 《国家责任草案》第25条危急情况为国际习惯法[4],美国铁路发展公司诉危地马拉案中将 《国家责任草案》直接作为国际习惯法予以适用,且未指出 《国家责任草案》中究竟哪一条款构成习惯国际法。
笔者认为, 《国家责任草案》主要内容为不法行为归于哪一国的问题,在其他领域易出现“决断”问题,在外层空间法领域出现的可能性更高。原因在于外层空间法框架更为简易,证明《国家责任草案》为习惯国际法的材料更少,“决断”方法出现实际是无奈之举。虽然此种 “决断”的方式并非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甚至可能在少数案件中,国际法院会援引具有法律效用的官方文本或权威著作,但援引的效果难以达到传统二要素的要求,这种决断更像是运用 “显而易见”这样的字样掩盖其论证不足。这一认定草案为习惯国际法的问题在外层空间法领域是应当引起警惕的。无论是出于争议解决经济成本的考虑,抑或是基于发展外层空间法治规则的迫切需求,还是客观层面下具体存在的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缺乏的证据问题,甚至是为了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场面,“决断”作为认定草案为习惯国际法的方法应当被谨慎使用。否则 “决断”可能会演化成外层空间司法造法的口径,以至于未来在外层空间法领域 “决断认定习惯国际法”被默认为合理方法。
故在外层空间法领域,认定 《国家责任草案》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二要素对习惯国际法认定要求过于苛责,外层空间法的习惯国际法证明难以建立在具体考察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归纳基础之上;二是传统二要素催生 “决断”问题,即在外层空间法领域认定 《国家责任草案》为习惯国际法缺乏论证材料,但出于对法律规则的迫切需求,司法实践可能会 “决断”即未对习惯国际法的确定加以严格论证,即便 “决断”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4 以演绎法解决习惯国际法的传统认定问题
鉴于草案在外层空间法适用路径下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试图缓解问题甚至解决问题:以归纳法、演绎法同时适用的方式解决习惯国际法传统认定问题。归纳法由于需要一定的法律、司法实践为基础,因此在外层空间领域适用空间小。但国际法院可以在使用归纳法的过程中搜寻考察资料,同时结合演绎法,寻找最优解。此外,当事国辩论与陈述意见也可作为重要参考。具体论述如下:
上文已述 《国家责任草案》在外层空间法被认定为习惯国际法的两大问题—— “传统二要素法”的苛责与 “决断法”的草率,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放弃 《国家责任草案》在外层空间法以习惯国际法路径得到适用。在外层空间法, “习惯国际法”的认定除了传统二要素 (归纳法),尚存在其他更适宜路径——演绎法。笔者建议,可以同时使用归纳法、演绎法,从而达到认定习惯国际法的目的。
演绎法的出现是存在特定原因的。当运用归纳法难以论证草案为习惯国际法,决断法又过于武断,演绎法即可被适用,即从已具有法律效用的公认规则中演绎推论出另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13]。例如,国际法院在1949年科孚海峡案中认为,沿岸国和平时期的雷区通知义务属于习惯国际法,来源于人道主义原则、海上交通自由原则、一国领土不得损害他国权利原则[14]。同样地,国际法院在1986年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15]因此,在外层空间法领域,草案中的规则可以通过演绎推理其他普遍接受的规则中得出,譬如,一国外层空间活动如何进行一般取决于一国意志,若一国进行空间活动时被胁迫,请求国际法院判决胁迫国承担责任,该国意图援引《国家责任草案》第18条, “胁迫另一国实施一行为的国家应该对该行为负国际责任,如果:(a)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该行为仍会是被胁迫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且(b)胁迫国在知道该胁迫行为的情况下这样做”。运用演绎法的语境下,《国家责任草案》胁迫一国的责任归属问题,转化为寻找有关普遍接受的国家法规则或原则的问题。此国际法规则并不难找寻,即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 《外空条约》第1条自由平等原则, “所有国家可在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因此通过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 《外空条约》第1条自由平等原则可以演绎推理出 《国家责任草案》第18条为习惯国际法。
归纳法是传统认定方法,在外层空间领域,其并非最优解。但国际法院仍然可以在使用归纳法的过程中搜寻考察资料,从而为草案认定为习惯国际法提供进一步的辅助论证,因此演绎法、归纳法并非相互排斥。譬如,在国家管辖豁免领域,国际法院在2012年德国诉意大利的国家豁免案中既利用演绎法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属于习惯国际法,同时通过归纳法进一步确认[16]。那么在上述假定胁迫案例中,国际法院仍然可以考察归纳法的 “一般惯例”和“法律确信”的素材,如蒙古曾对 《国家责任草案》第18条 “胁迫”一词提出质疑,并认为第18条胁迫一国承担责任目前不具有适当性[17]。因此,国际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也需充分考虑蒙古在 《国家责任草案》中提出的质疑。
此外,当事国辩论与陈述意见也可作为重要参考,即 “当事国对草案为习惯国际法并未提出异议”,“国家并未质疑该草案为国际习惯法”[3]。虽然这样的意见陈述并不能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关键性证据,但可以作为辅助参考资料,并在此无争议事项上进行进一步特定案件处理。这也与习惯国际法效力来源理论 “同意主义”不谋而合,即习惯国际法的效力来源各国同意 (consentualism)。国际法院曾在1927年荷花案中认为,国际法调整国际法主体的约束力来源于国际法主体的自由意愿,这些意愿的表现形式体现在国际法的具体规则中[18]。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同意应谨慎地认为是 “概括同意”,并非 “分别同意”,将国际法放置个案各国诉请利益上是值得警惕的,因此当事国的分别同意只能作为参考依据,并非认定草案为习惯国际法的关键性证据。
5 结语
外层空间在众多方面都堪称独特,在法律方面也具有其特殊之处。而空间碎片作为空间科技高速发展的产物,其带来的不法行为与责任的探讨,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去寻找过渡性法律产物实有必要。因此草案作为过渡性法律产物,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都存在着,它演变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正式法律文件也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因此,拓展草案以习惯国际法作为空间碎片损害责任领域的适用规则实为必要,同时在充分认识其问题的基础上,以演绎法解决习惯国际法传统认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