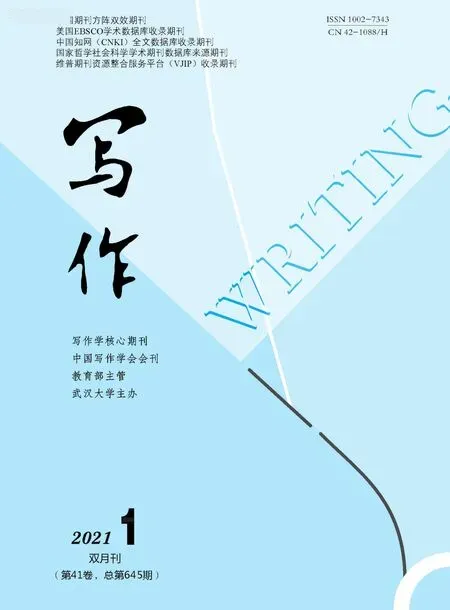论汪曾祺的小说
张 均
1941 年2 月,沈从文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西南)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于今观之,沈从文的预言似乎应验了,且“相对于同时代作家而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对汪曾祺的评价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②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不过我自己当年初读《大淖记事》,印象却并不为佳。小说中说:“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当时我刚从农村到大学读书,对农村原始劳动的艰辛刻骨铭心,因而对这种将他人艰辛予以审美化的文人写作深怀抵触。比较起来,《白狗秋千架》《塔铺》哪怕是《绿化树》,都比汪氏小说更契我心。这种印象,至今并无本质的改变。不过岁月荏苒,每个人都在逐渐学会接纳与自己不同的经验、眼光与叙述,何况那个“自己”也在势不可遏地变化着。以此观之,汪曾祺虽然缺陷明显,但置诸“短20 世纪中国”却又是独树一帜的特殊人物,是中国古老士大夫文化“起死回生”之关键人物。
一、“生活的艺术”
“士大夫文化”云云,并非指“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儒家淑世情怀。准确地说,是指其反面。中国传统政治至秦汉一统之后,便逐渐走向集权体制。生活于其间的士大夫,亦由此失掉了战国时期那种“士无长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杨雄《解嘲》)的“黄金时代”。相反,荣辱乃至生死系于一人之手的人生困局却逐渐成型,“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杨雄《解嘲》)的现象,渐成常态。在此情形下,兼之文人士大夫对佃佣仆从之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生活原本就缺乏普遍兴趣与正义感,儒道互补遂成为“古代士大夫精神结构的重要特征”,“许多时候,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志向遭到了挫折,他们不得不退居‘独善其身’的境地”,“道家思想认为,各种道德功名无非有形无形的桎梏,只有摆脱一切‘物役’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士大夫时常自如地往返于二者之间,左右逢源”。①南帆:《前世今生:士大夫、知识分子与文化趣味》,《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白居易《寄隐者》将此种士大夫心理结构说得分明:“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因此,隐逸生活方式或向往隐逸生活的心态,就成为士大夫文化的重要构成。当然,这并非说士大夫们真的会纷纷到终南山搭间茅屋、卧看云舒云卷,而是说他们往往会抱此种心态:即便居朝为官,即便奔走利禄之途,他们也仍会在生活中以闲淡、玩世为高,在文艺上以闲远、散淡为美。甚至,愈是在现实中热衷仕途者,愈是在文艺中倾心隐逸。这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宋人郭熙有很好的描述:
尘嚣僵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林泉高致·山水训》)
当然,在现实中,这种隐逸情怀并不止于“林泉之志”,诸如醇酒妇人,诸如饮食山水,诸如衣饰收藏,诸如清谈品评,甚至抱病养懒,都可以成为疏离庙堂甚至不与之合作的“生活的艺术”。
这种令汪曾祺执爱不已的“生活的艺术”,显然是以自适为旨而疏离现实政治的。故对此文化传统的评价,注定不稳定而与时俱变。在帝制时代,“政治”主要被理解为利禄之途,“生活的艺术”就多被认定为士大夫精神风姿的标识,但晚清以后,所谓“政治”实已增添“新民”“救国”“解放”“启蒙”等崭新内容,对“生活的艺术”的评价不能不变得复杂。文学革命期间,陈独秀对所谓“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激烈抨击可谓石破天惊的开端。直到今天,仍有评论家不太满意此类艺术,如摩罗叹息道:“(他们)彻底失去了安邦定国、济世救民的心力膂力。他们只好关起精神的门扉,躲在感官的院落里,或提笼架鸟,鼓瑟调琴,或狎妓戏柳,纵酒溺烟,或巧制玲珑,精养花草”,“(他们)不失时机地沉溺于某些特定种类(重技术训练的那些种类譬如博弈、弹奏、词曲、书画、园林、烹饪等)的娱乐文化和审美文化之中。至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则渐趋荒芜,只剩下满目榛莽”。②摩罗:《末世的温馨:汪曾祺论》,《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不过,在“后革命”的今天,人们对鲁迅毕生以求的“挣扎和战斗”兴趣寥落,诸如此类的批评就逐渐稀落了。与之相对,废名、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文人所承续的士大夫的“生活的艺术”,就重新唤起无数当代读书人久远而温暖的记忆。如周作人的“喝茶的艺术”,怎么看,都令人倾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喝茶》)
从早年始,汪曾祺就倾心这种“生活的艺术”。他之于此种士大夫文化的接受,并非因于自身的政治失意或命途坎坷。他的早岁经历,无非是读书、教书二事,中年时期遭逢诡谲不测的政治,但也不能说是经历了巨大的人生磨难。故汪曾祺与士大夫文化的亲近,更主要是集体无意识的濡染或天性使然。他的友人、小说家邓友梅的一段回忆可见一斑:
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腿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在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菜。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开饭时启锅……”①邓友梅:《再说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这是1951年的事情。其时汪曾祺不过31岁,但已孜孜于“生活的艺术”了。及至1970-1980年代之交,数年世态炎凉的袭来,也只是使他这种天性更得以发挥,但也由此造就了他在1980年代的“大器晚成”。
汪曾祺的文字,弥漫着士大夫文化的“生活的艺术”。其最明显者,是对故乡风物的摹绘,尤以饮食为甚。汪曾祺每以沈从文为师,实则沈从文极少涉笔吃事。与他相仿的,倒是前辈周作人与同龄人张爱玲。在现实中,汪曾祺即以爱吃、善烹饪而著称。他自称“什么都吃”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散文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265页。,甚至将“做做菜”与“写写字、画画画”并列,称做“我的业余爱好”③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散文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265页。。他爱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60 页。他甚至还宣布“退休之后,搞一本《中国烹饪史》,因为这实在很有意思,而我又还颇有点实践”⑤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1页。。当然,《中国烹饪史》最终未能面世,但已面世的汪曾祺文字中谈吃论食者,又何止一二?可谓俯拾皆是,且时有动人之处。如写于1945年的《老鲁》就已开始注目于“吃”了。当然,其时清苦,吃不到肉,吃的是一种当地人从未吃过的虫子:“(老鲁说)这种虫子可以吃。当晚他就捉了好多”,“老鲁笑嘻嘻地拿回来,掐了头,撕去甲翅,动作非常熟练。热锅里下一点油,煸炸一下,三颠出锅,上盘之后,洒上重重的花椒盐,这就是菜。”等到1980年代,这类涉及和专述吃食的文字就非常多见了,如《故乡的事物》《咸菜与文化》《端午的鸭蛋》,等等。《端午的鸭蛋》可谓当代散文的佳制名篇:
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记吃而成名篇,并不单因于文字的散淡、灵动。对此,汪曾祺倒是淡淡提过:“谈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那么,谈谈何妨?”⑥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60 页。那么,是怎样的“对生活的态度”呢?此即传统文人疏离庙堂、不屑与体制合作的狷介之姿。于是,吃,就不仅是吃。《绿化树》《平凡的世界》写吃或仅与饥饿有关,但汪曾祺或周作人写吃,则另有独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格调与姿态。这种姿态可清晰地见之于汪曾祺的历史哲学。他曾为同乡金实秋《戏联选萃》写过一篇序文,其中引用了一副戏联,云:“功名富贵镜中花,玉带乌纱,回头了千秋事业;离合悲欢皆幻梦,佳人才子,转眼间百岁风光。”在这迹近于《好了歌》的戏联的背后,潜隐着汪曾祺疏狂远世的人生立场:“最好永远躲在花荫柳下,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正剧闹剧、悲剧喜剧。”⑦胡河清:《汪曾祺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显然,汪曾祺的记吃述食,丝丝缕缕,牵涉着知识阶层久被埋没的精神的历史,勾连着久远的记忆与风骨。
不过,汪曾祺之所乐者,并不止于饮食。他回忆他的父亲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他会做各种灯”①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汪曾祺本人对这些不相干的物事,也是兴致盎然。而且,这些还都进入他的文字,变成了朴实而亲切的故乡的风景、风俗与人事。
二、“幻美的迷力”
“生活的艺术”置诸凡俗,多能养就性情中人,但对于操弄文字之辈如汪曾祺者,则可能另有所成。1940 年代末期,曾有左翼批评家批评汪氏小说《鸡鸭名家》,称它“以一种‘幻美的迷力’”,“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②转引自钱理群:《寂寞中的探索——介绍四十年代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追求》,《北京文学》1997年第8期。这一批评堪称准确,它既点明了汪曾祺与文学史的关系,也从反面映射出了汪曾祺小说的特点,甚至优点。汪曾祺曾经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所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③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页。
“小品”云云,不仅是指汪氏喜择短小故事而为之,更指他愿在这方寸之地上营造艺术的至境。实际上,“册页”“小条幅”者,更可以通过“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而使“文学作品之成为文学作品”④朱光潜:《谈美谈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严格地讲,在青年、中年时代,汪曾祺都算是生不逢时,因为“小品”或“册页”,都不合乎“短20世纪中国”的需要。从“五四”开始直至1970年代,最怀正义感的写作者们,从鲁迅、巴金、艾青以至丁玲、柳青,都企图以写作来改变现实的文化和秩序,以建构新的认同与制度。这样的写作,高度关注现实中的“无数的人们”,尤其关注文化/政治权力关系之下的个体生存,且往往通过个体或“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建构新的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显然,汪曾祺与这样的写作格外不相宜,因为士大夫文化的“林泉之志”,恰是以疏远现实斗争/改革为特征,或准确地说,是以默认现实秩序、“躲进小楼为一统”为特征的。然而对“短20世纪中国”的这种主流写作,汪曾祺也难以以“政治”为由、将之轻松打发到“尘嚣僵锁,此人情所常厌”的范围,而只能承认“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⑤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页。。这注定了汪曾祺在如此“大时代”的落寞。其实,即便不发生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动,汪曾祺也难以成为“短20 世纪”的“中心作家”。对这其间的微妙之处,汪曾祺自己是明白的。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去攀附时代。尤其在环境日益逼狭之时,他往往能做到不动笔,甚至不动心:“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我当时没有想写东西,不需要赶任务,虽然也受错误路线的制约,但还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的。我当然也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文艺思想的左右,但是并不‘应时当令’,较易摆脱,可以少走一些痛苦的弯路。”⑥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能为曹禺、老舍之不能为,当然与汪曾祺内秉的狷介心态有关:人间不过戏里戏外,如梦幻泡影,又何必要去“应时当令”呢?但革命终有落幕之时,进入1980年代,汪曾祺终于迎来了与自己相宜的年代。虽然这时期“伤痕”“反思”“改革”诸种小说潮流仍走在“短20 世纪”的文化轨道上,但汪曾祺的疏远现实、缺乏变革之意、用力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一类小说,却从真真假假的现实主义中异军突起。等到一个对革命“不再相信”的时代正式到来,汪曾祺小说中的“幻美的迷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的艺术”,就注定要广受欢迎了。
以我读《受戒》的感受,这“幻美的迷力”不在于故事,不在于命运,而突出地表现在对意境、诗境的营制上。《受戒》全篇,犹如一首幽净、纯美的小诗。小说结尾之笔,在文学史上久为称道: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如此纯净的诗境,对于经见诸多历史变幻尤其亲历“文革”结束之初政治波折的汪曾祺而言,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人生的“梦”。而这样的梦幻,是他有意为自己寻求到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平坦的生活道路对我个人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经过长久的学习和磨炼,我的人生观比较稳定,比较清楚了,因此对过去的生活看得比较真切了。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但是你用什么观点去观察和表现它呢,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①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7、16、22、192页。如果说谈吃述食源于久远的文化记忆,那么,《受戒》《大淖纪事》一类事关前尘往事的“梦”则是他所遭受的人世刺激的衍生物。而在这些“梦”的“幻美的迷力”的背后,是汪曾祺别具匠心的“小说学”。对此,他自述道:
意境一说最初只用于诗歌,后来涉及到了小说。废名(冯文炳,1901-1967)说过:“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何立伟的一些小说也似唐人绝句。所谓唐人绝句,就是不著重写人物,写故事,而著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物我同一,作者的主体意识很强。这就使传统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小说和诗变得难解难分。②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将小说当作诗来写,是高难度的叙事学。“五四”以后,废名、孙犁都是顶尖的作者。其要点在于轻故事、轻人物,恰如汪曾祺所言:“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③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7、16、22、192页。显然,曲折的故事,动荡的命运,在汪曾祺看来,未必能见出人生真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事能捕获的,至多只是人生外部的粗略行迹,做小说者,当然不宜拘泥于此。故他说:“我的小说也像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④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7、16、22、192页。“不求形似”,自然是为“忘形得意”,然而“意”又岂可易得?他的《受戒》《鸡鸭名家》《异秉》《鉴赏家》诸作,文字看似平易,实则极为讲求。汪曾祺重用字,讲求留白,点到即止,这使他的小说虽是白话近作,却深具古诗之余味、古笔记小说之悠长意蕴。以汪曾祺之见,这是他从沈从文那里“悟”来的为文之法:
在昆明,有一阵,他常常用毛笔在竹纸书写的两句诗是“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我就是从他常常书写的这两句诗(当然不止这两句)里解悟到应该怎样用少量文字描写一种安静而活泼,充满生气的“人境”的。⑤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7、16、22、192页。
“人境”,是汪曾祺制造“幻美的迷力”的“真意”之所在。他小说中那些幽美的意境,往往勾连着为人之初的本真与干净,蕴藏着天地之间的一份纯朴。
短篇小说《职业》写一个因为家境不济而卖点心的孩子,“这孩子也就十一二岁,如果上学,该是小学五六年级”,但他是个孤儿,得自己挣钱吃饭,不过他上街卖点心,却经常被放学的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模仿他的吆喝,他喊的是“椒盐饼子西洋糕”,由于昆明人读“饼”字不走鼻音,“饼子”和“鼻子”很相近,所以孩子们的模仿就变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他受到这样的捉弄倒也不生气。更特别的是,某天他不用卖点心而可上外婆家:“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有人(他没看见我,我去看一个朋友,正在倚门站着),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的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这无疑淡若无痕而又意味深长。有人认为此小说同情劳苦者,其实不然,汪曾祺从来不是革命同路人,“同情”“批判”“赞美”等关键词都不宜于他的小说。《职业》所叙者,实乃卖点心的孩子被谋生、被“职业”久久压抑的本真童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的“人境”之所以能充满“生气”,与这种“童心”是有关的。《受戒》《大淖记事》所记,既为“童心”又不止于“童心”,而另有尚未被社会所玷染的纯朴与干净。《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在救起落水的巧云后,却不懂得少女心思:“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十一子把她放在床上。巧云换了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的美丽的少女的身体)。十一子抓一把草,给她熬了半铞子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巧云起来关了门,躺下。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月亮真好。巧云在心里说:‘你是个呆子!’”如此幽美境界,如此动人情致,皆使文字成为生命的深深的痕迹。
无论卖糕点孩子的“童心”,还是巧云、小明子悄然萌动的性意识,都是汪曾祺在“唐人绝句”式文字之下对人性本真的理解。这类干净如初的人性,无疑使“幻美的迷力”更见底蕴。的确,这样的与现实环境比较游离的“幻美的迷力”,是会“蒙蔽”“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的。喜欢汪曾祺文字的人,估计也会喜欢《浮生六记》《陶庵梦忆》,这样的文字,即便笔涉苦难,也是平淡如水、不动声色,绝不与现实秩序“拔刀相向”。但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选项,“和谐”也是一种宽阔的、柔软的理解世界的眼光。人与人之间的体谅、温暖与爱,底层人物面对困境的坚韧、承担与乐观,本身也是一种结结实实的生命哲学。汪曾祺将自己定位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①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4、34页。,大约正是此意。
三、大隐隐于市井
有关“幻美的迷力”的营造,以及对于“生活的艺术”的执著,都疏远现实(尤其革命现实)而与传统士大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汪曾祺个性使然,更是他自我坚持的结果:“我从弄文学以来,所走的路,虽然也有一些曲折,但基本上能做到我行我素,经过三四十年缓慢的,有点孤独的思索,我对生活,对文学有自己的一点看法,并且这点看法就像纽子大的枇杷果粒一样渐趋成熟。”②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4、34页。不过,如此“我行我素”的汪曾祺,并非只是用现代白话重写明清小品,他的“小品”也不仅是士大夫文化在“短20 世纪”的投影。事实上,汪曾祺小说不但是对士大夫文化的有效复活,也是对士大夫文化的重新创造。“大隐隐于市井”,可谓是汪曾祺对士大夫文化的现代改写,别开生面,殊难复制。
“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是古代士大夫文化关于隐逸的常见观念,但无论是“小隐”“大隐”还是“中隐”,都是针对士大夫而言的选择,但汪曾祺的小说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人物,却并不出自缙绅之家或教授阶层。甚至可以说,身为读书人的汪曾祺,其实不大喜欢描绘知识阶层及以上阶层的人生。他所喜于刻画的,多是所谓“低层社会”的人物,如《鸡鸭名家》所谓“名家”,一个是炕房孵鸡的师傅,一个是养鸭放鸭的师傅,又如《鉴赏家》中最懂画、爱画的“鉴赏家”其实是一个卖时令水果的小贩,就是《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也不似其名号那样似有来历,“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诸如此类的人物,实话讲,传统士大夫未必屑于记述,至少不屑于浓墨重彩地去记述。古来文学史上,确实有过同情低层人物的篇什,但极少占据主流。汪曾祺喜古却不泥古,他的取材与立场,分明来自“五四”以后人道主义的濡染,甚至有着革命文化关于劳动主体创造的遗留。他说:
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③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4、34页。
将贩夫走卒之人与《老子》《庄子》相勾连,并从中掘发“中国色彩”,可谓是汪曾祺惊动文学史的地方。“大隐”并非隐于“市朝”(士大夫出仕之所),而是隐于“市井”,隐于炕鸡、刨烟、熏烧、卖豆腐脑一类营生之中,这是对士大夫文化前所未有的“颠倒”。然而汪曾祺丝毫不以为异。他欣然地用《世说新语》的笔法去记录这些“低下”之人:“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涉及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小说看。”①汪曾祺:《晚翠文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1页。借助古人以简写繁的经验,汪曾祺写活了一批市井中的“隐者”。
其中,最给人难忘印象的,是《鸡鸭名家》所写炕鸡的余老五。余老五是炕鸡一行的状元,“他炕出来的鸡跟别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炕出的鸡,他的鸡特别大。刚刚出炕的小鸡照理是一般大小,上戥子称,分量差不多,但是看上去,他的小鸡要大一圈!那就好看多了”,“怎么能大一圈呢?他让小鸡的绒毛都出足了。鸡蛋下了炕,几十个时辰。可以出炕了,别的师傅都不敢等到最后的限度,生怕火功水气错一点,一炕蛋整个的废了,还是稳一点。想等,没那个胆量。余老五总要多等一个半个时辰”。汪曾祺对“这一个半个时辰”里的余老五的刻画,极舍得气力:
余老五也疲倦到了极点,然而他比平常更警醒,更敏锐。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塌陷了,连颜色都变了,眼睛的光彩近乎疯狂。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恼怒,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很奇怪,他这时倒不走近火炕一步,只是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木床、棉絮,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吧?”摇摇头。——“起了罢?”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这是神圣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鸡鸭名家》)
这几乎是脱离一切时空的美的片刻!在“这一个半个时辰”里,余老五忘却周边的一切,惟与炕房浑然一体,不分你我,物我两忘。被叙述者如此,叙述者又何尝不如此?《鸡鸭名家》对陆长庚的描写同样攒足了气力。陆长庚是“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他到湖上吆“散了”的鸭群时:“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里小船的四围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
诸如此类的人物,即是市井中的“隐者”。称他们为“隐者”,自然不是指他们离群索居、不与人交接,而是指他们虽在人群之中,却又不沾滞于、不受限于人群中的主流价值观。他们游离于启蒙或革命的观念是显然的,但他们更游离于市井社会的价值观。像余老五这样有绝活的人,似乎并不以赚钱为念:“每一家炕房随时都在等着他。每年都有人来跟他谈的,他都用种种方法回绝了。后来实在麻烦不过,他就半开玩笑似的说:‘对不起,老板连坟地都给我看好了!’”“后来余大房当真在泰山庙后,离炕房不远处,给他找了一块坟地。附近有一片短松林,我们小时常上那里放风筝。蚕豆花开得闹嚷嚷的,斑鸠在叫。”(《鸡鸭名家》)这样的人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一份痴迷甚至有一份嗜癖。对周边世界则自在优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如此人物,当然“可能有老庄的影响”。
将这种“隐”的状态体现得更明显的,是另一些未必有绝活、有嗜癖却更加“散淡”的人物。《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落魄过,发达过,又落魄了,但这种种人世沉浮于他们仿佛都是身外之事,得失皆自在随意。《庄子·大宗师》讲“三外”,认为人若持“三外”(“外天下”“外物”“外生”)之法,则最终可以消灭各种对待关系而从世俗欲望中彻底解脱出来,最终获得真正的大彻大悟与自由,正所谓“三外”“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是也。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外生”之念当然没有,但“外天下”尤其“外物”之念则颇为显然。其轻薄世间利禄的“风流”姿态,甚至不低于《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其中,写得最惊心动魄的,是短篇小说《鉴赏家》。小说中,叶三以卖水果为生,因“知音”而得到大画家季匋民许多赠画,季去世以后画价大增,包括日本人辻听涛都来求画:
辻听涛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听涛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
“不卖。”
辻听涛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一句“埋了”,尽见市井人物的风度!对于以卖水果、开布行为生的家庭来说,尤其对于并不懂画、日日须计算银钱进出的叶三之子来说,要把价格惊人的画作“埋了”,非“外物”到了极深境界必不可为。“大隐隐于市井”在此实在不是虚言。可以说,汪曾祺在市井里巷之间赋予了士大夫文化以新的活泼泼的生命。
这些平淡、不动声色的文字,构筑着汪曾祺的世界,这个世界“发之于物我并生的性情,落实于市井人生,更酿造出在天地景物风致中看人生、赏玩人情世故的审美意绪”。①肖鹰:《中国美学通史》明代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置诸文学史,不能不说是汪曾祺的独有创造。无论是“大隐隐于市井”,还是“幻美的迷力”抑或“生活的艺术”,都可说是士大夫文化的复活与再生。对此,予以怎样的赞誉都有其特殊根据。不过,理解汪曾祺仍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区别。虽然沈、汪彼此皆承认他们在文学上的师承关系,尤其汪曾祺多称“我是沈先生的学生”②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但两人的精神底质实相去甚远。沈从文钟情的乃“乡下人”及其蛮强的气息,“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③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汪曾祺即便在乡下人身上,发现的也仍然是与士大夫相似的精神遗存,两人骨子里到底不同。二是汪曾祺毕竟身经革命时代,即便要做“最后一个士大夫”也必然不能竞得其功。他的少数文字里,仍埋藏着当代生活的悲剧与隐痛,如《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后者更像是非虚构写作:
小王一直似听不听,躺着,张眼看着房顶。忽然,他问我:“老汪,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下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告过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自己的工资数目,但是我跟小王认识不止一天了,我不想骗他,便老实说了。小王没有说话,还是张眼躺着。过了好一会,他看着房顶说:“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你就挣那么多?”他并没有要我回答,这问题也不好回答。
这样的问题与答案,古时的文人士大夫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于是,汪曾祺和他的这些精神的先祖们,终究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了。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