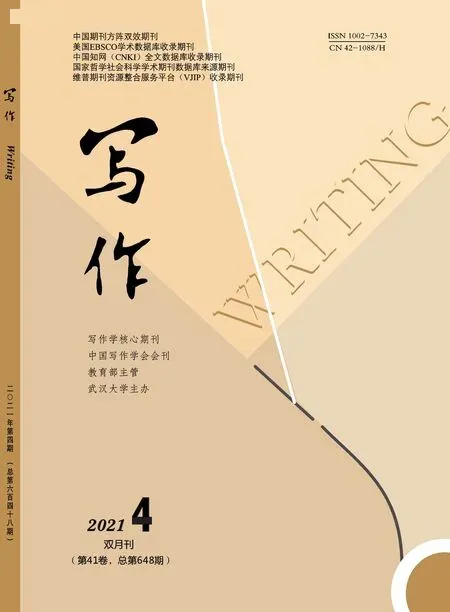论小说写作中的“故乡思维”
——以黄永玉为例
汤 达
一、引言
黄永玉以画家名世,但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过,文学在他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只相信文学带给他的自由①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序言,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他的文学创作履历,也佐证了这一说法。1981年,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获得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同时获奖的有艾青、邵燕祥、流沙河、舒婷等人。他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那些忧郁的碎屑》《从塞纳河到翡冷翠》,不仅受到学界好评,也广为普通读者所传颂。201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黄永玉全集·文学编》,这还不包括同年出版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以下简称《朱雀城》)和正在连载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已出版上、中两卷)。黄永玉已经96岁高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杂志连载了9年,至今仍在连载中,这一马拉松式的写作和连载,堪称当代文学界的一大奇观。
有些评论家意识到他的小说跟我们惯常接受的西方现代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如果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理解黄永玉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将有极大的难度②卓今:《黄永玉的文学》,《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有些习惯于阅读西方现代小说的读者,甚至会对他的长篇巨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感到无所适从。黄永玉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写作不能归入当代文学的常规评价体系,在《朱雀城》的序言中他称自己的写作是“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而实际上,他所作出的写作尝试,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来有自的,绝非凌空蹈虚。在一篇谈绘画的文章中,他说:“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画,却不明白他的主张何在。一个画画的人的主张是很重要的,没有主张,画什么画?”①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人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画画需要主张,文学创作自然也需要主张。那么,黄永玉的主张是什么呢?
他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序言中说:“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②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这里提到的故乡思维,不单指故乡带来的题材价值和自我认同,还可能是理解黄永玉文学写作的一把钥匙,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阐析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和传统特色提供帮助。须知当代中国文学,以先声夺人的故乡作为文学资源来改写文学格局的作家大有人在,如迟子建、刘亮程、李娟、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等等,都在写作中带有典型的故乡思维。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故乡思维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下,故乡思维会产生哪些不同的文学效应?在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中,这类故乡思维还会不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本文就以黄永玉为例,尝试从语言、文体、文学渊源、身份建构几个方面,来解读他所谓的“故乡思维”,以及这种思维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方言语境中的野趣和童真
黄永玉的文字,和黄永玉的画一样,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解放感和自由感,乍一看出乎意料,不符合常规套路,仔细品味,却又有熟悉和亲切的意味,不知不觉中我们消除了审美戒备。他的语言没有文艺腔,写起小说来没有小说腔。而且他的语言有较强的视觉性,有烟火气,虽也时不时引经据典,却似乎一点也不被经典束缚。
这种语言上的自由感,我认为首先来自它不同于普通话和书面语的“野趣”,天然携带陌生化效果,源头则是湘西方言。湘西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是北方语系,比正规官话多些幽默和狠劲,比现代普通话多了一层现实感,同时又比其它晦涩难懂的湖南方言更适合嵌入书面表达。在提到文学思维时,黄永玉首先提到的也正是语言,他说:“平日不欣赏发馊的‘传统成语’更讨厌邪恶的‘现代汉语’。它麻木观感、了无生趣。”③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5页。也就是说,他是有意识地从故乡语言和日常口语中寻找更具新鲜感和生趣的表达方式,来抵挡现代汉语带来的观感麻木。
黄永玉对湘西方言的使用,在小说《朱雀城》中达到了某种极致,能用方言的地方,绝不用现代汉语,能使用土语原话的地方,绝不用传统成语。比如小说写一个叫苏儒臣的染坊老板,想附庸风雅做文人,受到打击后想不开,黄永玉是这样写的:
苏大坨又添了个外号叫“苏蠢卵”。半个月苏大坨瘦了好几斤,路上遇到那些卵读书人,便铁青着脸,招呼都不打,也断了跟文人拉关系的念头,准备从政。其实,苏家染匠铺的布确实染得好,透蓝,匀称,犯不上去计较别的什么的。他想不开,就是想不开!④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5页。
“蠢卵”“卵读书人”这样的词汇,比普通话里的“蠢猪”“狗屁读书人”,明显更加有生趣,后面两个“想不开”,其劲道和幽默,直教人大呼意外。
最令人叫绝的,还是黄永玉笔下人物的语言。比如他写朱雀城外的饭店老板娘,不用一句外貌描写,却能通过人物语言将人物形象丰满地呈现出来:
“数目我看足够了,就不晓得你们手艺……”方若话刚出头,厨房里内老板出来了:“我们城外没有手艺的事!斋猪肉就是斋猪肉!”伸出两只手扳屈着指头算,“哪!辣子、花椒、大蒜、姜、橘子叶、红糖、绍酒、酱油、盐,殷勤点再放两块霉豆腐,几大勺油,一齐丢下去一炒一焖,天下都一样,跟你们城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灶好!火足,锅子大,翻炒起来痛快。”说完进厨房了。①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65页。
这里用了方言词汇如“内老板”“斋猪肉”“殷勤点”,契合了人物所处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方言节奏的运用,那种短促、野性和有力的节奏,是书面语和普通话所欠缺的,仅仅一个“哪!”,声音、动作和表情就都有了。实际上这段话里并没有全部使用方言,因为很多方言词汇和发音,在普通话里是没有的,只有通过方言的节奏来传达地域特色和人物性格。黄永玉持续在做一个语言试验,就是不断调和方言和书面语的比例,不影响大部分读者阅读的同时,想办法保留湘西语言的神韵。
除了来自方言的词汇和句式,还有一种语言也跟故乡息息相关,那就是童言。黄永玉在语言中刻意保留童真的味道,使之具备一种孩童般的无拘无束的视角,看待成人世界的一切,因之产生出其不意的反差。比如小说《朱雀城》中,写到朱雀城中的基督教堂,黄永玉这样写道:
陈家祠堂斜对门新开了一家“天主堂”,李承恩隔壁那家“福音堂”,都是信一种外国菩萨的。既然信一种菩萨,又各开各的店,让人搞不清楚。②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65页。
在散文名篇《这些忧郁的碎屑——忆沈从文表叔》一文中,有一段广为传播的文字,也是以童真的视角出彩:
打个比方说吧!党是位三十来岁的农村妇女,成熟,漂亮。大热天,扛着大包小包行李去赶火车——社会主义的火车。时间紧路远,天气热,加上包袱沉重,还带着三岁多的孩子。孩子就是我。我,跟在后面,拉了一大段距离,显得越发跟不上,居然这时候异想天开要吃“冰棍”。妈妈当然不理,只顾往前走,因为急着要赶时间。孩子却不懂事,远远跟在后面哼哼唧唧。做妈的烦了,放慢脚步,等走得近了,当面给了一巴掌。我怎么办?当然大哭。③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以孩童视角和语言写出来的自传体小说《朱雀城》,读起来就有方言和童言的双重陌生化效果,简简单单的事物,如中秋节、看电影、读古书,在这种语言的讲述下,都显得非常活泼和幽默。相比之下,正在连载的《八年》更接近成年人的视角,且主人公离开了朱雀城这一“母语”所在的地域,所以写起来更像记人记事的回忆录,多了些历史见证的价值,少了些《朱雀城》的小说意味和文学性。
黄永玉的文学语言,并非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陌生化”自觉,而是经过长年累月的实践而慢慢发展起来的。五十年代,黄永玉的散文和艺术评论也跟同时代的大多数写作者一样,与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话语拉不开距离。他评论电影《火凤凰》,使用的是这样的语言:“《火凤凰》是一部通过集体主义产生的好电影,它正式肯定了一个问题,‘离开人民,就没有艺术’。”①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杂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1、26页。评论波拉克的画作时,他写道:“由于这种艺术的出现,更有理由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了。”②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杂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1、26页。评论某画展时,通篇都是今天所谓的学者腔:“所谓‘颓废主义’,是十九世纪怀疑思想倾向下的表现病态偏颇的那种艺术。‘颓废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异状下的神经过敏要求新奇刺激的病态心理的基础上……”③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杂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21、26页。很难想象这会是黄永玉的文字。其实他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他也经过了痛苦的反思和磨砺,只不过,他的幸运之处在于艺术家的直觉最终将他带回了故乡,从故乡的语言中得到了一种新的表达,使他从一场语言的灾难中挣脱了出来。
黄永玉说过,他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最开始写于1945年,我们只能说,幸亏他没有写,因为这样一部大书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语言的成熟。1950年在《大公报》连载的长篇散文《火里凤凰》,可以算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个前身,里面出现了后来我们熟悉的湘西人事如王伯、古椿书屋等,但语言却脱不开“革命话语”,主题则是反映新中国气象之“新”,与旧社会传统之“恶”,无暇顾及语言的个性以及由此承载的更深的主题和更细微的人性。50年后的2001年,这些文字收入其文集时,黄永玉承认它很幼稚,是“左”的,满怀一派革命小将的乐观和天真,之所以收录进来,是想立此存照,留个见证。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黄永玉没有那12年的故乡记忆做思维的基底,他能否走出革命话语的统摄,能否拥有今天的语言和视野。这大概是故乡思维之于他的第一重意义。
三、民间视角与文体的“自由”
黄永玉的文字给人带来的自由感,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他的文体。西方的文体分类从一开始就对他缺少约束力。他的早期诗歌倒是“规矩”一点,直接师承自俄罗斯19世纪的诗歌,但他写起散文和小说来,文体就非常“野”,像笔记、话本和史传的杂糅,有民间趣味,跟沈从文在文体的跨界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黄永玉喜欢称自己的写作是“兴之所至”,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实际上可没有这么简单。进入21世纪之后,大陆很多优秀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倾向,都在文体上与西方现代小说刻意拉开距离,过来回头向中国传统的史志、笔记、话本回归。如阎连科的《炸裂志》使用了地方志的写法,韩少功的《日夜书》采用传统史书的列传体,金宇澄的《繁花》回归旧时方言说书人的民间传统。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无意中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但走得更远,也更自然。要做到这一点,“故乡思维”肯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种文体的自然和自由之感,并非如作者所言,建立在所谓的“兴之所至”上面,恰恰相反,它需要用心的经营。长篇小说最能见出作者谋篇布局的功力,我们来看看《朱雀城》的开篇。这部80万字的小说,一开场写的是爷爷回家之后的一次小宴和一次大宴,场景之大,人物之多,行文之开阔,有《红楼梦》一般的生气。那么多人物悉数登场,一丝不乱,中秋期间,写大人孩子们的生活日常,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最开始以两岁的狗狗做视角,随后又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局限视角之间不停切换,收放自如,整个湘西社会便如一幅完整的画卷,缓缓呈现。这个开篇是精心设计的,并非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送月饼,赏月唱歌,学校迎双十节国庆,看电影,得豫离乡远走,一个个场景如在眼前,同时又不着痕迹地埋下太婆离世的伏笔。而太婆的离世,则为第二部分狗狗去家婆家小住创造了条件,小说得以从空间上继续拓展,牵出得胜营的一大干人和事。等到第三部分狗狗回来,家已搬到文星街的古椿书屋,又是一番天地。作者有意要将朱雀城各个阶层的人写进去,构图的时候就是想着要画全景。这种场景构建的能力,当代大部分专业小说家可能都要表示惊叹。
那么,故乡思维和这种谋篇布局有什么关系?实则关系甚大。在凤凰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黄永玉感受到的社会文化、思维方式,确实跟往后的人生境遇截然有别,这区别首先就在于社会组织形态。黄永玉12岁离家之前的凤凰城,是一个前现代的熟人社会,如果要写一部展示古城群像的自传小说,黄永玉无须借助现代文学理论和叙事技巧,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红楼梦》《水浒传》和章回话本小说的结构和布局,这是一早就注定了的。这种选择是如此自然,呈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从容效果。
中国的散文本来就很难按照西方散文的标准去分类,我们今天泛滥成灾的文艺腔、翻译腔、学者腔,其中大概都有故乡思维缺失的缘故。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笔记小说以及二十四史的史传,在叙事上也和西方传统截然不同,通常都没有明确焦点,如同我们的中国画,是散点透视的。西方的长篇小说则讲究焦点透视,如油画和水彩。中国的话本小说,不分“讲述”和“呈现”,作者、叙事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很模糊,常常互相干涉。西方叙事文体则老老实实循着一根线索、按照特定视角、叙述一个故事。黄永玉顺着故乡思维和艺术家直觉来写作,从不考虑什么野不野、规范不规范的事,写出来的作品像西方小说才怪。就像《朱雀城》的主人公序子,听人说一种花叫野蔷薇时,心里直犯嘀咕:“这是卵话,太阳底下的花,哪里有野不野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的当代写作者可能太过在意文体的规范,反而框住了原生的想象力。
四、故乡自带的文学渊源
黄永玉和他的表叔沈从文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他不可避免要站在沈从文的肩膀上来写作,就像沈从文在写作时,总是忘不掉那个郁郁寡欢的屈原形象。湘西社会已然存在的文学传统,会在每一个严肃写作的湘西作家身上得到体现。当代湘西作家辈出,孙建忠、蔡测海、张心平等人在90年代营造过一波湘西文学的新热潮,而更年轻的湘西作家如田耳、于怀岸等,也正活跃在当代文坛上,展现出湘西文学的一些共同特质,这种传承应该也是黄永玉故乡思维隐含的另一层指涉,至少在黄永玉身上,这种传承是明显可见的。
我们都知道,在创作过程中,明确的隐含读者的存在,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黄永玉自己就说道:“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有沈从文、有萧乾在盯着我,我们仿佛要对对口径,我每写一章,就在想,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在的话,哪怕只有一个人在。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表叔如果看到了,他会在旁边写注,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①王悦阳:《黄永玉:流不尽的无愁河》,《新民周刊》2013年第43期。
在这种凝视之下,黄永玉的语言、文体、风格,不可避免地要与沈从文发生互动,关于沈从文和黄永玉之间的渊源,学界已经有过较多的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除了耳濡目染的文学熏染和精神传承之外,具体到写作的题材上,黄永玉也接过了沈从文的遗赠。黄永玉认为,沈从文将三个熟透了的好故事烂在心里,那就是他自己的家族史。沈从文的父亲、兄弟、妹妹,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平凡的故事,说出来都能震撼人心。
沈从文从不写自己的家族,却一再将黄永玉的家族写入小说。比如《一个传奇的本事》,写的是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已然成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读者怎么也忘不了那个求着沈从文替他写情书的表兄。文革期间,沈从文又动了写作的心思,听从黄永玉的建议,用小说来写“家史及地方志”,很快就写出了第一章,名叫《来的是谁》,但他仍然没有写自己的家史,而是写黄永玉的家族故事。即便如此,在那样一个年代,身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沈从文也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小说。沈从文半生习作,只为等待最后的成熟,但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写得最好的书是《边城》《湘行散记》《湘行书简》《从文自传》和《长河》,大都是来自他生命的直接体验,但他最好的素材还没有来得及写下哪怕一行。这对于沈从文和黄永玉,都是莫大的遗憾。
当黄永玉动笔写作时,当然会不自觉地试图填补这些遗憾。他在《那些忧郁的碎屑》中提到,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是《长河》,在《长河》中“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①孙冰编:《沈从文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页。。然而,《长河》是一本未完成的书,黄永玉为此深感惋惜,在他心目中,《长河》应该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书。“无愁河”的厚重,正是为了弥补“长河”的遗憾。在《朱雀城》中,他将自己的家族和沈从文的家族,以及城中那些似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各色人等,都写进了小说里。沈从文写得好的部分,黄永玉直接从中吸收现成的养分;沈从文没有来得及填补的缺憾,黄永玉予以浓墨重彩的书写。这是手把手地接力,是共同故乡带来的交接优势。
五、边缘人的身份建构
沈从文喜欢自称“乡下人”,学者们研究之后认为,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并不简单,其中包含了一种批判的视角,以及鲜明的边缘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②[日]金泉秀人:《“乡下人”究竟指什么?》,陈薇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这种立场决定了沈从文作品的思想基调。同样地,故乡也赋予了黄永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视角,在文字中,他以“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自居,反反复复地回顾自己在故乡度过的12年时光,并以此来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大时代的浪潮中没有迷失自己。
50年代从香港回国的黄永玉,经历过一场理想主义的幻灭,正是这次幻灭使他心中的湘西形象变得更明晰,也更有所指。他现在才真正发现了湘西真正迷人的地方所在,也发现了沈从文最可贵之处:一种带抒情味道的批判。比如,他频频提及“麻木”,前文讲语言问题时引述过,他讨厌的现代汉语,原因就在于它“麻木观感”,回顾文革的经历,他又提到“麻木了情感”:“一种荒谬而残酷的力量,令整个时代互相仇杀,颠倒伦理,以至于麻木了情感,忘记自己是人。”③黄永玉:《黄永玉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这是他在幻灭后对时代病症的诊断,为了疗救这种麻木,只有向故乡寻求启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用活生生的生命热情让人的感觉复活,他笔下的人物都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和浓厚的烟火味,让灵魂重返温暖的人性家园,让邪恶无处藏匿,他的文学主题某种意义上是反理性、反工具、反虚无、反异化的,在方法上打碎一切陈规,一切主义和一切叙事手法,他的文学让人重新记起被遗忘的存在,让人怀着乡愁寻找失去的精神家园。”④卓今:《黄永玉的文学》,《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
黄永玉笔下的湘西,是人情味浓厚的湘西,从最上层的“老王”,到最下层的乞丐和“朝人”(疯子),都有情有义。在这一点上,他和沈从文很相似。在他们笔下,连杀戮也很难激发人的愤恨,正义总是有人主持,不留遗恨和压迫。尽管真实的故乡不免也有残酷、血腥的一面,但他尽可能地使之变得柔和,使生和死变得更有人情味。如同沈从文笔下有两个湘西一样,黄永玉的笔下也有两个凤凰,一个来自历史的真实,其中饱含着五四运动以来所持续抨击的落后、愚昧和杀戮。在这个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和黄永玉都看到过杀人如麻的场面,见识过妇女儿童的悲惨命运,都在十一二岁的年纪离开了故土,然后才找到人生的出路;而在另一个湘西世界里,黄永玉和沈从文遵从的是情感的真实,营造出田园牧歌式的桃源景象,与“文明”的现代都市形成鲜明对比,是一种“礼失求诸野”的策略,是对现代文明的病症所做的批判,也是对历史进行的反思。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设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手太弱,或者没有对手,作品的力量就会缺失。《红楼梦》的对手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科举功名,男权文化和儒家正统;《水浒传》的对手是官方正史、文人话语和小市民秩序,为我们的文化平添一股草莽之气和狂野的活力;鲁迅反抗着一个时代的愚昧和堕落;沈从文一生都在跟方兴未艾的现代都市文明较劲。黄永玉也是有对手的,而且他有很明确的自觉。用学术的话来说,黄永玉的写作,是以一个湘西人的边缘视角,来对今天后工业时代人的疏离、异化和虚无做出反抗。
2012年初,《朱雀城》连载进入尾声,恰逢好友黄苗子谢世,黄永玉写了一篇怀念文章《难忘的清流绝响》,深为好友晚年未能写作回忆录而惋惜。他说:“不写‘回忆录’而东拉西扯一些不太精通的‘茶’、‘烟’、‘酒’的东西干吗?这类材料电脑一按,三岁小孩都查得到,何必要你费神?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善茶。可惜了……”①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人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他还说:“串在一起的大事,零零碎碎的小事,没有人有你的条件,有你的身份,有你的头脑,有你的记忆力和才情。这会是一部多么有用的书,多么惹人喜欢的书,多么厚厚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②黄永玉:《黄永玉全集·文学编·人物》,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这段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成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他自己写作的条件,他的身份,他的头脑,他的记忆和才情,都与故乡有关,是故乡的馈赠。一开始,黄永玉坚称他的写作跟画画一样,图好玩,自己写得开心就好。这种心态可能随着写作的深入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慢慢意识到了一种使命。像《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样一部100多万字的大书,从构思到写作,横跨半个多世纪,在黄永玉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中都投下了影子。没有强大的使命感,很难想象他能在这样的年纪完成如此壮举。他一定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步步确证和发现了故乡和自己,也由此看到了这种确证和发现对我们的时代具有怎样的意义。
六、结语
由此观之,故乡思维实则包含了一个作家的语言资源、文体意识、文学传承和身份建构,这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童年多样性、人格多样性和文学多样性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在我们的时代遭遇空前的危机。
对于无处还乡的当代都市人,从哪里寻得一种深层的精神依靠?黄永玉的故乡思维,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鲁迅的绍兴童年,卢梭的日内瓦情结,支撑了他们一生的独立品格,使他们能够在时代巨浪中不至于随波逐流,与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从而能够持续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和思想。
就像黄永玉说的,他在写小说时,经常写着写着就笑出声来。王国维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若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①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试问当今作家,有几个可以写到这种“真”和“深”,以至写到大哭或大笑?
学者张定浩在论及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时写道,倘若黄永玉的写作“真的值得我们珍重,绝非因为什么中国式书写或者某种类似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般的橱窗陈列,而恰恰因为它是极具现代性的写作,是一种就在当下生成的面向世界的有力存在,一种在隐秘中绵延传承的、爱和怜悯的小说学。”②张定浩:《爱和怜悯的小说学——以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为例》,《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确实如此,故乡思维滋养了黄永玉的写作,也滋养了他的人格。在黄永玉这里,写作和人格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对于喜欢读黄永玉文字的人来说,一定会对他文字中展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印象深刻、钦佩不已。在政治实践、伦理实践和艺术实践上,他都保持了高尚的情操和对自由的追求。他经历过那么动荡、复杂的时代变化,那么多思想和主义起起伏伏,作为一个从边城凤凰走出来的艺术家,读者会在他的文字中不自觉地追问,他是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那种浑然天成的童真、幽默和活泼?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地认识那段历史,发现当今社会习焉不察的残缺,重获那来自山野和民间的人性之善。这大概是黄永玉,也是沈从文,带给我们的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