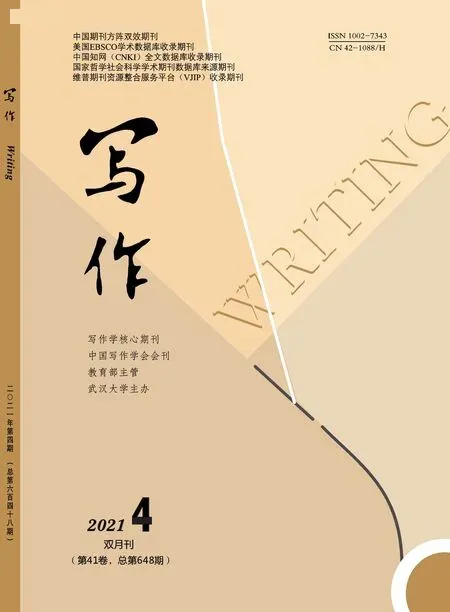情欲的现代言说
——施蛰存《石秀》的形式创新与“新路”开拓
严 靖
《石秀》发表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第2号,收入施蛰存第二个小说集《将军底头》,是他探索“创作的新蹊径”的代表作。
自1929年出版《上元灯》广受好评之后,已经写了六七年小说的施蛰存才对写作有进一步的信心。他立志道:“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①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79页。
所谓的“新的路径”是什么呢?“新”是相对于《江干集》《上元灯》两个集子而言的。这两个集子大都写江南市镇市民的生活及心理,对经验的倚赖较重。施蛰存试图寻求一种超越现实经验的写法。这时候席卷文坛的是普罗文艺,时代潮流冲击下的施蛰存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自觉失败,与主流格格不入,就不再继续。除了继续城镇男女故事的书写,他还将注意力转移至古事题材方面。第一篇是写圣僧的《鸠摩罗什》,第二篇是更为成功的写英雄好汉的《石秀》。施蛰存古代人物情欲世界的言说,显示了30年代海派现代性的先锋一面。
一、内心世界的深掘细写
《石秀》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后半回,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以及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拼命三火烧祝家店”前半回。原著相关语段约7000字,改写后的《石秀》成为一篇2万余字的小说。
施蛰存的改写首先体现在内容篇幅方面,他对原著做了外科手术般的处理。作为训诫意味甚浓的小说,《水浒传》有相当笔墨指向两个主题:一是强调色戒,二是丑化和尚。前者如四十四回对潘巧云出场的“有诗为证”、四十六回开头的“诗曰”;后者如四十五回开头的“偈曰”、裴如海出场的描写。“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和尚与偷情的相关性被一再强调,这一思想贯穿故事的始终,占据了相当篇幅。这种点评式的介入写法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在话本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
《石秀》则取消了这些俗套的笔法,改以更为简洁、冷静的第三者视角,而非全知全能的视角。小说没有直接叙述的部分包括:杨家做法事、报恩寺裴潘偷情、杨雄醉酒吐真言及潘巧云口诬石秀。省去不讲的部分则有石秀与潘公的误会等。这些处理对作者思想主旨的凸显大有裨益。《水浒传》原文的叙事重心是潘裴通奸、杨石智杀二事,《石秀》则以石秀为主角,叙述其对潘巧云的情欲心理。施蛰存对原著中与主旨无关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斫。
叙事手法方面,《水浒传》是顺叙,《石秀》则是倒叙加顺叙。这也对应着叙事为主和心理描写为主的两种不同的写法。为了彰显讲故事的技艺,传统话本小说极为重视情节,而对心理有所忽视,《水浒传》亦然。《石秀》则以填补空白的方式将小说的人物活动(包括心理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延展,使得小说的密度更大,人物性格更为饱满。
比如,《水浒传》对于石秀在杨雄家住下的头一宿,只用了寥寥数字:“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话休絮烦。”而新小说《石秀》恰恰是从这一习见的“话休絮烦”之处下笔,以将近4000字的笔墨,细细书写石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浮想联翩的思绪:
“却说石秀这一晚在杨雄家里歇宿了,兀自的翻来复去睡不着。”
“躺在床上留心看着这个好像很神秘的晃动着的火焰,石秀心里便不禁给勾引起一大片不尽的思潮了。”
“猛可地,石秀又想起了神行太保递给他的十两纹银。”
“可是,正如他的脾气的急躁一样,他的思想真也变换得忒快。好似学习了某种新的学问似的,石秀忽然又悟到了一个主意。”
“思绪暂时沉静了下去之后,渐渐地又集中到杨雄身上。”
不仅如此,作者让初入杨家的石秀的眼睛“看”起来,仔细巡视、端详他睡的床、潘家的摆设、女性的装扮等等。正是这些“看”,触及了他的性欲最敏感的部分。
再如,《石秀》创造性地设置了石秀三见潘巧云的情节,表现主人公曲折幽深的性心理活动。
第一次是杨雄带着拜见,让潘巧云认识结拜兄弟。石秀所见的潘巧云是美丽性感的,这一见构成石秀当晚浮想联翩的原因之一。这一安排拉开了小说表现的主题(情欲)的序幕,也为石秀的命运与性格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是翌日早晨,在杨雄不在家之际,寂寞无聊的石秀与潘巧云有一番对谈。后者制造暧昧契机,以言语挑逗石秀。石秀则欲拒还迎,感受着被挑逗的紧张刺激。不过,一方面为潘的美貌和言行“神魂震荡,目定口呆”,另一方面则因为眼前人是兄长妻而感到“一种沉重的失望”,构成石秀的矛盾心理。
第三次是几个月后的一个午后,石秀恍惚“走进了潘巧云正在那儿坐着叫迎儿捶腿的那间耳房了”。此时的石秀,已经知晓潘巧云勾栏出身这一经历,因而更新了对潘的认识和幻想:“这一次的情热,却比第一次看见了潘巧云而生的情热更猛烈了。石秀甚至下意识地有了‘虽然杨雄是自己的义兄,究竟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便爱上了他的浑家又有甚打紧’的思想。”于是,这一次的石秀不仅主动,而且自信,志在必得。不过,欲望炽热的石秀,一见到潘巧云,又变得紧张无措,“嘴里含满了一口粘腻的唾沫。这唾沫,石秀是曾几次想咽下去,而终于咽不下;几次想吐出来,而终于吐不出来的。”无情而必然的结果是,“猛一转眼,恰巧在那美妇人的背后,浮雕着回纹的茶几上,冷静地安置着那一条杨雄的皂色头巾,讽刺地给石秀瞥见了。”杨雄以一种特殊的在场方式击碎了石秀的幻想,也击碎了他的实践的机会,“爱欲的苦闷和烈焰所织成了的魔网,都全部毁灭了。”
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情节,也是《水浒传》所没有的,即石秀的勾栏体验。小说一再呈现石秀欲望的炽热与行动的无能的对峙。除了内在的道德束缚,外在的经验的缺乏也是另一重要原因。怀着这些复杂的心情,石秀走进了勾栏。他下意识地对一个长得像潘巧云的娼女产生好感。勾栏一夜的情节处于小说结构的重要关节点。它凝聚了石秀所有的性心理,并且是以参差的、对照的、多镜像的手法呈现出来的。石秀在娼女身上感受20岁的潘巧云的样子,以这种方式重现高冷的性幻想对象的过去,从而将他与潘巧云的关系扯平,克服自己的实际行动的无能。不仅如此,石秀眼中的娼女还综合了他一生所遇见过的三个女人的镜像:小巷少女、娼女、潘巧云,分别代表了三类女子:纯洁的少女、年少的妓女、少妇。在恍惚中,娼女的脚给予石秀的强烈的性暗示,是他性心理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勾栏体验既强化了石秀对女人的认识,也使其性幻想与杀戮心理连结起来。妓女不小心被水果刀割破食指而流血的环节,构成性幻想世界中的重要隐喻。这一隐喻在其后来一系列的杀人中都有细致的展示:
诧异着这样的女人的血之奇丽,又目击着她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潮着了。这是从来所没有看见过的艳迹啊!
勾栏一夜之后,英雄的石秀和凡人的石秀合为一体了。确切地说,是英雄的一面压抑了凡人的一面了。从街头巷尾的打抱不平到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石秀的英雄越做越大,但凡人的一面即将走到终点。“在任何男子身上,怕决不会有这样美丽的血,及其所构成的使人怜爱和满足的表象罢”,翠屏山之后的血再也没有这么丰富的意义了。
施蛰存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掘细写可谓纤毫毕现。为了达到最佳艺术效果,小说结构的谨严与刻画的细腻相得益彰,情节设置的取舍和创造显示了与《水浒传》原文的根本区别。简单平淡的叙事的同时,加以繁复的心理填充,生出人物内心世界和人与人关系的惊涛骇浪。
《水浒传》中的人物,大都属于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所说的“扁平人物”,性格较为单一,石秀亦不例外;而《石秀》中的石秀,则非如此。他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直接粗率,也有浮想翩翩犹豫不决的缜密多思;既有胆怯谨慎的一面,也有色胆包天的一面;既爱潘巧云,亦恨潘巧云。他的性格和气质是不断被唤醒的。他是施蛰存借由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蒙太奇、梦境解析等手法,加之现代人文观念塑造出来的圆形人物。
二、Freudism的手法与性心理书写
差不多和《石秀》同时,施蛰存还发表了普罗小说《阿秀》,和以现代都市的颓废萎靡为书写对象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左翼批评家楼适夷著文称道了施蛰存自认为失败的《阿秀》,却对另两篇给予严厉批评:“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①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1931年第33期。
面对这一批评,一向在政治上谨小慎微的施蛰存,两年后才写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进行低调的反对:
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原注:弗罗乙特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心理小说而已。②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80-81页。
约半个世纪后,他又旧事重提:“楼适夷同志熟悉日本现代文学,他大约当时也多看这一派的作品,因此他把我列入新感觉派。我不反对,不否认,但觉得我和日本的新感觉派还有些不同。因为我写的还是以封建社会小市民为主,而日本的新感觉派所写的是资本主义大都市里的男男女女。”③《施蛰存致吴福辉信》(1982年6月13日),引自吴福辉:《施蛰存对“新感觉派”身份的有限认同》,《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卷第3期。考虑到1930年代上海文坛左翼的强势,施蛰存的表态和自辩,有自我保护的意思。不过,他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关系上,依然是侧重后者的:
有人在我这几篇小说中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连我自己也要怀疑起它们的方法和目的来了。因此,我以为索性趁此机会说明一下,好让人家不再在这些没干系的小说上架起扩大镜来。④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第2页。
无论题材如何变化,他一以贯之的依然是心理分析手法。而其中最有特色、占据最核心地位的则是性心理。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⑤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第2页。这是与各种政治方面的主义无关的。
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倾心于普罗文艺理论,施蛰存却对精神分析学说情有独钟。在1930年之前,他就广泛阅读了弗洛伊德,对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尤其是其中的人格学说和梦的解析极为熟稔。他还翻译了以心理分析闻名的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又译“施尼茨勒”)的《妇女三部曲》《生之恋》《薄命的戴丽莎》等作品,详细揣摩了其艺术技法。对他们的借鉴、消化和吸收,构成施蛰存所谓“新的路径”的理论自信。
“二重人格”说是不少学者探讨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时的共同聚焦。苏雪林从正面角度认为:施蛰存小说充满“二重人格的冲突,普通心理学上自我分裂,灵肉冲突,和一切心理上的纷乱矛盾。”⑥苏雪林:《心理小说家施蛰存》,《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1页。严家炎则以为“二重人格”的理论是“一种荒唐的见解,也是弗洛伊德学说深深地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地方”,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石秀》,“将古人现代化、弗洛伊德化……石秀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⑦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无论正面肯定还是负面评价,都基于一种对立统一思维,包括人性与兽性、文明与野蛮、道德与欲望等。这一思维固然深化了对人物性格的认识,但未能从更高层面认识施蛰存心理小说的现代意义。
必须注意到施蛰存这一段对施尼茨勒的概述:
施尼茨勒的作品可以说全都是以性爱为主题的。……但是他描写性爱并不是描写这一事实或说行为,他大概都是注意在性心理分析。……或者有人会说他是有意地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的,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之被证实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特辟一个新的蹊径,以致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了劳伦斯和乔也斯这样的心理分析的大家,确是应该归功于他的。①施蛰存:《〈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施蛰存全集》第4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1325-1326页。
施蛰存正是怀着这一认识来写《石秀》的——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之被证实在文艺上,使欧洲现代文艺因此而特辟一个新的蹊径”,他也在30年代的中国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石秀》中,Freudism首先清晰地体现为弗氏的人格三结构说(“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存在于潜意识中,主要由人的本能欲望构成,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追求发泄与满足;“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根据现实环境理智和审慎地言行;“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受社会因素主导,能强有力地压抑“本我”的欲望和超越现实的困难。人格结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施蛰存笔下的石秀的三重人格冲突相当显著。童男子石秀的本我苦闷最为强大,即性欲之被唤起却无法得到满足。自我层面的石秀,又是一个底层出身的柴夫和屠夫,其生存境遇和社会阶层处处影响言语和行为,也导致其本我的性欲表达的困难。然而,石秀身上最有力量的却是超我部分。小说中,出现了3次“武士”,9次“英雄”,这是对石秀身份和气质的显著的说明。因此,贯穿小说的三重人格的冲突,最凸显的线索是超我的道德力量与本我的性欲热情的交织和斗争,是他对潘巧云的情欲与“凡是义兄的东西,做兄弟的是不能有据为己有的希望的”这种道义思想的纠结。这种纠结也是一种平衡,它维持了一种道德与欲望的均势。“嫉妒藏着正义的面具在石秀的失望了的热情的心中起着作用”的结果,是他用第一次进勾栏宿妓来转移受压的情欲,完成其性经验的补足和“本我”的部分满足。
打破这一平衡的,是他偶然撞见潘巧云与裴如海私通一事。(这一部分的改写再次凸显施蛰存“现代”小说家的意识和素质——《水浒传》用了1万余字,施蛰存仅以四五百字叙述这一桥段,这一处理大大推进了叙事的速度。)既然贯穿小说的是石秀的情欲挣扎,那么只有他亲眼所见的潘巧云偷情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其超我的道德力量,刺激其采取行动。一方面,因为潘巧云的私通,杨雄对潘巧云便不再是占有的丈夫关系,石秀嫉妒心不再,和杨雄平起平坐了;另一方面,潘巧云和裴如海,一个勾栏出身的淫妇,一个和尚,同属被自己所鄙视的阶层,石秀对潘的性欲就一定程度转移了。这一转移的部分,化为了杀欲。
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不是生殖意义上的性,而是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作为一种本能,是人所有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如果一个人的性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力比多的对象贯彻就会产生偏差,从而催生变态的爱恋。当力比多受阻,主体的理性能力又有限的话,欲望就常常以其他方式宣泄出来。勾栏少女的食指流血,激起石秀的力比多心理高潮——这是石秀的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施蛰存对这一细节用笔甚详:
这是从来所没有看见过的艳迹啊!在任何男子身上,怕决不会有这样美丽的血,及其所构成的使人怜爱和满足的表象罢。石秀——这热情过度地沸腾着的青年武士,猛然地将她的正在拂拭着创口的右手指挪开了,让一缕血的红丝,继续地从这小小的创口里吐出来。
这一段上承石秀欲望由压抑到激发,又下启其后的杀戮行为的自然性。性欲得到转移,而杀欲即将拉开序幕。不过,杀欲亦可视作性欲的某种升华。以打杀解决问题是更本质的力比多冲突的表现。杀人后的石秀,闻着清晨“寒风中吹入鼻子的血腥气”,看着手中握着的“青光射眼的尖刀”:
有了“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这样的感觉。……因为即使到了现在,石秀终于默认着自己是爱恋着这个美艳的女人潘巧云的。不过以前是抱着“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的思想,而现在的石秀却猛烈地升起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这种奇妙的思想了。这就是因为石秀觉得最愉快的是杀人,所以睡一个女人,在石秀是以为决不及杀一个女人那样的愉快了。
欲望的转移并不等于欲望的堙没。潜藏于石秀内心的对潘巧云的爱恋,只是以别一方式呈现罢了。
杀戮游戏的高潮发生于翠屏山。这一部分又几乎是施蛰存的重写。增添的400余字,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一是石秀之“思”,即他的心理活动。如“石秀故意这样说”“石秀正盼候着这样的吩咐”“不禁又像杀却了头陀和尚之后那样的烦躁和疯狂起来”“觉得反而异常的安逸、和平”。这部分显示石秀心思之缜密,远胜于刽子手杨雄;二是石秀之“行”,即他的行为活动。如“上前一步,先把潘巧云发髻上的簪儿钗儿卸了下来,再把里里外外的衣裳全给剥了下来。但并不是用着什么狂暴的手势,在石秀这是取着与那一夜在勾栏里临睡的时候给那个娼女解衣裳时一样的手势。石秀屡次故意地碰着了潘巧云的肌肤”,表现石秀享受杀人的乐趣和过程;三是石秀之“视”,即他眼睛所审视、品鉴的迎儿、潘巧云的身体,以及潘巧云临死前求饶的情景。经此种种,欲望宣泄得到的快感超过了得不到的挣扎。
最后,《石秀》中多次出现“昏昏然”“半梦半醒”等提示读者的关键词。这些词揭露了石秀所处的状态是介乎现实与梦境之间的。无论是对潘巧云的性幻想,还是对勾栏歌妓的观看,以及杀戮头陀和尚,都发生于他心思恍惚之际。这一点可以部分说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学说对施蛰存小说情境营造的影响。
三、道德、欲望与江湖
砍柴为生的石秀,本处于社会底层。进入杨家之后,虽然是杨雄的义弟,通过参与肉铺经营也有些许积蓄,但究竟属于蓟州城的中下层市民。但在故事的发展中,石秀是正面人物乃至所有人物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除了武艺高强、胆大心细等能力素质因素,还有什么是石秀更坚固有利的心理与思想武器呢?这就是伦理道德观念。
石秀的伦理观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家庭出身的“清白”。虽是牛羊贩子(商人)出身,但石秀十分珍视自己出身的“本分”。所以,戴宗试图招揽他梁山入伙时,他是婉拒的。当晚躺在杨家回忆、思考此事时,虽然有一点动心(“这个年轻的武士石秀不由的幻想着那些在梁山水泊里等待着他的一切名誉、富有和英雄的事业。”),但很快:
啐!那戴宗杨林这两个东西,简直地说得天花乱坠,想骗我石秀入伙,帮同他们去干打家劫舍的不义的勾当。须知我石秀虽则贫贱,也有着清清白白的祖宗家世,难道一时竟熬不住这一点点的清苦,自愿上山入伙,给祖宗丢脸不成?
其次是两性关系上的观念,包括“妇道”“贞操”“朋友妻不可欺”等。这一观念直接指挥着他的行动,包括面对潘巧云的性欲的控制,以及对潘裴偷情的惩罚等。
出身观念隐在地影响人物命运的发展。《石秀》的结尾与《水浒传》一样,都是石秀鼓动、引导杨雄共上梁山。这与小说开头部分形成一种辩证的对比。戴宗劝导石秀上山时,石秀的弱者的敏感是强烈的——戴宗赠送花银,在戴宗是“英雄惜英雄”之举,但在石秀视为一种施舍。进入杨家、成为潘公的合伙人,石秀则心安理得,因为自觉有恩于杨雄。而为杨雄锄奸,在本我欲望方面得到宣泄的同时,自我方面也最大程度地、全面地展现了石秀的能力和气概。惩杀奸人,让他名望迅速增长,成为好汉石秀上梁山的投名状。
相较而言,杨雄是粗心、少主见的人。杨石关系中,石秀反客为主。重大的决断,都是石秀在决定或推动。他提醒杨雄切勿酒后失言,还出了将潘巧云骗至翠屏山对质的主意。可以说,小说主要是通过石秀的“思”“行”“视”来完成的。杨雄与石秀关系,起始是杨雄为公家人,石秀是无业者,终末是二者地位变为平等,都成为无家的江湖人。
《水浒传》中,假如说石秀是急公好义的英雄,那么其“公”和“义”体现在何处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诚然,石秀的行为意在维护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但这终究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一行为并不具有公共正义意义,具有的是江湖义气意义。石秀杨雄的杀戮行为与“起义”“替天行道”的私、公区别还是较为明显的。
无论是情欲、锄奸还是最后投奔梁山,其行为的根本属性是个人的。这正是施蛰存创作《石秀》及其他几部以古事为题材小说的出发点。他聚焦和深挖的是人物身上的个人性。他们的道德,也首先表现为一种私德。人性首先是潜藏于每个个体的,而非在社会中集体呈现的。兄弟情义、江湖义气、礼教规范这三重力量形塑了石秀,与它们相抗拒的欲望并不落下风。这构成了一个完整丰满的石秀。
这是一个不同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心灵世界。鲁迅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①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这一“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是符合《石秀》的创作原则的。
四、石秀形象重塑:拼命三郎、天慧星、童男子
《石秀》中,出现2次“少年”、2次“青年”、3次“武士”、9次“英雄”(其中直接描述石秀的2次、描述杨雄的4次)。庶几可以从这些身份名词看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小说中石秀的“英雄好汉”身份,是让位于“青年”(或“少年”)和“武士”的。“青年”“少年”意味着血气方刚,情欲蓬勃;“武士”的行动特征则是快意恩仇、有仇必报。无论作为何者,都具非理性特征。二者的结合体,构成这种非理性的人物类型的典型。
《水浒传》中的英雄,大都是压抑或扼杀情欲的“武士”。情欲作为被压抑和扼杀的对象,在书中的形象是负面的,这一点在武松、宋江、李逵、鲁智深身上都有显现。施蛰存小说则加入了“情”这一维度,从而拓展了人性的宽度和深度。小说巧妙地让28岁的石秀和26岁的潘巧云年轻化(身体的和心理的),也通过各种直接说明或间接暗示呈现石秀“未曾触碰过女人”这一事实——有意思的是,《水浒传》中的众好汉,有着和石秀一样缺乏性经验的人生经历的占据多数。
“拼命三郎”,大约是水浒好汉绰号中流传得最广的之一了。《水浒传》用浓墨重彩介绍了石秀的出场和绰号由来:
……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有诗为证:
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
那堪石秀真豪杰,慷慨相投入伙中。
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拼命三郎……”
虽说石秀号称“拼命三郎”,但故事里丢掉性命的不是石秀,而是头陀、裴如海、潘巧云和迎儿四人,即通奸者及其助手。而且,其中智力的运用是远胜于身体性命的豁出的(排座次时,石秀星号“天慧星”。)。所以有学者曾提出异议,指出“拼命三郎”一词在《诚斋乐府》和《宣和遗事》等书中都写作“拼命二郎”。这一结构是与“短命二郎”(阮小五)近似的。“短命二郎”不是自己命短,而是像死神二郎神一样让敌人短命。“拼命”之“拼”有捐弃、豁出去之意,也可以解释为是让别人短命、断命。
《石秀》的主角没变,但故事的主题已经转换为情欲。石秀对潘巧云的情欲,说是施蛰存创造出来的并不为过。由于道德(顾及兄弟情分)、礼法(潘为有夫之妇)、性格弱点(出身卑微、不善言辞)和情感弱点(缺乏接触异性经验),石秀的情欲迟迟难以化为行动。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的想象性心理就最大程度地生长着、膨胀着。施蛰存的创造合乎现实人情。
这一情欲的源头与作者一再强调的“少年”或“青年”石秀的身份密切相关。28岁之前的石秀应该是有自然性欲的(数次回忆他在小巷遇见的丁香姑娘),但由于生计所迫,这种性欲缺乏条件以释放。街头与杨雄的相遇,改变了石秀,这才有小说开头石秀对人生无常之感浮想翩翩。进入杨雄家生活之后,街头的石秀开始家庭生活。安稳了,有固定收入了,遇见潘巧云,近距离接触女性(潘巧云、迎儿和勾栏妓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故事的最后,则是不再是童男子的石秀走出家庭,走向江湖。
五、新文学: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成熟
欲望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施蛰存运用精神分析手法,重写了国人熟知的水浒故事,以大量的心理描写表现两性关系中的“力比多”现象,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范畴,营造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施蛰存的写作意识和实践对五四文学精神既有继承,又有推进和深化。
五四知识分子对《水浒传》评价颇低。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评论“强盗书”《水浒》:“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鲁迅在研讨明代拟宋市人小说时,也认为价值不高:“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五四”形成了现代文学重人生、重现实的传统。但人道主义之“人”,起初是偏重于个人的,因而与个人主义契合,产生巨大的能量和影响。“五卅”和大革命之后,个人主义让位于集体主义,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转移至劳苦大众。社会现实成为新的书写对象和主题。
基于这一语境,施蛰存在两个方面贡献巨大:一是他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探寻,从小说内倾化维度看,开创了中国现代派的先河;二是他对小说技法的精益求精,在主题先行、轻视技巧的30年代上海文坛尤为难能可贵。
在30年代,书写社会(外部世界)的左翼文学,与书写人心(内部世界)的“新感觉派”或曰“心理分析派”,构成两支相颉颃又相促进的势力。无论是外向还是内倾,都可视作现代文学分别从宽度广度和深度密度推进到新的阶段。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到了30年代,一方面是“个人”与他人(社会)联结而产生左翼文学,另一方面是人对自我世界的深入观照而产生“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两股力量一起构成了30年代文学的独特风景,标示了现代文学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