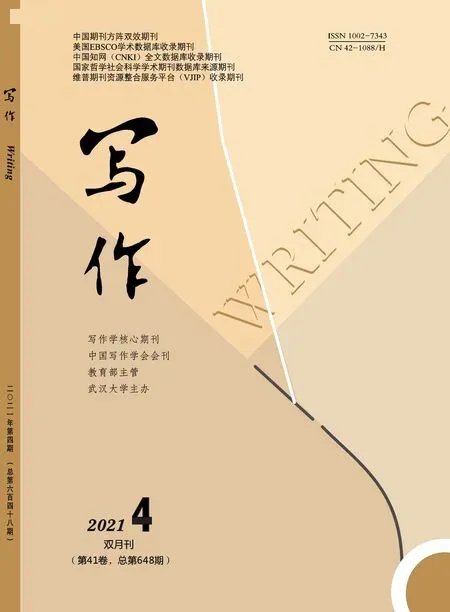当下英国高校的诗歌写作、教学与翻译
——与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拉什沃思的对谈
伯竑桥 [英]拉什沃思
一、边界:文学教学的限度
伯竑桥:詹妮弗·拉什沃思博士,您好!很荣幸有机会以这样正式的形式对您访谈。这是您第一次接受来自中文学术界的访谈吧,能否向《写作》的读者介绍一下您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后文同)的个人情况和学术研究方向呢?
拉什沃思:竑桥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接受访谈。我曾代表UCL出席过中—英人文学科联盟的年会,但这的确是初次一对一地与中文世界的读者进行文字交流。2017年以来,我一直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目前是UCL法语及比较文学系副教授,2019年开始担任比较文学学士(BA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项目系主任。
我所教授的,涵盖一系列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在比较文学硕士培养方案里,我主教诗歌、散文、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学批评。每年我都会指导一些特定方向的硕士生,比如,今年我有个学生,他的课题是伍尔夫①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20世纪伟大的英语小说家之一,女性主义先驱,代表作《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泰戈尔诗歌的;另一个硕士生的方向则是威廉·华兹华斯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和普鲁斯特③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20世纪伟大的法语小说家之一,意识流先驱,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对比研究。我的三位博士生,其中一位的选题,是将塞西尔·索瓦日(Cécile Sauvage)的诗歌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坦白讲,我个人挺喜欢UCL比较文学系那种把散文和诗歌两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方式。
在来到伦敦大学学院之前,我在牛津大学待了12年,先后读本科、研究生、博士,接着留校任教。现下,我个人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哀歌、中世纪主义和音乐,手头也正在写两本专著,一本关于普鲁斯特,一本关于罗兰·巴特①罗兰·巴特(Rolland Barthes),二战后重要的法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对后现代诸多思潮如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产生过重要影响。。还有两本与人合编的书,一本写文学史中的“悼亡”,一本写其中的“脆弱”。
伯竑桥:我注意到您在UCL除了负责教授诗歌写作之外,也从事诗歌翻译研究,这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在这个充满各类偏见和言语攻击的“后新冠肺炎时代”,翻译诗歌是一项跨越语言障碍、跨越文化边界的行动。您怎么看待自己目前在英国大学体系里从事的与文学写作、翻译有关的工作?
拉什沃思:我的第二本书通过考察伟大诗歌的“翻译”和“重写”(Re-writing)行为,来言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②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其创立的彼特拉克式十四行体与莎士比亚的商籁十四行体在西方诗歌传统中双峰并峙。在19世纪法国文化中的再现。关于诗歌翻译,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被翻译的内容——彼特拉克写了很多作品,哪些作品特别受欢迎?在这些作品中,有哪些诗歌在其他语言的语境中被翻译得特别频繁?若要简单地说,我认为对诗歌写作现象的研究,恰可以揭示写作行为中某些具体比喻和抽象观念间的亲缘关系;而在更复杂的层面上,它暗示了“什么不能译”的问题,以及究竟是什么在诗歌翻译中丢失了。
在伦敦大学学院,作为负责本科生培养的执行系主任,我得在不同的学术方向用译本进行教学,这就意味着课程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英文译本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当和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更偏好小说,而不是诗歌,他们对翻译的依赖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小说比诗歌更容易翻译(这挺可疑)。
理想地说,因为教师们认为掌握语言在比较文学领域是必须技能,所以学生们只有学一门新的语言才能拿到比较文学的学位。但我们也深知学生不可能掌握每一种语言,这么一来,译本反倒成了他们能否拿到学位的关键。
英国脱欧确实让人遗憾,作为学者,我希望它能趁机让人们更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目前,在英国的一些大学,各类语言文学系面临关闭的窘境。有些人认为,语言仅仅是学习一门语言,大可通过培训班,甚至一个个手机APP来达成目的。这一点,UCL文学系不敢苟同。相反,我们认为语言与历史、政治、文学、翻译和其他领域,都有着内生的隐秘联系,因此我们想努力改变目前英国国内关于“语言”甚嚣尘上的流行化叙事,也想努力让社会生活里其他机构的“语言供应”得到保护和珍视而不至于被漠视,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伯竑桥: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诗歌就是翻译中会丢失的那种东西。现下,有些人仍然认为,诗歌是不能通过人为方式教授的,除非一个人生来就有这样的诗才。那么您认为学生可以从您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诗歌课上学到什么?您能分享一下您在教学中最关心的事情吗?
拉什沃思:我教过不少和诗有关的课,在这儿我用比较文学本科生二年级必修课《从模仿、创造到作者性》举例。第一个作业,是写一首十四行诗和诗论。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不得不去写诗。
他们经常被这种作业吓到,后来却往往惊讶地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此类挑战。部分原因是,当他们在课上学习十四行诗的时候,只有自己动手去写一首,才是最好地了解十四行诗的方式。他们还发现,诗歌和所有文学一样,是阅读和写作、研究和灵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承认,我有时候不爱给这类作业打分,因为以数字来评判诗挺奇怪。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探索自己特有的诗歌禀赋的好机会;而对其他学生来说,至少,让他们意识到写诗比看起来难些。
我的很多教学工作是为了鼓励大学生更无拘束地用和任何传统文章都截然不同的全新方式去写作。就大学这一地方而言,我不觉得只有诗歌天才才能去教诗歌课,倒是认为教诗歌需要有敏锐的视听和对隐喻的热爱,以及向学生分享传递以上诸种妙处的能力。
二、当下:英国大学的诗歌景观
伯竑桥:我知道您正在UCL的硕士项目里开设“散文诗”(Prose Poetry)选修课。在这门课上,您总是提问“什么是诗”,这很有意思,因为它默认散文诗的定义取决于诗的定义。这似乎是要通过提出一组核心悖论来不断刺激学生们在这门课上的自我思考。由此我想知道,您在诗歌课堂里的核心教学理念是什么?
拉什沃思:我很享受教学生以“散文诗”,因着它迷人的“不确定性”。它是散文还是一种韵律?它属于叙事还是抒情?散文诗让我们在人文学科里设定一系列边界,随后又让我们意识到这类边界有多不稳定。由“散文诗的定义”始,学生们进而涉及“诗的定义”“文学的定义”,以研究生的程度而言,我只会向他们发问而不作预定的答案。没错,我知道这会让人有点儿沮丧、困惑,但我想让学生们像白纸一样重新审视每一个来自他人的回答。德里达说,“散文诗”是“蜷曲在路中央某只皮球里的一只小刺猬”,因此我更愿认为,隐喻有教育层面的意义——比起直来直去,我们能从隐喻里淘洗出更多真知。有些问题本就无法回答,对写作教学来说却富有启发。
伯竑桥:在20世纪的英语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乃至伟大诗人都有良好的学院教育背景,比如W.H.奥登①奥登(W.H.Auden),艾略特之后的20世纪杰出英语诗人之一,其诙谐、深沉、交杂的风格影响了包括汉语新诗在内的世界诗歌。之于牛津,T.S.艾略特之于哈佛,有些诗人甚至把在大学教书作为毕生职业,就像去年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诗人路易斯·格丽克。那么您认为在诗人和他们身后的学院之间是否有精神上隐秘的渊源?在西方,这条毕业后仍然“在学院写诗”的人生道路是否已经是个成熟稳定的传统了?您认为它对年轻诗人去平衡世俗世界和语言世界有什么影响?
拉什沃思:从许多方面来看,“学院诗人”(Poet-academic)的概念都已是昨日黄花。的确,为数不少的诗人都兼有学术身份,可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受教育的权力被局限在特定人群内部。有一种观点我很喜欢——诗的创造力和学术的判断力是可以相兼容的,写诗和批诗的人常是同一类人。然而,这一模式也正在急遽改变,现下诗人们更容易在推特或其他社交媒体上被阅读、被发现,而不仅在纯学术语境里。我们得把目光从学术范畴往外眺望,去听到新的不同的声音。如果你想要点儿和上述说法不同的“传统看法”,那么我会说,自己近来最欣赏的诗集是《与树同思》(Thinking withTree,2021年由Carcanet公司出版),作者贾森·艾略·派桑(Jason Allen-Paisant)也是英国利兹大学讲授加勒比地区诗歌以及反殖民主义思潮的一位高校教师。
伯竑桥:我想到一个现象:现代汉语诗歌曾经和英语诗歌有一次奇妙的交流,那是20世纪40年代,英国重要诗人、学者威廉·燕卜逊在抗战期间去到中国的西南联大任教,选修他诗歌写作课程的学生里,诞生了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穆旦、郑敏。像您这样的大学诗歌课教师,既是学者也是教育者,通常在一个年轻诗人的生涯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拉什沃思:我的确有不少学生后来公开发表诗歌,出版诗集,走上了这条道路,我感觉最大的扶持其实是不断提醒他们和更多写作者团结在一起,寻找同伴,融入作家共同体当中,向有经验的大作家请教。在学院,年轻写作者的收获主要来自课外,这收获源于年轻同伴间的交游和相互照亮。
在UCL这样的大学,我们当然是想要学生们在传统意义的学术上极尽所能,但同时也想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支持他们去探索一切天赋与兴趣所在的领域。所以,我帮助年轻学生诗人的方式常常是,读他们的作品,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的作家,为他们提供自由摸索的空间。
伯竑桥:我对英语世界的大学比如UCL中的校园诗人们的状态很好奇,作为文学现场的参与者,您可以谈谈他们在校期间的写作活动往往有什么特点吗?
拉什沃思:仅就UCL校内而言,我尤感惊讶的是,这里的校园诗人大都是多语言使用者(Multi⁃lingual),这意味着他们从宽泛而不同的文化里肆意汲取养分。抵达伦敦求学时,他们带着各自的语言、故事、壮志,而伦敦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空间,一个曾孕育了伟大作家和文学文本的地方,让志趣相投却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的彼此去碰撞。UCL比较文学系的本科生自办了一本杂志,叫Subtext;而校内也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者社群,对那些想让自身作品被更多人读到的年轻人来说,加入其中是颇为理想的第一步。
伯竑桥:对那些不想或无法成为所谓“职业诗人”的学生来说,在大学诗歌课的经历有何种意义?另一方面,就您观察到的而言,对另一些想要在诗歌道路上走得更远的学生来说,他们在毕业后会面对着什么?
拉什沃思:“职业”何意?我记得曾参加过苏格兰诗人唐·帕特森(Don Paterson)①唐·帕特森(Don Paterson),当代英国著名诗人,生于苏格兰,曾两度获得T.S.艾略特奖,现任教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代表诗集《最后之言:新世纪的新诗歌》。的一场朗诵会,他反复说,诗真的养活不了自己。在这个层面上,鲜有诗人是“职业的”(Professional)。相反,他们是“业余”(Amateur)的,因为“业余状态”意味着他们从心底热爱诗,而不是因为外力才去做。
多数年轻人告别校园、走入社会后,是以助理编辑的工作起步的,阅读并点校其他人的作品对他们的写作有好处,也能养活自己。努力成为优秀诗人,这挺好,但这种“成熟”也可能妨害语言新鲜的表达。我欣赏一代又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敢于站起来追寻新的诗歌语言,从既定标准来说,这“不成熟”,却相当刺激。对于想走这条道路的年轻写作者,我建议要去有意让自己被写作同行、有素养的读者、编辑、评论家包围,以此创造良性反馈,来保护自己的才华;大可留意诗歌比赛和奖项,但在走入公众视野之前,你得做好漫长而艰辛的准备。
伯竑桥:我知道UCL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府,国际学生占比高达40%以上(2018年数据)。文学史上,许多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著名作家曾于此求学或工作,比如日本的夏目漱石,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老舍。您认为和更加英式的学府,例如牛津、剑桥、杜伦、圣安相比,UCL的这种多元文化氛围,对其文学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
拉什沃思:就我本人在牛津受教育、最终在UCL任教的经历来看,这里的人文学科有比牛津更好的包容性、灵活性、可能性。譬如说,很长一段时间里,牛津都没有“比较文学”这个学科,因为相对英语文学、历史学这样的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它在牛津被认为“新得太越界了”。
在UCL,教师们会敏锐地根据世界学术思潮对课程做出即时调整。牛津开设的课程则多以具体作家或者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为核心;UCL的文学课则多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本身的目的,就包括超越所谓的经典作家(乔叟、莎士比亚等)和西方正统文学谱系(哈罗德·布鲁姆语),从而去拥抱这固定传统外的文化多元样态和新思潮,例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基因批评①文学基因批评(Genetic Criticism),战后兴起于法国的文学研究范式,有译为“文本发生学”,另有译为“基因批评”,命名较有争议。、身体政治等等。
三、未来:以诗实现沟通是可能的吗?
伯竑桥:现在让我们回到您的另一个学术领域:诗歌翻译。您有许多论著是关于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诗歌的,您觉得这些朝向母语以外的研究,对自己思考和教学的作用是什么?有趣的是,这篇访谈的主要读者是像我这样的中文母语者,您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母语外的域外之音,这就形成了一种互文。
拉什沃思:全世界的诗歌读者被诗联结起来,这事情本身便会令人振奋。我喜欢和UCL新近入学的国际学生交流,喜欢读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向我推荐的诗人。对我来说,致力于诗是我去学习新语言的一大动力,因为得掌握一门语言才能欣赏那一语言中诗的韵律、比喻、互文。但同时我也比较实用主义,人不可能懂所有语言,所以拥抱译本不可避免。理论家们常把诗歌看作不可译的。我偏爱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②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法国语言学家,女性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对“不可译”(untranslatable)的定义:“不可译,就是‘它不断在被翻译’的意思。”它强调了文学翻译行为的开放性和无休止,并赋予诗歌翻译长久的生命力——不是把译诗看作不可能,而是看作一件必须先让自己行动起来、参与其中的事情。
伯竑桥:在中文世界里,那些出身传统意义上的“好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文学教育的诗人,被称为“学院派”(College Genre),与之相对的是“民间派”(Folk Genre)③详见“1999年中国诗歌盘峰论争”事件始末。。它似乎就像华兹华斯与罗伯特·彭斯的微妙区别,同时指涉着现实世界里的社会阶层差异和文本世界中语言偏好的差异。这种情况下,年轻学院写作者们常常意识到,自己秉持的文学观,和大众所持的看法是相当不同的。所以他们总在两个极端上游走,要么彻底拒绝大众读者,要么调整自己的趣味和策略去亲近大众。就您的观察而言,这种现象在英语世界也存在吗?受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学院精英会否对诗歌有独立于普通读者的审美体系?
拉什沃思:这真是个相当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感觉和在学院里教西方正统文学史也有关。如今学生们经常通过民谣或者流行音乐来接触到诗歌,所以我常常乐意听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私藏的音乐,虽说,音乐并非我深耕的领域。往往是这样的:我领学生们体验中世纪意大利十四行诗,而他们带我听流行乐,然后我们看看是否会有什么化学反应产生。当代文学最好的一点是,它不分等级,没有严格的高下,也就是说它不会先入为主地替每个人判断什么是值得去了解并且学习的;这种语境下,如果一个人要写作,只需为自己写的东西找到理由就行了。当然,把目光放在特定作者群体上——比如你说的“学院派”诗歌或者我说的“学者诗歌”——它们的文本本身、它们的阐释批评,都更加成熟,所以也就更显见于世,更容易走进。
但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认为诗歌应该属于精英,哪怕是在带有精英色彩的顶尖大学里也如此。年轻诗人们常常由诗歌奖而被匿名评选出来,而不是看你拿的哪儿的学位。大学的文学教育,倒的确会加强你和诗的关联——比如英国当代诗人佩森斯·阿格芭比④佩森斯·阿格芭比(Patience Agbabi),英国女诗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其作品涉及种族、身份政治、跨文化、跨性别等多个议题,极具舞台感与公共性。(Patience Agbabi)就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她的写作为已成定式的生活经验带来了新的视角,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民间”和“学院”的分野。佩森斯是个表现力极强的诗人,她把乔叟诗歌改写为21世纪的新形式作品,这也意味着她正把自己所受的学院精英教育通过写作传递给更广阔的受众。
伯竑桥:相比起用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写作的其他地方诗人,其他西方诗人,中国诗人乃至作家整体,在英语世界都显得沉默。当老年歌德大谈未来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时,也有批评家指出,它的本质不过是“西方文学席卷世界”。那么,您认为汉语诗人和英语诗人们是否能够真正互相理解呢?怎么让中英诗歌的交流从英语诗歌的单向文化输出,转变为各自影响对方,从而避免落入爱德华·萨义德①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20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其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改变了战后文学研究的格局,促进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向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转型。所说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误区呢?
拉什沃思:出于某些原因,日本诗歌,比汉语诗歌更受西方世界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西方读者对俳句形式已生痴迷,毕竟俳句短暂而容易令人愉悦,且经常与人们认可的普遍主题有关,诸如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化、自然世界的美丽。同时,也和艺术领域大行其道的“和风”(法文为“ja⁃ponisme”②Japonisme,和风,日式风,19世纪中叶日本结束闭关锁国,其绘画与诗歌美学传播至欧陆后兴起的浪潮,对法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之造型艺术有过一定影响。)有关。考虑到中国诗歌的丰厚传统,中国诗歌在英国声名不显的情况,实在是广大英语读者的遗憾,就连我自己的诗歌课上也缺乏相关的内容。我做好了准备带领学生去探索一门新语言的诗歌世界,而当下,我们需要的是保持艺术性的同时,也易于让学生和教师进入那个世界的好译本。如果竑桥你看到优秀的译本,请随时向我推荐。